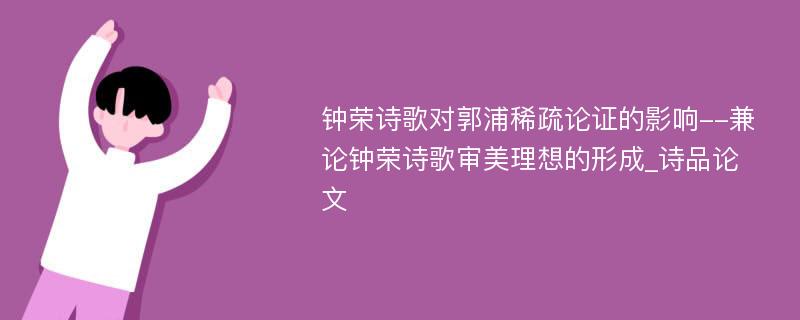
钟嵘《诗品》关于郭璞条疏证——兼论钟嵘诗歌审美理想之形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理想论文,诗品论文,钟嵘论文,兼论钟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钟嵘《诗品》中“晋弘农太守郭璞诗”评曰:“宪章潘岳,文体相晖,彪炳可玩。始变中原平淡之体,故称中兴第一。《翰林》以为诗首。但《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而云‘奈何虎豹姿’;又云‘戢翼栖榛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所谓“中兴”,指晋元帝司马睿在江东建立的“王与马共天下”的政治格局,史称东晋,他们君臣自比为周宣王“中兴”,但实际上只是艰难维持,在北方外族的进逼下,并无大的作为,仅能使晋室一线不致断绝而已。《文心雕龙·才略》篇就说:“景纯艳逸,足冠中兴”,其文学创作和“中兴”这一政治概念连接在一起,因此也必须与之相联系来加以理解。
一
对于这一时期文学发展情况,《世说·文学》第八十五条:“简文称许掾云:‘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刘孝标注引檀道鸾《续晋阳秋》曰:
询有才藻,善属文。自司马相如、王褒、扬雄诸贤世尚赋颂,皆体则《诗》、《骚》,傍综百家之言。及至建安,而诗章大盛。逮乎西朝之末,潘、陆之徒虽时有质文,而宗归不异也。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自此作者悉体之。至义熙中,谢混始改。
这里“妙绝时人”和“一时文宗”,以许、孙为冠冕,似乎与上述《诗品》以郭璞为“中兴第一”相牴,但实质上两者并不相干。檀氏只是从文学流变史角度,认为玄言诗兴起,许询和孙绰有开创之功;简文帝是玄谈家,自然对许询极为欣赏;而钟嵘《诗品》具有鲜明的诗歌审美理想,从其诗美尺度出发,他对玄言诗本无好感,郭璞虽与玄言有瓜葛,但是根本上与玄言相异趣,然则以当时玄风盛炽士人不撄世物之际,郭璞的特立独行犹如孤峰危峙,当推许为天下独步了。郭璞五言在时风众势中是不谐和音,何以引发钟嵘较高的评价,被置于中品,而许、孙享名不在郭璞之下,却只列在下品,观澜索源,将有裨于更深入理解《诗品》对历代诗人品评轩轾的美学思想。
《诗品上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词,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隽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逮义熙中,谢益寿斐然继作。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郭,凌轹潘、左。”这里要注意对永嘉之“黄老”的理解,学界一般把“黄老”看成庄老玄谈的同义语,其实钟嵘用“黄老”而非“庄老”,其遣词十分精确,后人因不知作为政治哲学的“黄老”为何物,就往往只看到“老”的一边,以偏概全,误解就由此产生。案“永嘉”为晋怀帝炽年号,永兴元年司马炽立为皇太弟,他以清河王司马覃本太子也,“惧不敢当”,典书令卢陵修肃为他分析进退利害,他才不再推辞,对修肃说:“卿,吾之宋昌也。”他出来做皇帝,自比为汉文帝当年由代王入主长安,他意识到此时身登九五之尊,和汉文帝的境遇十分相似。汉文帝受到军吏大臣、诸侯王及北方匈奴的牵制,《晋书·孝愍帝纪》说:“怀帝承乱得位,羁于强臣”,晋怀帝内为东海王司马越及首鼠两端的朝臣所左右,外受异族之刘元海、石勒辈的骚扰,还有乱民的暴动。在这种情势下,黄老作为政治策略,其出台实有必然的因缘。汉初文帝一朝最具有黄老政治特征,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常被假象所迷惑,认为文帝与民休养生息,所奉行的当然便是《老子》的无为学说。但《史记·礼书》说文帝好道家之学,而《史记·儒林列传》又说文帝好刑名家言,《汉书·张欧传》说:“欧孝文时以治刑名侍太子。”盖此时道家几以刑名家为主流,从《汉志》的道家类可得到佐证。《史记·外戚世家》说:“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长沙马王堆发掘到《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据唐兰先生考定此即列在《汉志》道家类的《黄帝四经》(注:唐兰《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研究》, 载《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其内容有浓郁的刑名家色彩,窦太后令晚辈所读的《黄帝》书,应与《黄帝四经》极为接近。这一切都说明汉初“黄老之术”是君臣较量并相互折中的产物,臣下高举《老》学以限制或消解君权的扩张和泛滥,而皇帝要建立集权,其真心所好乃以《黄帝》书为主旨的刑名家言,但是因为当时异己势力还很强大的缘故,文帝、窦太后不得不向《老》学做妥协,只能柔中克刚,虽外表为柔,但其骨子里却是刚,俟其子孙景、武帝时再改变这种隐忍的政治风格。
晋怀帝以汉文帝自况,说明他明确意识到:文帝式的黄老便是其选择的必由政治路线,他也要搞平衡,与非己从者虚与委蛇。如他与东海王越的离合关系,永嘉五年“诏下东海王越罪状,告方镇讨之”,《晋书》本纪称曰:“怀帝天姿清劭,少著英猷,若遭承平,足为守文佳主。”而所谓“守文佳主”,在历史上自然以汉文帝为第一典范,这也意指晋怀帝内心世界与汉文帝极为一致,他也同样是外柔内刚,只不过时势异矣,终遭杀害。然而可以极肯定地说,从政治角度看,“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在晋帝而言,所贵者主要是“黄”而非“老”,或内“黄”外“老”,《晋书·庾亮传》说:“中兴初,……时帝方任刑法,以《韩子》赐皇太子”,这说明渡江前后,晋帝之固守商韩法术始终不渝。上句“稍尚虚谈”,是指承正始余绪,王、何《老》学及向、郭《庄》学此时仍然由臣下在推波助澜,并且由于帝王尚刑名,更刺激了此风的滋长。但这与“黄老”峻切的一面恰好相反,这里“稍”字就有转折的意思,正表明钟嵘于黄老学术耳熟能详。《南史·钟嵘传》说:“时齐明帝躬亲细务,纲目亦密。于是郡县及六署九府常行职事,莫不争自启闻,取决诏敕。文武勋旧,皆不归选部。于是凭势互相通进,人君之务,粗为繁密。嵘乃上书言:‘古者明君揆才颁政,量能授职,三公坐而论道,九卿作而成务,天子可恭己南面而已。’”钟嵘上书同样阐发黄老之术,但其内容却是站在臣下立场要与君主分权。而曹旭《诗品集注》却以为:“《梁书》、《玉屑》、《集成》、《全梁文》本均无‘稍’字,车柱环《校证》:‘无“稍”字,文正相耦;征之下文,义亦较胜。今本“稍”字,疑后人所加。’路百占《校记》:‘有晋一代文人,大多崇尚虚谈,东渡江左,玄风弥烂,无“稍”字,是。’案:《竹庄》此句作‘贵黄老而尚虚玄’,亦无‘稍’字。”这里他们都认为“尚虚谈”是顺接前之“贵黄老”,则显然曲解了钟嵘本义,元延祐七年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山堂先生群书考索》本《诗品》,是迄今所见的最早版本,它有“稍”字是,后人妄改,都非的见。
郭璞与“尚玄谈”风习相左,其用世激情和对儒家经典的态度与钟嵘心有戚戚焉,才博得钟嵘的佳评。郭璞为河东闻喜人,察《魏志·杜畿传》,杜畿由荀彧举荐,建安中为河东太守,对河东学风影响深广,他有极强的实际才干,深得曹操信赖;其子杜恕嗣任于魏文、明帝朝,“时又大议考课之制,以考内外众官。恕以为用不尽其人,虽才且无益,所存非所务,所务非世要”。他上疏主张人、法并重,据此可见杜氏家学,他说:“唐、虞之君,委任稷、契、夔、龙而责成功,及其罪也,殛鲧而放四凶”,认为明主应明察臣下或“恪勤”或“尸禄”,其务实尚用与清谈玄远一派大相径庭,然他又批评“师商、韩而上法术”,从荀子后裔荀彧对杜氏的极力推崇来看,杜氏父子学术思想仿佛《荀》学的礼、法并用,避免商、韩犬羊治人的惨礉少恩,尤其主张人尽其用,则与商韩君主独裁专断的集权政治思想有明显差别,犹如《荀子》在讲《君道》的同时,也不废《臣道》。河东闻喜人裴松之注《魏志·杜畿传》引《魏略》说建安以来由于杜畿和乐详的提倡,“于是河东学业大兴”,正始中乐详门徒至数千人,河东一时成为儒学渊薮:并且才士辈出,大抵均有建安士人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气概,和唐长孺所考定流行于“大河以南”的玄学之风尚不同(注:唐长孺《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见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 三联书店1955年版。)。流风所及,后之郭璞想也受其沾溉。 《晋书》本传说“于时阴阳错缪,而刑狱繁兴”,郭璞上疏,可以视为对于永嘉以来“贵黄老”的回应,他指出“中兴”徒属空言,过错并不在“黄老”,而是为治者太强调刑名,他说:“夫以区区之曹参,犹能遵盖公之一言,倚清靖以镇俗,寄市狱以容非,德音不忘,流咏于今。汉之中宗,聪悟独断,可谓令主,然厉意刑名,用亏纯德。《老子》以礼为忠信之薄,况刑又是礼之糟粕者乎!”郭璞的黄老主张,以汉代为参照,赞美文帝之治,鄙薄宣帝“中兴”,一言以蔽之,乃以《老》学抵制《黄》学刑名家的严刑峻法,校正君主权力垄断格局,钟嵘上述见解与他完全一致。在此前提下积极进取,走向其理想中的中兴。他也是站在臣民立场上的黄老思想,具有黄老家“尽天极”、“用天当”的入世精神,不能忘情现实人生,也与纯《老》学的因顺无为迥然有别。《晋书》本传称“璞好经术”,但其学养极其驳杂,如其《易》学,“又抄京、费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卜韵》一篇”,他融合今、古文经学,特别应注意本传说他精通卜筮“虽京房、管辂不能过也”,而《魏志·方技传》叙述管辂行状,注引《辂别传》说管辂与人谈论阴阳五行时“少引圣籍,多发天然”,自出机杼,跨略陈说,则置经学师法家法于不顾,且郭璞具有东方朔式“秽德似隐”的人格特点,因此郭璞对于儒家经典的态度应与管辂十分相似。
然郭璞身上洋溢着阴阳神仙家气息,虽也受玄风洗礼,其为学还是逡巡在天人感应与自然论之间,他不是彻底的新起玄学的预流者。
二
钟嵘反对文学的玄言风气,也自有其思想的渊源。《南史》本传说钟嵘是颍川长社人,是晋侍中钟雅七世孙,《世说·政事》刘孝标注引《钟雅别传》说:“雅字彦胄,颍川长社人,魏太傅钟繇仲弟曾孙也。”虽钟嵘出于钟繇弟钟演一系,钟演声名远不及钟繇,但是,钟嵘先祖中出了钟繇这么一位一代伟人,必然会对其心灵产生强烈的震动,钟繇的功业学术、性情趣味均会对钟氏后人有深刻的影响。钟嵘的诗美理想也应从其颍川先祖身上沿波讨源。《魏志·三少帝纪》:“(正始五年)冬十一月癸卯,诏祀故尚书令荀攸于太祖庙庭。”裴注曰:“臣松之以为故魏氏配飨不及荀彧,盖以其末年异议,又位非魏臣故也。至于升程昱而遗郭嘉,先钟繇而后荀攸,则未详厥趣也。”钟繇勋绩,彪炳曹魏,先祖金戈铁马的建安时代,必然是令钟嵘缅怀不已的英雄岁月。
曹操父子在政治军事方面对钟繇等颍川士人非常倚重,《魏志·郭嘉传》说:“先是时,颍川戏志才,筹画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与荀彧书曰:‘自志才亡后,莫可与计事者。汝、颍固多奇士,谁可以继之?’彧荐嘉。召见,论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曹操明确邀进汝、颍士子,其心腹如荀彧、钟繇、荀攸、戏志才、郭嘉等都是颍川所产,这说明该地域士人特点投合了曹氏的政治需要。《汉书·地理志》说:“颍川,韩都,士有申子、韩非刻害余烈。”所谓“刻害余烈”,在认识论上主要体现为自然论,与天人共感相对立。除了才学之外,荀彧祖父荀淑,据《后汉书》本传,说他是“荀卿十一世孙也”,他们共同具有的自然论思想,祖述《荀子·天论》的天人相分的观点,可釜底抽薪般地摧毁汉儒崇奉的天人感应观,消除汉刘天授神与的神话,从而达到代汉的目的。《魏志·钟繇传》说:“太祖既数听荀彧之称繇。”所以钟繇学术、思想与荀氏应较接近,察荀彧言论,确实是荀子嫡裔。
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藐视天命,强调有为进取。《魏志·钟繇传》载钟繇议复肉刑,魏明帝诏曰:“太傅学优才高,留心政事,又于刑理深远。”注引《魏书》称赞钟繇“由于、张之在汉也”;又《魏志·钟会传》说:“及会死后,于会家得书二十篇,名曰《道论》,而实刑名家也。其文似会。”这都可以佐证,钟氏是上述颍川地域士人风习的典型代表,是战国以降三晋法家的薪火传人。而三晋法家与齐法家的根本区别,似可视作《荀子》(荀卿是游齐的赵人)和《管子》的差异,突出体现在前者主张天人相分;而后者则讲天人共感,经学的齐学一派在此点上与《管子》是相通的。既然天命、自然俱不足畏,那么人的意志就可以凌驾一切,这在思想上既可衍生出自强不息锐意进取的崇高人格,同样也可滋生小人无忌惮者的为所欲为。大凡政治尚可作为,颍川士子便以前仆后继舍身扶持者居多,一旦大树已倾,则无行者泛滥。其次,极其关注现实功用,则会置儒家经典于“六经注我”的位置。消灭天地自然人格神,也必然推倒五经的神性偶像。比如《荀子》还要树立思想宗主,提倡宗经,但是到其门下韩非、李斯变本加厉,则走向了焚书坑儒。一方面,这是因为《荀子》的“礼”已经透露“法”的意思;另一方面,他们是由自然论为通贯的,没有天命约束的现实功用论者,其思维方式不是去就范遵循已有规则观念,而是蔑视陈规旧习,以驱世从己,往往非但摧毁别人,甚至会否定自家作为一派的存在,过度的现实态度,会迈向目空一切思想宗主,《韩非子·五蠹》便是显例。虽然自魏晋到齐梁时隔久远,但是,一则发轫与曹魏邺许的魏晋玄学一直余势不减,辐射到南朝齐梁时期,江左名士对于正始玄学心仪不已,才有后来的玄释交融;二则建安年间群雄纷争,英雄人物在政治军事上的辉煌表演,令南朝士人心驰神往;同时风流人物在文坛上各握灵蛇之珠,三曹和七子更是树立了不可企及的范本,如谢灵运、沈约、刘勰辈谈论诗歌,无不以曹、刘等人为翘楚。因此魏晋学术和文学,不但没有随时间而被淡忘,相反这个英雄和名士如群星璀璨的时代,一次次在后人记忆里被唤醒,那一时代的人文精神包括其哲学思辩诗文佳作更凸现在人们心目之中。钟嵘是曹魏元勋钟繇的后人,他对这一时代必然情有独钟,于其钟氏先辈学术思想有更多继承,这是十分自然的。察《南史》本传及其《诗品》,在齐梁释氏大兴之际,钟嵘似与之丝毫无染,能够拔出于时尚,这都令人相信钟嵘于其先辈学术会有较完整的承袭。而南朝“神灭论”一派,其思想根源还是春秋战国以来的自然论,钟嵘的超然或与其一门自然论传统有关。上述钟氏学术特点,在钟嵘身上均有鲜明的体现,而这种学术特点转化为其审美理想,自有其逻辑的脉络,是有迹可寻的。
《诗品序》:“序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诗歌之兴,缘于物感,这是秉承《礼记·乐记》和《毛诗序》等说法,然与跼蹐于天人感应者相比,如陆机等很讲物感,人只是被动地感应于芳春劲秋,这里钟嵘就与之有非常大的差别,人虽受自然万物的感发,但是《荀子·王制》篇:“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人于三才,是人的存在,方使天地自然有生气有意义,人是第一位的。曹操《度关山》曰:“天地间,人为贵。”因此在天人关系上,认为诗歌可以“欲以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突出人的性灵情感使天地生辉,并且诗歌有“动天地,感鬼神”的巨大力量,则显然把汉儒主要是齐学一派天地人的关系颠倒过来了,是人情之所至,令天地鬼神受到震动,完全与汉儒式的物感观相反。因此,在心物关系上,钟嵘与三晋《荀》学一系是一致的。《诗品序》又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四候感诗,只是诗兴缘起的一个方面,自然相对于人类社会而言,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毕竟平淡孤寂,远不及社会生活的丰富多彩剧烈动荡,钟嵘认为诗歌更应侧重描述社会人生的种种情态,特别是灵魂置于拷问台上(鲁迅语)的众生相,作者谓之非诗歌不足展义骋情,这样的作品纯粹是人生血泪的结晶。然则人的情绪可以纵意摅写,丝毫不必考虑情感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并且须受礼义的节制,他引“《诗》可以群,可以怨”,“群”只是引起读者的共鸣之谓也,而“怨”在钟嵘看来,诗“怨”才能最大限度地沟通作者和读者的心理交流,正是五言诗诗美特质之所在,钟嵘只关注诗歌“感荡心灵”的心理势能的积聚,他与丹纳《艺术哲学》一样,发抉出“怨”在诗歌中具有感动人心的不可替代的功效,就对汉儒诗教产生了全方位的突破。而尊重人类情感,置之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发抉人类情感中并非温柔敦厚而是惨烈震荡之美;关注社会生活胜过欣赏自然山水。这一切都立基于三晋一系的自然论思想。因为彻底的自然论者,尤其是具有三晋刑名家色彩者,人的意志力可不受滞碍地张扬,礼岂为我辈而设,情感奔放,如飞瀑直泻,则无须受礼义和理智的辖制;或者驾御自然,或者看破天命,自然在其眼里不存在神秘的魅力,难以与自然产生亲和感,自然就不会成为其审美观照的对象。唯有“人为”——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历史演进、荣悴跌宕的人生遭际、缠绵悱恻恩恩怨怨的情感纠葛——才能够引发他足够的兴趣和激情,《诗品序》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五言诗适合于反映社会生活,能把诗歌从庙堂山林引向凡俗人世,表达人间真情实感,所以钟嵘认为是最切合人情的。在月旦郭璞和许、孙等玄言诗人时,钟嵘完全受到此种潜在意识的影响。
上已述及,郭璞的学养和所处地域环境,使他具有入世和干预现实政治的品格,这点在其上疏之中已经有所表现。而他的诗作与其此种品格是完全吻合的,钟嵘清楚地察觉到这一点。即使写《游仙诗》也主要寄寓了对纷乱现实的忧患,心系天下,忧心忡忡。《晋书·谢安传》说谢安“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桑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无处世意”。《晋书·王羲之传》说:“时刘惔为丹杨尹,许询尝就惔宿,床帷新丽,饮食丰甘。询曰:‘若此保全,殊胜东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许遇稷契,当无此言。’二人并有愧色。”足见其鹜求庸俗内心空虚。《晋书·刘惔传》载孙绰为刘惔诔云:“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其《三月三日兰亭诗序》说:“于是和以醇醪,齐以达观,决然兀矣,焉复觉鹏鷃之二物哉。”虽此辈有时也思念故园沦丧,但他们最终还是借助老庄和佛教,浇释块垒,平复隐痛。偏安江左,无所作为。在其诗文中,“世称孙、许,弥善恬淡之词”,大多以远离尘嚣的灵山仙境来掩盖现实的纷乱,回避现实矛盾,均与钟嵘所仰慕的建安英雄气概风马牛不相及。
南渡之后,士人对玄学时有反思,《世说·言语》第三十条注引汝南贲泰赞赏周顗曰:“汝、颍故多贤士,自顷陵迟,雅道殆衰。今复见周伯仁,伯仁将祛旧风,清我邦族矣!”从党锢人物到邺许谋士到正始名士以至林下贤士,身居南土,故国北望,汝颍士人悔悟清谈误国,此时颇有人又朝着儒家入世务实方向回归。钟嵘推崇建安风力,批评虚谈玄言,激赏情感浓烈,鄙薄寡味平典,都可视为此种思潮的响应者。那么他以郭璞高出许、孙,就是其必然的品第。
钟嵘诗美理想的另一重要内容,提倡“直寻”反对过分用典,也与其上述学养渊源有着直接关系。《诗品中序》说:“夫属词比事,乃为通谈,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台多悲风’,亦唯所见;‘清晨登陇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讨论用典适当的范围,认为朝廷之上的应用文,可引经据典,以显端雅;而诗歌是抒发个人性情之事,微妙飘忽,难以言传,则繁密用事,犹如“拘挛补衲”,有害性情的自然天成,有害真美。这里钟嵘把驳议奏铭之类应用文体和诗歌创作,看作不同的两个层次。诗歌至美上接“性与天道”,读《魏志·方技传》注引《辂别传》管辂说:“苟非性与天道,何由背爻象而任胸心者乎?”这句话作逆向的推理,则“性与天道”,非爻象之类可窥测,非陈陈相因的语词能尽其意,上已引及《辂别传》叙述单子春者与管辂论学:
辂言:“始读《诗》、《论》、《易本》,学问微浅,未能上引圣人之道,陈秦汉之事,但欲论金木水火土鬼神之情耳。”子春曰:“此最难者,而卿以为易邪?”于是唱大论之端,遂经于阴阳,文采葩流,枝叶横生,少引圣籍,多发天然。……管辂故作谦词,《诗》、《论》等均属浅显,葛洪《抱朴子内篇·释滞》篇:“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阴阳恍惚、精微高妙,才显学通天人,非俗流堪比肩。而臻此境界,却须刊落理障,进入“少引圣籍,多发天然”的语境。钟繇长子钟毓曾与管辂论《易》,魏晋以降士人《易》与《老》《庄》同参,言意之辩,把意之精和意之粗分为两个层次,则更把尺尺寸寸拘守儒家五经者,视为庸人俗学,曹植《赠丁翼》说:“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魏晋以来儒学也受玄学渗透,钟嵘虽身具鲜明的儒家品格,但他也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玄学思维的影响。《南史》本传称钟嵘“明《周易》”,《易》学是钟氏家学,前辈肇端乎《易》学的对于“五经”的态度,他必定有所继承,《诗品》上评阮籍《咏怀》诗曰:“可以陶性灵,发幽思。”诗美之极致,属于性灵幽思范畴,如电花石火,如惊鸿一瞥,似灵光初照,重在妙悟与独创,所以“讵出经史”、“皆由直寻”,钟嵘反对旁征博引,乃与管辂式的“少引圣籍,多发天然”,极具内在的一致性。
然而钟嵘反对诗歌用典,并非意味着割裂传统,如他所品第的诗人,推流溯源,都可归根于《诗经》和《楚辞》,使诗歌精神有最后的传统依归,而这样对于传统的态度,是在一个更高层次上的继承,完全脱略了形迹,与专事用典模拟者有着截然的不同。
三
如上分析,郭璞玄言形式下具有强烈现实入世激情的五言诗,作为独特的诗歌形态,进入钟嵘诗学审美结构,对之进行定位评估,便完全植根于钟嵘理路清晰的审美“准的”。一方面对钟嵘此种品第标准的铸成,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另一方面,在其观照下,历代诗人如何在其审美网络中占据一席之地,尝一脔而知全镬,也会更有理性的认识。
《诗品》中感觉到郭璞诗透射出一股勃郁之气,“始变中原平淡之体”,扼腕于建安风力之莫传,《诗品上序》说建安以下“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五言诗的盛衰,完全以建安风骨为参照,盛,乃是建安气象的重现,衰,则是与之相背离。西晋已有一次“中兴”,但随之趋于平淡。至郭璞出来,才又看到一线回归建安的转机,故而“中兴第一”,“中兴”用于政治上有嫌含混其词,移用于诗歌由空洞平淡,转而为充实清刚,这倒显得稍为贴切。钟嵘诗美理想寄寓于建安风力特别是曹植身上,将曹植诗歌赞美至“譬人伦之有周、孔”这样的高度,认为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曹植诗既怨且雅,文质相济,“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既有怨的动人心魄的内涵,而其怨又非声嘶力竭式的,有雅正的雍容气度,达到骨气与词彩的完美统一。
在如此高度下来衡量郭璞五言诗,钟嵘指出:“但《游仙》之作,辞多慷慨,乖远玄宗,……乃是坎壈咏怀,非列仙之趣也。”《隋志》说:“晋弘农太守郭璞集十七卷,梁十卷,录一卷。”其文集大多散佚,只剩近三十首诗,聊备管中窥豹,仅举其《游仙诗》为例,其中有云:“云盖随风回,手顿羲和辔。足蹈阊阖开,东海犹蹄涔。昆仑蝼蚁堆,遐邈冥茫中,俯视令人哀。”何焯评曰:“景纯之《游仙》即屈子之《远游》也。章句之士,何足以知之。”(何焯《义门读书记》第四十六卷)何焯的评价十分精当,《远游》是否屈原所作,姑且不论,他主要是从《远游》之“涉青云以泛滥游兮,忽临睨乎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来讲,这样的意思是切合郭璞《游仙》旨趣的,可以看作对郭璞《游仙》比较准确的概括,郭璞以真挚深沉的悲悯,关怀着人间的苦难,虽然《离骚》里也有近似的句子,但说郭璞祖述《离骚》,却有嫌拔高而不妥。郭璞与玄言诗人的漠视现实不同,所以他“乖远玄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揭示建安时期五言诗风貌曰:“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在钟嵘眼里,“辞多慷慨”,正可视为郭璞远嗣建安风神,使建安文学再现重振的曙光,“中兴”之评语也缘此而发。然而在表现形式上,前之《诗》、《骚》就代表着北、南两种地域文化,有较大的差异。《文心雕龙·辨骚》篇,虽高置屈《骚》于几与“五经”并肩的地位,但还是以《楚辞》夸诞的成分为“异乎经典者也”,所以说《楚辞》比之《诗》有欠雅正的一面,其地位只能是“经”之流亚。至迟到东汉王逸就已有了这种看法,沈约、刘勰、钟嵘等对此都有所认同。因钟嵘说郭璞“宪章潘岳”,而潘岳“其源出于仲宣”,又王粲“其源出于李陵”,李陵又“源出于《楚辞》”,追根究底,郭璞本源出于《楚辞》一系。此辈中李陵失节匈奴,“仲宣轻脆以躁竞”、“潘岳诡诪于愍怀”(《文心雕龙·程器》篇),而郭璞亦庄亦谐,俗念满腹,其人格、行事或有所瑕累,都与雅正尚有距离,所以钟嵘将他们一并归诸《楚辞》之流裔。郭璞远绍建安文学慷慨的特点,但是在曹植楷模面前,只是偏胜之才,够不上完美,列在中品,也是势所必然。
前引檀道鸾和钟嵘的文学史见解本就不同,前面已经有所论及。如何看待郭璞和玄言诗的关系,至今意见不一。判断相左的症结在于诗歌辨体的角度,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檀道鸾说:“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过江前主要由王、何正始之音独擅胜场,过江之后,佛教大兴,这里的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并不是说郭璞融会玄释,郭璞只是一个有学有术者,东晋时期,士人为学多端,如葛洪其人,就很难称他为哪一家,而一般杂家,就习惯归入道家类。他的五言诗杂糅了非常多的阴阳神仙家的语词,但仍然止限于中土范围,来表达他的思想情感,“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虽易于造成误解,但本意确乎如此。在诗体发展史上,檀氏认为郭璞是创格;而许、孙在他基础上,又引入了佛理和佛教语词,更加偏离了《诗》《骚》传统,在许、孙玄言诗形成过程中,从艺术形式来讲,郭璞是重要的一环,发挥了重要影响,这无疑是客观中肯的看法。而钟嵘则认为玄言诗之为体,应着重在内容上进行辨体,玄言诗应主要表达玄学的哲理思辨,较少人间的烟火气,平典似《道德论》,而郭璞五言,貌似逍遥游,而神系人间世,所以看出了其“乖远玄宗”,认为他和刘琨一起是反玄言诗风的健将。
在中国诗歌史上,像郭璞这样“正言若反”的诗人,可能郭璞并不是第一人,比如阮籍《咏怀》诗,就与之颇有几分相近。但阮籍是建安七子之一的阮瑀之子,于建安精神有最直接的继承,他是魏晋玄学第一线预流者,是最彻底的自然论者,《晋书·孝愍帝纪》说:“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也。”时昏道丧,无以济世,才使阮籍辈以乖异乎寻常的姿态来发泄其苦闷,是司马氏政权的强压使建安精神以变态的形式表现出来。故而钟嵘将阮籍《咏怀》诗置于上品,溯其源至于《小雅》,盖属建安先辈的“变雅”。因此,郭璞于阮籍既有所同,又有所不及。可见,钟嵘的品第并不随意,是有根有据十分审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