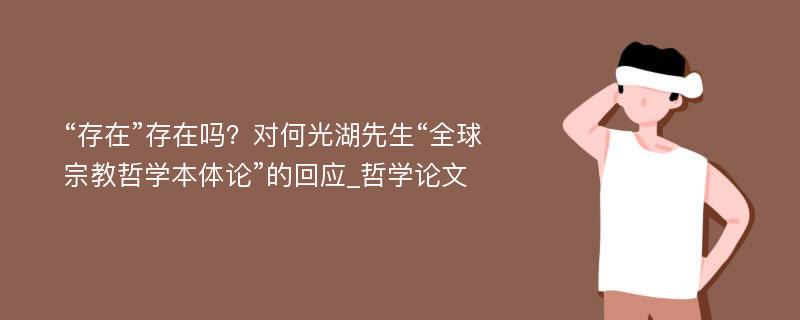
“存在”存在吗?——回应何光沪先生的“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宗教论文,哲学论文,全球论文,何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何光沪先生在《浙江学刊》2003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使在”、“内在”与“超在”——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的文章,所关注的问题正与我在做的博士论文相关,又恰好与我自己在同期发表的论文放在同一栏目, 自然引起了我的注意和兴趣。在何先生的慷慨赞许下,我也就顾不上自身学养浅薄,想从自己在研究的当代思想家雷蒙·潘尼卡(Raimon Panikkar)的一些洞见出发,就“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这一问题谈点不同看法,作为对何先生的一个回应。
何先生思考并尝试建构全球宗教哲学事实上由来已久,其中包含了他作为一位有良知、有思考的知识分子对全球和平与人性健康的深沉关切。(注:参看何光沪:《何光沪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尤其其中的“百川归海——走向全球宗教哲学(引言,第一章,第二章)”。)何先生在上述文章中表达了他新近建构的“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即“把哲学本体论的根本范畴即‘存在’,界定为‘使在’(使世界存在)、‘内在’(内在于世界)和‘超在’(超越于世界)的‘真正的神秘’,即无形无相又难以描述、看似‘空、无、非’实为‘实、有、是’的世界本源”。(注:何光沪:《“使在”、“内在”与“超在”——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浙江学刊》2003年第4期,第43页。)他在文中从中国的儒、释、道及三大亚伯拉罕传统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援引了大量理论表达,以支持他的这一界说,表明他所建构的这一全球宗教哲学本体论的普遍根据。
何先生的这一“使在—内在—超在”的世界本源界说确实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似乎可以在人类的许多宗教传统中得到印证,使人相信人类的诸传统在根本上是相通的。但我心中有多个疑问,比如这一本体论与世界各个宗教中的“本体论”究竟是什么关系?它归纳、整合或抽象了后者?它能否或能在多大程度上为后者所认同?如果说,它作为一个通约的中介,目的在于使诸宗教变得相通,那么倘若它作为通约的中介尚有待诸宗教的认可,也即在它与诸宗教之间还需要另一个中介,它作为通约中介的作用是否就被无限后推了呢?另外,说到通约,我们要问,可供通约的基础或根据是什么?是理性,或者确切说是一种唯一的可理解性?这些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在构造一种寻求普遍性的理论之前似乎不能不考虑。但在这里,我想仅就“全球宗教哲学本体论”的内容本身与何先生商榷,以下是我要冒昧提出的三个问题:
一、所谓本体究竟是“存在”,还是“非存在”?
二、存在或上帝(注:我认为在何先生那里,作为哲学范畴的“存在”与作为神学范畴的“上帝”几乎同义。)是实体,还是象征?
三、“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如何面对无神论的挑战和诸宗教本身的突变?
我已把本文的题目定为“‘存在’存在吗?”,我要表达的意思是:“存在”这一范畴本身需要反思;它所指称的“东西”存在吗?或者问,在什么意义上存在?以上列出的三点都是围绕这个意思来展开的。
先来谈第一点:本体究竟是“存在”,还是“非存在”?与迄今为止的大多数哲学家一样,何先生把“存在”作为思考世界及其所谓本源的基本范畴。虽然他说“存在”兼备“空、无、非”和“实、有、是”这两重悖论性特征,但我觉得他几乎完全偏重于“实、有、是”,而对“空、无、非”语焉不详,甚至把“空、无、非”最终归为“实、有、是”,这从他说世界本源看似“空、无、非”而实为“实、有、是”就可见他的“偏心”。由此,在这里我想从潘尼卡的洞见出发指出“存在”这一范畴所面临的挑战和固有的难题,并提出以“非存在”来思考实在的可能性。
“存在”的难题与“上帝”的难题连在一起。因为,作为世界本源的“存在”,从它一开始在人类的哲学头脑中冒出来,就与宗教的“上帝”难解难分。作为世界本源的“存在”,我们不能不将之神圣化。对于我们和世界从中来、又将回归到它那里、目前又内在于我们和世界的东西,我们如何可能不心存敬畏,甚至敬拜呢?潘尼卡已将这一现象称为“存在神化”。当然,反过来,宗教的“上帝”也不能不被赋予本体意味,一个至高的存在者,绝对者,如果不是内在而超越地支撑我们和世界的本体,那么它也难以维持它作为绝对者的地位。这就是潘尼卡所称的“神本体化”。两方面合在一起,就是存在与上帝的同一化。但存在与上帝之间又始终有一种微妙的张力:存在既需要被神圣化,又想摆脱像上帝那样被拟人化的结局,而上帝既需要本体化,又不想沾染本体论哲学的冷漠和中立。
何先生以“使在—内在—超在”的“存在”界说致力于东西方宗教哲学的相通时,似乎有意无意地作了一种调和,强化了中国诸宗教哲学中原本较淡的“存在神化”的倾向和亚伯拉罕传统诸宗教哲学中相对较弱的“神本体化”的倾向,使它们在作为“使在—内在—超在”的“真正的神秘”中相遇相通。何先生把“存在”和“真正的神秘”并用指称世界本源很有意思,“存在”是一哲学范畴,而“真正的神秘”却有浓厚的神学意味。
就像潘尼卡在西方思想史上看到的,人们似乎一直在“存在神化”和“神本体化”之间选择,本体论和神学不可避免地发生重合。然而到了我们目前这个时代,人们尤其是西方人多少个世纪以来为之努力的上帝与存在的同一化明显受到了质疑:从存在方面来说,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存在”的最完整意思是本质,也即支撑万物也支撑自身的东西,它比它所支撑的万物更真实,被认为真实的上帝不可避免地视为与存在同一,是最高的存在。但在今天的哲学中,本质主义的思想不再像从前那样占主导地位而确定无疑,本质失去了它特殊的本体地位。从上帝方面来说,经历了拟人论、拟本体论(ontomorphism)和人格论这几个阶段,仍然难以弥合宗教的上帝与哲学的存在之间的裂缝以及难以避免上帝拟人化的结局。这两方面的难题在何先生那里也可以看到:由于他的分析直接建立在诸宗教传统的描述的基础上,“存在”在中国的儒、释、道那里有明显的本质主义痕迹,在亚伯拉罕传统那里则有拟人化的倾向,而“存在”的本质化和拟人化都已经不能为我们当代人所接受了。
潘尼卡指出,难题的根源在于,“存在神化”和“神本体化”这两个解决办法都预设上帝和存在是我们理解实在的两个杠杆支点。除了上帝和存在,有没有别的更合适的范畴可以用来理解实在?潘尼卡注意到,在对实在的理解上,佛教传统与和它在轴心时代一道兴起的其他智慧传统不同,它的创始人佛陀也许会告诉我们,这两者都必须摧毁:“没有”存在,也“没有”上帝。从正面来表述则是:所存在的一切,包括我们所能知觉到的和所能意识到的,一切的一切,都是因缘缘起,都处在相对性之中。当我们说有存在、有上帝时,我们实际上立即把存在、上帝放在了诸存在物的行列,因为我们所说的甚至所能想像的“有”都是相对性中的“有”,不可能是绝对的“有”——绝对意味着没有关联,而这在我们这个充满关联的世界是不可能的。说有绝对的“有”,等于自相矛盾,因为当我们说“有”的时候,那绝对的“有”就立即因为沾染上我们的相对性而被摧毁了。所以,即便我们确信“有”存在或上帝,并以一种我们无法想象的、神秘的方式“存在”,我们也最好不要说出口,而只是在沉默中表达我们的信心,不去操心存在或上帝,因为,存在或上帝既然是作为终极者和绝对者,它自会自己照管自己,不依赖于我们的认识和关切。但佛陀连这样一种确信、假定或想像都不要,他宁可完全保持沉默。
在佛陀那里,用悖论性的话说,作为存在物之源的“存在”或“上帝”不是“存在”,而是“非存在”。非存在不是存在的对立者,不等于存在的否定,因为否定已属于存在。正是在这里,我要顺便指出,我认为何先生把“空、无、非”看成了存在的否定,而不是相对于存在而自成一类的“非存在”。他在另一篇相关的论文《“实有是”与“空无非”——中国宗教哲学与基督教哲学相通的一大障碍?》(注:载于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网站,网址:http://www.daofeng.net/art:cledisp.asp?ID=33。)中讲到中国宗教的“空无非”时,认为它们主要是用于描述包括主体和客体的世界本身,而不是用于描述世界本源,即令在某些情况下用于描述后者,“也并不是在绝对虚无的意义上使用”。他坚持,世界本源最终是“实有是”,说它“空无非”是指它所含的“对事物和世界的最高否定性”,是指它“无形无象、不可言说”。这样的理解从传统来看固然没有不对,但恐怕没有说出“空无非”的更深意思:作为“非存在”。什么是“非存在”?如何理解“非存在”?当我们尝试以非同一性而不是同一性来理解事物时,我们就可以理解“非存在”。我们习惯于以同一性理解事物,所以会说此物存在彼物存在。发现并强调事物的非同一性,是佛教传统的独特贡献。事物的同一性实际上是以非同一性为基础的,一个事物,正因为它不断地“不是”它自身,它才得以“是”。所以我们更可以倒过来说:事物看似“实有是”,实为“空无非”。非存在不是存在的否定,倒是存在的行动。何先生已把存在的属性之一界定为“使在”,但我们同样可以以“使不在”来描述之,或许甚至更确切!因为正是在“使不在”中,本源既使世界存在,又内在于世界的存在行动,又超越世界,如此,本源与世界既不二分也不混同。本源不断地使世界不在而显示了它的在,这比说它使世界在而显示其临在更恰当,因为本源的在与世界的在绝不相同,而后一种说法或者会使人混淆这两种“在”,或者会导致“无限的中介难题”,即如何沟通本源的“在”和世界的“在”,由于本源的在是超然的,而世界的在是相对的,无论由哪一方的在来沟通都无法消弥两者的鸿沟。
“非存在”这一范畴的出场,可以使我们走出存在本质化和拟人化的陷阱,避开“存在神化”和“神本体化”的两难选择,因为我们会发现那样的陷阱和两难是虚假的: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把“非存在”本质化和拟人化。
这里马上会产生另一个问题:当我们以“非存在”取代“存在”和“上帝”时,存在和上帝是否就变得多余了呢?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从此把人类诸传统中有关存在或上帝的种种言说统统撇开呢?我的回答是,不是变得多余了,也不是可以完全撇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对它们有新的理解,核心的一点是:它们不是实体,而是象征!
在言说上帝或存在时,我们有一个预设,就是上帝或存在“存在”。问“存在存在吗”,或甚至“上帝存在吗”,都简直是同义反复。就像安瑟伦的本体论论证所说的那样,上帝之为上帝,存在是其依定义就有的属性。其实进一步来说,何先生提出的存在作为“使在”、“内在”与“超在”都是从“存在”这一范畴的内涵中挖出来的,是经演绎而来的,本来就是题中之义。何先生对此看来是有所意识的,他在说到“存在即使在”时说:“‘世界本源是使在’这一命题的正当性,可以说就在这个定义本身之中……”但这样的同义反复是有意义的,因为“它也是对‘存在’这一概念的动态的深化”。(注:何光沪:《“使在”、“内在”与“超在”——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浙江学刊》2003年第4期,第45页。)在这里关键的一点出来了:看来我们对“存在”的无数言说和思考都不过是对“存在”这一概念本身的挖掘、深化,而这完全可以脱离“存在”的实际所指来进行!我知道王志成教授在从后现代哲学的角度回应何先生时会问:这说明到底是经验优先还是语言优先,我们是在揭示真理还是在艺术创造?我想他在问这些问题时会把我也想说的意思表达得很清楚,无需我多说。我在这里想要问的是:存在或上帝是一个实体还是一个象征?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实体论或者说本质主义的难题:一个自称是万物之基础的本质或实体,实际上已把自身放在万物之中而摧毁了自身,作为众存在物之一的所谓本质或实体不可能是众存在物的本源和基础,因为它自身的源泉都是成问题的。所以我要提出,存在或上帝不能再作为实体来看,而应视为象征。
但应该马上指出的是,这象征不是对某个“东西”的象征,那样的话那个“东西”成了实体,用潘尼卡喜欢的话说,这象征是对一个宇宙—神—人共融的(cosmotheandric)实在的象征。一个实在不是一个东西,而是由种种关联构成的复合体。我们处在其中的整个实在,有宇宙的维度(圣灵,世界性、世俗性)、神的维度(圣父,超越性、不可穷尽性)和人的维度(圣子,意识性、精神性),与何先生的“使在—内在—超在”联系起来可以说,宇宙的维度与“内在”对应,神的维度与“超在”对应,人的维度与“使在”对应。存在或上帝已经在人类的诸传统成为一个词,一个象征,它不只是一个概念,对应于一个所指的客观对象,而是一个象征,汇聚和含摄了实在的各个维度及其相互作用。所以毫不奇怪,道、法、天、耶和华、(基督教的)上帝、安拉的主要任务在于指导我们生活,教导我们如何在世界中处身,而不是像一千纯粹的哲学概念那样仅仅充当一个符号指向一个所指。
下面我们要说到第三个问题:“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如何面对无神论的挑战和诸宗教本身的突变?
我觉得,何先生的“全球宗教哲学本体论”有重要的一点不能令人满意,那就是它没有对在当代世界如此盛行的无神论作出积极的回应,对面临种种挑战以致处在突变的边缘的传统诸宗教仅仅限于一种现象学式的分析和描述。众所周知,无神论拒斥任何形而上学,否定可为我们的感官所证实的东西之外的任何实在,上帝作为这样一种实在也因此被否定。在潘尼卡看来,上帝与其说像尼采所说的被人杀死了,不如说是因为内在的耗竭,因为上帝所依赖的基础——存在被取消了。潘尼卡认为无神论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在这世界上确实“没有”像上帝这样的东西。但他认为无神论尚不够彻底,在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之后又确立起了属人层面的超越者,如理性、人性、社会等,它实际上没有杀死上帝而是让人吞并了上帝,由人来接管上帝在尘世生存方面的职能。这种无神论可以沿着它的线路走得更远,直至与佛陀的沉默会聚,最终接受完全的偶然性,意识到:没“有”上帝,最终是因为也没“有”人。
无神论与有神论是当代人在信仰上的两难。传统有神论的全面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无神论由于封闭在人的自足之中而造成的诸多灾难和危机也是有目共睹,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是回到传统有神论还是在现代无神论的路上走到底,都是不可取的和难以令人信服的。可以看出,何先生对无神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缺陷有很深切的体会,并希望以宗教的超越来克服之,他在他的《自选集》中说:“……哲学性的思考如果仍然仅仅‘以人为本’而不思向外超越,很可能会助长人本来已有的自我中心甚至狂妄自大,从而增加错误选择的可能。”(注:何光沪:《何光沪自选集》,第3页。)但我们认为,诸宗教所面临的挑战同样不可忽视。在现代世俗—多元社会的背景下,由于面临来自世俗主义的挑战也面临来自其他宗教的挑战,传统诸宗教都处在突变的边缘。在此情况下,当我们对诸宗教进行研究甚至致力于它们之间的沟通时,我们不能置它们所受的挑战于不顾,满足于对它们作现象学的描述。
现在回到本文题目中的问题也是以上三个问题的总问题上来:“存在”存在吗?我想我的回答是:存在的不是作为本体的存在,而是作为象征的存在;对于所谓本体,我们毋宁把它说成是“非存在”,或者毋宁像佛陀那样沉默;对于作为象征的存在,如道、法、天、耶和华、上帝、安拉等,我们则尊重诸传统关于它们的言说,但这些象征同时应该是活的,将随着生活在它们之中的人的改变而发生变形、扩展或突变等等。当我这样回答时,我发现自己已对何先生的“全球宗教哲学本体论”作出这样的回应:由于在本体问题上的不同思考,也由于对世界诸宗教本身所受的挑战的认识,我无法把何先生所说的“使在—内在—超在”作为本体论来接受,更难以把它作为“全球宗教哲学的本体论”来接受,但我欣赏它作为一种言说方式深化和扩展对诸宗教的终极象征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