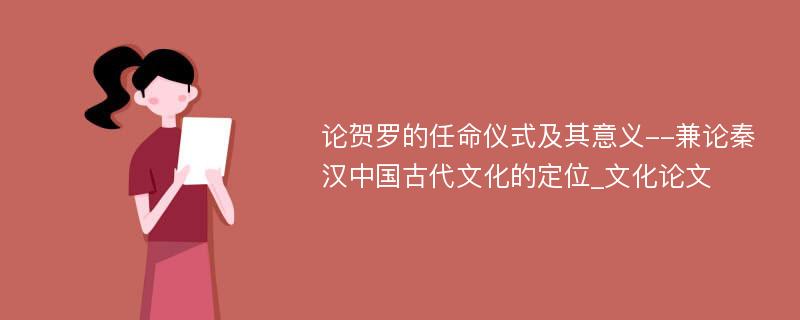
试论河洛受命仪式及其意义——兼论中国古代文化在秦汉时代的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秦汉论文,中国古代论文,试论论文,仪式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2;K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7)05-0215-07
西汉河洛受命说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摈弃秦代政治和接续三代文化传统。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及《货殖列传》中特别指出河洛地区与三代文化的关系,而他自己对三代文化是极为向往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载汉武帝封禅泰山,“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而子迁适使返,见父于河洛之间,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夫天下称诵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邵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爰及公刘,以尊后稷也。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首先,武帝封禅是汉家受命改制的大典,司马谈极为向往,以至称为接千岁之统的盛事,其承周启汉之意显然。其次,司马谈要司马迁继周公、孔子之绪以修史之志,一定要在“周南”和“河洛之间”宣示出来(周南即是洛阳),隐约可见河洛受命说的思想文化支撑背景。河洛受命说的影响之大,原因之一在于它拟设了一套受命仪式作为其法理正统象征,从而为三代以迄秦汉的文化传承及渊源构设起相应的思想理论根据,因此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极为深远。
一、河洛受命仪式
商周时代的天命观演化为秦汉时代的河洛受命传说。河洛受命体系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内容,一是其建立起以伏羲为首的三皇五帝史统,由于它成为中国古史的正统象征,从而就相当于为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关系就此定位;二是它构拟出一个河洛受命仪式,因此不仅使河洛地区成为中国古代的历史地理象征中心,而且又相当于为所拟伏羲为首的三皇五帝史统从思想文化上确立起合法化的信念根据。所谓“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瑞异应德之效也”(《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七》),“则有天命之应,盖龟龙衔负,出于河洛,以纪易代之征”(《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一》),都肯定了三代以来图书作为受命易代征应出于河洛的说法。河洛作为受命圣地性质的取得,与夏人作为中原先住民族首先建都于河洛地区,继则商周先后都于此的传统有关。如夏为中原先住民族得到商人的承认,《诗·商颂·长发》:“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商颂·殷武》:“设都于禹之绩。”夏为中原先住民族一点亦得周人承认,《逸周书·商誓》:“昔在后稷……登禹之绩。”《书·立政》:“陟禹之绩”。上举诸例,乃商周对夏人先居中原和经营中原活动的承认。夏人居于嵩山一带,北临河洛,河洛对夏人之重要亦不言而喻。河洛既为夏人都邑所近,商周二代又先后承之于此建都,河洛之重要亦因之而突出。在有关夏代的记载中,可以见到河洛二水密切相关之例。如《古本竹书纪年·夏纪》:“洛伯用与河伯冯夷斗。”《天问》:“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射夫河伯,而妻彼洛嫔?”《归藏易》:“昔者,河伯筮与洛伯战而枚占。”[1] 河洛地区重要的政治文化地位,是三代以来逐渐形成的。
司马迁指出:“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三代古族虽皆临河而居,但居处各异,在地域起源上原有其不同的渊源,相互间本无直接的传承关系。可是因夏商周三代先后皆建都河洛,于是相互间可以入居河洛的时间次序,排出一个先后的承袭关系,夏商周三代由此成为政治一统。三代建都河洛的事实,又派生出“河出图,洛出书”的预言,谶纬则利用之作为制造河洛受命中心的舆论根据。谶纬既以伏羲为膺受河洛之命的首位帝王,又以伏羲为首构拟起河洛受命的古代帝王法统,以此为基础又派生出三皇五帝的史统。现存谶纬文献中所载帝王临观河洛,沉壁行礼,神龙玄龟负图书而出代天授命之事,包括伏羲、黄帝、仓颉、尧、舜、禹、汤、文王、武王、成王、秦始皇、汉高祖诸人,从而形成伏羲以来的河洛受命帝王谱系。揆诸事实,似伏羲以下帝王皆受命于河洛地区本无可能,此乃是在河洛受命传说基础上构拟而成的古代帝王受命谱系。《春秋说题辞》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其运明授命之迹。”[2] 856按孔子删书,断自唐虞,故《书》所载乃二帝三王之事,亦即以唐虞夏商周为时间架构的早期王朝演变史。后来纬书依据此王朝史演变模式,又主要根据《易传》所列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的古帝排序,复加以增益推衍,制造出伏羲以迄秦汉的纬书河洛帝王受命统系。如若溯其本原,河图洛书乃是春秋以来流传的盛世即将降临的期盼预言,但在谶纬河洛体系中,又成为上古帝王的受命符应。在谶纬文献中的帝王受命系统,就是以河洛图书作为天赐法统的象征,进而推衍出临观河洛、沉壁行礼、神龙玄龟负图书而出的授命仪式,从而使纬书中构拟的伏羲以来帝王传承统系,具有法理信念上的神圣合法性,因此这种古史缔构体系,在观念层面上得到后世的完全认同。
如前文所言,“河出图,洛出书”之说,应是由三代皆建都河洛的事实派生而出。后来秦都咸阳,南临渭水,渭水于是成为显现秦德瑞应之水,《汉书·五行志》中之下有曰:“昔三代居三河,河洛出图书。秦居咸阳,而渭水数赤,瑞异应德之效也。”按此渭水瑞应乃是由三代河洛说的推衍无疑。纬书《河图括地象》更有“地有四渎,以出图书”之说[2] 1091,按四渎即江,河、淮、济,此说应是河洛说的扩大。《初学记》卷六引《穆天子传》曰:“河曰河宗,四渎之所宗也。”河既为四渎所宗,那么,河出图书,四渎皆应出图书。似此皆应为纬书作者的随意推衍,要之,还当以河图洛书之说为有本原。按纬书之说,当河出图、洛出书之际,河、洛之水皆先有瑞应显现。《易纬乾凿度》载孔子曰:“天之将降嘉瑞应,河水清三日,青四日,青变为赤,赤变为黑,黑变为黄,各各三日,河中水安井,天乃清明,图乃见。”这是河图出现之前的河水变化瑞异。又载孔子曰:“帝德之应洛水,先温九日,后五日变为五色,元黄天地之静,书见矣。”[2] 49-50这是洛书出现之前的洛水变化瑞异。这里的描述,是为突出图书作为天命法统象征的神圣性;在河洛受命仪式中,图书的授予是最基本的要素,天命内容全载录于图书之上。
古代出于生存需要,因而在居址选择上必须考虑到自然资源及环境等条件,于是有所谓“国必依山川”及山川崇拜观念。周代祭山林川泽可归结为埋沉之礼,《周官·春官·大宗伯》:“以貍沈祭山林川泽”,郑注:“祭山林曰埋,川泽曰沈。”孙诒让指出:“埋沉祭礼所献兼牲、玉、币三者。”[3] 以祭川泽为例,以沉玉为主,一般称之为“沉璧”。《管子·形势》:“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矣。”所言即祭川渊沉玉之礼。川泽之祭主要对象为江、河、淮、济所谓四渎,其中河称河宗最为隆重。记载所见祭河皆用玉,如《左传》文公十二年:“秦伯以璧祈于河”,襄公十八年:“晋侯伐齐,将济河,献子以朱丝系玉二珏而祷之……沈玉而济。”这就是河洛受命仪式中“沉璧”的由来。三代皆建都河洛,因此三代皆应祭河洛。纬书中虽记载一些禹临观河洛之事,但夏代祭河洛之事不甚清楚。商代祭祀最多、最隆重的是“河”神,有关卜辞不下五百条之多,“河”即河神。此外,卜辞中所祭还有洹水、漳水、淇水、湡水等,都是流经商都及其附近的河流,但受祭的次数和规模远不及河[4] 67。商代祭河及流经商都附近的河流,可与秦代比较。秦代注重名山大川之祭,故对河水之祭加隆,其他如灞、产、泾、渭等水虽非大川,但因其近都城咸阳,故“尽得比山川祠”(《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由殷商及秦代之例,可知三代居于三河,故皆应祭河;洛水虽为河水支流,但以近都邑之故,于是得配河而祭。总之,因三代皆建都河洛,于是皆祭河洛,不过当以祭河为主而配以洛水。“河图”概念较早见于《书·顾命》,至《穆天子传》所见祭河仪式,不仅有“沉璧”仪式,亦见相关的“河图”概念。《穆天子传》卷一:“天子命吉日戊午,天子大服……奉璧,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官人陈牲全,五[牲]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柏夭受璧,西向沉璧于河。再拜稽首,祝沉牛马豕羊。河宗[致]命于皇天子……天子受命,南向再拜。已未,天子大朝于黄之山,乃披图视典,周观天子之宝器,曰:天子之宝(注:曰,河图辞也)……曰柏夭既致河典(注:典,礼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图所载,河伯以为礼,礼穆王也),乃乘黄之乘,为天子先,以极西土。”[5] 按河宗应即河伯,乃守河诸侯,助周穆王行礼祭河;河伯保有河图、礼典,其上载贡献于天子之宝器及祭河礼仪;河伯据河图、礼典助天子祭河。《穆天子传》所言殆为河洛受命说所本。其事自当有渊源,《史记·大宛列传》:“河源出于寘,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此所谓“古图书”,殆与河伯国世守之图书有关。
据纬书所载,作为帝王受命的根本象征有一套河洛受命仪式,此仪式的中心是图书授受,因为图书是记载所受天命内容的符录简册,是天命兑现的根据。有学者对河洛受命仪式的程序进行了归纳:(1)归观河、洛,沈璧行礼;(2)荣光起,某德之色的云浮至;(3)某德之色的龙(或凤凰,或鱼,或雀)负图出(或化图,或衔书);龙没而图在;(4)图是用某德之色的玉为匣的,其封泥上盖的印章是‘天某帝符玺’五字(某帝之某,即某德之色);(5)拿匣子打开,其中有卷着的图,写着天帝的秘密;(6)应当禅让的于是行禅让礼,应当征伐的于是兴师征伐,并誉之为“这可称为最有具体表现性的受命”[6]。《水经注》对黄帝、尧、舜、禹、汤的受命之事进行叙述,其对于理解河洛受命仪式颇有助益,现录于下:“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璧,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赤文绿字。尧帝又修坛河洛,择良议沈,荣光出河,休气四塞,白云起,廻风逝。赤文绿色,广袤九尺,负理平上,有列星之分,什政之度,帝王录记兴亡之数,以授之尧。又东沉书于日稷,赤光起,玄龟负书,背甲赤文成字,遂禅于舜。舜又习尧礼,沈书于日稷,赤光起,玄龟负书,至于稷下,荣光休至,黄龙卷甲,舒图坛畔,赤文绿错,以授舜。舜以禅禹。殷汤东观于洛,习礼尧坛,降璧三沉,荣光不起,黄鱼双跃,出济于坛,黑乌以浴,随鱼亦上,化为黑玉赤勒之书,黑龟赤文之题也。汤以伐桀。故《春秋说题词》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王者沈礼焉。”[7] 按河洛受命仪式主要包括修坛行礼、沉璧、神龙玄龟负图书出等节目,同时伴随有荣光、风云、休气等天地感应现象。其中“沉璧”之外,又有“沉书”之说。祭川泽本有“沉璧”之礼,此外纬书中又有刻璧为书以告天言事,如《帝王世纪》曰:尧“率群臣刻璧为书,东沉于洛,言天命当传于舜之意。今《中侯运衡》之篇是也。”[8] 因河洛与天地相通,故可以“天苞”、“地符”等圣书秘文授予受命者,这是河洛受命仪式中的根本象征。
由于河洛受命仪式的最实质内容可以归结为图书的授予,于是有学者探求图书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如有学者指出图书的三种制造方式,第一是制造一幅图书,令龟负之而出;第二是根据龟背的文理,写出文字来;第三种是在河岸筑坛,利用河边的沙土为盘,以龟行成文,用时文书写。他认为第三种方法最妙,不容易察觉其作伪的痕迹,利用龟行沙上也与后世降乩的沙盘相似,只是难做[9]。又有学者对河洛受命仪式的可实际操作性提出质疑。他认为后世的受命帝王不可能像河洛神话中那样,设坛于河洛,等待龙马玄龟负图而出,或举行《穆天子传》中的祭河仪式,因为这种具有灵异色彩的祀典不可能如实举行。所以东汉光武帝虽利用了谶纬有关刘秀受命的神话,而实际举行的却是封禅泰山的国家祀典。所以,由于河洛神话与祀典脱离,河洛受命仪式没能成为汉代国家祀典[10]。其实,河图洛书的宣传与河洛受命仪式的构拟,其最大意义在于社会文化心理上的价值预期,而不在于它们能否在现实中实际施行,说到底,它们只是作为一股学术思潮,向人们灌输一种文化思想理念。考自春秋战国以来,道家在“道”的哲学思辨层面达到相当高度,但在社会政治理想方面,仍以儒家最具影响力。如儒家的太平理想既是对当下乱世浊政的批判,也可以唤起人们对未来社会历史的期望,其意义不容低估。但由于秦国为统一而推行强烈的法家功利政策,热衷于宣传军国尚武意识,终使儒家思想文化受阻,继则又以极端的焚书坑儒暴行打击摈弃儒家,使三代以来积累起的文化传统岌岌可危。秦文化中本有戎狄异质文化因素,它靠挟持武力打造起的强大威势,有似旋起旋扑的暴风骤雨,转瞬即逝,于是遭受阻遏的儒家思想席卷重来。司马迁《五帝本纪》乃是以孔子儒家的历史文化观念为秦汉一统构筑理念根基,河洛传说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恢复三代文化传统和扫除秦代法家酷吏政治为宗旨。汉武尊儒使这一思想趋势益加弘扬,同时谶纬的兴起使河洛受命传说更加光大。它既接受了司马迁完善而由孔子儒家缔构的五帝体系,又接受了主要以《易传》提出的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古帝文明史统,以构拟新的古帝谱系,且为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塑造新的民族心理认同元素。经纬书构拟起的河洛受命仪式,意义极大,因为它使纬书重塑的以伏羲为首下迄秦汉的受命帝王谱系,得到想象性的法理正统依据,它同时又使纬书构拟的新三皇五帝史统,成为魏晋以下普遍认同的象征性文化传承核心。所以从秦汉帝国的角度看,河洛受命神话有似学术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又似历史文化思想的政治化,是为秦汉帝国一统局面服务的国家神话。纬书缔构的新三皇五帝史统之所以能在此后的文化传承中处于主流核心地位,是因为它发扬了孔子儒家总结三代文化时所奠定的以历史为思想根基的主流文化传统。
二、龙为河洛受命仪式中的主要灵物
在河洛受命仪式中最常见的节目,就是神龙玄龟负图书而出,授予受命者。此龙、龟担当的是传达天命的使者与中介角色。张光直曾言,在萨满文化里,通天地的最主要助手就是动物。他又结合《左传》关于夏鼎的记载指出,在青铜器时代的各种器物上还可见到许多动物的形象,这种动物实际是古代巫师通天地的助手[11]。此说当有助于对龟、龙角色的理解。除龟、龙负图书之外,在河洛受命仪式中还有鱼担任此角色。据《韩非子·内储说上七术》载,齐人有意为齐王会大神河伯,“乃为坛场大水之上,而与王立之焉。有间,大鱼动,因曰:‘此河伯。’”由此大鱼被视为河伯大神之例,可以推见到龟、龙的角色性质。正是因其河伯大神的地位,被河洛受命说选为传达天命的中介使者。《礼记·礼运》以麟凤龟龙为四灵,《孔丛子·记问》载孔子之言,认为四灵乃圣德致太平的象征:“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则麟凤龟龙先为之祥。”纬书继承了此说,如《礼稽命征》以龙凤麟虎龟配五行为五灵,这显然是四灵被五行化的结果。《乐稽耀嘉》以鳞虫龙为长,羽虫凤为长,毛虫麟为长,介虫龟为长,倮虫圣人为长。龟、龙的四灵属性,也是河洛受命仪式选中二者为天命使者的原因之一。《大戴礼记·曾子天圆》又谓四灵本阴阳之气所生,“龙非风不举,龟非火不兆,此皆阴阳之际也。兹四者,所以役于圣人也。”即谓四灵具阴阳的属性,特以龙、龟为代表,俱为圣人所役使,亦即乃圣人通天地的助手。此外若从神话学的角度视之,也自有其原因。神话起源于原始社会采集、狩猎时期,动物在其时的人们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除动物图腾崇拜之外,动物又往往扮演着造物的文化英雄角色。如原始先民同动物广泛经久的接触,往往会凭借直觉和经验把某种文化起源同动物联系起来,如我国佤族神话说谷种是蛇从水取出的[12]。神话中的动物意义已然如此,再加之既以河洛为受命圣地,那么以水族动物龟龙为授命使者也是必然的。《易纬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应先于河,瑞应之至,圣人杀龙,龙不可杀,皆气感也。君子得众人之助,瑞应先见于陆,瑞应之至,君子杀蛇。蛇不如龙,陸不若河。”(以下纬书俱出《纬书集成》,不再出注)按所谓“圣人杀龙”殆与《墨子·贵义》帝杀四龙之说相关。① 所谓“君子杀蛇”殆与刘邦以赤帝子斩白帝子之说有关。最重要的是圣人受命瑞应“蛇不如龙,陸不若河”,这对于我们理解纬书设计河洛受命圣地及其选中龟龙为授命使者一点,应极具启发性。此外,龟龙授命使者之重要,因为它的属性关系到受命者制度属性等特征,如《易纬乾凿度》:“帝王始起,河洛龙马,皆察其首。蛇亦然。其首黑者人正,其首白者地正,其首赤者天正。”纬书接纳了儒家三统说,这实际是讲授命灵物的属性特征预示和决定了受命者的制度特征。这说明授命使者在河洛受命仪式中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
在河洛受命仪式中,要以龟龙乃授命灵物中最主要亦最具代表性。龟龙作为授命灵物原具有一定的神性,如《管子·水地》曾有曰:“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和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上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谓之神。龟与龙,伏闇而能存能亡者也。”是龟的神性在于它能预知存亡祸福,纬书中亦有相类论述,如《洛书灵准听》曰:“灵龟者,玄文五色,神灵之精也。上隆法天,下平法地,能见存亡,明于吉凶。”据《管子》所言,龙的神性更强,其变化莫测高深,《史记·老子韩非传》孔子关于老子犹龙之喻与此合。所以,在河洛授命灵物中虽以龟龙为代表,其中龙较龟更重要。按纬书“河洛龙马”之说,龙与马为同类。古有“马八尺为龙”之说,②《仪礼·觐礼》:“天子乘龙”,《礼记·月令》:天子“驾仓龙”,所谓“龙”皆指马。《吕氏春秋·本味》则谓:“马之美者,青龙之匹。”这在民俗中也得到证明,如对龙形象的比附随地域而出现差异,黄河、长江流域习惯于把鳄鱼比作龙的世俗形象,而内蒙古草原龙的形象却被人们更为熟识的马所取代[13] 311。关于马的属性,纬书中有谓:“地精为马,十二月而生,应阴纪阳以合功。”(《春秋说题辞》)纬书中“龙马负图”之说,殆与马“应阴纪阳以合功”的属性有关。历来的研究者都意识到,龙是综合了数种动物的局部特征而形成的抽象图腾崇拜物。上述龙与马的关系应说明,在龙崇拜的观念中,有取于马的部分因素。在天文上,房星为龙,又为马,《论衡·龙虚》:“世俗画龙之象,马首蛇尾。”至少从汉代以来,马已经被附会到综合创造出来的龙的概念之内,这是纬书“龙马”概念的思想文化背景。
关于龙的传闻不仅在记载上出现较早,而且在考古发现上出现亦较早。如据说龙的形象,目前考古界已追溯到山西吉县柿子滩岩画上的“鱼尾鹿龙”,距今约10000年前;辽宁阜新查海遗址出土的用石块堆塑的巨龙,距今约8000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出土蚌塑龙,距今约6000年[14]。其他如红山文化玉龙、二里头文化陶寺遗址陶盘上的彩绘蟠龙,时代亦较早。据记载所见,早期龙是供人骑乘的,如《大戴礼记·五帝德》载黄帝“乘龙扆云”,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冬乘马”,尧则“丹车白马”而无乘龙之事,舜、禹以下乘马之事亦不言。证之《左传》帝赐孔甲“乘龙”,则龙确为骑乘之类,其用与马同。于《山海经》,《海外南经》载南方祝融“乘两龙”,《海外西经》西方蓐收“乘两龙”,《海外北经》北方禺强“践两青蛇”,一本作“乘两龙”,《海外东经》东方句芒“乘两龙”。又《海外西经》、《大荒西经》俱谓夏后启“乘两龙”。③《春秋命历序》把开辟至获麟二百七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驾龙,周密与神通,号曰五龙。”这显然把乘龙之事推源于太古之初。若所言可信,则后世乘马是否亦与乘龙的启发有关?那么,在传闻中龙的出现极早,且可供人骑乘。据另外的记载,龙在上古曾是人们习见之物,且供人豢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因“龙见于绛郊”,引起蔡墨关于龙的一段议论。他指出,龙在古代为人所豢养,如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而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及有夏孔甲,扰于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于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他又主要根据《周易·乾卦》爻辞中有关龙的文句指出,龙在古代是人们习见之物,“若不朝夕见,谁能物之”?据豢龙氏、御龙氏二职推测,至少在虞夏时代龙乃习见动物,除上述记载外,又如《国语·郑语》:“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记载中又把龙说成是夏代的祥瑞,如《史记·封禅书》谓夏得木德,青龙止于郊,又谓“帝孔甲淫德好神,神渎,二龙去之”,证之上引《郑语》,“二龙去之”乃夏衰之异。《括地图》:“禹平天下,二龙降之。”(敦煌旧抄《瑞应图》残卷引《括地图》)此以龙降为禹平天下之祥。所以会把龙视为夏代兴衰祥异,应从另一侧面证明夏代多龙。④ 再从《左传》昭公二十九年魏献子“今何故无之”一语推断,龙在当时已罕见到几乎绝灭的地步,人们只是借助传闻还保留着对它的记忆。《庄子·列御寇》载朱泙漫学屠龙之事,亦可从另一侧面证成此点。现实中龙的罕见,却使之在传闻中进一步被神化。战国时代方士与神仙家的兴起,使《庄子》中已可见龙与神仙家言的结合,《逍遥游》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楚辞》中的龙亦已与神话结合,如《离骚》:“驾八龙之婉婉兮,载云旗之委蛇”,其中提到“昆仑”、“赤水”、“不周”等,都是昆仑系统的神话地名,《九歌·河伯》:“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离。登昆仑兮四望。”至汉代龙已与神仙家言结合,如《论衡·龙虚》:“仙人骑龙……世称黄帝骑龙升天”,所言即《史记·封禅书》所载黄帝学仙成骑龙升天事。总之,龙是很早出现的一种物类,但随着时间的流转,其真实形象日益隐没,而其属性则日渐被神化,相应它也在众多事物上留下自己的影像,使之益加神化。
龙至少在虞夏时代还是习见的动物,同时它也在各方面留下自己的多层影响。首先是在天文历法方面,自汉唐以来就有学者据《周易·乾卦》爻辞所述指出,中国古代曾存在所谓六龙历历法[15]。闻一多则指出《乾卦》中的龙就是天文上的苍龙星座,夏含夷认为《周易》乾卦“是以昏时龙体在夜空中的位置来标志冬、春、夏、秋季侯的”[16]。是后有学者指出,秦汉以前,二十八宿中的东方苍龙七宿,在春分的黄昏时,开始出现在东方,随着季节的推移,其方位逐渐向西方移动;至秋分时,开始隐没于西方的地平线;《乾卦》中的龙就是指苍龙,龙位就是指这个时节黄昏时的苍龙在天空的方位,一个爻位对应于一个时节[17]。上述关于《乾卦》六龙的各种认识,都牵涉到龙的形象属性在天文历法上的影响。苍龙星座在指示季节方面,对人们的生产活动、祭祀活动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尚书》、《左传》、《国语》中的记载可为佐证,龙的声誉随之日彰。这些认识至少应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龙本是上古习见的动物,它在人们思想上留下普遍深刻的印象,以至据其形象属性为根据,在天文历法的范畴内予以引申发挥和再加工,从而留下这样的比附影响[13] 306。其次,龙的形象在三代旗章、礼器上留下其影响。如《礼记·明堂位》载鲁用四代礼乐制度,其中灌礼所用舀郁鬯的勺乃“夏后氏之龙勺”,所用钟磬架为“夏后氏之龙簨簴”,韨制中有“周龙章”。《书·益稷》载天子冕服十二章之中有龙,周代冕服九章之制龙为首,《周官·春官》掌九旗之物名,其二“交龙为旂”。在商周礼器中亦可见到龙的形象,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璜、玉玦有作龙形者,殷代彝器有龙形铜觥[13] 308-309。此外,亦有以龙为人名乃至氏族名者,如《书·舜典》所命二十二人中有朱虎、熊罴、夔、龙,此四人当是四个各以动物为图腾的氏族族长,即龙原为该氏族的族名,氏族长按惯例冒以为己名。记载中夏桀之臣有关龙逢,关龙者,豢龙也。逢乃豢龙氏之后,是豢龙氏在夏代的余裔,豢龙氏即后之龙氏[18],见于《孟子·滕文公上》所称者有龙子,为战国秦汉时代的闻人[19]。这是龙在姓氏人事上留下的影响。龙的最大影响之一,是它在春秋战国以来进入阴阳五行家学说,继则进入纬书之内,成为传达天命的使者授伏羲以河图。
《墨子·贵义》载墨子对日者有曰:“且帝以甲乙杀青龙于东方,以丙丁杀赤龙于南方,以庚辛杀白龙于西方,以壬癸杀黑龙于北方。”此所谓龙已与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鬼谷子·本经阴符七篇》:“盛神法五龙,盛神之中有五气”,此“五龙”、“五气”必与五行相应,故陶宏景注云:“五龙,五行之龙也。”⑤ 证以《淮南子·地形》所言,与中、东、南、西、北五方相应的是黄龙、青龙、赤龙、白龙、玄龙等五色龙,其为阴阳五行说无疑。龟的阴阳五行化于《周官·春官》之《卜师》、《龟人》已见端倪,这是龟、龙进入纬书并成为主要的代天授命灵物的关键性原因,因为阴阳五行之学是谶纬的哲学思想基础。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审视,纬书中的龙已脱离原始的图腾崇拜意识,并被赋予人类的属性特征。有研究者指出,龙图腾的徽帜图案,不断被加工神化,最终使之变成脱离原始造型的超现实神灵;龙是不同图腾的综合,其形象源自似蛇大鱼,又增加了角与足,但保留了蛇身之鳞、鳍。春秋以后龙的图腾意义消失,成为祥瑞或受天命的象征[4] 89-90,96-97。但纬书中的龙已不仅仅是祥瑞或受天命的象征,它在帝王感生说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自先秦以来,即流传帝王感生说,如简狄吞玄鸟卵生契,姜嫄履大人迹生稷之类。此二感生类型稍异,前者为吞物感生,后者可称意感感生。此二说为纬书继承下来,见于《诗含神雾》、《春秋元命包》。纬书又增加了华胥履大迹生伏羲之说,见于《诗含神雾》、《孝经鉤命决》;含始吞赤珠生汉皇之说,见《诗含神雾》。此外,纬书中增加了大量意感而生的事例,如《诗含神雾》:“大电光绕北斗枢星,照郊野,感附宝而生黄帝。”《春秋元命包》:“大星如虹,下流华渚,女节梦接意感而生朱宣。”⑥《诗含神雾》:“瑶光如蜺贯月,正白,感女枢,生颛顼。”《诗含神雾》:“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帝舜。”《尚书帝命验》:“修纪山行,见流星,意感栗然,生姒戎文禹。”《诗含诗雾》:“扶都见白气贯月,感黑帝生汤。”以上意感而生之例,所感多为天象星光等自然现象,均为无生命之物。纬书中出现感龙而生之例,龙为神灵生物,在这点上它迥异于以上无生命自然现象诸感生之例。《春秋元命包》:“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子,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孝经钩命决》:“任已感龙生帝魁。”但如何感龙而生?这里并未明言。值得注意的是尧的感生,《春秋元命包》:“尧火精,故庆都感赤龙而生。”《诗含神雾》:“庆都与赤龙合昏,生赤帝伊祁,尧也。”两相比较,所谓感龙而生,即与龙合婚而生。考《帝尧碑》:“庆都与赤龙交而生伊尧”,《成阳灵台碑》:庆都“感赤龙交始生尧”,皆明言庆都与赤龙交配生尧(洪适:《隶释》卷一)。又《论语譔考》称孔子母“感黑龙之精以生仲尼”,《春秋演孔图》则谓孔子母“梦黑帝使请已,已往,梦交……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之中”,是感龙而生包括交配的情节。其实感龙而生的内涵主要应指与龙交配生子,这在刘邦的神话中最可为证。《诗含神雾》:“赤龙感女媪,刘季兴。”《史记·高祖本纪》曰:“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逐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须,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是人与龙交即人与神交,刘媪与龙交配而生高祖的记载,应是纬书中帝王感龙而生的原型。自《易·乾卦》以龙喻大人君子之后,龙已成为神圣帝王的象征,由此生出《新书·容经》“龙也者,人主之辟”一说,是后《广雅》径曰“龙,君也”。总之,纬书感生说中的龙,乃是神圣化的帝王代表,因此它也具有人的某些属性,可以代表天帝生育受命人间的帝王天子,故为神圣其事而采用感龙而生的神话形式,同时龙的这种角色又使之在河洛受命说中扮演了代天帝授图书的灵物使者之任。
纬书所以拟定神龙为授予伏羲图书的灵物,亦事出有因,即伏羲本与龙有着种种联系。如《左传》昭公十七年:“太皞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汉书·百官公卿表》则谓“宓羲龙师名官”,颜注引张晏有谓,因伏羲兴起之初有神龙负图之祥,于是乃以龙“名师与官”。其实综据各种记载看,伏羲与龙联系密切,这是纬书以神龙授伏羲河图的原因所在,而《左传》“太皞氏以龙纪”是一个重要的线索。按《月令》五行体系,春季配东方,其帝大皞,天子驾苍龙,其德木。东方与龙相配,在其他记载中亦可得到证明,如四象中东方青龙,《管子·五行》:黄帝“得奢龙而辩于东方”,皆可为证。太皞伏羲既为东方之帝,其与龙的联系自然密切。在五行体系中龙配东方属木,亦可用于解释《论衡·龙虚》“龙无尺木,无以升天”之说。《周易》六十四卦以《乾》为首,故《乾》可为《易》学体系之代表。《乾》六爻象六龙之位,应与太皞以龙纪有关,因此又有伏羲始作《易》八卦之说。《易纬坤凿度》亦曰:“乾为龙,纯颢气,气若龙。”纬书中《易》八卦乃由神龙负出,如《尚书中侯》曰:“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以伏羲龙图为端绪,于是神龙就成为河洛受命说中负图书授命的代表性灵物。
三、结语:谶纬河洛说与秦汉时代的文化定位
兴起于战国秦汉之际的河洛受命说,在汉代发展起两个值得注意的内容,其一是以伏羲为首的三皇五帝史统,其二是构拟出一个河洛受命仪式。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基础是父家长制家族,在王朝国家的政治结构之后,其实是由新老家长的血缘班辈传承所形成的父家长权力的转移交接过程,这才是国家权力运作的实质性内容。三皇五帝史统正是与此父家长权力转移传承关系相应的文化佐证模式和思想支撑基础。河洛受命仪式虽作为一套礼仪程式在人们的倡导宣传中发生着影响,但最终还是从思想理念上构筑起三皇五帝史统合法性的历史文化信仰根据,也就是能使王朝国家与宗法文化秩序从思想舆论上获得社会认同的律法演绎形式。这些有利于秦汉一统帝国模式的存在发展,有利于汉民族共同体的巩固形成和融合扩大,更有利于社会文化传统与民族心理意识的进化成熟。龙本是一种渊源久远的图腾崇拜动物,后来又在各方面留下其广泛深入的影响。龙作为一种灵异神物被阴阳五行化之后,进入到纬书神话体系之内。在纬书中它不仅担任着负图书授予受命者的灵物天使角色,还扮演着帝王受命感生神话中的主角。随着纬书的传布广播,尤其是龙与三皇首君伏羲的密切联系,使龙的文化地位日益提升,终于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信仰崇拜象征。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关于龙的概念内涵的滋育丰富,乃至最后在社会民俗和文化心理上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和标志,纬书的造作传布对此都有着不容低估的极大推动作用。因此,对纬书的学术价值与文化意义必须重予估价定位,它在汉代经学史上的意义也必须再予阐释评说。综之,在中国古代发展的长河中,秦汉时代是大一统奠基成形的重要时期,而秦汉时代的文化定位,与谶纬河洛说密切相关,这是本文力图向人们阐明的一个观点。
注释:
①《易·乾卦·彖传》:“时乘六龙以御天”,《庄子·逍遥游》:“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以二文相校,“六龙”当“六气”,殆此“龙不可杀,皆气感也”所本。又据《论衡·龙虚》汉人以龙为云气之类。
②《周官·夏官·廋人》。《公羊》隐公元年注:“天子马曰龙,高七尺以上。”是别一说。
③《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史记》曰:“昔夏后启筮乘龙以登于天,枚占于皋陶,皋陶曰:‘吉而必同,与神交通,以身为帝,以王四乡。’”此《史记》佚失,而载“启筮乘龙”,可与《山海经》相校证。
④闻一多曾言伏羲之外,要以夏与龙的关系最为密切(见《伏羲考》,载《神话与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57—58页)。
⑤转引自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54年版,280页。
⑥朱宣,即少皞,宋均注:“朱宣,少昊氏。”(见《纬书集成》中册,590页)。
标签:文化论文; 中国古代文化论文; 文化属性论文; 神话论文; 读书论文; 穆天子传论文; 乾卦论文; 乘龙论文; 左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