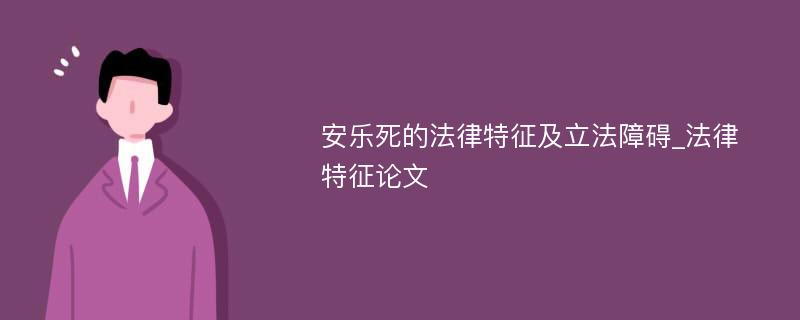
安乐死的法律特征及立法障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安乐死论文,障碍论文,特征论文,法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57;D922.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479(2007)02-104-04
今年“两会”期间,28岁的李燕,因患有“超级癌症”——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全身肌萎缩,而写了份《安乐死申请》议案,希望通过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提出并通过立法。李燕的申请虽然不可能会有什么结果,但是又一次掀起了对安乐死立法的大讨论。
自从全国首例安乐死案发后的近20年中,几乎每届人大会议均有代表提出安乐死立法提案,但年年均被卫生部以“时机尚不成熟”为由,予以回复。笔者认为,安乐死立法的时机是否成熟,决定于民众对安乐死的认可程度及社会的需要,而不应当由某个主管部门来决定。
一、历史回顾
安乐死是个古老的问题,史前时代就有加速死亡的措施。在原始部落迁徙时就常常把一些年老体衰的人留下,任其在自然中淘汰。古希腊、古罗马普遍允许患者及残废人“自由辞世”。在古印度也有抛弃老人和缺陷儿的习俗,有时还有外人的帮助。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习惯上处死天生病废婴儿。古希腊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思想家与政治家们,赞成当病痛无法治疗时以自杀作为解脱手段。当时认为,对于老人与衰弱者,经自愿使之安乐死是合理的。
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主张人的生死是神赐的,禁止自杀或安乐死。“文艺复兴”运动带来了人文主义兴起,赋予人以生的尊严,并不提倡安乐死。20世纪30年代,欧美各国都有人积极提倡安乐死,但后来由于纳粹德国在1938~1942年间利用安乐死杀害了数百万计的缺陷儿童、残疾人、慢性患者及精神患者,于是使这种提倡被看作是纳粹主义而声名狼藉,旋即销声匿迹。
国际上对安乐死问题的再次兴起,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的文明,医学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人工呼吸机的应用普及,虽然使许多人,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得以起死回生,但也使其中的一部分人长期处于一种半死不活的境况下,过着悲剧般的痛苦生活。其中有些人为了求得解脱,拒绝医院为他继续治疗,甚至要求医生帮助他早日结束自己的生命。但传统的伦理观念与法律规定是不允许的。一些医生由于满足了患者的这一要求而被指控为“谋杀”;另一些未得到这种满足的患者或家属则向法院起诉,提出“人既有生的权利,同样也应当有死的权利”(即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如生不如死时,有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使法官和医生们处于两难之中。
二、死的权利
人到底有没有处置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权利?传统法学或是伦理观念均持否定态度。古今中外从来都将自杀视作反人伦的不道德行为。协助他人自杀更是一种犯罪行为,甚至与杀人同罪。中国传统儒家道德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
但笔者认为,人应该享有死的权利,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生命属于个人,个体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进行处置,这是对个人自由权的一种保障。当然,这种自由并不是绝对的,应该受到一定的限制。因为,人作为个体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负有对社会应当承担的责任。如果个体行使自己的死亡权并不会损害集体、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不会造成负面影响,同时,自己又有足够的理由行使这一特殊的权利时,社会应当予以肯定,而不是全盘否定。(2)每个人都有生命的尊严。人的尊严具有最高价值,是不可侵犯的。当一个人的生命正遭受着疾病的折磨,同时又承受着难以忍受的苦痛时,他会认为自己的人格尊严正在被践踏,往往就会采取一定的方式来摆脱这种折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当所有的方式都不能达到要求时,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便成为了一种选择。(3)追求生命的最高质量,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目标。但是,当一个人的生命只具有纯粹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成为植物人),或是只能在极大的痛苦中等待死亡而又不能治愈,其生命质量几乎为零时,如果坚持用医学的手段去拖延其生命,使其遭受本可结束的痛苦,这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是残忍的。(4)有生就必然有死,生和死作为生命的两极应受到人类同样尊重。随着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人们已不再谈死色变。树立正确的死亡观,正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标志。
三、关于安乐死的定义
符合伦理的安乐死必须具备三个要件:有一个必死的病因;有不堪忍受的痛苦;出于自愿或不违反本人意愿。这三个要件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均不能认为是符合伦理学意义上的安乐死。
学术界对安乐死的定义有多种讲法,如《法律词典》的定义是:对患有不治之症,生命垂危且遭受巨大痛苦折磨的危重患者,明确表示要求大夫采取措施使其无痛苦地离开人世时,由大夫以仁慈的方法帮助其离开人世,大夫则不负法律责任[1]。《牛津法律大辞典》的定义是:在不可救药的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其死亡的措施[2]。《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是:指对无法救治的患者停止治疗或使用药物,让患者无痛苦地死去[3]。
若按前两条解释,像李燕这样痛苦的绝症患者,由于其不符合“生命垂危”或“病危”的条件,便要被排除在安乐死对象之外。所以其定义存在不周延的缺点。而《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则更不像话,它只是被动安乐死的定义,并不包括主动安乐死,而被动安乐死在中国早就合法化了,是无须讨论的。
笔者认为,符合伦理的安乐死定义应表述为:安乐死是指对于患有现阶段医学科学技术所不能救治而又极端痛苦的患者,在不违背其本人意愿的前提下,为了解除其痛苦,由医务人员所提供的使患者在无痛苦状态下加快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的医疗性服务[4]。
这一定义体现了安乐死的三大原则,即:无危害原则、无痛苦原则和不违背本人意志原则。它的优点在于:(1)它肯定了安乐死是一项医疗性服务。(2)它接受了国内学者关于“死亡并不是瞬间来临的事件,而是一个连续进展过程,是由生到死的过渡”的正确观点[5]。(3)它以“加快结束或不再延长死亡过程”,表述了安乐死的全部外延。(4)摒弃了安乐死对象必须是“濒临死亡”、“濒死状态”或“病危”等过于保守的提法,因为“濒死状态”在临床上一般是指患者已经进入了濒死期,在濒死期中患者已不可能有任何意志表示[6]。对于一个已经进入了死亡期的患者实施安乐死,实在没有多大意义。(5)已处昏迷状态的不可逆性脑损伤患者是不可能有真诚请求(或委托)的。同时,从法律角度讲,对于人的生命权(在这里是指死亡权)是不允许由他人(包括监护人)代理处置的。因此,该定义避免了用“自愿”和“家属要求”这样的字眼,而代之以“不违背本人意愿”来表述,这就更准确地揭示了安乐死的内涵。因为无意识的“植物人”或“脑死”患者是没有意志的,所以对他们实施安乐死并不违背本人意愿。这就为医生们对已确诊的脑死亡患者,在没有生前预嘱,也无须家属请求的情况下,停止一切复苏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归纳起来,符合伦理的安乐死必须同时具备以下特征:(1)安乐死的实施对象只能是现阶段医学科技认为是无可救治的患者;(2)安乐死的实施不能违背患者本人的意愿;(3)其目的仅限于解除患者的痛苦;(4)实施的方式必须符合伦理要求;(5)它是由医务人员向患者提供的一项医疗性服务;(6)它是在特定情况下患者利益的最高体现。
四、安乐死的法律关系
所谓安乐死的法律关系,无非是指安乐死的主体、客体和内容三要素。
安乐死的法律关系同普通民事法律关系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通常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是指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即指物、行为和智力成果;然而,安乐死作为医疗服务的一部分,它的法律关系的客体(权利义务所指向的对象)却是仅指患者的生命或健康权。
生命健康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是受法律绝对保护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无权剥夺人的生命。然而,安乐死法律关系的客体竟然是生命健康权或者死亡权,这样,问题就产生了:(1)从法律关系的概念出发,因为生命权是不可剥夺的,因此安乐死行为就是违法的,这里还有讨论它的必要吗?如果仍有讨论的必要,那么,安乐死的合法性当作何理解?(2)在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中从来就没有将人的生命健康权作为客体的提法,那么,医患关系是属于民事法律关系的范畴吗?若不属民事法律关系,又属何种法律关系(由于医疗机构不是行政机构,当然也不属行政法律关系),难道在民事法律关系和行政法律关系之外,还有第三种法律关系吗?(3)任何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中从没有“死亡权”的提法,那么,法律应当认定人有死亡权吗?
其实,上述问题的提出,本身就表明了安乐死问题的复杂性,也正说明了安乐死问题的提出,其本身就是对传统医学、传统伦理、传统法律的一种挑战。谁要是想从现行法律或者现成的法学理论或法学教科书中找到关于安乐死问题的现成的答案的话,就是对安乐死的无知。由于上述问题不属本文讨论的范围,且笔者已著有专文[7],故这里不予讨论。现在需要讨论的是安乐死法律关系的特征,即它相对于一般其他法律关系有什么不同?
根据上述有关安乐死法律关系主体、内容及客体的涵义及本文提到的相关理论,可以看出安乐死法律关系相对于一般民事法律关系主要有以下特征:
第一,安乐死法律关系的主体是特定的。其主体只能是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医疗相对人。安乐死不可能由医务人员之外的其他主体来施行,也不可能对医疗相对人之外的其他主体行使;安乐死若在其他主体之间发生,便不能称之为安乐死,而只能称之谓“谋杀”。
第二,安乐死法律关系的客体是特有的,在安乐死法律关系中权利和义务所共同指向的对象,既不是物,也不是行为及智力成果,而仅指医疗相对人的生命健康权或者死亡权。
第三,由于安乐死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仅指医疗相对人的生命健康权或者死亡权,因此,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是不对等的。对医方偏重于义务,而对患方则偏重于权利。
第四,同样,法律关系的内容,对不同主体将有所偏重。对接受主体偏重权利,对实施主体偏重义务。这就决定了在安乐死案件的诉讼中,人民法院往往偏重于审查医方是否尽到了注意性义务,即是否存在过错,而较少审查或追究患方是否有过错。
五、安乐死的立法障碍
安乐死问题是医学伦理学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哲学与法学的一大难题。它之所以难,不仅在于理论论证上,而且是属于“真理再向前走一步便是谬误”的典型情况。
安乐死立法之所以难以通过,其主要障碍在于:人们对于安乐死是否应当纳入医疗服务的范畴、以及对医疗权的本质认识的缺位。
笔者认为,所谓医疗权,就是处理人体与生命的权利。这一概念是与传统法学理论相悖的,故很难为现代法律人所接受。正是由于人类对“医疗权就是处理人体与生命的权利”这一最本质特征尚无认识。所以,对安乐死立法人们仍停留在对传统法律认识的基础之上,这样就很容易总是在“人有没有处置自己的身体和生命的权利”这一问题上纠缠不休。
其实,这是将医疗权同传统的伦理观与法律观念相混淆的结果。然而,医术(医疗权)却正是处置人体与生命的权利。因此,若将安乐死放到“医疗服务”的范畴中去,那么,安乐死的立法问题便会变得十分容易解决。我国著名学者邱仁宗教授给安乐死下的定义就是:“有意引致一个人的死亡作为他提供医疗的一部分。”[8]
医疗权是一项相当广泛的权利。它关系着每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它可以行使其他任何人(包括行政官员、甚至国王)都不能行使的权力或权利。如为了治病的需要,医生有权了解患者的隐私,有权查验患者最隐秘的部位;有将毒药给人服用的权利;有将人的腹腔、胸腔、颅脑打开而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医生用上述危险的、对患者有重大伤害的方法治病,不仅意味着治愈,还意味着有死亡或残废的可能。因此,医疗权就是处分人体与生命的权利,其原则是必须在对医疗相对人有利期望的前提下,基于医事共同体的授权或医事相对人的委托或承诺,对医事相对人的人体与生命(生与死)进行处置的权力和权利。
医疗权的产生是基于对医事相对人生命与健康的有利期望,这一点非常重要,正因为医疗权的行使是基于人们的“有利期望”,故可使其违法性得以回避,而不构成违法或犯罪。
综上,笔者认为:安乐死是医疗服务的一部分。医疗权就是处置人体与生命的权利,其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对医疗相对人有利期望的前提下,基于医事共同体的授权或医事相对人的委托或承诺,对医事相对人的人体与生命(生与死)进行处置的权力和权利。安乐死的法律关系的客体不同于民事法律关系的客体,安乐死的法律关系的客体是仅指患者的生命或健康权。
法学界若能对安乐死的上述特征达成共识,那么,安乐死立法也就为期不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