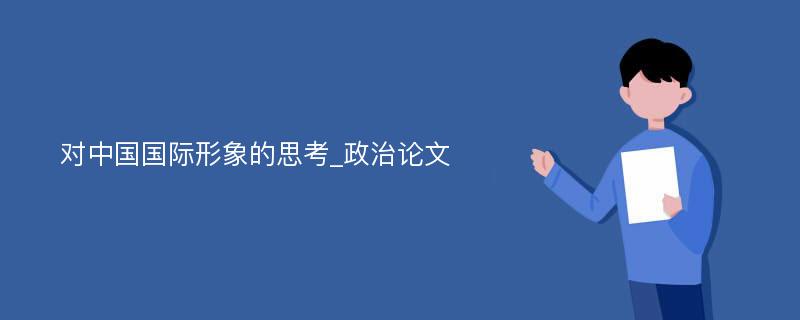
有关中国国际形象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国际论文,形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构建21世纪中国国际形象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其意义超出大众传播学科本身。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日益瞬间化和全球化,媒体对国际和国内政治的影响愈来愈大,国际传播中的国家形象在国际政治中因而也具有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媒体对中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然而,在中国看来,国际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对中国仍然不能予以公正客观的报道,有的甚至刻意地“妖魔化”中国,别有用心地制造障碍。如何改变这种现象,在国际社会中构造和建立一个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形象,的确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构建和传播21世纪的中国国际形象至少涉及这样几个问题:什么样的国际形象是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形象(或者说,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看到和接受什么样的形象)?谁来制作或构建这种形象?如何构建这种形象?如何使这种形象在国际媒体乃至更广泛的国际社会中建立起来并使之产生预期的效果?恐怕难以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其中牵涉国内和国际政治两方面,而它们本身又分别牵涉到另一些更复杂的问题,包括一些超出我们控制能力以外的问题。但正是因为国际形象的问题与国内国际政治的现状和发展有十分紧密的联系,我觉得非常有必要对此展开一种坦率的探讨。
所谓“中国的国际形象”,准确地讲,实际上是国际传媒中的“中国的国家形象”。一个国家注重自己的国际形象,是因为这种形象对本国在国际政治和其他事务中的地位有直接的影响。国际形象要影响的是国际社会,所以它的效果是国际性的。但是国际形象的构建却并不完全是一种国际行为,相反,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包括国际传播)中的形象更多的是一种国内政治和国内事务的延伸。国际关系学中有一句老生常谈:“外交是内政的反映”。这句话同样适用于表述一个国家的国际形象与其国内事务间的关系。
无论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看到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构造这个形象的素材必须是来源于现实的中国。中国社会本身发展的速度、质量、结构以及对未来发展的预期,是构建中国国际形象的基本素材。国际社会(包括媒体)对中国的反映、解读、分析和评论,从本质上看,都是一种制造中国国际形象的工作。毫无疑问,国际社会的报道与评论有自己的立场和特定的目的,但它们必须是对中国的内部事务的一种反映。国际社会可能对某一事实有不同的解释,但事实本身必须是存在的(这里我们暂且略去那些有意无中生有的报道)。中国本身的发展是塑造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的基础。我们首先要有具有正面意义的发展,然后才谈得上构建正面意义上的国际形象。南非在取消种族隔离制度以前,无论怎样在国际上粉饰自己,它的地位始终是孤立的,而当曼德拉一当选,整个南非的国际形象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
对于中国来说,如果我们希望国际社会看到一个不断进行深入改革开放的中国,我们必须有深入改革开放的行动和事实。如果我们称自己是一个政治在不断走向民主的社会,我们至少应该有令人信服的事实。如果我们希望国际社会把中国看成是在国际上伸张正义的国家,我们必须在国际事务中有勇气来做到这一点。简言之,有利的事实是有利的国际形象的基础。
如果国际(尤其是西方和美国)媒体能够(按照我们所想像的)如实报道和评论中国的国内发展,我们可能不会提出构建和传播中国国际形象的问题。不幸的是,国际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分析往往是不公正、带有偏见的,同时由于西方媒体在国际传播界占有极大的优势地位,它们对中国的国际形象的制作带有极大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掌握自己的形象制造权的问题,必须打破西方媒体在制造中国国际形象方面的思想模式和话语霸权的垄断。
在我们构造21世纪的中国国家形象时,无论其形式如何,至少应该格外注意民族性和思想性的特点。为什么要表现民族性呢?我认为,一个有力的国际形象首先应该是而且必须是一个充满鲜明的民族性特征的形象。中国的国际形象的主要内容应该表现中国和中华民族特定的历史情感、历史使命和历史追求。世界虽然在走向“一体化”和“全球化”,但民族国家仍然将是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民族文化仍然将是新的世界秩序中的基本单位。中国的改革开放首先是为了保护和发展民族利益的开放,中国的发展必须首先是以创造中华民族的繁荣为出发点的发展。民族性应该是中国国际形象的核心内容。在现阶段,超越民族性,简单地追求一种虚幻的“全球化”,只会制造出一种不伦不类的国际形象。
在国际形象中强调民族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角度(或立场)问题。尽管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中国人的历史经历充满了曲折和起伏,但近年来在国内和国际传播中,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民族性都无一例外地被压缩了、简单化了、公式化了,有时则是完全扭曲了。西方媒体这样做可能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也可能出于无知。西方媒体最常用的(同时也是最拙劣的)手法便是在高兴时给中国带上一顶“改革开放”的帽子,在不高兴时给中国套上一顶“共产党国家”的帽子, 仿佛中国和中国人的历史和追求都是从1949年后(甚至从1989年后)才开始的。正面的中国国际形象应该表现中国人丰富的历史深沉感,建立自己民族的话语模式。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诚实地重新审视我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
我认为,在21世纪的国际关系中,中国的国际形象内容中尤其需要非常有分量地表现中国特有的民族观和世界观。在过去500 年的历史中,西方世界以经济扩张为先导,辅之以政治和军事强权,将西方文明和利益推广到全世界,建立起以西方价值体系和利益体系为核心的政治经济秩序以及思想和文化霸权;在“全球化”的口号下,这种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更是肆无忌惮地蔓延,扼杀非西方的民族思想和文化。中国人在构建国际形象时,应该要有自己的思想,应该要有自己的政治语言,而不是盲目地跟随西方的“全球化”口号,人云亦云。我们追求和提倡国际间的合作,我们力求和平和发展,但是我们不能糊里糊涂地跟在别人后面跑。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民族的历史、面临的历史使命以及承担的世界责任。真正具有感染力的、能赢得尊重的国际形象,其力量不是来源于对西方的模仿,而是对自身民族性的尊重和对西方价值观的修正和挑战。正是通过这种民族性的国际形象,中国人的世界观才得以表现。
其次,一个有感染力的国家形象应该是一个具有思想和道德力量的形象。在国际政治中,“道德”、“正义”这些概念并没有确定的内涵,但中国的国际形象应该表现出一种道德和思想的力量和风范,这种力量和风范的特征就是表现一个大国对世界和全人类发展的关切和责任感。我并不是提倡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一个“道德领袖”的角色,但我坚持认为在重大国际问题上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立场,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应该能够有力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应该有勇气在国际事务中伸张正义。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解放思想,了解世界,活跃我们的思想,对国际社会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作出准确的理解和判断。而这一切都必须以中国国内在政治、学术和思想上的开放和活跃为基础。
关于西方制造中国国际形象的做法,我想补充一点。西方媒体在构造中国的国际形象时常常采用这样一种模式,即按照中国某某领导人的起落来界定中国国家形象的内容和质量。在西方媒体的影响下,我们似乎也都接受它们的一些说法:某某领导人是改革的,某某领导人是保守的,这些领导人的上台与下台决定着中国的未来等等。遇到西方媒体喜欢的领导人,它们可以吹吹捧捧,遇到不喜欢的领导人,便极力“妖魔化”。中国的国际形象无形之中成为了领导人的个人形象。坦率讲,这种情形的出现与中国现实的政治情势有关。但是,我们不应该顺理成章地接受这种形象制造的模式。实际上,西方媒体在塑造自己国家的国际形象时往往遵循另一种模式:使用“意识形态”(或西方世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而不是某某当选的领导人,作为它们形象的基础。西方的意识形态是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它弥漫和渗透在西方社会的种种机制和实践中,得到一种“普遍的”认可,成为西方媒体塑造自己和他国国家形象的哲学轴心。无论是在主流媒体的新闻评论还是在私营公司的广告中,都非常有效地包含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内容。而那些当选或落选的政客不过是这种意识形态的推销者。我们不应被此迷惑,领导人则更不能幼稚地以此为荣来迎合和助长西方媒体。
一个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要进入国际社会和国际传播界,将面临许多困难。首先,所谓国际传媒都是不同国家的利益的代表者,是一个混杂的集合体。指望这个传媒体系来忠实地不带偏见地报道中国是不现实的。但国际媒体社会又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媒体的本质就是传输信息。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传媒本身可以成为中国形象进入国际社会的重要渠道。
中国若希望国际社会对自己构建的国际形象持一种比较严肃和认真的态度,必须彻底摆脱简单粗糙的宣传模式和对西方“宣传”模式的盲目模仿和接受。此外,国际形象的传播渠道是多层次多维度的。报纸、广播和电视节目自然是构造和传播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媒介,中国政治和民间的各种(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外交行为(包括政府在国际问题上的立场、政府官员在国际场合中行为举止以及民间层次上的各种交流等)也都是构造和传播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渠道和媒介。而通过这些渠道表现的中国国际形象往往是更具有影响力的。而这些政府官员和普通中国民众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对于他们在国际环境下展示这种认识有重要的联系(1998年在白宫欢迎访美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时,美国总统克林顿曾特意指出,自中美建交以来,中国有许多留学生来美学习和任教,这些中国学生本身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素质对他们的美国同学和学生是有影响的)。应该说,无论我们用哪一种媒介,由中国人传播的中国国际形象都是中国国内政治文化、经济文化、教育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延伸和表现。中国国际形象的质量与所有中国人素质有重要关系。所以,国际形象的质量最终还是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