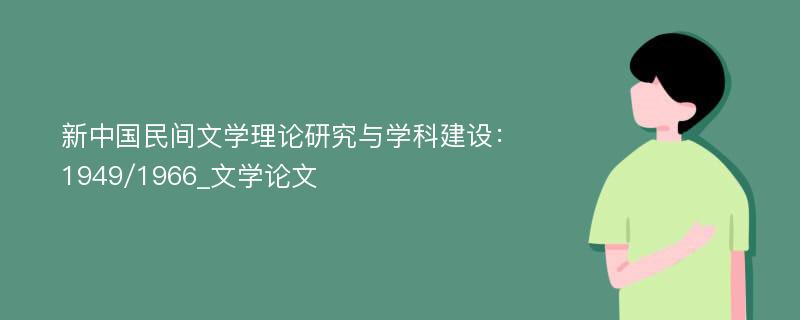
新中国民间文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1949~1966,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间文学论文,学科建设论文,理论研究论文,新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887(2003)01-0063-07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结束了长达22年的内外战争和分裂局面,给全国人民带来了 渴望已久的和平环境,也给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坦途。民间文学作 为一门人文学科,从1949年10月共和国建国起,到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前1 7年间,虽然也曾或多或少地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整 个60年代,在政治上受到“左”倾思想的干扰越来越烈,但总的看来,民间文学的理论 研究和学科建设还是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就和进展。
一、民间文学理论的主导思潮
新中国的建立为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特别是为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带 来了蓬勃的生机和难得的机遇。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在“双百”方针 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道路并不是笔直的。1956年中央提出“双百”方针不久,很 快就被1957年早春的反右斗争所打断,“左”的气氛越来越浓,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也被 纳入“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总框架内。前进固然是前进了,却东摇西摆,左支右绌。
建国初期,郭沫若和周扬在1950年3月29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就发 展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民间文艺事业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办法,他们热情地肯定和鼓吹搜集 研究民众自己的文艺,建立一个新的机构和一种新的学科。[1]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 先例的,但毕竟还属于继承民族文化优秀遗产的一般性观点,并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 民间文艺学内部的一些深层问题。钟敬文教授从香港来到北京,在被选为民研会的副理 事长之前,已连续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提出了一些观点,如1949年7月28日在中 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的《文艺报》第13期上发表的《请多多地注意民间文艺》,19 50年3月1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民间文艺论片断》,3月1日在《新建设》上发表 的《关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等,以及《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 [2],也都是比较偏重于从社会政治的或从社会学的层面上谈论民间文艺的价值、作用 。显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业待兴,整个文艺工作也在创建时期,因而还不具备提出以 新观点和新方法建立中国民间文艺学的时机和条件。
文化学术界的人员是从四面八方聚拢来的。他们带来了不同的经历,当然也带来了不 同的观点。从延安来的文艺干部,多数原本都是轻视民间文艺的,受毛泽东的延安文艺 座谈会讲话的感染和教育,转而开始重视民间文艺了。但他们大致上是把民间文学和作 家文学等同对待,用思想内容的进步与落后、是否能为政治服务、艺术上是否典型、情 节结构是否合理、语言是否提精等等,来作为衡量民间文学的标准,没有看到更不可能 强调民间文学的特殊性。从国统区来的学者教授们,则比较熟悉西方民俗学的理论和方 法,他们把民间文艺当作民俗学的分支之一,通常是从社会、思维、宗教、民俗等角度 来看待民间文艺,却常被当作资产阶级的学术来对待。同样都重视搜集和阐述民间文艺 ,但这两种不同的学术立场观点,却显出很大的差距。
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学术界都在热情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学术研究不应有国界,要广泛吸收外来文化发展自己的学术。但由于历史的 局限,那时中国只能“一边倒”,倒向苏联。苏联的确在社会科学许多领域里比我们高 明,但他们也有严重的教条主义。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的民间文学理论是时 代的潮流,苏联的理论和方法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惟一理论体 系。《民间文学》发表过恩格斯青年时AI写作的《德国的民间故事书》[3]和《爱尔兰歌 谣集序言札记》[4],以及高尔基的《论民间文学》[5]、《论故事——<一千零一夜>俄 译本序言》[6]、《谈<文学小组纲要草案>》[7]等文章。《民间文艺集刊》和《民间文 学》杂志从创刊之日起就不断发表余绳荪、王智量、曹葆华、连树声等翻译的苏联学者 的民间文学研究文章。最早翻译的是克拉耶夫斯基著《苏联口头文学概论》[8]和阿丝 塔霍娃著《苏联人民创作引论》。[9]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研究部又编选出版了 《苏联民间文学论文集》[10]。同时出版的还有:《民间文学工作者必读》[11]、《什 么是口头文学》[12]、《苏联民间文艺学40年》[13]等。那时,连老民俗宗教学家江绍 原先生,也沉浸在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和苏联民间文学理论之中。他发表 过《恩格斯论德国民间传说中的英雄龙鳞胜和》的长文[14],还出版过一本以“文种” 的笔名翻译的《资产阶级民族学批判译文集》[15]。其中就选译了苏联著名民间文艺学 家、莫斯科大学教授契切罗夫的《拉格朗男爵——反动民俗学的理论家》。由于主客观 条件的限制,当时我们所翻译和介绍的苏联民间文学理论,还多是些单篇文章或入门读 物,许多重要的理论专著并没有介绍过来。在一般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的心目中,苏 联的理论就是这样的,其实苏联民间文学界和民俗学界是有不同流派存在的,在主流之 外,就还存在着和发展着被西方学界称为“形式主义”的流派,而我们却对此一无所知 。而更重要的是,对西方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理论成果,亦步亦趋地跟在苏联人后面, 对其采取排斥和批判的态度,不能不使我们自己长期处于半封闭的状态中。
对于这种“一边倒”的情况,钟敬文曾写道:“十月革命后的苏联的学术,对我们的 新学术的建设有过很多影响。我个人在这方面的经验是微小的。可是,它可以证明在苏 联科学的引导下,我们能够怎样避免错误和比较快步前进。解放以来,我比较有机会学 习苏联学者和教育家们关于人民口头创作的优秀理论。凭着这种理论的启发和帮助,使 我能够抛弃了那些不正确的看法,使我能够解决那些有疑惑的问题,和重视那些原来不 大留意的课题。”[16]《民间文学》1957年11月号发表编辑部文章《认真深入学习苏联 先进经验为发展我国民间文学事业而奋斗》,提出了学习苏联先进经验是“我们必须坚 持的方针”。同期的《编后记》说:中国的民间文学工作,是“直接在苏联的文学艺术 和民间文学工作的经验的影响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那时的情况就是这样。苏联的理 论和影响,一方面推动了我们的学术发展,另一方面,他们的教条主义也给我们自己的 “左”倾思想推波助澜。
“左”的思想是越来越严重的。1954年《民间文学》创刊时的钟敬文撰写的《发刊词 》曾指出:“过去人民所创造和传承的许多口头创作,是我们今天了解以往的社会历史 ,特别是人民自己的历史的最真实、最丰饶的文件。……在这种作品中,记录了民族的 历史性的重大事件,记录了广大人民的日常生活和斗争,记录了统治阶级的专横残酷和 生活上的荒淫无耻……作为古代社会的信史,人民自己创作和保留的无数文学作品,正 是最珍贵的文献。我们都读过或知道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它是列 宁所称赞的‘现代社会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在这部原始及古代史的经典著作里,恩 格斯就引用了希腊等民族的神话、史诗、歌谣去论证原始社会的生活、制度。人民的语 言艺术,在这里发挥着远古历史证人的作用。我们今天要比较确切地知道我国远古时代 的制度、文化和人民生活,就不能不重视那些被保存在古代记录上或残留在现在口头上 的神话、传说和谣谚等。”[17]这个《发刊词》除充分地估价了民间文学的文艺作用即 教育作用和审美功能外,特别阐述了民间文学的认识作用,是力求兼顾到民间文学作为 文艺创作的源泉和参照与作为学术研究的资料这两个方面的功能的。到1957年5月号的 《编后记》中还理直气壮地提出批“左”,说“‘左’倾教条主义在民间文学的各种有 关工作——搜集、整理、编辑、出版、研究、教学……中都起着作用。”但当反右运动 开始后,“左”的声音和做法不断升级。主要作为人类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也必须“ 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搜集和研究中所运用的方法,基本上堕入了庸俗社会学 的和文艺学的观点和方法,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作家文学,对于民间文学作品的分析研究 ,也往往只限于对主题思想、教育意义的阐释和演绎。《民间文学》被用来作为政治宣 传的工具,从发表《狼外婆》的故事以配合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斗争,到发表 《兄弟分家》故事以配合宣传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发动新民歌运动以配合“三面红旗”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大政治运动,到组织创作新歌谣去配合 国际上反修反帝斗争……使中国民间文学缺乏自觉的学科意识。
民间文学是群众中传承的口头文学,与作家文学相比,在创作上往往是不自觉的。它 与一个民族和地区的民俗生活、信仰、生产方式等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大多数国家的 学者把民间文学看作是民俗的一部分或与民俗有密切联系的精神现象。我国则把民俗学 批评为资产阶级的科学,把民俗学的学者斥为资产阶级学者,在研究民间文学作品时完 全不顾其与民俗的关系,更无视人类思维、语言、巫术等对民间文学的影响,而把它作 为一种纯粹的文学现象来对待,显然是进入了误区。这种倾向的造成,固然是与片面地 理解毛主席的《讲话》和苏联经验有关,而在“左”的思想下,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一般 文学创作,把它当成“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的思想泛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二、民间文学界的几次大讨论
(一)关于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
“搜集整理”一词在《民间文学·发刊词》里第一次以官方文章的形式出现,此后便 被广泛运用于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中。但当一篇口述作品被记录下来后,搜集者在对其 作加工整理时,其幅度有多大,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量”的规定。加之从事民间文 学搜集的人又多是从文学的营垒里过来的人,而他们在加工整理民间作品时,为适应政 治的或教育的需要,往往拔高作品的主题,篡改作品的内容情节,用知识分子的语言代 替讲述者的口语,其结果弄得面目全非。这种状况的加剧,就在民间文学界引发了一场 大讨论。最早出现的争论是围绕着当时中学课本中选用的《牛郎织女》一文展开的,李 岳南肯定和赞赏整理编写的成功[18];刘守华则批评故事中对人物心理的细致入微的刻 画,不符合民间作品的艺术风格。[19]继而刘魁立在《民间文学》1957年6月号发表《 谈民间文学的搜集工作》,除阐述自己的见解外,还对董均伦、江源的做法有所非议, 于是引出了董、江二人的答辩。一场讨论从此展开。许多从事搜集和研究工作的同志, 如朱宜初、陈玮君、巫端书、陶阳、张士杰、李星华,以及1959年云南省参加搜集整理 叙事长诗歌的一些同志也都参加了讨论。1961年,毛星在《民间文学》第4期上发表《 从调查研究说起》,贾芝在《文学评论》第4期上发表《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 题》,系统地发表了对“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阐释意见。讨论文章结集而成《民间 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1集。[20]但实际上,讨论还在发展。到1963年,《民间文学》 和《奔流》上还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不仅有张士杰谈义和团故事搜集整理和创作的经 验(《民间文学》1963年第1、2期),有陈玮君的《必须跃进一步》(《民间文学》1963 年第3期),也有李缵绪和谢德风关于《游悲》的整理的讨论(《民间文学》1963年第2、 6期)。讨论继续延伸到了近现代革命题材的传说故事的搜集整理问题领域。中国民间文 艺研究会研究部于1963年邀请河南、四川、广西、江苏、安徽、吉林6个省的搜集研究 者,就此举行了一次座谈讨论,各省参加者不仅有经验总结发言,还各自都提供了若干 传说故事的记录稿和整理稿,以供研究讨论。这次座谈会上提供的文章和记录或整理稿 ,汇编为《民间文学参考资料》的第6辑(1963年8月)和第7辑(1963年9月)两辑。应当说 ,搜集整理问题的讨论,是学科意识提高的一个表现。
(二)关于文学史的主流问题的争论
贬低民间文学作为文化史现象的价值以及贬低民间文学作为口头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 值的观点,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屡见不鲜。胡风在建国初期向中共中央就文艺问题提出 的意见书里说民间文艺是封建文艺,对其持贬低甚至否定态度。尽管作为政治问题对胡 风进行的批判和监禁已经得到了平反,但他对民间文艺问题的见解,仍然不能不认为是 错误的,是不能赞同的。在当时的文艺界和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当然不止胡风一人。从 而引出了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的讨论。最早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是陆侃如发表在《 文史哲》1954年第1期上的《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一文。到“大跃进”时,出版 了以民间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两部著作:北京大学中文系55级 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集体编写的《中国民间文学史》 。作者们提出了民间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和“正宗”的口号。对这两部书的出 现,报刊上充满了一片赞美之词,同时(1959年)也围绕着“主流”问题展开了争论。《 光明日报·文学遗产》、《解放日报》、《文汇报》、《文学评论》、《文史哲》、《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复旦学报》、《读书》等报刊都发表了许多文章。中国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召开过讨论会。被称为“红色文学史”的学生著作是 新生事物,但“主流”论和“正统”论的提出,显然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左”倾幼 稚病的产物。尽管在这种“左”的思潮面前,许多知名学者不愿意去硬碰批评,但还是 有许多学者发出了不同的声音。《解放日报》1959年3月19日发表程俊英和郭豫适的《 应该把作家文学视为“庶出”吗——“民间文学正宗说”质疑》,《光明日报·文学遗 产》1959年4月5日发表乔象钟的《民间文学是我国文学史的主流吗?》,《光明日报· 文学遗产》1959年4月19日发表刘大杰的《文学的主流及其他》后,何其芳在《光明日 报·文学遗产》1959年7月26日起连续三期发表了《文学史讨论中的几个问题》。到此 ,“主流”论就告结束了。
(三)关于民间文学范围界限问题的讨论
第一次提出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问题的,是克冰(连树声)在《民间文学》1957年5月号 发表的《关于人民口头创作》一文。到1958年新民歌运动起来之后,又出现了群众创作 的新故事。新民歌与新诗的界限模糊了。新故事与传统故事之间哪些属于继承,哪些属 于创新?人人作诗,人人画画,人人唱歌,农民知识分子化,共产主义很快就要来到了! 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不是很快会“合流”了吗?这些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新 问题”历史地提到了民间文学研究者们的面前。1961年4月和11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 会研究部与《民间文学》杂志联合召开了两次“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范围界限问题讨 论会”,并在刊物上陆续发表文章。来自一些大学的民间文学教师,许钰、段宝林、朱 泽吉、义龙、吴开晋和李文焕等,在会上发言;贾芝、天鹰、巫瑞书、陈子艾、王仿等 发表了文章,都对“新事物”持肯定态度。所谓社会主义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问题,包 括:第一,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特征;第二,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的范围界限与 合流问题;第三,新民间故事问题。[21]在头脑发昏、思想膨胀的情况下,认为民间文 学和作家文学会很快合流的想法,如同“一觉醒来就进入了共产主义天堂”一样,是多 么天真多么荒谬呀!这个问题,始作俑者是周扬,他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 里说:“诗歌和劳动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基础上重新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 义上,新民歌可以说是群众共产主义文艺的萌芽。”研究者们正是从这里出发,去想象 民间文学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合流的。到1960年8月,讨论中出现 了尖锐的意见分歧,问题再次摆到了周扬面前。他说:“总的趋势是要合流的,但合流 的时间有多长?当然是要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民间文学、民间文艺是一个历史的范畴 。它同人民和历史的范畴一样,同历史上发生的任何事情一样,有它的发生,也有它的 消灭。民间文艺将来是会没有的。要搜集新民歌,也要搜集旧民歌。毛主席说,民歌新 的要搜集,旧的也要搜集。毛主席非常重视旧民歌。因为旧民歌里面有很多宝藏。(民 研会)既然是研究会,还是要强调搜集工作,强调研究工作,新旧都要,新的要搜集, 旧的要搜集,新的有个范围,旧的也有个范围。……正是因为发展中的民间文艺就在群 众创作里头,包含了许多新的不定性的民间文艺,因此民间文艺研究会应当去重视它, 推动它,但不能把推动群众创作作为全部任务,因为它还要去搜集、研究过去的……它 是从研究新旧时代的民间文艺,用研究的成果去推动。”[22]经过两年多时间,周扬显 然冷静下来了,他的话讲得科学多了。
(四)关于民间文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讨论
民间文学与宗教信仰的关系十分密切。有些古老的作品,甚至是与宗教糅合在一起难 解难分的。在搜集整理民间文学作品时,遇到有关宗教的情节,如图腾信仰、神灵人物 、宗教氛围等,为了避免惹来麻烦,往往会被搜集整理者无端地删去或改编,这就给读 者一个虚假的文本,给研究者造成迷误。讨论是在昆明的《边疆文艺》杂志上开展的。 该刊自1961年4月、5月号至1962年10月号,先后就这个问题发表了5篇文章。争论是由 陈戈华的《泛谈宗教与文学》引起的。讨论涉及到五个重要问题:第一,关于对宗教的 理解;第二,关于宗教对文学的作用问题;第三,关于民族民间文学神话中的神和宗教 中的神的问题;第四,关于宗教与民族民间文学的关系问题;第五,关于宗教文学的产 生问题。[23]这次讨论是在坚持“宗教是人民的鸦片烟”论断的前提下发表意见,其局 限性是显而易见的。这次讨论的积极作用是提出了和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宗教对文学的 发展既有消极的作用,也有积极作用;承认了不是任何宗教和任何时期的宗教对文学的 影响都应该予以否定。宗教的神与神话中的神,没有明确的界限,但也不可相提并论, 有时二者是对立的。这无疑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态度。
(五)关于“花儿”的“来龙去脉”的讨论
“花儿”是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的一种民间对唱歌曲形式,为当地汉、回、撒拉 、藏、东乡、裕固等民族的共有民歌。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的浮夸风与虚假风,渐而为 人们所认识,因而从1961年起,青海省“花儿”研究者们围绕着民歌如何发展和提高的 问题展开了讨论。《青海湖》1961年第9期发表黄荣恩的《青海“花儿”的来龙去脉》 后,讨论渐而进入了“花儿的来龙去脉”即“花儿”源流的层次。接着,该刊第12期发 表了赵村禄的《“花儿”的来龙去脉再探》,《青海日报》1962年3月10日发表刘凯的 《可疑的和可信的》,《青海湖》1962年第6期发表南京大学教授孙殊青的《“花儿” 的起源——“花儿”探讨之三》,《青海日报》9月9日发表黄荣恩的《河州是“花儿” 的正宗质疑》,《青海日报》11月7日发表刘凯的《“花儿”与“叶儿”》,《民间文 学》1962年第6期发表王浩和黄荣恩的《“花儿”源流初探》,《青海湖》1963年第1期 发表刘凯的《再谈“花儿”与元代“散曲”》等。这次关于“花儿”的源流的讨论持续 了两年,虽然文章大多发表在青海的报刊上,“花儿”的流行区甘肃省的研究者和文化 界没有响应,就其深度和影响来讲,是具有相当学术水平的。20年后,甘肃民间文艺研 究者魏泉鸣在《青海民族学院学报》上发表《青海对花儿来龙去脉的探讨》的文章,认 为这次讨论“为尔后的花儿学研究,开了良好的先河”,可看作是这次讨论的一个总结 。青海省民间文学界20世纪60年代关于“花儿”的讨论,作为“花儿”研究的开端,走 在其他民族和地区的民歌研究的前面。
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开拓
(一)建国之初到1957年反右斗争为第一个阶段
这一阶段中,民间文学的研究和评论甚为活跃,在理论研究和评论的队伍里,既有民 间文学专家、历史学家,也有从事一般文学研究的理论家,在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 尽管当时基本上或多数是在社会学的、文艺学的框子里进行的,但其发展状况是良好的 、平稳的、有创造性的。《光明日报》1950年3月起开辟《民间文艺》专版,每周一期 ,发表民间文艺作品和研究文章。以发表理论文章为主的《民间文艺集刊》也于1950年 11月在北京创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主编的《文艺集刊》第1册于1951年9月29日出版 。相继出版的民间文学理论著作有:钟敬文编《民间文艺新论集》(中外出版社1950年8 月,北京);赵景深著《民间文艺概论》(北新书局1950年,上海);钟纪明著《向民间 文艺学习》(华东新华书店1950年10月,上海);袁珂《中国古代神话》(商务印书馆195 1年4月);钟敬文著《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 51年,北京);钟敬文著《歌谣中的觉醒意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2年9月,北京) ;唐因著《谈民间歌谣》(人间书屋1952年,北京);钱静人著《江苏南部歌谣简论》( 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李岳南著《民间戏曲歌谣散论》(上海出版公司1954年);天 鹰著《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文化生活出版社1954年);何满子《神话试论》(上海 出版公司1957年);匡扶著《民间文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1957年);天鹰著《中国 古代歌谣散论》(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王焕镳著《先秦寓言研究》(古典文学 出版社1957年);李岳南《神话故事、歌谣、戏曲散论》(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等。
重要文章有:钟敬文的《对于民间文艺的一些基本认识》(《光明日报·民间文艺专刊 》1950年3月1日)、《民间文艺学上的新收获》(《新建设》1951年5卷1期)、《略谈民 间故事》(《民间文学》1955年10月号),严辰《谈民歌》(《人民文学》1950年6月1日2 卷2期),何其芳《论民歌》(《人民文学》1950年11月1日3卷1期),孙作云《说羽人— —羽人图、羽人神话及飞仙思想之图腾主义的考察》(《国立沈阳博物馆筹备委员会汇 刊》1951年),孙剑冰《<阿诗玛>试论》(《文学研究集刊》1956年第1期),毛星《不要 把幻想与现实混淆起来》(《民间文学》1956年4月号),乌丙安《第二次国内革命老根 据地歌谣简论》(《教学研究集刊》1956年第1期),徐旭生《禹治洪水考》(《新建设》 1957年第7期),顾颉刚《息壤考》(《文史哲》1957年第10期)。
这一阶段的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从选题上看,多数属于阐释民间文学的社会历史价值 的;也有的属于民间文学专题研究,如民歌、神话、叙事诗等,这方面的文章数量虽少 ,却达到了较高的水平。钟敬文、何其芳、天鹰、孙剑冰、孙作云的著作或文章,在各 自不同领域里带有开拓性的作用。建国初期在神话研究方面,几乎同时出现了两部专著 :一部是袁珂的《中国古代神话》,一部是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袁珂的书 于1951年初即出版,且颇受到读者欢迎,一版再版,到1956年已印行67000册之多。丁 山的书稿于1950年12月15日完成后,一直未能出版,直到1961年2月才得以以龙门联合 书局(科学出版社副牌)的名义作为“内部资料”出版,而且第一次印数只有1300册。这 两本神话研究著作在研究方法上各有特点。袁著以夹叙夹议的方式,归纳梳理散乱庞杂 的中国古神话资料,使其系统化,以求恢复中国神话固有的“旧观”,同时作者还力求 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阐发其文化的内涵,探讨其历史化的原因,从而成为我国第一 部系统的中国神话全书。丁著则以比较神话学和比较语言学的方法,考订和论证包括史 前神话、夏、商周、秦诸代的世系传说在内的中国古代神话与宗教的关系和演变,从而 探索中国文化的来源。这两本神话研究著作,很自然地成为建国初期中国神话学的代表 作。这个时期研究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是,对于民间文学的一些重要问题,特别是基本 的问题(例如民间文艺的本质、它的特征、境界及演变的规律等)还没有人着手去做深入 的探究。而“有些讨论问题的文章,大概由于作者一般理论修养的缺乏和钻研精神的不 够,多少不免犯着材料主义或主观主义的毛病。他们往往在文章里罗列了许多材料,却 没有什么新颖精确的解说,论断,或者不仔细研究资料和相关的各种情况,只凭着一些 社会科学上的抽象原理、原则,就大意地下判词。”[24]
(二)1958~1966年为第二阶段
1956年提出“双百”方针后不久,就开始了反右斗争,正常的学术研究和秩序被打断 。尽管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搜集工作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民间文学的学术研究却一直 滞后,学术性的研究被对新民歌的虚夸赞扬所掩盖。三年困难结束,中央提出“调整、 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文艺界相应地于1962年出台了《文艺八条》,调动一切 积极力量,一向被当作资产阶级学者的老专家顾颉刚、魏建功、常惠、容肇祖、周作人 、杨成志等,也被请出来参加活动,写文章。(注:《民间文学》1962年第一、第二和 第六期集中发表了“五四”歌谣运动老专家的文章。)过去宣传的是延安文艺座谈会把 我国民间文学工作“引上了无产阶级的轨道”,1962年却能够举办《歌谣》周刊创刊40 周年的活动,也承认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是我国歌谣运动的肇始。理论研究因而出现了 一个小小的高潮,以往仅限于政治性和社会性研究的狭隘局限也得到了一定的拓宽。毛 泽东1963年、1964年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使文艺领域的阶级斗争形势严重加 剧,文艺整风迅即开始,短暂的宽松局面很快就结束了;1966年则更是爆发了史无前例 的“文化大革命”。
这一阶段出版的理论著作有: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55级学生编著《中国民间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作家出版 社1958年),《向民歌学习》(作家出版社1958年),策·达木丁苏荣著、白歌乐译《格 斯尔的故事的三个特征》(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58年),安旗著《论诗与民歌》(作家出 版社1959年),天鹰著《扬风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天鹰《1958年的中国民歌 运动》(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谭达先著《民间童谣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 、《民间文学散论》(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李岳南著《与初学者谈民歌和诗》(上 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民歌作者谈民歌创作》(作家出版社1960年),路工等《白茆 公社新民歌调查》(上海文艺出版社1960年),丁山著《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龙门联 合书局1959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文艺 出版社1962年),张紫晨著《民间文学知识讲话》(吉林人民出版社1963年),高亨《上 古神话》(中华书局1963年),贾芝著《民间文学论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
报刊文章值得注意的有:萧三《<革命民歌选>序言》(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汪玢 玲《试论长白山区人参的传说》(《吉林师范大学学报》1959年第4期),罗永麟《试论< 牛郎织女>》,王一奇《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化身》(《民间文学》1960年第5期),马昌 仪《研究被压迫民族民间文学的珍贵文献》(《民间文学》1962年第1期),刘守华《谈 动物故事的艺术特点》(《民间文学》1962年第3期),陶阳《琶杰的诗歌艺术》(《民间 文学》1962年第3期),天鹰《<哭嫁歌>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载《哭嫁歌》,上海文艺 出版社1962年),贾芝《民间故事的魅力》(《民间文学》1962年第12期),钟敬文《晚 清革命派著作家的民间文艺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2期),许钰《民间文 学中巧匠的典型》(《民间文学》1963年第2期),刘锡诚《马克思恩格斯与民间文学》( 《草原》1963年第2期),袁珂《关于舜象斗争神话的演变》(《江海学刊》1964年第2期 )和《神话的起源及其与宗教的关系》(《学术研究》1964年第5期)等。
这期间民间文学研究重点表现为对歌谣、特别是新民歌的研究与阐发。文章很多,好 的却少见,能够在历史上留存下来的则更少,包括郭沫若和周扬的《红旗歌谣·前言》 在内。在歌谣研究方面用力最多、成绩最显著的是天鹰。他的《1958年民歌运动》固然 是趋时之作,而《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却是一部探讨各类歌谣的艺术特征和表现手 法的专著,时有真知灼见。他对哭嫁歌的研究也富有新意。诗人萧三为其所编的《革命 民歌选》所写的序言,较早地预示了一股民间文学潮流的出现,文章写得有思想有文采 。谭达先远离政治斗争的中心北京,倒能潜心作些学问,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散论, 一本专著,实属难能可贵。故事研究方面,显然较第一阶段有所进步,对以《义和团故 事》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传说的研究评介固然带有有失客观的政治色彩,毕竟还是达到 了一定的成就。贾芝、毛星、罗永麟、汪玢玲、刘守华对故事传说的研究,虽然没有脱 出一般文艺学的分析的范畴,但都有发别人之所未发之论,是值得肯定的。神话研究的 进展相对缓慢,甚至还徘徊在二三十年代《古史辨》开创的考据思路上。只有袁珂另开 一路,着手进行神话的理论研究,除以古典神话为对象外,开始关注在民间流传的口头 作品和若干理论问题(如与宗教的关系)。史诗和叙事诗的搜集成就较大,带动了理论研 究的前进,这在建国前的中国是没有的。从历史的角度检讨起来,仍然是属于工作性和 搜集整理问题的居多,而属于探讨史诗和叙事诗内部问题的嫌少。民间文艺学史的研究 处于起步阶段。
标签:文学论文; 民间文学论文; 青海日报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钟敬文论文; 神话论文; 青海湖论文; 民谣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