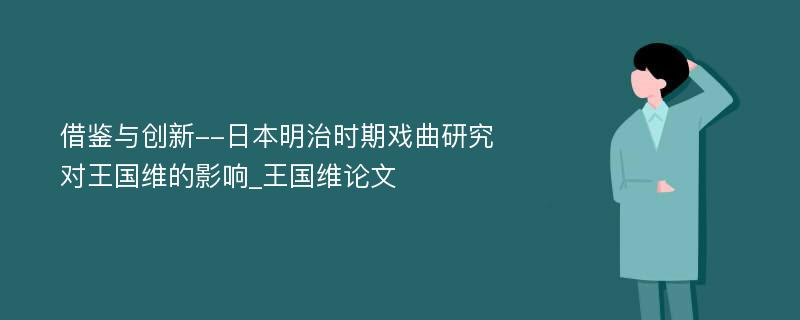
借鉴与创新——日本明治时期中国戏曲研究对王国维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治论文,日本论文,时期论文,王国维论文,中国戏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07年,王国维有感于戏曲在中国文学中处于最为“不振”的地位,而从词学转向曲学。此后四五年间,撰成《曲录》、《戏曲考原》、《古剧脚色考》等一系列著述。1912年冬天,在日本京都,更以三月之功,完成《宋元戏曲史》一书。他在序中说:“凡诸材料,皆余所搜集;其所说明,亦大抵余之所创获也。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①
王国维的工作,在日本也有着很大的影响。盐谷温说:“王氏游寓京都时,我学界也大受刺激,从狩野君山博士起,久保天随学士、铃木豹轩学士、西村天囚居士、亡友金井君等都对斯文造诣极深,或对曲学的研究吐卓学,或竞先鞭于名曲的绍介与翻译,呈万马骈镳而驰骋的盛观。”②
以上所说的,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的一个方面;而不为人知的另一面,则是在日本明治时期(1868-1912),学者就已经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展开了对中国戏曲的研究,他们的著述,对王国维的戏曲研究,曾发生过重要影响。今试述于后,以求正于方家。
一
日本近代学术的变化,是与“明治维新”紧密相关的。1868年,日本结束幕府时代,实施文明开化、追慕西方的政策,其教育体系与思想学术体系全面接受了西方的模式。到明治二十年(1887)以后,与明治维新同步成长起来的一代年轻人开始登上舞台。在了解西方学术文化的同时,加强东方文化研究的呼声日益高涨,从而出现一股“复兴汉学”的热潮。这种“复兴”并不是简单地复兴幕府时代的汉学,而是以西方学术为参照,对汉文学的一种重新认识。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获得了近代学术意义上的开拓。
虽然戏剧在中国本土向来不登大雅之堂,但在西方,自古希腊时期开始,就一直占居崇高的地位。以故,早在18世纪,西方学者就开始关注中国戏曲,并予以翻译和介绍。至19世纪中叶,从杂剧到南戏,出现了英、法、德等多种语言的译本③。这使自以为比西方人更精通中国文学的日本人深受刺激。一些对西方学术有所了解又对中国文学十分熟悉的年轻学人,开始涉足中国戏曲领域,他们张扬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相提并论的观点,把戏曲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部分加以研究,从而开启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大门。
1891年3月14日,日本著名汉诗人、东京专门学校(1903年以后改名为早稻田大学)讲师森槐南(1863-1911),在东京的“文学会”上,以“中国戏曲一斑”为题,作了一次专题演讲。两天后,东京《报知新闻》以《中国戏曲的沿革》为题,用两千余字的篇幅,刊出演讲的梗概。其内容则如报道的标题所示,概述了中国戏曲的变迁史。这是日本第一个中国戏曲的专题演讲。
同年7月,森槐南在《支那文学》杂志上连载《西厢记读法》一文。这堪称是日本近代学术史上第一篇中国戏曲研究论文,也是近代日本第一个《西厢记》译本(未载完)。同时,森槐南还在课堂上讲解了《桃花扇》等名剧。早稻田的学生柳井絅斋(1871-1905)因为听了森槐南的精彩讲授,深感兴趣,便为《桃花扇》的每一出都撰写了情节概要,题为《桃花扇梗概》,1892年3月开始在《早稻田文学》杂志上连载。因此,森槐南是第一位在日本的大学讲坛上讲授中国戏曲的学者。
此后至明治末(1912)的二十年间,日本的学者、作家纷纷涉足中国戏曲,或作解题,或编写概梗,或作训读翻译。从元杂剧(特别是《西厢记》)、《琵琶记》,到《牡丹亭》、《长生殿》、《桃花扇》、《笠翁十种曲》、《红雪楼九种曲》、《吟风阁杂剧》,以及北京、旅顺等地的演剧,戏曲所用的音乐、器乐及其与戏剧变迁的关系,均已有专门论述或译解。源于西方戏剧的悲剧、喜剧等学术概念,也被很自如地运用到了对中国戏曲的论述之中。俳优与中国戏剧的关系,词与曲的变迁,宋杂剧、金院本与元杂剧的关系等,也都有所讨论。
1895年1月,当时正走红的小说家幸田露伴(1867-1947)撰写了《元时代的杂剧》这篇数万字的长文,从《太阳》杂志创刊号开始,分数期连载,成为日本对元人杂剧专题介绍与研究的开端。露伴在文中译介了十五种元杂剧,并且特别推崇关汉卿的《窦娥冤》,以最大篇幅介绍其情节内容,尤为赞许其“悲壮”之美。
1897年6月,年仅二十七岁的笹川临风撰成《中国小说戏曲小史》(东京:东华堂),是为第一部中国小说戏曲史。笹川临风(1870-1949),名种郎,1896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史学科。严格地说,临风此时的学术积累无多,故此一史著匆促成书,还称不上是一部成熟的著作。随后,笹川临风与四位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岭云、大町桂月、白河鲤洋一起,以三年时间编纂出版了十六卷(册)本《中国文学大纲》(东京:大日本图书株式会社,1897-1899)。此书各卷独立成册,其中引人注目的是笹川临风撰写的《汤显祖》(1898)和《李笠翁》(1897)两卷,不仅较此前的《小史》明显成熟,而且《汤显祖》一书的前两章,题为“中国戏曲的起源及发达”和“中国戏曲的性质”,已近乎元明戏曲的简史。临风还出版了一部《中国文学史》(帝国百科文库第九编,东京:博文馆,1898),第一次将戏曲小说作为元明清文学的主体部分,列入文学史。此外,临风当时所刊出的论文,也以中国戏曲小说的研讨居多,这些论文随后结集为《雨丝风片》,由东京博文馆出版(1900)。这几种著述合而观之,可见笹川临风对中国戏曲史的总体看法,其中娴熟地使用了悲剧、喜剧等美学观点,并依照个人的理解,对中国戏曲史作出评价。
1899年6月,森槐南受聘为东京帝国大学讲师,从而第一个在帝国大学的讲堂上讲授了中国戏曲。他在授课时所用的讲义《词曲概论》,前半论词的变迁,后半论曲的流变,实是一部简明中国词曲发展史。其中对唐宋俳优及演剧的研究,与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颇有重合之处。其论唐宋音律的变迁与戏曲九宫的形成,尤为精彩。这是王国维所不擅长的,所以在《宋元戏曲史》中未能加以讨论。森槐南于1911年3月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九。其《词曲概论》遗稿由弟子整理,1912年10月在新创刊的《诗苑》上连载,至1914年刊登完毕。它与《宋元戏曲史》在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上连载,几乎在同一时间。只是在《宋元戏曲史》的万丈光芒之下,在这本冷僻的汉诗杂志上登载的森槐南的遗著,完全被人们遗忘了,例如当今日本的中国戏曲研究者中,很少有人知道森槐南的功绩。
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戏曲研究的关注,也可以说是日本戏剧运动兴盛所发生的一种折射。明治维新之初,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方,掀起戏剧改良运动和新剧运动,把戏曲小说作为教育民众的工具。所以日本戏剧对于启蒙民智、传播西方思想,发生过重要的作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也萌生了维新变法的愿望与举措。在文学领域,随后掀起了“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运动也应运而生,走的是日本明治戏剧运动同一条路径。在戏曲所具有的教育功能被放大的同时,戏曲史的研究也开始受到关注。刘师培撰写了《原戏》一文,初刊于1904年12月《警钟日报》,再刊于《国粹学报》第三年第九号(1907年10月),探讨了戏曲的起源;又撰《舞法起于祀神考》,刊于《国粹学报》第三年第四号(1907年5月),讨论舞与巫的关系。1906年3月,在横滨出版的《新民丛报》,在“译述”栏登了渊实(廖仲恺)的《中国诗乐之迁变与戏曲发展之关系》的长文,《丛报》主编梁启超为之作跋,谓“承著者寄稿,自云从东文(日文)译出,惟未言原著者为谁。以余读之,殆[翻]译者十之七八,而译者所自附意见,亦十之二三也。其中所言沿革变迁及其动机,皆深衷事实,推见本原,诚可称我国文学史上一杰构”。此外,日本学者宫崎来城(1871-1933)1905年在《太阳》杂志上连载的《清朝的传奇及杂剧》论文,被翻译刊登在1908年3月出版的《月月小说》杂志第14号上,改题作《论中国之传奇》,编者称赞此文,“于吾国传奇之优劣,月旦甚详”。
但戏曲小说要获正统士大夫阶层的认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03年,上海中西书局翻译出版了笹川种郎的《中国文学史》,改题为《历朝文学史》。1904年,林传甲(1877-1922)编就《中国文学史》,作为“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使用。他在卷首声明:“传甲斯编,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此书在体例上模仿笹川临风的《中国文学史》,但价值取向则大异。林传甲认为:“日本笹川氏撰《中国文学史》,以中国曾经禁毁之淫书,悉数录之。不知杂剧、院本、传奇之作,不足比于古之《虞初》,若载之风俗史犹可。阪本健一有《日本风俗史》,余亦欲萃‘中国风俗史’,别为一史。笹川载于《中国文学史》,彼亦自乱其例耳。况其胪列小说戏曲,滥及明之汤若士、近世之金圣叹,可见其识见污下,与中国下等社会无异。”④另据《奏定学堂章程》之《奏定各学堂管理通则》,其中“学堂禁令章第九”规定:“各学堂学生,不准私自购阅稗官小说。”⑤这里可以看到笹川临风的《中国文学史》在中国的影响,但戏曲小说仍然难以得到正统学者的认可。
以上这些,构成了王国维开始转向戏曲研究时的学术史背景。
二
从王国维早年求学经历来看,他是在日本学者的思想启蒙下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的。
1897年5月,罗振玉(1866-1940)在上海创办《农学报》,邀请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藤田丰八担任日本及西方农书的翻译。次年3月,在藤田丰八的创议下,罗振玉与友人合资创办“东文学社”。这是中国私人开办的第一所日语学校。
王国维曾两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1898年2月,时年二十二岁的王国维,赴上海接任《时务报》书记的职位。3月,王国维报名成为东文学社的首批学生,每天下午去东文学社学习三个小时日语。12月,罗振玉邀王国维担任东文学社庶务,从此,王国维在罗振玉的提携下,走上学术之路。
1899年5月,东文学社又聘请藤田丰八的同学田冈岭云出任助教。田冈岭云(1870-1912),名佐代治,1894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汉学科,当时已经在哲学与文学评论等领域卓有建树。
田冈岭云执教王国维仅一年(1899年5月至1900年5月,因肺病回国休养),但他的思想与著述,对王国维影响很大。王国维说:“是时社中教师为日本文学士藤田丰八、田冈佐代治二君。二君故治哲学,余一日见田冈君之文集中,有引汗德(康德)、叔本华之哲学者,心甚喜之。顾文字睽隔,自以为终身无读二氏之书之日矣。”(《三十自序》)在两人的劝导下,王国维拜藤田、田冈为师,兼学英文。
田冈岭云对王国维的影响,并不只是从中知有康德、叔本华二氏这么简单。田冈岭云当时已经出版有《岭云摇曳》(1899年3月)、《第二岭云摇曳》(1899年11月)和《云的碎片》(1900年4月)三部文集。据日本学者须川照一的研究,田冈岭云对青年王国维的思想有过多方面的影响⑥,《云的碎片》中的《美与善》一文,是田冈岭云的代表作之一,直接对青年王国维的《孔子之美育主义》(1904)和《人间词话》(1908)发生了重要影响。田冈岭云与王国维都反对把文学作为政治或道德的手段,反对庸俗的功利主义文学观,明确地指出文学有自己的立场。从两人对自己的人生经历的陈述,也可见其因袭的轨迹。田冈岭云剖析自己,称:“欲为哲学家,吾过于热情;然则欲为诗人,吾又过于冷静。则既不能为诗人,又不能为哲学家,呜呼,一如骈拇伛偻之畸形,造物以畸吾之才以戏吾欤?”⑦后来王国维则说:“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吾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⑧两者的承袭十分明显。
此外,日本的研究者已经指出,王国维的“境界说”,明显受到田冈岭云的启发⑨,只是中国本土的研究者对此说未加留意,单纯从古人的著述中去寻其源头而已。
藤田丰八、田冈岭云是笹川临风的前后届同学与好友,他们三人也是十六册本《中国文学大纲》的主要编纂者。他们自然会向中国的友人印证自己的成果,所以,王国维当是通过这两位老师,读到整套的《中国文学大纲》,并了解到其中笹川临风写的《汤显祖》、《李笠翁》这两册关于中国戏曲的专门论述。
1902年2月,经藤田丰八安排,王国维游学东京,昼习英文,夜至物理学校习数学,为时近半年。因“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而此时为余读书之指导者,亦即藤田君也”⑩。此后遂着意于西哲著作,因得以用日文译本作参证,通其大略,并进入其“独学”时期。1904年,王国维成为《教育世界》的实际编集责任人,至1907年,借助日本学者的著述,撰写、编译了许多介绍西方哲学与文学的文字。所以,王国维早期的思想与学术,深受日本思想界、教育界的影响,已无异议(11)。
1906年后,王国维因“疲于哲学”,兴趣发生转移,热衷于填词。次年,又因“填词之成功”,“嗜好之移于文学”。他在《三十自序》(1907)中说:“因词之成功,而有志于戏曲,此亦近日之奢愿也。……余所以有志于戏曲者,又自有故。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元之杂剧,明之传奇,存于今者尚以百数,其中之文字虽有佳者,然其思想及结构,虽欲不谓至幼稚至拙劣,不可得也。国朝之作者虽略有进步,然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然目与手不相谋,志与力不相副……故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12)
同样的话语,又见于他的《文学小言》(第十四,1907):“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则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
再见于《人间词话》(第二十八条,1908):“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也。叙事诗,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故曲则古不如今(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至本朝之《桃花扇》、《长生殿》诸传奇,则进矣),词则今不如古。盖一则以布局为主,一则须以伫兴而成故。”
这三段话,表述了王国维走向戏曲的原因,同时也反映了当时他对中国戏曲的总体判断,其中明显可以看到笹川临风的影响。
笹川临风论述中国戏曲,称“论其词采虽不乏名篇,观其结构,若于戏剧之意义上观之,犹是稚气纷纷耳”(《雨丝风片》第213页;《汤临川》第70页);“专用力于曲,其弊在不重结构而沮害戏剧之进步。曲虽为戏曲之一要素,而戏曲之生命,非当在其结构耶?中国戏曲迟迟才发达,亦全因乎此”(《汤临川》第46页);“中国戏曲列之世界戏曲史上,显然逊色,固无可疑”(《汤临川》第47页)。这些观点与王国维的《三十自序》两相对看,其前后承袭,十分明显。
但另一方面,王国维“有志于戏曲”,也是有感于临风的著作难以令人满意,而国人之著述,尚未之见,才“欲作搜讨之助,补三朝之志”,以待“异日”“成一家之书”(《曲录·序》,1908)。只是王国维此时刚由词学转入戏曲,犹不敢自以为必,所以谦逊地说:“他日能为之与否所不敢知,至为之而能成功与否,则愈不敢知矣。”
到1912年底,王国维经过四五年的努力,对曲学的理解已经与初涉此一领域时全然不同,所以他充满自信地说:“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其所贡于此学者亦以此书为多。”
这里说“世之为此学者自余始”,显然王国维并不把临风的著述作为成功的戏曲史著作看待,而是直视为无物。他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以往“为此学者,大率不学之徒;即有一二学子,以余力及此,亦未有能观其会通,窥其奥窔者”。这里所说的“不学之徒”,大约笹川临风就是其中的一员。
三
从1911年11月东渡日本,到1913年元旦前后草成《宋元戏曲史》,期间王国维一直住在离京都大学不远的田中村。
当时,狩野直喜、铃木虎雄对中国戏曲研究甚为关注,与王国维时相过从。狩野直喜的戏曲研究,与王国维几乎是同时开始的。在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之前,狩野直喜已经发表了《关于以〈琵琶行〉为题材的中国戏曲》(《大阪朝日新闻》,1910年1月)、《〈水浒传〉与中国戏曲》(《艺文》,1910年8月)、《元曲的由来与白仁甫的〈梧桐雨〉》(《艺文》,1911年2月)等论文。铃木虎雄则在1910年译介了王国维的《曲录》和《戏曲考原》,并撰有《蒋士铨的〈冬青记〉传奇》(《大阪朝日新闻》,1910年8月),又有译介《鸣凤记》、《琵琶记》的想法,并撰写了初稿,不过后来因为西村天囚已着先鞭而放弃。不难想见,他们之间的交谈,可能更多地是向王国维请教,但另一方面,也为王国维了解日本学界戏曲研究的情况提供了诸多的便利。王国维与诸人来往信札中,多有烦请代为借阅图书的记载,如1912年11月18日致铃木虎雄的信:“前闻大学藏书中有明人《尧山堂外纪》一书,近因起草宋元人戏曲史,颇思参考。其中金元人传部分,能为设法代借一阅否?”(13)
关心日本学者与自己同领域的研究成果,是王国维一贯的做法。例如他1916年回国之后,兴趣转到蒙古史地研究,曾屡屡写信给神田喜一郎,请其代为寻找那珂通世、白鸟库吉这方面的著作(14)。所以,在撰写《宋元戏曲史》期间,王国维关注日本学者的戏曲研究著述,是很自然的事情。
幸田露伴的戏曲论文《元时代的杂剧》等,收入了他的《露伴丛书》(东京:博文馆,1909),王国维应当可以很方便地读到。
森槐南死于1911年3月,他的早期论文一直未能结集,所以不易读到。但1898年他与森鸥外等人在《目不醉草》杂志第27卷上关于《琵琶记》的讨论,由于西村天囚当时为翻译《琵琶记》而经常登门求教,有可能已被介绍给王国维。此外,在东京大学讲课的内容,据学生的课堂速记整理后,题作《作诗法讲话》,于1911年冬出版,其中两章,含有中国戏曲史的概要。这也是王国维可能读到过的。森槐南的《词曲概论》遗稿随后在《诗苑》上连载(1912年10月—1914年1月),前半论唐宋元明清词,后半论词如何变为曲,阐述中国戏曲的兴起及其在元明清的变迁。只是其中戏曲部分,在《宋元戏曲史》撰写时还未刊出,故王国维无法读到。诗词集《槐南集》二十八卷,森槐南殁后,由文会堂出版(1912)。铃木虎雄在1912年5月8日给王国维的信中说:“《槐南集》近者上木,谨呈一本,叱留为幸。”(15)王国维则在6月23日回信说:“《槐南集》卷帙甚富,敝国近代诗人无此巨帙,容缓缓细读。”铃木虎雄是森槐南的学生,他在明治末年关注中国戏曲研究,固然有狩野直喜的影响,但森槐南的授课与著述,对他的影响也许是更为直接的(16)。森槐南在当时日本汉诗界有填词作诗第一人之称。由于以上缘由,王国维关注到森槐南的曲学,读过他的一部分论著,也是很自然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的某些论述,或许可以得到合理的解答。
例如,王国维论“元剧之文章”,用悲剧的观念作观照,认为:“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初无所谓先离后合、始困终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公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17)
如前所说,东方学者以“悲壮”视《窦娥冤》而大加称赏,始于幸田露伴的《元时代的杂剧》一文(1895)。1910年,京都的山田茂助排印了《元杂剧二种》,收录了《汉宫秋》和《窦娥冤》。这是出于狩野直喜的安排。狩野随后在课堂上讲解元曲,即用这个排印本作为教材。而日本学者之所以关注此二剧,除了研究者个人的判断外,西方学者曾经译介此二剧,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窦娥冤》作出很高的评价,奠定此后百年间《窦娥冤》在戏曲史上的地位。但王国维并不是一开始就高看《窦娥冤》的。迟至1910年撰写《录曲余谈》时,王国维仍称:“余于元剧中得三大杰作焉。马致远之《汉宫秋》,白仁甫之《梧桐雨》,郑德辉之《倩女离魂》是也。”(18)即依然没有脱离明清以来学者的传统看法,《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剧作犹不闻焉。故王国维对此二剧的评价发生巨大转变,当是在1911年底东渡之后。
1913年夏,王国维完成《宋元戏曲史》之后不久,给西村天囚著译的自印本《南曲琵琶记》用中文撰写了序言,序中说:“我国戏曲之作,于文学中为最晚,而其流传于他国也反是。佛人赫特之译《赵氏孤儿》,距今百五十年,英人大维斯之译《老生儿》,亦且近百年;嗣是欧利安、拔善诸氏,并事翻译,讫于今,元杂剧之有译本者,殆居三分之一。余虽未读其书,然观他书所引大维斯之言,谓元剧之曲,以音为主,而不以义为主,故其义颇晦,然则诸家所趋译者,但关目及科白而已。”据1909年定稿刻印的《曲录》,其“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目下有注:“德人叔本华《意志及写象之世界》第三册诗论中,述英人大辟曾译此本于千八百十七年,在伦敦出板,迄今九十余年矣。”似此前王国维所知西人翻译元杂剧的情况,仅限于此,而至1913年,王国维所了解的情况,显然大不相同。既然王国维本人并没有读过原译本,他所得信息,实从“他书”而来。这“他书”,除了叔本华的著作外,还包括日本学者的著作。据笔者所见,森槐南、森鸥外、笹川临风等人均在所发表的有关戏曲的论文中引述过法人、英人译著。又,狩野直喜有着良好西文素养,据说其口语足以使人误以为欧洲人。王国维本人在撰写《宋元戏曲史》之前,应有机会阅读到这类日文文献,或通过与狩野直喜等人的交往而有所知闻。所以我们不难想见,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对《窦娥冤》、《赵氏孤儿》等作品予以高度评价,与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对此二剧加以推崇有关,即他对西方学者观点的具体了解,主要是通过日本学者。
今人多以为王国维是第一位运用“悲剧”理论来评论中国戏曲的学者,这并不符合事实。笹川临风才是始作俑者。临风称:“元杂剧中有悲剧,如《西厢记》亦有惊梦一折,离而不合,散而未聚,洵属异色。……然《西厢记》素是单纯的情话,歌彼人生之行路难,以及浮世之辛酸,义理人情、境遇动机,终不得与陷于大破裂之悲剧相等同。这般悲剧,于中国未之见。”尤其是入明以后,“不见悲剧之沉痛,而多是喜剧。既无大破裂,亦无惨绝悲绝,其终即大团圆,聚而散、离复合”(《汤临川》第49-51页);故“中国戏曲列之世界戏曲史上,显然逊色,固无可疑”(《汤临川》第47页)。如此看来,前引王国维所述元剧中有悲剧而明剧无之,称《窦娥冤》、《赵氏孤儿》等“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显然是受到临风的影响,只不过他不完全同意临风的结论,所以尽力为中国戏曲在世界悲剧之林中争得一席地位。显然,《宋元戏曲史》中的判断,与1907年王国维初涉戏曲时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国维又说元剧“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明以后其思想结构,尽有胜于前人者”。笹川临风则称“论其词采虽不乏名篇,观其结构,若于戏剧之意义上观之,犹是稚气纷纷耳”(《雨丝风片》第213页;《汤临川》第70页);临风又谓入明后,作者稍用力于结构,如《牡丹亭》之结构颇出人意外,其间寓有作者哲学的思考。至李笠翁,曲虽不及《西厢》、《还魂》,而结构布置则过之云云。两者相较,若合符节。
四
中国戏曲史之以“戏曲”为名,可以说是因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刊行而得以确立的。但选用“戏曲”一词作为中国传统戏剧的总名,其实也是“出口转内销”的结果。
“戏曲”一词,今知最早出自元代刘埙的《水云村稿·词人吴用章传》,指的是诞生于浙江温州的南曲戏文。但在明清时期,此词用得并不普遍。明清戏曲评论家更常用的是乐府、院本、杂剧、南戏、南词、传奇、花部、乱弹等词;其研究戏曲,则称“曲律”(王骥德)、“剧说”(焦循)、“曲话”(李调元),其述观看戏曲,则用“观剧”、“听戏”等词。
以“戏曲”一词代指整个中国戏剧,当是始于明治时期的日本人。日本学者最初是用“戏曲”一词来称呼本国戏剧与西方戏剧。用“戏曲”称西方戏剧,如1886年大阪刊印的《罗马盛衰鉴:沙吉比亚戏曲》、1887年松久定弘译介的《独逸戏曲大意》等,均是其例。用以称呼日本演剧著述,如1892年刊《戏曲从书》,所刊凡十八种,收录近松左卫门等人的剧作;又如1894年诚之堂刊《江户时代戏曲小说通志》、庚寅新志社刊印依田学海的《新评戏曲十种》等,也可见其一斑。在明治二十年代(1887-1896),汉学家开始涉足中国文学史,也就很自然地用“戏曲”一词来称呼中国戏剧。当时的汉学科目中有小说戏曲之目,所设讲义则归入“戏曲小说门”。到了20世纪初期,中国本土学者开始关注戏曲研究,因受日本著述的影响,也自然而然地移用“戏曲”一词。如王国维撰《戏曲考原》,著《宋元戏曲史》,都是如此。由于这一称谓在中国“古已有之”,所以直到现在,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最初是经过日本学者选择而被固化的词汇。
从1902年到1907年,王国维在编刊《教育世界》杂志时,以编辑与主笔的身份,通过日文著作,大量译介了西方和日本的思想学术著述,因而对译述时如何选用与创造词汇,也即“新学语”问题,深有感触。他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说:
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学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于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中间之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好奇者滥用之,泥古者唾弃之,二者皆非也。夫普通文字中,固无事于新奇之语也,至于讲一学,治一艺,则非增新语不可。而日本之学者既先我而定之矣,则沿用之何不可之有,故非甚不妥者,吾人固无以创造为也。……余虽不敢谓日本已定之语必贤于创造,然其精密则固创造者之所不能逮(日本人多用双字,其不能通者,则更用四字以表之,中国则习用单字,精密不精密之分,全在于此)。(18)
这里虽然说的是西文译词所用新学语的问题,但在移用日本人创造的词汇这一点,他显然是持一种开放的态度的。
19世纪后期的日本,由于认真学习西方思想,模仿西方制度,在学术文化领域,远远走在中国的前面。近代学术史上关于中国的第一本文学通史、断代文学史、戏曲史、小说史、赋史……实是由日本学者首先草创的。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的先驱,也大多曾留学、行走于日本,或借道日本以取法西方,因而明治学者的著述与观念,对20世纪前期的中国学术影响至深。王国维在研究戏曲之初受到日本学者的启发,与他的《曲录》、《宋元戏曲史》等著述给日本学者以巨大影响,原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中可以窥见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一斑。
注释:
①《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版,第3页。
②盐谷温著、孙俍工译《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上海开明书店1933年版,第170-171页。
③参见孙歌等著《国外中国古典戏曲研究》第一章第三节“中国古典戏曲在西方”,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30页。
④林传甲《京师大学堂国文讲义·中国文学史》,编成于1904年,今引文据广州存珍阁1914年版,第24页。
⑤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五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482页。
⑥须川照一《王国维与田冈岭云》,《王国维学术研究论集》第3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13-436页。
⑦此为1899年9月10日田冈岭云为“在上海客寓”的评论集《云的碎片》而写的序中的一段。
⑧《三十自序》(二),见《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612页。原载1907年《教育世界》第152号。
⑨竹村则行《王国维の境界说と田冈岭云の境界说》,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第15号,1986年版。
⑩《三十自序》,见《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11页。原载1907年《教育世界》第148号。
(11)参见钱鸥《青年时代の王国维と明治学术文化》,《日本中国文学会报》第48集(1996),第250-264页。
(12)《三十自序》(二),见《王国维遗书》(第3册),第614页。
(13)(15)铃木虎雄《王君静安を追忆す》,《艺文》1927年第8号。
(14)参见神田喜一郎《忆王静安师》:“先生的学术兴趣渐次移到蒙古的历史地理。先生屡次给我写信,寻求我国那珂、白鸟等博士在这方面的著作。”(原载《中国文学月报》1937年第26号。此据滨田麻矢的译文,见陈平原等编《追忆王国维》,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376页)
(16)钱鸥《京都时代の王国维と铃木虎雄》,认为铃木虎雄之研究戏曲及词,深受王国维的影响,其说亦是。见《中国文学报》第49册(1994),第90-118页。但铃木虎雄在东京帝国大学就学时,尝聆听森槐南讲授词曲概论,其影响亦不可无视。
(1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85页。
(18)王国维《录曲余谈》,《王国维戏曲论文集》,第227页。
(19)原载1905年《教育世界》。兹据《王国维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40-41页。
标签:王国维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明治时代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赵氏孤儿论文; 窦娥冤论文; 戏剧论文; 桃花扇论文; 琵琶记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