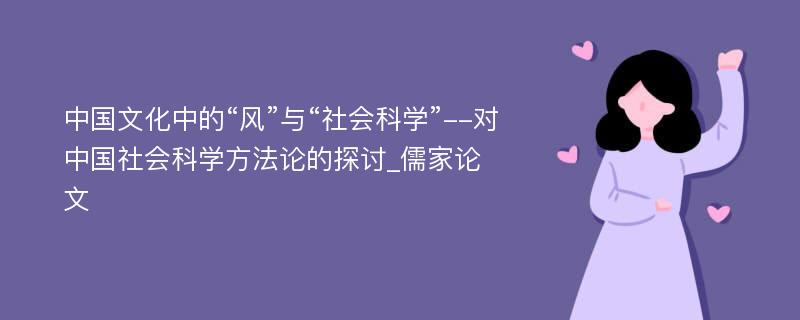
“风”与中国文化中的“社会科学”——关于中国社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方法论论文,中国文化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时代状况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危机
在20世纪中国人所做的所有引进“西学”的工作中,“社会科学”可以说是一个全新的事物。这一点,与人文科学相比显得尤其明显。人们通常倾向于认为,像伦理学、哲学等一类西方人文科学学科,在中国传统学问中并不是不存在。但是,很少有人会说像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等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学科在中国古代也曾存在过。这不是说古人没有研究过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而是说这种研究在古代学术中没有成为一门或几门独立的学科;毋宁说,在中国古代学问中,社会科学领域的问题几乎都被当成了伦理道德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科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全新的”。
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不仅在很短的时间里引进了几乎所有的西方社会科学学科,而且史无前例地建立了一套完整、规范的学科体系,形成了一支庞大的专业研究队伍。今天,在各个领域社会改革飞速进行、各种社会问题蜂拥而至的特殊时代背景下,人们对中国社会科学的期望可以说是与日俱增。特别是经过将近一百年的文化运动和思想革命的洗礼,中国人今天似乎更加意识到制度变革的重要性。比起当初的“维新”、“共和”来,只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制度变革才真正显示出其巨大的建设性力量,只有“改革开放”才开始把中国近代以来千呼万唤的制度变革落到实处。然而,令人深思的是,中国社会今天所经历的巨大变革决不是某种出色的理论的产物,而是出于多年政治动荡的惨痛教训;在改革从“一波三折”到平稳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似乎也没有提出太多的理论资源来指导它,更加行之有效的原则却是“摸着石头过河”;最有趣的是,在改革带来了一系列思想、道德及制度的问题之后,似乎没有一种社会科学学说能对之做出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解释,或提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对于中国社会科学在解释中国现实问题面前的“苍白无力”,可以找到许多理由来解释。其中一个重要解释是,中国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引进的,它们在中国还太年轻。对于中国人,可能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地消化它,而只能说引进了一系列新的标签而已。这种解释当然很有道理。但是除此之外,似乎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因为社会科学毕竟与自然科学有所不同,在对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一个国家的民族性、文化传统以及国情的因素影响甚大,中国社会的许多现实问题不能像套用数学公式那样照搬套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理解或解释。许多人都已认识到,中国社会科学目前采用的研究方式完全是西方式的,在解释中国社会的现实时未必总是适用的。长期以来,人们似乎只是习惯于应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来理解或解释中国的问题。这与中国人文科学诸学科形成了鲜明对照。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都在强调中国哲学等与西方的不同,尽管“中国特色”在某些人心中已经变成了满足其民族自尊心的主要途径,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汉学界,经过几代学者的努力,已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承认存在着一种“中国特色”的哲学思维及其对于现代世界的特别意义。本文试图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社会科学难道真的可以避免讨论“中国特色”的问题吗?或者,中国社会科学的确立,难道只是意味着将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直接引进到中国来研究中国问题吗?为了开展真正有价值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及方法之外,是否还需要建立一整套新的理论预设、概念系统或方法论?这正是本文的一个要点。本文认为,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正是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对今天的中国自己感到无能为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如何建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及方法呢?本文提出了这样一个思路,即鉴于目前没有找到一种更好的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理论或方法,我们不妨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曾经在理解或把握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发挥巨大作用的某种学说为例进行个案研究。这种学说虽然算不上“社会科学”,而充其量只能称之为一种“经验的总结”,但是,它确曾在理解或解释中国社会现实方面发挥过强大的作用,并且总能在关键的时候提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解决现实问题的办法来。我们试图通过对这种学说的个案研究,看看能不能找到对于今天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有启发意义的思路。这门学问就是“儒学”(儒家学说)。尽管儒学的历史作用20世纪以来饱受人们的批判,但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儒家学说在过去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一直在用自己的一整套理论来解释中国,包括解释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以及几乎所有重大的现实问题,并在解释的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不管儒家的解决方式该如何评价,我们不能不承认,儒家对中国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方案曾经在很长历史时期内发挥过无与伦比的巨大作用。它曾经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制度系统,非常有效地整合了中国社会的各阶层,使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在相当长时期内居世界领先地位;它有一整套相对完备的学说体系,它使得中华民族经历了一次又一次重大的历史考验,使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多次免遭分裂和毁灭的命运,对中华文明的兴起、发展和保存起到过决定性的作用。儒家对中国社会问题的“解释”,虽然没有形成一门“科学”,但是,它对于我们今天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是不是会有借鉴作用呢?
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对儒学的研究,为建立一种可能是真正的“中国社会科学”寻找起点。笔者的研究在思想上有如下几个基本假设:
1.一种可称为“中国社会科学学说”的东西,不应当是西方迄今所建立起来的既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的直接应用。相反,中国社会科学的建立需要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外建立起一套独立的理论预设和方法系统。这种理论和方法要在对中国社会各种复杂因素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基础上,经过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能形成。中国社会科学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既有同质性,又有异质性;它可能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一个“延伸”,二者在研究方法上有相通之处,但是与此同时它又可能包含着自己的独立的理论前提和方法论。
2.“中国社会科学”之所以有中国特色,可能与中国文化的习性有关。我们的假定是,中国社会的整合规律可能以某种经过几千年漫长发展积淀起来的特定的民族文化心理为基础,这种长久形成的(虽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习性,导致了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不能不有一套新的理论和方法。因此,任何一种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都应关注中国文化的习性,特别是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与中国社会自我整合规律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之所以不能直接在中国套用,正因为它们的理论预设与方法论不是以中国文化的习性为基础建立的。
3.儒学虽然本身不能被称为一门科学,但是作为一门对解释中国现实问题有过特殊作用的学问,它的理论观点可能对于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社会有巨大启发意义。因此,我们把儒家当做一个案例,试图通过对儒家提出来的若干与社会科学问题相关的范畴的研究,来揭示中国文化的某种“秘密”,从而找到解读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的“钥匙”,以此来寻找“科学地”研究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自我整合和发展规律的合适的出发点,对于建立起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提供某种有借鉴意义的思路。
我们的具体做法是,选取儒家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风”为突破口,在广泛搜集儒家学说中一系列与“风”这一概念相关观点的基础上,试图分析这些政治观点背后的文化心理基础,借以揭示中国文化的习性,以及中国文化的习性与中国社会自我整合规律之间的关系,从而试图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问题提供重要线索。我们在下文中提出的所有概念,都是“试探性”的,它们可能在某些“社会问题域”内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并不是说可以解释中国社会所有的问题。
二、“风”在儒家政治学说中的地位
“风”是儒家政治学说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让我们先来看下面这段话: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注:《论语·颜渊》。)
这段话的基本精神是说一个国家治理的好坏,取决于领导者好不好。孔子用“风”与“草”之间的关系来形容上对下的影响力。孔子暗示我们,一个国家的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它所导致的“社会风气”之上,而一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又是由“官场风气”所决定的,官场风气的形成则取决于官场中最有影响力的人。总之,如果要改变一个国家的局面,就要从改变“风”做起。
“风”在儒家政治学说中的特殊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出来:
1.“风”与“民”。
儒家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政局好坏的主要标准之一,是这个国家的“社会风气”。古人没有“社会”这个概念,所以把它称为“民风”。因此,“观民风”是治政的开始,一个好的政治家应该学会“观风”、“辨风”、“省风”: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命市纳贾以观民之所好恶,志淫好辟。(注:《礼记·王制》。)
风行地上,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注:《周易·观·象》。)
天子省风以作乐,器以钟之,舆以行之。(注:《左传·昭公廿一年》。)
天子学乐辨风,制礼以行政。(注:《大戴礼记·小辨》。)
2.“风”与“政”。
儒家认为,“改变民风”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改变民风”的工作可以称为“治风”;为了改变“民风”,需要“树新风”,这也被称为“树之风声”:
帝曰:“俾予从欲以治,四方风动,惟乃之休。”(注:《尚书·大禹谟》。)
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注:这是《周易》“姤”卦的“象辞”。按:姤的卦体是巽下乾上,八卦中“巽”卦卦象为“风”,“乾”卦卦象为“天”,故曰“天下有风”,本卦以“风”说明“施命”(参见孔颖达《周易正义·姤》)。)
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注:《左传·文公六年》。)
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瘅恶,树之风声……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公其念哉!(注:《尚书·毕命》。)
3.“风”与“德”。
由于“风”总是从最上层刮起的,“风”的根子在“上”。因此,为了改变一个社会的“风”,需要从最上面的人做起。而最上面的人能够影响一个社会的“风”的东西,主要是他的“德”。只有最上面的人“修德”,才能真正改变一个社会的“不良风气”:
王曰:“呜呼!说!四海之内,咸仰朕德,时乃风。”(注:《尚书·说命下》。)
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诗》曰:“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注:《中庸》第33章。)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曰:“呜呼!……敢有恒舞于官、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注:《尚书·伊训》。)
4.“风”与“教”。
由于“风”的形成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不能指望在一夜之间改变它。除了国君要修德之外,还有一项改造社会的持久工程,就是“教”。在儒家所推行的“教”之中,尤其重要的是“乐教”。儒家认为,通过“乐教”可以改变一个社会的风气,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
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注:《礼记·乐记》。)
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注:《孝经·广要道》。)
不过,“乐”的内容原本是“诗”,“乐教”同时意味着“诗教”。因此,儒家的“风教”之中,“诗教”亦是重要一环。《毛诗序》从《国风》第一篇“关睢”出发,系统地论述了“国风”之“风”的深刻政治含义及其与儒家“诗之教”的内在关联,可以说是一篇最经典的“风的政治学”:
《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
当然,这决不是说“风教”仅限于“诗”和“乐”;“风教”的精神实质是要通过“鼓风”、“树风”,让被教育者能够“闻风而动”。
5.“风”与“化”。
“风”的另一重要政治含义是“化”。《说文解字》从字源上告诉我们,“风”的本义之中就包含着“化”:
风,八风也。东方曰明庶风,东南曰清明风,南方曰景风,西南曰凉风,西方曰阊阖风,西北曰不周风,北方曰广莫风,东北曰融风。风动虫生,故虫八日而化,从虫凡声。(注:另见《大戴礼记·易本命》:“八主风,风主虫,故虫八月化也。”)
儒家常常用“风”来比喻政令(注:以“风”比喻政令,在《周易》中多见。《周易·姤·象》曰:“天下有风,姤;后以施命诰四方。”《周易·巽·象》曰:“随风,巽;君子以申命行事。”),用“化”来形容王道政治的成就,并谓“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注:《周易·恒·彖》。)。“风”与“化”之间的这一联系可以深刻地说明什么是圣人之政。儒家王道政治思想的重要观点之一是,最成功的政教不是通过强行灌输来改变人民,而是“潜移默化”。所以“化”的主要含义是,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被“感化”而向善,即孟子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注:《孟子·尽心上》。)之义。郑玄《周礼·春官·大师》注称:
风,言贤圣治道之遗化也。
孔颖达《毛诗正义》在疏《毛诗序》时,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风”与“化”的关系:
风训讽也,教也……言王者施化,先依违讽谕以动之,民渐开悟,乃后明教命以化之。风之所吹,无物不扇;化之所被,无往不沾。
三、“风”与中国文化的习性
现在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儒家政治学说中,“风”会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提出和产生的背后,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文化心理因素在起作用?“风”这一概念是否反映了中国文化的某种习性?仔细想想,在目前人类各民族当中,也许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华民族那样容易受到“风(气)”的影响。在我们的国度里,几乎无论在哪个时期,都盛行着某种“风气”。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热”,60年代的“红卫兵热”,70年代的“参军热”,以及80年代以来的“出国热”、“下海热”等等,无不代表着一系列特定时代的特定社会风气。尽管在一种“风气”过去之后,人们常常会嘲笑当时人们为何会那么愚蠢,盲目地热衷于某个并不值得他们热衷的事物,近乎疯狂地崇拜某种并不值得崇拜的对象;然而,他们却时常忘记了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在他们嘲笑前人的同时,他们自己现在可能也正沉浸在崇拜或热衷于另外一个事物的风气之中。这种新的崇拜或热衷与前者的惟一不同也许仅仅是对象发生了变化。与前人的盲目崇拜或热衷相比,他们今天的崇拜或热衷在盲目性上似乎并不比前人低。问题的关键在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各种社会风气的流行?稍加思考即可发现,正如今天的国人对于“出国”的崇拜主要是由于一种盲从心理在作怪一样,前人对于一些事物的崇拜也多半出于盲从。
这就涉及到一个中国人的盲从心理从何而来的问题。盲从心理来自中国人的特殊文化心态。“风”的事实暗示我们,在中国社会有这样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心理,即人与人之间在心理上的相互模仿、相互攀比、相互依赖的思维方式。这种心理或思维方式导致那些比较突出的人的所作所为,容易对其他人的行为方式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因此,我们可以初步得出,导致“风”的产生以及“风”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根“神经”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一种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攀比、相互依赖、相互追随为主要特征的心理活动。我们把这种心理活动称之为中国文化中的“人际本位”心理。这种“人际本位”的文化心理,也就是中国文化的习性。所谓“人际本位”,是相对于西方的个人本位提出来的,其重要含义之一是指,中国人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普遍有一种不自觉的心理倾向,即把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地位或形象当做衡量自身存在价值的主要准绳之一。
比如说,中国人所谓“功成名就”、“出人头地”、“人图名声树图荫”、“光宗耀祖”、“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丢人现眼”、“死要面子活受罪”等一类话语,就是这种心理活动的典型体现。很多时候,正由于人们都很在乎他人的认可,故而会不自觉地追随社会潮流。因此,当一种东西在某个地方变得很有影响时,往往会成为他人争相效仿的对象,由此引发的往往是一种时髦或风气。当一种社会潮流形成时,它所产生的效应也是“马太式”的。这就是说,正是一种“人际本位”的文化心理在起作用,才会导致中国社会在任何时期总会流行一些不同的“风”,极大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人们之所以会盲目地“从风”,往往是因为现代社会人们都认同它,只有追随它,人们的内心才会得到平衡,这种心理平衡对于他们把握自身的存在价值至关重要。有时风气的影响力过分强大,达到了扼杀人的个性的程度,因为“不从风”会遭到世人嘲笑、轻蔑,而不会因此被视为“有个性”。
“从风”心理并不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的确,即使在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文化中,仍然会有从众心理,会有“社会风气”,也会有人们对领袖人物的仿效效应。可是要知道,在人类其他文化中,“风”也许从来没有像在中国文化中那样,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政治制度的建设、对于国家的安宁等等发挥着如此巨大的作用。我们可以设想,西方人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把人理解为同一个至高无上的“上帝”的子民,从这种意义上看,不是人对人的依赖,而是人对上帝的依赖才最关键。许多西方学者指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在西方的兴起,是与基督教传统有关的(注:参见杜威《人的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2~103页。)。由此也使我们理解了为什么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东方文化中一直没有大行其道。
通过对“风”背后的文化心理机制的揭示,我们就能理解儒家的一系列政治思想是如何提出来的。比如儒家的“德治”思想、“任人唯贤”思想、“重教化”思想之所以提出来,显然是因为认识到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影响对这个社会的自我整合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认识到中国人普遍的“从风”心理决定了改变这个社会最有效的措施莫过于改变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特别是他们的心理倾向。因此,最重要的工作不是放在制度建设上(尽管制度建设总是必不可少的),而是放在影响大众的心理活动状态上,并通过这种影响进一步影响整个社会。用儒家的话来说就是:“正人心而后正天下”。在这一过程中,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1.针对现在流行的不好的“风气”,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扭转之,这叫做“治四方风动”;2.利用大众的“从风”心理,把德行俱佳的人放到政府部门的最上层,通过他们的言行影响一大批人的心理取向,从而极大地带动整个社会风气的改变,这叫做“树之风声”;3.由于“从风”心理带有极大的盲目性,要让人们从这种盲目性中走出来,就要提高全民的道德素质。因此,对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真正具有长远意义的工程是“教”和“化”的工作。“教”是教育,“化”是改变。
四、“风”与中国社会科学
现代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时,最容易犯的错误之一就是不考虑中国社会的文化特征,企图将西方的理论直接应用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期望从中得出有益的结论。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确实有一整套完备的方法系统,但是,在运用它们来研究中国社会时,人们却时常会失去“感觉”。当然,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对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运用得不好的缘故,但是,事实上在运用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社会时,有时人们找不到“感觉”确实是由于他们未能抓住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现象来说最关键的因素,从而使他们找不到“驾驭自己的研究对象”的感觉。
“风”代表中国文化以及中国社会中的一根“神经”。有很多时候我们确实可以从各种“风”——社会风气、官场风气、地方风气、部门风气、学校风气、行业风气等等中找到理解中国社会问题的途径及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法。这一点我们往往可以从政府部门所谓“狠刹歪风邪气”、“消除行业不正之风”、“纠正校风”、“狠抓学风建设”、“净化社会风气”等一类政策性宣传中看出。严格说来,这些政府部门的政策性宣传往往不是从科学研究或应用西方某个社会科学理论中得出的,而更像是一种直观、素朴的经验总结。相反,如果真的应用西方社会科学思维来理解中国问题的话,很可能得不出上述政策性宣传来,乃至于根本不能为诊断或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提供有意义的方案。尽管“风气”的兴起或流行有许多原因,有时是当时当地一个有影响的人鼓吹或煽动的结果,有时也可以是其他一些偶然的原因激发了公众的兴趣所致;但是它一旦形成,就可能对人心造成强大的冲击,就可以让成千上万的人“闻风而动”,甚至许多政策、法规、权威都会因它而变化,它成为这个社会中最大的“权威”。
显然,并不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切都与“风”有关,或者由“风”决定的。但是更重要的,我们以“风”为案例来研究,本来就不是想以“风”来解释中国社会中的“一切”,而更主要的则是想说明为什么“风”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根“神经”?我们的观点是,导致“风”成为中国社会的一根“神经”的东西,是某种特殊的中国文化心理——“人际本位”的中国文化心理,或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习性。从中国文化的习性出发,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很多现象。例如,“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运动”对“人权”的践踏,我们如果从今天的“法制”角度来理解是很困难的。为什么法制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一纸空文?要知道,当时许多红卫兵们做事情确实出于自愿,他们往往是“义正辞严”甚至“义愤填膺”地做那些事情的。这体现出中国文化中某种对个人人格尊严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但是这种毁灭却不能用“极权专制”一语简单地加以解释,因为是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践踏人权的。这种情况只有从中国文化的习性的角度才能得到恰当的解释。后者决定了在中国文化中有时“风(气)”的力量会表现得十分强大,会在某些地方对人们的行为方式产生强制作用,从而达到了扼杀人性、践踏人权的程度。
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失败,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各种改革,特别是那些激进的变革为什么往往会失败?因为那些改革者不了解引进一项制度很容易,但是改变人却是一项持久、宏大的系统工程,而改变一种文化则更是难上加难。这一方面有某种超越中国文化的普遍因素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与中国文化习性相关的特殊因素的作用。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了中国文化中真正起作用的力量不是制度而是人,人际关系的力量,特别是人与人之间、人群与人群之间实力的对比与悬殊,才是决定这个社会的当下走向以及一切制度变革成败的关键。
正因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最具有决定性力量的东西有时不是“法律”,而是“人际关系”,因此,改变这个社会最重要的途径往往是改变人、改变人群关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习性。中国历史上的儒家通过他们朴素的经验观察,发现了这一事实,并形成一种政治理论,用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实践: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注:《论语·颜渊》。)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注:《论语·子路》。)
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注:《孟子·离娄上》。)
人际本位的中国文化习性,是不是可以解释中国社会的一切?当然不是。我们必须承认,中国社会发生的很多事情,还由其他许多历史与现实的因素、普遍与特殊的因素、个性与共性的因素、经济与政治的因素等等在起作用,不能都归之于本文所谓的“中国文化习性”。但是,文化习性因素毫无疑问是影响中国社会的主要因素之一。惟其如此,我们今天要开展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不能回避它。对中国文化习性的发现与思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寻找建构一套新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社会现象的途径,从而对于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理解和解释中国问题的社会科学的理论预设、概念体系乃至方法论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标签:儒家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社会科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社会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社会风气论文; 风气论文; 国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