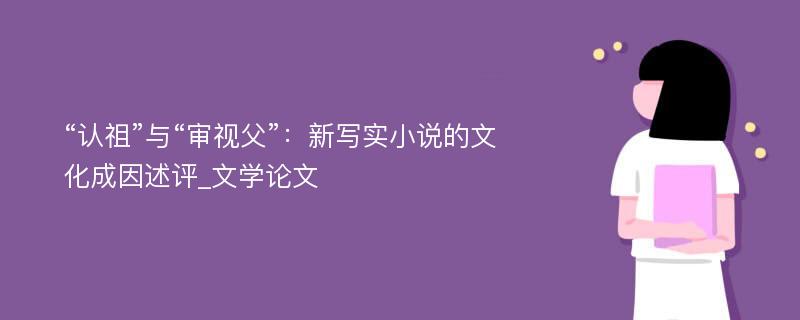
“认祖”与“审父”:新写实小说的文化发生学检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生论文,文化论文,小说论文,审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51(2001)06-0069-05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文坛旋风骤起,狂飙突进。在尚无切当的理论阈定之前,人们暂以“新写实”为之命名。评论认为,以方方、池莉为代表的新写实作家群,“将‘新写实主义’的大旗哗哗展开,在当代文坛掀起一股沸腾的潮流。人们从历史的寻根与先锋的新潮中走过来,迎面触及到的是‘中国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一时间,‘太阳出世’般的耀眼光芒鲜亮了文坛,一道道生活状态的‘风景’热闹了文坛”。[1]而今,十余年过去了,新写实小说业已成为参照型历史话语。但其凶猛的来势、峥嵘的表象以及带给新时期文坛的巨大冲击,足以表明该文学“存在”文化学意义上的超时空阐释可能。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试从创作表象、文化生成、文本品格等三个层面切入新写实小说“内幕”,以求得某些具有当下意味的启示。
一、表象:东风夜放花千树
新写实小说的发生、演进,有如东风夜放花千树:创作来势猛、作家阵容大、作品数量多、勃兴时间长、鼓吹劲头足、文化效应广。
创作来势猛 正值反思文学后继乏力、先锋思潮风雨如晦之时,文坛新动已在孕育之中。1987年,方方、池莉的《风景》、《烦恼人生》竞相推出,令人刮目而视。经过近两年的调试、聚合,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写实小说疾风劲雨,蔚为大观,攻夺文坛主战场。《钟山》火眼金睛,飞鹰逐兔,率先推出“新写实小说大联展”,并阐释说,“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实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一时间,新写实小说创作成为文学主流向,颇有独占文坛鳌头之势。
作家阵容大 总体上趋于年轻化、知识化,观念上拥有先锋意识,操作上刻意花样翻新的新写实骄子们,以其凌厉攻势迅速壮大了作家队伍。除方方、池莉等“老将”外,其他部落或散兵游勇也竞相投其麾下,汇成浩浩荡荡的“主力兵团”:刘震云、刘恒、叶兆言、范小青、余华、苏童、格非、朱苏进、周大新、周梅森、阎连科、陈怀国、李锐、李晓等等。可以认为,其庞大阵势与群体默契在新时期乃至整个当代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作品数量多 新写实小说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长中短篇三“管”齐下,硕果累累。《落日》、《白驹》、《白雾》、《桃花灿烂》、《祖父在父亲心中》等扯出破碎的人生“风景”线。《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等涂抹出“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的无奈色彩。《白涡》、《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等裸露出芸芸众生的食、性原欲。《塔铺》、《新兵连》、《头人》、《官场》、《官人》、《单位》、《故乡天下黄花》等撒满“一地鸡毛”。范小青的《光圈》、《伏针》、《人与蛇》、《顾氏传人》吼出平庸者沙哑的“清唱”。叶兆言的《状元镜》、《艳歌》则无异于哽咽难语的“挽歌”。类似的圈内作品不胜枚举,如《罂粟之花》、《妻妾成群》、《红粉》、《米》、《现实一种》、《往事如歌》、《绝望中诞生》、《金色叶片》、《祭奠星座》、《迷舟》、《夏天太冷》以及“军歌系列”、“厚土系列”、“瑶沟村系列”等。新写实小说作品之多于此可见一斑。
勃兴时间长 新时期以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你消我长,此伏彼起,各领风骚三两年。而新写实小说昂首走过七八个春秋,堪称文坛盛事。到了1993年,新写实创作以坚挺的姿态完成了出色的冲刺。方方在《中国作家》三月号和《作家》三月号分别推出《作为艺术》和《推测几种》,阎连科的《自由落体祭》同时刊于《作家》三月号。刘恒的《苍河白日梦》、李晓的《一种叫太阳红的瓜》被《收获》第一期拿来压阵。范小青英勇不减当年,继《月色融融》之后,又在《春风》第一期和《峨眉》创刊号上相继亮出《茶客》与《老岸》。苏童的《沿铁路行走一公里》和余华的《活着》都被视为新写实小说力作。显然,在新状态、新体验鼓噪文坛之前乃至同时,新写实小说无可争辩地妆扮了新时期文坛的前台景观。
鼓吹劲头足 新写实小说滥觞伊始,犹如“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评论家们兴之所至,鼓而吹之,诚如李万武所言:“一些人一听说有一种以‘还原生活’为旗帜的新品种小说出来……真是好生喜欢了一阵子。”[2]有人宣称:“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无异于沉寂中的一声爆响,黑暗中的一线光明,它使许多翘盼中国文学腾飞于世界艺术之林的评论家从中捕捉到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光明前景”。[3]王干来得更干脆:“如果本世纪有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话,肯定是写实型的作家和写实型的作品。”[4]而今看来,上述判断无疑是带有冲动性的估计,但在当时,它们确实刺激了作家们的创作热情,因而客观上成为新写实现象的一部分。
文化效应广 曾几何时,新写实小说以其喧嚣的声色阵容促发了广泛的文坛骚动,牵动了报纸、广播、影视的神经中枢。一向沉稳的大师级作家王蒙也禁不住预言,以王朔及新写实为代表的调侃文学现象将继续走俏90年代的文坛。很清楚,新写实小说尽管缺乏石破天惊之作及深层轰动效应,但作为某种时代情绪的文学投射,它们业已引发广泛关注并一度成为各大文学刊物的抢手货、镇卷作。饶有兴趣的是,当刘恒的《伏羲伏羲》走红之时,电影《菊豆》旋即搅动观众心潮。当《大红灯笼高高挂》赢得意大利威尼斯银狮奖时,人们重新翻阅《妻妾成群》,渴望从中读个明白。周大新的“预西南盆地”刚一面世,《香魂女》便轻松捧回第4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大奖。除张艺谋、谢非等名导外,其他导演也先后看好新写实小说,甚至为购得《红粉》的优先导演权,姜文和李少红陡生版权之争。显而易见,新写实小说大潮所致,已经超越了小说和语言艺术范围,俨然结成耐人寻味的享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化现象。这意味着,拒绝进一步阐述其社会文化生成是不明智的。
二、“认祖”:多极文化生成
喧闹的表象掩饰不住生成的混杂,疾风暴雨式的来头往往标示出生命的某种内在虚脱。面对轰然作响的新写实小说大潮,我们不禁要问:你从哪里来?
细加考辨便不难发现,新写实小说生成于主客源与内外因的矛盾撞击之中。其中,主客源揭示了文学与生活的依存规律,内外因显示出文学内部复杂的承传关系。
(一)主源——作家主体的创新求变意识
作家主体的创新意识是文学嬗变的基本内驱力。新时期的核心时代范式是改革开放及由此而来的主体行为方式的标新立异。承此,广大中青年作家块垒消释,创新求变成为群众指向。新写实小说的作者大都具有较高学历(有些作家是硕士研究生或高校教师),知识储备相对全面,理论素养较好,创新意识强烈,拥有先锋或潮头意识。当传统“新潮”不再新潮时,这支新军便开始操纵新一轮文坛革命。观念的清醒与指向的自觉,使之有可能把握新的创作界域,即传统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如今已觉不新鲜,古典主义、自然主义也各自有着程度不等的缺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两结合”方法因主流意识形态色彩过浓使作家心怀余悸,主张“向内转”的现代主义未必完全适合中国国情。因而,这些作家有意突破过往语言艺术的创作维度,较多地借用摄影、绘画、雕塑乃至影视艺术的表现手法,企图以反常的文学思维超越艺术真实,返回生活真实,以缩短日益扩张的艺术与生活的距离。于是,在他们笔下,再也听不到微风轻拂,黄莺婉转,看不见蓝天白云,山河壮丽,百花争妍,充斥其间的是普通人的吃喝拉撒睡和食欲性欲钱欲权欲,即所谓生活如网,人生似梦。如此“世故心态”,在造成作品诗意消解的同时,又无可挽回地导致了新写实小说文学性的削弱。
(二)客源——现实社会生活的掣动与大众审美期待的召唤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文学艺术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这是文学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则。无论新写实作家如何追异逐变,从根本上讲,其作品仍是现实社会生活的一种回眸。当代社会生活节律空前加快,生活事象异常繁复,生存境况不同程度地遭受现代工业和都市文明的破坏,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出现严重异化,人的价值与尊严面临前所未有的怀疑和挑战,莫可名状的焦躁、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惊惧、希望的失落、选择的痛苦,把人逼向扭曲的误区、压抑的深渊。从一定意义上说,新写实小说正是这种临渊之作。我们注意到,在错综而强悍的多元化社会律动面前,新写实作家更多地采取了貌似贤达的视而不察、存而不论、放任自流的态度,既无歇斯底里的嚎叫,也无不痛不痒的说教,而是沦为“局外人”,任尔东西南北风,吹皱一池“污水”。
相对于作家创作而言,读者的审美期待不失为重要的客体动力。新时期以来,春秋数度,文变频仍,练就了文学消费多维度、开放型的审美召唤结构,猴子扳苞谷似的趋异心态,促使读者的阅读趣味水涨船高,并反过来牵引或压迫作家创作,带动新写实小说家们不断地调制作品口味。这表明,新写实小说自身也有着演进与发展的潜在空间。
(三)内因——中华母体文学的濡染
从本民族文学传统对新写实创作的影响来看,不难判断,新写实小说盘桓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缠绕着新潮文学的藤,点缀着通俗纪实小说的叶,以此粘和自身的树干枝叶。
我国传统现实主义承《诗经》背景,中经杜子美、曹雪芹、鲁迅等巨擘的托举,到社会主义时代已是煌煌大观。现实主义按照生活本来形态及其发展规律真实而具体地反映社会生活、强调客观叙述与冷静分析等基因,都明白无误地遗传给新写实小说,以致屡屡有人称之为现实主义的“回归”与“深化”。究其实,新写实小说在接纳传统现实主义写实本色这一半时,又拒斥了理想抒发与浪漫表现的另一半。
中国式先锋文学着实激荡过一阵,对新写实小说不无启示作用。王蒙的东方意识流,徐星、刘索拉式的荒诞小说,马原的“套盒式”语言暴力,莫言、洪锋、残雪等作家的“黑色幽默”以及魔幻现实主义倾向,都可在新写实小说中窥见或浓或淡的影子。大批先锋、新潮作家之于新写实小说的转轨或加盟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
与此同时,80年代以来,随着务实心态与平民意识的普遍增强,通俗小说与纪实文学显示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金庸、梁羽生诸人的《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龙虎斗京华》等通俗文学的世俗化处理,冯骥才、邓友梅等人既有浓郁乡土气息又不乏深厚文化意蕴的乡味小说,以及《5·19长镜头》、《公共汽车咏叹调》、《北京人》等纪实文本,以特有的真实性、公共性“笑傲”文坛。借此,接受主体实现了消遣、愉悦、知事的目的,对经由改造、夸张、变形、虚构的“天方夜谭”式的创作倍感陌生和厌倦。实践表明,新写实小说以其特有的通俗性和纪实性尽展生活之“实况”,并因此获得某种程度的成功。
(四)外因——西方异域文化因素的参照
哲学、美学的联袂而行,往往以其高能放射效应规约着文学操作。新写实作家以文化人惯常的敏感自觉或不自觉地融汇了西方诸如现象学、实证主义、存在主义乃至弗洛伊德主义等思想观念,转而扩展自己的文学话语空间。
新写实小说的自然主义倾向,已为评论界所公认。左拉曾极力标榜:“自然主义小说不插手于对现实的增删,也不服从一个先入观念的需要……我们只须取材于生活中一个人或一群人的故事,忠实地记载他们的行为。”[5](P248)从众多新写实作品中,依稀可见左拉的幽灵:主张实录生活,不事艺术概括;崇尚真实性,反对倾向性;强调用生物学、遗传学观点写人,忽视典型性格的塑造。新写实小说的所谓“原生态”记录和“零度介入”,与自然主义小说一脉相承。
在西方现代主义创作中,存在主义小说、“新小说”派及荒诞派戏剧给予新写实小说的滋养或许最多。上述流派的荒诞感、死亡感、非英雄及物象至上在新写实小说中有明显呈示,弥漫着萧瑟落寞的“世纪末氛围”。这种反主题、反人物、反虚构,亦即反传统艺术法则的做法,正好体现了新写实小说之“新”。
主客穿越,内外相连的复杂生成背景,势必导致创作欲念的盲动、操作方式的琐碎以及叙事指向的平冷,并由此规定了新写实小说的“混血”特质。一方面,它较传统现实主义还“土”,另一方面,比现代派还“洋”;一方面有着过往自然主义的“本色”,另一方面,又创造了世纪末中国文坛的“新潮”神话;一方面,俯首于生活实态,另一方面,执着于艺术反叛。欲说还羞、琵琶遮面式的“经验游戏”,使之在纷乱的文化夹缝中最终丧失了独立的文本品格。
三、“审父”:“四无”式文本品格
文化生成的驳杂,大杂烩式的“煮粥”,使新写实小说文本最终沦为“四无”式嫁接品,即无倾向、无英雄、无技巧、无深度。这也说明了新写实现象虽属积极却远未成熟的实验性现代文本品格。
(一)“中止判断”与“零度情感”——无倾向
新写实小说有意阻挡作家主体因素的深度介入,要求“中止判断”,倡导零度写作。这种貌似不动声色、不偏不倚的反观念、反主题意向,本质上是非理性、反文化倾向的表现,因而注定会落空。正如谢冕先生所说,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因迎合了所有人而可能掩饰和冲淡原本的积极动机。
我们不妨考察一下“中止判断”与“零度情感”的实践可能性。众所周知,作为审美反映的文学方式隶属意识形态范畴,而社会生活属于存在范畴。一方面,意识从来都是被意识到的存在,亦即生活是第一性的。另一方面,文学以其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而成为一种特殊社会意识形态,主体的主观情感因素渗透进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之中。题材的选择、情节的组合、人物与环境的安排、语言及表现手法的运用等,都不可避免地要打上作家个性的印记。其中,必然负载着作家主体的生命感悟和精神意识。在这种情况下,绝对的真实是不存在的,因为谁也不能认为自己就是一面完美无缺的镜子。因此,“中止判断”与“零度情感”与其说是一种艺术追求,毋宁说是新写实作家玩的一个花招:以寓虚于实的羞答答的姿色诱使读者钻入本文的叙事圈套,去接近或寻找“元语言”裂缝中的“潜主体”或“结构意义”。这样,作家既达成了与现实最亲近、最相似、最高粘合度的关联,又以“上帝”式的公正面貌拉开与现实的距离,以求识得“庐山”面目。这种凡人、超人两验的企图,致使作家两难。因此,新写实小说主体的退场、意义的缺席“意味着‘已有的现实主义’或现实主义‘先锋派’文学蕴含的权力话语、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及现代主义对于生存意识的追寻与诘问,对于虚无与沉沦的超越与反抗均被其‘零度叙述’所一一拒绝,叙述从而成为丧失主体判断的现象还原,从作家逐渐冷漠的叙述之中,我们再难寻觅其理性批判与人文激情的面影,甚至其情感的脉动也难以触摸”。[6]其结果,作家只得与其所展示的“小人物”同流合污。
(二)边缘搜索与类型罗列——无英雄
新写实小说的犬儒主义“近视症”,使得作品文本缺乏大度量的宏观审视,苍白的叙事背景下无主角、英雄和伟人,生活大潮不再有主旋律。
机器文明的轰响,商业大潮的涌动,观念的摇摆,信仰的危机,生存的艰难,将普通人挤到生活的边缘,沦为可怜巴巴的边缘人、多余人。这既是现代社会的现实风景,也是新写实作家自动放弃急流冲刺、转而尝试边缘搜索的必然结果。《风景》中的“哥”们,《落日》中的丁如虚,《老人角》中的老汤,《烦恼人生》中的印家厚,《太阳出世》中的赵胜天,《热也好冷也好活着就好》中的猫子,《一地鸡毛》中的小林,都是消磨掉典型性的边缘化类型。在程式化生活面前,人也被机械化,生活空间遭到无情的压缩,活动方式日益简化。刘恒畅言,一个粮食,一个性,是人的两大基本需求。刘震云也表现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生活是严峻的,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生活琐事。单位、家庭、上班、下班、洗衣做饭弄孩子,如何求人将孩子入托,如何将老婆调到离家近一点的单位,每一件事情,面临每一个困难都比上刀山下火海还令人发愁。”[7]可见,在新写实作家笔下,涂抹着浓郁的“泛悲剧”色彩。南帆曾敏锐指出,对于新写实作家,“文学似乎成了一只粗糙的大手,它毫无情面地撕去诗意的面纱,裸露出一片千疮百孔的庸常图景。在这里,人们看不到气势磅礴的事件与伟岸不群的人物”。[8]
综上所述,边缘搜索造成了新写实小说人物的类型罗列。他们没有个性,前途黯淡,希望渺茫,成为命运的玩物。这种反英雄、反崇高的美学情绪,最终取消了人物和文本典型性。
(三)卑琐、仿拟与拼帖——无技巧
新写实小说承袭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反传统、反倾向、反英雄、反技巧品格,吸纳了中国新潮文学极度随意的“玩法”,因此纠缠着伊哈布·哈桑所说的仿拟与拼贴,总体上呈卑琐形态。
这集中体现在叙事策略与语言组合方面。新写实小说中,没有了“愤怒的呐喊”,不见了“大彻大悟”,“绝对相似性”的孜孜以求以及“嘲弄性模仿”(Parody)的套用,使作品成为灰色的“长镜头”。作家们认为,既然无力也不用改变对象性世界,那就应该尽力保留一份未曾启封的现实的纯真。唯其如此,才能成为生活的忠实朋友、公共的现场保护者。余华认为:“很久以来,我越来越感受到先验世界的真实。……一切景象都是先验世界描绘出来的,人在现实世界里只不过是道具而已。”[9]新写实小说也是在这种意义上“回到了小说自身”。
但事实很快证实了这种反艺术的逆反心理的虚妄性。黑格尔早在《美学》第一卷中就精辟地指出:“艺术总不能和自然竞争,它和自然竞争,那就像一只小虫爬着去追大象。”[10](P357)于是,新写实作家只能转而以折中的“仿拟”和“拼贴”手段向现实妥协。除群体性仿拟外,拼贴作为新写实小说的惯用手法被派上用场。《故乡天下黄花》中的大量“附记”,显然是一种仿拟式的拼贴。实际上,这种拼贴造成了叙事技巧和语言模式的卑琐,损害了文本的艺术深度。
(四)深度模式的解构——无深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新写实小说的超越性努力使之多少具有后现代意味。按照王岳川的理解,后现代主义的核心标志是中心隐遁,主体死亡,作者瓦解。其结果,造成深度空间的消解,作品呈现给我们的大多是“缺乏深度的浅薄”。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F·杰姆逊概括出四种“深度模式”:现象与本质的辩证模式;显在与潜在的弗洛伊德模式;确定性与非确定性的存在主义模式;能指与所指的符号学模式。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作品因解构或瓦解了“深度模式”,因而是平面的艺术,“你并不需要解释它,而应该去体验”。新写实小说作品大多一眼望穿,没有弹性与厚度,亦即取消了“空间感”——现象失落了本质不再有辩证空间,显在丢弃了潜在不再有阐释空间,非确定性放逐了确定性不再有“存在”空间,能指与所指的叠加堵死了维度上的结构空间。因此,新写实小说客观上扮演了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学的重要角色。
无论如何,只看现实,不问原因,不计后果的平板写作,说明作家一时难以肩负起“人类灵魂工程师”的重任。难怪人们诘问,新写实作家“除了在‘情感的零度状态’里‘还原现象’,把玩鸡毛遍地的风景,撕扯人生烦恼的白雾,还能做些什么?”[11]
如今,因生活的速动、批评的困倦及读者的疏远,新写实小说的风流年华已逝。因其鼓噪有余而操作乏力,也因其缺乏厚重的历史审视和精深的文化内蕴,它注定是一种写法而不是一种方向。轻率地断言新写实小说“将成为文学在当代中国的永恒选择和不变的方向”,只能是痴人说梦。
时过境迁,文以代变,作为世纪末情调在文学上的特殊关照方式,新写实小说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新的时代将选择新的文学,正是新写实小说的文化发生学检视给予我们的最好启示。
收稿日期:2001-0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