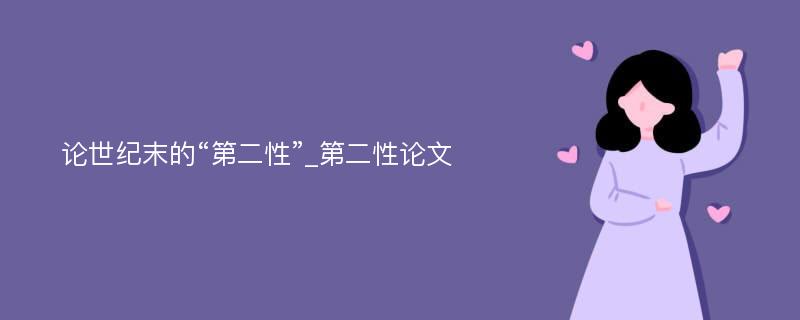
世纪末看“第二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第二性》出版五十周年。年初,法国女界选择在西蒙娜·德·波伏瓦的诞辰期间举办了一个国际研讨会,世界各国许多受过该书影响的女士或敬慕波伏瓦的人士纷纷前往庆贺。
事后得知,巴黎会议的与会者中无一人来自中国大陆,尽管我们这里早已有了《第二性》的中译本,不久前又有全译本面世,会上却无人知道,也无人打听。有朋友因此忿忿不平,以为还是西方中心作怪,将中国女人和中国的妇女研究排斥在“世界”之外,由此可以证明,首先张罗张扬起“后现代”的法国人很有些“后殖民主义”嫌疑,面对东方的和“发展中的”还远不是那么现代。我倒不大以为然。一方的拒绝背后一定还有另一方的拒斥。或许是因为我们的某种拒斥在先?
一九九一年底去丹麦讲学,阿胡斯大学妇女研究中心给我的题目是“谈谈《第二性》对中国妇女的影响”。没有想到,这个题目着实有些让我为难。当我面对它时,才发现,此书对我们的影响,远不像在西方妇女中和她们想像的那么大。她们想当然地认为,此书既然在西方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震动,在古老落后封建的中国一定会有振聋发聩的作用。
我让她们失望了。
我告诉她们,在中国大众读者中,这本书的影响不在它的内容,而在它的名字——但却不是它的本名“第二性”,而是台湾中译者和大陆盗版人另外附加的名字“女人”。最早在大陆面世的书名是《女人——第二性》。一个“女人”,比“第二性”的说法更重要、更触目,是因为在我们的意识形态中,女人原本是“被压迫、被奴役”的第二等级,说她是“第二性”,不是什么新鲜的或犯忌的观点;但说到“女人”,并且用作书名,却很有些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个体书市也刚刚出台,这本书出现在书摊上,与久违了的政治秘闻和色情报刊陈列在一起,“女人”两个大字赫然入目,留人驻足,很是新鲜,于我们这个“男女都一样”、久已丢失了女人的社会像是一种别有意味的挑战。
当时,我就这样实话实说了,很让人家沮丧。还记得那位曾经被该书带上女权主义一线的“蓝袜子”领袖人物一脸尴尬,不大礼貌地责问我:“既然这本书对中国妇女没有什么影响,你为什么还要组织人去翻译它?”
仅仅因为它是现代女权主义经典之作,翻译经典也是我们的传统;还是因为它开启当代新女权运动之先河,曾经是西方女人的床头书、必读书?
是的,这些都是理由。更重要的是,尽管它在我们的社会中没有产生太大影响,甚至在出版评论界也没有得到应有的反响,可它却影响过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影响过我们一批在这块土地上较早从事妇女研究的女性学人。
在我,当时读这本书,要紧的不是它对女性的论述,而是作者研究女人的女性立场和自我反观的态度。它给我一个信念: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上,无论在哪片土地上生活,女人其实并不孤独。对女性的认识,可以从女人、从我们自己起步。
关于女人,《第二性》有两个主题。一是“观念中的女人”,讲夫权社会和男性中心观念怎样诠释和塑造女人,以及女人在这种境遇中的历史过程,即女人是怎样被造成的。二是“现实中的女人”,波伏瓦详尽陈述了女人作为第二性别的种种表现,不无尖刻地指出:“是男人所完成的技术发展解放了今天的妇女;是男性的伦理转变,通过节育引起了家庭规模的缩小,使她部分地摆脱了母性的束缚。……多数女人是听天由命的,她们不想采取任何行动。那些试图改变命运的女人,不想受她们特质的局限,不想被它战胜,而是想战胜它。即使她们干预了世界事务的发展进程,也还是和男人一致,还是在根据男人的观点行事。”全书大约六十多万字,围绕着一个基本思想: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造成的——是按照男性的愿望和意志被造就出来的。这句话像是《第二性》的代言词,广为流传,成为新女权运动向夫权社会作战的宣言。
但是,波伏瓦从来也没有打算认同女权主义,她始终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忠实的追随者和表现者。
如果说,女权主义企图划清“性别”阵线,将妇女看做一个阶级以共同对付父权社会;那么,波伏瓦则是走了另一条路线:在存在主义哲学引导下,通过“个人”奋斗去改善个人的处境,既不与阶级结盟,也不与女人为伍,无论“他者”(the other)怎样, 径自塑造一个自我(the one)——观其一生,波伏瓦自己是这样认识, 也是这样实践的。
我们不难发现,“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社会造成的”这种思想,其实不是波伏瓦的独创,而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回声;正像当年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虽然通篇都在批判卢梭,其思想基础仍然主要来自“天赋人权”。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正是具有法国自身传统的启蒙思想和人文主义精神的自然延续。在这里,不幸正被波伏瓦自己言中:无论当年的玛丽还是日后的自己,即使她们可以自立,并且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干预世界事务的发展进程”,其思想基础和人文立场仍然难逃男性中心之窠臼。
了解了波伏瓦的生平经历和她与萨特的关系之后,人们总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个时代,当她与社会上的普通妇女保持距离并且与女权运动划清界限,她从哪里得到支持并不断汲取精神上的力量?
不是别人,就是萨特!
我们总在颂扬波伏瓦的特立独行、独立不羁,细看她的一生,她在思想上和情感上其实从来就没有真正独立过。在思想上,她始终是萨特的追随者;在情感上,她一直没有摆脱被萨特奴役的地位。难怪萨特对她会说出那句名言:“我把你接管了。”
这样看波伏瓦和萨特,像是现代的“男人和女人”的创世神话——一个新的夏娃,仍然追随着亚当——解构这个神话,也成为当代女性真正地走向真实的(而不是虚假的)独立的必要起点。
再说《第二性》的影响。
读过或没有读过《第二性》的人,都知道波伏瓦的这句话:“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生成的”,并且不假思索地引用或附和,像是在附和一条公理。
但我不赞同它。从我所生活的事实和我成长的环境出发,很难苟同波伏瓦的这种说法——因为我的“走向女人”的起点,就是必须面对“天生是女人”的种种不便;我的妇女研究的起点,就是尽量客观地(而不是理想地)面对生为女人种种不可改变的、自然的和历史的命运。
我当然理解波伏瓦为什么这样讲。它向“天生的”宿命论宣战,反对以自然生理结构为基础的性别本质主义,企图为女人的独立和平等在理论和观念上扫清道路;很有些像是我们的社会中曾经广为宣扬的“男女都一样”,竭力把女人提到男人的高度,旨在倡导并鼓励妇女解放。两者用心同样良苦,在妇女解放进程中都起到了切实的推动作用,但从今天的生活出发,从更长远的妇女利益出发,却不能不指出,以上两者无论在理论上怎样可以自圆其说,在现实生活中其实都是“不真的命题”。
真实的情况确实有些像自然界中的“公理”,明摆在我们面前,如果不是蓄意扭曲或者有什么特殊的动机,原本是谁都可以看到的事实:
首先,无论时代怎样变迁,男女其实仍然不同;
其次,女人的确是天生的,而女人身为“第二性”的屈辱地位则是后天生成的、是男性中心社会的产物。
波伏瓦当年详尽分析了“(男)人造女人”的历史,力图破除将女人“第二等级”的社会身份本质化的神话,鼓励妇女向所谓“天生的”性别挑战,与世代沿袭的依附性告别,做独立自主的人。我们今天再破波伏瓦的“人造女人”的神话,则是要在本体论的起点上重建女人的主体地位,从思想上与男性中心的文化价值观念决裂。就是要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认同女性的主体身份;与自然共处,而不是否认自然差异或向自然宣战——这才是女人可能在精神和情感上真正站立起来、实现独立自主的基础。
在这里,我的评价和反省,不妨看做历史的反省。因为自《第二性》发表,五十年过去了。这是怎样的半个世纪啊!看看全球范围内妇女生活的巨大变迁,没有人可以责怪波伏瓦们的过时,因为没有她们的努力和身体力行的探索,一定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巨变。
就我读这本书至今,也差不多二十年过去了。如今再读,好奇的心态消失了,多出了冷静的审视和批评——尽管我带着批判的眼光重新解构波伏瓦建构的神话,却仍然不由得会时常赞叹她的机智和敏锐、她的博览群书和她的独到见地。无论时间多么久远,这些智慧的见解永远给人崭新的启示。我以为,全书最有价值的部分,是作者对既往一些重要的“妇女理论”的批判性清理。
首先,是对生物学论据的批评,这通常是将女人置于“第二性”的最常见也是最顽固的依据。为了完成这种批评,波伏瓦几乎要把自己变成生物学家。她承认:“这些生物学上的原因极其重要。它们在女人的经历中起着头等重要的作用,是构成她的处境的一个基本要素。但我不承认这些事实为女人确定了一个固定不变的、不可避免的命运。这些事实不足以确立两性等级制度。”
进而,是对精神分析学的批判,这在当时是一种被人广为引用、直接制约女人独立的所谓“科学”的及其追随者观点。波伏瓦毫不留情地向声名显赫的弗洛伊德宣战,把他的理论定名为“性一元论”。她着重分析了他为女人创造的“恋父情结”和“阴茎缺损”理论,指出“弗洛伊德以与(男孩)完全对应的方式去描述小女孩的经历,……但是显然,他在解释时所根据的不是事实本身,而是他的男性模式”。
最后,她以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为蓝本,认真分析其中隐含的“历史唯物主义妇女观”。她肯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了某些十分重要的真理。人类不是动物,而是一种历史现实”。却没有盲目地追随它,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经济决定论”在性别研究中的局限性。她承认恩格斯的理论体系比前面已经考察过的理论前进了一步,但却没有回答诸如:原始公有制怎样向私有制过渡、私有制是否必然要涉及对女人的奴役、以及为什么要将男女之间的对立归结为阶级冲突……这些最基本的问题。
在妇女争取解放的道路上做出种种努力之后,我们不能不钦佩波伏瓦理性思维的清晰和透彻,她的许多见解不仅是现实的,而且是先驱的,至今对我们仍有启发:
女人不仅仅是青铜工具创造出来的,所以单靠机器也不会把她消灭掉。为女人争取每一种权利、争取每一个全面发展的机会,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对她的特殊处境视而不见。为了认识这一处境,我们必须放眼于历史唯物主义之外,因为它在男女身上只看到了经济要素。
所以,基于同样理由,我们既不接受弗洛伊德的性一元论,也不接受恩格斯的经济一元论。精神分析学家会把女人对社会的所有权利要求,都解释为“男性化抗议”。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她的性欲不过是以多少有些曲折复杂的方式表现了她的经济处境。但是,“阴蒂”同“阴道”这些范畴,和“资产者”与“无产者”这些范畴一样,同样不适于全面认识一个具体的女人。
五十年代,波伏瓦和萨特以及他们独特的情侣关系一度成为社会反叛的标志,同时成为具有反叛精神的青年们的偶像——一旦成为偶像,他们最终也难以逃脱被人反叛的命运。这些年来,关于萨特的色情欲望,关于波伏瓦的个人品质,多有非议,一些不利于他们的新的材料不断面世。前几天,一位朋友从英国寄来刚刚英译发表的波伏瓦给美国作家阿格伦的情书,企图揭穿她与萨特的“理想爱情”神话。去年底,大陆也翻译出版了当年作为“第三者”被波伏瓦写进《女宾》一书的朗布兰女士的回忆录,对波伏瓦人格的另一面以及给她给他人造成的伤害进行揭露……一些公开批评的文章不断见诸报端。
对此,我能说什么呢?
早在十几年前我就说过,我不喜欢波伏瓦,不赞同她对母性的诽谤,不赞赏她一味迎合和迁就萨特的态度,从来就没有相信过她与萨特的爱情神话,更不欣赏他(她)们在存在主义的幌子下搞什么“三角”乃至“多角”的性爱关系……可是今天,当我重读她的《第二性》,尽管比往年多出了批评的眼光,却也更多了尊重。毕竟,她竭尽全部人生做出了她的努力,做了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可能做的事,也做了那个时代一般人做不到的勇敢探索——这种探索和革新精神,以及自我选择、敢为人先的勇气,我想,会是永恒的,总会在人类生活中得到共鸣,或听到回声。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日
(《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瓦著,(全译本)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一九九八年二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