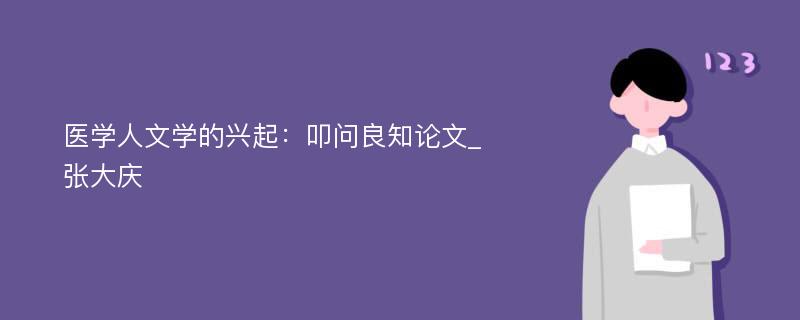
(北京大学医学史中心)
张大庆,医学博士。北京大学医学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医学史专业委员会主任。主要研究成果有《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医学人道主义的凯歌:科 学技术与20 世纪的医学》、《中西医学伦理学比较研究》 等论著多部。
医学人文学的兴起:叩问良知
1960 年秋,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达特茅斯学院。在这所以文理本科教育而著名的学院里,一场主题为“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的讨论会正热烈地进行着。虽然与会学者不多,但都是当时颇有影响的人物:杜博斯(R. Dubos,1901- 1982),洛克菲勒医学研究所著名微生物学家,第一个抗生素—— 短杆菌肽的发现者。他在这次会议上的角色是一位现代医学的批评家,一年前,他刚出版了一部名为《健康的幻影:乌托邦、进步和生物学变化》的著作,批评了人们将健康寄托于生物医学进步的奢望,后来他又以力倡环境保护而闻名世界。因此, 邀请既是著名科学家又是人文学者的杜博斯担任会议主席,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出席会议的学者有牛津大学荣誉内科教授皮克林爵士(Sir G. Pickering)、时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的齐索姆斯(B. Chisholms)、美国神经外科学奠基人彭菲尔德(W. Penfield)、著名内科学家麦克德莫特(W. McDermott)、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遗传学家缪勒(H.J. Muller)、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科学技术顾问基斯佳科夫斯基(G. Kistiakowsky) 等科学家, 以及《两种文化》的作者斯诺(C.P. Snow) 和《美丽的新世界》作者赫胥黎(A. Huxley) 等人文学家。
20 世纪60 年代是现代医学的转折时期。在基础医学领域分子生物学的兴起,为医学家探索生命与疾病的奥秘开辟了新路径,关于遗传、神经、免疫、内分泌等生命现象的研究获得重大突破,在临床医学领域,抗生素、激素、化学药物、心脏外科、器官移植、人工器官等的应用,让医生相信现代医学什么都能做也应当做。技术的力量助长了医学的家长制权威,医生们普遍认为,病人所需要的就是耐心地配合医生的各项诊疗程序,治疗效果就是对病人最好的关怀。人们也相信,医学技术的进步将逐步解决所有的疾病问题。
然而,此时也有人看到了现代医学面临的危机。由于疾病谱的变化,生物医学将对付急性传染病的策略应用于慢性病防治上不再灵验。伴随高新医学技术出现的医疗费用急剧上升、医学伦理和法律问题的增多,迫使人们重新审视现代医学。在这会议的开幕致词中,达特茅斯医学院院长特尼(S. M. Tenney) 博士指出,虽然现代医学的基础更加理性,但原应融科学与人文为一体的医疗实践却越来越偏离人的价值。因此,需要反思医学,人本身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考察医学与科学进步的良知问题,不是简单地追问人的生存与存在,而是要追问是何种生存、如何存在。
实际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忧虑是20 世纪60 年代西方社会的一种较为普遍的情绪。有人认为出现这种情绪来自三方面的原因:人口迅速增长的压力,福利国家那些大事铺张不近人情的计划,以及太空竞赛开始后,人们认识到只有一个地球, 人类同舟共济的观点成为了常识。“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 会议的举行,是一些学者睿智的洞察力在这个具体问题上的折射。1962 年,卡森《寂静的春天》所展示的杀虫剂对人类的危害, 以及随之不久发生的妊娠呕吐缓解药物“反应停”导致畸形儿出生的事件所暴露出来的时髦药物的潜在危险,都验证了杜博斯们的担忧。
在达特茅斯学院“现代医学中良知的重要问题”讨论会的同时,来自美国循道会和长老会的牧师们,也在讨论宗教在医学教育中存在的意义。在西方,宗教与医学的缠绕根深蒂固, 但在现代医学的冲击下,宗教之于医学的意义日渐淡薄。如何促进医学中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成为牧师们重建医学与宗教联系的核心问题。1965 年5 月,美国循道会和长老会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医学教育问题的“医学教育与神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由8 位成员组成,其中有4 位牧师、1 位心理学家、3 位医生, 医生中2 人是医学院行政管理官员,1 人是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AAMC) 成员。委员会认为当时在医学教育中有三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即去人性化(depersonalization)、分子生物学中心论(centrality of molecular biology)、基于机械论医学的教学(teaching of mechanistic medicine),因此,应当在医学院增设有关人文教育的教席,以制衡医学过度技术化的倾向[1]。
科技的进步让医生相信现代医学什么都能做也应当做,医生越来越依赖大型医疗设备等技术手段。
医学人文学科建制化:融通与创新
美国教育家弗莱克斯勒于1910 年发表的关于美国医学教育的报告,导致了美国医学教育的革命性变化。美国的医学教育以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为模式,建立了基础医学科学和全日制临床医生制度,极大地提高了美国医学教育与医学科学水平, 并在不长的时间内,使美国的医学科学跻于世界前列。“医学教育与神学委员会”期望能重复这个美国医学教育的神话,将人类价值引入医学教育以革新美国的医学教育。
1966 年,“医学教育与神学委员会”通过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向84 所四年制医学院发出调查问卷,了解医学人文类课程的教学情况,大多学校的回答是暂无,只有10 所开设过此类课程。委员会通过问卷和考察,发现医学教育存在着严重忽视人文教育的倾向,于是决定设立一个计划,筹集资金和建立机构, 通过开展一系列活动来促进医学人文教育,主要包括课程体系、设置专门学科和长期教席。委员会希望该计划能获得美国医学会(AMA) 和美国医学院校联合会的支持,获得学术上的合法性。
1969 年,该委员会的学院组举行会议,来自芝加哥大学、佛罗里达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大学医学院的10 位从事医学与人类价值教学和研究的教授与会, 其中包括1960 年达特茅斯学院那场讨论会的主席杜博斯。随着工作的深入,该委员会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更加世俗化和学术化,并于1969 年更名为“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Society for Health and Human Values),其目标是促进将人类价值作为医疗卫生专业人员教育的基本、明确的内容[2]。为了获得来自包括联邦政府和国家人文基金会的更多资金的支持,该学会淡化其宗教色彩,并成立“健康与人类价值研究所”,主要关注在医学研究和实践中缺乏考虑人的价值或考虑不够的问题。
第一个在大学中设立医学人文学教育和研究独立建制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医学院医学人文学系。1964 年,佛罗里达大学医学院院长哈里(George T. Harrell) 应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之邀创建一所新的医学院。哈里设想建立一个新型的医学院, 其新的课程体系将强调理解社会中家庭的重要作用,研究慢性病发生中生活和行为方式的影响,理解疾病和医疗保健中的哲学、精神和伦理问题。因此,该学院继设立了内科、外科学系后,1967 年又设立了家庭与社会医学、行为科学和医学人文学三个系[3]。医学人文学系旨在应用人文学科方法和理论来审视医学教育和实践。当时,医学人文学和生命伦理学的概念尚未形成,该系创建后首要任务是确定课程设置,将人文教育综合到医学教育体系中,这无疑是一个创举。1970 年代中期,该系与临床学系合作,建立了一个“人文医学:临床教学计划”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人文医学中心”(The Center for Humanistic Medicine)。
20 世纪70 年代以后,现代医学技术带来的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日显突出,促进了医学人文学科的建制化发展,许多大学的医学院纷纷成立了医学人文学教学和研究机构。医学人文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也得到迅速发展,许多大学设立了跨学科的医学人文学研究生培养计划。医学人文学科在美国的发展也影响到世界其他国家,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欧洲、亚洲、南美洲、大洋洲一些国家的著名大学也陆续建立了医学人文学的教育和研究机构。
一般认为,一个学科的建立应有三个代表性标志,即在大学中设立教席、建立独立的学术团体以及拥有自己的专业期刊。最早的医学人文学术团体是“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在1970 年代以后,随着生命伦理学的兴起,生命伦理与医学伦理学科得到迅速发展,在医学人文学科群中占据了突出地位。因此, 有学者指出,在20 世纪上半叶,欧美各国主要是通过医学史课程来培养医学生对医学中人文价值的认识,在20 世纪下半叶, 医学伦理取代了医学史,成为医学生认识和分析当代医学危机的工具[4]。
20 世纪后期,面对当代医学和卫生保健中日益增多的人的价值问题,人们认识到解释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宽阔的视野。1998 年,美国健康与人类价值学会与生命伦理咨询会(Society for Bioethics Consultation,SBC) 及美国生命伦理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Bioethics,AAB) 合并为美国生命伦理与人文学会(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Bioethics and Humanities,ASBH)。1999 年,英国医学人文学会(Association for Medical Humanities) 成立,并创办了一本国际性同行评议的《医学人文学》杂志(Medical Humanities)。2001 年5 月, 由威尔士大学和Nuffield 信托基金会联合发起的一个研讨会在威尔士波厄斯郡举行。会议目的是提供一个深入探讨医学人文学的机会,研究如何能使之发展为一个有价值的大学教育与研究领域。2004 年11 月, 澳大利亚医学人文学会(The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Humanities) 也宣告成立[5]。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我国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在各医学院校陆续开展起来,来自医学史、自然辨证法、医学伦理学以及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在承担着传统医学人文学科的教学和研究的同时,也开设了一些新兴的医学人文学课程并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如医学文化人类学、生命伦理学、医学美学等。90 年代,国内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到建设医学人文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必要性,在南京、大连、上海、北京分别召开过医学人文学学术研讨会,《医学与哲学》等杂志上也不断有呼吁和讨论医学人文学学科建设的文章,也有部分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新闻出版界人士开始关注医学人文学问题。医学人文学科研究的相关机构有了一定发展,这些举措表明国内学者对医学人文学的学科建设已有了共识。
医学人文学强调人的存在和价值,在此方面,中医的优势日渐明显。图为同仁堂中医专家义诊。
理解医学人文学:躬行更待深知
虽然医学人文学的概念已为学界所接受。然而,关于医学人文学的学科性质、研究领域、学术范式等却存在着不同的理解。例如,《医学人文学》杂志将医学人文学定义为一种跨学科的探索,旨在研究和阐释医学实践的性质、目的和价值;寻求一种对生命特性的科学理解和对个体经验的人文理解的综合。而澳大利亚医学人文学会给予的概念是,医学人文学是有关“人的科学”,以历史、哲学、文学、艺术等学科的观点来理解健康、疾病与医学。它旨在跨越临床医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藩篱, 促进跨学科的教育与研究,从而使得病人获得最好的医疗服务。医学人文学反映了医学界逐渐认可了医学是一门包括“人的科学”(science of the human) 在内的复杂学科。
在医学文献中,医学人文学这个词具有多重含义,有人仅仅将之视为医学伦理学的同义词,或将其作为人际沟通技巧、行为科学的一部分,也有人提出医学人文学实质上是一种人文的医学。有人将它视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也有人认为它应当是一个学科群。
著名生命伦理学家佩雷格里诺(E. D. Pellegrino) 则从医生素质的构成上来阐述他所理解的医学人文学:作为医学基础的人文学科包括文学、哲学、历史、艺术、音乐、法律、经济、政治学、神学和人类学等。这些人文学科在医学中具有正当合理的位置,它不应只是一种绅士的品质,不是作为医疗技艺的彬彬有礼的装饰,也不是为了显示医生的教养,而是临床医生在做出谨慎和正确决策中必备的基本素质,如同作为医学基础的科学知识和技能一样[6]。
佩雷格里诺的概念实际上涉及到医学人文学的性质问题, 即医学人文学与医学科学的关键问题。一种看法是医学人文学可“软化”医学科学的“硬核”,强调医生对病人的理解与关怀, 但并未在本质上改变医学实践。这种“医学人文”实质上等同于过去所谓“医疗的艺术”,一般被看作为医学科学的平衡力量, 形成与医学科学的互补。另一种观点认为医学人文学是将人放在医学的中心位置,来重建医学的框架。它提出医学需要哲学上的根本转变,跨越传统的边界,使临床医学不仅基于科学观察和实验室数据,也应基于理解和减轻病人痛苦所形成的经验。这种观点期望将病痛的经验、病人的观点带入医学解释的模式。因此,医学人文学应是医学整体的一部分。
期刊文章分类查询,尽在期刊图书馆医学的艺术只是使医生人性化,而医学人文学则是要使医学人性化。
医学人文作为一个学科群的出现与20 世纪70 年代以后医学伦理学或生命伦理学的迅速发展密切相关。无论是从学者身份、学术团体还是专业期刊上看,两者间的交叉、重叠明显可见。最为典型的例子是英国《医学人文学》杂志的主办机构是英国医学杂志集团下的《医学伦理》杂志社。在美国也出现了医学伦理与医学人文教学研究机构和学会的融合。
将医学人文学科看作为一个旨在关注和考察医疗保健和卫生服务中的人类价值、探讨医学的终极关怀问题的学科群,其意义在于从历史的、哲学的、伦理的、文化的、宗教的等多个维度来审视医疗保健实践、卫生服务制度以及卫生政策的制定, 来探讨医学的本质与价值。尽管医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健康问题,但也动摇了长期以来医学所坚守的人类价值标准的基石。实际上,近几十年来,医学界也开始怀疑当代医学的安全性问题,循证医学(Cochrane) 的出现、循证医学合作中心以及临床优化研究所的成立,意味着医学界期望收集更多的临床治疗数据来重建医疗方案的准确度。当下对医学人文精神的强调,对医学职业价值的重估,目的也在于确保医学的正当性。英国医学总会在“明天的医生”中提到,人文学可以提供几个益处,包括培养临床医生与病人的交流能力,更敏锐地抓住病人散漫叙述的核心,寻找更多样的方法促进健康、减轻疾病和残疾的不良后果。特别是对于慢性病( 生物医学只提供部分对策),临床医学似乎可以通过将治疗本身与对病人独特经历的理解相结合,更好地服务于病人。这可以有助于避免开过多的处方( 或者偶尔开过少的处方) 和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再者, 患者对自己病因的解释往往不足取。况且疾病除了身体因素外, 心理因素也起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更多的交谈来理解疾病, 在诊断上也可能是重要的。此外,医学人文学还具有沟通医学与公众的作用。对医学技术和卫生服务的正确、适当的宣传是影响社会舆论的关键,目前医疗卫生中的问题,部分上也是由于医学界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不足所致。
在当今强调专业划分的境遇中,区分医学人文与医学伦理或生命伦理,或者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颇具吸引力的问题,以至于1999 年的国际生命伦理学大会( 在英国伦敦举行) 上,以及牛津大学和美国生命伦理研究机构海斯汀中心联合举办的研讨会上,都有专题讨论医学人文与医学伦理或生命伦理的关系。
格利夫斯(D. Greaves) 等人提出三种对医学人文与医学伦理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医学伦理是医学人文学的分支学科之一。另一种看法是医学人文学是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考察医学和卫生保健中伦理问题的一种跨学科方法,因此,道德问题只是影响整个医疗保健活动中的多种文化因素之一。第三种观点是将医学人文学作为研究临床医学中的知识探索与价值诉求的一种综合方法[7]。哈佛大学的医学伦理学家威克勒(D. Wakler) 认为, 医学人文是叙述性的,通过它可以理解人类的疾病经验,而生命伦理学是分析性的,可为制订医疗保健政策提供依据。尽管存在着一些分歧,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赞同从宽泛的意义上来定义医学人文学。
其实,当代医学发展和医疗卫生服务所面临的难题,的确不是哪一门学科所能单独解释和解决的,需要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和跨学科的交流。医学人文学科作为一个由多学科交叉、综合形成的学科群,正是旨在确保医学技术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正当、公正与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与协调发展。2005 年,英国医学人文学会举行会议,主题就是“医学与人文学:走向交叉学科的实践”。会议的目标是:推进医学人文学在临床实践中的价值的讨论;关注医学与人文学科交叉研究;创造一个不同专业背景交流思想和经验的场景[8]。
当然,医学人文学科沿着这条道路发展也有其潜在的风险。作为一个多学科组成的交叉学科群,需要找到适应于交叉学科研究和教学的理论与方法。交叉学科的名称容易取,但实行起来有难度,有些交叉学科实际上是多学科的集合,学科间的联系不强,甚至是各自独立的话语,缺乏跨学科的对话。医学人文学需要的是真正成为一个各分支之间有机联系的交叉学科, 能进行跨学科的交流。
医学人文教育:知难,行亦不易
人文知识作为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并不是今天的创新,西方医学之父、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提出医生应具备哲学家的全部最好的品质:无私、谦虚、高尚、冷静地判断、必要的知识,以及不迷信。希波克拉底的思想被认为是最早的医学人文主义纲领。中国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则指出,欲为大医,除医学知识外,还需涉猎五经三史、诸子庄老。医学的人文传统历来为医生们所珍视。“偶尔治愈、常常缓解、始终安慰”(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的格言,体现了医生内心的谦逊与关爱。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生物医学的迅速发展使得医学与人文学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医学分科的不断细化, 科学课程的内容日益增加,从而导致人文社会科学的内容被逐渐压缩,医学生的人文教育被专业教育所取代,更加注重实验室技能的训练。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 世纪70 年代。
伴随医学技术发展而出现的一系列社会、伦理、法律问题, 不仅刺激了学术界的研究转向,在医学教育中,人文学科的价值再次得到强调。欧美各国医学院校都将医学人文学科作为医学教育的必要内容,提出医学人文学科是培养高素质医生的基础。这种跨学科的医学人文学建构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当代卫生保健难题,无论是地区、国家还是国际的,不能在任何单一学科范围内解决,都需要多个学科合作与综合:科学、人文、历史、法律、医学、公共卫生、哲学、教育、人类学、社会学。
美国大学的医学人文学科设置大多以教学和研究生培养项目的形式出现,参与项目的成员来自不同院系,一般专职教师不多,主要采用双聘制来解决师资问题。也有部分学校设立了医学人文学系或研究所,教学研究力量较强,可培养医学人文学科的博士。美国许多医学院属于专业学院,学生在本科毕业后进入医学专业学习,他们在本科阶段已学过医学人文课程, 因此具有较好的人文素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校的科学史和医学史系的本科生,几乎有一半是准备本科毕业后考入医学院的。所以普遍来说,美国大学医学人文课程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如通过学习能判别卫生保健和研究中的道德、哲学和社会问题;理解医学伦理学的核心概念;评鉴不同观点;理解相关法律、文化和历史观点;具备阐明、评价和辩护特殊医疗情况的能力。通常情况下,医学生要参与学术活动, 独立完成一个医学法律、伦理或人文学科方面的研究课题。
美国医学生在医学院学习期间,每年都安排有医学人文学课程。前两年主要是与医疗实践相关的重要的伦理、法律和政策问题。第三年学生进入临床,故安排以医患关系为主题的讨论课,要求学生从不同角度探讨医患关系问题,包括其伦理基础、权利和责任相关法律、医患交流的重要意义、影响职业判断和临床决策的因素等问题。由于在学生承担病人照顾的责任时是学习人文知识的最好时机,所以医学人文教学安排在临床阶段是较适当的选择。此外,学生还需参加有关“社会、法律和卫生保健:医生的作用”之类的讨论,使学生更多地了解美国卫生保健的制度、经济问题及质量评估,以及管理保健的伦理、法律和政策等宏观领域的知识和判别能力。
虽然,各学校开设的医学人文课程不尽相同,但目的都是拓宽学生的视野,掌握初步的解释和解决当今复杂的医疗保健问题的理论与方法。然而在有限的时间,学生不可能涉猎门类众多、内容庞杂的人文学科,医学人文学核心课程的概念因此被提出了,核心课程包括授课、小组讨论以及社会实践活动。如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医学院规定的4 门核心课程是:(1) 医学人文学: 工具与基础;(2) 伦理学的哲学与宗教观;(3) 医学科学导论;(4) 当代社会的生命伦理学,同时还要求学生参加一个研究伦理的讨论班,采用基于问题的学习(Problem-based learning,PBL) 教学法。完成核心课程后,学生可选择一个研究方向,如遗传研究与治疗、生殖技术、临终问题、生物恐怖主义、文化问题等撰写研究论文。还有学校将医学人文教学与学生的社会实践结合在一起,如参观医学博物馆,阅读或观看医学相关的文学、艺术、电影、电视作品,编排有关当代医学难题的戏剧,组织学生社团研讨医学人文问题等等。
20 世纪90 年代,英国医学总会提出了本科医学教育指南, 改革课程设置,重新引入更加注重医疗实践中的认知和情感成分的博雅教育[9]。伊文斯(M. Evans) 提出应将医学人文学科列入医学教育的基本的、核心课程体系中,作为理解医学和医疗保健的基础[10]。虽然,医学人文学科不是采用传统的医学方法, 以目的、方法、结果、讨论和结论的形式来呈现“研究证据”, 而是按照人文研究的范式,以沉思、阅读和理性的辩论,为医学的人文价值提供辩护,但这种理性的争辩,对传统观念的挑战和疾病经验的诠释,在某种程度上却是原来的医学教育中所缺乏的[11]。
我国目前医学人文学科还处在创建初期,国内一些高校建立了医学人文学研究所或中心,医学人文学科教育与研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还有许多大学尚未形成独立的建制,课程开设随意性大,缺乏学科规范,而且大多数课程是依据学校或教师的兴趣开设的,缺乏学科整体性规划,课程变动性大,因此许多课程的教学和师资质量难以保证。因此,现有的学科划分严重地制约了医学人文学科的发展,确定医学人文学的核心课程, 是目前我国医学人文学科教学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欧美国家,新兴学科的创建大多以项目的形式出现。诸
如医学人文学之类的交叉学科项目,大多由来自不同院系的教师组成,项目不仅开设课程、进行学术研究,而且还承担研究生培养,经过一定时期的发展,必要时可建立专门的系、所。这种灵活的模式有利于新学科的成长。而我国过分强调学科划分,如医学人文学科被分散在哲学类、社会学类、政治理论类、教育学类、中医学类等不同的类别中。客观上讲,这种以知识源流为依据的划分方法,虽然可反映出分支学科与母体学科之间的衍生关系,但也忽视了交叉学科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因此, 以横向联系而不是按纵向梳理构建学科群更适合于跨学科发展和交流的特点。
纵观我国医学人文学教育的现状,有待改进之处实多。但医学人文学作为当代医学的一个日益凸现的方面,它倡导、宣扬和维护人文精神,珍视“人”的概念,是医学传统中最为绵长深远的一脉,也是医学的实质和精髓。医学人文的研究和教学对医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人文教育在医学生身上播下的种子,日后的收获将会从广大的医疗卫生工作者的实践中体现出来,医学教育在这个地方如若留下空白将是至大的遗憾。目前在我国推行医学人文教育面临着众多的问题,可谓知之不易, 行之维艰,任重道远,尚需奋勉与努力。
参考文献:
[1]Fox. DM. Who we are: the political origins of the medical humanities, Theoretical Medicine 6:327-342,1985.
[2]www.asbh.org/about/archives/shhv.htm,2006-4-7
[3]Hawkins, AH,Humanities Education at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Medicine, Academic Medicine,78(10): 1001-1005,2003
[4]Jackson M. Back to the Future: History and Humanism in Medical Education, Medical Education. 2002,36:506-507.
[5]Gordon, J. Medical humanities: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 The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2005, 182(1):5.
[6]Pellegrino ED, Humanism and the physician. 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ee Press, 1979.
[7]Greaves D. et al. Conceptions of medical humanities. J. Med. Ethics, 2000, 26:65.
[8]Evans, H M; Macnaughton, J. Should medical humanities be a multidisciplinary or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Medical Humanities. 30 (1): 1-4, 2004
[9]General Medical Council, Tomorrow’s Doctors. Recommendations on Under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London: GMC, 1993.
[10]Evans M, Finlay I., eds. Medical Humanities, London, BJM Books,2001:pp197.
[11]Macnaughton J. Research in Medical Humanities:is it time for a new paradigm? Medical Education, 2002,36:500-501.
论文作者:张大庆
论文发表刊物:《中国医学人文》2015年第6期供稿
论文发表时间:2015/9/7
标签:医学论文; 人文学科论文; 人文论文; 人文学论文; 学科论文; 伦理论文; 美国论文; 《中国医学人文》2015年第6期供稿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