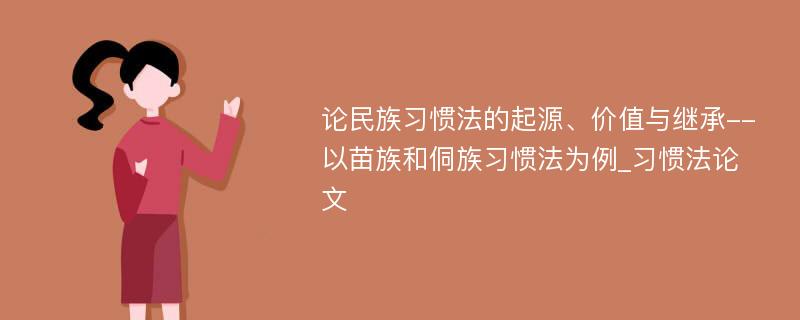
论民族习惯法的渊源、价值与传承——以苗族、侗族习惯法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习惯法论文,侗族论文,苗族论文,为例论文,渊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习惯法是民族地区适用的民间法,相对于国家法而言,民族习惯法具有民族习惯路径、个体心理依赖、民族文化传承的支撑。在当代“以法治国”观念下,要想有效利用习惯法的资源,就需要研究习惯法的基本渊源、功能,以谋求如何传承更新,形成现代法律文化观念,在实践中通过理念与制度的双轨推进民族地区法治,维护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
一、民族习惯法的本质、渊源与形式
民族习惯法是由少数民族或民族地区的社会组织约定的一种民族性、区域性的人们的行为规范。关于民族习惯法,有不同的称谓。有的叫规约,有的叫款约,有的叫章程,有的叫古法,有的叫榔规,有的叫民法,有的叫规矩,有的叫料条(规条),有的叫阿佤理。(注:参见吴宗金主编:《中国民族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56页。)“习惯法”一词,是经由近代西方法学、民族学等学科传入我国并采用的。根据我国台湾学者杨仁寿先生的考察,成文法、习惯法与法理,为法律之三大渊源。在18世纪以前,各国几以习惯法为主要法源,因为一则法典未立,二则社会关系单纯。迨19世纪,各国法典纷纷制定,在“法典万能主义”思潮影响下,成文法为法律之全部内容,对习惯法固多方歧视,更根本否认法理可为法源。洎乎20世纪以后,社会情况复杂,且变化甚巨,成文法不能适应实际需要,习惯法与法理之地位因而日趋重要,判例及学说,亦成为补充的法源。但一般而言,习惯法在民事领域广泛存在而且普遍适用,而刑事领域的习惯法则因与罪刑法定原则有所悖反而遭到排斥。(注: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209页。)习惯法作为民间法之一种,弥补了国家制定法之不足。尤其在民族地区,民族习惯法因为地理、文化等因素深深地植根于少数民族社会,影响少数民族的社会运行与文化发展。
(一)民族习惯法之本质
一般认为,习惯与习惯法是不一样的。习惯法与习惯之区别标准,论者观点不一,有意思说、确信说、惯行说、国家承认说四种。实务上一向认为,习惯法之成立要件有四个:人人有确信以为法之心;于一定期间内,就同一事项反复为同一之行为;法令所未规定之事项;无背于公共秩序及利益。此乃兼采诸说。在实质上,固以多年惯行之事实及普遍一般人之确信心为其基础;在形式上,仍须透过法院之适用,始认其有法之效力。法院如认其有背公序良俗,即不认有法之效力。(注:参见杨仁寿:《法学方法论》,第205—209页。)这是对习惯法的传统判别标准,是沿袭着“习惯法反映国家认可和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习惯”的概念。(注:《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87页。)笔者所理解的习惯法是相对于国家制定法而言的,依靠某种社会组织、社会权威而实施的具有一定强制性的行为规范。这种理解在一定意义上与“民间法”、(注:参见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66页;张晓辉等:《云南少数民族民间法在现代社会中的变迁与作用》,《跨世纪的思考——民族调查专题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固有法”(注:参见周勇:《法律民族志的方法和问题》,《人类学与西南民族》,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和“原始法”(注:参见田成有:《原始法探析——从禁忌、习惯到法起源的运动》,《法学研究》1994年第6期。)比较接近。
习惯法是法吗?围绕该问题法学界曾经展开过激烈的讨论。(注:参见田成有:《“习惯法”是法吗——国家法立场上的审视》,王鑫:《习惯法不是法吗——从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立场审视习惯法》,http://www.ynift.edu.cn/yld/web/Article/index.asp;孙国华、杨思斌:《“习惯法”与法的概念的泛化》,《皖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形成原因既有自然地理、生活环境、经济状况、风俗习惯的因素,也有文化发展、历史传统不同的因素。(注:参见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我们区分民族习惯与民族习惯法的标准在于:习惯或风俗习惯包括的范围很广,是本民族全体成员共同自觉遵守的规则。习惯法则是民族内部或民族之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调整、处理人们的相互关系,由社会成员共同确认的,适用于一定区域的行为规范,它的实质是惩处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的法则。
(二)民族习惯法的渊源
习惯法之雏形,我们无法精确地判断它的产生时间。根据史料证明,原始社会末期已出现习惯法,自此后习惯法一直存在和发展。不同的少数民族习惯法渊源略有不一:比如苗族的“团规”、“联团合约”(即埋岩会议规约);瑶族的“石牌制”;侗族的“款”、“款条”。在侗族聚居的从江县信地乡,至今仍利用“款”的形式维护社会秩序。1979年立款碑“信地新规”,在序言中说,“国有律,寨有规”,确立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十六条规约。习惯法之所以能在民族地区沿袭下来,主要是基于三个原因:一是民族地区统治者鞭长莫及,所谓“听调不听宣”,“大抵人物犷悍,风俗荒怪,不可尽以中国教法绳治,姑羁縻之而已”,(注:《文献通考》卷330。)“蛮夷之俗,不知礼法,与中国诚不同”,(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0。)“不必绳以官法”。(注:乾隆《大清律例》卷37,《条例》。)民族地区在古代被视为“蛮荒”、“化外”之地,故习惯法能够保存良好且有一定发展。二是民族地区法制不健全。中国古代法典刑法规范发达,但关于钱债、田土、户籍、婚姻等方面的民事法律规范简陋,传统法律文化中存在“厌讼”意识,且民族地区的头人为控制本民族人民,也严禁“私自奔告”。三是王法与民族习惯法相辅相成,甚至出现过朝廷王法与民族约法相互援用的现象,使少数民族的习惯法有一个长期蕴存的客观条件。
根据笔者对云贵川三地少数民族状况的考察,各少数民族因为居住地域、文化习俗相异已经形成不同的民族习惯法,渊源及形式也表现不一。以苗族、侗族习惯法为例,我们可以管窥民族习惯法的渊源。
1.苗族习惯法。苗族西迁以宗支队伍为序,各宗支都置有一个木鼓,相互敲鼓以作联系。迁到新地方后,就按宗支重新建立自己的社会组织,叫做“立鼓为社”。各鼓社均有自己的民主议事制度,根据古理和传统习惯,制订规约。即苗族习惯法之重要的“议榔”制度。
“议榔”为黔东南之称,在湘西称“合款”,在云南叫“丛会”。榔规款约就是苗族的习惯法。苗族习惯法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过去都是口头传诵榔规,民国前后则用汉文记载于石碑、木牌上,立于寨旁路口,然后杀一头牛或猪。牛或猪拴在坪地中央,人们围在四周,寨老念毕《议榔词》后,把牛或猪杀掉,每户分一块肉,表示牢记榔规。饮血酒盟誓,表示遵守。明清时期,苗疆各民族的习惯法经过长期的演化,逐渐丰富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苗例》。(注:参见徐晓光、吴大华等:《苗族习惯法研究》,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29—41页。)经过中央王朝的认可,《苗例》在苗疆地区长期使用。《大清律例》明确规定:“苗人与苗人相争讼之事俱照苗例归结,不必绳以官法,以滋扰累。”(注:乾隆《大清律例》卷37,《条例》。)据一些资料所载,《苗例》所调整的范围相当广泛,涉及刑事民事诉讼程序各个方面。如,清朝贵州布政司冯光裕在其奏折中说:“其苗例杀人伤人赔牛十条、数条而已,弱肉强食,得谷十余石数石而止。”(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朱批奏折》(民族类),胶片编号70。)又据民国《贵州通志·土民志》:“苗有不明者,只依《苗例》,请人讲理。”该文献对苗疆地区司法审判中的神明裁判做了详细的记载。
苗族习惯法的实践说明,“议榔”之称虽略有差异,但不改其作为苗族习惯法的本质。比如贵州省从江县加勉乡苗族立有专门管理农业生产事宜的“发财岩”,专门用于管治偷盗事宜的“禁盗岩”,专管婚姻纠纷的“女男岩”。(注:参见徐晓光、吴大华等:《苗族习惯法研究》,第50页。)从江县孔明乡则将刻有习惯法条款的石碑称为“民法”。广西苗族通过“埋岩会议”,把一块平整的石碑的1/3埋入土中,碑上刻有大家商定的条规,违反何条受何处分,轻者罚款、戴高帽游街,重者活埋。
2.侗族习惯法。侗族的习惯法,最初为侗族“约法款”,主要表现为“款条”。“款”作为村社会议制的残余,(注:正是所谓“有款无官民作主”。参见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6—87页。)说明侗族仍然残留着原始社会的部分痕迹。(注:参见杨一凡、田涛主编,张冠梓点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少数民族法典法规与习惯法(上)》,第九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点校说明,第11—12页。)侗族的“款条”分别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款碑条。款碑是早期款组织起款时树立的一种特定石碑。这种碑一般都立在款坪中,日后的讲款仪式和执法仪式都在碑前进行。款碑有成文和不成文两种。一般来说,凡是建有款组织的侗寨,都有一个神圣的象征物——款碑。早期的款碑不刻文字,属于不成文法的象征。汉字传入侗族地区后,才以汉字刻成。这种款碑属于成文法。二是款词条。款词条是侗族习惯法的主要形式。原始的款词条由款首聚众共商,款首当众发布并付诸实施。它是一种立石为碑的盟诅要约,故有人称之为“石头法”。这种“石头法”最初比较简单,也没有什么固定的表述形式。由于当时侗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无法将有关条款用文字记录下来,不利于款众掌握。款首们为了便于款众记忆及在发布时使款众兴奋,于是采用词话形式,把约法编成歌词,日夜吟唱,世代相传。后来侗族文人将这些约法款词用汉字记音的方法记录下来,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手抄本”,这些手抄本就成了侗族习惯法中的主要成文法。近年来,在抢救民族古籍的工作中,湖南、广西、贵州等地均已整理出版流传于当地的约法款词。这些书籍和资料,对研究侗族习惯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广西三江侗族自治县程阳马安寨老款师陈永彰保存有一部款书手抄本,该书迄今已有150多年历史。该书对款规款约的记载较全,其中约法规有18条,共756句。
(三)民族刑事习惯法
民族习惯法集中在生产活动、民事关系、婚姻家庭、社会组织和选举、刑事关系、诉讼证明等方面。刑法在习惯法中占有重要地位。民族刑事习惯法分为犯罪与刑罚两个部分,对具体犯罪行为和刑罚措施做了详细的规定。
1.民族刑事习惯法的犯罪规定。各少数民族认为构成犯罪的行为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侵犯财产。通过非法手段把集体的和他人的财产(动产和不动产)破坏或据为己有,主要表现有诈骗、勒索、偷盗、抢劫、贪污等。偷盗是各族中常见的罪行。但由于偷盗、犯罪观念的不同,处理上也不一样。如侗族《约法款》对“偷了圆角黄御,盗走扁角水牛并杀死卖掉的和不要的”处以一处葬、一坑埋的死刑;对“挖池破塘、钻箱撬柜、盗楼上谷米、偷地下金银”者,处以游乡示众,赶走他乡,其父不准再住寨中,其母不准再进寨里的刑罚。(注:参见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侗款》,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48—91页。)凉山彝族社会里,奴隶主黑彝偷盗甚至明拿奴隶白彝的财物,习惯法上不加追究。这表明某些习惯法已渗入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并且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了。佤族习惯法则规定偷盗本族成员的财物有罪,偷盗甚至抢劫外族的财物无罪,这是个别民族的特殊情况。在少数民族中,也存在某些坏头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敲诈勒索、贪污肥私,打击首倡罢免他的群众,使自己逍遥法外,破坏传统的习惯法。
二是侵犯人身权利。构成这种罪行的有:杀人、诬告、强奸。杀人有两种情况,一种在本族内部、本族与外族的械斗中,杀死了对方的人,这种情况不构成罪行,一般向对方赔偿命金或付抚恤金。佤族猎人头祭谷,杀人也无罪。凉山彝族奴隶主杀奴隶,也不会犯罪。用刀时误杀了人,也不构成犯罪,除道歉、赔命金或付抚恤金外,一般不加惩治。佤族剽牛时,乱刀之中误杀死人,操刀者无罪。如杀人致伤,不致死,一般是负担伤者的医疗费。另一种是出于个人利益的仇杀、抢劫杀人等故意杀人罪。一般的民族是一命偿一命,或赔命金。而在有些民族(如珞巴、怒、傈僳等),就会造成血亲复仇的武装械斗,直至对方死亡的人数与本族死亡的人数对等为止。
三是危害集体安全。犯此罪的表现有,在本族内部、本族与外族的武装械斗中,应出征的人员逃避出征,泄露军事机密给敌方,要治罪。失火,如自己的房屋也被火烧,无罪;如自己的房屋财产无损失,他人的房屋财产损失严重,视为纵火罪,如家财多,要赔偿。
四是其他方面的犯罪行为。如流氓罪、赌博罪、盗墓罪、拐卖妇女罪、虐待罪等,一般都要给予轻重不一的刑事处罚。
2.民族刑事习惯法中的刑罚规定。刑罚是对罪犯施行的最严厉的强制方法。当精神力量已较难保障习惯法实行时,便出现了刑罚。我国各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刑罚种类,各有不同。一般对案情不严重的初犯者进行教育,有的要写悔过书,除本人签名或按手印外,头人和家族的人也画押,悔过书由头人收执,如日后再犯,就按悔过书中所说的严惩。其种类有如下几种:(1)罚款。偷盗、诬陷、通奸、强奸等罪,以案情的轻重、坦白程度确定罚金。如系偷盗,一般是按原物的价值计算一倍到几倍、十多倍。但布朗族却例外,他们认为东西被偷盗是“水泼了是不能还原的”,罚款比原物价值少。重犯重罚。如果犯罪本人(家庭)无财产或财物甚少,由近亲或保人代之受罚。在审理过程中,头人、当事人误工、酒肉钱,均由罪犯承担。(2)逐出。屡教不改,危害、连累到本家族、本村寨者,驱逐出去或可留原居地,但要断绝一切的关系,不相来往,不能参加祭祖活动,对罪犯的生活、生死不过问。(3)囚禁。一般没有监牢,多系民房临时改制或兼用的。捕人、看守是头人本身或临时指派人去执行。如有钱赎罪,可免囚禁。(4)肉刑。有吊梁、鞭打、针刺、火烧、炮烙、戴刑具、水泡、挖眼、割鼻、断肢、去耳等等。有钱代罚,可减刑或免刑。(5)抄家。将罪犯家中所有的牲畜、家禽吃光。没收一切财产充公或没收部分财产充公。(6)死刑。屡教不改,民愤极大,或触犯习惯法严重条规者,经头人会商,本族或本寨、家族同意,才能执行死刑。计有活埋、淹死、烧死、五马分尸、刀砍、枪杀等刑种。最严重者会殃及家属遭到死刑。罪犯在偷盗、抢劫过程中,如被打杀至死,执行者无罪。一些民族的习惯法用刑十分严酷,不分年龄性别,主要刑具有木鞋、铁链、绳子等,有的还专门修了地窖做监狱。
关于刑罚的运用,有的民族的刑罚种类比较完善,基本体现罪刑相适应。如侗族《约法款》中规定了“六面阴”、“六面阳”、“六面厚”、“六面薄”、“六面上”、“六面下”等轻重不同的刑种。(注:“六面阴六面阳”是侗款罪行轻重的标准。六面阴六面阳也称六面重六面轻、六面厚六面薄、六面上六面下或六面死六面活。“阴、重、厚、上、死”和“阳、轻、薄、下、活”是对罪行轻重的形容。前为重罪、死罪,后为轻罪、活罪。比如,在湖南通道侗族自治县,六面阴六面阳的内容包括:六面阴指盗牛、盗银钱、盗林木、绑架杀人、勾生吃熟、挖墓盗坟六种重罪。六面阳指破坏家庭、弄虚作假、偷放田水、小偷小摸、移动界石、勾鸡引鸽六种轻罪。针对罪行轻重,款约规定不同的刑罚。)多数民族的习惯法没有制定出施行刑罚的细则,量刑的标准也不同,弹性大,往往不准确。
二、民族习惯法的价值定位
民族习惯法是少数民族的社会意识形态之一,是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少数民族的结构要素。习惯法既是法律规范,具有强制的法律效力,又是道德规范。它反映少数民族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少数民族社会构成反作用。关于民族习惯法与民族社会的互动性影响,由伊斯兰习惯法可以管窥。伊斯兰习惯法既构成伊斯兰社会的要素,反映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又对社会的各个层面施加控制、影响等。(注:参见杨经德:《回族伊斯兰习惯法的功能》,《回族研究》2003年第2期。)在少数民族的社会生活中,民族习惯法的作用是巨大的。对民族习惯法,我们应当从各个层面来系统地对其进行价值评判。
(一)裁判价值
民族习惯法的裁判价值在于通过社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对行为进行善恶判断,从而认可某种行为是否道德和是否合法。这一价值是基本而显在的,在侗族《款的起源》中叙述道:立款的目的是为了裁判纠纷。款词中说:在很古的时候,“舅王争天为大,汉王争地为重,二王相争,刀枪相杀,死伤无数,胜负难分……于是舅王断事在岩洞,汉王断事在岩上”,各讲各理,断事三年不成,最后“写书请客,奉牌请人”,倒牛合款,制定款约。(注:吴治德:《“侗款”的“款”字探源》,《贵州民族研究》1992年第2期。)侗款《永世芳规》写道:“盖设禁碑流传,以挽颓风,而同昌古道。事照得人有善恶之悬殊,倒有轻重之各异……朝廷制律以平四海,而安九洲。草野立条以和宗族,而睦乡里。……臻于盛世,则世食旧德,农服先畴工而居,疑商贸易,俾我等人人各安于本分,户户讲仁义而型仁。此善条维微,岂非千古不朽,章程未尽修斋,门例条规于后。”还规定:“衙门一切公务,应宜同心即办,不可违误。半途盗劫,务要齐团送官治罪。”(注: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第70—71页。)即要求对一切违反习惯法的行为严加惩处。正是通过榔规、款约等习惯法,少数民族肯定善行,否定恶行,通过善恶褒贬以培养人们的良好道德品质,为树立良好社会风尚起到了较大作用。
(二)教育价值
民族习惯法的教育价值在于帮助人们正确认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明确自己的责任与义务,让人们懂得区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学会做人的道德。以苗族、侗族的榔规、款约为例。苗族在举行议榔活动时,要用一头牯牛系于坪地中央,人群围于两边,寨老在中央庄严肃穆地念着榔词榔规,念毕把牛杀掉。议榔会议确定的榔规,人人都得遵守,不能违背,否则,轻者认罪、罚款,重者吊打以致处以火烧或投河的死刑。(注:参见徐晓光、吴大华等:《苗族习惯法研究》,第167页。)至于侗族款之教育价值更为明显:为了使款众能自觉遵守款规、规约,各个基层组织的款首,每年都要向款众宣讲款词、款约,名曰“讲款”。讲款时,集众于各坪,举行庄严的仪式,如黎平县的《六洞议款条规》开头讲:“今天老少都到款堂里来了,一个挨一个坐,人多很拥挤,请大家听我讲话,讲古人的道理……一片树林,总有一根要长得高些,一个班辈的人,总有一个来承头,古人过世了,我们后人来继班,代代来相替。”每当款首讲完一段款词,群众便齐声应和:“是呀!”侗族对款规、规约的宣传工作,除了“讲款”这种正式形式外,民间艺人或一些村庄的芦笙队在本村寨或到其他村寨演出时,也有演讲款词的义务,《侗款》中规定的“鸡尾的款”,就是芦笙队到其他村庄做客时演讲的“法规阴阳款”。(注:参见湖南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侗款》,第421—431页;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第167页。)
正是通过经常不断的榔规、款词的演讲活动,苗族的议榔和侗族的款将习惯法观念灌输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从而实现教育价值:
第一,它教育人们认识榔规、款词在道德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款规说:“汉家有朝廷,侗家有岜规,坡上的活路有十二样,大家都要来管好”。款规规定:“侗族的社会运转,都得按最高款规(即《九十九公款约》)的规定办事”;“种田要符合九十九公才熟谷,处世要符合九十九公才成理”。(注:吴大华:《民族法律文化散论》,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
第二,教育大家团结互助,宣传朴素的集体主义思想。侗族的款词说:“根据我们祖公的道理,祖父的道理,像溪水归河一样合成一条心,大家一起来合款,把两股水汇集拢来才有力量。”苗族的榔规讲:“我们地方要团结,我们人民要齐心,我们走一条路,我们过一座桥,头靠在一起,手甩在一边,脚步整齐才能跳舞,手指一致,才能吹芦笙。”(注:徐晓光、吴大华等:《苗族习惯法研究》,附录。)在生活方面,救济扶贫是同一村寨或同宗族人的义务。在节庆时,有共同的娱乐场所,村寨或四周的人还要互相请酒饭和唱歌或举行“添我”(打平伙)。同村寨或四周的人如有婚表喜庆之事,要请“满寨酒”,从而加强了互相之间的团结。
第三,教育人们遵守民族成员之间的人伦关系,防止乱伦行为发生。榔规说:“为了十五寨的道理,为了十六寨的规矩,勾久才来议榔,务记才来议榔。上节是谷子,下节是道杆,上面是龙鳞,下面是鱼鳞。公公是公公,婆婆是婆婆,父亲是父亲,母亲是母亲,丈夫是丈夫,妻子是妻子……各人是各人,伦理不能乱。要有区分才有体统,要有区分才亲切和睦。谁要如鸡狗,大家把他揪,拉来杀在石碑脚,教乖十五村,警戒十六寨。”(注: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省文联:《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第14集。)
第四,教育人们的行为符合“理”的原则,提倡道德修养。认为“理学没多重,千人抬不动”,“深山树木数不清,款碑理数说不尽”。要求人们加强道德修养,提倡为人要正直。“要学谷仓那样正,要像禾晾那样直”。“是好人,就要行正道”。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团结友爱,助人为乐。“见人落水要扯,见人倒地要扶”,“会做人栽甜瓜,不会做人栽苦瓜”。坚决反对品行不正,弄虚作假的行为。对那种“当面讲八百,背后讲八千”、“穿钉鞋踩人家肩”的可耻行为,习惯法形成强大的道德舆论加以谴责和制止,必要时辅以刑罚手段。
(三)调整价值
民族习惯法的调整价值体现在促进民族地区和谐稳定发展的功能上。民族习惯法本身没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但具有很强的约束力,从而间接补充民族法制,具有调整价值。(注:[日]小林正典著、华热多杰译:《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序论——以民族法制及其相关领域为中心》,《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基本上,民族习惯法的调整价值可以概括为十二个字:倡导善行、排除障碍、制止恶行。
第一,组织管理生产,防止和惩处违规犯罪行为。苗族《议榔词》说:“为粮食满仓而议榔,为酒满缸而议榔,在羊子跺庄稼的地方而议榔,议榔庄稼才有收成,议榔寨子才有吃穿。”早期的《议榔词》还对破坏生产活动的行为规定了明确的处罚:“剪人家田里的谷穗,盗人家田里的庄稼,轻罚白银六两,重罚白银十二两,不准拉别人家的牛,不准扛别人家的猪,谁违犯了,轻者罚银十二两,重罚白银四十八两。”(注:贵州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省文联:《贵州民间文学资料》,第14集。)各地的榔规都有若干管理和维护生产的规定。如规定生产的季节和每个月的具体耕作时间,规定了封山育林、禁止偷盗砍伐的条款。这说明榔规款约有利于维护民族地区的正常生活秩序,促进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
第二,加强社会治安,维护社会稳定。各民族社会组织的最重要的作用是加强自治联防,维护社会治安。侗族款词说,为了解决“内部不和肇事多,外患侵来祸难息”的不安定局面,要求做到“村脚着人管,村头着人守”;“村村有人把守,寨寨有鸡报时,事事有人处理”。为了保证村寨的安全,各寨联成大款,共同抵御外敌,倘若某村寨受到外敌入侵,就擂鼓、吹牛角、点燃烽火报警,火速向联款各寨求援,发出鸡毛炭木牌,鸡血沾几根鸡毛在木牌上,表示要飞速传信:加上火炭,表示十万火急。倘若接到木牌的村寨不履行应援的义务,事后就要按习惯法加以严惩,开除款籍,各村寨都会孤立这个村寨。对于危害社会治安者,“务要一呼百应,把他抓到手,擂他七成死”;对杀人犯“要用铜锣焙脸,铜镜砸脑,三十束麻线做头发,五十两蚕丝做肚肠”,(注:参见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第60、70—78页。)等等。
第三,维护恋爱自由,调解婚姻家庭纠纷。民族地区在恋爱婚姻习俗上历来主张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认为青年男女谈情说爱乃自然之事,不必约束过紧。但是,习惯法对婚姻恋爱中的越轨行为亦有规定:“如果男无信手,女无把凭,一身许两个,一脸贴两人……被我们抓住了,用手就拉,用绳就捆”;对“脱姑娘的花裹腿,揭女人花头帕”的道德败坏者,“就拿来千个石头,万塘水,把他沉放水里头”。(注:徐晓光、吴大华等:《苗族习惯法研究》附录。)在处理婚姻家庭问题上,榔规、款约也做了具体规定。比如,黎平肇洞的《六堂议款条规》规定:“男不要女,罚十二串钱,婚已过门,男弃女嫌,各罚十二串钱。吵嘴、打架、各罚钱五串。”(注: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第70页。)也有的民族习惯法规定:女方提出离婚,付给男方白银八两,男方提出离婚,付给女方白银十六两。(注:傈僳族的习惯法。)通过这些规定,使少数民族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传统习俗得到了保障,并进一步巩固和调整了民族地区的婚姻家庭关系。
三、民族习惯法之传承与民族法律文化之重塑
民族习惯法对少数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对调节社会的矛盾,巩固民族团结,保持和发扬民族传统道德等方面均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在承认民族习惯法在本质上、主流上具有积极意义的前提下,不应忽视习惯法的消极因素:(1)民族习惯法的制定组织产生于原始公社时代,原本是一种地域性的自治联防组织,但进入阶级社会后,它曾经被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统治阶级镇压贫苦农民,放纵邪恶的工具。(2)民族习惯法在处理纠纷时,有“神判”的作法,是人们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状况时产生的一种落后意识和宗教迷信活动,有一部分习惯法内容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如发生山林、风水、偷葬龙脉、典当田契等纠纷而公断不服的案件,就采取“砍鸡”、“捞油锅”等形式解决。“砍鸡”就是当着乡老或鬼师,对着当事人的面,把雄鸡的头砍断,放到地上,鸡倒在哪方,就断定哪方输。“捞油锅”就是把油烧沸,放斧头或其他东西进锅,叫当事人双方用手去捞,手不伤者为赢,手伤者为输。(3)保存有血亲复仇的遗风。郭子章在《黔记》中写道:“苗家仇,九世休。”即血亲复仇的遗风。又如侗款规定:各村寨之间村民生衅无法和解时,受害村寨就通过议会决定进行复仇,先派几个人去追捕逃犯,其余的人就到对方村寨进行报复,杀猪宰羊,捣毁房屋,直到抓获罪犯为止,(注:参见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第70—78页。)这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少数民族习惯法作为黄宗智教授笔下的“中间阶段”、梁治平教授所称的“第三领域”,(注:参见梁治平:《习惯法、社会与国家》,《读书》1996年第9期。)究竟如何发挥效用,以控制民族地区社会治安,化解民族地区纠纷矛盾,维护民族地区秩序?
(一)继承并创新民族习惯法,充分发挥民族习惯法的积极价值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伴随的是一个国家法与民间法并行的局面。民族地区的民族习惯法表现尤甚。如何利用民间的组织力量形成自生秩序,笔者认为必须实现社会自我控制和调节。民族地区的习惯法通常以乡规民约形式出现,是法律的一种重要补充,只要不与国家的法律相矛盾,能准确打击违法者,妥善调解纠纷,就应该予以提倡。从实证上考察,恢复乡规民约已多年的民族地区,以事实证明了习惯法在控制民族社会治安和维护民族地区秩序方面的潜在功能和巨大作用。比如侗族的起款、议榔等,通过拟定款约并经全村寨人举行喝鸡血酒的仪式后,款约产生约束力,任何违犯它的行为,都要受到一定的处罚。实践证明,“议榔”和“起款”只要加以改革,便能发挥很大的作用。法律是一种文化,与变化演进的社会相伴相生。(注:参见梁治平:《法律的文化解释》,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74页。)通过继承和创新民族习惯法,可以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发展,进而促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第一,民族习惯法中的优良传统丰富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它可列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精神文明建设当中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思想道德建设,各民族的习惯法本身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厚重遗产,怎样看待这份遗产,曾有两种不无偏颇的看法流行一时。一种认为,习惯法产生于旧的经济基础上,阻碍了任何人和社会的发展,主张全盘否定弃之如敝屣;另一种认为习惯法可以解决一切问题,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主张用以儒家为代表的伦理道德和社会规范来作为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良药。这两种或“全面否定”或“全盘肯定”的方式都是割断历史,没有出路的。
第二,民族习惯法是民族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好形式、好传统、好习俗。通过民族地区制定乡规民约的实践证明,它是行之有效的、成功的,可是在旧社会,它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在受到“左”的思想路线影响的时期,少数民族群众也不敢运用。现在应当继续发挥习惯法的作用,使它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笔者认为它的形式可以不变,但其内容是应当变更的,应当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更新和丰富其内容,使其更加完善,更好地为社会进步和民族共同繁荣做出贡献。
第三,以科学、理智的态度来对待民族习惯法。每个民族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一些传统的习惯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民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生活。这些从旧时代传袭下来的习惯法,尚有不少不健康、不科学,甚至与国家的根本大法相抵触的内容。这些糟粕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法治文明需要识别和剔除的。另一方面,民族习惯法中有不少属于民族文化精华的成分,不但符合和顺应国家的法律,还与民族的生产生活状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以及各种社会主义建设活动相适应,对民族和社会发展具有积极和正面的功能。
第四,以现代化的行为准则来检验习惯法。所谓现代化,从人的角度说,首先是人的行为方式的现代化。人的行为方式有一个从低级向高级、从简单到复杂、从单一到多样化的演化过程。以现代精神来衡量,现代化的行为方式至少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主动进取,二是讲求效率,三是开拓创新,四是诚信守纪,五是追求个性特征与群体意识的兼顾。(注:参见黄光成:《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页。)以此检视各民族习惯法,虽然不乏与现代化行为方式相同或相近的要求,例如很多民族都以诚信守纪为美德,但却很难指出哪一个民族的习惯法与现代化行为规则完全一致。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变革,社会在进步,各民族都应自觉将其传统行为方式及习惯法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使习惯法中优秀的成分发挥更大的现实作用。
第五,以国家法律引导民族习惯法的演变和发展。习惯法是“准法律规范”,它在民族地区与国家法律并行。执法中如果“一刀切”地将这些民族习惯法取消,既不现实也没有必要。少数民族习惯法具有重视群体利益,确认团结互助,鼓励勤劳能干,肯定合理需要,保护生态环境,处理简便迅捷,注重内在接受,形式生动形象等多方面的优势,在当代中国的法制化进程中值得采纳、吸取、继承。(注:参见高其才:《中国少数民族习惯法研究》结语。)但是,法治时代需要统一的国家法律,因此,习惯法只在一定时期内的特定地区适用,伴随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民族习惯法将逐渐向国家法的要求靠近。
第六,吸收民族美德,完善习惯法的内容。在侗、苗民族中,“款约”具有习惯法的性质。其内容主要是保护农业生产,维护社会治安,预防火灾等。根据侗、苗民族“款”意识较浓的特点,可以将“款约”中不合乎法律法规的内容删掉,将社会主义法制的内容注入“款约”之中,使之成为新型的少数民族自治的村规民约。侗、苗族在长期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传统美德。在运用习惯法调解民间纠纷时,应当发扬侗、苗族传统美德作为重要调解原则,并向当事人宣传“敬老歌”、“赞老歌”,宣扬侗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宣讲《侗理乡规》等。(注:参见邓敏文、吴浩:《没有国王的王国——侗款研究》,第127页。)1991年,贵州玉屏自治县的石洞、高酿等7个镇采取这种方法调解49起赡养纠纷,调解成功46起,成功率为94%,并聘请了200多名侗、苗歌手为义务调解员和普法宣传员,以生动活泼的形式开展纠纷预防工作。这样,既继承了民族传统美德和完善了习惯法,又对民族地区的治安秩序起到了维护的作用。
(二)协调习惯法与国家法的冲突,重新塑造民族法律文化
我国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作为治国基本方略。依法,主要指的是国家的制定法,但是否完全排除民族习惯法的固有功能与价值?笔者以为未必尽然,当下需要迫切注意的是解决民族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的冲突问题。比如,传统的所有权制度、传统的婚姻习惯法、传统的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制定法都有一定程度的不一致。民族法制的通行办法是变通法律制度,比如在刑事司法领域形成了“两少一宽”的刑事政策。我们应当重视运用民族习惯法解决纠纷,对少数民族习惯法予以特别考虑,但是要防止一个倾向:过分强调保持风俗习惯,这将背离民族法制的基本原则。笔者倡导,在国家法的主导下,尊重民族习惯、民族文化,重新塑造民族法律文化。
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文化”包括观念、制度和实践三个层面。观念的法律文化是法律应否被遵从、如何遵从以及调整范围的问题,统摄法律文化;制度的法律文化包括立法、司法解释等;实践的法律文化是在法律适用、法律实施中形成的。民族法律文化是伴随着各民族独特历史过程发展、繁衍起来的全部法律活动的产物和结晶,是各少数民族公民参与法律实践活动的基本模式。法律文化存在内生法律文化和移植法律文化之分。在各民族法律文化中,内生法律文化是历史发展的脉络,而移植法律文化多具有文化的强势。各民族的内生法律文化一般是在自身历史发展过程中,基于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特征积淀而成。之后的法律文化的发展对其存在惯性式的依赖,换言之,内生法律文化是民族的“活的法”,深刻地影响各民族的法律文化发展。我们必须承认,民族内生法律文化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也即卢梭所指称的除根本法、公民法和刑事法之外的“第四种法”,铭刻在大理石上,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笔者以为,要通过国家制定法的适度妥协和民族习惯法的不断更新式的传承,形成新型的法律文化,促进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