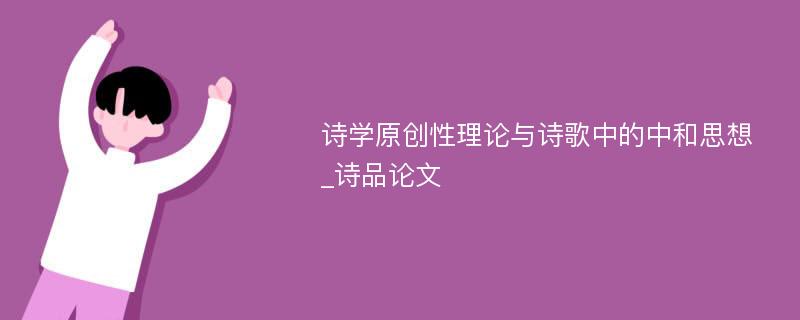
《诗品》的诗歌本原论与中和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原论文,诗歌论文,思想论文,诗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1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3)03-0152-04
(一)
从本原论的一个方面言之,钟嵘写作《诗品》的动机是为了使当时诗歌创作界、评论界由“邪”趣“正”,从“无序”至“有序”,从而达到一种新的平衡谐和。
中国诗歌从先秦至梁代,发生了许多变化。以诗体论,先秦有四言,有骚体;而从汉代起,四言退位,五言崛起,到汉末建安年间,遂蔚为大国,文人之作,蓬勃发展,作者如羽,作品如林;其盛况正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言:
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笃好斯文。平原兄弟,郁为文栋。刘桢、王粲为其羽翼。次有攀龙托凤,自致属车者,盖将百计。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
尔后,或陵夷衰微,或勃尔复兴。至齐梁之代,作者更夥,遂成风气。
《诗品序》述及当时士庶喜作五言诗的情况云:
词人作者,罔不爱好。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
裴子野《雕虫论》亦云:
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摒落六艺,吟咏情性。
魏晋南朝,风格屡改。除建安体外,相继有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玄言诗、田园诗、山水诗、永明体、宫体等。从而确立了五言古诗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崇高地位。但在“五言之制,独秀众品”[1]的时代,理论家们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祟,仍然把四言诗视为正体、雅音,而对五言诗采取了一种轻视、鄙薄的态度。如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即云:
古诗率以四言为体。……五言……于俳谐倡乐多用之。……然则,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
后之颜延之《庭诰》、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也有类似说法。前者云:
至于五言流靡,则刘桢、张华;四言侧密,则张衡、王粲。
后者云:
若夫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
甚至唐代伟大诗人李白也曾说过推崇四言,轻视五言、七言的话。孟棨《本事诗·高逸》即云:
(李)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已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故陈李二集,律诗殊少。尝言:‘寄兴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
钟嵘对挚虞、颜延之、刘勰把五言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只可为俳谐倡乐用之的俗体、流调、淫声的“高论”,是断断不能同意的。他写《诗品》专“品古今五言”,就有为五言“争正统”、“正声名”
的初心。其动机有似孔子“正乐”,为的是“使雅颂各得其所”(《子罕》)。名正才能言顺(《子路》有“名不正则言不顺”之语),只有先为五言脱掉“非音之正”的帽子,《诗品》亦才有写的必要。
而当时的创作界和批评界也呈现出混乱无序的状态。《诗品序》云:
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独观谓为警策,众睹终沦平钝。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朓,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
又云:
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
所谓“庸音杂体”,即非雅音正体;“人各为容”之“容”作“法”字解。《老子》“孔德之容”,《释文》引钟会注云:“容,法也。”《梁书·钟嵘传》和《全梁文本》、《古逸书本》、《诗品会函本》、《广博物志本》、《古今图书集成本》并作“各为家法”,即是对“容”字的诠释。彭铎《诗品注补》云:“或姚氏(梁书作者姚思廉)以意改之。”苏彦《苏子》云:“哀王道,伤时政,没过乎诗;……载百士,纪治乱,没过于史、汉。孟轲之徒,溷淆其间。世人见其才易登,其意易过,于是,家著一书,人书一法”(严可均《全晋文》)。“人书一法”亦即“人个为容”之意。由于创作上的无“正法”可依,作者们以“文质兼备”的曹植为嘲笑鄙视的对象,而“谓鲍照羲皇上人”,把“淫丽”的代表诗人鲍照捧上了天,并纷纷向他学习。和创作界的以“郑”为“雅”、视“中”为“偏”之风相应的是诗歌批评界的“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所谓“朱紫相夺”,是用的《论语·阳货》“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家邦也’”语义。故实际是说“雅郑相夺”。而“淄渑并泛”,亦和孔子有关。《列子·说符》、《吕氏春秋·精谕》、《淮南子·道应》皆有云:“孔子曰;‘淄、渑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此见《精谕》)。《诗品》用此以喻评论家的见识低下,不似易牙高明,能辨别诗的各种滋味。为此,钟嵘道出了他作《诗品》的本原:
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
原来,钟嵘之作《诗品》是为遂刘绘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之遗志。故《诗品》有树准的、溯源流、品高下、论利病等内容。其作法,亦与孔子托古改制、以复为创、以因为革相似。如钟嵘在为三十六位著名的五言诗人追溯历史源流时,把所有诗人都纳入《诗经》、《楚辞》两大系统,分属《国风》、《小雅》、《楚辞》三条源流。其用意就是使学诗者分清五言诗作中的“雅”、“郑”和“正”、“伪”,不要学近代的鲍照、谢朓,而要以古代的《诗》、《骚》为源头,从而革除诗坛弊端,把创作和评论引上正途。在这里,钟嵘表现出的“诗体无雅郑”而“诗作有雅郑”的观点,是十分正确、高明的。可惜的是,钟嵘并未能将此“雅郑”观贯彻到底。
(二)
从本原论的另一方面言之,钟嵘把诗歌的起源看作是“天人合一”的产物。
《论语》中言天处甚多,殆从自然和道德角度强调“天人合一”。《阳货》云: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这里,孔子把自然界的存在和变化视作天。认为春夏秋冬四时的代谢,万事万物的盛衰生灭,都是天的产物。和此以“自然”为“天”的说法相反,孔子又觉得“天”是有意志的,它可以主宰人的生存命运。故他说:
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
又说: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述而》)?
认为人的“德”和“文”(亦即“言”)都是“神灵的天”和“义理的天”的“与”和“夺”。在孔子的“自然”与“人”的“合一”而产生“万物”观念的影响下,后代儒家提出了关于文学艺术的起源新论——物感说。《礼记·乐记》即云:
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心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心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以,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乐记》这里第一次指出了“乐”是客观“外物”和主观“人心”相结合的产物,亦即“天”、“人”“合一”的结果。
钟嵘《诗品序》在论述诗歌的本原时云: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故照烛三才,晖丽万有。灵祇之以致飨,幽微籍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
又云:
至于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疑当作雪)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霜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
所谓“物之感人”云云,即《乐记》“感于物而后动”之意。注《诗品》者,多引《乐记》之文以笺之。如古直《诗品笺》云:“《礼记·乐记》: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后动,故形于声。”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在引古《笺》后而云:“《乐记》云云,又见《史记·乐书》、《说苑·修文篇》。”又云:“曹植《赠白马王彪诗》:‘感物伤我怀。’阮籍《咏怀》:‘感物怀殷忧。’潘岳《悼亡诗》:‘悲怀感物来。’张协《杂诗》:‘感物多思情。’……正所谓物感也。”因此,《诗品》是《乐记》以来的“物感说”的继承者。《乐记》所言“感于物而后动”之“物”,一指客观存在的自然界,一谓社会生活、人际关系。《诗品序》所言“物之感人”之“物”,也是如此。“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雪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即谓前者。钟嵘在评论中甚重这类因“四候所感”而产生的描写自然风物的诗篇。如他先在《诗品序》之末举证“五言之警策”时,就列了“王微风月”。于此“风月”,古今中外注释《诗品》者,多不能解,惟王发国师云:“风月”,这里指描写清风朗月、四时美景的五言诗。而王微今存的五首五言诗中恰有一首《四气诗》是写四季景色的。诗云:“蘅若首春华,梧楸当夏翳。鸣笙起秋风,置酒飞冬雪”。此诗写了春华、夏云、秋风、冬雪等四季(四气)中各季最有代表性的景物,所谓“王微风月”当指此[2]。后又在《诗品中》评顾恺之诗时,对顾恺之的一首描写四时美景的诗作,加以称道云:“长康能以二韵答四首之美”。无独有偶,古今中注释《诗品》者,对此句所指,亦多不能确诂。又是王师云:《诗品》原文中有误字:“四首”当作“四峕”。“峕”乃“时”之古文,与“首”形近易混。其句意当为:顾恺之能用有两个韵脚的四句诗描写四时美景。《艺文类聚》卷3所载的顾恺之的那首《神情诗》而后被《升庵诗话》卷11、《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74叫做《四时咏》或《四时诗》之诗作,就完全和钟嵘此评相合。其诗云:“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秋月扬明辉,冬岭秀孤松。”这正是一首以为两个韵脚(峰、松)、四个句子写四时(春、夏、秋、冬)美景的好诗。故品文之长康“以二韵答四时之美”者,必指此首《四时诗》无疑(同上章一八《晋常侍顾恺之〈四时诗〉》)。《诗品上》评谢灵运的“山水诗”云:“内无乏思,外无遗物”。其“物”亦指感荡心灵的自然景物,而“思”则是谓被自然景物所触动而产生的情思。钟嵘认为:把这种被自然景物所触动而产生的情思用吟咏的形式表达出来,就形成了诗歌。从这一认识看,诗歌当是自然之物和人之情思相结合的产物,换言之,即“天人合一”结晶。
“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云云,则是论述“物”的另一所指——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如何“感荡心灵”而产生诗歌。钟嵘说:“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此说有似后来韩愈《答李翊书》所说的“不平则鸣”。人的心情原本是平静的,但如果遇到幸事(如嘉会)和不幸(如离群)的影响,即“心灵”受到外界事物的“感荡”,人的心态就会失去平衡:或欢乐,或悲伤。长此以往,会严重影响其正常生活和身心健康。为了维持心理心态平衡的需要,人就需要运用种种社会性的手段来调节,其手段之一,就是诗歌。通过诗歌,人们将自己的波动情绪发泄出来,此即“陈诗展义”、“长歌骋情”。这样,心理上就可以获得一种满足,一种安慰,倾斜了的心态又恢复了新的平衡,“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马蒂思说:“一种艺术,对每个精神劳动者,象对艺术家,是—种平息手段,一种精神慰藉的手段。熨平他的心灵,对于他,意味着从日常辛劳和他的工作中获得安息”[3](P.261)。可与钟嵘“诗可以群,可以怨”之说合参。而“诗可以群,可以怨”云云,正见于《论语·阳货》。由此看来,钟嵘认为诗歌的产生确实为了实现心态中正和平不悲不喜(“怨”)的需要,也是为了谐和人与社会(“群”)的需要。
钟嵘还进一步把《礼记·乐记》的“气动说”第一次用之于诗歌发生论。《乐记》云:
地气上齐,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天地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
而《史记·乐书》也有相同的记载。当然,《乐记》此论仿自《周易·系词上》:“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王充《论衡·变动篇》云:“夫风至而树枝动,树枝不能致风。是故夏末,蜻列鸣,汉将啼,感阴气也。雷动而雉惊,蛰发而蛇出,起阳气也。夜及半而鹤唳,晨将旦而鸡鸣,此虽非变,天气动物,物应天气之验也。”钟嵘“气之动物”之“动物”之“气”即同于王充的“天气”、《乐记》的“阴阳”之气,亦即“自然之节气”、“天地之元气”。钟嵘认为:“物感说”并未能探得诗歌发生的终极本原,故在“物之感人”前又加上一句“气之动物”,把“气”这一根本性的范畴,作为全书开宗明义第一句的第一字劈头道出。因此,钟嵘的“气动说”,实际是“气本说”,曹丕的“文以气为主”[4],在钟嵘这里也就变成“文以气为本”了。
钟嵘关于诗歌本原的“气本说”、“物感说”,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实质。
(本文是在恩师王发国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谨此致谢。)
收稿日期:2002-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