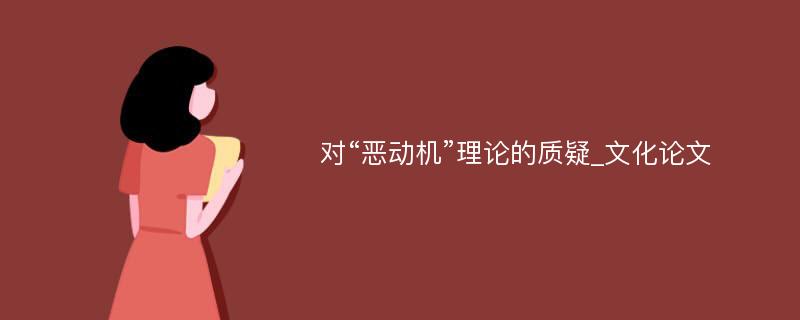
“恶动力说”质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一些领域的道德失范,在我国冷落多年的“恶动力说”又被重新提起。初衷是为社会开出一付济世良方。然而,其结果必将与我们的愿望相反,导致道德领域的混乱。
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因吗?
持肯定见解的同志大都是到黑格尔的著作中寻找理论根据,认为恩格斯曾就黑格尔的关于恶的观点发表过“肯定性”的意见。因此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自然也就成了不可动摇的真理了。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黑格尔的“恶动力说”问个究竟。
黑格尔从唯心主义的“人性恶”角度阐述过他的道德理念,认为人先天就是 恶的,如果没有恶为动力,就不会有人类及人类社会的进步;但他也洞察到善与恶的相互转化及恶的可克服性,认为,人只有常怀“罪恶感”,认识到自己是不道德的,才会产生道德自我超越和完善的追求,因为“人类绝对的和崇高的使命,就在于他知道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他的使命便是他的鉴别能力。”(《历史哲学》73页)在辩证思维方面,黑格尔远远超过他的前辈。
然而,黑格尔的理论偏见也是明显的:他一再重复“唯有人是善的,只因为他也可能是恶的。”(《法哲学原理》143页)“恶的本性就在于人能希求它,而不是不可避免的必须希求它。”(同前)他在张扬善的同时又肯定了恶,在肯定了恶的同时又混淆了善,在神秘的思辨中暴露出诡辩的痕迹,把人们误导到“善就是恶,恶也是善”的旁门左道之中。
黑格尔的“恶动力说”还留有大日尔曼民族骄横一世的印记。他毫不掩饰地说:“历史发展的本质是民族精神。在每一个时代,都有某一个民族受托负担起领导世界通过它已到达的辩证阶段的使命。当然,在现在这个民族就是德意志。”为此,黑格尔极力推崇凯撒、亚历山大和拿破仑,鼓吹“战争还有更崇高的意义”,国家是不受平常道德的约束的。罗素不无怀疑地说:“依黑格尔之见,人不做战争征服者是否能够是‘英雄’。”“他的国家理论同他自己的形而上学大有矛盾,而这些矛盾全都是那种偏于给残酷和国际掠劫行为辩护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286—290页)在政治上为恶势力辩护的黑格尔“恶动力说”,是赞美残暴、鼓吹战争、毁灭善良人性的理论,在以和平、稳定、发展为主题的现代社会,我们没有必要从黑格尔的一些业已过时的个别结论中寻求理论支撑。
如果不是将历史割成碎片残章,而是把它看作完整连贯的鸿篇巨著,我们不难发现,尽管“无论过去或将来,每个时代都有个别的、局部的、时而前进时而后退的运动,都有脱离一般运动和运动的一般速度的各种倾向。”(《列宁全集》21卷,123页)尤其是在社会阶级矛盾难以调和、民族矛盾难以解决、社会发生剧烈变革时期,社会超越常态发展,各种恶的势力就会突现或恶性泛滥,但这并不能证明恶的价值,恶性最终必然要被真理、正义所战胜。
人类确是踏着血泪走向光明的。但每一步留下的都是社会发展与道德进步大体一致的历史,都伴随着人的本质的重新改造、精神上的新的觉醒与个性的进一步解放。奴隶社会把“本能的人”从混沌、蒙昧中解放出来,标志着人与动物的真正分野;封建社会废除了奴隶人身占有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生存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打破了人身依附的封建枷锁,在一定程度上使农民成为自由的人;社会主义则从根本上清除了阶级分裂与对立,平等、友爱、互助、和谐的人际关系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开始实现。从完整的历史画卷上,我们看到的是恶不断被善克服的历史,恶的作用日益被削弱的历史,道德不断进步的历史。
如何理解恩格斯的那段话?
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的历史观时,曾提到过黑格尔,他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马恩选集》第四卷23页)主张“恶动力说”的同志,在回答历史发展与道德进步的规律时,曾依据恩格斯的这段话,力图说明恶在一定条件下对历史起推动作用,以解开“恶是历史发展杠杆之谜”。这是不应有的曲解。如果我们联系这篇文章的全文、马恩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他们的完整学说,那么,从恩格斯的这段话中应得到出的是与“恶动力说”完全相反的结论:
第一,不是恶对恶的惩罚,而是善对恶的合理否定。恩格斯所言的新的进步对神圣事物的亵渎,并非肯定恶的价值或对真正美德的不敬。它所表明的是,由于经济关系与社会关系的变化,原来的美德已经失去它存在的意义,而新质的善虽然按传统观念的标准是大逆不道的,但它毕竟是代表社会未来的那种道德。因此,在道德观念及评价标准上也必须弃旧图新,不能拘泥于传统习俗。而这种新质的善,不仅是社会发展进步的需要,而且也是道德领域革命的必然,这已赋予更新鲜、更生动的内容,使传统美德内涵在新的时代得扩展和补充。它不是简单盲目的抛弃,实质是否定之否定式的前进与上升。
第二,道德评价既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又是有一定客观标准的。“恶动力说”同时犯了两个错误:一方面陷入伦理相对主义不能自拔。另一方面又步入伦理绝对主义误区。他们不加任何分析地一律把情欲、物欲、权欲统斥为恶的本性的发作,从而确认恶是个人人生目的与历史发展的驱动力,但又不愿对人的欲望哪些是合理的应当满足的予以充分肯定,更不打算对不合理的欲望作出具体的令人满意的分析,笼统地把一切欲望斥之为“恶”,且又得出它是历史与社会发展动力的简单结论,这是不足以说服世人的。
诚然,道德标准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的确相距甚远。即便是从抽象意义上被视为“恶”的“政治野心”,如果置于一定历史阶段、特定阶级利益的社会背景下,也未必没有善的意义。历史上此类情况不胜枚举。如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礼崩乐坏”、“臣弑君、子杀父”,对于周王朝来说,必然是“大逆不道”、“违背纲常”、“来绝人伦”,因此周王朝的维护者力主“克己复礼”。但对新兴地主阶级来说,社会进步乃是“大义”,仅此而论,“灭亲”之举未必不仁,“子为父隐”肯定不义。而那些纯粹以恶的面目出现的社会罪恶现象,如横征暴敛、滥杀无辜、强取豪夺、鱼肉百姓等,除了加剧社会的动荡不安、最终导致“官逼民反”之外,对历史的发展从来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古今中外一切严肃的理论家,极少有直接为恶辩护的。
第三,对事实本身的认定与历史地批判,并不是一码事。一些人引证恩格斯上述那段话时,忽略了恩格斯分析恶的历史发展杠杆作用的前提是“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的社会。由于私有制本身的弊端,决定了在私有制社会里当权者的心灵活动不可能象无阶级社会的人那样纯洁,那样善良,他们对私利的无限追求,经常导致社会的道德危机、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长期的动荡不安,从而对人类生存构成严重损害和巨大威胁。马克思与恩格斯并不回避事实本身,但又坚持历史的批判态度。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建立在对以往一切社会的客观分析与深刻批判基础上的,其中也包括在道德方面对私有制社会的批判,从而得出资本主义一定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科学结论。他们在分析恶的真实历史作用时,除了无情的义愤和强烈的谴责之外,没有一丝一毫对它肯定的意思。我们对于经典作家的某些论点和论断,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客观前提和语言环境,而仅仅抓住一些只言片语,加以主观的理解。
我们今天需要“恶的杠杆作用”吗?
任何理论研究都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影响。“恶动力说”被重新提起,当然也不例外。
第一,关于评价善的新标准。坚持“恶动力说”的同志因为把善与恶同时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因而他们主张“不能简单地把效果上有利于历史发展的都看作本质上的善”,那么正确的道德标准是什么呢?由于善恶的主观颠倒,决定了他们无力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全面的回答,实际是主张无善恶标准。而在一切是非不明、美丑不分、善恶不辨的社会环境里,人们连何去何从都不清楚,又怎么能象“恶动力说”主张的那样去弘扬主体精神、追求自我实现呢?
善作为恶的对立面,它表现为对应当是的东西和值得赞扬的东西的道德上的肯定,本质体现利他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实际,判断行为的正当与否,价值有无,意义大小,归根到底要看道德主体的行为是不是“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是不是“有利于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是不是“有利于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弘扬正气”,是不是“有利于履行公民权利与义务、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决议》)。有了这样科学、明确的道德评价新标准,就能有效扼制各种假恶丑现象,极大地焕发起全民族奉献国家、造福社会、同心同德、振兴中华的高度热情,从而实现十二亿人共同绘制的美好生活蓝图。恶的现象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虽然还会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变换形式不断出现,但它犹如阳光下的个别阴影,我们有能力消除它,把不道德的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
第二,要用新眼光审视新事物。毫无疑问,坚持“恶动力说”的同志也看到了不道德现象大量滋生对社会的销蚀破坏作用,因此不无忧虑。但由于他们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常常把善的事物作为恶的去否定,而把恶的又当作善的来赞扬。例如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人们道德观念的转换,本是代表了社会进步的要求,是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但是一些同志一方面对否定个人利益、抹煞个性存在合理性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另一方面又把对个人正当需求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看作是用“卑劣的情欲”、“自私的物欲”来调动人的积极性,甚至把勤于经营、乐于冒险、“毛遂自荐”等行为也一律称之为对“恶”的刺激、利用的直接证明。这实际是在慷慨陈词的壮怀激烈之后,用更落后的观念裁断新生活,看不到当今道德内涵的丰富与道德本身的进步。我们的理论工作者应面向火热的现实生活来个思想道德观念的合理转变,不认识生活就不能真正解释生活,评价生活。
第三,我们必须摒弃“恶动力说”。社会主义条件下,道德上的恶受到了根本的限制,因为大量滋生它的土壤已不复存在。但是,作为与善对立的另一面,恶仍然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尤其是在新旧体制转轨、社会矛盾相对集中的改革时期。因此,我们不能放松包括道德建设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十几年改革的风风雨雨,我们已付出了不少代价,各种恶的行为也曾公开登场表演过,对于这些不道德现象人们早已深恶痛绝。实践证明,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