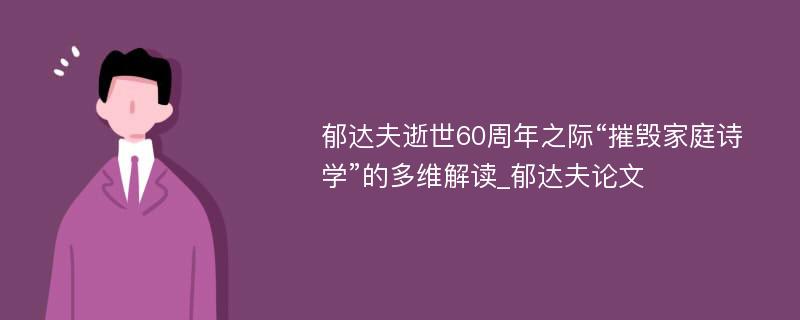
《毁家诗纪》的多维诠释——写在郁达夫遇难60周年之际,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维论文,写在论文,达夫论文,周年论文,毁家诗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39年初,香港《大风》旬刊计划出版周年纪念专号,编辑陆丹林特约郁达夫赐文。郁达夫便将自己从1936年到1938年间所写的诗词,选出诗19首、词1阙,详加注解,冠名以《毁家诗纪》寄了出去。以今天的眼光看,它们堪称郁达夫的一组自传诗史。对其进行多维阐释,是很有意义的。
《毁家诗纪》第1首诗是:
离家三日是元宵,灯火高楼夜寂寥。
转眼榕城春欲暮,杜鹃声里过花朝。(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这首诗原写于1936年的“花朝节”之夜,地点为福州。诗写好后本想寄给王映霞,后因它故未能及时寄出。三日之后,因有五六天未能接到妻子的来信心中忐忑不安,郁达夫遂在当天的日记中将此诗录出以抒想望妻儿之情。原诗并没有加“注”,所谓的“注”是后来加上去的。这首诗的“原注”是:
和映霞结婚了十余年,两人日日厮混在一道,三千六百日中,从没有两个月以上的离别。自己亦以为是可以终老的夫妇,在旁人眼里,觉得更是美满的良缘。生儿育女,除夭殇者不算外,已经有三个结晶品了,大的今年长到了十一岁。一九三六年春天,杭州的“风雨茅庐”造成之后,应福建公洽主席之招,只身南下,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实就是我毁家之始。风雨南天,我一个人羁留闽地,而私心恻恻,常在想念杭州。在杭州,当然友人也很多,而平时来往,亦不避男女,友人教育厅长许绍棣君,就系平时交往中的良友之一。(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诗人在这里告诉人们,1936年他离杭赴闽任“蛮府参军”时,他和王映霞的婚姻还堪称是美满的,也自认和娇妻是能白头偕老的;次之,诗人又明言了他“只身南下”的目的,是“意欲漫游武夷太姥,饱采南天景物,重做些记游述志的长文。”事实也的确是如此,来闽后,一连串的游闽文字相继发表在全国的报刊杂志上。再次之,诗人表白了“风雨南天”,独自“羁留闽地”时对王映霞的思念之情。从离杭那天起,他就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的映霞,又是诗又是信又是日记,仿佛初恋时。如1936年2月28日的日记云:“晚上,独坐无聊,更作霞信,对她的思慕,如在初恋时期,真也不知是什么原因。”最后,诗人点出了毁灭他们家庭的罪魁祸首——许绍棣,此人乃诗人在杭州时的良朋好友之一。许绍棣是浙江临海县人,参加国民党后走向仕途,官至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兼教育厅长。郁达夫定居杭州后与其多有来往,关系也不错。
《毁家诗纪》的第2首是:
扰攘中原苦未休,安危运系小瀛洲。
诸娘不改唐装束,父老犹思汉冕旒。
忽报秦关悬赤帜,独愁大劫到清流。
景升儿子终豚犬,帝豫当年亦姓刘。(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诗应写于1936年的岁末,地点仍是在福州。当时的政治形势是,日寇的铁蹄已践踏了东北三省,大片国土沦丧;民怨沸腾,群情激愤,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反动政府又奉行不抵抗政策,数十万大军节节败退,拱手让出了半壁大好河山。广大的爱国志士无不痛心疾首,而适逢此时又发生了西安事变,情况未明,消息不畅,更增加了诗人对祖国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忧虑情怀。该诗就是在这种情景下应运而生的。诗的“原注”是:
这一年冬天,因受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一月后,绕道至台湾,忽传西安事变起,匆匆返国,已交岁暮。到福建后,去电促映霞来闽同居。宅系光禄坊刘氏旧筑,实即黄莘田十砚斋东邻。映霞来闽后,亦别无异状,住至一九三七年五月,以不惯,仍返杭州。在这中间,亦时闻伊有行迹不检之谣,然我终不信。入秋后,因友人郭沫若君返国,我去上海相见,顺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许绍棣夫人因久病难愈,许君为爱护情深,曾乞医生为之打针,使得无疾而终,早离苦海。(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诗的原注实为诗人一年生活历程的“自述状”。
1936年冬,郁达夫名为应“日本各社团及学校之聘,去东京讲演”,而实则肩负着重要使命——即宣传鲁迅,秘密劝说郭沫若回国抗战。
郁达夫是鲁迅相濡以沫20年的老朋友,他对鲁迅的创作和人格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了解。在鲁迅逝世后的第三天,他就怀着无比哀痛和悲伤的心情写下了《怀鲁迅》,用火一样的激情和诗一般的语言,记录下了无数青年因鲁迅逝世而引起的巨大悲哀和愤怒,抒发了自己对战友绵绵无尽的哀思和沉痛的悼念之情;在文章的末尾处,他用无比愤怒的语言,猛烈地抨击了迫害鲁迅致死的黑暗社会和凶暴残忍的民族败类——国民党反动派。
秘密动员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是郁达夫东京之行的另一主要任务。郭沫若自1927年遭蒋介石军阀政府的通缉,亡命日本已达10年之久了。日寇大举入侵我东北后,国共两党及文艺界的同仁们都急切地希望郭沫若能回国领导文艺界抗敌御侮。与郭沫若既是留日同学又是“创造社”战友的郁达夫,比别人更知他在中国文艺界的地位及其对抗战的重要性,特别是鲁迅逝世后,中国文艺旗手的桂冠更是非他莫属。为此,郁达夫利用自己和福建省主席陈公侠的特殊关系,积极活动取消国民党对郭的通缉令、以政府的名义欢迎郭回国为抗战效力。在疏通国民党上层关系稍有眉目时,他便开始了东渡之行。征得郭沫若的同意,郁达夫从日本一回国便四处活动国民党政府中的高级官员,一接到国民党中央政府同意取消对郭沫若的通缉令,以中央政府的名义请他回国参与政治事务的消息,郁达夫立即向在海外的郭沫若发快信报告。
郁达夫在日期间,又是座谈,又是讲演,又是访问。在如此繁忙紧张的工作里,他仍没忘怀爱妻王映霞。忙中偷闲,撰文向她报告行程,介绍在日期间的所见所闻和感受。《从鹿囿传来的消息》就是最好的证明。郁达夫心系王映霞,时时在想念她。初来福州时,环境不熟悉,人事关系生疏,局面尚未打开,在那个时候,他是极力反对王映霞前来相聚的;而不到一年,他便感觉还是有夫人在身边好,于是就力促她速来闽团聚。
王映霞自和郁达夫结婚后就很少分离过,即使有,时间也是相当短的。郁达夫初到福州时,她还是一个心思都在郁达夫身上,相互分别刚过一个月,她便星急火燎般地要去福州相见;但一年后,郁达夫敦促她去时,情形却有了天壤之别。他们好不容易在福州相聚了,却没有了往日的热情,在生活上也处处表现出了不和谐。不足4个月,她便以不适应闽地生活、牵挂老母和幼儿为由,匆匆离别而去。细究起来,王映霞不愿在福州相聚的原因恐怕有这样两点:其一是确实过不惯福州的生活。在杭州时,无论是官场,或是社交界,王映霞都能纵横捭阖,挥洒自如,随心所欲,率意而为;而在福州,她却没有了这番风光,除作为配角偶尔随夫君赴几次宴会之外,大部分时间是蜗居斗室侍弄小儿,这一点是她离闽回杭的首要因素。其二是她在杭州已有了精神寄托。郁达夫离开杭州后,昔日的朋友们仍一如既往地和她保持着亲密的来往。个别风流倜傥的“正人君子”便渐渐地进入了她的感情世界。他们比郁达夫会伪装,甜言蜜语,且有钱有势,能满足她的各种虚荣心,于是乎,王映霞的情感天平失衡了,心灵被迷惑了。一度迷惑住王映霞的这个人就是许绍棣。不错,许绍棣曾是郁达夫的好朋友,这在郁达夫的日记里可以查得到。如1937年5月2日:他“一整天都是和许绍棣在一起。午前十一时,绍棣偕同校长至柔来,同去杏花村喝酒。因与幼甫阎氏有于午后去九溪之约,故饭后即匆匆驱车往。……车中,绍棣为讲红舌村故事,听者讲者,两都忘倦。九溪茶场,今天游客特多,程远帆氏夫妇,邵裴子先生等,都不期而遇,坐至午后四时,返城。晚上由绍棣作东,约慕尹主任夫妇在三义楼吃饭,饭后并去东南日报馆看演《狄四娘》话剧,至十时始散。”(注:《郁达夫日记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96页。)
无疑,王映霞急欲离闽回杭,与许绍棣的情感纠葛不能说没有关系。就实际而言,这时的王映霞对许绍棣还仅处于朦胧的好感阶段。是许绍棣的妻子病重期间,许的精心呵护,百般调理,又进一步将王对他的好感推向一个新的阶段。王映霞对许绍棣的推崇和好感,她本人并没掩饰,在郁达夫面前就曾多次有所流露。他在该诗的原注中的一段话就是事实。“入秋后……顺道返杭州;映霞始告以许绍棣夫人因久病难愈,许君为爱护情深,曾乞医为之打针,使得无疾而终,早离苦海。”喋喋不休地向自己的夫君夸赞别的男人,心中自然是对其人有羡慕之情存在的。
《毁家诗纪》的第3首是:
中元后夜醉江城,行过严关未解酲。
寂寞渡头人独立,满天明月看潮生。(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诗应写于1937年的仲秋之际。这一年的7月,郭沫若在国内一片抗日的浪潮声中终于秘密回到了国内。得悉郭沫若回国行程后,郁达夫特地从福州赶到上海去迎接。与郭沫若会晤后,郁达夫顺便回了杭州。在杭时,他曾为王映霞设计了逃难方案,即一旦上海沦陷、杭州危险时,让她带领全家去富阳老家隐居。富阳面水靠山,地势险要,日军是不敢轻举妄动的。再之,二哥养吾在当地很有威望,人缘极好,有困难时他会出面解决的。安抚好家中的妻儿老小,郁达夫辗转由水道改陆路返回福州,继续他的“俗吏”生涯。此诗就是回闽的途中愤时而作。诗的“原注”是:
八·一三战事,继七·七而起,我因阻于海道,便自陆路入闽,于中元后一夜到严州。一路晓风残月,行旅之苦,为从来所未历。到闽后,欲令映霞避居富阳,于富春江南岸亲戚家赁得一屋。然住不满两月,映霞即告以生活太苦,便随许君绍棣上金华丽水去同居了。其间曲折,我实不知。只时闻自浙江来人言,谓许厅长新借得一夫人,倒很快乐,我亦只以一笑付之。盖我亦深知许厅长为我的好友,又为浙省教育界领袖,料他乘人之危,占人之妻等事,决不会做。况且,日寇在各地之奸淫掳掠,日日见诸报上,断定在我们自己的抗敌阵营里,当然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人之情感,终非理智所能制服,利令智昏,欲自然亦能掩智。所以,我于接到映霞和许君同居信后,虽屡次电促伊来闽,伊终不应。(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原注所言主要是他这次离杭后家中发生的变故。“七·七”事变之后,杭州危在旦夕。按原定计划,王映霞携母带子前往富阳。应该说,有养吾照顾,王映霞在富阳期间并没有受什么委屈,大人小孩饮食起居尚属正常。但过惯了“风光”“排场”生活的王映霞,两月有余,便开始滋生厌烦情绪,急欲寻求出路摆脱此境。按常理,她就是要离开富阳,也应该先与郁达夫商量商量,一是前往福州合家团聚,一同进退;二是再寻别的更为安全的栖居地,而绝无去和省政府机关同甘共苦的道理。郁达夫没有在浙江省政府机关任过职,王映霞自然也不是机关家属,她是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享受省政府机关家属待遇的,惟一可解释的理由就是为了许绍棣。
许绍棣乃系浙江省政府要员,省政府机关迁往何处,他的家也就移至何方。省政府机关家属们迁至丽水不久,王映霞也携老带小而至,正好与许绍棣同住一个楼。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绯闻”,郁达夫在这之前已有所闻,但他并不相信。他相信妻子知书达礼,忠贞清白,绝不会做蝇蝇苟苟之事;同时他也相信许绍棣乃谦谦君子,党国要员,在国难之秋,更不会“乘人之危,占人之妻”。当友人言之凿凿向他通风报信时,他只有苦涩一笑,随风而去。到后来,他不得不相信这是铁定事实时,仍多次急电促王映霞去福州,躲开魔爪。但王映霞却我行我素,不予理睬。
《毁家诗纪》的第4首是:
寒风阵阵雨潇潇,千里行人去路遥。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这是一首签诗,郁达夫在福州天王君殿里求得的,因签诗苍凉、悲伤的意境正和诗人当时的家境和心情十分吻合,所以就拿过来借用了,借此来表达他那哀伤之中兼而有愤懑的情怀。诗的“原注”是:
这是我在福州天王君殿里求得的一张签诗。正当年终接政治部电促,将动身返浙去武汉之前夜。诗句奇突,我一路上的心境,当然可以不言而喻。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果然大雨连朝;我自福州而延平,而龙泉、丽水。到了寓居的头一夜,映霞就拒绝与我同房,因许君这几日不去办公,仍在丽水留宿的缘故。第二天,许君去金华开会,我亦去方岩,会见了许多友人。入晚回来,映霞仍拒绝和我同宿,谓月事方来,分宿为佳,我亦含糊应之。但到了第二天,许君自金华回来,将于下午六时去碧湖,映霞突附车同去,与许君在碧湖过了一晚,次日午后,始返丽水。我这才想到了人言之啧啧,想到了我自己的糊涂,于是就请她自决,或随我去武汉,或跟许君永久同居下去。在这中间,映霞亦似曾与许君交涉了很久,许君似不肯正式行结婚手续,所以过了两天,映霞终于挥泪别了许君,和我一同上了武汉。(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1937年郭沫若回国后,被任命为国民军事委员会政府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领导全国的文艺宣传工作。他就任伊始,即电邀郁达夫去武汉担任第三厅对外宣传处处长。接到郭沫若的邀请电,郁达夫即离闽去武汉就职。在这战火纷飞的年代为免得彼此相互牵挂,日夜不得安宁,他顺便接家眷一同赴任。
在福州时,听到王映霞与许绍棣相恋的传闻,郁达夫还有点不敢相信;这次到丽水搬家,耳闻目睹,他不得不相信这是铁铸的事实了。一是王映霞对他已没有往日久别胜新婚的激情,二是以“月事”来临为由拒绝和他同房,三是置他于不顾私自和许绍棣玩了两天。为此,郁达夫和王映霞曾有过激烈冲突,并给她指出两条路任其选择:一是断绝和许绍棣的关系,与他一同去武汉;二是毁了这个家,成全她和许绍棣的姻缘。经过一番痛苦的选择,王映霞最终选择了前者。
这期间,王映霞与许绍棣恋爱一事,不但外界传得沸沸扬扬,就连王映霞自己也是供认不讳的,且还有向人炫耀之意。如向孙百刚展示许绍棣给她的信件就是一例。王映霞携母带子在富阳避难期间,孙百刚因事路过这里时,特别抽暇去看望她们母子。老朋友相见,一不谈战事,二不谈远在异地的郁达夫,王映霞却拿出了许绍棣给她的信让友人看,真是匪夷所思,这令孙百刚浮想联翩,心中多有郁结。
《毁家诗纪》的第5首是:
千里劳军此一行,计程戒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
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伫看雄师复两京。(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这首诗写于1938年抗日前线。郁达夫一向以国事为重,家事为轻。王映霞与他一同到武汉后,他很快抛开家庭的恩恩怨怨,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全民的抗战事业中。他多次以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的身份,冒着枪林弹雨到前方战区视察工作,慰问伤兵,赠送纪念品,报告战斗状况。
《毁家诗纪》第6首是:
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昙。
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这首诗写于台儿庄大捷之后。1938年4月6日,中国军队在台儿庄一线阻击日寇进犯,歼敌一万多人,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信心。郁达夫奉命代表政治部及文协到前线慰问,所感所受,激动不已,即兴挥毫,多有佳作。诗人没有为第5首和第6首分别作注,而是将“注”放在了一起。第5首和第6首的“原注”是:
四月中,去徐州劳军,并视察河防,在山东、江苏、河南一带,冒烽火炮弹,巡视至一月之久。这中间,映霞日日有邮电去丽水,促许君来武汉,我亦不知其中经过。但后从一封许君来信中推测,则因许君又新恋一未婚之女士,与映霞似渐渐有了疏远之意。(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原注”中所言,王映霞日日有电去丽水,催促许绍棣来武汉相会,当属实情。一是在这之前,王映霞与许绍棣早已是鸿雁传书不断,已多达“一束”了;二是这期间,王映霞正受李家应之托,介绍许绍棣与孙多慈见面,故有诸多书信来往。但信的内容除为许介绍新夫人之外,是否还夹杂着彼此间的情感纠葛,那只有天知道了。然而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既然郁达夫已因为她和许绍棣的事大闹一场,险些劳燕分飞,那么她就该有所收敛,尽量避免与许接触,可她却不然,仍与他来往有加。可见,这时他们的感情已升温到了难以自禁的地步了。
南奔北征,为抗日的大好形势所鼓舞,郁达夫对家庭的变故已看得很淡了。再加上王映霞与许绍棣山水相隔,已不可能通款曲了,所以激愤的情感稍有平复,对过去的事情也不那么斤斤计较了。
《毁家诗纪》的第7首诗是:
清溪曾载紫云回,照影惊鸿水一隈。
州似琵琶人别抱,地犹稽郡我重来。
伤心王谢堂前燕,低首新亭泣后杯。
省识三郎肠断意,马嵬风雨葬花魁。(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这首诗,应为诗人以政治部第三厅设计委员的身份巡视浙江时所作。时值1938年的初秋之际。诗中所用词句和典故,都含有切肤之痛的悲伤之意。“惊鸿”出自魏曹植的《洛神赋》:“翩若惊鸿,宛如游龙。”后以代指美女。又如宋陆游的《沈园》:“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无论是曹植倾慕的“洛神”女,或是陆游心仪的表妹唐婉儿,最后都以无力回天的悲剧而告终。诗人面对金华的山水,想到妻子红杏出墙的羞辱,以及险些毁家的劫难,真是大有“沈园再到之感”。全诗抒发的是“家忧”、“家难”的悲情,含血带泪,无限凄凉。诗的“原注”是:
六月底边,又奉命去第三战区视察,曾宿金华双溪桥畔,旧地重来,大有沈园再到之感。许君称病未见。但与季宽主席等一谈浙东防务、碧湖军训等事。(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从河南、山东前线回来后,郁达夫又奉命到浙江等防区视察。巡视到浙江省党政机关所在地金华时,诗人禁不住心中涌起万顷波涛、千层巨浪。金华是个美丽富饶的地方,抗战前,郁达夫曾旅游到此,为它写下美文数篇,以赞其“胜”;金华是个神奇的地方,诗人对它一见如故,情深深,意长长。然而,数年后旧地重游,却恍惚有隔世之感。这里有他的夺妻之敌许绍棣。一场几乎毁家的悲剧就是在这里演绎的。
《毁家诗纪》第8首是:
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
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
碧落有星烂昴宿,残宵无梦到横塘。
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诗写于1938年的仲秋之时。郁达夫从前线慰问回来,本应得到王映霞的笑脸相迎,而不料满腔热血、浑身激情,得到的却是一张冷冰冰的脸,稍有不慎,便吵闹不已,时不时还以“出走”相威胁,最后竟真的不辞而别,置幼儿老母于不顾。一忍再忍,一让再让,这一次实在无法忍受了,他便在《大公报》登了一则寻人启事,着实地对王映霞羞辱了一番。更不幸的是,郁达夫在屋角无意中竟捡到了许绍棣寄给王映霞的3封情书。他失望了,彻夜难眠,第二天便找来郭沫若、范寿康等老朋友及第三厅的同事,来家看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而且将这3封情书照相制版广为散发。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未到伤心落泪时。郁达夫面对许绍棣寄给王映霞的情书,是再也不能自禁了,嚎啕大哭不已。他的好朋友汪静之就曾亲眼目睹了这一幕。他说:
我要到广州去了,去向达夫告别。一进去看见达夫和映霞正在争吵。达夫一见我,就指着映霞,一边哭一边向我说:“这个不要脸的女人,她居然和人家睡觉!”我一听,心里就很着急,怕达夫声张出去,杀人魔王马上会置他于死地。为了免得他闯祸,我就帮忙为映霞掩饰。我说:“不会的,你不要相信谣言。”达夫马上说:“哪里是谣言!她的姘头许绍棣的亲笔信在我手里!”我听了马上就放心了。(注:汪静之:《王映霞的一个秘密》,《郁达夫研究通讯》2001年第18期。)
汪静之所说的“杀人魔王”系指戴笠,因为他已掌握了王映霞和戴笠姘居的秘密。他原以为郁达夫和王映霞吵闹是由戴笠而引起的,一听是许绍棣,他紧张的心弦也就稍微有点松驰了。汪静之不仅见证了郁达夫为王许之恋伤心落泪的样子,而且还亲身经历了王映霞瞒着郁达夫偷偷打胎的事。郁达夫长年漂泊在外,偶尔与王映霞相会,也已失去了往日的温存。二人到武汉后,乘郁达夫到前线慰问之际,竟到私人诊所偷偷打胎,其中的奥秘也就可想而知了。汪静之对这事的回忆是:
有一天王映霞来信说:“我肚里有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某某姐,我要请某某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某某是最忠诚老实的,达夫最信任他;如果请别的男人陪我去,达夫会起疑心的。”我的妻子马上说:“没有问题,让他陪你去好了。”(注:汪静之:《王映霞的一个秘密》,《郁达夫研究通讯》2001年第18期。)
确切地说,王映霞私自打掉的这个孩子,绝对不会是郁达夫的,否则王映霞也就不会瞒着他,去找别人冒充自己的丈夫了。除堕胎的隐私之外,汪静之晚年还向世人透露了一个秘密,即王映霞不仅和许绍棣恋爱,而且还是特务头子戴笠的姘头。下面也是他耳闻目睹,亲身经历的一幕:
一天我到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我看见阳春(达夫的长子郁飞的乳名)满脸愁容,我问他:“为什么不高兴?”他说:“昨夜姆妈没有回来!”我问:“她到那里去了?”他说:“不知道。”我就问王映霞的母亲:“映霞到那里去了?”她说:“不知道。是一部小汽车来接去的。”第二天我再到达夫家去,想问问映霞头一天到那里去了。见了王映霞,她倒了茶请我坐下,我还没有开口,她就谈起戴笠家是花园洋房,家里陈设富丽堂皇,非常漂亮。谈话时露出羡慕向往的神情。(注:汪静之:《王映霞的一个秘密》,《郁达夫研究通讯》2001年第18期。)
王映霞和戴笠姘居,不但在郁达夫时代有过,就是她再次结婚后,也仍未中断。这个秘密,不但汪静之夫妇知道,王映霞的另外两个同学叶雅棣、叶雅珍也知道,而且彼此间也相互议论过,口径一致,都缄默不言。《毁家诗纪》第8首诗的“原注”是:
七月初,自东战场回武汉,映霞时时求去。至四日晨,竟席卷所有,匿居不见。我于登报找寻之后,始在屋角捡得遗落之情书(许君寄来的)三封,及洗染未干之纱衫一袭。长夜不眠,为题“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数字于纱衫,聊以泄愤而已。(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结合汪静之的回忆,重读《毁家诗纪》第8首的“原注”,应该说,诗人在这里所言并没有捏造事实,捕风捉影,而是有许、王恋爱的真凭实据在手。
《毁家诗纪》的第9首是:
敢将眷属比神仙,大难来时倍可怜。
楚泽尽多兰与芷,湖乡初度日如年。
绿章叠奏通明殿,朱字匀抄烈女篇。
亦欲赁舂资德曜,扊扅初谱上鲲弦。(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诗应写于1938年武汉疏散后郁达夫全家在湖南汉寿避难期间,诗的原题为《杭、富沦陷后,姬王氏为友人浙教厅长某乘危占去半岁,复来归,遂令避居汉寿,易君左赠诗,有:“富春江上神仙侣”句,感而有作》。当时的背景是,经过武汉那场家庭风波,郁达夫和王映霞各自都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也都有重归于好的想法,于是举家迁离伤心地武汉,到湘西小镇汉寿安居乐业。
汉寿是郁达夫留日同学,安庆同事、好朋友易君左的家乡。这里没有烽火硝烟,没有金戈铁马,再加上老朋友相伴,郁达夫全家相对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目睹郁达夫与王映霞在汉寿时的宁静生活,亲朋好友们都真诚地为他们祝福,希望他们从此以后相敬如宾,美美满满白头到老。易君左一番热情洋溢的祝福就是心声:
我们希望这一双嘉宾永远居在汉寿。希望达夫像苏东坡买田阳羡,王摩诘筑室辋川,希望达夫不要老像屈原行吟而真正卜居,希望达夫心身康健安静多想几篇东西煽动南国抗战的热情。希望映霞惩治大都市的罪恶而鼓励乡村的清气。希望这斗大的城池中永远有一个长身玉立的康健女郎提着篮儿买鱼。希望那三个小朋友永远离不了母亲替他们洗澡一直洗到生出很长的胡子。真的,人生是要放达观一点,达夫是不必悲伤了!(注:陈子善、王自立编《回忆郁达夫》,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438页。)
对朋友们的真诚祝福,郁达夫是十分感激的,《毁家诗纪》中的第9首就是在这种情景下有感而发的。诗人的原意,一方面自省缺乏对妻子的道德和情操教育,一失足而成千古恨;另一方面则期望妻子能够安贫乐道,亲操井臼像古代的孟光一样,那么,他们不但可以破镜重圆,而且还会更加恩爱。诗的“原注”是:
映霞出走后,似欲重奔浙江,然经友人劝阻,始重归武昌寓居,而当时敌机轰炸日烈,当局下令疏散人口,我就和她及小孩、伊母等同去汉寿泽国暂避。闲居无事,做了好几首诗。因易君左兄亦返汉寿,赠我一诗,中有“富春江上神仙侣”句,所以觉得惭愧之至。(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经过几多波折,诗人对红杏出墙的妻子已经原谅了。这从当时寄给刘开渠的信中也有所表示。如:
弟现已卜居于“汉寿北门外蔡天培号内”,大约战事不结束,决不离此地,以后有信,乞寄此处。内人王女士,与许绍棣恋爱,家庭几至破裂,现则仍归于好,来汉寿住,亦为伊计,欲使静养数月,将此段情事忘去也。我已辞去政治部工作,只打算多写一点文章,从前未完之稿,于此时结束一下,对世事完全绝望,唯等待老死而已。(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信写得甚是凄凉,可见王许恋爱对郁达夫的伤害有多么深。
《毁家诗纪》第10首是:
犹记当年礼聘勤,十千沽酒圣湖濆。
频烧绎蜡迟宵拆,细煮龙涎涴宿熏。
佳话颇传王逸少,豪情不减李香君。
而今劳燕临歧路,肠断江东日暮云。(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诗也是在汉寿所作。心情平淡了,所思所想也就趋于公正公平。回想往事,犹如昨日。诗的第三句叙述的是新婚之夜的情景:红烛频燃,春宵飞逝,彼此只希望迟一点听到象征天明的宵柝之声,以期美美享受一番这无与伦比的欢欣;诗的第四句叙述的是婚后情景,二人都十分珍惜呵护这来之不易的爱情之花。“细煮龙涎涴宿熏”,这情这景,是多么美好,令人神往,让人陶醉。而这大好的姻缘,如金似银的日子,却已随风飘逝,眼前留下的是痛苦是灾难,是貌合神离的悲惨结局。真是越思越想,越令人肝肠欲断,无颜回江东。诗的“原注”是:
与映霞结合事,曾记在日记中。前尘如梦,回想起来,还同昨天的事情一样。(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一部《日记九种》饱含了诗人对王映霞所有的情,全部的爱,泣天地,惊鬼神,至今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犹如昨日。然而,这毕竟是凋谢的黄花,过眼的烟云了。一切都随风而去。
《毁家诗纪》第11首是:
戎马间关为国谋,南登太姥北徐州。
荔枝初熟梅妃里,春水方生燕子楼。
绝少闲情怜姹女,满怀遗憾看吴钩。
圆中日课阴符读,要使红颜识蛰仇。(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这首诗的大意是,抗战军兴后,自己只顾国家民族的大业,而忽略了对妻子的教育和引导,以致她目光短浅,认不清形势,摆不正位置,做出了既荒唐又可悲的事情。诗的原注中说王映霞不关心时事,一味地追求生活的舒适安逸,这连她自己也是自认不讳的。“芦沟桥”事变后,王映霞误认为,这场战争也和过去经历的数次军阀混战一样,躲避一时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她既没有作好吃苦的准备,也没有长期逃难的打算,仍与平常一样,行则要汽车,住则要洋楼。不管前方将士如何流血奋战,马革裹尸,自己还是该游山时游山,该玩水时玩水。她在《自传》中的一段话就是证明:
我憧憬着的浙东的几处名胜,像永康的方岩和金华的北山,往昔只能在郁达夫写的游记里了解一些,到丽水之后,一有时间,我便约几个朋友去玩个痛快,游踪所至游兴之浓,我在家信中都告诉了郁达夫……(注:王映霞:《王映霞自传》,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06页。)
这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郁达夫为了抗战,辛劳的汗水洒遍了大江南北,而他的妻子却在后方游山玩水。诗人怎么能会“高兴”起来呢?对她“冷嘲热讽”是必然的。诗的“原注”是:
映霞平日不关心时事,此次日寇来侵,犹以为系一时内乱;行则须汽车,住则非洋楼不适意。伊言对我变心,实在为了我太不事生产之故。(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王映霞虽然是书香门第,但骨子里流淌的却是商人的血液。金家祖上是大盐商,王家祖上是经营钱庄的。所以,她虽从小耳闻目染的是书卷,长大后又嫁给了作家,但在其心灵深处却看不起“不事生产”的穷文人,尤其羡慕的是做官的,平常开玩笑时曾以“厅长夫人足矣”自我表白。她也曾向郁达夫坦言,之所以会对他变心,另寻精神寄托,就是因为他太不会挣钱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她的家传。她的母亲当初之所以反对她和郁达夫恋爱,就是认为他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将来肯定是要吃亏的。特别是举家迁杭以后,王映霞的感情生活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上海期间,来往他们家的都是和郁达夫一样的“文人”,经济状况大致都相同,显现不出富贵贫穷的差别;而定居杭州则不一样了,出出进进都是达官贵人,相比之下,她这个作家妻子就相形见绌了。于是,她开始不满了,希望郁达夫也能跻身官场,自己跟着去享受高官夫人的荣耀。
论才学,论声望,如果郁达夫愿意的话,恐怕早就是国民政府中的要员了,绝对不是一个区区厅长能比的,但他对做官却不屑一顾,一次次谢绝了蒋委员长的允诺。这一点也是王映霞所想不通的,同时也是他们夫妻最终分手的一个潜在因素。假若,郁达夫像王映霞期望的那样,步入仕途,不断升迁,她也许就不会委身于什么厅长、局长了。
《毁家诗纪》的第12首是:
贫贱原知是祸胎,苏秦初不慕颜回。
九州铸铁终成错,一饭论交竟自谋。
水覆金盆收半勺,香残心篆看全灰。
明年陌上花开日,愁听人歌缓缓来。(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诗人自比为一箪食、一瓢饮而不改其乐的颜回,将王映霞比作贪图富贵不惜人格的苏秦。王映霞之所以会失身于达官,是因她太爱慕虚荣、太贪图富贵了,什么高尚的人格,洁白的灵魂,在她眼里都抵不上金币的辉煌。俗言道,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郁达夫秉持的就是这种理念。王映霞失身了,背叛了自己的情感和良心;诗人尽管很伤感,但仍原谅她,夫妻名份不变,惟一变的是“情”。但怎样努力,无论如何是恢复不到新婚时的那种热情了。诗的“原注”是:
映霞失身之夜,事在饭后,许君来信中(即三封情书中之一),叙述当夜事很详细。当时且有港币三十七万余元之存折一具交映霞,后因换购美金取去。(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许绍棣虽系官僚,但毕竟是文化人出身,也喜欢舞文弄墨,附庸风雅。也许他和王映霞的交欢之夜太激动、太忘我了,竟不期然地诉诸文字,大概希望王与自己一同欣赏,流连回忆。对许绍棣的“情书”,王映霞可能是再三展读,一直沉浸在幸福的回忆中而忘了将其收藏,后不幸被郁达夫发现,遂导致夫妻大战。
《毁家诗纪》的第13首是:
并马汜州看木奴,粘天青草覆重湖。
向来豪气吞云梦,惜别清啼陋鹧鸪。
自愿驰驱随李广,何劳叮嘱戒罗敷。
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这首诗应是诗人再度赴闽前而作,地点仍在汉寿。武汉疏散后,诗人并没有随郭沫若等人南下,而是携妻儿老小避居汉寿。他原打算在山青水秀的小县城长居下去,只到战事结束。同年的9月,福建省陈公侠主席得知他已辞去政治部第三厅的职务,遂电召他回闽,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接到陈主席的电报,诗人顿时豪气猛生,决心抛开家庭的恩恩怨怨,重返沙场,为国效力。诗的“原注”是:
九月中,公洽主席复来电促我去闽从戎,我也决定为国家牺牲了一切,就只身就道,奔赴闽中。(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抗战爆发后,出于安全考虑,王映霞一直要求和郁达夫在一起。她担心一旦郁达夫“负气离家”出走,老母幼子将陷入无人照料的困顿境地。武汉那场夫妻大战的导火索也是这个原因。而这次郁达夫真的走了,却不知她为何没有携全家一同前往。无论从何种角度说,王映霞也应该随夫前往。其一汉寿不是她们的家乡;其二是这里不在郁达夫任职的区域,没有熟人照顾她们。孰是孰非,只有后人去猜测了。
《毁家诗纪》的第14首是:
汩罗东望路迢迢,郁怒熊熊火未消。
欲驾飞涛驰白马,潇湘浙水可通潮?(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这首诗写于赴闽途中。诗人途经汨罗,突然间风雨大作,似有为壮士远征送行而奏乐之意,禁不往意气风发,引亢高歌。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之气魄。同时,面对波涛翻滚、浪花飞涌的东逝水,诗人遥思两千年前忧愤国事,无力回天,怀石自沉于江的屈原,对祖国所遭的灾难更增加了几分忧虑和不安。他恨不能跃马挥戈,斩尽杀绝所有的侵华倭寇,还我中华大地金瓯无缺。诗人是爱国的,然而他所热爱的祖国却正在蒙受耻辱,横遭血光;诗人是爱家的,然而他所心爱的妻子却背叛他与友人私通。这一切,都令诗人的心在汩汩流血。诗的“原注”是:
风雨下沅湘,东望汩罗,颇深故国之思,真有伍子胥怒潮冲杭州的气概。(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说也很伤感,大有倾尽钱塘水也难洗尽心中羞辱之愤懑。
《毁家诗纪》的第15首是:
急管繁弦唱渭城,愁如大海酒边生。
歌翻桃叶临官渡,曲比红儿忆小名。
君去我来他日讼,天荒地老此时情。
禅心已似冬枯木,忍再拖泥带水行。(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诗为诗人返闽途中,夜宿浙江江城时有感而发。诗人暂居汉寿,经过田园风光、山野情趣的熏染陶冶,心中的愤火已渐渐平息,对不贞的妻子也有所原谅。但在江城听流娼所唱京剧《乌龙院》时,又勾起了他的伤心往事。《乌龙院》的剧情,与诗人的婚姻遭遇极其相似。此诗的原手稿是:“重入浙境,情更怯矣,酒楼听流娼卖唱,百感俱集,又恐被人传作话柄,向王姬说也。”怕入浙境,恐人耻笑,应该是诗人当时真实的心境。诗的“原注”是:
重入浙境,心火未平。晚上在江山酒楼听江西流娼高唱京曲《乌龙院》终于醉不成欢;又恐他年流为话柄,作离婚的讼词,所以更觉冷然。(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浙江是诗人的故乡,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这里留有他少年时代的梦幻,青年时代的豪情,中年时代的牧歌,而如今却因主持浙江教育厅的“禽兽”诱奸了他的妻子,羞愧难当,无颜面对这大好河山。诗人自幼喜欢听戏,而如今却怕听戏了。因为戏中所言,多是自己不幸命运的写照。
《毁家诗纪》的第16首是:
此身已分炎荒老,远道多愁驿递迟。
万死干君唯一语,为侬清白抚诸儿。(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诗乃在返闽途中,行至建阳时所作。经过一翻激烈的思想斗争,诗人已下定决心离开故国故土故人,到海外去宣传抗日,即使终老蛮荒之野,也在所不惜;同时也殷殷期望妻子,能清清白白抚育三个幼儿长大成人。诗的“原注”是:
建阳道中,写引二十八字寄映霞,实亦决心去国,上南洋去作海外宣传,若能终老炎荒,更系本愿。(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诗人也是人,儿女情长的心怀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自己将要赴南洋为抗战而奔走呼号,生死难料,何时回返更是未知。这时候他惟一牵挂的就是尚未成年的三个儿子。他是多么希望孩子的母亲能够洁身自好,含辛茹苦地将他们培养成国家的栋梁呵!
《毁家诗纪》的第17首是:
去年曾宿此江滨,旧梦依依绕富春。
今日梁空泥落尽,梦中难觅去年人。(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诗系诗人旧地重游,追思往事,念及旧人,睹物生情之作。旧人当指王映霞。由此可见,诗人对王映霞的旧情未忘,仍耿耿于心。诗的“原注”是:
宿延平馆舍,系去年旧曾宿处,时仅隔一年,而国事家事竟一变至此!(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的确,过去的一年,对祖国、对诗人的家,都是多灾多难的。对祖国,日寇的铁蹄几乎踏遍半个中国,烧杀抢掠,奸淫施暴,残不忍睹,令人发指;对家庭,先是老母亲饿死故里,继之是夫妻感情生变,险些妻离子散,家将不家。这一年,真是应了一句古语:国破家亡。
《毁家诗纪》的第18首是:
千里行程暂息机,江山依旧境全非。
身同华表归来鹤,门掩桃花谢后扉。
老病乐天腰渐减,高秋樊素貌应肥。
多情不解朱翁子,骄俗何劳五牡騑。(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此诗系诗人去国赴南洋途中所作,故有“江山依旧境全非”之感慨,同时又引发了他对朱买臣老夫子皓首穷为当官的理解,但也对朱为官后不能原谅贫贱时离他而去妻子的行为表示了不满。既然对朱老夫子复水难收表示了不满,那就说明,他对王映霞的错误也给予了宽恕。诗的“原注”是:
船到洪山桥下,系与映霞同游之地,如义心楼之贴沙,为映霞爱吃的鲜鱼,年余不到,风景依然,而身世却大变了。映霞最佩服居官的人,她的倾倒于许君,也因为他是现任浙江最高教育行政长官之故。朱翁子皓首穷经,终为会稽郡守,古人量似太窄,然亦有至理。(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郁达夫对王映霞始终是有情有义的。他不满意王映霞的虚荣,厌恶她的骄横跋扈;他也曾努力去理解,去探索她的内心世界,也想尽最大能耐原谅她的过失,希望这个千疮百孔的家能够复原。诗人的宽大宽容和良苦用心,在这里也可见一斑了。
《毁家诗纪》的第19首是:
一纸书来感不禁,扶头长夜带愁吟。
谁知元鸟分飞日,犹剩冤禽未死心。
秋意著人原瑟瑟,侯门似海故沉沉。
沈园旧恨从头数,泪透萧郎蜀锦衾。(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写作此诗时,诗人已决心断绝对妻子的所有情义,不再流连忘返。导致诗人下此决心的原因,是王映霞的浙江之行。郁达夫离开汉寿不久,王映霞不顾母老儿幼,更不顾郁达夫的情感,只身去了浙江。用诗人的话说,她这是旧情未忘。既然她已身在曹营心在汉,那么,是去是留,一切都顺其自然了。诗的“原注”是:
到闽后即接映霞来书,谓终不能忘情独处,势将于我不在中,去浙一行。我也已经决定了只身去国之计,她的一切,只能由她自决,顾不得许多了。但在临行之前,她又从浙江赶到了福州,说将痛改前非,随我南渡,我当然是不念旧恶的人,所以也只高唱一阕《贺新郎》词,投荒到这炎海中来了。(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从这首诗的“原注”中得悉,郁达夫到福州不久,接到王映霞的一封书信,大意是说要回浙江一趟,处理一些未了的琐事云云。对王映霞乘自己不在时独自回浙江一事,郁达夫甚是敏感,他以为这是王映霞仍未忘怀许绍棣,明目张胆地去苟合。他接到王映霞的信后,出于义愤,以弱者最无奈的报复手段,曾分别打电报给浙江省政府几个大的机关,寻觅王映霞的行踪。王映霞这次独自回浙,彻底断了郁达夫对她尚有的那一丝情感,完全是无所谓了:你来闽也好,不来也罢,任尔自由。幻想破灭了,终老“炎海”的信念更增加了几分坚定。王映霞与郁达夫避居汉寿时,许绍棣与孙多慈正在热恋中。王思前想后,只有随郁达夫相聚福州一途可走了。若不然,得悉郁达夫往浙江打电报寻觅她一事,她早就暴跳如雷了,但是这次她忍了,而且很屈辱地任其摆布——让去福州就去福州,让去南洋就去南洋。
《毁家诗纪》中的词一阙是《贺新郎》:
忧患余生矣!纵齐倾钱塘潮水,奇羞难洗。欲返江东无面目,曳尾涂中当死。耻说与,衡门墙茨。亲见桑中遗芍药,学青盲,假作痴聋耳。姑忍辱,毋多事。
匈奴未灭家何持?且由他,莺莺燕燕,私欢弥子。留取吴钩拚大敌,宝剑岂能轻试?歼小丑,自然容易。别有戴天仇恨在,国倘在,妻妾宁非妓?先逐寇,再驱雉。(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郁达夫是一个真正的爱国主义战士,时时处处都是以国为重家为轻。许绍棣勾引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红杏出墙,作出了越轨之举,使他蒙羞。但是现在大敌当前,他忍了,从没因“家”事而贻误投身抗战的大事。从武汉到汉寿再至福州,这期间,他除了到各大战区视察慰问之外,还奋笔疾书,撰写了大量宣传抗日救国的文章,并自觉地转换方向,减少那种闲适的游记文字的写作,而是以其匕首投枪式的战斗杂文,来为抗日战争呐喊。像《战时的文艺作家》等,就是在他“蒙羞”期间写的。国事和家事孰重孰轻,诗人是很分明的。尽管和许绍棣的仇“不共戴天”,但与抗战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先逐寇,再驱雉”就是这个意思。也正如词的“原注”所言:
许君究竟是我的朋友。她奸淫了我的妻子,自然比敌寇来奸淫要强得多。并且大难当前,这些个人小事,亦只能暂时搁起,要紧的,还是在为我们的民族复仇!(注:《郁达夫诗词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209—220页。)
《毁家诗纪》及其原注文字是血和泪的结晶,是郁达夫的一段自传式的诗史。它记录了诗人三年来间关几万里的种种遭遇和不幸,心是灰色的,苦涩的,悲凉的,但却充满了报国之士的慷慨豪侠之气,其英雄本色虽经过了六十余年的风吹雨打,至今仍熠熠生辉。这就是郁达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