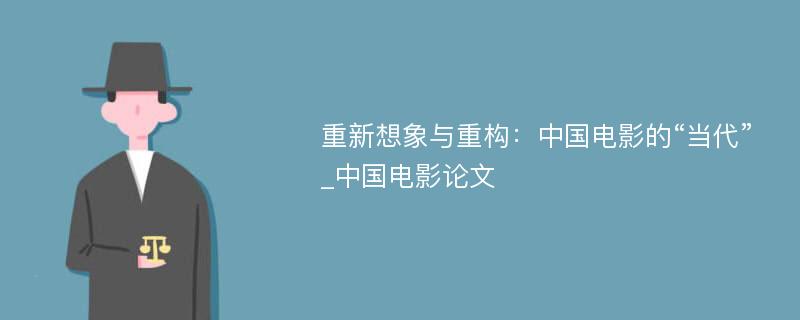
再想象和再结构:中国电影的“当代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电影论文,再想论文,当代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下中国电影的形态和路向正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其实已经完全超出了过去中国电影史的历史限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人们都已经看到中国电影的状况已变成了一个重要的具有高度意义的指标和象征,它一方面指向了一个具有丰富的形态和想象空间的电影的制作和生产机制的生成,另一方面指向了一个具有全球意义和巨大的商业与文化潜力的市场。所谓“当代性”其实正是指向一种当下的电影所呈现的形态,一种在历史和空间之中所展现的新的此时此地的电影的多重的运作和展开。其实也是我们从理解我们的当下开始,通过对于历史的“回溯”和对于空间的“展开”来观察我们自身的电影存在的方式。“当代性”其实喻示了我们切入中国电影的“现实”的必要策略。
在今天来把握中国电影的“当代性”其实就是需要我们观察中国电影的想象现在所达到的新的可能性以及中国电影在当下的全球和中国内部的新的结构中的位置。这个具体而微的“中国电影”的形象具有着某种五光十色、花样百出的特色,也有着全球华语电影越来越充分融汇的状况,同时它也在全球电影的整个结构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些都使得中国电影的形态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从2002年《英雄》开启的“大片”时代带来了中国电影新世纪的发展之后,中国电影已经走了很远很远。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正是从这已经变化了的电影的“当下”去探究历史和空间的大变局。这些变化既是电影本身的,也是中国和世界之中所发生的一切所投射于电影并通过电影所展开的。这里有两个话题应该是最为关键的:一是关于中国电影所展开的对于“中国”和“世界”的不同于既往的“再展示”;二是关于中国电影所呈现的新的“中国”与“世界”的不同于既往的“再结构”。这两者可以说一是对于电影本身的阐释,二是对于电影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的语境的理解。其实二者是如此密不可分地融为一体。
二
在探讨中国电影对于中国状况的“再想象”方面,我们需要看到最近的中国电影所呈现的新的面貌。值得探讨的是两部引起公众和社会整体高度关注的电影《唐山大地震》和《山楂树之恋》,这样的电影直接表征着电影在今天和现实之间的关系。
让我们感到惊异的是,中国电影最有影响的两位导演张艺谋和冯小刚的最新电影《山楂树之恋》和《唐山大地震》中,他们都表现了强烈的“怀旧”的倾向,试图从一个上个世纪70年代封闭状态下的中国的情境来探索中国电影想象的新的可能性。《唐山大地震》是以1976年的唐山地震为故事起点来展开故事,将故事结束在2008年的汶川地震。而《山楂树之恋》则完全是一个在70年代发生的单纯的爱情故事。两个故事都回溯到了70年代中国的日常生活之中,将其作为故事内在的动机。这一想法在十年前可能是难以接受的,7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处于“文革”之中,被认为是普遍压抑和物质极度匮乏的社会。在那一时代结束后的1978年之后的“新时期”文化中,那个时代的“伤痕”和对于那个时代的“反思”是一个时期的文化标志。当时的“伤痕文学”和“伤痕电影”都是时代的象征。正像电影中的《天云山传奇》或《青春祭》都是在对20世纪70年代社会不堪回首的压抑性的表现中凸显中国历史的变化。中国历史的命运在故事中是人的命运绝对的主宰,个人在历史中的际遇其实就是他生活的全部,生活被历史完全旋卷在其中,没有任何可能性的空间。“伤痕”是历史刻在个体生命上的不可摆脱的印记。但今天的《唐山大地震》和《山楂树之恋》则与此有巨大的区别。这里的个体超出了历史的限定而具有了不同的可能性。这两部电影具有引人瞩目的“超历史”的特征。而同时,这两部电影彻底超越了“第五代”电影深深地缀入到文化之中,将文化或民俗的力量加以强化的传统套路。“第五代”电影所常见的独特的来自中国内地的神秘民俗的表现或文化压抑性的表现都被相当程度地淡化了。这其实正是这两部电影在中国“大片”的发展已经将近十年之后所展现的新的“当代性”之所在。对于《唐山大地震》,我曾经多次进行过解读,这里不做更多的展开。①这里对《山楂树之恋》做一个简要的分析。
《山楂树之恋》显然具有一种强烈的感伤性,这感伤纯美的爱情似乎是将我们融入剧情之中的关键。这种“感伤性”是和一种相当接近于电影“默片”时代的风格相互交织的。张艺谋在这里凸显了一种对于中国电影早期传统的“回返”。作为电影风格外在的标志,电影一是通过大量字幕来推进情节,交代事件的过程,可以看出默片风格直接的表现。这种说明字幕的作用是这部电影表现的基础。这显然是今天并不常见的传统的“回返”。作为电影发展重要阶段的默片时代,字幕的作用是无与伦比的。有分析指出:“无声片时期,它是剧作构成的元素之一,是表现时代背景,刻画人物,叙述故事情节等方面不可缺少的表现手段。”②二是出现了大量的渐隐和渐显,这也是默片的典型特色,用来标识段落并显示场景和情节的转换。这显然也是对于传统默片的回返。“这种手法用以表现一个情节的终了和另一个情节的开端,使观众视觉上得到短暂的间歇,以领会进展中的剧情。”③这两种手法的作用在于显示这部电影向中国电影传统致敬的含义,也会看到一种人为的、刻意“做旧”的痕迹。通过这种“做旧”让这部电影有了回返电影青春时代的意涵。
同时,这部电影的情节并不像《唐山大地震》那样涉及到自然的巨大的不可抗的力量导致的伦理悲剧。没有像唐山地震一样笼罩整个电影的关键性的情节,而是如同淡雅的抒情散文一样具有某种纯粹的“爱情”电影的感觉。电影赖以支撑故事的情节推动力并不强烈,而是近乎于平淡无事的。虽然也有“文革”时代历史背景的显示,但相对当年的“伤痕”来说,仅仅是一个稀淡的背景,对于两人的爱情所形成的压力也不是决定性的。这部电影的爱情故事好像是重述张艺谋自己的《我的父亲母亲》(有趣的是,张艺谋最近的电影几乎都包含对于他自己的电影的重述,如《三枪拍案惊奇》是对《菊豆》的重述)。张艺谋本人关于“清纯”的言论引发的讨论在这两部电影的宣传期都出现了。张艺谋所期望的绝对的爱情其实一直是张艺谋电影所想象和追寻的东西。这种爱情疏离于利益、人际关系和历史以及文化,乃是一种绝对之物。而这种绝对性的爱情的不可实现一直是张艺谋所关注的主题。从《红高粱》开始,这种爱情的追寻始终萦绕不去。可以说,老三在这里是强烈的追求者,他有点类似《我的父亲母亲》中的母亲,而静秋相对被动,有点像《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父亲。男女的角色有所变化,但其故事情节则相当接近,其中男女之间的追求与应和等都有一种类似性。
但今天的《山楂树之恋》,历史条件的空洞化却远比《我的父亲母亲》强烈。电影一开始就有一段新来的包括静秋在内的城里高中生围在山楂树边听到关于“山楂树”历史的叙述的表现。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山楂树,李雪健扮演的本地人对它的了解,居然还不如带队的城里来的教师。教师用一种宏大的叙述讲述着这棵树的传奇历史,而本地人却在这样的宏大叙述面前唯唯诺诺地应和着。教师的语气里有一种毋庸置疑的权威性,他的叙述代表了权威性的历史叙述对于这棵树的大叙述,这种叙述对于这个电影的故事来说几乎是高度玄虚和抽象的,这里的历史含义被叙述者反复地架空了。此后,静秋在书写这种叙述的时候,被老三所打断。这其实是一个具有意义的隐喻,它其实说明了这个故事和这棵山楂树的历史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剩下的是关于其他山楂树开白花,而这一棵山楂树开红花的特异性的叙述。而这棵山楂树也变成了在老三患病后,两个人之间感情最热切时刻的见证。《我的父亲母亲》里的具有定情物意义的青花大瓷碗现在被山楂树和一个绘有山楂树形象的脸盆所替代。人们熟悉青花瓷在中国文化中所具有的象征意义,而西文的“中国”一词的来源也和瓷器有关。但现在《山楂树之恋》中青花瓷碗的历史和文化的意涵被山楂树自然的形象所替代。而且山楂树意象的来源是苏联歌曲,显然其中所引发的却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某种国际性的背景。这种背景不会引起更多历史和文化传统“积淀”的复杂内涵,而是将这个浪漫的故事刻意地国际化。招娣的红棉袄或修理青花瓷碗的工匠等等都是传统习俗的展开。而在《山楂树之恋》中,这些带有巨大文化性的表征已经淡化。
在今天的张艺谋这里,历史和文化的大背景显然已经没有纯情故事的普遍性那么重要。在《我的父亲母亲》中,爱情所受到的阻碍来自于具体文化和历史的限制,男主人公被打成右派构成了故事最关键的障碍,克服障碍的努力乃是对于历史和文化的状况的“克服”。女主人公招娣的努力就是要克服这种历史和文化的限制。这里中国的历史“特殊性”是爱情最终的障碍,而克服这一障碍的路径就是对于这些限制超越的努力。周蕾曾经对《我的父亲母亲》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解读,她点明:“张艺谋的中国性,只是附着在国家政治历史光环下的情感渣滓。不管如何讲究美学效果,类似《我的父亲母亲》这样的电影,如果少了历史感伤,以及它极力夹带的希望包袱,就没有什么意义了。”④这一说法凸显了《我的父亲母亲》中所具有的文化和历史的限定性所带来的内在要求。而在《山楂树之恋》中,这种限定虽然还有出现,但显然已经并非绝对的障碍,而关于这部电影的一些争议也在于它对于历史背景的虚化处理。虽然物质的匮乏、走资派的身份、留校的希望都对于这个爱情故事有影响,但它们都无从支配和决定这一故事的进展。这里具有悲剧性的却是自然的不可抗力,来自白血病所造成的死亡的绝对性才是故事的痛苦和悲伤的来源。这其实和《唐山大地震》有了深刻的相似性。那是自然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对于家庭和亲情的冲击。而《山楂树之恋》中出现的是白血病所造成的死亡对于个体生命绝对的伤害。这种伤害都共同带有偶然性,是人物命运中所遇到的状况,也是人类普遍可能遇到的状况。这里不再指向中国历史的特异性和中国文化的特异性,而是出现了超越历史和文化限定的新的状况。70年代的中国人所遇到的问题,其实和当年出现的轰动一时、让人震惊不已的好莱坞电影《爱情的故事》有了惊人的相似性。这当然是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淡化的结果。一种纯爱,一种超脱于具体性的人性的感动,一种完全从日常生活出发进入人类生活的普遍性的努力。这种爱不需要理由、超越了社会的限制,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歌颂纯爱,其实说明纯爱之难得,越是缺少的东西就越是被渴望的,今天在一个消费社会已经建立,物质的丰裕使得感情生活越来越被欲望所弥漫的时代,纯爱似乎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品。张艺谋在阐释这部电影的意义时所突出的正是这方面的含义。因此,这种历史和文化的淡化正好和《唐山大地震》所表现的格外相似。这说明了中国电影几乎在同一个时刻超越了过去几乎必然受到的历史和文化的限定,展现了其“超历史”和“超文化”的从来没有得到表现机会的一面。人物的命运和情感的来源都是生命本身所带来的,而不是历史和文化所带来的。文化或历史的压抑性现在被转变为一种自然力量不可抗拒带来的困扰。生命所遇到的问题,从在文化和历史的限定之中所呈现的转换到了由自然的限定所呈现的。“山楂树”是自然的符号,而白血病也是自然所造成的。这里所传达的乃是一种新的视角,爱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的选择的具体化,它所对抗和超越的首先是自然本身。爱所需要对抗的最后并不是社会、文化或政治,而是生命本身的终结。
值得注意的是,在《山楂树之恋》和《唐山大地震》两部电影之中,有一个相似的结局。作为情节支点的女主角静秋和方登在电影中都以出国作为新生活的标志。出国后的生活在电影中几乎没有什么表现,但关于出国的一笔却仍然有其意味深长之处。这里静秋和方登正是在出国之后,才更加发现了对于一种“原初”感情的珍重,更加着眼于回到生命的源头去寻找自己的回忆。《唐山大地震》中的方登重新回归了母亲的家庭,《山楂树之恋》中的静秋则不断地在山楂树下凭吊她已经无可挽回的爱情。这里都出现了空间上的出国所带来的跨文化的经验,这种经验显然是在新的空间中再度凸显了感情本身的普遍性的价值。在这里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经验的展开,而是全球性的一部分,是全球性“内部”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方登或静秋这样曾经在一个封闭环境中的个体,今天却是在一个全球的背景之下来回溯自己的历史,追索自己的记忆了。这其实就是中国和中国电影历史的一部分。
由这样的两部电影,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影对于“中国”本身其实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再想象”。这种“再想象”正构成了一种新的“当代性”本身。这里的“想象”其实具有了新的“超历史”和“超文化”的新的含义:
首先,在这里,中国不再是一个“特殊性”,深深地局限于自己的问题,对于外部世界来说是和一般的感情和心理有所不同的“特异”空间,而是一个由个体的生命直接升华为人类普遍性的新的角度所构成的人的生活空间。个人的经验和心理的感受具有了超越性的意义和价值。这些都不再是特殊历史文化所限定的集体经验的表征,而是一种个人的和生命的经验的陈述。20世纪90年代我们在讨论中国电影的时候经常引用杰姆逊关于“民族寓言”的论述。⑤杰姆逊的核心论点认为:“第三世界的文化和物质条件不具备西方文化的心理主义和主观投射。正是这点能够说明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讲述个人和个人经验的故事时最终包含着对整个集体本身经验的艰难叙述。”⑥对于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以表现个人都市际遇为中心的“第六代”电影,我曾经使用过“状态电影”的概念,来描述其超越寓言的企图。⑦但显然当时的“状态”其实也是一种集体经验直接性的表现,只是这种集体经验开始经历了一个新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转型而呈现出新的形态而已。今天看来,在《山楂树之恋》和《唐山大地震》这样的电影中,“民族寓言”才真正转化为具体的生命状态和心理反应的表现。这已经完全超越了杰姆逊对于“第三世界文化”的描述。其实这也是“新世纪”的中国在其新的发展中所达到的新历史“临界点”的征兆。正是由于今天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全球化的进程,尤其是在2008年以来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及其复苏的过程之中,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所瞩目焦点的时刻,我们对于自己的想象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张艺谋和冯小刚这两部新的电影正是这种变化的一个表现,也是对于中国的“再想象”。
其次,这种新的表达正是在回溯中国电影史的同时超越了它基本的想象方式。《唐山大地震》或《山楂树之恋》都是向中国电影史致敬的作品。它们一是回返了中国电影早期的感伤的传统,二是都强烈地调用了“情节剧”的技法,这都是早期电影常用的策略。但其实这些电影正是由于它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痛苦的经验的表述,而具有了新的全球性的空间的意义。中国的苦难不再仅仅是中国人自身的苦难,它其实也是人类的痛苦;中国人的感情也不再仅仅是中国人的感情,它也是全人类的感情。这里中国电影开始不再纠结于中国自身的命运,而是将中国的个体命运与人类的命运有了一个有机的“结合”。这些电影是在中国电影之中生长的,却是在一个全球性的华语和中国电影的新的空间里创造的。它们在回到中国电影史起点的同时其实彻底地在一个全球的语境之中超越了它。这种“再想象”的出现说明我们“走向世界”的想象史,我们自我确定的世界电影和文化的“边缘”的特异性,已经转变为世界电影和文化的一个有机的、不可或缺的“构成”。这个从“边缘”到“构成”的经验正是中国新的历史经验的一部分,也是“新新中国”新的形象的一部分。
三
我们在讨论“再想象”的同时,所看到的是“再想象”所具有的新的历史背景和条件的“再结构”。其实“再结构”是“再想象”的前提和归宿,“再想象”是“再结构”的结果和投射。它们共同构成了新的“当代性”之所在。
在当下的变化中,有两个现象值得我们深入思考:一是全球热映的好莱坞灾难片《2012》,中国作为一个积极的元素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了表现。中国不再仅仅是一个外在于世界的诡异和不可思议之地,反而成了当下世界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世界灾难的避难所。中国的形象从20世纪初叶在好莱坞电影中就难于避免其负面和压抑的状态,但这部电影和2008年的《功夫熊猫》等一样,见证了好莱坞在面对中国时的想象的深刻变化。这个想象当然是凭空而来的,但其实却并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狂想。这其实也投射了中国电影市场对于全球不可或缺的作用。我们都知道电影当然不仅仅是话语和想象的结果,而且也是市场、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多重投射,不仅仅是个体随心所欲的表现,而且是多种元素决定的结果。二是电影《建国大业》所吸引的全球华语电影的众多明星的加盟。这些明星来自全球不同的空间,却通过这部电影显示了其认同感的所在,显示了经过多年来的“大片”的努力和积累,中国电影已经具有巨大市场和资源的整合能力。它的制作精良,显示了在今天中国电影市场活跃的态势之下中国的电影制作能力和营销能力都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已经具备了国际性的竞争力。备受关注的一百七十多个全球华语电影明星的加盟,这其实是非常难以做到的电影资源的整合,像好莱坞也难以做到这样的事情,而如果没有今天中国高速发展的大平台和中国电影业大活跃的小平台,这种资源的整合是不可能实现的。如果没有中国和中国电影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让这些明星感受到这部电影具有重要的意义,就不可能实现这一举措。这其实不像有些人想象的是一个炒作的行为,而是集中显示华语电影分量的重要举措。
这样两个现象在过去当然是难以想象的。其实是中国电影在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变革之中多年积累的结果,也是当下世界全球化新的状况和格局的投射。因此,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电影在全球华语电影和世界电影格局中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历史已经把中国电影带到了一个新的现实之中,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历史的“临界点”上,这里所见证的正是中国电影、华语电影和世界电影格局的深刻变化。
中国电影和华语电影都是相当复杂和具有极为丰富内涵的概念。一般来说,从社会概念上,“中国电影”当然是包括中国大陆和香港、台湾的电影的一个总称,但在一般的习惯中人们往往用这一概念阐释中国大陆电影。香港、台湾电影无疑是中国电影整体的一个部分,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20世纪后半叶相对平行的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的传统和运作模式,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市场。我们常常将其以大陆电影、香港电影和台湾电影等加以界定或以“两岸三地”电影等称谓进行描述。而华语电影则既包括“两岸三地”电影,也包括海外华人所制作的电影,是以华语观众为目标观众的电影。海外华语电影的制作在整个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都极少出现,70年代的李小龙电影一度引发过较为广泛的关注,而其真正产生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人们往往认为王颖的《寻人》是其重要的标志性的作品。⑧王颖20世纪90年代拍摄的《喜福会》也有相当的影响。而作为海外华语电影真正地具有全球影响并进入好莱坞主流运作的乃是李安在2000年拍摄的《卧虎藏龙》。这是海外华语电影在全球的“主流化”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作品。而“世界电影”在20世纪80年代到最近的中国电影的语境中是我们要“走向”的新的空间。我们一直讨论的“走向世界”的命题就是在“新时期”电影的开端时刻,我们所焦虑的是中国电影如何“走向”“世界电影”,如何让原来封闭在内部的“中国电影”获得一个新的开放的空间。因此,中国电影、华语电影和世界电影这三个重要的关键词就是我们认知中国与世界电影最为重要的概念。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也在迅速地改变中国电影的格局。在中国大陆电影领域之中,“世界电影”和“华语电影”概念的意义的展开,对于整个中国内地的电影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世界电影”所指认的“世界”其实还是在西方“现代性”框架中的“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尤其是以好莱坞和欧洲电影节为代表的。从“第五代”电影开始的中国电影的“走向”世界,实际上显示了其时间上的滞后和空间上的特异。正是由于这种时间上的滞后,中国电影被视为通过借用时间上先进的视角观察中国的电影,也被视为用一种空间上的普遍性来透视中国的电影。因此,中国电影乃是一种“世界电影”边缘的存在,仅仅具有在中国内部的意义,而不具有世界性的意义。在中国内部,电影的功能是进行国民的“启蒙”和国家的“救亡”,因此,外部的观众对于中国电影的兴趣仅仅是由于中国电影具有社会的认知价值和意义而存在的。而在中国电影内部对于“世界电影”的兴趣也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动力。
其次,“世界电影”实际上还包括自“新时期”以来才纳入我们视野、成为一种现实存在的全球华语电影。它包括海外华语电影和港澳台地区的电影。这些电影在新中国电影的前半期几乎完全不为我们所了解,而中国大陆的电影界在1949年之后也对于全球华语电影缺少了解。这种在海外和大陆完全隔绝的条件下,“世界电影”之中的“华语电影”也处于一个分化为不同部分独立发展的电影。它们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传统的传承都有极大的差异。因此,中国电影也和海外及港澳台的华语电影之间有着断裂性。可以说,全球华语电影有“海外”和“大陆”两个独立发展的平行结构,两者之间并不相关地独立发展,在各自的语境之中延伸成为当代电影史的独特现象。因此,20世纪80年代后期张艺谋、陈凯歌的电影,《黄土地》和《红高粱》产生的广泛影响力,和几乎同时期台湾电影以侯孝贤、杨德昌等导演为中心的20世纪90年代早期在国际主流电影节上的获奖,则标志着虽然来自不同的空间,但同步展开的“中国电影”世界性格局的生成。全球华语电影的交流和沟通也由此而成为现实。这时的华语电影还存在着“海外”和“内地”两个不同的市场,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进程的进展迅速,中国电影市场的全球开放也已经完成。
进入21世纪,李安的《卧虎藏龙》以其好莱坞“大片”的全球影响力提示人们,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世界格局的转变,华语电影已经有可能进入世界电影的主要部分,它有可能在面对自己华语观众的同时,成为全球观众所喜爱的电影。同时,中国“武侠”来自传统武功神秘性渲染的飞腾的“反重力”形象也成为了一时的焦点,为未来中国大片国际市场的运作准备了类型方面的条件。而在中国内地形成的以冯小刚电影为中心的“贺岁片”市场也可以看到中国内地巨大的、尚未被开发的电影的巨大潜力。中国大陆电影的发展进入了高速成长的新的历史阶段。张艺谋的《英雄》以其新华语“大片”的形态,打通了中国电影的“海外”和“内地”两个市场,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此后中国“大片”的发展逐步形成了规模。一方面,中国内地大都市的中等收入者和青年观众的电影消费习惯随着大片的繁荣而逐步形成;另一方面,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在影响力已经逐步扩大,中国电影在全球电影格局中的作用已经越来越不可忽视。经过了这些年持续的努力,2009年中国电影的繁荣正是“大片”在全年持续形成观影热潮的结果。在华语电影中,一方面,以中国电影“两岸三地”的整合为标志,以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为中心新的广阔电影市场的形成就是一个明确的标志,全球华语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一个整体。另一方面,“两岸三地”的电影生产越来越形成了以内地为中心的人才和制作方式等方面的整合。如2009年引起轰动的内地电影《风声》的导演陈国富就是台湾著名导演,在大陆从事多年幕后工作后与高群书联合执导了这部电影。
当下中国大陆电影已经成为世界电影一个有机的部分,也开始成为全球华语电影的中心。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是对于全球电影格局重要的改变,也是全球华语电影格局重要的改变。
三十年来我们的电影所走过的道路其实是有重大的扩展和开拓的。对于中国电影而言,一个新的世界性的电影平台已经形成了。过去华语电影曾经经历过内地、香港和台湾分别发展的格局。而从今天看来,华语电影整合发展的格局已经伴随着内地市场的崛起而形成了。内地市场在整个华语电影市场中的主力位置也已经确立,这当然给了内地电影产业巨大的机会,内地电影制作在整个华语电影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也已经和内地市场的崛起一样引人瞩目。如中影集团这样具有巨大影响力的国营公司和像华谊兄弟这样的民营公司等等都有一系列成功的电影和雄厚的实力,这些企业无疑构成了华语电影运作的主力。而这其实也给了两岸三地和海外华语电影整个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过去人们一般认为只有美国“好莱坞”的全球影响和印度“宝莱坞”的本土制作能力和影响足以成为世界电影的两个中心,而如今,以中国内地巨大的电影市场为依托,创造一个新的电影中心,其前景已经清晰可见。以大陆和两岸三地的整合为标志的华语电影的新发展也足以使中国电影成为“世界电影”的一个结构性要素,而不再是一个时间滞后和空间特异的“边缘”存在。它已经不再是巨大的被忽略的电影创作,而是一个全球性电影跨语言和跨文化观看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构成”,是所谓“世界电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个重要的中国电影发展的“临界点”已经来临。
与此同时,如上所述,中国电影市场在短短几年之间出现了巨大的爆炸性的增长,中国大都市的电影观众已经从无足轻重的票房比例转向了举足轻重。中国电影市场已经不仅仅是全球华语电影市场的绝对中心,而是已经成为好莱坞电影需要高度关注的中心。从今天看,如何进一步扩大这个最有潜力的市场就成了全球电影工业最为重要的增长空间,这和中国消费者开始在最近的全球消费衰退中显示自己的消费能力一样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主题。今天中国电影市场的活跃和电影的影响力还极大地依赖于超级大都市的票房,而中国二三线城市的电影生活尚未完全形成,还有待今天的开发。三十多年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既让大都市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其中的中等收入者和青少年消费者的消费能力和趣味开始对于全球的消费市场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二三线城市中等收入者的影响力已经越来越大,他们在电影市场中的地位越来越举足轻重。如《三枪拍案惊奇》就是对于这些观众的直接作用,而《唐山大地震》和《山楂树之恋》显然也是对这些新崛起的观众的正面应和与回应。这个庞大市场的打通和开拓,必将创造出中国电影高速增长新的未来,为华语电影和世界电影提供新的可能性。这都说明,中国电影的影响力、辐射力和市场潜力都使得一个新的“再结构”的进程正在展开。
四
中国电影的“当代性”,正是中国和世界新的变化的一个新的重要表征。这其实完成了中国电影由世界电影的“边缘”向世界电影“构成”的深刻转变,也形成了中国电影在全球华语电影中的中心位置。历史将我们带到了这个新的“当代性”的临界点上。今天,在人们开始讨论“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讨论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给予世界启发的时刻,我们这里无法展开探讨,但今天所出现的现象启示我们的是,我们需要在今天的临界点上继续观察和思考,我们可能需要提出新的问题:
是否有一个已经开始出现的电影的“中国模式”?
注释:
①见:《唐山大地震》的两重含义.艺术评论,2010,(9).
②③许南明等主编.电影艺术词典.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351,425.
④周蕾.多愁善感的回归.文化的视觉系统2.台北:麦田出版城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6.69.
⑤见: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纪文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0-262.
⑥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纪文学.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51.
⑦见:全球化与中国电影的转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82-96,
⑧见:单德兴.空间族裔认同.周英雄,冯品佳主编.影像下的现代.台北:书林出版有限公司,2007.130-133.
标签:中国电影论文; 张艺谋论文; 唐山大地震论文; 华语电影论文; 山楂树之恋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故事文化论文; 爱情论文; 大导演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文艺电影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