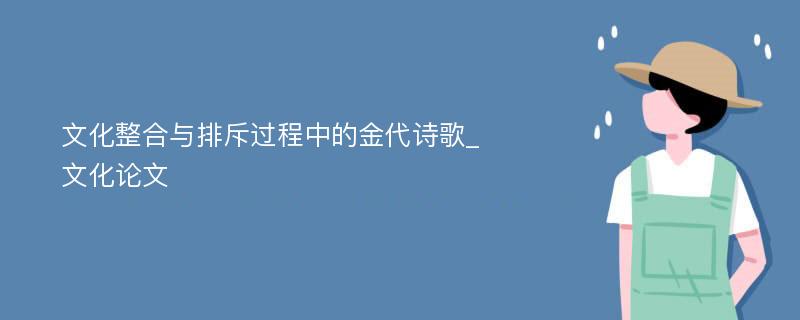
文化融合与排拒中的金代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金代论文,文化论文,排拒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238(2002)03-0059-03
民族文化之间的交融互动,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学风貌的形成,是有相当深刻的关系的。研究辽金文学,如果对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视而不见,就会失去一个很好的切入视角。以金诗为例,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的互渗及其动态发展,在金诗整体特色的形成中,是值得重视的成因。
金代的文化形态,无疑是汉文化与女真文化相互融合的产物,金代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其实也正是女真民族接受汉文化的过程。但这种接受与融合并非女真文化与汉文化关系的全部,而只是一种趋向;另外一方面,则伴随着作为民族特质的女真文化教育对汉文化的某些文化质点的排拒。这就形成了金源文化形成的复杂性与丰富内涵。不同民族的文化关系在彼此的吸收、融合的同时,还有着为人们所易于忽略的逆反趋向,就是在某些文化质点上的彼此排拒。所谓“文化质点”,也称为文化因子,指的是一种民族文化区别于他种民族文化的最小单位。它既可以是具体的,又可以是抽象的;既可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而文化的变迁,首先是个别文化质点的变异、互借与趋同。作为一个系统的特定的民族文化,有着属于此一系统的结构、功能与系统质,对于外来文化的吸收,要受到这些因素的选择。在外来文化大量涌入,以至于使原有的文化民族特征受到被覆盖、被吞噬的威胁时,它必然会在某些排拒外来文化的大量渗透,以维护该文化的基本物质特质,使之不至于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
女真人原有的文化,是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的,未建国之前,女真人君臣之间、君民之间,没有明确的尊卑观念,也没有森严的等级秩序,宋人洪皓记载了当时女真人那种朴野的君民关系:“胡俗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而食,灸股烹脯,以余肉和綦菜,捣臼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吴乞买(金太宗)称帝,亦循故态,今主(指熙宗)方革之。”(《松漠纪闻》)这里描述了女真人在未进行封建化的改革时的古朴风俗,同时,也指出了从金熙宗起在文化上所起的更张,其实也就是对汉文化的吸收融合。“靖康之难”随着北宋王朝的倾覆,大量的中原文物流向北方,而汉文化因子也随之进入女真人的社会生活。战争成为最为快捷的文化传播方式,女真贵族非但没有把中原文明付之一炬,反而主动地接受汉文化的渗透。
大量吸收汉文化因子的工作,在金太宗那里尚未来得及全面展开,“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金史》卷二十八《礼志》)而到熙宗则开始全面接受中原文化。他对儒家学说深所服膺,倾心于中原王朝那种“君君臣臣”、尊卑分明的封建纲常秩序。对于女真文化的原始状态,他是十分蔑视的。尤其是太宗以前那种亲切随易、尊卑不分的君臣关系,更为他所不满。熙宗即位后,以韩昉为翰林学士,制订典章礼仪,严明君臣之间的尊卑关系,一改女真旧俗。因而导致君臣关系相当紧张,女真旧贵族对熙宗强烈不满。接下来的世宗也对中原的文化十分推崇,但主要是撷取儒家的“仁义道德”的观念体系,力图使之成为女真民族的思想基础;而章宗则是在文学上更为嗜爱中华文学的审美传统,侧重于“文”。这些文化层面又是互相补充、逐渐深化的。
女真文化之于汉文化,吸收、融合是一种主导倾向,没有对大量文化元素的吸收、融合,女真的迅速封建化是不可设想的。但女真人的的汉化带来了一个不可忽视的后果,就是使那些勇武强悍的“猛安谋克”,逐渐变得文弱儒雅起来。女真人赖以起家的“法宝”——勇武骠悍的民族精神,正在逐步沦丧。女真统治者愈来愈看到,汉文化的大量涌入、渗透,在使女真民族文明起来的同时,给女真民族精神带来的威胁。因此,在吸收一些根本性的汉文化因子如政治制度、伦理思想、经史坟典等的同时,对一些他们认为会侵蚀女真人纯朴风俗的文化因子不断地进行排拒。
女真统治者十分珍视那种淳朴刚健的民族精神,唯恐失去这些女真人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于是,一方面吸收汉文化的深层元素,一方面又力求保持女真淳朴刚健的旧俗。意在得二者之长而兼之,使女真民族既如以往的孔武骠悍,又得汉人之高度文明,尤其是仁义道德的伦理观念、君君臣臣的封建秩序、繁文缛节的宫廷排场,这些又是他们深所向往的。
在对某些汉文化因子的排拒方面,要数世宗最力。他对汉文化的吸收是有甄别,有选择的。对于儒家政治思想、伦理观念等,他不遗余力地加以提倡,并力图使之成为女真民族的精神支柱。然而,他又一贯提倡保存和弘扬一些女真旧俗,视如家珍,而对与之对应的汉文化因子进行排拒。他认为:“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如书,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金史》卷七《世宗纪》)在世宗看来,女真民族淳朴自然的“旧风”,不但不与儒家的伦理观念相背谬,反而十分契合,因此要加以弘扬,以这种“女真旧风”,来实践儒家伦理思想,世宗还希望通过艺术途径,给女真旧风打强心剂。大定二十五年(1185)四月,在一次宗室宴会上,世宗感慨于多时未闻有人唱本曲(本朝乐曲,指与外来乐曲相区别的女真乐曲)亲自歌之。上曰:吾来数月,未有一人歌本曲者,吾为汝等歌之。命宗室弟子叙坐殿下者皆坐殿上,听上自歌。其词道王业之艰难,及继述之不易。至慨想祖宗,宛然如睹,慷慨悲激,不能成声,歌毕泣下。世宗亲歌本曲,自然不是什么酒后豪情,而有着政治意图,其目的主要在于通过这种民族之音,唤回被渐趋汉化的女真民族意识。大定十二年(1173)四月,世宗在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真词,并对太子说:“朕思前朝怕行之事,未尝暂忘,故时听此词,亦欲令汝辈知女真醇直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同上)这就尤为明确地道出了世宗通过本朝乐曲来维护女真旧俗的政治意图。在吸收汉文化过程中,很多女真人将姓氏译为汉姓,改穿汉装,还有不少女真人只会汉语而忘了女真语,世宗认为这些汉化倾向会直接危及女真民族精神的存在。他屡次诏令女真人“毋得译为汉姓”,强调“大抵习本朝语(女真语)为善,不习则淳风将弃”。(同上)“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同上)以法律的形式来排拒某些汉文化因子的侵蚀,说明了当时女真人汉化倾向的严重性。同时也表明,世宗在需要对某些汉文化因子进行排拒时,同样是不遗余力的。大定十三年世宗的一次谈话全面地反映出他对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态度。他说:“会宁乃国家兴王之地,自海陵迁都永安,女真人寝忘旧风,朕时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饮音乐,皆习汉风,盖以备礼也,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真风俗,第以朕故,庶几习效之。”(同上)世宗对汉文化的吸收、融合,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对于女真旧俗的大力提倡,对某些汉文化因子的排拒,也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他既希望女真社会有完善的封建文化,又唯恐女真民族在汉文化的氛围中迷失了自我。到了章宗时代,女真人的汉化倾向更为严重,章宗自然也是心存忧虑,屡次训戒“女真人不得改为汉姓及学汉人装束。”(《金史》卷第十二《章宗纪》四)“制诸女真人不得以姓氏译为汉字。”(《金史》卷九《章宗纪》一)同样表现出排拒倾向。
金源社会文化,就是处于女真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与排拒的动态关系之中,这对于金代诗歌的风貌形成是有着很深的联系的。金源诗歌创作,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就是产生于上述的文化土壤里。金诗的文字、形式,都是汉诗的传统。女真文字的创造,是很晚的事情。在灭辽战争期间,尚无女真文字。金诗的起点,被称为“借才异代”,这时期的诗人们,几乎都是由宋入金,此前金源并无文人之诗。他们把宋诗的体貌风神带到了金源,如宇文虚中、高士谈、吴激、蔡松年、张斛等。他们把中原诗歌传统与诗艺移植于金源土壤之中,使之成为金诗发展的重要基础。而由于自然环境和诗人心境的变化,大漠霜寻的清刚寒劲之气,成为金初诗人作品的底蕴。
到大定、明昌年间,金源诗歌逐步成熟,一方面在诗的技巧与艺术形式上进一步发挥了汉诗的文体特征和审美旨趣,而同时又使属于金人自己的诗歌有了自己的特色,这被称为“国朝文派”。金代大诗人、诗论家元好问提出“国朝文派”的概念:“国初文士如宇文大学士(虚中)、蔡丞相(松年)、吴深州(激)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蔡珪)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怀英)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无异议云。”(《中州集·中州鼓吹翰苑英华序》)从这段论述的意思中可以明确看出,“国朝文派”是以之区别金初“借才异代”的诗歌创作而作为金源诗歌的成熟标志的。“国朝文派”不是指金诗中的某一流派,也不是指某一时期的创作,而是指金源诗歌区别于宋诗的整体特色。它在这个层面上的内涵又是十分丰富而广泛的,同时又是动态发展变化的。金诗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妨可视为“国朝文派”的流变史。这种区别,不意味着诗的文字与形式与汉诗有什么不同,而主要是一种底蕴的、风格的乃至于气象的差异。“国朝文派”,就其突出的特征乃那种清刚朴野之气。“国朝文派”的开创,首推蔡松年之子蔡珪,蔡珪的诗作确实是体现了北方文化的朴野雄悍之气的。如《野鹰来》蔡珪一诗:“南山有奇鹰,置穴千仞山。网罗虽欲施,藤石不可攀。鹰朝飞,耸肩下视平芜低。健狐跃兔藏何迟;鹰暮来,腹肉一饱精神开,招呼不上刘表台。锦衣少年莫留意,饥饱不能随尔辈。”野鹰非凡鸟可比,它勇猛矫厉,凌然超越。在野鹰的意象中,有一股扑面而来的雄悍朴野之气。显示着与宋诗不同的风貌。诗的句式参差变化,适宜于表现诗人那种慷慨豪宕的气质。蔡珪诗中这类作品是最有代表性的。雄奇矫厉,带着北方大地所赋予的朴野之气。
再以金代最有成就的文学家元好问为例,尤可说明金诗的文化特色所系。元好问是鲜卑后裔,生长于金源的北方土壤之中。但他的诗词创作,不仅继承了中华诗词的优秀传统,而且在一些诗歌样式上和词的艺术造诣上升华到一个更新更高的境界,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如他的七律,气魄宏大、境界雄浑而在艺术上又无粗糙鄙陋之弊,音律、造语都非常精工。在七律发展史上,遗山是继杜甫、李商隐后的又一高峰。清人赵翼论及遗山七律成就时说:“七言律则更沉挚悲凉,自成声调。唐以来律诗之可歌可泣者,少陵十数联外,约无嗣响;遗山则往往有之。如:《车驾遁入归德》之‘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原有地行仙。’‘蛟龙岂是池中物,虮虱空悲地上臣。’《出京》之‘只知灞上真儿戏,谁识神州竟陆沉。’《送徐威卿》之‘荡荡青天非向日,萧萧春色是他乡’;《镇州》之‘只知终老归唐土,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尽随天北转,古今谁见海西流。’《还冠氏》之‘千里关河高骨马,四更风雪短灯檠。’《座主闲闲公讳日》之‘赠官不暇如平日,草诏空传似奉天’,此等感时触事,声泪俱下,千载后犹使读者低徊不能置。盖事关家国,尤易感人。惜此等杰作,集中亦不多耳。”(《瓯北诗话》卷八)这里的推崇,侧重于遗山七律的沉挚悲凉,气魄雄浑,而其诗之意象新奇,声律精美,使七律诗的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以词而论,遗山词是对北宋以来词坛上的婉约与豪放两大艺术流派的融合与超越。他以其天赋的气质更多地汲纳了苏、辛一派的豪放气度,而又有着雄浑苍莽的气象,这一点是苏辛也未尝有过的;但遗山词又并非仅以雄浑苍莽、悲慨激壮见长,而且还能以深婉绵密的手法与雄浑沉郁的风格糅而为一。宋末著名词人和词论家张炎这样评价遗山词:“辛稼轩、刘改之作豪气词,非雅词也。于文章之暇,戏弄笔墨,为长短句之诗耳。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及观稼轩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词源·杂论》)可见,遗山词是将豪放与婉约冶为一炉的,从而达到了词的新的高度。
遗山对于中华文化传统尤其是诗词文的传承,非常熟悉,十分精诣,而于其中又有着浓厚的北方文化意识。在《题中州集后》五首中,遗山以金源文学为自豪。他这样吟道:“邺下曹刘气尽豪,江东诸谢韵尤高。若从华实评诗品,未便吴侬得锦袍。”“陶谢风流到百家,半山老眼净无花。北人不拾江西唾,未要曾郎借齿牙。”“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诗学亦有长沙帖,莫作宣和阁本看。”这是明显地从北方民族的文化心态所产生的自豪感。他认为与江南诗歌相比,如果从“华实”的角度来看,北人完全可以不让“吴侬”而夺得“锦袍”。遗山还以“乾坤清气”来作为北方诗风的文化气质的概括,很能道出其神韵所在。
在其诗论名作《论诗三十首》中,遗山也对北方民族的那种豪犷雄奇的诗风深为推崇,如第七首诗云:“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这是赞扬北朝民歌《敕勒歌》,最为欣赏其慷慨豪放,出于天然,勃发着一种英雄气。清人宗廷辅评之曰:“北齐斛律金《敕勒歌》,极豪莽,且本是北音,故先生深取之。”(《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说得极是。
金代的文化形态是女真民族吸收、融合汉文化的产物,从原来的原始文化跃迁到封建文化,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主要是在于对汉文化的接受汲纳。而金源诗歌的起步,也是直接从汉民族的诗歌中借用过来的,但在其发展流变过程中,北方民族的文化心理成了它的底蕴,造就了金诗的独特品格。不从民族文化关系的角度来透视,很难说清其间的一些原因所在。
[收稿日期]2002-0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