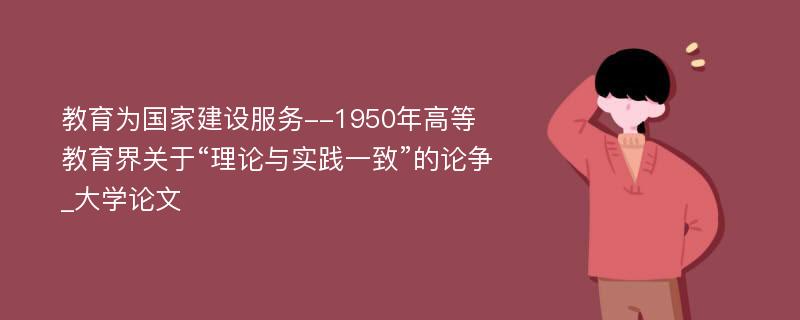
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1950年高教界关于“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争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14)02-0076-07 1949年9月,担负开国重任的新政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份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文件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教育方法为理论与实际一致。”①围绕此项方针的具体落实,以北大、清华、燕京三校为主的大学教授,在次年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召开的前后,展开了一次热烈的争论。 一、改进工程教育的大讨论 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恢复和重建工作的启动。各业务部门对专门人才的需求陡增,大专院校的毕业生供不应求,尤其是工农医等实科,人才供需的缺口最大,产销脱节的矛盾最深。从数量上看,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必然需要大量的科技工作者,但过去的工业院校却因战乱频仍等原因而规模有限,发展缓慢,完全跟不上客观形势的骤变。从质量上看,当时的经济建设迫切需要为数甚多的专业人才,但原有的理工学院大都取法英美,课程庞杂,用之训练专才则专门的程度不足,产生理论与实际不能结合的弊病。显然,如何使工程教育基本满足工业扩张的需求,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际,便成为摆在眼前的燃眉之急。 面对业务部门提出的“专、快、多”(学习的技术要专,学习的期间要快,培养的人员要多)的规格标准,教育部不得不极力应对,而知识界人士也开始研究讨论,各抒己见。针对工程教育改进的热门话题,不少专业人士以《光明日报》为主要媒介,展开了一场大讨论。综合归纳之后,主要有以下几种主张: 茅以升“习而学”的工程教育:茅先生认为过去的工程教育,理论与实际脱节、通才与专才脱节、科学与生产脱节。对此,他提议先习后学,将现行程序完全倒置,即把全部课程按难易深浅分成若干阶段,每阶段内都是先实习后上课,同时实践与理论彼此呼应,实习要先简单后复杂,修课则要先读业务课,再读基础课。②他坚信先习后学的方法,符合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认识规律,并真正把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为国家在短期内培养大量的专才。但平心而论,茅先生的大胆主张不仅“非立时即可实行”③,而且在理论上也值得商榷。马大猷就质疑“先学专业课程,以后再学基本工程课,最后学基本科学”的做法。④而钱伟长更是毫不客气地暗示:“假如有人主张以经验累积的学习来总结出科学理论,那么我们人人将重复我们祖先的努力,浪费青年精神,莫此为甚。”⑤ 其实,茅以升早在1926年就已构思出这套“大破大立”的方案,而1950年“崭新的革命形势,又重新唤起了”他的“憧憬与期望”。⑥因此,茅先生只想借助时势来实现自己多年未遂的理想,并非追赶时髦,宣传造势。他虽与政府在教改的基本精神上若合一契,但他却认为“仿效苏联”“似乎也不太理想”。这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培养专才,而是“中国工业落后的情形”,实在无法做到苏联的“分系之专”。⑦不过,透过茅以升激进的意见,我们仍可窥见:即便是在文教界,当时倾心于专才教育者恐怕也不在少数。 大学内添设专修科:1949年解放之初,中央各产业部门就与清华、交大、农大等校商议,开办各类专修科,以期在短时期内培养大批急需的专业技术人才。与另起炉灶办独立的专科学校相比,这种方案可以利用大学原有的师资和设备,省时省事省钱,因而被广泛视为高等教育满足当时生产建设需要的切实可行的最佳模式。然而,大学内的专修科教育也遭遇到不小的挑战。首先是招生困难,高中毕业生对专修科感觉陌生,只愿升入大学本科念书。其次是学生的思想问题。专修科的学生入学后易产生自卑感,羡慕正规的本科学生。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课程内容的问题。专修科的课程本应以实际为主,配以必要的理论,但大学办专修科,却很难摆脱系统理论教育的影响,加上时间的限制,又不得不借用本科的师资和教材,结果课程完全是大学的简化和缩编,达不到专精一科的目的。⑧ 一言以蔽之,大学加设专修科,虽然可能产生以实用验证理论,以理论提高实用的相得益彰的效果,但也容易制造相互争抢资源的紧张关系。有鉴于此,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高名凯提出“专门学校只能够在无损于大学的原则之下利用他,政府另外还得特为专门学校而给予一笔经费。”⑨但教育部却另持一套评价标准,他们认为大学附设的专修科普遍地办成了大学的预科或速成班,不仅难以达到专门化的要求,招生数量也受到限制。因此,大学兼办专修科的设计只能是临时性的救急措施,想要真正持久地获得大量合格的专业人才,必须依据苏联的经验,新建众多高等专门学校(学院),这正是后来全国大规模院系调整的理据所在。 费孝通的“寓专业科于大学”:费先生的拟议看似与上述大学内添设专修科的主张大同小异,但两者在组织和课程的设置上则有根本的区别。费先生认为“专业科的设立并不需要把院系体制取消”,而是“以现有行政基础为出发点,各系开课”,“各专业科依其需要在各系中挑选它所要的课程,由组织该科的主任会同各课程的教师成立一委员会,推进关于该专业科本身的行政事宜。”这两个系统“可以并行,甚至相辅”,但“原则上必须确立专业科不得附设于学系的办法”。⑩简言之,寓于大学之中的专业科实际上只是根据业务需要,综合各系原有的课程,组织起一个个大拼盘,把各门学科最基础的知识挑拣出来传授给学生。除了增加几个管理专业科的委员会,大学先前的体制和课程一律照旧。 由此可见,费孝通的专业科与教育部的专修科虽然都附设于大学,但却名似实异。政府希望学校培养掌握一门技术,一出校门就能在岗位上承担工作任务的人才,因此学校应多多联系实际,并尽可能向专门化发展。但费孝通以为要达到学以致用,就应让学生多学点知识,替学生多搭些桥,凭借样样皆通来增加就业机会。这种摆杂货摊的想法清楚地表明费先生是在用民国通才教育的理念办理专业科,而寓专业科于大学的拟议本质上是在维持现存大学制度不变的框架下嵌入为国家培养专业干部的临时设施。费先生深知“培养大量中等技术干部并不是高等教育的任务。买货色走错了铺子。”但当经济建设因人才匮乏而受限时,他又不忍心袖手旁观,只好让大学出来越俎代庖,即“大学是老母鸡,带出一批小母鸡,小母鸡生出大量的鸡蛋来,在过渡时期不妨由老母鸡直接生蛋,虽则不太经济,但是可以应急。”(11)他乐观地相信大学和专科并不冲突,不过,在寓专业科于大学的方案中,他竭力维护大学性质的举措必然严重瓦解他为国分忧的良好初衷。因为专修科的任务与大学并不相同,课程和教法都必须量身定做,如果完全照搬本科的教学模式,甚至还在民国通识教育的基础上更加宽泛化,训练出来的只能是统统不通的毕业生,对于纾解干部供求的紧张,终归于事无补。 另设中等技术学校:钱伟长并不直接谈工程教育改进的对策,而是长篇论述现代工业生产运转的内在规律。他先把技术人员大致分为四级:技工、技术员、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由于四类人员的分工不同,职能各异,所以培养他们的机构和方式也就各不相同。“普通技工的训练在生产机关里做”,“技术员的训练,应该通过中等技术学校来做,这种训练要专,可以快,也可以大量的训练。工程师的训练应该通过高等教育机关来做,要全面,要在全面的科学基础上专门化,不宜操之过急。”技术专家则要通过长期的研究和专业工作养成。(12)至此,钱先生全盘道出了他的结论:目前全国严重吃紧的是中级技术员,教育部如欲根本解决问题,就必须“大量和全力开设艺徒学校及中等工业专门学校”。(13)换言之,大学并非一定要去帮助产业部门解决干部荒的难题,它仍应依循自己的轨道发展,追求更长远的目标。 从学理的层次来看,钱伟长的条分缕析自然无懈可击,但从现实出发,坐而论道的述理却总难解决当下的燃眉之急。首先,在专门学校奇缺而国家又无力兴办的困境下,大学如不暂时承担部分培养中等技术人才的责任,实在是不近情理。其次,技工和技术员的缺口不及时填补,工业建设必然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大学所培养的高级人才自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但钱先生的致命伤还在于他所阐述的道理都是欧美发达国家正常情况下的一般规律,未必完全适合于家底薄、刚起步且久梦复兴的新中国。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长远需要与现实需要很难兼顾,而政府为了实现赶超战略,不会亦步亦趋地重蹈西方均衡发展的覆辙,必然会在一段时期内集中力量优先推进某些事业。钱伟长的本意是希望工业教育逐步接入正轨,循序渐进地提高,但由于历史背景的错置,他的意见虽极具思想价值,却总因太过理想而难于施行。 二、民盟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 就高等学校的类型而言,新政权提出“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方针,明显指向的是“约占全国高等学校总数85%的新解放区原有的高等学校”。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毫不讳言地指出:这些学校的“教学内容基本上还不能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它们的教学方法一般地还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点”。(14)政府希望全面借鉴苏联经验,对从民国遗留下来的正规大学进行彻底改造,以实行专门的科学技术的教育:第一,课程内容力求适合国家建设的需要,融合理论学习与业务实习;第二,削减综合性大学的数量,兴办高等专门学院,同时追求院校分布在地理上的相对平衡;第三,加强与业务部门的联系,单科学院应直接由相关的行政部门负责领导。面对如此宏伟的改革计划,多数具有留洋资历且常年执教于国统区的文教界民主人士不能不议论纷纷。在这种背景下,民盟文教委员会和光明日报社于1950年5月27日联合举办了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20余名与会者围绕当时高教改革中的重大议题广泛发表了意见。 关于理论与实际一致的问题,与会者均认为大学应以提高理论水平、鼓励发明创造为己任,即便要联系实际,也是在较高层次上的联系,应严格区分实际与实用,避免走入狭隘经验主义的歧途。汤用彤说:“大学是一种高级的全面的教育”,如果我们“只要求学生向一条很狭路上走,结果恐怕这样的教育对我们的建设不会有很大益处。”曾昭抡也说:“大学的任务是造就有广泛理论基础,有高度适应性,有创造能力的人材”,而那种“百分之百合用的人才,不是在大学中就一下子可以培养出来的。”“大学一部分责任,在于解决技术问题,但是要在基本的研究上解决技术问题。”雷洁琼同样指出:大学的“训练应着重于培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考虑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应只着重于某一种职业或某一种职位的训练。”金岳霖也同意大家的说法:“大学不是专门训练狭隘实用人材的,它是在广泛的科学的基础上教育学生掌握理论,使能灵活运用,并从事专门研究工作的。”(15) “就一个大学的本质来说:学术的研究成分应当重于实用的技术成分”。但有人会问:大学是不是不结合实际?是不是没有用?张奚若解释道:大学的有用“应该是广义的,长期的和全面的。如果我们只顾到目前的,狭义的,局部的‘有用’,而完全忽视了长期的,广义的,全面的‘有用’,那是不对的,那就要造成‘狭隘的实用主义’的偏差。”费孝通则强调应准确理解理论与实际一致的内涵:“一切从实际里得到的理论必然是会‘实用’的,但是在短期看来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可能不很显著的。我们反对的是和实际不合的空谈,科学是唯物的,唯物就是反映物质,反映实在。从实际里获得的理论,必然能回到实际里去,那就是‘实用’。”钱伟长对此深表赞同:“凡不是空洞的理论,就能和现实连系。譬如说大学讲的微积分,本身不一定有直接的实用,但微积分仍然是与现实连系的。因为许多实在的东西,要用微积分来讲才讲得通。”(16) 关于通才与专才的问题,与会者均指出大学与专科的性质不同,大学以培养通才为主,专门学校以培养专才为主。钱端升说:“大学与专科学校的性质不同,任务也不同,不应该将它们混淆在一起来看。”“专科学校培养的学生,学什么,出来就要做什么。”“大学培养出来的,却不是这么样专门的人材。大学的教育在使学生能在较广的专门范围内,较高的理论基础上,去掌握一部分的知识。”目前大学可以“替政府负担一部分专门教育的工作”,“但不能因此而使大学变质。假使单是为眼前的需要,而不为将来打算。我认为将酿成极大的损失。”钱伟长主张大学训练“在通才基本上的专才”,“大学的‘专’,不是像螺丝钉那样‘专’,还是相当广泛的‘专’”,是在“经过全面的、科学的训练之后贯穿了技术的‘专’”。费孝通则比较悲观:“我们现在并不是在争‘通才’与‘专才’那一种才重要,而是在要不要打好基础的问题。”在目前的基础上,“立刻要在大学里搞专门,像是要在沙土上造高塔。”而奢谈培养通才,也名不符实,“通才是不必反对的,只能说通才不会太多,不能太快,不能希望大学去培养罢了,大学只能为通才打基础。”(17) 关于院系调整的问题,与会者均提出应稳步、慎重地推进,并反对文理不通、理工分家和均衡布点等做法。金岳霖主张“大学中的理、工、文、法、医、农学院不要分开。这正是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学问一方面要专,一方面要互相交流,互相联系。学问是不可孤立和分割的。”潘光旦“和金先生的意思一样,认为综合大学不但要包括文、法、理三字所代表的种种学科,更要包括工农医各路的学科。这样才可以加强学术的交流合作,才可以促进理论与实际的真正配合。”“总之,要真得到综合与融会贯通的好处,大学的院系不厌其多。”张维则从理科与工科的鱼水关系来细陈工学院不能独立的缘由,“发展工学院是应当使他能得到适当的,以及必须的在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上的滋养,而不应当使工学院孤立起来。”会上,陈岱孙批评高等学校均衡分布是一种不顾实况的平均主义,“如果人口高度集中区是在沿海各省市,高教机构的分布似乎应该照应这情形和需要,人口集中区是应该有较多较大的高教机构。”曾昭抡建议院系调整宜“采取稳步前进的办法”,“暂时将原来大学少动一些,另外办一些学院试验一下”。“不要弄成要淘汰坏的,反淘汰了好的,要更合理,反而搞成更不合理。”(18) 三、高等教育会议上的博弈 1950年6月1日,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正式开幕。在听取多个主题报告之后,六大行政区的代表开始就理论与实际一致等原则性方针展开热烈讨论。从华北区小组的发言情况来看,专家学者与教育部的分歧依旧存在。李继之说:“目前的紧急需要,将来长远的高级的需要,我们都要兼顾,不可偏废。因为国家建设是长期的工作,现在是在开始。我们为国家建设培养人才,眼光要顾到全面,不可短视。”周培源则透出些许抱屈的意思:“高等学校里面训练出来的人才,只能达到某一种程度,是有限度的。培养专门人才,工厂要与学校合作。”把“这一任务完全交给高等学校来负责,是有困难的。”钱端升也持同样的观点:“如希望在大学中造就非常专门的人才是不妥当的,也是极不经济的,不如让他们打好基础,到实际工作中以最短时间求专。”费孝通再次谈到自己对理论联系实际的认识:“如果理论是科学的,理论与实际一致,是不成问题的。”“一种科学的理论,在学校里教学的时候,并没有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拿到社会上“尚无用到的地方”,是“因社会发展的限制”,不是理论本身的毛病。“我们要从发展的观点来看问题,社会向前发展,它的用处也就自然的显示出来。”钱伟长也反复强调:“所谓联系实际,不只是指的要联系目前的紧急需要,而且是要联系国家建设长期的需要。”“大学要准备后备军,决不能为目前紧急的需要而乱了步伐。”(19) 面对如此之多的质疑,中央政府不能不发扬民主,加强沟通,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来逐渐拉近思想上的距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在会上一语中的地全盘道出高教改革的基本思路:“‘尺蠖之曲以求伸也’。一时性的假象的降低,实际上是永久性的真实的提高。这种假象的降低我们是用不着担心的。如医药教育,我们受过正规医药教育的医生还不到2万,我们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照苏联的比例,一千人中有一个医生,我们要47.5万名医生,还差45万5千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照旧办法,要费很长的年限训练出有数的高级医生,这固然好,但只能是杯水车薪,不能解决问题。因此,要采取新式的教育方式,短期地训练大批医生,这样的专才虽然没有通才那样高的水平,但不仅可解决当前的问题,而且会普遍提高人民的医药知识,从而提高整个的医疗水平,即使是短期训练出来的专才,也随时可以向提高的方向迈步,继续深造为通才。”(20) 这番略带交底意味的说理陈情确实值得仔细体味。首先,郭沫若指明今后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应该是以质换量,即先把人才培养的数量搞上去,以敷急用,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之后,慢慢就会发生质变。其次,郭沫若暗示高等教育向苏联模式的转轨是大势所趋。当时国家各部委(如卫生部)都已开始参考苏联的指标计算未来人才的需要量。教育部门只有与之配合,全面采用苏联的体制才可能按质按量地完成部委交来的订单。这表明高教模式的转换并不全是出于教育事业本身的需要,而是不得不与国家制度的顶层设计相一致。最后,郭沫若传递出政府加快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坚定意志,这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集体心理的自然流露,无疑会触动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为旧教育改造的顺利推行减小阻力。另一方面,民国精英教育的曲高和寡及其改造社会的无力,都与即将到来的建设高潮格格不入,这也使得一部分知识分子无法坚持自己原有的理想。郭老的发言不仅暗合知识分子的情感,而且击中他们的隐痛,自然颇具感染力。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既然以苏联为样板,那么苏联专家以介绍情况的形式来现身说法就必不可少。在6月8日的全体会议上,阿尔辛杰夫到会发言。他首先简述了十月革命后苏联高等教育的飞速跃进,然后以阶段论的逻辑毋庸置疑地断言:“现在中国高等学校所遇到的任务,也和苏联的高等学校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后所遇到的任务是原则上相同的。”肯定了这个大方向,教育改革的具体政策就不难制订。首先,中国的“大学要从抽象的教育转变到具体的教育”,应培养“具体的专才”,而“不是大而无当的博学通才”。其次,“中国的大学不应该包罗万象地大而无当,不应照这种只求其大的方针来扩充,而应该照专门化的方针发展”,应该切实加强高等技术学院。再次,“中国的高等学校必须转变到与实践发生联系,转变到专门化,并因此转变到切合于工厂的、农业的、医院的、学校的等等实践。”(21)苏联专家的建议几乎可以视为一份中国高等教育转型的行动纲领,因此,官方在将之公开发表时,特加按语:“这篇讲话,非常重要,希望全国各高等学校以及研究高等教育的同志们注意。”(22)不过,对比民盟座谈会的发言纪录,苏联专家所言差不多完全与之针锋相对。由此可知,教育部负责人希望利用这次会议彻底解决思想问题、全面推动教育转轨的想法恐怕的确有些不切实际。 会场上激烈的争论也惊动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在得知情况后迅速指示:“旧的高等教育是要改的,但力量既然有限,就必须慢慢改,不能性急,不能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譬如关于大学院系调整归并问题,我们说是‘易地为良’(指调整有好处),人家都说‘勿动为大’(不愿调整)。所以在一定时期内,还以少动为妙。在这次会议上,不要要求过高,能改进一点就是好的。”(23)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亲莅会场,接见了与会代表。周恩来还从团结的角度作了讲话。针对会上议论的焦点,他展开论述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基本是不偏不倚的中庸态度:“在大学里反对理论与实际联系,或者主张少联系,都是不对的。另一方面,不适当地强调实践,忽视理论,把大学降低到专科学校的水平,也是不对的。”(24) 至此,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只能在未完成预定任务的情况下闭幕。实际主持工作的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洋洋洒洒的总结报告中再次阐述了中共的教育理念,并极力廓清高教界的思想混乱。钱俊瑞直言:“在这次会议上,讨论最久,争论最多,对今后高等教育的实际工作影响最大的问题,也就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贯穿着我们教育的方针、任务、制度、内容和方法的一条红线,是今天高等教育中最基本的问题。”他借用毛泽东“有的放矢”的经典语录,把理论联系实际定义为“努力用科学理论之箭来射中国革命与中国建设之的,来解决革命与建设的各项实际问题。”但他认为现在的大学却很难做到这一点,主要是存在两大障碍:第一,学校中所授的一部分理论还“是陈腐的,甚至是反动的”,即手中拿的不是好箭,而仅是一根“软软的芦苇”。第二,一部分大学教授不愿意联系实际,不愿搞革命的功利主义,即有箭不放。钱俊瑞明确指出:理论必须应用于实际,否则就只是僵死的教条。“我们学习理论,并不是因为理论好看、神圣、玄妙或神秘,或者把理论当作高尚于实践的东西,也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为了运用它来解决实际问题。”(25) 总而言之,“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必须为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国防的建设服务,必须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首先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包括长远的与目前的、直接的和间接的需要),必须为此而实行具体的适当的专门化的教育,培养上述的高级建设人才;而决不可采取‘为教育而教育’,‘为学术而学术’,‘孤芳自赏’,与国家建设的需要脱节的方针。”“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贯彻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正确学风,”“一面克服‘为学术而学术’的空洞的教条主义的偏向,力求与国家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这是我们现有高等学校主要的努力方向;另一方面要防止忽视理论学习的狭隘实用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偏向。”(26) 全国高教会议期间的这场争论起因于民国大学无法适应新中国工业化战略的事实,而这种矛盾又突出地集中表现在工农医等实科上。因此,1950年的大讨论首先始于改进工程教育的献言献策,渐次扩展到大学的性质任务(大学与专科的异同)、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通才与专才)及院系调整等多个方面,其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主题是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原则。 “大学究竟是为社会服务还是批评社会?是依附于社会还是独立于社会?是一面镜子还是一座灯塔?是迎合眼前的实际需要还是传播及光大高深文化?”(27)这个称之为“赫钦斯之问”的无解谜题实际上也深深困扰着新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这场围绕“理论与实际一致”的争论本质上是高等教育适应论与高等教育引领说的争论,是一场深陷于价值悖论(value paradox)的泥潭而难分伯仲的争论。在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府以推动工业化的崇高目标来征用学术资源是无可置疑的,甚至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为了实现赶超战略,过度但非无限度地管控高等教育也可视为特殊情境下的无奈之策。因此,教育部的主张自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片面强调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压抑高等教育追求高深知识的本质属性,必然会阻碍高等教育自身的正常发展,反过来又会使生产事业的发展后继乏力。知识分子正是于此立论,他们认为大学只应进行知识生产的活动,如果屈从于外在目标,就无异于让高等教育背负了不能承受之重。而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教事业的实践也恰恰证实了他们的预言,现实中确实存在大学过分依赖政府,办学自主权匮乏,学术自治无法得到尊重,认知理性无法充分彰显的弊病。然而,人类有史以来的学校教育无处不在枷锁之中,一穷二白、积贫积弱的新中国显然远不能为教育的自由发展提供前提条件。因此,对于一个工业化刚刚起步的国家,知识分子的进言未免太过超前,染上了陈义甚高而阳春白雪,一叶遮目而不见泰山的毛病。总之,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高等教育理应为国家建设服务,但也不能以牺牲大学的学术性为代价。中共党人为国为民的筚路蓝缕,历史无法抹去,而知识分子所留下的空谷足音,也时时令后来人警醒。 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A].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1. ②茅以升.习而学的工程教育[N].光明日报,1950-04-29(1). ③茅以升.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N].光明日报,1950-06-04(1). ④马大猷.工程教育的习与学[N].光明日报,1950-05-20(1). ⑤钱伟长.目前工程教学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1950-05-27(1). ⑥茅以升.征程六十年[A].茅以升选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530-531. ⑦茅以升.工程教育的方针与方法[N].光明日报,1950-06-04(1). ⑧史家宜.一年来我们办专修科的几点经验教训[N].光明日报,1950-06-08(2). ⑨高名凯.谈高等教育的改革问题[N].光明日报,1950-06-06(1). ⑩费孝通.在大学内设立专业科计划拟议[A].费孝通文集(第6卷)[C].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62-64. (11)费孝通.教育者本身的教育——记首届全国高等教育会议[J].新观察,1950,(1):33-35. (12)钱伟长.目前工程教学的几个问题[N].光明日报,1950-05-27(1). (13)钱伟长.大学工学院的课程改革[J].新建设,1950,(9):35-36. (14)马叙伦.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开幕词[J].人民教育,1950,(3):11-14. (15)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记录[N].光明日报,1950-06-01(2-3). (16)同上. (17)同上. (18)高等教育问题座谈会记录[N].光明日报,1950-06-01(2-3). (19)理论与实际一致的问题[N].光明日报,1950-06-05(2). (20)毛礼锐,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59. (21)А·П·阿尔辛节夫.从苏联高等教育的经验略谈几个问题[J].李敬永译.人民教育,1950,(3):25-27. (22)编后[J].人民教育,1950,(3):14. (23)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312. (24)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的讲话[A].周恩来选集(下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 (25)钱俊瑞.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而奋斗[J].人民教育,1950,(2):8-14. (26)钱俊瑞.团结一致,为贯彻新高等教育的方针,培养国家高级建设人才而奋斗[J].人民教育,1950,(2):8-14. (27)方展画.赫钦斯[A].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3卷)[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94-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