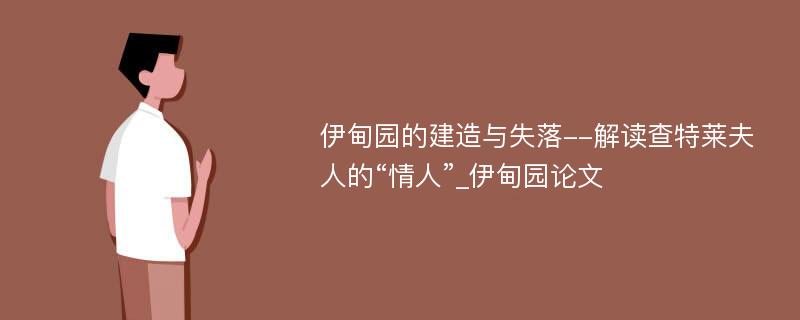
伊甸园的营造与失落——《查特莱夫人的情人》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甸园论文,夫人论文,情人论文,查特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劳伦斯的文学“遗嘱”:两大主题之总结
英国二十世纪初的伟大作家D·H·劳伦斯毕生致力于两大主题的探索:一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如何摧残人性,造成人性的异化;一是如何“建立男女之间的新关系,或者调整旧关系,”〔1〕以一种“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来弘扬生命的力量,以克服工业文明的弊病。
工业文明摧残人性,造成人性的异化,对此,劳伦斯在其作品中作了不遗余力的揭露,喊出了发聩振聋的呼声。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新房子、新家俱、新马路、新衣裳、新床单,/新的、 机器制的一切把我们的生命吸干,/把我们冻得冰冷,活力全无。/东西愈多,愈重这包袱。”〔2〕他还这样批判英国的工业化:“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兴盛时期,有钱阶级和推动工业发展的人所犯下的严重罪行是:他们将工人投入丑恶、丑恶、丑恶、丑恶;投入卑贱和丑恶凌乱的环境,投入丑恶的理想、丑恶的宗教、丑恶的希望、丑恶的爱情、丑恶的衣服、丑恶的家俱、丑恶的房屋、丑恶的劳资关系。”〔3〕他是矿工的儿子, 对于工业文明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有着痛苦的切身体会。在他的传世之作《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妇女》里,他通过描绘矿区这个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代表和象征,淋漓尽致地暴露了它对矿工们心灵的残酷压榨和剥夺,以至于践踏、破坏他们家庭的严重恶果。
至于如何调整男女之间的关系,劳伦斯从他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1911)开始,经过《逾矩的罪人》(1912)、 《儿子与情人》(1913)、《虹》(1915)、《恋爱中的妇女》(1920)、 《迷途的姑娘》(1920)、《亚伦的杖杆》(1922)、《羽蛇》(1926)及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始终予以深切的关注。他宣称,“我认为,艺术的唯一源泉,使艺术复活的唯一途径,是使艺术进一步成为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连接杠杆。”〔4〕
劳伦斯于1928年发表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以下简称《查特莱》),正是对他一生中坚持的这两大主题的总结。由于这也是他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他在此书发表两年以后,即1930年,便因病去世——因此我们不妨把这部作品看成是他的文学“遗嘱”。
看看劳伦斯在这份“遗嘱”中对于他一生坚持不懈孜孜探索的两大主题,尤其是男女关系这一主题有什么新的发现,对于我们应该是不无兴味、不无启迪的。
二、寓言神话:伊甸园的营造
自远古起,人们便一直怀着对象征着幸福美满生活的乐园的憧憬和信念。《圣经》对伊甸园里的亚当、夏娃的描述,就折射出远古人类的这种心态:
“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生物。”
“上帝在伊甸的东方设了一个园子,把他造就的人安置在那里。”
“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
“上帝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让他修整、看管这园子。”
“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用肉补合起来。”
“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两人成为一体。”
“当时他们夫妻俩都赤身裸体,而且并不感到害羞。”〔5〕
《圣经》中传达的人们对乐园的这种憧憬,其余音袅袅不绝,在以后各个时代都能听到回响,我们在劳伦斯的《查特莱》里也听见了他的应和之声。
如果说《儿子与情人》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那么《查特莱》则洋溢着浓郁的寓言气氛。其中的“人物有时候与其说是活人,不如说是象征,宣传目的也时有流露。”〔6〕劳伦斯也许急于在这份“遗嘱”中表达他的思想,用他笔下的人物来充当他思想的传声筒(尤其是书中的梅勒斯),这未免使他在人物塑造上有所欠缺。尽管他几经修改,使此书的第三稿终于成为一本既有充实的社会背景、又有流畅的情节、人物形象也尚属生动的小说,但比起《虹》和《恋爱中的妇女》来,毕竟在艺术上略逊一筹。小说的情节在劳伦斯作品中也属于最简单的,这也非常适合寓言的结构。
在这部寓言中,劳伦斯继续关注着工业化对环境的破坏:“到处是污黑的砖房,屋顶的边缘乌黑发亮,路上的烂泥由于混着煤灰而一团漆黑,连街沿也是湿淋淋、黑溜溜的,好象阴暗和忧郁渗透进了每一样东西。自然的美遭到彻底的否定,生活的快乐遭到彻底的否定,那种连鸟兽生来也有的追求形体美的天性,已经荡然无存,人类的直觉与本能已经完全死寂。”〔7〕
他更为关切的是工业化对人的摧残:“人啊,人!天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顺从、善良的人;从别的意义上说,他们是不复存在的人。人应该具有的那种东西,在他们身上稍一萌发便横遭扼杀。 ”〔8〕
激于义愤,他借梅勒斯之口对工业文明提出强烈的抗议:“汽车、电影院和飞机吸干了他们最后一点勇气。我对你说,每一代都养出更加懦弱的一代,有着印度橡皮管做的肚肠,锡制的脚,锡制的面孔。一批锡人!”〔9〕
对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成的罪恶,劳伦斯深恶痛绝,他大声疾呼,他极力抨击。可是,怎样治疗现代工业文明的弊病呢?他开出了典型的劳伦斯的处方。“他认为,只有使人的全部自然本性特别是性的欲望充分发挥,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罪恶;只有使人的原始本能充分复活,才能使机械统治下暗淡无光、郁郁寡欢的人类生活发出照人的光彩,才能从事使人与宇宙之间和人与人之间恢复和谐的关系。”〔10〕有位评论家这样分析劳伦斯:“现代文明对他的精神横加摧残,而他又不象威尔斯所做的那样,在为一个新世界制作蓝图中找到任何慰藉。这个病症不能接纳任何理智的医治,因为在劳伦斯看来,现代世界已经腐蚀了人的情感生活。甚至情欲已经变成了理智的某种微不足道的副产品。重新发现情欲生活的一种自由的流露,对于他几乎是一种神秘的理想,因为其中存在着满足,也存在着力量。”〔11〕劳伦斯的目光并不是向着未来,“为一个新世界制作蓝图,”而是转向过去,企图寻找那已经消逝的“黄金时代”。他从年轻时就有一种信念:“回归到古老的日子。回到《圣经》之前的日子,在那里为当代人重新找到那时候人们的感觉和赖以生存的手段。”〔12〕这一信念,在《查特莱》中得到了寓言式的抑或神话式的表达。对于代表工业化社会的太弗歇尔工人区和莱格比庄园充满了厌恶之心,劳伦斯掉转了头,到别处去为他的主人公寻觅乐园。他终于在庄园的树林里找到了一方远离尘嚣的净土:“树林在傍晚蒙蒙的细雨里显得安谧、寂静而神秘,林间到处是使人迷惑的虫卵、吐绿的新芽和待放的花苞。在朦胧的暮色里,树木象是卸了妆,闪耀着它们裸露黝黑的身躯。地上一片幽绿似乎在浅声低吟一片盈盈绿意。 ”〔13〕正是在林间小屋里, 康妮和猎场看守人梅勒斯度过了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看完这部作品,读者脑海中都会留下这样一幅图画:“在这幅画的后景,黑魆魆的机器无情地映衬在愈益黑暗的天空;在前景,孤立而又隔绝地耸立着一片葱绿的树林;在林中,两个一丝不挂的人在翩翩起舞。”〔14〕
面对这幅画面,读者自然而然地会联想起前面所引的《圣经》中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的情景。这正是劳伦斯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为了和工业文明相对抗,他在书中那工业社会的一角,精心营造了一座伊甸园,供他的夏娃和亚当栖身、休憩、相亲相爱。
三、夏娃的追求:灵与肉的完美结合
劳伦斯曾说过:“总有一天,我要写‘爱的胜利’这样一部小说。我将为女人而创作,这要比投票赞成妇女参政更好。”〔15〕他在一生的创作中都信守着后一半诺言,其明显标志便是,他的许多小说都采用女主人公的视角,并深入到她们的心灵深处,披露她们的心路历程,展现她们的内心追求。
劳伦斯的笔下涌现出许多充满追求的女性形象。《白孔雀》里的莱蒂就一心追求“真正的爱情”,却由于它在乔治和莱斯利身上都显得不完备而心猿意马,进退维谷,最终作出了错误的抉择。《儿子与情人》中的葛楚德·莫瑞尔有着高尚的精神追求,可是由于年轻时作出错误选择而饮恨终生,只得把爱寄托在儿子身上,结果把她畸形的爱变成了儿子精神上的重负;米丽安也由于对精神上的结合过于执着、鄙视肉体生活而导致她与保罗的恋情终归失败。《虹》里的安娜从少女时代便耽于梦想,婚后过了段甜蜜生活,但是她还想了解人生的意义、宇宙的奥秘,却由于和丈夫信仰的分歧、性格的冲突而使他们的生活充满了斗争和痛苦,结果她放弃了对人生的探索,任凭她追求理想的努力半途而废;她的女儿厄秀拉是位富于独立精神的叛逆精神的现代女性,她蔑视宗教,蔑视“民主制度”,厌恶狭隘闭塞的家庭小圈子,敢于走向社会,要求男女享有平等权利,寻求男女之间在平等基础上的完美结合。尽管如在探索路上屡遭挫折,却毕竟看到了“彩虹拱架在大地上。……她在这道彩虹中看到了大地上的新建筑,看到腐朽不堪的旧房子和旧工厂被一扫而光,看见世界将建筑在生气勃勃的真理结构之上,与笼罩大地的苍穹正好协调。”〔16〕在《恋爱中的妇女》里,厄秀拉与茹伯特·伯金经过一番爱情的试探、碰撞和搏斗,终于形成了一种比较融洽的关系。不过,“茹伯特和厄秀拉的关系虽然比起杰拉尔德与古特伦来取得了比较圆满的结局,但是他们并未找到建立人与人之间完美关系的真正途径,他们还得在探索的道路上边走边看,所不同的是原来两人各奔东西的寻找,现在变成了携手并进的探求。”〔17〕《迷途的姑娘》中的爱尔维娜不满文明社会的压抑和传统家庭教育的约束,不愿被困在资产阶级文明的樊笼里,却在一个巡回剧团的意大利演员西西欧身上找到她所渴求的“男性”,终于弃家出走,委身于他,到意大利一个偏僻荒凉的乡间定居。在《羽蛇》里,凯特出于对现代文明的厌倦,来到墨西哥寻求她的理想,逐渐被那里的土著宗教所吸引,终于嫁给了土著人西波里亚诺。这些女性(以及劳伦斯中、短篇小说中的许多女性)和《查特莱》中的康妮一起,组成了劳伦斯笔下的“夏娃”群像。尽管这些“夏娃”性格不同,禀赋迥异,追求的侧重点也各呈异趣,有的倾向于与男子精神上的结合,有的较耽溺于肉体的和谐关系,但她们无疑都体现出同一个追求目标:男女之间的完美结合。通过这些女性形象,劳伦斯阐述了他的性爱观、婚姻观,而康妮和梅勒斯的结合,则是劳伦斯对他的性爱观、婚姻观的最终探索和总结。
劳伦斯的婚姻观、性爱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他强调男女之间的完美结合,认为“那是圣灵的法则,是完美无缺的婚姻的法则……每个男人都从自己最深切的愿望出发,希望在他自己和另一位女人之间建立完美的婚姻关系,希望达到一种将使他获得充分满足和表达的存在的完整性。”〔18〕因为“男女正是在相互关系中——在接触中,而不是不接触——才获得真正的个性和独特的存在价值。”〔19〕他认为完美的婚姻必须保持男女两极的平衡。起初他认为夫妇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一定的隔阂,保持各自的特异性,才能达到平衡,如《虹》里的汤姆和莉迪亚,他们结婚后仍然彼此感到陌生,经过多年的冲突和疏远,终于在性爱中得到满足。但是这种通过肉体满足来维持的两极平衡关系只是初级的。在《恋爱中的妇女》里,他认为,男女双方必须保持独立自由的人格,在这基础上建立起一种超越肉体和物质的精神关系,才能保持两极平衡。伯金和厄秀拉最后似乎达到了这种平衡。但是通过超越肉体的精神关系来维持平衡也并非理想境界,因此在《恋爱中的妇女》及《阿伦的杖杆》里,他又提议以男人之间的友谊来加以补充。在《迷途的姑娘》里,他又转而提倡建立男女之间的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宣扬男性对女性的统治,女性对男性的服从,近乎否定他先前的婚姻理想。经过一番曲折,劳伦斯才达到了否定之否定,提出,“我认为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令人讨厌的关系,而男人和男人、男人和女人之间新型的关系应是温柔、敏感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在上、另一个在下的关系。”〔20〕正是在《查特莱》中,他终于找到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之间充实、自然、和睦的关系。”〔21〕如果说康妮以前的“夏娃”们的追求对男女关系的肉体和精神层面各有侧重,从而或多或少有些偏颇的话,那么康妮才算达到了劳伦斯的理想境界,她通过和梅勒斯的恋情,包括他们之间的性接触,终于做到了男女之间灵与肉的完美结合,她也因此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一个原型意义上的“夏娃”。对此作者有着明确的表述:“突然地,在一种温柔的、颤战的痉挛中,她的整个生命的最美妙处被触着了……一切都完成了,她已经没有了。她已经不存在了,她出世了:一个女人。”〔22〕
在叙述康妮通过性爱走向新生的过程时,劳伦斯大胆描写了康妮和梅勒斯的性爱场景。他解释说,“我始终苦心孤诣地在做同一件事情,就是使人们在提到性关系时,应感到是正当和珍贵的,而不羞愧。”〔23〕在他看来,“性和美是一回事,就像火焰和火是一回事一样。如果你憎恨性,你就是憎恨美。如果你爱上了有生命的美,你就是在敬重性。”〔24〕他还说,“整个色情的问题都是个隐秘的问题。一旦秘密被捅穿,也就没有什么色情可言。”因此“唯有以自然、清新的坦率对待性才是上上策。”〔25〕他在书中的性描写就表现出他“自然、清新的坦率。”
通过康、梅的性爱经历,劳伦斯向我们展示了人类性爱的三种境界。由于丈夫克利福德下身瘫痪。丧失性功能,康妮在身心上与他日益疏远,处于一种抑郁、消蚀状态。这时她和孤身独居的梅勒斯相识,逐渐熟稔、了解,互相的欲求使他们彼此接近,发生了性关系。这是男女间自然的相互投合,是性爱的第一种境界,即“性互投境界。”但在这第一境界中,康妮还未曾真正投入,她显得被动和隔膜,她感到,“如果你是个女人,并且置身于这整椿事之外,那么……男人的这种姿势和动作无疑显得可笑之至!”〔26〕
随着两人亲密关系的深化,他们逐渐进入性爱的第二境界,即“性和谐境界。”他们在雨中林间小径的欢情便是这一境界的绝妙写照。她奔窜着,他只看见她那圆圆的湿漉漉的脑袋,湿漉漉的脊背在逃遁中前倾着,圆满的臀部闪着光:一个惊遁的妇人美妙的裸体。……他疯狂地把它紧搂着,这柔软而寒冷的女性肉体在接触中很快变得火一般地暖热。大雨淋在他们身上,直至他们冒出蒸汽。他两手捏着她可爱的、沉甸甸的双臀,在雨中狂乱地、战粟地、一动不动地把它们紧按在自己身上。接着他突然抱起她,和她一起倒在小径上,在大雨呼啸的寂静中,短促而迅猛地占有了她,短促、迅猛、一蹴而就,犹如动物一般。”〔27〕就这样,他们在大自然的怀抱中,体验了一次人生的极乐。
在康妮去威尼斯旅行的前夜,他们终于达到了性爱最完美的阶段:“性超越境界。”“那是个情欲之夜……那是火一般尖锐灼人的肉感。”“在那最秘密的地方,把最深刻、最古老的羞耻心焚毁了。……当肉感之火通过她的脏腑和胸脯时,她觉得自己直欲死去:但那是种痛快的、奇妙的死亡。”“这时她觉得自己到她天性的真正根底,并且毫无羞耻。她的肉感的自我,赤裸裸的,并不感到害羞。她有一种凯旋感,几乎是一种自负感……这是人生!这就是人的本来面目!没有什么可伪装或害臊的。她同一个男子,同另一个人分享着她最终的赤裸。”〔28〕这是劳伦斯理想中的最高性爱境界:一种灵与肉的完全的、完整的、亲密无间的融合与升华,一种向原始的返朴归真,一种神圣的、不无宗教色彩的自我超越。〔29〕这似乎便是劳伦斯梦寐以求的“爱的胜利”!至此,劳伦斯终于兑现了本节开头引语的前一半诺言:他写成了“‘爱的胜利’这样一部小说”。
平心而论,他在本书中提倡的不计门第、财产,只求男女之间真心相爱、灵与肉完美结合的性爱观与婚姻观,在当时无疑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即使从性科学的角度看,他的观点也应该说是合理的。
自然,我们更不应忘记,书中描绘的康梅这一对现代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旖旎场景,其实体现了作者的哲学观点。书中叙述的康妮通过性爱走向新生的经历,集中反映了作者“对血性和肉体的信仰”和对文明再生的信念。劳伦斯坚信,“我们的头脑可能搞错。但是,我们的血性所感到、所相信、所表达的事情总是真的。”〔30〕他对资本主义文明早已感到绝望,“英国民族濒临死亡,这一点他在战争年代就已经预言了,正是古老意识最终消亡的一个方面。”〔31〕而康妮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英格兰的代表,如同一个睡美人,只有当阳物王子‘猛烈的撞击’到来时才会再生。劳伦斯只要谈到再生这个问题总不免变得启示性很足,他的这部预言性小说又吸收了不少他的启示理论的最后形式。”〔32〕
四、骑士爱模式:对神话的修正
如前所述,劳伦斯在书中精心构筑了一座伊甸园,编造了一个现代亚当、夏娃的神话。他在书中进行的探索与他以前许多作品似乎是一致的。可是,仔细观察一下,我们却会发现书中的亚当、夏娃模式偏离了神话原型,发现他在书中的探索与他先前作品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神话原型的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第一对夫妻,而本书中的现代亚当、夏娃——梅勒斯与康妮——却并非夫妻,而是情人。难怪有人说康妮的故事和安娜·卡列尼娜、包法利夫人一样,是又一个“通奸妇的故事”。
在以前的小说中,劳伦斯一直在探讨男女之间的婚姻关系,而本书却一反常态,描写的是婚外恋。为什么会发生这种变化呢?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劳伦斯先前在婚姻关系中寻求理想的男女之间的平衡,基本上可说是归于失败。莱蒂和莱斯利,葛楚德和瓦特、安娜和威尔,古特伦和杰拉尔德都是失败的例子,汤姆和莉迪亚也不算成功,厄秀拉和伯金的探索则还未结束,尚难盖棺定论。也许正是对婚姻内关系探索的失败使劳伦斯把目光转到了婚姻外。他这么做其实无意中恰恰触及了阶级社会中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常态。正如恩格斯所说,“随着专一婚制出现了两种经常的、为以前所不知道的特殊的社会人物:妻子的经常的情人和带绿帽子的丈夫。……跟专一婚制和淫婚一并成了不可救药的社会现象的是通奸行为,这种行为是虽被禁止、严罚,但终究不能铲除的。”〔33〕
有的评论家注意到,劳伦斯经常涉足这一题材:一个地位较高的妇女受到一个地位较低的男子的吸引,结果或是抵御、或是屈从了这一冲动。他的短篇《一块彩色玻璃》、《牧师的女儿》、《春天的色调》、《母女》、《另来那一套》,中篇《狐狸》、《小甲虫》、《烈马圣莫尔》、《公主》、《少女和吉卜赛人》,长篇《白孔雀》、《儿子与情人》、《迷途的姑娘》、《羽蛇》,都是表现这一题材的,而在《查特莱》中,康妮也屈身俯就了梅勒斯。
也有人评说,劳伦斯喜欢描写与现代文明抗争、决裂的“自然人”,《白孔雀》里的安那贝尔,《迷途的姑娘》里的西西欧便是很好的例子,本书的梅勒斯无疑又是一例。这些说法当然都有一定道理。
但是,倘若换一个角度看问题,我们对本书男女主人公的关系便会有一种全新的眼光。劳伦斯在他精心营构的伊甸园里上演的,实质上是一出中世纪的“骑士爱”。
梅勒斯这个现代“亚当”,其实不妨说是个现代“骑士”。他虽然是矿工的儿子,但受过教育,在军队里当过军官,与普通劳工截然不同。在康妮看来,“他简直就是个绅士”。实际上他是劳伦斯心目中“天生的贵族。”〔34〕在劳伦斯看来,“有些人永远是贵族”〔35〕。但这不是从血统继承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梅勒斯与康妮就谈不上地位高低悬殊了。
究其浪漫情调,康、梅恋情确实大有“骑士爱”之风。“构成普罗温斯情诗精华的就是《albas》,用德语表示便是Tageliedet (破晓歌)。它用鲜艳的色彩描绘骑士如何卧在情妇——他人之妻——床上,而侍者守在门外,一见晨曦(alba)初上便通知骑士,使他能悄悄地溜走,不致被人发觉;叙述离别的情景,便是歌中最动人的地方。”〔36〕只不过在本书中,悄悄地溜来溜去的不是“骑士”,而是他的情妇。
从本质上看,康、梅恋情更应归于“骑士爱”。恩格斯指出:“当作一种情欲,当作肉欲的最高形式(这也就是它的特性)而头一个出现于历史上的性爱形式,即中世纪的骑士爱,决不是夫妇爱。恰恰相反!古典式的骑士爱,在普罗温斯人中间常见的骑士爱,正是极力破坏夫妇贞操的,而诗人们且对之加以歌颂。”〔37〕劳伦斯(他本人正是一位诗人!)在书中尽情“加以歌颂的,不正是这样一种“极力破坏夫妇贞操的”“性爱形式”吗?他以“骑士爱”模式对神话原型的亚当夏娃模式作了变形处理,对他的伊甸园神话作了修正,也许事出无心,但却流露出他对以往的婚姻关系探索的失望和迷惘心情,同时也反映出他在缔造他的伊甸园神话、他的性宗教、他的性爱乌托邦时,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现实感占了上风。他书中的描写恰好反映了阶级社会的婚姻现实。“当私有财产的份量超过公共财产以及随着对继承权的关切而父权制和一夫一妻制占了支配地位的时候,婚姻的缔结便开始完全以经济性的考虑为转移了。”〔38〕“结婚乃是一种政治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情感。”〔39〕这种婚姻制度决定了性爱在婚姻中必遭扼杀,注定了劳伦斯婚姻探索失败的命运,终于迫使他到婚姻之外去寻觅他理想的爱情。就此意义而言,劳伦斯以“骑士爱”模式来修正他的伊甸园神话,正是表明了现实主义的胜利。
五、伊甸园的失落:劳伦斯的幻灭与彷徨
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蚀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梅勒斯与康妮的自我实现竟要倒退到人类的洪荒时期,竟只能躲在林地一角的“伊甸园”里偷食禁果,这本身已带有极其浓郁的悲剧意味。更为可悲的是,甚至连这一可怜的伊甸园也注定无法长久维持。在文明社会的干预下,它终于无奈地失落了,亚当和夏娃毕竟还是被逐出了乐园。
伊甸园的失落看似偶然——由于梅勒斯的妻子突然想同他重修旧好,硬要与他同居,从而发现了他与康妮的私情,并大肆张扬,导致他被迫辞职出走——其实却具有必然性。纯洁的爱情必然不能见容于把经济利益考虑放在首要位置上的机器文明社会。“我们的那些资产者不以他们工人的妻女受其支配为满足,更不必说正式的娼妓,并且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其特别的乐事哩。”〔40〕可是他们却不能容忍以男女间的相互理解与真挚感情为基础的真正的、纯洁的爱情,反而视之为洪水猛兽,千方百计地加以破坏和扼杀。在这种社会环境里,康妮和梅勒斯的伊甸园从一开便注定要失落。它也果真失落了。
劳伦斯怀着无奈与惋惜的心情叙述了这一“失乐园”悲剧。他亲手缔造了一个现代伊甸园神话,却又眼睁睁地看着这一神话破灭而一筹莫展,计无所施。神话的破灭实际上反映了劳伦斯性爱理想的幻灭。在书的结尾,梅勒斯和康妮还在等待与各自的配偶离婚,以求能最终彼此结为夫妻。这表明劳伦斯尽管感到幻灭,却还没完全绝望,他还在彷徨,还要继续探索,继续追求。但是他的神话的破灭,实际上已清楚地告诉我们,他的性爱观、婚姻观在阶级社会中毕竟只是个美好的幻想,是个仅仅存在于神话之中、无法真正实现的乌托邦。因为“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及其所造成的财产关系的消灭已把今日对选择配偶尚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顾虑消灭以后,才能普遍达到。到那时候,除了相互的爱慕以外,再也不会有别的动机存在了。”〔41〕
至于以“自然完美”的两性关系来弘扬生命的力量,并以此对资本主义文明,克服现代机器文明的弊病,使“濒临死亡”的英国获得再生,这种想法自然更显得荒诞不经。其实,劳伦斯本人对此也未必坚信不疑。他在一首题为《爱当作逃避》的小诗里便自己驳斥了这一观点:“是时候了,男人们别去想女人,/还有爱、性等等。/因为他们把女人、爱、性当作/逃避,藉此免除对文明牢狱的恐惧。/由于女人同样受困于缧绁,不比男人强,/男人最终只会把她们恨得更深,因为避无可避。/男人当务之急是把金钱打倒,筹建一座崭新的生活大厦。/然后才能去爱。 绝望绝非爱,它只会破坏。”〔42〕
这首诗送给劳伦斯自己,不是挺合适吗?
注释:
〔1〕See A.West:D.H.Lawrence,1951,P146。
〔2〕《影朦胧——劳伦斯诗选》,花城1990版,P39。
〔3〕D.H.Lawrcnce:Sclected Essays,Penguin 1950,P119。
〔4〕《劳伦斯书信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P152。
〔5〕The Holy Bibic,Metidian Books 1967,P10。
〔6〕A.Macleish:To Mr.Rosset,see Lady Chattertey's Lover,Grove Press,P6。
〔7〕〔8〕〔9〕D.H.Lawrence: Lady chattcrley's Lover.Grove Press,P204,P213,P278
〔10〕候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P196。
〔11〕艾弗·埃文斯:《英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P313。
〔12〕吉茜·钱伯斯:《一份私人档案》,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P313。
〔13〕D.H.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Grove Press, P171。
〔14〕Mark Schorer:Introduction to Lady Chatterley'sLover,Grove Press,P24~25。
〔15〕《劳伦斯书信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P58。
〔16〕D.H.Lawrcne:The Rainbow,Penguin Books 1981,P495~496。
〔17〕候维瑞:《现代英国小说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P214。
〔18〕D.H.Lawrcnce:Study of Thomas Hardy and other Essay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P127。
〔19〕D.H.劳伦斯:《我们彼此需要》、《性与可爱——劳伦斯散文选》花城出版社1988年版,P145。
〔20〕〔21〕〔23〕《劳伦斯书信选》,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P561,P578,P543。
〔22〕D.H.Lawrc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Grove Press,P229。
〔24〕劳伦斯:《性与可爱》,《劳伦斯散文选》花城版,P106。
〔25〕劳伦斯:《色情与淫秽》、《劳伦斯散文选》花城版,P124。
〔26〕〔27〕〔28〕D.H.Lawrence:Lady chatterley's lover, Grove press,P174~175,P238,P312.
〔29〕参阅张健:《三种性爱境界》、《环球文学》1959年第三期P39。
〔30〕《劳伦斯书信选》,北方文艺出版社,P63。
〔31〕〔32〕弗克默德:《劳伦斯》三联书店1989年版,P188。
〔3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二卷,P224。
〔34〕〔35〕劳伦斯:《巴黎来鸿》、《性与可爱——劳伦斯散文选》花城版,P297,P296。
〔36〕〔37〕〔38〕〔39〕〔4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二卷,P227,P227,P235,P234,P237。
〔40〕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恩文选》第二卷, P26。
〔42〕《影朦胧——劳伦斯诗选》,花城版,P1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