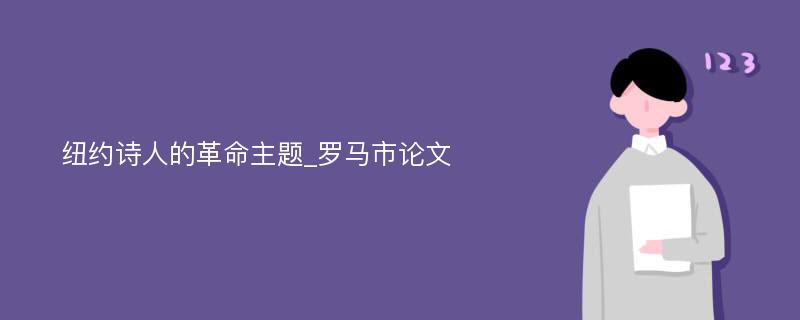
《诗人在纽约》的革命主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人论文,主题论文,在纽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班牙历史上,20、30年代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那时,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艺术都产生了种种危机。1929年的美国股市风潮很快就在国际范围内引起波动,西班牙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一事件的冲击,在经济气候的影响下,政治很快成为国家社会生活的主调,政治因素渗入到社会活动的各个层面,对当时的西班牙文学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艺术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许多艺术家都毅然选择了“承诺文学”的道路,关注时政,将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引入到自己的创作中来。加西亚·洛尔卡在创作《诗人在纽约》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影响,但与其他诗人不同,洛尔卡并没有按照当时“社会诗”面向大众的要求而将诗歌进行简单化处理,相反,他没有避开那些会影响大众化传播的难点,而是经常使诗中一个简单的意象具备多重含义。尽管如此,洛尔卡诗歌创作中的社会“承诺”的目的还是十分明显的,在《诗人在纽约》中,我们还是能看到他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剖析与批判。纵观全集,洛尔卡分别从黑人、犹太人、宗教等几个角度来将他的“革命”主题进行铺展。
《诗人在纽约》的第二章题名为《黑人》。在这一章中,洛尔卡选择了纽约社会中的一个侧面——以哈莱姆区为中心的黑人社会来作为他诗歌创作的对象。鉴于这个种族所处的社会现实状况,诗人在创作中对黑人采取了一种声援、同情与批评、揭露相结合的态度。在诗人眼中,纽约城是忧伤的象征,一种切实、深刻的痛苦是诗人的诗歌世界同纽约的非诗化世界之间的一种纽带。在这两个世界之间,生活着那些忧郁的非洲民众和他们迷失在北美大陆上的兄弟,正是这些黑人,用他们的忧伤构成了美国的一种精神轴线。《黑人的准则与天堂》便描绘了黑人的所爱和所恨,还设置了黑人作为一个具备家系和寻根意识的民族所拥有的天堂。这个假想的天堂里充满了“没有历史的蓝色”,是一个“黑夜(黑人)不惧怕白天(白人)的蓝色”的世界,在那里,“躯干在草的喉咙下梦想。”(MCM,p.123)然而,梦想的天堂在纽约城的现实中是不可能找到的,在这个“燃烧的天堂”里,只有“舞蹈的空洞留在最后的灰烬上”。纽约城将黑色与白色的居民划分在两个水火不容的阵营中。黑人痛恨白人的世界,热爱大自然,因此,自然界哪怕同白人的世界有一点点关系,也会令他们反感、厌恶,所以,“他们仇恨那只鸟的阴影,落在具有白色脸庞的大海的潮峰”(MCM,p.123),但可悲的是,这种仇恨却无法维系黑人的传统,他们已经失去,或更确切地说,就要失去他们的自我,他们受着白人的统治,同时在文化上也被白人所控制,诗人在《哈莱姆国王》中曾写道:
永恒的火睡在燧石上
而喝醉了茴芹酒的丑陋的矮子
已将村庄的苔藓遗忘。
(MCM,p.125)
代表着黑人民族生命力的原始的火焰正处于休眠状态,它并没有消失,只是在静静地蛰伏着,暂时没有了光辉和热量。那些黑人喝着白人酿制的烧酒而烂醉如泥,被迷乱的苦恼折磨着,他们无法与《吉卜赛谣曲》中的吉卜赛人相比,因为他们在纽约无法拥有一个神话式的世界,在这个远离非洲的大都市里,他们只是一个失去了前进方向的迷惘的民族:
在雨伞和金色的太阳之间
黑人们哭得模糊一团。
(MCM,p.128)
雨伞和遮阳伞这些工业产品在哈莱姆区产生了如此巨大的蛊惑力,黑人们不愿意自己有黑色的皮肤,他们用伞挡住金色的阳光,希望自己变白,面对着这种迷乱,哈莱姆国王表现出他的失望,他既庄严,又怪诞,在“水泥丛林”中,这位临时扮成的巫师在游荡:
用一把坚硬的勺子
将鳄鱼的眼睛抠出,
用一把坚硬的勺子
敲打猴子的屁股。
(MCM,p.128)
如仪式一般的举动,遭到放逐的王者的手势,这明明是一个与其根源断裂的民族的活生生的记忆。这种断裂还对那个令人痛心的称呼做出了一定的解释:“啊,化了装的哈莱姆!”带着对血脉溯源的最后一点记忆,哈莱姆王已迷失在纽约的大街小巷中。黑人作为生活在两种文化夹缝中的空虚而孤独的人群,在作者眼中,一直是被剥削的无产者,他们是“厨师、跑堂和用舌头为百万富翁清洗伤口的人们”(MCM,p.130)中的一部分,在《向罗马呐喊》最后一段那受压迫者的长长的名单中,也曾出现了他们的名字(“端出痰盂的黑人”),作者想通过这种方式将种族压迫所具有的阶级压迫的特征也表现出来,于是,在《沃尔特·惠特曼的颂歌》中,洛尔卡便让“沙滩的黑人”与“北方的白人”一起出现在一群“不男不女的人群”中,来将对“黑人问题”的探讨扩展以表现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关系的更广阔的画面中去。在诗人看来,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往往以一种辩证的方式联结在一起,从纯粹的黑格尔主义的角度来看,被压迫者总是拥有或拭图拥有压迫者的某些特点,压迫者与被压迫者成了一件事物的“两半”,在了解到这一点后,黑人民族的迷失便也找到了原因。
但黑人的迷失并不等于他们已失去了一切,在《哈莱姆国王》中,诗人便表达了他对黑人民族的希望。在这首诗的第一部分,诗人指出,黑人“必须过桥去”,必须摆脱他们所处的环境,“抵达那炽热松塔的黑色细语”(MCM,p.127),这是诗人希望黑人能回归自然,回归民族本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黑人们必须用“握紧的拳头”去对付那些统治纽约的人物,只有这样,哈莱姆之王才有可能与他的“臣民们”一同放歌,鳄鱼才会“在月亮的石棉,排着长队进入梦乡”,而黑人用“掸子、礤子、铜锅、铁铲”所从事的工作才能恢复其原有的价值。在这首诗的第二部分中,第一部分的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黑人民族那“已被动摇的血统”正处于一种不公正的、一盘散沙似的状态。“那猩红色的暴力,在半明半暗中沉默而不闻”,受到压抑后便转而去“燃烧金发女人的叶绿素”,“猜疑并寻找白种女人的肉体”(MCM,p.129)。对于这种偏离道德准则的迷乱的发泄,诗人是持批评态度的,他认为黑人民族的鲜血应该是“树林的精髓”,它“从裂缝渗入”,在人们的“肌体上留下一个日食轻微的痕迹”(MCM,pp.129-130)。在《哈莱姆国王》的末尾处,诗人向黑人民族提出了他的忠告,他建议他们去寻找“中心那伟大的太阳,要化作一个菠萝嗡嗡作响。”他指出黑人民族所具备的强大生命力将为哈莱姆之王的臣民们带来新的希望,就象“蛇、斑马、骡子”(来自非洲的动物,可看作是黑人民族的一种象征),“永远不会变成惨白直至死亡”,“伐木者不了解所砍伐的呐喊着的树木(黑人受迫害、受奴役形象的化身)什么时候气绝命断”,而那“伟大的绝望的(哈莱姆)国王,他的胡须垂到了海上”(MCM,pp.125-132),在这里,“胡须”的意象可以暗指黑人民族的古老,也可以借指一个漫长的等待时期,而“海”的意象则是指黑人们将会得到的新的希望。洛尔卡对黑人民族寄予厚望,因为他们还会相信,还会盼望,还会歌唱,他们所具备的一种宗教带来的优雅的懒散,使他们置身于那些危险的对物质利益的现实热望之外。带着这线希望,洛尔卡塑造了“哈莱姆国王”的形象,让他成为全体黑人的代表,成为黑人获得完全的民族个性的一种标志。
可以这样说,洛尔卡在涉及黑人主题时,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没有将黑人问题仅仅作为种族问题来考虑,而是将这个问题同更广泛的社会压迫现象结合起来,并进而开始进一步深入探讨社会体制的问题。洛尔卡认为,在这个充斥着主人和奴隶的世界里,有一个神经中枢,一个支撑着整个资本主义体制、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所在,那就是华尔街(Wall Street),诗人将华尔街称为“un columbrario”,意为“放骨灰瓮的壁龛”,借此来暗指华尔街同死亡的最直接的关系。华尔街的唯一产物是金钱,它缺乏情感,遵循着“唯利是图”的原则,只会使生命腐烂变质,营造一个建立在不公正和苦难基础上的世界。
在涉及到“揭露社会”的主题时,洛尔卡并没有停留在问题的表面,正像他处理黑人主题时的态度一样,他已感觉到一个不公正的体制所带来的令人迷乱的后果,那就是人们的生活最终会成为一种空虚的形式,一种纯粹的表面现象:
在无人的空中有一种空洞的痛苦
而我眼中的娃娃穿着衣裳却没有躯体。
(《一九一○年(间奏)》MCM,p.113)
毫无疑问,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深刻理解是当时经济危机影响的结果,作者在离开美国时就已经对这场危机的严重后果有所感觉,而后来的反复思考也使他就这个问题的想法更加成熟。虽然在洛尔卡眼中,华尔街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心,但他并没有忘记指出那些华尔街的帮凶,其中便有那已被制度化的基督教。纵观整部诗集,有关宗教方面的内容,被作者分成四个阶段来加以体现。
第一阶段,人们可以感到《死神舞》中宗教的存在。教皇同其他一些有权有势的人物(国王、蓝色牙齿的百万富翁等等)一起出现在一个充溢着不祥气息的庄园里,宗教的身影在游荡,它便是“教堂里面无表情的舞女”(MCM,p.141)。“面无表情”这几个字不由让人想起教堂里泥塑圣母像的冷漠。诗人看到“死亡之舞”中的舞蹈者们所具有的共性,并将这种共性展示给读者:
别再起舞,教皇!
别再起舞,国王,
还有那蓝色牙齿的百万富翁,
教堂里面无表情的舞女
建造者、绿宝石、疯子和不男不女的人。
(MCM,p.141)
在这里,神圣的教皇同世俗中丑恶的“疯子和不男不女的人”一同成为造成精神死亡的元凶,这不可不说是一次大胆的揭露和抨击。
第二阶段反映在《哈莱姆国王》一诗中,在这首诗中,洛尔卡对黑人们这样说,一俟这个城市毁灭,他们将可以“杀死我们的摩西”,“我们”这个物主形容词相对于黑人而言,具有很深的意义,它说明基督教是同白人世界相一致的,它并不站在受难者一边,而是站在压迫者一边。这样,作者再一次将宗教定位于“统治者同盟”的位置上。
第三阶段,即《犹太人的葬礼》阶段中,作者将敏感的犹太人问题同对宗教的讨论结合起来。这首诗的主线实际上是一次葬礼,是埋葬一位犹太权贵的葬礼,暗示为犹太人社会和基督徒社会安排的命运最终都是延伸向死亡的,诗中人物们到达的墓地其实就是一个“活的”墓地,是一个渐趋没落的高层社会的所在。犹太人集团和基督徒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在诗中是显而易见的:
基督的女儿们在歌唱
而犹太姑娘
用山鸡孤独的眼睛注视着死亡,
千万个景色的苦恼使这只眼睛闪光。
(MCM,p.206)
在被神意选定的基督徒们歌唱时,犹太人却与死亡面对面地相遇,被一场致命的痛苦所控制,像等着被捕猎的山鸡一样睁大眼睛盯视着死亡。那只唯一的眼睛,则是那种令人伤痛的精神赤贫的见证。诗人在这里写到“山鸡的眼睛”,是因为犹太民族为基督教世界所排斥的命运已同那可怜的脆弱禽鸟的命运没有什么两样了,他们是一个流浪的民族,经历过无数的苦难,正因为如此,在他们那“面临死亡的眼睛”里,才会反射出“成千上万的风景”。但我们不能仅仅因为犹太人所受过的苦难而将他们简单地看成受压迫者,如果黑人不是简单的牺牲品,那犹太人就更不会是。诗中有一段内容对此加以反复强调,犹太人“在墓地走廊的恐怖”中哭泣:
一个人有一只表的齿轮
另一个人有会说话的毛虫的战利品
(MCM,p.207)
犹太人曾是伟大的发明者,第一句诗使人毫不困难地想起犹太思想家斯宾诺莎,他在完成他的思辨工作的同时,还干着钟表匠的活计。犹太人还是精明的商人和工厂主,依靠对工人和雇员的剥削,积累起了大量的财富,凭借财富,他们或许可以买到物质上的一切,但森严的基督教世界仍然将他们视为异类,他们永远是一切重大社会变革的首批牺牲品,永远是精神上的孤独者,所以说,犹太人既是受害者,也是迫害者,在对现代文明进行控诉的过程中,他们也不能完全脱掉干系,然而,说到我们所关心的主题,最主要的责任者还应该是基督教会,《犹太人的坟墓》这首诗虽然在诗句含义方面显得异常复杂,但有关这个内容的表现却十分明确。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这一点,我们只要想想“基督的女儿”的歌唱之外的世界,就不难看到犹太民族那已被投射到死亡世界之上的命运,看到基督教那漫长的排外的历史。
《向罗马呐喊》可以被看作是宗教主题反映的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洛尔卡在这首诗中表现了非常强烈的反教会倾向,他指控教会同那些压迫者沆瀣一气,指责教皇应该对这个世界的无序状态负责。诗人认为,教会从来未曾同受苦的大众站在一起,罗马已成为即将把世界引向战争的狂人的同盟者,变成了一个阿谀奉承的献媚者,(“这一切都在那伟大的穹顶降落,它在军人的舌头上将圣油涂抹。”MCM,p.215)教会已经忘记并背叛了基督提出的兄弟友爱的宗旨(“已经没有人分发面包和葡萄洒”……MCM,p215),这个世界的未来,将只会存在着奴役和一个集体毁灭的结局,将有成千上万的牺牲者绝望地等待末日的审判:
只有一百万铁匠
为将要出世的孩子们锻造锁链。
只有一百万木匠
打制没有十字架的棺材。
只有怨声载道的人群
敞开衣服等待着枪弹。
(MCM,p.216)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提一下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在作者创作《向罗马呐喊》前不久,意大利独裁者墨索里尼刚刚同教皇皮奥六世签订了“雷特朗(Letran)协议”,统治者与教会公然勾结在了一起,天主教已经成为权贵们的帮凶和同盟,并且已构成压迫者的思想理论和经济机器的一部分。从洛尔卡在诗中表达的激忿和不满中,可以看出诗人还勇敢地站在了“反战”和“保卫和平”战线的最前沿,诗中对宗教的批判与揭露在这个基础上与全书宗旨达成了完全的一致,成为一种超出主体理论内容的完美结合,具备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
从某种意义上说,洛尔卡诗里对宗教的批判中还包括了对宗教造成的“迷乱”状态的揭露。他指控教皇背叛了福音书中的精神真谛,这可以被看作是对以教皇为首的教会的最猛烈的抨击之一。《向罗马呐喊》并没有提出什么形而上学层次上的争论,因为这首诗的主旨就在于用一种具体的方式表现福音与教皇势力的强烈对比。在《哈德逊的圣诞节》中,这种对比也是存在着的,基督教徒唱着“哈里路亚”,却“不懂得世界由于天而孤单”(MCM,p.149),在“荒凉的天际”,没有一个人,但“哈里路亚”却依然在被一遍遍地歌唱,那些信徒没有觉察到那天际只有死亡和空洞,诗人却清楚地看到:“没有黎明。(只有)无生命的童话。”(MCM,p.150)也就是说,基督教没有给人们提供什么希望;它已经成为一段古老的历史,已经枯竭、衰败,就像“无生命的童话”,可尽管如此,教会对人民的欺骗还是会毒害人们的精神,因为它使人们看不清事实的真相:
砒霜的鱼群宛似鲨鱼,
鲨鱼就像使人群失明的珠泪颗颗,……
(《向罗马呐喊》(MCM,p.215))
诗人之所以为宗教这样定性,是因为他将基督教也列入了世界上存在的各种“迷乱状态”中的一种。在《向罗马呐喊》这首诗中,诗人将教会的那种不合作、分裂的态度同来自人类痛苦的真正的爱对立起来,他用“罗马巨大的穹顶”和“白衣男人”的形象来代表教会,对教会的权势提出了猛烈的抨击。在诗人眼中:
那些雕像下面没有爱情,
在那些毕竟是玻璃的眼睛下面没有爱情,
爱情在被渴望撕裂的肉体中,
在与洪水抗争的茅草棚里,……
(MCM,p.216)
正是由于教会一直持这种与爱对抗的态度,这世界已处在一种无爱的状态下,“已经没有人分发面包和葡萄酒”,“只有一百万木匠在打制没有十字架的棺材”,“而那身穿白衣的男子,不懂得谷穗的奥秘,不懂得分娩的呻吟,不懂得基督还能赐人以水”(MCM,pp.315-217)。从这些诗句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洛尔卡对教会所怀有的强烈的不满,诗人为这篇作品原定的题目是《不公正的颂歌》(Odadela injusticia),这一题目深刻揭露了教会的不公正态度,在这种态度面前,所有受压迫的人——“端出痰盂的黑人,在校长苍白的恐怖面前颤抖的孩子们,在矿物油脂中窒息的女人们”——势必要向罗马的“穹顶”发出呐喊,“因为我们想要每天吃的面包”,“因为我们要求大地的意志能够实现,将它的果实分给所有的人”(MCM,p.217)。通过“我们想要”(queremos)这种动词第一人称复数形式所表现出的反映团结情绪的语调,可以看出诗人把自己也作为忍受苦难的人们中的一员,“锤子、提琴和云彩的人群”,也就是说,所有靠双手劳动生活的人,那些艺术家,那些梦想者,都会团结起来,根据基督的指示,要求得到一个他们该得到的大同世界,一个能够给予他们每天的面包的世界。
当然,罗马并不是西方世界的唯一象征,在洛尔卡的作品中,还提到了维也纳。维也纳是西方世俗世界古老传统的化身,听起来似乎不像美洲这个“新世界”那样遥远。它是一种优雅得近乎荒唐的没落文化的代表,而这种文化的外在象征,便是华尔兹。这种舞蹈往往同贵族的腐化联结在一起,它同哈莱姆黑人的舞蹈和古巴黑人兴高彩烈的“松舞”有着天壤之别。它是没落的宫廷贵族的舞蹈,以宏大华丽的宫殿来作为表演的舞台,但这种宏大与华丽无法掩盖其腐糜的本质和没落枯竭的结局,于是作者在诗中将“小提琴”和“坟墓”这两个毫不相关的意象排列在一起,来隐喻“艺术”与“死亡”,将西方传统中的消极成分同死亡、腐败和谎言联系了起来。
然而,洛尔卡并没有将他的诗句仅仅局限在对一个腐朽世界的批评和揭露中,而是在批判的同时,提出一些改造现实的建议。首先,他对理智的力量加以嘲弄,对那曾引导人们创造了这个满是“电缆和死亡”的城市的理智力量进行无情地嘲讽,对美国城市这那偏离自然的景象和美国先进的科技发展都进行了批判:
光明被锁链和喧嚣埋葬
在没有根的科学
厚颜无耻的挑战中。
(《黎明》MCM,p.161)
这句诗很重要,它表明,诗人并不是在否定所有科学,而是反对“没有根的科学”,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诗人才会赞颂那初始的、未经污染的大自然,才会将白痴和儿童所具备的本真状态作为获得拯救的途径。可以肯定的是,诗人的这些观点都是以爱为基础的。在这里,对本体不公正的抗议同对历史不公正的抗议紧密结合起来,这两种不满的情绪在那些“马丽卡”们、银行家们、教皇和权贵们所无法理解的“分发欢乐王冠的爱”中融为一体。这种爱只存在于那些受压迫者中间,在他们那“被饥饿撕裂的肉体”中,在他们的苦难中。可是,有时,这种爱也会被各种暖昧的关系破坏掉,也有可能被他们受到的压迫所扼杀。在看到纽约城终将成为现代机器文明侵害的牺牲品后,洛尔卡提出了建立一个天堂般新世界的希望,他认为在白人们得到他们悲惨的结局后,将由一个黑人孩子来宣布这个希望:
我愿深沉的夜晚的强风
将你安息处拱门上的字母和花朵抹去
让一个黑孩子向金发的白人
宣告麦穗王国降临的消息。
(《沃尔特·惠特曼的颂歌》MCM,p.224)
诗中这个黑人孩子是所有被压迫者的代表,尽管这些被压迫者们正在经历着精神和肉体上的迷乱,但他们仍不失为这个世界上最有才智、最文雅的人群。然而,“麦穗王国”的到来又将如何实现呢?在这一点上,“革命主题”便显示出它特别的重要性。《诗人在纽约》中交织着一系列带有预言意图的诗句,这有助于人们理解洛尔卡的建立一个美好社会的充满诗意的理想。洛尔卡在《哈莱姆国王》中预言了城市那被森林湮灭毁掉的未来,在《死神舞》中也展示了一个类似的恐怖的情景,但是诗人有关“革命”内容的深入却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出发的,而且是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反映出诗人在这方面的思想认识:
眼镜蛇会在最后的楼层中咝咝游动
荨麻将使院落和平台上颤抖
交易所要成为一座泥的金字塔
在枪决以后
野藤将蔓延而至
很快,很快,很快,
啊,华尔街!
(《死神舞》MCM,p.141)
这几句诗展示了“森林”会给纽约带来的灾难,诗人设想“森林”对纽约的统治将会是许多具体的历史事实的后果。上面引用的这段诗中的第四行最为关键,“在枪决以后”,森林会大举侵入,也就是说,森林的入侵实际上是一支革命队伍毁灭城市的行动的后果。这场革命的胜利将会给纽约城带来最终的覆灭,对于一个新社会来说,纽约已经成了一座不可救药的死城。在诗人看来,革命的最终发生是不容置疑的,因为那些受压迫者的态度决不会是完全被动的,“失业工人的呻吟声将因你没有光明的时代而在沉沉黑夜中怒吼!哦,北美的森林!哦,不知耻的森林!……”(MCM,p.139)所有这一切都会“很快发生”。在《向罗马呐喊》中,也出现了失业工人的呻吟声、怒吼声,洛尔卡断言,那些被践踏、被奴役、被嘲弄的人群,终将发出怒吼,在一场没有兵营的战斗中清醒过来,进行反抗,“尽管会在墙上碰得脑浆迸裂”,他们还是“要呐喊”,“直至城市都像女孩儿们一样抖颤,并把储藏油和音乐的监狱打烂”(MCM,p217),来实现“大地将它的果实赐予所有人的意志”。为了使“麦穗王国”的到来成为事实,必须要经过一段充满暴力和骚动的时期,我们可以看出,在哈莱姆黑人民众的呼吁声中,已充满了对这个时期到来的要求和渴望:
必须将卖烧酒的金发人杀死
将所有苹果和沙子的朋友杀死
必须用握紧的拳头打击
那些颤抖的充满水泡的犹太小姑娘
让哈莱姆王和他的人群一起歌唱,……
(《哈莱姆国王》MCM,p.127)
然而,除了这一预言,还有另一条途径可以实现“麦穗王国”的降临,这条途径与革命的道路并不冲突,而是对革命道路的补充,那就是对一切迷乱状态和欺骗行为的摒弃。何谓“迷乱状态”?对此,洛尔卡已通过他的诗歌对人们作出了解释,所谓“迷乱”,就是事物没有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而是偏离或失去了“自我”。这是诗人要传达给黑人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信息,在他看来,黑人的世界充满了空虚的造物,黑人因迷失自我而感到孤独,从这方面来讲,孤独主题是具有一定独立性的,但如果从深层发掘,就可以发现。黑人的这份孤独是与他们所处的“迷乱状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的,而改变这种状态的唯一途径是恢复对黑人民族潜质的信心,寻找到真正的民族个性,使他们在社会的发展中不致迷失自我。
至于对宗教所造成的迷乱后果,诗人采取了坚决抵制和反抗的态度。他在《被遗弃的教堂》中写到了一位拒绝宗教抚慰的父亲,因为他看到,在死神的面前,宗教虚伪的面纱已被剥得精光:
我知道他们会给我一只衣袖或领带
然而我会在弥撒的中心打破船舵……
(MCM,p.134)
这位父亲对那些虚伪可笑的抚慰的拒绝是坚决的,他甚至要在“弥撒的中心”,在圣餐礼拜的奉献仪式中,打碎船舵,这里的“船”暗示“信仰的航船”。这位父亲这样做,是要向那些毫无意义的宗教传统和规范说“不”:“……那时,海鸥与企鹅的疯狂将来到石头上”,来自大海的动物的聒噪将传到教堂和祭坛的石头上,这是在教条和信仰沉落的同时升起的希望,是反抗无尽的孤独和不安的本真所在。
在提出改造迷乱状态的建议的同时,洛尔卡还提出人们之间团结的必要性,反对只有个人获得拯救的途径,诗人认为,“团结”的精神应该同对“恐惧”的摒弃联系在一起,因为一个满心恐惧的人会在他的逃避中被自己的恐惧撞得人仰马翻,于是,诗人写道:
为自己的痛苦而痛苦的人将会永远痛苦
而畏惧死神的人将把死神扛在肩上。……
而那个带着破碎的心逃跑的人
冒着星宿温和的抗议
会在街头碰上令人难以置信的平静的鳄鱼。……
(《不夜城》MCM,p.151-153)
在摒弃内心恐惧的同时,诗人希望人们能够梦想,因为这是发掘每个人创造力的可行途径,他希望“活的鬣蜥会来咬不眠的人”,让他们脱离那些低俗情欲的控制。
诗人设计的这条道路也许可以为“麦穗王国”的到来做些准备,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诗的形而上学的意义和社会意义如何联系在了一起。然而,读完《诗人在纽约》的全部作品,也许有人会问,凭借这样一个带着悲观色彩的宇宙论——已注定的一切造物的死亡,时间流逝带来的惩罚,明暗面的展示,洛尔卡心目中的“麦穗王国”会有可能实现吗?我们不能忘记,诗人的宗旨是让“麦穗王国”的形象在一个超现实的神话层面上获得它的全部意义,我们不能试图用一种概念化、简单化的观念来解释洛尔卡诗歌创作中的“革命主题”,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再一次表明,在下面这些带有预言性质的诗句中,洛尔卡使诗的美学含义和社会含义得到了完美的结合:
另一天
我们将看到蝴蝶标本的复活
并沿着一个
灰色海绵和沉寂船只的风景跋涉
我们将看到戒指在闪烁
看到从我们的舌头上涌出玫瑰的花朵。
(《不夜城》MCM,p.1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