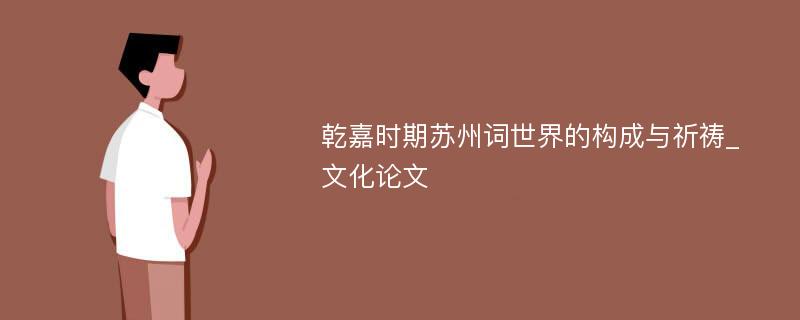
乾嘉时期苏州词坛的构成与祈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州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01(2010)06-0064-04
一、浙派“主潮”:吴翌凤之“峻峭”与郭麐之“性灵”
清初顺康二朝,苏州专以词名者数量不多,且与当时阳羡、浙西两大词派较少瓜葛。雍乾以降,苏州一带(含今上海、嘉定、青浦等)则渐渐成为“浙派”全盛时期的一个重要据点。以过春山、吴翌凤、郭麐、陶梁、“后吴中七子”等为代表的大批名词人堪称“浙派”中后期的骨干中坚。而太仓诸王的“小山词社”、张埙、彭兆荪、宋翔凤等,则或反拨时风,或戛戛独造,或折中“浙”、“常”二派而自出面目,都各自有所树建,使姑苏词界呈现了百派争流的多元局面,其瓣香遗韵直接影响了与新文学接轨的“南社”诸子。陶梁、“后吴中七子”、宋翔凤等行辈较晚,于晚近词坛关系较大,拟另文再述,本篇仅就乾嘉时期作一简略梳理。
吴翌凤(1742-1819),字伊仲,号枚庵,吴县人,诸生,青年时客游楚南,垂老始返,筑室曰“归云舫”,是时文人多从其游。博雅工诗文,著有《与稽斋丛稿》、《国朝诗文征》,而以《吴梅村诗集笺注》最为有名,词集名《曼香词》,二卷,又有《红沫词》。
翌凤自序其词有“大抵文生于情,不觉哀多于乐”之语,这是就基调而言,其风格其实颇为密丽峻峭而富于情韵,短调如《苏幕遮》:
片帆张,孤棹拥,渺渺长波,只有青山送。衣上花枝钗上凤。
月冷香销,都付秋衾梦。养鱼苗,量鹤俸,生怕相思,红豆休轻种。
借酒浇愁开宿瓮。一掬西风,泪洒颇黎冻。
又如《临江仙》:
客睡厌听深夜雨,潇潇彻夜偏闻。晨红太早鸟喧群。霁痕才着树,山意未离云。
梅粉堆阶慵不扫,等闲过却初春。谢桥新涨碧粼粼。茜衫毡笠子,已有听泉人。
前阕向不为选家所重,然用语皱折而颇见流利,襟怀脱略而不乏深情,同时,不大有人能具此手笔;后阕则是名作,精彩处在末二语,清怀雅致,举重若轻,即谭献所称“高朗”是也。前人论乾嘉词界,于翌凤许为“功力独深”,其实是真气贯穿,深于言情,故平凡语乃能出奇境。如《婆罗门令》云:
看不得、一绳纸雁,听不得、送隔墙鹅管。待较深愁,除得是、长江练。愁无限。只怕长江浅。
芳菲陌,杨柳岸,计当时、那许游情倦。风花纵得红如旧,人别后、奈双鬓千点。
雁书难寄,蝶梦空恋,日近江南偏远。试检春衫泪,已洒春衫遍。
此调应歌功能较强,俚俗絮叨处近于曲子,柳永后几无佳篇,本词可称难得之作,其上片寥寥数语,一韵一转意,尤其自然出奇。
行辈晚于吴翌凤一辈的吴江郭麐本有“浙派殿军”之誉,但自谭献与陈廷焯下了“滑”和“最下乘”的判决之后,一直遭受着种种冷落。他生前清寒,身后又遇不公,思之增人感叹。
郭麐(1767-1831),字祥伯,号频迦,因一眉莹白如雪,又自号“白眉生”,年五十号蘧庵,六十号复翁。先世本秀水(今浙江嘉兴)人,明中叶移家吴江之芦墟村,至频伽复于嘉庆四年(1799)迁居嘉善之魏塘。郭麐少有“神童”、“异材”之称,及长则一第累踬,长期困于科场,奔走江淮之间多年,坐馆课徒,吟诗著述。他虽地位寒贱,却能领袖一方,为彼时文坛一不可忽略之重镇。今存《灵芬馆全集》中,诗多达三十九卷,四千余首;诗话四部,二十七卷。仅就诗题考见之交游即达四百人,为人作诗词集序跋近六十篇,点定诗集数十种。舒位著《乾嘉诗坛点将录》,点为天巧星浪子燕青之位置,可见其巨大影响[1]。词有《灵芬馆词》四百余首。又有《灵芬馆词话》二卷。
频伽述其学词经历云:“予少喜侧艳之辞,以《花间》为宗,然未暇工也。中年以往,忧患尠欢,则益讨沿词家之源流,藉以陶写厄塞,寄托清微,遂有会于南宋诸家之旨”,夫子自道,其浙派家数甚明。问题在于,他所面对的浙派既非朱彝尊登坛树帜、以卓绝的词创作成就号令天下的前期,也不是厉鹗以清峭幽远绍继姜张宗风、力辟新境的中期[2],而是“浮词”、“游词”、“鄙词”翕然风靡的后期。对此,郭麐看得很清楚。《灵芬馆词话》卷一论袁通词云:“袁兰村少时喜为侧艳之词,余尝为之序,未敢许也。后见所刻捧月楼词,居然大雅。前所见者十不存一二,因叹其竿头之日进也”。卷二又云:“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然必得其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近人莫不宗法雅词,厌弃浮艳,然多为可解不可解之语,借面装头,口吟舌言,令人求其意旨而不得。此何为者耶?昔人以鼠空鸟即为诗妖,若此者,亦词妖也”。郭麐作为浙派后期的主盟者,他对词坛状况的感知、所持批判的态度、意欲药石其萧飒的企图,与常州词派的创辟者之间都是大体相通的,二者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只是在如何拯衰救弊这一点上采取的方法不同而已。常派讲“寄托”,讲“意内言外”,郭麐则拈出“通变”二字。这是一个几乎被用滥了的词汇,但郭麐还是有自己的体会,放在乾嘉词坛的大背景下,强调“通变”也别有意趣在。
他说:“能卓然成家者递沿而递变……各自有其规模,此文章流变一定之理”(《与霁青论文书》),又说“一代有一代之作者,一人有一人之独至”(《与汪楣庵论文书》)。那么,何谓“独至”呢?在他看来,“独至”就是建立在“不欺其志”(《友渔斋诗集序》)基础上的“自己而出”(《刘芙初尚綗堂集序》),也就是从自己的个性出发,尊重自己的性情所至,以“真”作为一切文艺活动的指归。他强调说:“夫人心不同,所遭亦异。托物造端,惟其所适。但论真赝,不问畛畦”(《江昕香诗引》),“学之者之心思才力,足以与古人相深而自抒其襟灵”(《桃花潭水词序》)。《灵芬馆词自序》从自身落拓飘荡的感受出发,语气颇冷傲:“春鸟之啾啁,秋虫之流喝,自人世之观,似无足以悦耳目者,而虫鸟之怀,亦自其胸臆间出,未肯轻弃也”。应该指出,这些思想既得力于郭麐自身的人生况味与创作实践,又与他师从袁枚,受到“性灵说”的一定影响有关。先师严迪昌先生以为:“郭麐诗属南宋杨万里‘诚斋体’一路,与稍后的同乡江湜是清代最出色的以白描抒性灵的诗人,故在乾嘉之际系‘性灵诗派’行列的作家”,“郭麐作为‘性灵诗派’的成员是力图援性灵入词的”[3]1324。这是实事求是的判断。正因为讲“性情”、“独至”,所以,郭麐虽推崇朱彝尊为“国初之最工者”(《梦绿庵词序》),不废浙西家法,却能旗帜鲜明地表示:“纷纭门户,不足置论也”(《朱铁门文稿序》),对于乾嘉词坛根深蒂固的门派观念,也包括浙派中人的某些习气深致不满。
这是“通变论”的重要基础。具体到词的问题上来,在早年所作的《灵芬馆词话》中,他开宗明义,提出词派有四种,其中姜张为极则,而东坡虽“雄词高唱”,乃“别为一宗”,稼轩则“粗豪太甚”,显然都寓有贬损之意。到后来作《无声诗馆词序》时,他的看法出现了很大的转变:“苏辛以高世之才,横绝一时,而奋末广愤之音作;姜张祖骚人之遗,尽洗秾艳,而清空婉约之旨深。自是以后,欲离去别见其道而无由,然写其心之所欲出,而取其性之所近,千曲万折以赴声律,则体虽异而其所为词者,无不同也……进幺弦而笑铁拔,执微旨而訾豪言,岂通论乎?”不难看出,这种“习玩百家,博涉众趣”(《词品序》)的词史观已经相当精辟而理性,不仅不像以保守顽固著称的浙派阵营,甚至还超过了继起的很多常派中人。
郭麐的“性灵词学”理应还包括他的名作《词品》。《词品》十二则既是幽雅清隽的四言诗,更是基于“通变”观念的词风格论的佳作。十二则的标目是:幽秀、高超、雄放、委曲、清脆、神韵、感慨、奇丽、含蓄、逋峭、秾艳、名隽。其中至少雄放、感慨二品是不见赏于当时的浙派,也很久没有人为之张目的了。试看郭麐的阐释:
雄放海潮东来,气吞江湖。快马斫阵,登高一呼。如波轩然,蛟龙牙须。
如怒鹘起,下盘浮图。千里万里,山奔雷驱。元气不死,乃与之俱。
感慨人生一世,能无感焉。哀来乐往,云浮鸟仙。铜驼巷陌,金人岁年。
铅水迸泪,鹍鸡裂弦。如有万古,入其肺肝。夫子何叹,唯唯不然。
那么,不妨这样说,以《无声诗馆词序》和《词品》为标志,郭麐辛勤建构的“性灵词学”已获大成。至此“完全可以认定,郭麐的词学观以及从中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的文艺观,是清代中叶以至晚近时期最具开放性的观念”[3]1326,它并非如许多论者定谳的那样,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常州词派的“先进”理论冰炭不同炉的。频迦是后期“浙派”中卓有识见的理论家,同时,也是嘉道之际独具面貌的重要词人。一部《灵芬馆词》无论长短调,无论常用词牌或是僻调,皆能“清折灵转”(吴衡照《莲子居词话》语),触手欲飞,而结撰中慧心别裁,处处可以感知到疏朗而又折叠的美感,《水调歌头·望湖楼》一阕最称典型:
其上天如水,其下水如天。天容水色渌净,楼阁镜中悬。
面面玲珑窗户,更着疏疏帘子,湖影淡于烟。白雨忽吹散,凉到白鸥边。
酌寒泉,荐秋菊,问坡仙。问君何事一去,七百有余年?
又问琼楼玉宇,能否羽衣吹笛,乘醉赋长篇?一笑我狂矣,且放总宜船。
严迪昌师评说此词云:“下片二问,看似清狂之语,其实正是他‘廓落鲜欢’的情怀流露,是对人世间的难以长啸一吐胸臆的愤懑”[4]446。这是抉中频迦深心之言。他命运偃蹇,内怀畸苦,轻倩的笔墨后面时时闪现着痛楚和辛酸。郭氏笔下多罕见的沉痛之作,也是乾嘉词坛不多见的悲凉心音。
二、词坛别调:彭兆荪之“精悍”与张埙之“恢奇”
乾嘉时期,不逐时好而独来独往者还应提到彭兆荪和张埙二人,与郭麐等人一样,他们也是“高才无高第”、声名甚响而实遭埋没的才人。
彭兆荪(1768-1821),字甘亭,一字湘涵,镇洋(今太仓)人,诸生,少神隽有声,年十五应顺天乡试,后屡试不举,遂绝意仕进,专力于诗古文词,其人品耿介拔俗,所云“节目本来多磊坷,况抱冬心恬漠”(《贺新凉·戈小莲科头箕踞长松下图》)适可自为写照。道光元年(1821),与娄县姚椿同被荐孝廉方正科,相约不赴,未几卒。有《小谟觞馆全集》行世,词存一卷,即称《小谟觞馆词》。
甘亭骈文是乾嘉一大家,诗词名与郭麐相埒,声气交通,足称莫逆,然风格多沉厚博丽,有别于频迦的通爽豪隽。其《卖花声·雁门道中》句云:“西风尖似弩牙机。吹过紫崖松一片,卷出红旗。”《台城路》句云:“一握飞云,春波横上酒边脸”、“六月琼疏,日光钗焰闪”都能见出奇横的炼句功夫。《木兰花慢·寄尤二娱金陵》则通首体现他这一特色,词云:
酒边人去也,雁络起,一天凄。有瞰烛饥鼯,吟莎潜蛩,叫树醉鸡。
牢耶石耶满眼,问何人、解唱白铜騠。欲赋郊居传客,愁他读错雌霓。
小姑祠屋水东西,邸舍僦青溪。想桃叶江空,石桥巷小,丁字帘低。
杨家槓家无恙,定翻香、小令脆于梨。记否寒斋风雨,寒花一稜秋畦。
甘亭词集前有自序短短数语云:“填词至近日,几于家祝姜张,户尸朱厉。予方心沓舌,无志与诸子争长,而浏览所及,颇不欲囿于时论……”[5]其不情愿搅入“浙派”营垒也明矣。象《满江红·客中寄张子白八首》挥洒狂啸,虽时露粗疏,要非浙派中人能言之语,其八是前七首种种行迹的总结,因而最为沉痛:
仆本恨人,干甚事,泪花扑簌?平历遍,中年哀乐,哀丝苦竹。
最薄断推才子命,难消第一团圞福。怪来年,骑省鬓星星,何其速?
《蓼莪》什,我废读;“渴凤”句,君应续。算两番人事,一般枨触。
开合迟君拏艇至,埋愁共把糟丘筑。故悲歌,和尔七哀诗,同声哭。
历来学者论甘亭词,多取其一部分清雅的小令,比起这样精光干练、令人悚然的篇什来,是有一点不痛不痒了。
最后论张埙。张埙(约1735-1786后),字商言,一字商贤,号瘦铜,又号吟芗,先世居于吴兴(今浙江湖州),门第高华,清初始迁至吴县,乾隆三十年(1766)举人,官内阁中书,有《竹叶庵文集》,诗二十六卷,《林屋词》七卷,系晚年据平生所作《碧箫词》五卷、《春水词》二卷、《荣宝词》十卷、《瓷青馆悼亡词》二卷删定而成,另有《红榈书屋拟乐府》二卷。
张商言官位甚卑,然才望重一时,与当时文坛名辈如沈德潜、毕沅、翁方纲、钱载、赵翼、吴锡麒、洪亮吉等交好,与蒋士铨尤契,诗风奇肆沉厚亦略同,填词则有“小迦陵”之目,嗣响阳羡词宗陈维崧的风格,在当时苏州词坛是一位琵琶别抱、冷调独弹的名词人。作于早年的《贺新郎·观演(长生殿)院本》不仅步了陈迦陵《虎丘五人之墓》的原韵,其激荡的词情、卓绝的史识乃至冷峻的口气亦都能得这位前贤的精髓。上片云:
雨摆梨花罅。佛堂前,风波平地,可怜人鲊。
未必卿卿能误国,何事六军激射。唐天子、何其懦下。
一世夫妻犹如此,为今生、反使来生怕。双星恨,高高挂。
《沁园春·登丛台放歌》则愈加胆开气盛,恢奇肮脏,魄力似比同时师法阳羡的郑燮、姚椿、蒋士铨等人犹有上之:
高会当年,置酒从台,明灯既张。有五铢一握,烟云幂历;千金双靥,白皙清扬。
妾亦长生,君惟不死,月烂星辉照洞房。又说甚,探些些雀鷇,骨肉仓皇。
我来盱眼都鄣,便屠狗、亲蚕事已忘。
况笙歌珠玉,临风则散;精神魂魄,遇穴则藏。
来者古人,去者明日,此意悲凉孰可商。凭阑久,但乌乌城角,吹入浑漳。
商言在《林屋词自序》中如此评价自己各小集的长短:“大概《碧箫》少作,最不足存,《瓷青》屡境惨毒,词旨哀伤,当非正声。《荣宝》其庶几精华昭灼,有暾然难掩者矣。”其实他所得意的《荣宝词》已经开始敛才就范,清疏敦厚的倾向渐重,可喜之作反不及《碧箫》、《春水》二集为多。其中如《饮酒十首》之四作于其妻殁后七年,耿耿伤悼之情仍可令人动容:沧海明珠不可寻,七年井臼剧伤心。衔杯独自意沉沉。鬼蝶莫胜寒食雨,山花长似美人簪。也曾同醉一楼深。
《瓷青馆悼亡词》删存后尚得六十余首之多,其《洞仙歌·悼亡日近,舟楫杂词十六首》等皆情见乎辞,读之恻恻然,比之纳兰容若虽有距离,亦自有特色,在悼亡词史上可占有一席之地的。与郭麐、彭兆荪等沉沦者比较不同的,张商言因分校四库,得亲禁近,集中“纪恩”、“奉和”之诗作颇累篇牍,似多了些“奴气”。这是大多文士的常态,不能苛责的,但他自顾“马周身世”,常有“蛣腹生涯,蟁眉伎俩,逆旅风光去住难”(《沁园春·十二月二十四日作》)的悲慨,认识毕竟清醒且沉痛。晚年的一阕《念奴娇·次偃师县》不徒自言心境,亦适可为处于“十全王朝”盛景笼盖下一大批才士下一痛切的转语,兹录之以为本文之结末:
阴阳夕路,问道旁逆旅,谁谭元者?入洛才华空叹息,略似鬼谋于社。
膏以香煎,兰宁永馥,鹤唳伤心话。生不五鼎,死而五鼎何也?
何如有视鸡翁,亮风千载,赁屋尸乡下?邻曲忘机差自乐,岂在神仙声价?
物累无涯,吾生有限,智士知真假。龙云蛇雾,不然将为八鲊。
收稿日期:2010-09-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