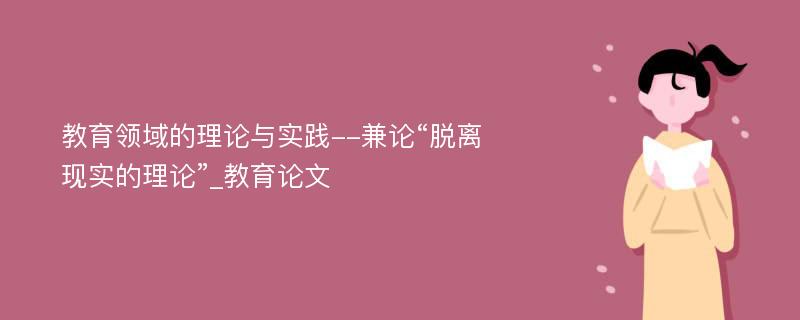
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践——兼评“理论脱离实际”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论论文,领域论文,兼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不同性质的理论,不仅构成了对实践的性质的不同解释,而且它们还包含了关于理论的实线目的的一些不同观点。所以,我们首先要探讨教育理论的性质。
在教育中,“理论”一词的含义基本上可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教育者的教育活动中一般是以一个理智的或自我反思的过程为前提,并引起进一步的思考,它依赖于目的及手段之间的关系的假定,以及对既定情景的解释。产生这种思考的那些意见或看法被称之为广义的“理论”,即教育者的主观思维构成。它部分依赖于教育者自己的思考和观察,部分地依赖于从他人那里获取的知识。这种理论是伴随着教育实践而出现的。从狭义上理解,“理论”意谓有关某一领域的系统化的观点体系,或是一种非实践的思想体系,或是一种令人崇尚的知识,这类理论的出现是滞后于实践的。
关于教育理论性质的考察,必须从教育理论性质的划分问题入手。在西方学术界,关于理论的二分法可追朔至古希腊,柏拉图把纯粹的理论知识当作“科学”,他认为,人们从事研究是为了认识永恒的事物,即把握事物的本质,而不是为了认识暂时出现的、将会消失的事物。他所指的“科学”,实际上是哲学的代名词;亚里斯多德认为,“科学”不仅指理论知识,还包括实际知识(如政治学、经济学知识)与应用知识(如修辞学等),这就承认了实践知识的独立地位。他的“理论科学”还是哲学。这是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二重区分的原始依据。
到了近代,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指的是实证——实验科学。它旨在分析现象发生的原因与条件,揭示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即揭示隐在现象背后的客观规律,简言之,它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不直接指导实践。典型的实证——实验科学是自然科学。随着自然科学地位的不断升高,人们试图按其模式构建人文科学。这其中,率先起步的是教育学。但是,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其任务在于认识世界,而教育是人所参与的有价值的活动,这就意谓着教育学不仅要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尤其需要回答“应当是什么”、“应该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由于科学的任务是认识世界,所以把回答“是什么”问题的教育学称为“科学”的教育学、或教育科学或“理论教育学”,而把回答“应当是什么”、“应该做什么”、“怎样做”问题的教育学称为“实践教育学”,这就形成了教育理论的二重区分。
但是,在很长时期里,由于教育理论在指导实践上留下了空白,人们对教育理论的性质一直存在争论。经典性的论争主要由英、美两国的分析教育学家发起的,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奥康纳( D.J.O Connor )和赫斯特(P.H.Hirst)的观点, 他们讨论的焦点在于教育学是科学理论还是实践理论。奥康纳认为,自然科学提供了理论的范式,他把这种范式界定为“一组逻辑地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explain)它们的题材(subject matter)。 这些假设的另外两个职能为描述(describe)和预测(predict)。 (注:O Connor,D.J.,An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econd impression,1985,转引自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 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67页。)他持坚定的实证主义态度, 认为真正的科学理论必须满足解释、描述和预测三个条件,而迄今为止的教育理论大都由三个部分组成:形而上学的部分、价值判断的部分以及经验性的部分。这三者当中,前两者都不符合“科学理论”的标准,而经验部分中又包括了心理学和社会学知识在教育情景中的运用。所以,他指出,“只有在我们把心理学或社会学上充分确立了的实验发现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地方,才有根据称得上理论”。(注:O Connor,D.J.,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econd impression,1985,转引自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484页。)对奥康纳的观点。赫斯特进行了尖锐的反驳,他指出, 奥康纳把“理论”理解为“科学理论”,忽视了非科学性因素的重要性,完全误解了教育理论的性质。赫斯特认为,教育是一种以理论为基础的实践性活动,“理论”必须能提供基本的实践原则,所以说,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理论,是“为决定某种活动而组织的知识”。(注:P.H.Hirst,Educational Theory in J.W.Tibble (ed.),The Study ofEducation.1996,P.40)由此可见,他们分歧的焦点在于对“理论” 一语的理解,它除了对教育事实作出解释外,是否还包括价值判断等内容。
其实,关于教育理论性质的观点还远不止于此。英国教育学者卡尔(W.Carr)通过对教育理论取向的分析,揭示了这些理论取向所内含的实践观和理论——实践观。卡尔把教育理论分为四种取向:常识(common sense)取向、应用科学(appliedscience )取向、 实践的(practical)取向、批判的(critical)取向。卡尔认为, 关于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不能脱离于怎样理解理论的问题。
常识取向的持有者认为,教育理论的任务在于识别、整理和检验体观了教育者观点和信念的“实践原则”。由此得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理论揭示和阐明蕴含在“好的实践”中的观念、原则和技能并以此为依据来认识实践和修正实践行为中的不足。
应用科学取向的持有者认为,教育理论是“应用科学”的一种形式,它把经过经验论证的法则作为解决教育问题和指导教育实践的依据。这种取向内含的理论——实践观是:通过科学理论知识取代实践常识来联系实践。
实践取向的持有者认为,教育理论旨在培养实践智慧,它能提供的只是一种总是不确定的和不完全的知识,但这种知识仍然能够提供一种根据,藉此对某些特殊实践情境下应该做什么事情作出明智而谨慎的判断。
批判取向的持有者认为,教育理论的主要任务是考察教育实践中各种无可非议的信念、不证自明的命题,以及实践者的常识性的理解,旨在增强实践者的理性自主。它所反映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理论与实践是相互构成的,并且是辩证相关的。这种转化不是从理论到实践或者从实践到理论,而是从不合理性到合理性,从无知和习惯到理解和反省的转化。(注:Carr,W.,Theories of Theory and Practice,Journal ofPhilosophy of Education,Vol.20,No.2,1986.)
当代,随着元教育学研究的悄然兴起,学术界对教育理论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这其中的杰出代表当属德国教育学者布雷岑卡( W.Brezinka),他考察了欧洲教育学史的发展,独辟蹊径, 从元研究的角度,提出了解决教育学理论性质问题的思路。他指出,一些教育学者在教育理论是哲学、是科学、还是实践理论的问题上争论的原因在于,人们企图在同一个命题体系中将实践理论的规范性任务与科学理论的描述性任务结合起来。其实,这个大杂烩式的理论构成,既达不到对一门科学提出的方法论层面上的要求,又对教育(实际)工作者不适用,而期望对其有用的,正是他们对实践教育理论所期待的。布雷岑卡认为,在认识论上产生毫无结果的争论的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误解。事实上,“存在数种建构教育理论的可能性,而且各种教育理论并非必然是相互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注: W.Brezinka, Philosophy
ofEducational Knowledge,1992, P35,布雷岑卡著、李其龙译:《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分析、批判、 建议》, 《华东大学报(教科版)》1995年第4期。)我们既需要一种关于教育的经验科学, 同样迫切需要有各种为教育工作者服务的实践教育理论。这两种理论不能互相代替,况且,科学理论也不可能达到实践理论必须达到的目的。正是基于上述认识,布雷岑卡建议把教育理论分为三类:教育的科学理论(教育科学)、教育的哲学理论(教育哲学)、教育的实践理论(实践教育学)。(注:W.Brezinka,Philosophy of Educational Knowledge,1992,P35,布雷岑卡著、李其龙译:《教育学知识的哲学——分析、批判、建议》,《华东大学报(教科版)》1995年第4期。)
在布雷岑卡看来,教育科学主要研究教育事实,揭示教育规律,采用描述性命题,回答教育“是什么”的问题。其任务是获得关于教育行为方面的科学认识。与以往的教育学者所不同的是,他认为教育科学并不是一种只描述事实的科学,而是一种分析目的——原因的科学;教育哲学主要从哲学观点出发,回答在制订教育计划和采取教育行动时出现的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即在广义上采用评价性命题,回答对教育“应当怎样评价”、“教育“应当是什么”问题,在狭义上采用规范性命题,回答教育“应当做什么——怎样做”问题;实践教育学没有科学目的,而只有实践目的,它的创立是为了用实践知识武装教育工作者,以便指导他们进行目的合理的教育活动。其任务之一是对教育行为和建立教育机构提出实践观点、规范、建议或指示,它采用规范命题与描述性命题混合体系,它把教育义务告诉给生活在某一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的各种教育者群体,也把履行这种义务的手段告诉给他们,并根据一定的意识形态和道德,激励他们的教育行为。
鉴于布雷岑卡未把教育理论中的规范成分与价值成分、科学成分与技术成分区别开来。陈桂生教授提出了关于教育理论成分四分法的构想,即教育科学理论、教育技术理论、教育价值理论、教育规范理论。通过这种划分,使我们更加明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这四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表述如下:
“教育科学”产生于教育技艺、经验,并将随着教育技术的发展而演进;它经过教育价值评价与选择才能对实践发生效用。
“教育价值理论”基于关于教育“是什么”的事实判断(教育科学研究成果)和一定社会——文化情境的价值观念,对已经存在的教育事实,作出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教育价值观念转化为教育规范才能在人们的行为中发生效用。
“教育规范理论”根据教育价值观念和一定教育情境对教育技术作出评价与选择,把技术知识转化成特殊情境中可用的知识,据以确立教育行为规范;缺乏技术基础的规范不具有科学性,很可能同教育规律相悖。在名副其实的教育技术理论形成以前,可借助于包含一定技术、技艺成分的经验。
“教育技术理论”是根据教育科学研究成果构建的;教育技术理论的成果纳入规范,才能在具体实践中产生效用。由于迄今为止的教育科学研究进展不快,尚未出现真正的“教育技术理论”,故一般把“教育技术”研究成果归入“教育科学”;这也未尝不可,但科学理论和技术理论终究是有区别的,前者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后者回答“做什么——怎样做”的问题。(注:陈桂生《“四分法”:教育理论成分解析的新尝试》,《教育研究与实践》1995年第2期。)
通过上述关于教育理论性质的考察,对我们理解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是很有帮助的。不同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度是不一样的,揭示规律与指导实践虽然相关,但毕竟不是一回事。
二
另一方面,教育实践并非是一种完全无思维的或机械的方式完成的机器人式的行为,而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它是以实践者的理性反思的过程为前提的。教师是最初的教育专家,他们在经历了成功和失败后,总要试图理解为什么成功或失败。于是,在实践者的头脑中产生了想法或观念,它们越系统就越像“理论”,它们是伴随实践而产生的,相当于西方古代教育中的“艺术”,即一种做好事情的能力。亚里斯多德认为,艺术是活动能力的合理状态。迪尔凯姆把艺术定义为行动的方式系统,它们指向特定的目的,或产生于教育的传统经验,或产生于个体的个人经验。一个人只有在行动的过程中亲自思考它们,才可以获得之。
某人一旦拥有这些经验,无需理解其理论根据,也能做好事情。亚里斯多德早就指出,一些人不知道艺术的理论根据,但他们有经验,这些人比那些了解理论基础而无经验的人更会实践。有些教育者,很少有教育思想,却做得很成功;也有些教育理论家,他们拥有丰富的教育学思想,却仍然缺乏教育实践的能力。由此,施莱尔马赫认为,实践是“独立于理论”的。这些观点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站得住脚的。从历史的观点看,实践是先于理论的;即便在今天,也存在很多没有理论体系指导的实践。但是,这不等于说,有理论指导的实践不可能更好一些。
事情的另一面是,如果教育者没有成功地理解影响教育活动的条件,以及教育成功或失败的可能原因,那么,“教育艺术”未必能成功。因为,教育者在自我实践中形成的“艺术”也许在解决有限范围内的问题上是有效的,但是,即使这位教育者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始终是天才,他也不可能概括出一门理论学科所得出的知识体系。更何况每门学科所显示出的东西,不仅是通过积累并不断提炼而形成的思想体系,而且还是一套批判的工具和标准。
其实,父母和教师在教育实践中经常会遇到困难,正是这些实践中出现的困惑成了发展理论的动力。为了清楚问题何在,以及问题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我们需要借助于理论。这些理论可以给教育者的教育活动提供建议、指令或规范,也正因如此,它们被称为规范理论。尽管这种类型的教育理论在规范观点、逻辑的和系统的特征、经验内容、实践性和应用范围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它们都具有一个实践的目的。甚至赫尔巴特也把他的《普通教育学》构思成实践理论,即“为无经验的教育者提供一张地图”。一般而言,教育规范理论不仅提供有关教育目的和手段的信息,而且还激励教育者,使他追求善,并不断地完善自己。
还存在另外一种情况,即一位教师也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在他的实践中蕴含着理论,或者他不承认自己有任何理论意识,也拒绝使用理论。即便如此,他与理论的关系也许比他所认为的还要密切。这是因为,教育实践是一种理性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实践者必须先有一系列关于他要做什么,怎么做,以及预期目的等信念,这些信念或多或少应该是连贯的和系统的,可称之为理论图式。这些理论图式并非孤立获得的,而是由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传统所保存下来的,它已作为一种思维习惯积淀在实践者身上,告诉他该如何开展活动。
一位教师的工作与理论发生联系,还表现在制度化学校教育的许多方面,诸如教科书、仪器、校舍和学校的总体安排上。学校的整个环境是一个人为的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它是在过去和观在的理论观念的指导所形成的,所以,理论为“零”的实践在制度化教育中根本就不存在。
值得考虑的另一种现象是,教育实践者常常了解到理论家对他们所作所为的理论解释,与他们自己的解释迥然不同。这种矛盾的存在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当理论家以类似实践者的方式对实践进行解释时,理论会以一种相应的方式联系实践,如规范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不过,当理论家和实践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分析实践时,在实线者看来,理论与实践没有关系,如实证——实验科学关注的事物与人们的实践中关注的事物没有直接的联系。令人奇怪的是以下的误解:人们仅把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中存在的困难看作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一种差距,而不把它看作是关于对教育实践的理解的不同的理论之间的一种差距。从上文有关教育理论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不同性质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大不相同的。
三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理论与实践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鸿沟,所以,每种理论都有一个如何联系实际的问题。即使是实践理论也不等于实践本身,其实,愈是贴近实践的理论就愈不像理论了,甚至连规范理论都算不上。因为,理论总是具有普通性和抽象性的,过于结合具体实践的理论往往丧失了理论的上述特性。
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如何运用理论来指导实践。涉及教育理论指导教育实践的问题,不妨从教育实践所需要的指导谈起。其实,教育实践所需的指导与教育活动本身的类型及机制有关。不同类型和不同机制的教育实践,需要不同的理论来指导。
一般而言,实践者所期望的,可能是“师傅带徒弟”式的指导。通过“师傅”(有丰富经验的教师)的言传身教来规范“徒弟”(缺乏经验的教师)的行为。这样的指导与具体的情境密切联系,或许能收到显著的效果。但是,教育学则不能提供这种指导,因为所有的教育理论都不可能以具体情境中的少数实践者为指导对象,适合某种情境的指导势必脱离了另外情境的需要。假定有一种理论能提供这种狭隘的指导,那它是否还算得上理论,将令人怀疑,因为它已不具备理论的概括性和抽象性。
还存在一种“职业培训式”的指导,主要是使实践者熟悉并理解实践中的一套规范(从教育政策、教育目的规范到各种教育手段规范),然后懂得按规范进行操作。如我国以往编的“教育政策图解式”的教育学,或“工作手册式”的教育学。它实质上不过是教育实践规范的说明书。这种类型的理论,尽管有存在的必要,但它不是“实践教育学”,而是另外的学问,如“教育行政管理学”或有关教材教法的“教学法”等。而“实践教育学”应当而且可能对教育实践提供的指导,主要是提供一套有别于教育实践规范的规范理论,它诉诸实践者的理性,主要以价值原则和有关规范的知识来指导教育者的教育行为,旨在培养教育者的实践智慧。
当代的分析教育学哲学和教育行动研究,都把启发实践者的意识作为理论与实践联系的纽带。前者着眼于对实践者的启发,通过分析实践者所用的概念、术语、命题、隐喻,澄清隐在其中的教育价值观念,使实践者获得自我意识。后者诉诸以实践者为主体的“实践者自我批判团体”的自我反思,尤其注重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并且不止于启蒙,更注重实践的变革。这也反映了当代教育理论作用于实践的一种趋势。
实际上,由于教育者所处的教育情境的不同,他们对理论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所以,每一种教育理论都有存在的理由,重要的是,要让每一种理论各司其职。
以上所述,如属不谬,我们就可以推知,谴责教育理论脱离实际的说法,是基于对教育理论可能性和局限性的误解,基于对教育学家的义务与权利同教育者的义务与权利之间的混淆。其实,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理论工作者只负责探讨教育“是什么”的问题,并对回答问题作出暂时性的设想(假设),然后在它们是否与事实相一致的视角上,在它们同其它比较成熟的理论假设的关系的视角上进行检查。所以经验教育科学能够向教育实践工作者提供的帮助,主要在于提供关于教育因果关系和目的——手段关系的描述性教育知识。而要求其负责回答超越其可能性的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都是不恰当的。这只能表明提出此类要求的人不清楚教育科学理论与教育实践理论之间的逻辑鸿沟,混淆了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别,混淆了客观存在的事实(实然状态)、逻辑上可能发生的事实(盖然状态)、应有的事态(应然状态)与可行的抉择这样四个层面的区别。如上所述,即使是实践教育学,作为一种理论,它若保持某种普遍的指导意义,也不能不超脱具体教育情境中的实践,所以,它对具体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也是相当有限的。明乎此理,可以预防狭隘经验主义对教育理论建设的干扰。
当然,在我国,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误解还有文化层面的原因,有待于另做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