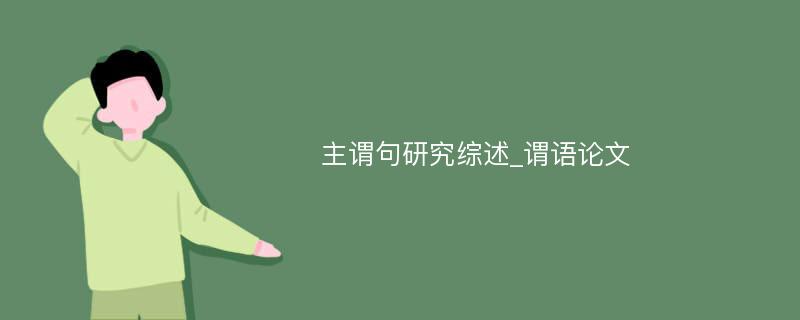
主谓谓语句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谓论文,谓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谓谓语句指由主谓词组充当谓语的句子,是汉语语法特点之一。本文试从纵横两方面对主谓谓语句研究情况作简要介绍。为行文方便,我们用S[,1]代表全句主语,S[,2]代表主谓词组中的主语,P[,1]代表全句谓语, P[,2]代表主谓词组中的谓语。
一
早在1898年,《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就注意到了这一句式:“句读内有同指一名以为主次,为宾次,或为偏次者,往往冠其名于句读之上,若起词然”。①但马氏并未进一步论述。1924年,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也论及主谓谓语句。他认为“王冕天性聪明”句中“王冕”和“天性”是“主位”与“同位”的关系,一起作句子的主语,同时又说:“或将‘天性聪明’认作形容子句作述语用”。所谓“形容子句作述语”,就是主谓词组作述语。黎氏的观点虽模棱两可,但却认定汉语中主谓谓语句这一特殊句式的存在。
四十年代,语法学家对主谓谓语句作了进一步的描述。
吕叔湘从表意功能角度来确定主谓谓语句。他认为主谓谓语句属于“表态句”和“叙事句”,即谓语本身是个表态句或叙事句。②王力不主张扩大主谓谓语句的范围。他认为“句子形式里的名词必须是人所领有的事物,而且以习惯所容许者为限”。③就汉语事实来看,这一范围显然过于狭窄。
这一时期,学术界未对这一句式命名,对其范围限制过死。
五十年代,学术界引起了关于主语宾语的讨论,由此,人们开始深入研究主谓谓语句。
1953年11月何霭人和易刚在《语文学习》上发表《是倒装句,还是句子形式作谓语》一文。何、易二人从结构出发,认为“写提纲我没功夫”等七个受事词在句首的句子是句子形式作谓语的主谓谓语句,而非“宾语倒装句”。他们打破了以意义为析句标准的成规,主张以结构作为分析句子的主要标准。
接着,张其春在《语文学习》1955年10月号上发表《主语和谓语的关系》一文。他根据S[,1]和S[,2]的关系把主谓谓语句系统地分为三类:分子关系、领属关系和游离成分。他认为“什么书他都看”的“什么书”是全句主语,“他”是“看”的主语,但却为全句主语另立一句目——标词。显然,对于这类句子的归属仍有分歧。值得一提的是,张其春把全句主语称为“大主语”,把主谓谓语的主语称作“小主语”,在后来的语法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
“主宾讨论”确定了结构和意义结合的析句原则,扩大了主谓谓语句的范围。
1961年出版的丁声树等著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正式提出了“主谓谓语句”这一术语,并依据意义把主谓谓语句分为三类,即:
1.主谓谓语中的主语和全句的主句有关系;
2.全句的主语在意义上是主谓谓语的受事;
3.主谓谓语当中常有“也”字、“都”字,其中的主语对谓语讲是受事。
这一主张已为学术界认同。但书中又提到:“有些句子可以解释成宾语倒装”,不能“顺装”的是主谓谓语句,能“顺装”的则属于“宾语倒装”。④把相同的句子割裂为两个不同的句式,这表明作者仍然依重于施受关系,对主谓谓语句的范围限制。
朱德熙的《语法讲义》(1982)中所定主谓谓语句的范围最为广泛。《讲义》把所谓的“宾语倒装”全部纳入主谓谓语句范畴,且把句首时间词和处所词都看作S[,1]。今天一般认为,时间词在句中的位置若可变动,那么它是状语,如“下午我们开会”句中的“下午”;当它是描写对象时,才看作主语,如“今天天气真好”句中的“今天”。朱德熙以话题作主语,过分扩大了汉语主语的范围。
目前对于主谓谓语句范围的认识基本趋于一致,分歧在于范围的大小。胡裕树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本)和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增订版)大致反映了这一分歧。
胡本的范围较窄,只有三类:
1.把主谓句中某一动词的宾语或宾语某一部分提到句首;
2.大主语与小主语有领属关系;
3.由全句修饰语减去介词“关于”、“对于”等构成。
胡本关于“1”类的表述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而把它看作“宾语倒装”句。
黄本的范围仅次于《语法讲义》,但它不包括句首时间词作状语的句子。
二
(一)主谓谓语句的范围
目前,学术界所认同的主谓谓语句有以下七类:
A:他身体健康。
B:他待人有礼貌。
C:什么书他都看过。
D:他一口水都不喝。
E:无线电他内行。
F:这枝钢笔,我很喜欢它。
G:他一只手牵着一个孩子。
A类(他身体健康)是典型的主谓谓语句。其特点是:S[,1]和S[,2]有领属关系。有关这类句子的争议在于它与句首带定语句子的区别。例如,是把“我肚子饿了”看作主谓谓语句呢,还是把它看作句首带定语的句子。
王力用联系上下文的办法判定A类为主谓谓语句。他说:“‘狗儿名利心重’,既可认‘狗儿’为主语,‘名利心重’为描写语,又可认‘狗儿名利心’为主语,‘重’为描写语。但是若连下文看起来,‘谁知狗儿名利心重,听到此源,心中便活动起来’,就明白‘狗儿’是主语,因为‘听’是‘狗儿’听,而‘名利心重’也就是描写语了”。⑤
苏联汉学家龙果夫用副词的位置来鉴定A类句,这一方法仍是目前用来判断主谓谓语句的重要手段。例如,如果在主谓之间加入副词,“他身体健康”可说成“他本来身体健康”或“他身体本来健康”,但“他的身体健康”就只能说成“他的身体本来健康”。⑥可见它们的结构是不同的。龙果夫的办法划清了主谓谓语句与句首带宾语句子的界限。
B类(他待人有礼貌)句子的特点是:S[,1]是S[,2]的施事。一般容易把它与主谓短语作主语的句子混淆。我们判别的办法是联系上下文。例如,“他待人有礼貌,心底善良”,显然是两个主谓词组同时说明主语“他”。若无上下文,按照逻辑语义也可判别。例如,“他一天到晚写信忙”。
C类(什么书他都看过)句子的特点是:S[,1]在逻辑语义关系上是P[,2]的受事。对于这类句子以前曾有过“宾语前置”的说法。理由是:1.“什么书”是及物动词“看”的受事或动作对象;2.有些句子在结构上能够倒装,例如,“这个问题我不懂~我不懂这个问题”。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提到了“宾踞句首”是这一主张的代表,这是以意义为析句准则,必然会遇到难于解决的问题。“这个道理你懂,我也懂,只有他还在那儿捉摸呢”一句,黎先生又承认是“反宾为主”,“这个道理”为全句主语。⑦看来,意义标准是无法贯彻到底的。陆俭明在《周遍性主语及其他》一文中对“宾语前置”观点作了详尽的探讨并得出结论:无论从语法形式或语法意义来讲,“什么也看不见”、“一句话都不说”都不是“前置宾语句”,而是周遍性主语句。⑧。那么,C类句子自然属于主谓谓语句。
主张把C类看作主谓谓语句的理由是:1.语法分析应以结构为主,意义为辅,采取结构和意义相结合的原则,不能单纯依据意义分析语法;2.某些句子“顺装”后意义发生变化,成为两个不同的句子。例如,“什么书他都看过”≠“他都看过什么书”,后句有疑问意味;3.从广泛意义上理解,S[,1]与P[,1]之间存在着陈述与被陈述关系。因此,C类是主谓谓语句。
D类(他一口水都不喝)句子的特点是:S[,2]在意念上是P[,2]的受事。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把它看作“宾语提前”。吕叔湘称它为“前置宾语句”。⑨胡附、文炼认为,S[,1]和S[,2]不处于同一平面,动词的受事处于S[,1]的位置,就属于另外一个层次,可看作全句主语;若动词受事处于S[,2]的位置,这只是同一平面上的位置变化,成分性质未变,是“前置宾语”。依此观点,胡本《现代汉语》把D类列入“变式句”范围。我们认为,既然承认C类句子是主谓谓语句,那么同样是宾语提前的D类也应属于此列。
目前,大多数语法著作都把D类看作主谓谓语句。理由是:1.“宾语前置”是一意义范畴的概念,不符合结构分析的原则;D类与宾语提前的倒装句不同,后者是一种修辞手段,是临时性的,而D类有大量的事实存在,且是一种固定的句式,因此S[,2]不应看作“前置宾语”;2.词序是汉语的重要语法手段之一。除修辞需要之外,汉语一般是主语在动词前,宾语在动词后,既已认识到汉语的主语有施事、受事、与事等多种类型,那么不妨把D类句中的S[,2]看作受事主语。因此,我们应该从结构分析出发,承认D类的主谓谓语句性质。
E类(无线电他内行)句子的特点是:S[,1]既非施事亦非受事,S[,1]前加介词“关于”、“对于”等成为全句修饰语,句意不变。持意义标准的人认为S[,1]和P[,1]无直接的陈述与被陈述的关系,把S[,1]看作省去介词的全句修饰语,整个句子是“状·主·谓”结构。我们认为,语法研究应以客观的语法事实为基础,不能凭主观臆测任意增删成分、改动原句。加介词构成的“状·主·谓”结构与E类句是两个不同类型的句子,不应混为一谈。目前,关于E类句子的分歧已经消除,语法学界一致认为,S[,1]是话题主语,P[,1]间接说明S[,1]。
F类(这枝钢笔,我很喜欢它)句子的特点是:S[,1]在意念上是P[,1]中的一个成分,与P[,1]中的某一词语形式构成复指和被复指关系。对于这类句子的看法有三种:
1.“外位成分”说。吕叔湘、朱德熙提出“外位语”和“本位语”两个术语,他们认为:“实际上指相同事物的两个词或短语拆开来放在两个地方,用一个做句子的成分,把另外一个放在句子的头上”。⑩这是依据两个词或词组的词汇意义指同一事物来确定句型,实质上是“宾语前置”论。
2.“提示成分”说。胡本《现代汉语》把S[,1]称作“提示成分”,没有把它与复指词看作同一成分,这是胡本较“外位成分”说合理之处。
3.“主谓谓语”说。持此说的人认为,E类句的意义和形式都与C类相同,只不过P[,2]后多一个代词,从词序和结构来看,它是主谓谓语句,P[,2]后的代词是P[,1]中的宾语。
G类(他一只手牵着一个孩子)句子吕叔湘认为能否归入主谓谓语句“不好决定”,因为其中的S[,2]可解释为施事,也可解释为工具。(11)事实上,汉语存在许多“工具主语”,且G类的许多特点与A类相近,例如,S[,1]和S[,2]有领属关系等,因此,它应属于主谓谓语句。
综上所述,主谓谓语句范围分歧的症结在于形式和意义的矛盾,具体说,就是“位置的先后(动词之前,动词之后)和施受关系的矛盾”。(12)单纯的意义标准已被证明无法贯彻到底。近年来,胡裕树、张斌等人主张区分语义、语用、语法三个平面,主张语法、语用、语义三者的结合。但是形式和意义如何结合,学术界仍缺乏统一标准。一般认为应以结构为主,辅之以意义,但主与辅的尺度至今仍未确定。缺乏一致的标准,主谓谓语句范围的分歧不可避免地存在着。
(二)主谓谓语句的表意功能
句子就谓语的性质和作用来说,一般分为叙述句、描写句和判断句三种,分别与动词性谓语句、形容词性谓语句、名词性谓语句大致对应。主谓谓语句究竟属于哪种类型,仍众说纷纭。
王力认为主谓谓语句是“描写句”,即P[,1]对S[,1]起描写作用。这种看法不够全面,例如,“一口水他都不喝”一句,“他都不喝”对“一口水”并不起描写作用。黎锦熙认为主谓谓语对主语来说是“形容性”的,这里的“形容性”实质上等于王力的“描写句”。
吕叔湘认为“主谓谓语句作用,说明性多于叙事性”。(13)“说明”是一个贴切的概念。汉语句子是话题主语句,主语与谓语之间的关系松散,以“话题—说明”来概括主谓语的关系是客观的。
李子云认为主谓谓语的作用是多样性的、综合性的,他根据P[,2]的性质,把作用概括为三类:说明—判断性,说明—描写性,说明—叙述性。(14)我们认为主谓谓语不可能具有叙述性,因为叙述是相对动词而言的。主谓谓语句中的P[,2]动词叙述的对象是S[,2],同S[,1]并未处于同一平面,因此,其叙述作用无法波及S[,1],S[,1]只与整个主谓短语发生关系。
(三)主谓谓语句的分类
大多数语法著作根据意义给主谓谓语句分类,主要有三种类型:
1.以主语的施受关系为标准。黄本《现代汉语》采用此标准把主谓谓语句分为三类:①S[,1]是受事,S[,2]是施事;②S[,1]是施事,S[,2]是受事;③S[,1]既非受事亦非施事。
2.以S[,1]与S[,2]的关系为标准。《语法讲义》是此类型的代表。
3.融合前两种标准。大多数语法著作均采用此方法,如《现代汉语语法讲话》。
这三种分类方法都是从意义出发,着眼于S[,1]和S[,2]的性质和关系,主观性较强。依据它们对主谓谓语句分类,很难产生一致看法。句型的确立主要依据结构,但迄今以结构为标准确定主谓谓语句下位句型的语法著作很少。李子云的《主谓谓语句》一文和北京语言学院句型研究小组的《现代汉语基本句型》根据P[,2]的性质对主谓谓语句进行结构分类。李子云把主谓谓语句分为四个类型:1.P[,2]为名词性词语,2.P[,2]为形容词性词语,3.P[,2]为动词性词语,4.P[,2]为主谓词组。(15)这种分类法虽然注意到了结构和系统性,但在很大程度上抹杀了主谓谓语句的语义特征。例如,“这个意思我懂”是意念上的“宾语前置”,“你才眼瞎呢!”的S[,1]与S[,2]具有领属关系,二者存在明显差异,但依结构分,它们是同一类型。怎样才能建立一个科学的、系统的主谓谓语句的下位句型体系?意义标准和结构标准应该怎样结合?这些问题有待学术界的进一步研究。
总之,对于主谓谓语句的研究,多年来焦点集中在其范围的确定上。范围的确定同主宾语的认识息息相关,迄今对于主宾语的看法仍未一致,因此关于主谓谓语句的范围问题也还存在争议。对于主谓谓语句的表意功能和结构两方面,语法学界尚缺乏广泛、全面的探讨。
注释:
①《马氏文通》39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
②《中国文法要略》56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
③《中国现代语法》49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④《现代汉语语法讲话》26页,商务印书馆,1980年。
⑤⑥《汉语语法纲要》117页,新知出版社,1957年。
⑦《变式句的图解》,载《语文学习》1953年3月。
⑧《周遍性主语及其它》,载《动词和句型》,语文出版社。
⑨《现代汉语八百词》28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⑩《语法修辞讲话》2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79年。
(11)(12)(13)《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546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
(14)(15)《主谓谓语句》,载《语言教学与研究》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