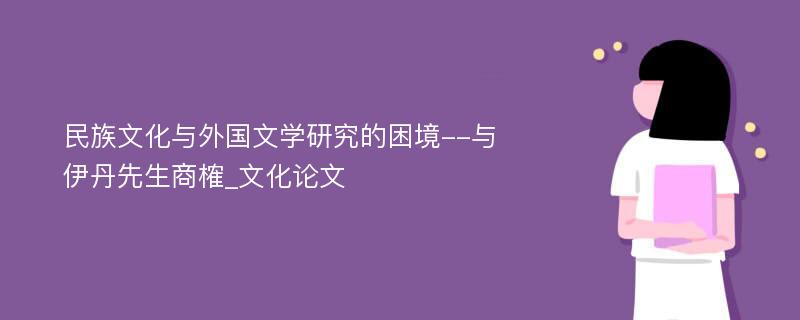
民族文化与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与易丹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文学论文,文化与论文,困境论文,民族论文,易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易丹先生的《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外国文学评论》94年2期,以下简称易文)引起了热烈的反响。黄宝生先生的《外国文学研究方法谈》(《外国文学评论》94年3期,以下简称黄文)虽然没有正面与易文交锋,但显然是有感而发,针对性是很明显的。而张弘先生的《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外国文学评论》94年4期,以下简称张文)则正面全方位地与易文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在看了两篇商榷的文章之后,笔者觉得易文中的观点尚有一些可以讨论。
一
易文首先对外国文学研究者工作的价值提出质疑,认为他们已经不再能够体会到自己工作的价值。他们“进行无休止的阅读、翻译和评价,或是为自己固定一个饭碗,或者玩智性和话语游戏收不了手,或是为职称评定的需要,或是其他。一本本书一篇篇文章从我们手中出来,又散发进我们共同的圈子或者圈子之外。这些书和文章在圈内或圈外发挥了什么样的学术甚至文化功效,我们似乎是不太清楚、或者至少是不关心的。”张文对此感到愤慨,认为“就是在眼下商品经济大潮冲击学术的形势下,一个严肃的有责任心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也不会不问自己研究工作的社会效益,把它当作一种纯知识纯学术的逍遣,更不会把它当作单纯糊口的饭碗或晋职的敲门砖。”张文的愤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愤慨之余,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也不得不承认易文说的也是事实。抱着崇高的目的,不计报酬待遇,一心埋头学问的人不是没有,但毕竟不多。大多数人在研究的同时,也必然关心自己的饭碗与职称。然而问题不在于外国文学研究者是不是关心“饭碗与职称”,而在于这种关心应不应该。我以为,这种关心是应该的。至少在现阶段,社会还未发展到人们不关心个人利益的阶段。每个人在为社会做贡献的同时为自己谋利益,完全是正常现象。文人们写书写文章,自然有保饭碗、评职称的动机,但这也并不防碍他们为社会做贡献。
不过,易文的质疑更多地是表示了一种困惑,一种对人文知识分子劳动成果的价值的困惑。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问题,它不仅关系到社会对人文科学的评价,也关系到人文知识分子对自身的评价,必须从理论上辨析清楚。
我以为,这种困惑的产生,除了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尺度过多地摆向实利方面等等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我们一直未能正视科学研究中的无效劳动并承认它的必要性。
对于科学研究来说,要在现有的知识中增加哪怕一点新的知识,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前进哪怕是极其微小的一步都是极其艰难的,需要大量的艰苦的工作,有的甚至要花费毕生的精力。常常有这样的情况,有的研究者做了无数次探索,只有一次产生了成果,相对于产生成果的这一次,其他的探索都是无效劳动。有的研究者终其一生,都未能产生新的成果。从这个角度看,他的一生都是无效劳动。另一方面,就研究者个人来说,研究能力并不是天生就具有的。仅仅为了胜任某一领域的研究,就需要付出大量的劳动,而这些劳动一般是不会产生成果的。相对而言,从事生产实践的人,在这方面花费的劳动就少得多。
与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科学相比,人文科学还面临一个社会接受的问题。与前两者相比,人文科学的功利作用显然要弱得多,无法产生前两者特别是自然科学那样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人文科学诉诸的是人类的精神与情感,这方面的衡量标准总是不确定的、可伸缩的。因此,有些人文科学的研究成果虽然的确为社会提供了新的东西,但是却不一定能为社会接受,或者虽然接受,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对待。而从功利的角度看,未被社会接受的成果所花费的劳动实际上也等于无效劳动。另外,人文科学的成果时效性不强,可以反复使用,不像生产实践和某些应用科学的成果具有一次性消费的特点。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社会对人文科学新成果需求的迫切性,这也影响到社会对它的接受。
由此可见,在科学研究特别是人文科学研究中存在着大量的无效劳动是必然的。自然,所谓无效劳动是相对于社会功利而言的。从科学研究本身来看,无效劳动又是有效的。因为任何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的产生都需要经过大量的可能是失败的探索,换句话说,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无效劳动。没有这些无效劳动,新成果就不会产生。因此,在科学研究中,无效劳动又是必需的。
十几年来,我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其中当然不可避免地也包含着一定的无效劳动,但取得的进展也是明显的。只要把70年代末的外国文学研究状况与现在的状况加以对比,任何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因自己的某些文章、书籍没有产生影响而感到困惑,再没有必要因此对自己工作的价值产生怀疑。
二
易文的另一个重要命题,是外国文学研究者等于杰出的“殖民文学”的推销者,或者说,是“殖民文学”在中国的总代理。其理论背景是后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是美籍阿拉伯学者E·赛义德在《东方主义》一书中提出来的。对任何一种事物,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从后殖民主义的角度看,一切外来的强势文化都可以称为殖民文化,但从思想史和文化交流的角度考察,不同文化的互相吸收、利用则是十分正常的,这里就不是一个殖民与被殖民的问题。如果,一味只从后殖民主义出发而不是全面地探讨问题,就会犯绝对化的错误。
在思想文化方面,任何国家、民族都无法“自力更生”,互相学习、借鉴、利用是常有的事。如在本世纪上半叶,英美思想界基本上是受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德两国思想的影响,尽管在19世纪末,美国在经济上就已跃居世界首位。既然西方国家之间思想文化可以互相吸收利用,我们为什么不能吸收利用西方的思想文化呢?
易文认为,“‘殖民’所指涉的意义从来就是同一个强大文明对一个相对虚弱文明的征服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研究‘汉学’或者‘中国文学’的外国人不会被认为是‘殖民文化’的传播者、在外国从事佛教传播的华人不会被认为是在进行文化侵略的根本原因。前者对于外域文化的研究具有主体性,而后者在探讨和接受外域文化时,则有相当的被动性和自动性。”张文曾对易文的这一观点进行反驳。张文认为,首先,对外来话语结构的接受和应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上,都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照搬,必然要渗进接受者主体的因素。其次,话语结构永远无法和话语操作割裂开来,话语结构只能存在于话语行为中,并只能在话语行为中发挥作用。张文谈的虽是话语结构,但也适用于文化交流。这里关键是接受者的主体性与主动性的问题。易文其实也看到了这一点,只是它把主动性与强势文明联在一起,把被动性与自动性与弱势文明联在一起。然而,弱势文明并不一定必然被动地接受强势文明,它也可以在保持自己的主体性的前提下采取主动性,根据自己的情况,按照自己的需要,主动地选择强势文明中于己有用的东西,加以吸收、消化、改造、发展,成为自己文化的组成部分。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有。自然,在两种文明的交流中,弱势文明接受的要多一些,但这并不构成本质性的区别,只要弱势文明吸收的是于己有用的东西,并且在这种吸收中没有丧失自身,这种吸收就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至少,是利大于弊,笼统地说成是“被殖民”是不恰当的。
弱势文化吸收强势文化中于已有用的东西,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须的。文化不像一个个岛屿那样,相互之间是封闭、隔离的。各民族文化中,既有本民族独特的东西,也有全人类共通的东西,因为各民族毕竟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面临着同一个宇宙,具有相同的生理结构与欲求,有着许多同样的问题与烦恼。而这民族文化中共同的东西,具体到某一因素,不一定在各民族文化中同时出现,总有先后迟早。但相对而言,强势文化中要出现得先些、早些。那么,后出现这一因素的民族从先出现这一因素的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这一因素,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我们既然能够毫不踌躇地接受万有引力定律和相对论,不把它看成是被殖民,那么,对上述文化接受现象也理应不感诧异。
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从游牧社会到农业社会,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各个民族社会的发展有较大的一致性,但发展的速度却不一样。有的民族进入了信息社会,有的还停留在工业社会,有的甚至还处在农业社会。而不同的发展阶段必然要产生不同的文化现象。因此,正在向高一级的发展阶段迈进的民族向已处于高一级发展阶段的民族的文化吸取某些自己到了这一阶段也必然具有的因素,以避免走弯路,也是完全应该的。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殖民的一面,也要看到不同的文化之间正常交流的一面,看到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学习、吸收强势文化于己有用的东西的必要性。看不到前一方面,甚至把对强势文化的盲目崇拜、不加分析地照搬也说成是正常交流,是不对的;看不到第二个方面,把对强势文化的任何接受都说成是“被殖民”,同样也是不对的。自然,要准确地把两者区别开来并不容易,但这正是包括外国文学研究者在内的外国文化研究者的任务之一。这种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由此可见,易文把西方文化统称为“殖民文化”,把介绍与传播西方文化的人都称为“殖民文化”的推销员,把外国文学研究称为“殖民文学”,是有失偏颇的,而且也不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这样至少会产生两个不良后果。首先,它将模糊正常的文化交流和文化殖民的区别。其次,它也容易导致一种盲目排外的情绪,导致对西方文化的全面拒绝,这是不利于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的,更不利于外国文学研究的繁荣与发展。
三
易文反复强调,它超脱具体的话语,“站在一个相对形而上的视点”审视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其目的并不是要“雪上加霜地对它进行非难”,而是要把“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推到一个极端”,以便引起国人的注意,建立一个“在有外国的参照系的基础之上建立的以我国文化为基本出发点的话语体系。它将以‘我们的’来取代‘他们的’,它将使我们超越目前这种只有说话没有对话的‘殖民文学’的状态,而真正进入平等对话的境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方法论,建立和我们的文化相吻合的话语”。我们相信易文的真诚,而且易文的目的也是高尚的,但这里仍然存在两个问题。
首先,是否存在一个纯属中国的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在这一点上,黄文的观点值得重视。黄宝生先生认为“不存在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各自为政’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所谓中国和外国的文学研究方法也只是表现形态不同,本质仍然是相通的。”理想的研究境界是“打通古今中外人文学科”,“站在更高层次上认识古今中外人类共同的思维规律”。笔者以为,也不存在纯属中国的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话语体系。因为方法和话语只是一种工具,既能为本民族使用,也能为别民族使用。实际上,任何有价值的方法和话语,只要一经形成,就不可能为某一民族所独享,必然越过国界,为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吸收利用。比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说,它产生于奥地利,接着影响欧洲大陆,然后在美国找到最大的市场,然后又传播到东方各国,为许多民族的文化所吸收,早已成为一种具有国际性的研究方法。
易文强调建立自己民族的方法论和话语体系,是因为它认为方法论与话语体系决定了使用者的文化立场。文章写道:“当代哲学已经证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方法就是本质;在一般的学术语境中,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学术结论。”接着文章以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为例进一步论证道:“我们的研究对象是外国文学,我们使用的方法是外国的方法,我们得出的结论已经预先设定,我们的立场因此也不会是中国的而只能是外国的。”这里的关键仍是方法。因为预先设定的结论是由所使用的方法决定的,而研究对象是什么在易文的推论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因此,这里实际上是等于说,运用了外国的方法,就站在了外国的立场。
然而,易文的观点只有部分的正确性。所谓“在一般的学术语境里,用什么样的话语体系就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学术结论”这种说法,只有在把“什么样的学术结论”理解为“什么类型的学术结论”的前提下才是正确的。用弗莱的神话模式来解读乔依斯的《尤利西斯》,我们固然难以得出一个关于1904年6月16日都柏林的阶级关系与斗争的结论,但却完全可以得出一个与西方的神话-原型批评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结论。也就是说,我们运用西方的方法,完全可以得出与西方不同的结论。而这正是易文所忽略了的。它没有看到文化对方法的运用的巨大的制约作用,没有看到结论的得出归根结底取决于研究者所具有的文化体系,而不取决于他所运用的方法与话语。
再退一步说,即使运用西方的方法,提出了与西方相同的结论,是否就意味着研究者丧失了民族的立场呢?恐怕也不能一概而论。这里的关键是要看这结论是否与民族文化有着内在的一致。
这就牵涉到第二个问题:如何理解民族文化。民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从纵向看,它可以分为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从横向看,可分为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传统文化按理说应是民族文化,可是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内容正是我们要抛弃的,如女人的小脚、专制思想、门第观念等。我们无法用传统文化的模式来规范今天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外来文化本来是外在的东西,但有些外来文化已在民族文化中扎根,与民族文化融为一体,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国历史上,外来文化有两次大的入侵,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入侵,一次是鸦片战争之后西方文明的入侵。如果以中原为中国的核心,那么在先秦之前,还有南方文化对中原文化的入侵。而前两次入侵的外来文化,现在已成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区分也是相对的,它并不必然隔绝于民族文化之外。易文概叹“我们的整个新知识系统,我们的整个新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对西方传来的样品的仿制的基础之上”,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有些就是直接从国外引进的,比如电影、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然而现在谁也不能否认它们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也无法以本土文化来规范民族文化。“来源”和“产地”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民族文化不是一个抽象的一成不变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有机的生命体,它本身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那么,民族文化变化发展的基础是什么?只能是民族的现实生活。现实生活发展了,民族文化也必然跟着发展;现实生活发生了变化,民族文化也必然跟着发生变化。五四时期,由于当时的国情,我们不能接受西方现代派文学和批评。但到了80年代,我国已经进入现代化建设时期,救亡的需要不复存在,文化大革命的经历却记忆犹新,人们感到了社会的复杂、人性的扭曲。这一切形成了适合西方现代派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于是西方现代派便在我国迅速地传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引发了我国的新时期文学运动。由此可见,决定民族文化的基础是民族的现实生活,因此,衡量民族文化的标准也只能是民族的现实生活。因此,任何文化因素,只要符合民族现实生活的需要,与民族的现实生活合拍,能为民族的现实生活所接受,就是民族的,而不管它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
由此可见,易文主张以“我们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来取代“他们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以摆脱“殖民文学”的状态的观点是不正确的。正如前面所分析的,是否“殖民文学”的关键并不取决于谁的话语体系与方法论,也不取决于某些结论是否与西方一致。我们可以有“我们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但它们只是在“我们的”民族文化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我们独有的”。我们也没有必要非拥有一套独有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不可。我们形成“我们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同时把它们推向世界,同时,我们也要大量地吸收“他们的”话语体系与方法论,吸收世界各民族文化于我们有用的东西,这样,才能繁荣与发展“我们的”话语体系和方法论,繁荣和发展“我们的”民族文化。
《复印报刊资料》责任编辑注:易丹先生的文章《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见本刊199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