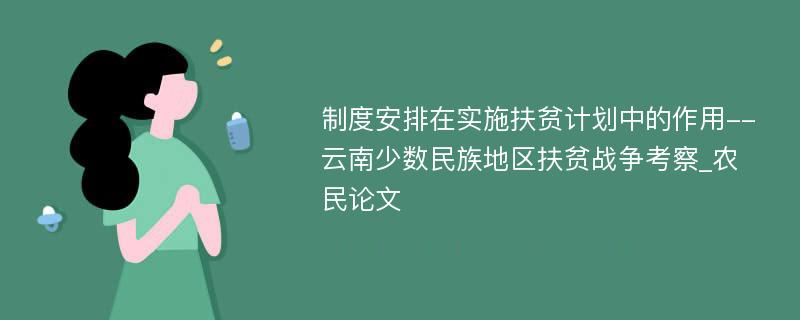
制度安排在扶贫计划实施中的作用——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攻坚战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攻坚战论文,云南论文,排在论文,少数民族地区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扶贫行动不仅由资金和物资援助所组成,而且还包括文教、卫生和科技等诸方面的综合投入,这在我国决策层、实际操作部门和学者之间均已达成共识。然而欲使援助有效地传递到扶贫计划的目标人群,还需要辅之以适当的制度安排,即进行制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一点,国际社会已有广泛讨论,但在我国扶贫领域尚未引起充分的关注。依笔者之见,正是这种疏忽阻碍着目前扶贫效率的改善,故而拟通过对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扶贫攻坚战的个案研究,概述信贷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制度安排,分析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探寻进行制度创新从而改善扶贫手段的途径。
一、云南的贫困人口
任何扶贫计划的制订,都必须以明了贫困产生的原因、贫困人口的分布及特征为前提。随着体制转型过程带来的社会变动,目前我国既出现了与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制度、就业和工资制度改革相关联的城市贫困,又产生了以财产分配不均为基础的阶层贫困,还不乏由市场竞争导致的失败者的贫困,同时依然存在着因生态环境恶劣造成的地区性贫困。迄今为止的扶贫计划尚未包容除地区性贫困之外的其它类型,以下讨论因而亦局限在计划所指的目标人群。
提起云南的贫困,人们大概就会想到一些学者所刻画的“富饶的贫困”(王小强、白南风,1987)。其实,那多半是10多年前占全省面积不到6%的山间盆地的情景。在云南省39.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94 %的地域由绵延起伏的大山和高原组成,这里的扶贫工程因资源贫瘠、交通不便和贫困人群居住环境封闭而异常艰巨。据统计,云南省的人口尚不足全国的3.3%,它的农村贫困人口却几乎占全国的10%,达700万人之多(以年人均纯收入不足300元为贫困标准)。这其中,70 %以上为少数民族同胞(云南省以工代赈办公室,1995)。“七五”以来,中央和云南省政府以每年对每个贫困县直接投入1000多万元扶贫资金和实物的援助密度,支持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的改善以及食品短缺问题的缓解,已使500万人迈出了贫困门槛(和志强,1994)。现在的700万贫困人口中间有一部分当属社会救济范围,例如五保户、身体严重残疾或因遗传病、地方病而智力不健全的人。据南涧、洱源和武定县计委的同志估计,这些失去正常劳动能力的人群大约占现有贫困人口总数的1/4。扶贫计划实质上是以具备正常劳动能力的人口为目标人群的, 他们正如“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所描述的那样,绝大部分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和高寒山区。曾有国际友人对这几个关于山区的词汇所表达的内涵发生疑问,以为它们指的是相同的意思,即高山和深谷。云南的例子恰好能够对此给予直观的注解。笔者所见到的深山区不仅交通不便,往往还缺少农业生产所必不可少的水源;石山区、尤其是岩溶地区土壤瘠薄,农民只能利用石头缝隙里的每一抔抔黄土种庄稼;高寒山区的耕地不仅坡度陡峭、水土流失严重,而且因热量不足复种指数低而产出微少。虽然每一类山区都可能同时具备另一类山区的某些特点,而且也许不只缺少一种生产条件,但“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的类别概念,至少是突出强调了它们各自与食品生产相关联的主要缺陷。山区贫困人口为获得食品保障所要解决的关键性难题依其居住的区位有别而大不相同,因而必须针对不同的人群制订有区别的扶贫计划。
二、发展计划与扶贫项目
如前所述,我国迄今为止的反贫困政策,基本上是围绕着缓解和消除地区性的乡会贫困这一目标设计的,公共援助的传递机制因而也一直采取区域瞄准方式(朱玲,1993)。这种方式的特点在于操作简便,确定重点扶持的贫困县以后,便可将财力物力集中投向列入名单的县域。然而即使不考虑城市和非贫困乡村地区,贫困县里也有非贫困、一般贫困和最贫困人群之分,一些设在贫困县的扶贫项目,也许对地区发展有利,却未必能使贫困人群直接受益。因此,区域瞄准机制还需要个人瞄准方式来补充,以便把援助便捷、及时、准确地传递到贫困人群手中,有效地防止传递过程中的“渗漏”。其实,这也是国际发展援助组织和众多发展中国家扶贫计划决策集团共同关心的一个主题。可是,“扶贫”这一概念在我国往往包含两个含义:其一,扶持贫困地区改变落后面貌;其二,帮助贫困人口获得食品保障,即解决温饱问题。根据国际社会通行的理解,前者显然属于地区发展的范畴,后者表达的才是扶贫概念的本义。目前的概念混淆不仅在理论上引起“富民”还是“富县”孰先孰后之争,而且在国际交流中给中国官员与外国同行的对话造成困难,因为中国人常常把发展计划当作扶贫项目提请资助,使评审专家困惑莫名。更重要的是,在实践中这种混淆还导致扶贫项目偏离预定的目标人群,也就是说使项目资源流向非贫困人群。发展项目虽然有助于减少贫困,但并不一定确保以扶贫为目的的资源直接用于贫困人群。可以肯定,发展计划与扶贫项目二者缺一不可。其根本原因在于,为了缩小地区差别以维护国家的统一,中央政府仍将运用区域瞄准机制向贫困县提供援助,那就不可能将非贫困者排除在受益范围之外。为了满足低收入人群的基本需求以保持社会稳定,那就有必要采取个人瞄准机制,救援最贫穷的人群。有鉴于此,笔者留意在田野调研中分别从地区发展和缓解贫困的角度考察云南扶贫项目,以下也将基于上述概念区分对观察所得展开讨论。
1.以工代赈项目
在诸多扶贫手段中,以工代赈是最为巧妙地将地区发展和扶贫目标相结合的一个。项目的实施既为贫困人口直接提供短期就业机会从而增加他们的收入,又有效地改善基础设施,为当地的经济增长创造必要的条件。90年代以来,云南平均每个贫困县每年获得的以工代赈投资,至少占其全部扶贫资源的50%以上。现在的以工代赈项目,除了仍然包括原有的乡村道路和人畜饮水工程以外,还拓展到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造林、人工草场培育、电话线路架设、农村卫生站房屋更新、乡村小学危房改造、供销社网点水毁修复等等领域,成为各贫困县影响最大的公共工程。只是项目所具有的“赈济”色彩越来越淡薄,资源被用作纯基本建设投资的倾向则越来越鲜明,因为某些财政困难的贫困县配套资金不足,便挪用应作为劳动报酬发给农民的代赈券购买工程材料。据估计,1994年工程参加者便因此而减少代赈报酬3000万元左右(云南省以工代赈办公室,1995)。对于贫困人群来说,倘若在参与以工代赈工程期间牺牲了其它增加收入的机会,那么以无酬方式参与工程反倒使他们在此期间更加贫困。
不过,在以工代赈形式下进行的农田基本建设和人畜饮水工程,虽然没有直接赋予贫困人群现金报酬,却增加了他们的家庭资产,并因而为之带来稳定的收入增长。这一类项目在以南涧彝族自治县为代表的亚热带山区效益最为显著。南涧县地处横断山脉纵谷区,在境内海拔1000—2000米的地带,种植业生产所需要的光、热、水、土等自然因素样样俱全。问题首先是坡地不易涵水、蓄肥、保土;其次在于此地不具备灌溉条件,而全年降雨量虽然平均达到700多毫米,却季节分布不均, 70%以上的降雨集中在7—10月,冬春和初夏的干旱不仅影响玉米、 烤烟的栽种和出苗,而且造成严重的人畜饮水困难。这几个难题通过以工代赈项目的实施一并获得解决:第一,当地项目组织机构(县农业建设办公室)将雷管、炸药无偿发给项目区的农户,在统一规划下由农民将坡地改为梯田(在那些土层极薄的高寒山区,基本农田建设项目多半不经济。在那里,若将25度以上的坡地退耕还林,村民们几乎就都沦为无地农民;而实行坡改梯工程,则成本巨大却效益不高,还有可能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所以此类地域贫困人群的出路在于劳动力转移)。第二,推广良种和适用技术(例如农业部倡导的杂交玉米地膜栽培技术),调整作物结构,进行合理轮作。第三,组织农民修建小水窖,每个小水窖补贴价值500元左右的钢筋水泥(农民自筹1500元)。 利用雨季一个小水窖可储水20立方米,浇地3—5亩(每棵玉米或烟苗用水1公斤)。 每个农户一般至少修建两个水窖,一为饮用,一为浇地。
这样将山区基本农田建设、微型水利工程建设与农业科技推广措施相结合,既解决了人畜饮水困难,又把旱作节水方式引入了深山区的种植业,使粮食亩产平均提高100多公斤。这其中, 小水窖工程可谓扶贫行动中的一种技术创新。首先,它在技术设计上比作者在其它省(区)所看到的更为合理:用钢筋混凝土灌注成椭圆柱形,水泥抹壁,上覆窖盖,结构坚固,使用安全,节约材料。其次,小水窖也许是云南山区效率最高的水利工程。南涧县一个包括1万亩旱地的项目区,投资88 万元于小水窖工程(不包括农户投资投劳)便解决了灌溉问题。倘若在同一项目区修建一个小型水库,至少需要上百万元。此外,还需要砌筑几十公里的引水渠。加之深山区地块零散,要将水流引到地里必得耗时费工建支渠。进一步讲,水库的管理与农户分别维护各自的小水窖相比,成本显然要高得多。再其次,云南73个贫困县里目前还有367万人和257万头大牲畜饮水困难。在高寒缺水山区,小水窖即使不一定成为显著的增产措施,至少也可以迅速消除当地人民的季节性缺水之苦。可是,小水窖正因其微小而且散播在千家万户成为农民的资产而难以列入正规水利基本建设投资计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因为如果仅仅依靠以工代赈项目投资,数万山区农户到本世纪末还依然得不到安全饮水。
还值得一提的是,以工代赈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项目的筹资方式与80年代的路桥工程相比更趋多样化。除了中央、省、州、县配套投资和农户集资投劳外,还使用了专项扶贫贴息贷款,由项目执行机构县农建办(农业建设办公室)承贷并负责偿还。贷款用于落实科技推广措施,即转贷给项目区农户购买地膜、良种和化肥等投入品。只要不遇灾害,绝大多数农户都能按期还贷。尤其是在那些适于种烤烟的地域,农户往往在改土造地、修建水窖之后,收获一季烤烟便可清偿债务(种植烤烟毛利润:1700—2000元/亩)。
以工代赈项目的实施方式,采用的是政府组织公共工程的常规手段,项目执行期间更多的是由公共部门与百姓打交道。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类似的项目相比,它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强政府传统的国度尤其显示出较高的组织效率。以此为前提,项目资源配置和使用亦显示出较为合理的成本—效益关系,微型水利项目的运作便是明证。
2.信贷扶贫
与公共工程相比,以信贷手段扶贫事情就复杂得多了,因为这不仅要借助于金融媒介操作,而且还关系到借款者的经营状况和信用意识等诸多因素。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银行和信用社都经历了因借款者拖欠而沉淀大量呆滞、呆帐贷款的教训,相当一部分金融组织至今仍然承受着不良资产的巨大压力。于是在承担扶贫信贷业务的过程中金融机构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既要把钱借给贫困人群,又要保证回收贷款,10多年来几经周折,目前似乎采取了一种两全其美的办法,那就是贷款给企事业机构,由它们承担扶贫任务。结果是农户被排除在直接贷款对象之外,具有借款资格者包容了贫困县绝大部分企业和职能部门(吴国栋,1994)。相对于农户信贷业务,金融机构贷款给企业和机构至少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县政府则既可能通过企业的发展增加财政收入,又可以帮助下属机构维持运转。这样看来可以皆大欢喜了。可是,此类制度安排带来的首要问题在于,企事业机构申请的项目多在贫困县内自然经济环境相对优越的地方实施,扶贫贷款因而基本上投到了路边、城边和工厂边这些“相对富裕点”,受益者并不一定是贫困户。如果考虑到借款者本身亦享受了贷款所包含的福利(贴息),得益于专项贷款者就包括承贷单位及其个人、参与项目的非贫困户和贫困户。
第二个问题在于,借款者资格的变化,表明关于贷款用途的种种规定弹性变大,由此而引发出县政府与金融机构(主要是县农行)日益尖锐的冲突。前者从增强地区经济实力、增加财政收入和解决农民温饱问题、降低贫困率的全局角度立项,后者以金融机构保障信贷资金安全、流动和赢利的眼光遴选。不少项目经银行评估最终被否决,这就引起县政府的强烈不满。加之如今借款必须办理抵押或担保手续,更使原本习惯于将银行视为财政部门钱柜的县乡领导们怨声载道。至于已通过银行批准的项目,大多数执行机构对专项贴息贷款到位迟缓、使用期限短亦颇有微词。论及扶贫信贷的使用效果,根据省扶贫办的统计,1986—94年期间全省累计发放扶贫贷款12.68亿元,到期贷款回收率将近60%, 而省农业发展银行的计算结果,则比这一数据低了十多个百分点。不过,无论采用那一家的信息,都可以确认一点,那就是扶贫贷款的回收问题不容乐观。
依笔者之见,尽管信贷扶贫项目也不乏成功的范例,其运行中一个关键性的弊病,就在于从贷款的分配、申请到发放的全过程都是政府、银行和企业的活动。贫困人群既不能参与决策,贫困户也没有资格直接申请贷款。现行的制度设计显然将贫困人群置于不可能主动利用正规金融市场的地位。贷款项目执行过程中,非贫困者与贫困人群一起受益;项目一旦结束,那些没有学会利用信贷服务独立从事投资决策的农民,将仍会是市场经济下需要救援的贫困人群。笔者在楚雄彝族自治州武定县高寒山区走访的特困户的农民几乎不发生借贷行为,因为无论是正规信贷机构还是其亲朋好友都清楚他们不具备偿还能力。其它贫困人群则主要依赖非正规信贷,因为信用社为确保贷款安全,一般要求以存单抵押或担保,贫困人群往往无所抵押,结交的穷朋友也无以担保,故而越是需要贷款的人越借不到钱。即使是在相对富裕的乡村,农户也很少利用正规信贷。例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景洪县嗄栋乡曼回索村,家家户户发展多种经营,或养猪种菜,或种西瓜栽橡胶,或开作坊,年人均纯收入已超过1000元,却无论是生产投资还是消费急用,都靠各自的社会关系网借贷,在信用社只存款不借钱。主要原因是农民认为信用社手续麻烦,借款一次既要抵押存单或找担保,又要提交申请找村长签字、到村委会盖章,还要到乡信用社跑几趟。用经济学术语来表述,那就是农民认为正规信贷交易成本太高。从嗄栋乡信用社营业人员那里笔者还了解到,1995年信用社存款余额630万元,贷款余额190万元,贷款对象以个体商业户为主。这意味着大多数非贫困户也未被纳入正规信贷服务体系。可见,少数民族地区乡村一般信贷服务与扶贫信贷操作一样,需要进行制度性改善。
3.减灾扶贫组织
可以肯定,从去年10月下旬到今年2 月武定和丽江地区的两次大地震,已使全国人民都意识到,云南的贫困往往还与频繁的自然灾害相联系。即使是非贫困户,一遇天灾便陷入贫困;而那些走出贫困的家庭,每逢灾害打击便重返贫困。除地震外,云南的山区屡屡遭受旱灾、风灾、冰雹、山洪和泥石流袭击,抗灾减灾行动与扶贫计划的实施因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工代赈显然是救灾行动中的传统手段,如今依然不失为援助灾民重建家园的有效措施。不过,政府的公共开支则是救灾行动的主要经费来源。这笔经费平均每人每年大约一元钱,远远不能满足救灾行动的需要。于是在80年代末期民政部门便拨款扶持农民成立互助储粮储金会(简称“双储会”),试图动员民间社会补充政府的公共行动,逢灾抗灾,无灾扶贫。这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制度创新。然而由于此类组织的外部环境及内部制度安排存在着种种不合理之处,它们中间的大多数都运行不力。以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源县为例,1987年全县12个乡(镇)都成立了双储会,如今只有两个非贫困乡(镇)的组织运转正常。
首先,所有的双储会都没有营业执照,不能象金融组织一样经营存贷业务。因此,甚至在定义自己的债权债务关系时都尽量避免“存款”、“贷款”和“利息”这些概念。为了体现与金融组织的差别,双储会将贷款利率压低到法定利率之下。为此,它们就不得不确定更低的储蓄利率,这就很难吸收高于其会员资格最低限的储蓄额。洱源玉湖镇鹅墩村成立双储会时,以农户为会员,按人头集股份,每股5元人民币或4公斤粮食,每户入股钱、粮总共大约20—30元,全村223 户人家聚集资本不足7000元。自粮食市场放开后,粮价上扬储粮不如卖粮合算,双储会的粮食均已出售,该组织变成了储金会。其帐目由乡民政员管理,储金以活期存款形式放在乡信用社,月息在3‰左右;贷款利率定为7.2‰。到如今,该组织的储金规模不曾扩大(如果考虑通货膨胀因素,它甚至还有些许缩小),抗灾扶贫的作用也就极为有限。到目前为止,借款户才有20多家,还不到全村总户数的10%。其次,存、贷利率之间的差额微小,不足以弥补储金会的日常运转费用,也难以支付管理人员的劳动报酬,自然削弱了他们拓展业务的积极性。再其次,双储会既缺乏储蓄动员机制,也不具备强有力的违约惩治手段。因此,不少呆滞贷款或其它风险导致它们中间大多数组织日渐萧条。尽管如此,它毕竟是贫困地区成长起来的新生事物,表明少数民族同胞可以组织起来利用金融工具解难济困。如果允许它有一定的浮动利率权限,并将其置于金融监管之下,目前的情形也许就会换一个天地。
三、结束语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我国扶贫计划实施中的制度安排大有值得改进之处。这不仅指政策法规的修订,而且还包括执行机构和组织的调整。改善的目标,应该是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保障扶贫计划设定的目标人群的权益,即尽可能地杜绝渗漏,使贫困人群直接受益。当前绝大多数国际发展组织都在从事“参与式”的扶贫项目试验。也就是说,广泛动员贫困人群主动参与设计和执行脱贫行动,信贷互助、生产或供销合作、妇女发展小组等等即是与此相联系的组织。目前,云南省境内就有多种多样的国际合作扶贫项目。但是有相当一部分援助组织因强调其非官方色彩而没有(或者不愿意)得到政府系统的密切配合,许多项目设计本应对国内的扶贫政策提供参考,却由于难以进入大众传媒而鲜为人知,例如自助性小额信贷项目、参与式村社综合发展项目,等等。所以,国内扶贫机构有必要帮助他们走出这一误区,因为国际经验必须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才具有生命力。
就目前正在实施的反贫困措施而言,区分地区发展计划与扶贫项目至关重要。前者的受益范围可以包括非贫困、一般贫困和最贫困人群等整个计划区的全部人口;后者选择的援助目标应局限于贫困人群。以工代赈项目因其公共工程性质不可能排除非贫困人群受益,以扶贫为宗旨的信贷项目却应当把贫困户纳入直接贷款范围。这并非意味着笔者反对以优惠贷款支持贫困地区的开发项目或工商企业,而只是强调,应从现有的优惠贷款中至少划分出一定的份额,用于直接扶助贫困户。在这一领域,其它发展中国家(例如孟加拉)的经验值得借鉴。为了解决既使贫困人群获得贷款,又能保证贷款安全的两难问题,类似自助性信贷小组的一些制度创新在许多国家应运而生。信贷小组活动于村社基层,交易成本低且包容了众多贫困户。小组内推行强制性储蓄并将此存入商业银行,同时以承担连带责任的方式申请贷款和还贷。关于农民信贷自助组织的利率如何确定的问题,一些乡村经济发展专家们曾建议,应由每个组织自己确定它和会员之间从事存、贷交易的价格。利率至少应该足以弥补资金的运转费用和管理支出,还必须包括风险准备金和利润成分。银行与这些组织之间的资金使用价格,应采用市场利率,足以使银行弥补自己的费用、风险并获得利润(Kropp and Marx,etc.1989)。 这样,就把正规信贷与非正规信贷联结起来,扩大了正规信贷服务的范围。尤为令人振奋的事实,是在严密的制度规范下,贫困人群不仅能够储蓄,而且可以在高于市场利率的条件下按时还贷,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否获得贷款,而补贴利率往往使非贫困人口率先得到好处,而且损害银行的健康运行(Zeller,Ahmed and Sharma,1995)。笔者注意到,此类信贷小组的正常运行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小组成员必须从事能够获得现金收入的经济活动。这在我国商品生产相对发达的地区还不难办到,而对于那些依赖生存经济的贫困小农,例如云南资源贫瘠的高山、石山区里的贫困人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加之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一方面,从国外引进的非正规信贷组织的运行方式必须有所修正,才有可能正常操作(杜晓山、孙若梅和徐鲜梅,1995);另一方面,如果将中国农民自己的创造辅之于成功的国际经验,非正规信贷组织也许在乡村金融领域将会产生更加积极的作用。
针对少数民族制订的扶贫计划,更需要配合适宜于不同民族特点的制度建设。例如信贷扶贫,就需要将贫困人群组织起来,由知识人群坚持不懈地帮助他们学习信贷知识和获得现金收入的生产技能,寻找适合于他们经营的生产领域进行投资。在文盲率较高的少数民族地区,信贷小组的培训不仅需要增加扫盲的内容,而且还应辅之以家政管理教育,不少已有的调研结果都已经提到,某些少数民族人群的文盲率至今高达70%左右,储蓄意识与合理消费习惯也尚未形成(中共云南省委农村政策研究室,1995)。这无疑显示出少数民族贫困人群脱贫的艰巨性,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拒绝陌生事物。本世纪初曾有法国传教士在文盲率极高的少数民族地区传教,竟然留下了西方宗教的种子。这说明只要具备足够的勇气、耐心和吃苦精神,尊重少数民族固有的传统,是能够使他们改变原有的观念、习俗和生活生产方式的。新中国成立40多年以来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足可以承担帮助贫困人群从事制度创新的角色。笔者相信,官方与非官方组织相配合、公共行动与个人积极性相补充,必将有益于集中和利用各方面资源,推进少数民族地区的扶贫事业。
(本报告主要基于1996年元月作者在云南省景洪、洱源、南涧和武定县的调研写成,调研中得到云南省计委以工代赈办公室、省民政厅和云南省委政研室的大力协助,大理白族自治州计委和民政局、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政研室、4 个调研县的有关部门和调研农户也曾给予积极合作;本文由李月琴进行计算机文字处理。谨在此一并致谢)
标签:农民论文; 扶贫贷款论文; 信贷业务论文; 项目贷款论文; 信贷规模论文; 扶贫论文; 云南发展论文; 贫困问题论文; 银行信贷论文; 三农论文; 经济论文; 时政论文; 以工代赈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