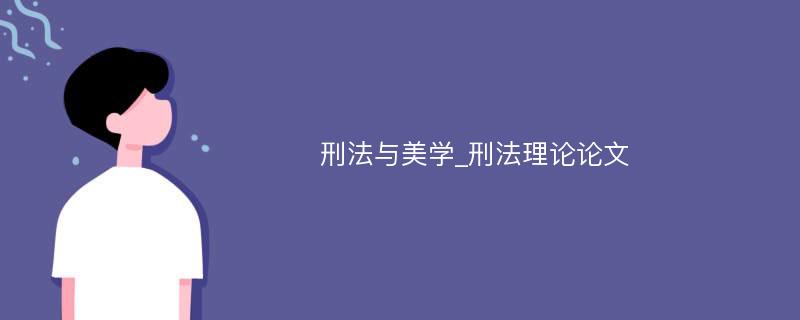
刑法与美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刑法论文,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F6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09)01-0096-05
当代科学的发展,常常使某一门学科有一种超越自己原有视野去拓宽研究领域的趋势。刑法学家高铭暄教授曾经指出,“要综合运用刑法学的理论和相关学科的知识来揭示刑事法治的内在客观规律”[1],陈兴良教授也谈道,在法学领域,达到一定的学术境界,应当是哲学、文学与法学——三学合一[2](P33)。美学,作为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法律学科关系密切。因为,“法律这样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所暗含的所谓无意识的‘隐秘秩序’(verborgene Ordnung),有时也必须通过美‘这扇清晨的大门’才能被人们所知觉和认识”[3](P56)。
一、审美之维是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根本上说,人类对世界的改造总是按照美的规律在进行,无论是在物质生产领域,还是在精神生产领域。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刑法不但包括其真、其善,还包含着美。
一方面,美的旨趣之一在于阐释矛盾和反题,作为价值冲突表现突出的刑法领域,与审美有着天然的亲近。德国法哲学家、刑法学家拉德布鲁赫尝言,法在根本上蕴藏着某种“戏剧化的冲突”(Der dzamatische Konflikt),内在地包含有一个多样态的反题,如事实和价值、实然和应然、实在法和自然法、正统法和革命法、自由和秩序、正义和公平、法和宽容之间的对立性[3](P57)。就刑法领域而言,作为最为复杂的社会现象之一的犯罪,通过犯罪人的“自由意志”表现为对他人人身、财产甚至生命的侵犯,对公共法秩序的破坏或曰个人反对国家的“孤立的斗争”。相应的,刑罚作为最严厉的法律制裁手段,通过国家的“强制意志”表现出对犯罪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的否定与剥夺。可以说,刑法总是与自由、生死等重大人生命题相关,关乎人“存在状态”的大悲大痛。作为法的最后一道防线,刑法始终围绕着罪与罚这个永恒但却沉重的主题,通过刑事立法、司法裁量和刑事执行等国家法的形象的交替上场,将法所蕴藏的“戏剧化的冲突”推向高潮,直至落幕。国家与个人、法意与人情、一般与特殊,罪孽与宽恕、残酷与仁慈、冤苦与正义……刑法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人性冲突与价值对立。这种冲突和对立之间的痛苦抉择和无穷张力本身就蕴涵着强烈的审美意蕴。
另一方面,善恶与美丑问题其实是相通的。陈兴良教授认为:“刑法学是以犯罪为研究对象的,犯罪是一种恶。因此,刑法学可以说是一门研究恶的学问。正因为刑法学研究恶,才要求我们的研究者有一种善的冲动。在刑法学研究中,通过观察与剖析恶,使我们更加向往与信仰善。”[4]更进一步来说,恶是丑表现的一个侧面。而丑通常是指非理性、非道德的感性存在的释放[5]。在罗丹眼中,所谓“丑”,是毁形的,不健康的,令人想起痛苦,是与正常、健康和力量的象征与条件相反的[6]。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负面的社会现象,犯罪既是一种恶,也是一种丑。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因此,套用上面诗意的表达范式,完全可以这样说:刑法学是一门研究恶和丑的学问。正因为刑法学研究恶和丑,才要求我们的研究者既要有一种善的冲动,还要有一种美的观照。在刑法学研究中,通过观察与剖析恶,使我们更加向往与信仰善;通过感知与发现丑,使我们更加追求和通向美。
二、人性问题是刑与美的契合点
人性是哲学的基础,也是一切人文社会科学包括法学的理论根基。美学之父鲍姆加通指出,美的领域包括感性、情感和人性。而“刑法是以规制人的行为作为其内容的,任何一种刑法规范,只有建立在对人性的科学假设的基础之上,其存在与适用才具有本质上的合理性。因此,刑法本原性思考,必然将理论的触须伸向具有终极意义的人性问题”[4]。这样一来,以人性为基础的刑法基本问题的展开和深入就离不开审美。
第一,审美彰显人性。康德提出,审美是一种“反思判断力”。所谓“反思判断力”,不像理性判断力那样从普遍性的概念、规律出发去判断特殊事实,而是从特殊的事物和感受出发去寻找普遍。相对于追求所谓判断客观性的自然科学和其他社会科学而言,美学视角一方面强调现象的重要性,要求研究者关注、参与、深入现实,另一方面,它强调受众情感(感受)的重要性,倡导在社会中释放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的声音,使他们的诉求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的框架内得以与主流话语相抗衡。从历史上看,正是美学的发展使在理论上长期处于遮蔽状态的人的感性问题,如情感、体验、想象、沟通、理解等被逐渐彰显出来。
第二,人性是一种互动关系。审美倡导对话关系和终极关怀,一般而言,对话意味着平等关系之上的沟通和理解,即不存在一方支配和宰制另一方的局面。在这种关系中,主体能够从对象上“直观自身”,体验、感受、认同、领悟到与自身存在息息相关的精神、意义或价值意蕴,从而产生共鸣,形成交流。终极关怀是对话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升华,它需要主体“忘我”的投入或“整体的生命承担”态度。就刑法领域而言,陈兴良教授曾谈道,在我国目前的刑事司法语境中,定罪的法治化并未完全实现,因而罪与非罪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权力的操纵过程,而非法律自治与自主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改变归责的单向性与封闭性,努力建构一种定罪机制;在这一机制中,归责是一个沟通的过程。这里的沟通意味着商谈与交流,既是日常语言与法律语言的沟通,也是司法者与被告人的沟通。通过这种沟通,使刑法上的归责正当化与合理化,真正使定罪从权力的审判成为法律的审判,最终过渡到人的审判或者良知的审判[8]。用何庆仁博士的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刑法需要沟通[9]。不难想象,这种以人性互动为特征的沟通可以使刑罚的分配公正更接近现代法律的真意,从而使刑法能够获得受众情感上的尊重与认同。
第三,终极价值的思考和形而上的关切是审美的旨趣所在。可以说,作为一个终极价值域,审美是对人生存的真相、对人性的终极价值的呼唤、寻求和探索。“刑法的人性基础”这个极富想象力的命题,本身就把刚性的刑法与柔性的美和谐地勾连在一起,给人一种冲和之美。人性基础或曰审美之维,正是欲通过形而下的发微通向形而上的关怀。因为相对于“思想观点迟早都是会被超越而过时的”刑法理论思考而言,追求真善美的形而上关怀却是永恒的。
三、关系范畴(一):“刑法的形象”与“刑法的情感”
美是事物的形象性,且总是和人们的感觉联系在一起的。美学思考,可以将刑法学的研究引入一个新的场地。
(一)刑法的形象
形象一词,自古有之。在《尚书》、《周礼》中“形象”的基本意思是人之相貌,物之形状。到了今天,形象已被理解为“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他人或事物由其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或“人们所持有的关于某一对象的信念、观念与印象”[10]。刑法,作为一种制度设计,同样存在着知识性、功利性和形象性三种属性。刑法的形象,一方面是指符合刑法的精神、价值、理念或理想要求的感性表象,另一方面还可表现为刑法文本带给受众的心理感受、情感体验、心理效果等统一体。
形象在本质上是人对真善美的追求。长期以来,刑法给人的印象常与刀把子、狰狞、打击、冷漠、法不容情等词语联系在一起。但这不是刑法的现代形象,或者说,这样的一种形象不是刑法的本来面目。现代意义的法治只不过是人类关怀自己的一种方式,法治关怀也就是对人自身的尊严和生存的关怀。美是事物的形象性,作为内含着“美”的刑法,其形象性既有自由展开自己的向度,又与刑法的功利性同处一物。刑法的形象性,如何脱离其功利性而展开自己,这既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命题,也是一个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二)刑法的情感
情感,通常来说,是人对客观事物或客观环境的态度和体验,是人的一种直接反应状态,折射着人的价值观。情感在心理—文化结构中长期占据核心位置。情感认识不同于简单的情感体验,虽然对情感的体验是个体的、非理性的,但对情感的认识必须是社会的、理性的。对刑法进行情感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第一,“情”是刑法的应有之义。尽管可以举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法律是没有激情的理性”加以反诘,然而此言似乎只是在强调法律是与情感相对而言的一个概念,这种相对性并非意味着法律与情感是相悖的。而且,“片面将法与情绝缘,那不是对法的无知,就是对法的曲解。其实法是最有情的,法条与法理是建立在对情——一种对社会关系的最为和谐与圆满状态的描述与概括之上的,是情的载体与结晶”[2](P33)。刑法的情感,一方面是指刑法文本中意蕴的情感基础或情感特征,另一方面还可以体现为刑法受众的感受、态度和行为选择等。当然,一方面不能把刑法文本的情感品格同受众所产生的某种情感反应混为一谈,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二者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一种合宜的刑法文本所蕴涵和传达的刑法观念,能够赋予“充满刚性的刑事法治”以丰富的情感底蕴和强烈的人文关怀,“使刑事法超越其单纯的强暴性和威慑性,强化公众对刑法规范的亲近感和认同感”[11]。
第二,情感问题是进一步推动以刑法为本位的,关涉犯罪学、刑事政策学、刑罚学等领域“刑事一体化”研究的一个很好的契合点。“刑事一体化”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简单地说,就是旨在打通学科边界。因为一方面为应对犯罪必然要求刑事法整体运行的和谐,另一方面,人文社会科学具有普适性的话语,刑事一体化研究范式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将刑事法学知识置于更为广阔的视域中加以思考,使刑事法学更具人文性——或者说更具人文关怀。美学是最具人文精神的学科,情感现象及其认识规律是其中的重要内容。毋庸置疑,这些内容及其研究成果可以与现行刑事法领域中存在的一些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实现对接。通过对这些问题进行情感透视,可以进一步揭示隐藏在不同刑法观念背后的哲学根基,从而使我们更加理性地、人性地看待刑法。
第三,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形式合理性、文本观念等刑事法治理念。“形式—文本—情感”始终是美学理论中最重要的关系链,这种关系范畴的统一性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典型的人文反思方式。这种反思对于高度要求精确性的刑法理论而言,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形式与情感具有同一性的结论,可以使我们较直观地认识到现代法治情感的培育必然在于形式合理性的优先。再如对于刑法工具主义、刑法万能主义,文本观念提出的质疑是:我们到底是在拿怎样的情感态度对待刑法——是怀疑、功利?还是信赖、认同?也就是说,文本观念始终强调文本自身的尊严与品格,即文本的自主性问题。
当然,刑法的形象和刑法的情感是互为涵摄、共同展开的。对刑法文本和刑法现象进行审美观照,就是旨在通由法律践行者的“妙手仁心”和刑事法治旁观者的“冲和静观”,秀出“刚柔相济”的现代刑法形象。
四、关系范畴(二):“刑法受众”与“刑法文本”
定罪与量刑是一个过程,是文本表达与受众接受相互作用,即互动的过程。在这个互动过程中,表达和接受只是相对的,且主要围绕“刑法受众”与“刑法文本”这一关系范畴展开。
一方面,按照传统社会理论,受众就是指“大众”。现代文化研究学派则强调受众与大众的差别:受众不是绝对被动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和选择能力,他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解读文本,并建构意义[12]。从大的方面说,刑法受众,即刑法文本的接受者和阅读者。在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它与下文提到的“公正旁观者”在所指上存在着重合。不过,“刑法受众”的提法,一方面旨在突出与之相对应的刑法文本这一重要的概念范畴,另一方面则基于这样一种研究立场:非站在司法主体一方唯其马首是瞻,而是站在受众视角看待问题,即关注刑事法律现象中人们的心理、情感、态度等如何影响其行为选择以及相互之间的互动、对话、交流与沟通等。
另一方面,文本是达意传情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讲,定罪与量刑活动不过是使刑法文本的“达意传情能够适切的一种努力”。强调文本观念,必然包含着文本的接受心理。这样一来,就把受众与文本这一关系范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除受众之间的对话关系外,刑法受众的接受心理或曰刑法文本的接受效应,亦应当成为刑法理论关注的重要范畴。
此外,前面提到,刑法是一种精神产品。精神产品对于人的主体需求就不是像物质产品那样,呈现为一种物质对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精神价值。对于精神产品,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不是单线抛出的,而是全面辐射的。因此,刑法文本不是一个单元的价值载体,而是一个负载着以自由、秩序、正义、功利四大法律精神(价值)为中心的多元价值的复合系统。在这个多元价值的复合系统中,值得注意的地方有两个:其一,价值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不同价值的对立统一的运动过程,在这个动态过程中,要注意体现和实现刑法受众之间、受众与文本之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其二,效应是价值的实现,文本的接受效应则是某一阶段具体的价值关系的最终建立,是文本价值在接受者身上实现的静态成果。这种“静态的”文本效应,是否要以实现多元价值为目标,则是又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五、关系范畴(三):“刑法公正感”与“公正旁观者”
(一)公正感问题应成为刑法理论关注的重要课题
刑法上的公正问题,从来都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因为刑法涉及对公民的生杀予夺,公正是刑法的首要价值和生命,刑法中的一切问题都应当让位于公正性[13]。然而,对于什么是公正以及如何做到公正,却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正如博登海默那句脍炙人口的总结一样: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可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模样。我们在仔细辨认它并试图解开隐藏于其后的秘密时,往往会陷入迷惑[14](P261)。也就是说,界定正义(公正)非常困难。
公正在于公正感。“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认为,我们用以判断公正的标准始终不能脱离活生生的个体,不能脱离他们基于情感的判断[15](P118)。凯尔森则进一步指出,公正的客观标准是不存在的,因为说某些东西是公正的或不公正的,指的是对最后目的的价值判断而言,而这些价值判断就其性质来说是主观的,它是建立在人们的思想、感情和希望的情绪上面,既不能用事实来说明,又不能用逻辑来证明[16]。分析哲学家艾耶尔甚至直接将关于诸如公正与否的价值判断称为“情感的呼唤”。而情感首先是一种感觉,然而,问题是,“没有比对我们的感觉订一些普遍的规则更易受欺骗了,这些感觉交错得那么细致、那么复杂,甚至连最细心的观察都几乎不能厘清头绪”[17]。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种情感判断,能够证明公正存在的事实既不是普遍规则,也不是客观标准,而是人们“感觉”到了公正。
感觉并非混乱的认识,它也有自身的完善[18]。而且,随着人类在控制其难以理解的自然力方面、在发展一种更为强有力的道德意识方面和在获得更高的相互理解力等方面的进步,人类的公正感也会变得更为精致[14](P15)。最高人民法院前任院长肖扬曾经谈道,人民法院必须重视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需求,通过利益衡量、司法平衡等方式,合理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使裁判结果不仅在法律上符合规定,而且在实质上公正合理,满足民众的公平心、正义感。新任院长王胜俊在与珠海中院法官会谈时也提出,对待判不判死刑的问题,一是要以法律的规定为依据,二是要以治安总体状况为依据,三是要以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为依据。这些话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司法实践部门开始认识到司法受众的“公正感”对于社会公正实现的重要意义。然问题在于:人民群众的感觉(情感)能否作为正义法则产生的根据。作为应具前瞻性的理论研究而言,对此类问题应当给予及时的、理性的回应和关注。
(二)公正感是一种“旁观者理论”
通常来说,社会中的人是不断反思着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立地进行观察是人的一种普遍反思能力,是人的基本特性。发现并强调人是有可能置身于对方,或者能够处在某个中立的立场来对事件作出判断,这对当代社会科学来说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15](P350)。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人物的“公正旁观者”理论,与哈奇逊所设想的作为仁爱化身的旁观者概念不同。其理论的人性假设是:“所谓人就是具有同情共感能力的自利个体。”在其代表人物亚当·斯密看来,正因为有了这种同情共感,才使人得以超越了单纯生物学意义上的自利本能,由此具有了最本质的特性,也就是社会性。也就是说,人天生具有情感换位(交换)的能力。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斯密较为全面地讨论了公正旁观者的观点与公正感之间的密切联系。比如,从公正旁观者的视角来推导一个人对他人的侵害的严重性以及应该受到的处罚的程度,提出“最神圣的正义法律,也就是那些一旦被违反就引起最严厉报复和处罚呼声的那些法则”[15](P106);从人们达成关于罪与罚的共识的情感作用机理出发,提出正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总是基于个人的同情共感,基于一种愤恨和处罚的激情。一言概之,即斯密把人类理性和情感作为某种秩序如正义法则产生的根据。
不过,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情感体验:看到罪大恶极的罪犯,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而一旦这个罪犯遭受理应承受的酷刑,则又产生恻隐之心,试图宽恕他。也就是说,与所谓的冷静而公正的旁观者的判断相比,我们对于“坏人”的态度常常会发生改变。对此,斯密进一步提醒道:尽管在某些情况下,人类对于恶、对于犯罪的态度会随激情变化而波动不定,但确实还是存在一种一般的标准,一个人冷静下来以后必然会赞同的标准,一个置身于公正旁观者的立场会坚持的标准[15](P113)。显然,斯密的“公正旁观者”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生活的均衡力量,这种力量有‘时是一种局外人的眼光,有时是人类自身的良知,而有时则是某种共识性的标准或者秩序本身。同时,在这种理论框架中,始终存在着三个主体,一个行为人,一个行为的承受者和一个旁观者。正如我国学者罗卫东所总结的那样,“公正旁观者”理论要解剖这三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中所蕴涵的整个社会化机理[15](P131)。
从这个意义上讲,公正感问题的探讨,可以使关于刑法公正的命题由一种“犯罪—刑罚”的线性结构凸显为一种“犯罪—公正旁观者—犯罪”的函变结构。王世洲教授曾经提出,刑法学是最精确的法学,并认为“精确的刑法学理论,就像一把精确的尺子,可以用来厘定国家和社会在使用刑法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民中的各种要求,由此满足保护人权和发展法治的种种需要”[19]。我认为,较单一的线性结构而言,一种关于罪与罚的情感函变结构无疑是刑法精确性的必然要求。
收稿日期:2008-08-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