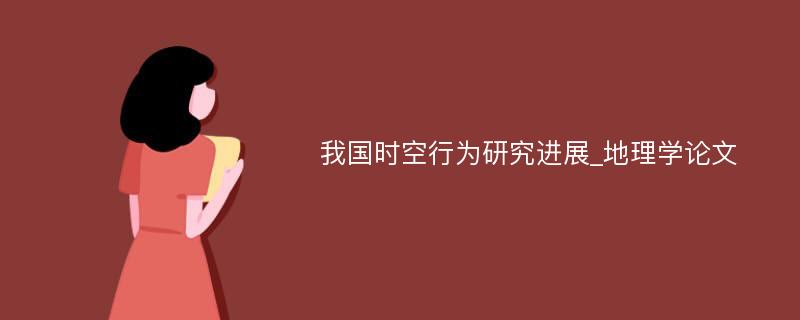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研究进展论文,中国论文,时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11820/dlkxjz.2013.09.006
修订日期:2013-08.
1 引言
时空间行为研究为理解人类活动和城市环境之间在时空间上的复杂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Hanson et al,1993;Kwan,2002a;Miller,2004)。自从哈格斯特朗创立了时间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以来(Hagerstrand,1970),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发展成为城市地理学、城市规划学和交通规划学中一种很具影响力的研究方法(Dijst,1999;Kwan,2002b;Timmermans et al,2002)。近年来,基于GIS的分析工具和高质量个体时空行为数据的发展,大大促进了时空间行为研究的主题多样化和应用工具化,使其在当代的城市研究理论和方法中享有更大的声望和影响力(Kwan,2004;Shaw et al,2009;Neutens et al,2011)。
在过去的20年里,面对中国城市转型及其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者和规划工作者已经开始尝试应用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居民的时空间行为模式,揭示微观层面上的个人生活经历与宏观层面城市社会空间转型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并将这一研究广泛应用于规划实践中。
本文较为系统地综述了中国城市地理学界的时空间行为研究进展,旨在促进来自不同领域学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在简要介绍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发展历程之后,本文总结了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的主要特色,即:以解读中国城市转型为核心、以规划应用为导向,关注城市空间重构的描述与解释,试图从行为角度解释中国城市社会转型,强调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与居民个体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重视日常生活、生活质量、社会公正、低碳社会、智慧城市等热点问题,探索在城市交通、旅游和城市规划等领域中的实践应用。这些研究成果为理解中国城市制度与空间转型背景下人类行为模式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2 时空间行为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引入
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是在西方时间地理学与活动分析法的理论支撑下,通过中西方的不断交流合作而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柴彦威将时间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介绍到中国,并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时间地理学的关键概念、理论观点和实证研究进展的文章(柴彦威,1998;柴彦威等,1997,2000);其后,柴彦威等对基于GIS的时间地理学及活动分析法的研究动向进行了反复回顾与总结(柴彦威等,2009a,2010a)。2010年,《国际城市规划》出版了一期由中美时间地理学者共同组织、撰写的关于时间地理学与城市规划的专栏,介绍了时间地理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以及在城市规划、旅游规划、社区规划等方面的应用(柴彦威等,2010b)。
与此同时,伴随着城市交通领域对于四阶段规划方法的局限性认识的深入,活动分析法作为一种出行需求预测模型也在2000年后开始引入中国(隽志才等,2005;周钱等,2008)。地理学领域也从城市空间研究的角度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全面介绍(柴彦威等,2008a;张文佳等,2009a)。总之,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的理论发展主要以引入和介绍西方的理论方法为主,在理论创新方面仍显滞后。
3 多源时空行为数据采集与分析技术的发展
一直以来,对中国城市地理学者来说,缺乏个体水平上的时空行为数据成为研究的主要局限。早期,个体水平上的出行调查或者时间利用调查数据只局限于在北京、广州①等大城市进行的由政府主持的调查,而且大部分数据并不对学术研究开放。因此,20世纪90年代,当活动日志调查或者相关类型的活动调查成为西方时空间行为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时(Dijst et al,2000;Kwan,1998;Shaw et al,2000),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者也开始设计和实施活动日志调查来采集中国城市的时空行为数据(柴彦威等,2002a)。经过20年的发展,现已逐渐形成了以出行调查、活动日志调查、GPS调查和大规模交通数据为支撑的时空间行为数据体系。
3.1 面向交通需求的居民出行调查
随着四阶段法在中国城市交通规划领域的普及,出行调查成为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最成熟的数据源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天津、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先后进行了以“居民一日出行调查”为核心内容的城市综合交通调查试点(全永燊等,2009)。经过几十年的发展,中国城市居民出行调查作为交通规划OD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常态化,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城市研究之中。
交通研究者认为,居民出行调查可全面地再现城市交通复杂的特点,能揭示城市交通问题的原因和交通需求与土地利用、经济活动的规律(张卫华等,2005)。在上海(潘海啸等,2009)、长春(周钱等,2008)、北京(Zhang et al,2008)等城市进行的出行调查丰富了学者对于城市居民交通出行行为的认识。但是,随着活动分析法的引入,基于个体的强调活动类型、出行目的地、出行方式、出行路径的活动日志调查受到更为广泛的重视。
3.2 基于时间地理学的活动日志调查
随着时间地理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入,活动日志调查作为时空间行为研究最重要的数据源之一,在调查规模、周期、精度等方面快速显示出其优越性。中国第一批活动日志调查分别于1996年在大连、1997年在天津、1998年在深圳得到实施(柴彦威等,2002a);这些调查收集了一个休息日与一个工作日的连续48小时的活动日志。
近年,在北京的活动日志调查不仅将活动记录和详细的出行信息结合起来,而且大大提高了时空间的精度(柴彦威等,2009b)。并且,活动日志调查也逐步从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少数沿海城市(柴彦威等,2002a,2009b;周素红等,2010a)扩展到兰州、乌鲁木齐等内陆城市(柴彦威等,2002a;郑凯等,2009)。另外,调查抽样越来越强调“居住区—家庭—个人”的分层抽样规范(柴彦威等,2009b),调查对象也开始包括城中村居民、低收入群体、少数民族等特定群体(兰宗敏,2010;刘玉亭,2005;郑凯等,2009)。
但是,由于活动日志调查本身的局限,在问卷数据精度和有效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误差(柴彦威等,2009b),例如,容易忽略短时间的出行,被调查者往往回忆不起当天的非工作活动等。
3.3 大数据时代的新型数据源
在大数据时代的驱动下,通过整合基于GPS和GMS设备的定位跟踪技术与活动日志调查,中国的时空间行为数据也向实时化和精确化发展。2010年,首次基于移动定位设备的活动日志调查试验研究在北京郊区的天通苑居住新城和亦庄开发区开展(柴彦威等,2013a)。该调查招募了100位志愿者参加,要求每位志愿者携带一个内置GPS和GMS芯片的移动定位跟踪设备,并在网络调查平台上完成一周的活动日志调查。与传统的日志调查不同,网上调查平台能够让被调查者在填写活动日志信息时交互式地看到其在城市地图上的活动轨迹。尽管这次调查的样本规模较小,但却是中国城市地理学者在时空行为数据采集方面整合传统日志调查和移动定位技术的第一次成功试验。此外,这次调查还显示了这类整合技术在收集长时期、高精度个体时空行为数据中的优势,以及进行大规模调查的潜在可能性。
近年,手机通话数据、浮动车数据、公交IC卡数据等大规模交通出行数据为描述和理解城市空间和居民行为提供了新的渠道,并已经开始应用于交通规划和城市研究(Fang et al,2012;Li et al,2011;Liu et al,2012;龙瀛等,2012;赵慧等,2009)。
3.4 时空间行为分析技术的发展
在时空行为数据趋于多元化和精细化的同时,相应的分析方法也在逐步改进。20世纪90年代,中国时空间行为的实证研究通常采用统计学的工具,并在汇总水平上描述时空行为模式(例如,柴彦威等,2002a);而此时的西方地理学者已经开始使用数学模型进行时空间行为的解释,并开始探索时空间行为模式的地理可视化和基于时空棱柱的可达性测量等。
近年,中国的时空间行为研究也开始引入这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应用结构方程模型、次序Logit模型、嵌套Logit模型和其他统计学方法分析建成环境对于居民出行时间、方式、距离等因素的影响机制(例如,周钱等,2008;宗芳等,2007),解释城市的建成环境和制度背景对个体时空间行为的影响(例如,柴彦威等,2010c;Wang et al,2009;张文忠等,2006;朱玮等,2008)。
通过中西方地理学者之间大量的学术交流,非汇总水平上的时空路径分析也取得了重要的方法论上的突破。早期的时空路径分析经常使用二维的图表,横轴代表离开居住地的距离。但是,迅速发展的GIS技术和高精度的时空行为数据使得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者进行基于GIS技术的三维时空路径分析成为可能(例如,古杰等,2012;申悦等,2012)。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空GIS工具包APA的开发及其在时空路径可视化中的应用使得在三维环境下进行时空行为模式研究成为可能(Chen et al,2011)。此外,其他一些计算机辅助的数据挖掘方法,如序列模式挖掘(李雄等,2009)、时空密度趋势面(张艳等,2011)等也被引入到时空间行为模式的研究中。
尽管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在数据采集和分析方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也面临着考验。一方面,以GPS为代表的定位跟踪技术的应用使得行为数据在精度和信度上实现了突破式的发展,但是隐私保护问题、调查成本较高、数据缺失和数据噪声等依旧是亟需解决的重要难点。另一方面,数据分析方法仍亟待提高,特别是针对GPS数据数据量大、对数据清理与处理算法要求高的特点(柴彦威等,2013a),需要进一步开发完善时空GIS分析算法与工具。
4 中国特色时空间行为研究的发展
诚然,中国的时空间行为研究受益于西方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但是,近20年来的本土化过程也为中国城市的时空间行为研究创造了独特的条件,形成了以解读中国城市转型为核心、以规划应用为导向的鲜明特色。中国人文地理学“以任务带学科”的特色赋予了时空间行为研究以学科发展与社会需求并重的目标导向。柴彦威等在21世纪初就从时间地理学关注生活质量的角度,提出时空间行为研究要面向转型期出现的单位解体、老龄化、社会不平等等社会问题(例如,柴彦威等,2002b),将中国城市居民的微观时空间行为模式置于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宏观背景之下,从活动空间分布、时间利用等多维度分析转型期城市制度—社会—空间转型对于居民个人生活的影响。另外,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也注重规划应用导向,提出了时间地理学在城市老年服务设施的时间管理和空间管理、老年福利服务以及老年社区建设等方面的应用前景等(柴彦威等,2002a)。
随着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在数据、方法上的不断成熟,其研究越来越鲜明的指向城市转型与居民生活方式转变的机制解释。2005年,柴彦威提出了人的行为研究整体框架,强调微观个体行为与整体社会的结合、短期行为与长期行为的结合、主观能动性与客观制约的结合、定量研究与质性分析的结合,将从宏观到微观、从描述到解释作为未来研究的主导方向(柴彦威,2005)。在这一方向下,时空间行为研究开始关注城市空间对居民行为的影响,以及居民在城市空间制约下的行为决策,挖掘城市空间与居民行为的互动机理。
在总结国外活动分析法研究的基础上,柴彦威等(2006)试图构建一个居民移动—活动行为与城市空间之间互动的研究新框架,企图沟通传统城市地理学研究与时空间行为研究的互动关系,将个人的移动—活动行为置于城市空间环境的大背景之中,以便透视经济转型和社会变化引发的城市空间重构过程对人的活动的制约和影响。周素红(2011)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通过加入时间维度来解释广义层面的社会空间问题。
中国时空间行为的研究也促进了其在规划应用方面的拓展。在城市规划由以服务经济增长为目的转向促进宜居、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被认为是城市规划和交通规划中最以人为本的研究方法(陆化普等,2009;柴彦威等,2010a)。在交通研究领域,潘海啸提出了基于行为分析的规划策略,认为空间形态是社会活动变化的结果,在城市发展中行为具有先导性作用,应当加强规划设计与政策组合的行为分析(潘海啸,2011)。另外,时空棱柱(戚铭尧等,2010)、可达性分析(陆化普等,2009)等时空行为模型在交通规划研究中逐步出现。在城市规划方面,时空间行为研究在智慧城市、商业规划(王德等,2011;朱玮等,2008)、设施规划(王德等,2009)、旅游规划(黄潇婷,2010)、社区规划(塔娜等,2010;农昀等,2012)等方面的应用得到快速发展。
4.1 理解空间: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的不断深化
近年来,城市研究的视角逐渐由城市物质空间转向社会空间,而时空间行为研究将行为空间看作是理解社会空间形成过程与机制的重要要素,试图从人类空间行为的视角来解读城市内部空间(Chai et al,2007)。早期的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关注描述个体日常活动的时空模式,提供了对于中国城市空间结构的微观层面的解释。时间利用结构、活动节奏和时空路径被广泛应用于研究总体时空模式,分析在24小时的时间周期中城市居民如何分配时间并进行不同类型的活动和出行,形成与城市空间的整体性互动(柴彦威等,2002a)。当然,也应当看到,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在早期发展阶段也面临方法论的挑战,比如,局限于讨论汇总层次上的活动模式并且对制约的考虑不足等。
后期的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发展由于方法论上的差异而形成了两大分支。其一是以行为地理学为基础,兼顾时间地理学方法,将各类日常行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细致剖析。例如,在迁居行为研究中,从微观层面分析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城市居民的迁居特征和机制(柴彦威等,2002a;冯健等,2004);同时引入居住偏好、迁居决策等视角,丰富了中国城市居民迁居的微观机制与决策的研究(刘旺等,2006;刘望保等,2007;杨永春等,2012;张文忠等,2003,2004);在购物行为研究中,学者检验了消费者行为与零售商业空间结构之间的关系(柴彦威等,2008b;冯健等,2007;王德等,2001),并从不同角度分析居民购物行为空间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决策过程(张文佳等,2009b,2010;张文忠等,2006),深化了商业郊区化对于居民行为决策的认知和对商业设施利用影响因素的理解;在通勤研究中,已有研究分析了中国大城市居民通勤行为的基本特征,并将通勤与转型期城市空间的变化相关联,将通勤行为置于居住郊区化、城市空间扩展、土地利用变化等宏观背景之下(刘志林等,2011;张艳等,2009;郑思齐等,2009;周素红等,2005,2010b)。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从时间地理学的活动空间概念出发,利用活动椭圆、缓冲区等分析方法构建居民一日或一周的活动空间,分析活动空间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柴彦威等,2013b)。
可以说,在居民各类日常行为的时空间特征分析和时空行为模式的基础上,学者越来越关注城市空间对居民行为的影响,挖掘城市空间与居民行为的互动机理,从物质空间的分析逐步发展到社会空间的分析,进而提出行为空间的决定性作用。
4.2 理解社会:与中国城市社会前沿问题的结合
面向全球化与郊区化背景下的各种社会问题,生活质量、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发展问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地理学者(柴彦威,2011)。通过学习西方文献,中国的城市地理学者开始快速地将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应用于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中,以求理解中国城市转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影响。
时空间行为研究强调个人与家庭的视角,从非工作活动和家庭内部联合行为等角度提出了生活质量研究的新视角。一方面,购物、休闲等非工作活动的研究逐渐增多,从非工作活动的时间利用、空间分布、时空间决策等方面说明了中国城市非工作活动的距离衰减规律和时间破碎化特征(冯健等,2007;马静等,2011a;许晓霞等,2012;周素红等,2008);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的共同相处时间被看作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通过分析家庭内部分工来研究家庭成员的时间利用特征(Cao et al,2007;张文佳等,2008),比较工作与家庭压力的性别差异和家庭内部协调策略,通过分析个体从事各类活动时的同伴类型,提出共同的活动参与有利于促进家庭生活质量提高和社会网络质量的提升(Zhao et al,2013)。
生活质量与社会公平是城市社会可持续性的重要维度。生活质量涉及到个体利用社会资源产生的社会效益,而社会公平则体现了这一效益在城市中的分配问题。与传统的中国城市地理学研究不同,时空间行为研究强调基于日常行为的视角来理解社会空间分异,将时空可达性作为社会排斥、社会隔离的指标,通过比较不同类型居民时空行为模式的差异,关注低收入、女性等劣势群体,探讨中国城市扩张和郊区化过程中的社会公平问题(周素红等,2010b;柴彦威等,2011a)。例如,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时空行为研究认为,由于职住空间错位,低收入群体在日常通勤中面临着比其他群体更大的困境(刘志林等,2011),日常活动空间显著收缩(张艳等,2011;周素红等,2010a),时空行为模式呈现破碎化(张艳等,2011)。
时空间行为研究在低碳社会方面的贡献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低碳出行以及构建低碳城市空间等方面。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低碳城市运动,促进了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在解释土地利用特征影响下的个体出行决策所导致的交通出行碳排放研究中的应用。基于北京不同社区的时空活动模式和碳排放量的比较研究,发现居住在用地功能混合的单位大院中的居民的碳足迹更低(柴彦威等,2011b)。基于社区的城市形态要素,如土地利用结构、公共交通的可达性、步行友好的街道设计、公共设施的可达性等,对于降低个体出行的碳排放量有重要意义(马静等,2011b;肖作鹏等,2011)。
4.3 理解转型:构建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行为范式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转型的范围和复杂性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者已开始探讨城市空间重构的过程与机制,从历史视角、积累体制视角、全球与地方视角、单位视角等多种角度对中国城市空间重构进行分析,已有研究注重体制转型的根本性影响,着眼于对转型过程中制度环境与制度安排以及主要行动主体的行动策略及其社会互动过程的分析(Huang et al,2002;Wu,1997)。
近年来,中国城市转型与空间重构的研究重点逐步转向对微观过程与机制的剖析,微观个体行为与城市空间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透视转型的重要切入点。时空间行为研究在这一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使城市研究者能够从个体日常生活经历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转型的过程和结果,成为理解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行为范式。当进行与出行目的地选择、出行频率、出行模式和其他时空行为模式相关的活动—移动决策时,个体居民必须适应不断变化的建成环境带来的制约(柴彦威等,2010c)。因此,时空间行为研究通过分析城市建成环境制约下的个体决策与城市空间重构机制,关注城市形态对于非工作活动出行(张文佳等,2009b)、基于巡回的出行时空决策(柴彦威等,2010c;赵莹等,2010)、家外活动决策(Wang et al,2011)等的影响,将单位解体、郊区化、行为偏好等作为解释城市转型的关键词。
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的另外一大特点就是探索以单位为基础的城市空间组织及其解体对于个体日常活动产生的重要影响。柴彦威的早期研究发现,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的日常活动空间被局限于单位大院中,单位大院形成了一个集工作、生活、服务于一体的自给自足的独立地域单元,中国城市的内部生活空间是以单位空间为基础的(柴彦威,1996)。但是,随着城市土地和住房的市场化进程,这种以单位为基础的城市空间组织逐渐解体,而单一功能、分区制的土地利用规划开始在中国城市中兴起,但是单位制仍然对通勤模式、出行模式、出行率、户外活动时间和其他时空行为模式产生重要影响(Wang et al,2009,2011)。相比于住在商品房社区的居民,单位大院居民的职住距离和通勤时间更短(刘志林等,2009;张艳等,2009)。上述这些研究均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时空间行为研究。
此外,郊区化对个体时空行为的影响研究也是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的又一特色。周素红等(2010c)研究了郊区保障性住房社区居民的空间不匹配现象,Zhao等(2013)比较分析了内城居民与郊区居民日常活动中的时空路径与时间预算制约。
4.4 规划应用:时空行为空间规划与智慧出行管理
近年来,城市学者和规划者开始认识到中国城市转型期间满足城市居民多样化需求的重要性,时空间行为研究在交通规划和管理、智慧城市总体规划、旅游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等方面开始进行实践探索。
与西方城市相似,交通拥堵和可达性不足已经成为中国城市面临的最主要的挑战。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在中国的交通研究、规划和管理中得到广泛应用(例如,Fang et al,2012;古杰等,2012;申悦等,2012)。基于时空行为研究方法的交通研究强调以个体为分析单元,关注基于活动的出行需求和出行决策的时空制约。基于时间地理学的理论框架,以可达性为导向的规划方法在分析关键交通连接通道的时空模式时显示出独特的优越性(Fang et al,2012)。同时,时空行为的地理可视化和时空行为的模拟建模也被用来反映和预测客流量和活动模式,在上海世博会的客流预测与设施规划(王德等,2009)等方面显示出其有效性。
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也应用于其他规划实践中。王德等基于在北京市王府井大街(王德等,2009,2011;朱玮等,2007)、上海市南京东路(朱玮等,2006,2008)和新天地(许尊,2012)等地开展的消费者购物行为研究,讨论了商业街的空间优化布局问题。另外,在对北京颐和园的研究中,黄潇婷等应用时间地理学方法研究了游客行为的时空模式(黄潇婷,2009;黄潇婷等,2011),建议通过时空行为研究方法在旅客游览路线优化及旅游时间规划中的应用来实现对旅游景区的动态管理(黄潇婷,2010)。
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正在被运用于中国智慧城市的规划与管理之中。北京大学联合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等单位共同承担的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项目“城市居民时空行为分析关键技术与智慧出行服务应用示范”,旨在整合多源时空行为数据,进行时空间行为的数据挖掘与时空行为模拟,在北京市内的示范区建立智慧出行服务平台,以此从个人时空间行为研究的视角促进智慧城市的规划和管理。
5 结论与讨论
时空间行为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已经成为中国城市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城市时空间行为研究已经形成了鲜明的特色。一方面,将微观层面的时空行为模式分析置于城市宏观层面的制度转型和空间重构中进行解释,加深了对于中国城市社会转型及其机制的理解。过去10年取得的成果表明,应用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从微观视角去理解中国城市转型的过程、动力和影响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范式。另一方面,与社会需求紧密结合,致力于推动时空间行为研究在规划领域的应用,已经成为服务于中国城市规划创新理论与方法演进过程中的重要方向。
尽管中国的地理学者在时空间行为研究中已经取得了方法论上的巨大进步,但是在这一领域理论上的发展仍显滞后。尤其是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时间地理学和时空间行为研究如何创新当代城市转型理论,已经成为亟需回答的科学问题。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现有城市理论,并不能充分解释城市转型过程及其对城市土地利用和个体日常生活产生的重大影响。因此在这种背景下,时空间行为研究就需要更多地关注于中国城市的理论建构。
此外,尽管在技术上已经取得了巨大突破,但目前中国和西方的城市地理学者仍面临着一些共同的挑战。比如,尽管高质量的时空行为数据采集已经成为可能,但是在何种程度上更多的数据能够带来更好的信息仍不得而知。尽管大样本、高精度的时空行为数据能够使我们对时空行为模式进行更精确的地理可视化研究,但是基于这种模式的解释将如何加深我们对于个体时空间行为和城市转型过程之间相互作用的理解,仍需要探讨。最后,尽管时空间行为研究方法在理解城市空间方面很有影响,但是这种研究方法如何使城市规划实践更加强调城市的社会和环境问题仍然是规划应用面临的重要挑战。
致谢:本文是根据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AAG)2011年会“地理学与地理信息科学中的时空整合”研讨会的主题发言加工整理而成,对清华大学刘志林副教授、北京联合大学张艳助理研究员、北京大学赵莹博士在本文写作过程中的重要贡献深表谢意,同时感谢美国伊利诺伊州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Kwan Mei-Po教授在本文成文过程中提供的建议与支持。
①北京分别于1986、2000和2005年进行了大量样本的活动调查;广州在1984年(总人口数的3%)和1998年(10000个样本)进行过活动调查;中国国家统计局于2008年在全国范围进行了时间利用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