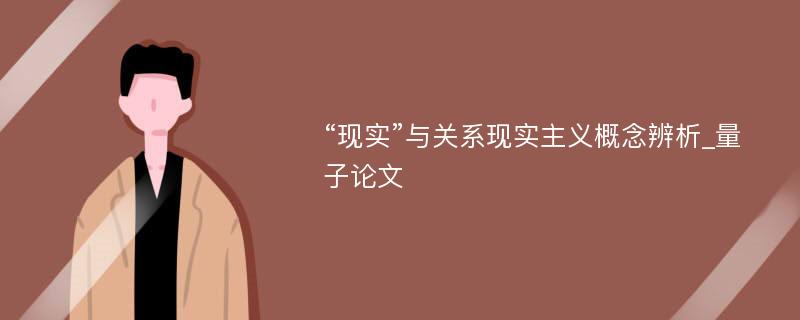
“实在”概念辨析与关系实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在论论文,概念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是哲学史上的基本论题之一,也是当代科学哲学的理论前沿。尽管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通常并不直接构成对于哲学问题的逻辑支持或否证,但是,使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获得其现代意义并再次成为哲学讨论焦点的关键因素,无疑正是现代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中对于物理实在、尤其是微观实在的种种性质、特征的认识和理解。从一般的“实在”概念辨析入手,探寻它的定义方式及其可能的逻辑悖难,特别是它如何在微观领域中面临实证困难并被引向反实在论的方向,从而修改和补充我们的实在概念以涵盖具有特异性质的微观实在,驳斥反实在论者的挑战,这应当是实在论者的一项紧迫而必做的任务,也是我们发展关系实在论的初衷。
一、“实在”概念辨析
实在论问题的讨论首先要求“实在”概念的澄明。因为对基本概念立足于平凡自明而缺乏分析界定,对其中的种种预设不加澄清,对论域的含混不加限定,常常是在论辩中造成歧义、误解、各言其是的原因。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澄明有助于说明:当前实在论所面临的困难或挑战,实际上是与某种特定的、具体的“实在”概念、“实在”观或“实在”描述方式相关的。对于一个实在论者来说,他所允诺的“实在”概念必须至少满足两个条件:“实在”的独立性或在先性;“实在”的可描述性。前者是实在论者的基本立场,一种本体论态度,后者则使“实在”成为对象化的、具体的、可认识的,而不流于空洞的名称或玄想。相应于这两个条件,亦有两种对“实在”加以定义的方式:
1、界定性或规范性的,即用相应的其它概念来界定,突出“实在”的独立性、在先性和第一性;
2、描述性或构造性的,即用其它的实在基元或要素来描述,突出“实在”的本质特征、结构或属性。
显然,第一种方式定义的是一般“实在”,它意在揭示“实在”概念的内涵,概括其类特征或本质属性,以利于把握作为各种具体实在的共相的“实在”概念。这是一种典型的哲学定义方式,简洁明了,高度概括。由于“实在”概念是实在论者哲学体系中的最基本的概念,一种元概念,因此只能用体系中其它相对应的元概念来定义。例如,由心物相应,即可用心来界定物,定义实在;同样,由主客二分,主体可用以界定客体,但用作实在的界定物时,则需剔除主体中的实在成分,剩下心灵以定义实在,因此“实在是独立于人心的存在”。这是一个相当经典的实在定义,为众多的实在论者所认可。①再如在波普尔(K.Popper)的哲学体系中,这种定义就是用世界2即思维世界来界定世界1——物理世界。但由于他的理论是一个三元世界体系,因此世界1显然也应能由世界3——从对象性思维的结果客观化而得出的理论世界来界定,即“实在是成功的理论所确定具有的指称物”,这正是科学实在论的基本观点。类似的定义还有“实在是第一性的存在”②,它显然是以与“第二性的存在”相对应、相比较的方式来定义的。
第一种定义方式的困难在于,“实在”概念作为一种元概念,一个出发点,其涵义对于实在论者似乎浅显自明,人人皆可意会,但一旦涉及言传或用其它概念来表述和澄明时,就会遇到若干形式上或语义上的悖难。从形式上说,“实在”概念作为出发点是很难定义的,采用其它平行的元概念来界定至少难免彼此间的逻辑循环,因为它们之间没有递归关系。从语义上讲,再严格的定义其谓词部分也是容易产生歧义的,其分析说明是有认识论或理论负荷的。以“实在是独立于人心的存在”这一定义为例,对什么是“独立于”,什么是“人心”,什么是“存在”等都须澄明。即便对这些词汇的涵义都已澄明并能达成共识,从肯定的方面说,这个定义也不只是允诺了实体(个体)实在,还允诺了属性、关系、过程、事件、规律等等都是实在(因为它们都是“独立于人心的存在”),但对这种种实在之间的关系并未作出断言;而从否定的方面说,它则面临自反性悖难和人工物悖难,前者是指当以自身为思考对象时,主体由于难以符合定义而丧失其之为客体和实在;后者则指充斥我们生存环境的人工物(大至摩天楼和人造卫星、小至人工合成的核素、粒子)作为心与物的结合,将由于不符合“独立于人心”的标准而被排斥在“实在”之外,只有自然物才能位列其中,这将只是一种相当原始、干瘪的实在观。同样,“成功的理论所确定具有的指称物“用作界定物时不细加辨析也会出现类似问题。例如“成功的理论”本身就不是个清晰严谨的短语,关于“成功”的评判标准的多元和混乱,显然只能给被界定物带来更多歧义而不是平凡自明。“第一性的存在”这一短语机敏地用奥卡姆剃刀剃去了“人心”、“理论”这类对应的词,避免了一些可能的歧义,但也由此缺乏限定,给种种把精神、心灵类存在引入实在的泛实在论或反实在论留下了缺口。因此,第一种定义方式中的种种抽象的一般的实在定义,一方面无疑是合理的、可辩护的、应坚持的,另一方面则仍需展开细致的论证和澄明以足自洽。例如对“实在是独立于人心的存在”这一定义,需要由论证身体对心灵的独立性以克服自反性悖难,由引入时态限制,把实在定义为“其现时存在与否不依赖于人心的存在”以克服人工物悖难等。
第二种定义方式强调了“实在”的可描述性、可认识性,立足于“实在”的可感特性和本质特征,它定义的是具体的、个别的实在,即作为殊相的实在,以区别于不可认识的“物自体”和形而上学的“空名论”等。“实在”的定义由此化解为用其它基元或要素所作的描述或建构,并因而具有某种类还原的意义。还原的类型依基元要素的选取而不同,例如当将其选为“基本粒子”时,可称作结构还原或本体论还原,当选为“性质”时,可称作认识论还原。一般而言,“实在”的描述性定义是一种认识论定义,或立足于科学的定义,它相应于人们从日常生活到科学实践中对于实在个体的认识过程,因为正是由性质入手,人们才得以感觉、认识到某一实在个体并由此定义它,把它与其它个体相区分。也正是由实在的不同类性质(如声、光、电、热和化学等)出发,发展出科学中的不同学科,并得以不断深化对科学对象的本质认识。因此,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性质描述逐步兴起,并取代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图景而成为最基本的实在表象之一。从洛克提出“实在”的定义与其一组属性同一,到罗素的“摹状词理论”,性质还原已逐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即使由结构还原得出的“基本粒子”,也被认为不过是由一系列把握了其微观本质的量子性质(即量子数,如电荷、宇称、自旋、同位旋、奇异性、超荷、重子数等)来表征的。
第二种定义方式似乎在哲学上是无懈可击的,人们只能如此去认识、描述和定义实在个体,他们也这么做了。问题是一旦这成为一种传统,成为一种教条,人们就习惯于把这种性质描述凝固化、本质化、本体化,认为这些性质是独立不变的,它反映了实在的本质。这样,实在个体的实在性即表现力这组性质的实在性,或者说性质本身就是实在。这种定义方式的典型表现即为经典物理学的“性质实在观”。而当科学的发展揭示出其中若干性质的非不变性、非独立性、或非本质性,危及的就不仅仅是这些性质本身的实在性,而且是实在个体的实在性,从而给反实在论者的进攻留下了缺口。物理学领域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循此展开的。
二、“性质实在观”的困境
“实在”概念在物理学哲学中的对应物为“物理实在”。“物理实在”也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尽管受物理学理论和实践的约束,它显然更为具体、确定和实证化,同时又趋于远离直观和亲知,尤其是在微观领域和天体物理中。
相应于实在的第一种定义方式,“物理实在”可以被定义为物理客体,它在本体论上独立于人的认识而存在,在认识论上与认识主体构成不可分割的认识统一体,是为物理学理论所对象化并可由观测程序所认证了的客观实在。
相应于实在的第二种定义方式,“物理实在”即为可由一组完备的物理量(物理性质)确定描述的物理客体的状态。在经典物理学中,物理客体分为轨道粒子和连续的场两类,由于它们与观测仪器遵从同样的物理定律,观测对其状态的影响原则上可以排除,因此物理量描述的是客体的真实状态,物理实在是可认识的,其存在与否不依赖于对它的观测。同时,由于粒子与场都不再是直接可感受到的直观实物,而是基于物理学理论思维和实验操作的知识而形成的科学抽象,理论思维和操作对物理实在的性质表述或性质构造的作用愈发突出:物理学理论中各种基本方程中所表述的,是关于物理量即物理性质之间的关系即物理学定律,而实验室中所操作测量的,也是种种物理性质的特征和数值。物理性质似乎已不仅仅是表述物理客体的桥梁和构造物理实在的要素,而且本身也已客体化,实在化;特别是那些被洛克称为“第一性质”的基本物理量(如质量、广延、时间间距等),它们被看作反映客体本质的固有属性,既不依赖于客体的环境,也不依赖于人们的观察认识,在量上和质上都是确定不变的。“第一性质”的独立不变性反映了其实在性,也由此确保客体的实在性,这就是经典物理学中的“性质实在观”或“第一性质观”的由来和主旨。
“性质实在观”为物理学家们所广泛接受和默认,这既因为在观念上它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一致,特别是与几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经典物理学的传统相一致,也因为物理学家们在工作实践中直接与之打交道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验上都是各种具体的物理量。实在的客体本身被同样实在的性质所淡化而“退隐”于后,抽象的观念被具体可操作的物理量所取代。与此同时,“性质实在”也“继承”了经典物理学概念框架赋予“实体实在”的若干基本特性,即应具有独立不变性、可量化(即可作数学处理)特性、量与质的确定性、决定论性、空间可分离性、时空可描述性、系统性质的可还原性,等等,这些特性分别成为构造“性质”实在性的要素。
“性质实在观”在哲学家中也留下了久远的影响。从洛克提出区分第一性质和第二性质及通名的意义与一组属性同一,到贝克莱、休谟把客观对象看作一束性质,尤其是到了罗素,“用以区别事物与性质的那种假设的理由就似乎是虚幻的了”③,“实体”作为概念丧失了其独立性,不过起吊起一束性质的挂钩的作用,因为“实体被认为是某些性质的主体,而且又是某种与它自身的一切性质都迥然不同的东西。但是当我们抽掉了这些性质而试图想象实体本身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剩下来的便什么也没有了”④。克里普克从本体论上批判了上述将实体等同于一簇性质的现象主义理论传统,试图恢复亚里士多德的实体概念,重新肯定其关于实体的本质属性和偶然属性的区分,但他同样面临着一个难题,即“本质属性”的确认是有赖于理论情境,并会随着科学认识发展变化的。过分依赖于“本质属性”的必然性、不变性,就会在科学的发展面前面临窘境,进而危及实体的实在性。
事情正是这样发展的。随着现代物理学的进展,“性质实在观”开始面临挑战:
首先是狭义相对论揭示出那些反映客体本质属性的第一性质(如广延、质量等)不再是不变量,而是依赖于参照系的,由此危及这些性质的实在性;
接着是量子力学所带来的更大冲击。按照不确定性关系,微观粒子不能同时有确定的位移和速度,即不再是轨道粒子,无法在时空中作清晰的描述,同时,对量子跃迁、波包扁缩等基本量子过程也不再有时空可描述性;
按量子态的几率本性,对量子性质的数值只能作几率预言而不再有决定论性,对量子事件的发生也同样如此;
按不确定性关系,量子性质的测量结果不仅在量上受测量仪器的影响,而且在质上也受仪器选择所制约,在经典物理学中相容的物理量在量子描述中成为互斥的,而曾是截然对立的粒子性和波动性却随不同仪器的选取兼容于对同一客体的描述中——第一性质在量上和质上都不再是独立不变的;
按贝尔不等式实验检验所支持的量子预言,曾有相互作用的空间分离系统间存有某种奇异的量子关联,系统的量子性质是纠结的而非可分离的。如此等等。
这就是“性质实在观”的困境。
如果说第一性质作为实在的实在性有赖于其独立不变性、时空可描述性、决定论性、量与质的确定性、可分离性等等,而现代物理学的上述结论危及甚至否定了第一性质的这些特性,那么推理链的尽头自然是质疑第一性质的实在性,甚至通过“实体是性质的组合”这一环节,进而去质疑实体的实在性,从而打开了通向反实在论的大门,即由“性质是依赖于人及其仪器的”走向“实体是依赖于人及其仪器的”这样的违背实在定义的结论。
在这儿,这种推论与实在论者的根本信念发生了激烈的冲突,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爱因斯坦所问的“月亮在我们不看它时存在吗”⑦这一问题,正体现了他的这种实在论信念,而要回答微观领域的反实在论倾向,则需要实在论者作更为严谨的分析和充分的论证。
三、解决问题的实在论途径
显然,上述“性质实在观”的困境表明,量子力学问题对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既非处于中性地位,也非不相干的⑤,至少对于经典的物理学中的“性质实在观”这种具体的实在论形态是如此。为了坚持实在论立场,我们必须认真考察和分析随量子力学的发展而出现的非实在论和反实在论倾向,并寻根溯源,力求克服它,而不是漠视它或回避它。
在肯定量子力学、即承认其基本内容(包括不确定性关系)的科学性的前提下,要斩断上述得出反实在论结论的推理链,可以从三处入手,或者说有三类方法。相对于“性质实在观”而言,它们可分别称之为保守论、否定论和改造论。
所谓保守论,即试图继续保持“性质实在观”的基本立场,对之稍加修改以适应新的科学事实。例如,有人认为大多数相对论效应是表观的、不真实的运动学效应,因而不危及第一性质的实在性,有人则主张立足于四维空间中的不变量来定义物理实在⑥;有人反复试图重建量子跃迁、量子关联等过程的时空描述;有人致力于把量子几率性化归为亚量子层次大数量粒子决定论性运动的统计规律,即“隐变量理论”⑦;有人把不确定性关系解释为同时测定共轭物理量时的“模糊”⑧;也有人坚持贝尔实验中每个粒子的量子性质有确定值,而得出量子关联说明粒子间有超光速信号传递的结论,等等。但这些修改基本未触动经典实在论的概念框架,很难使其摆脱所面临的科学上和哲学上的困境,因为相对论效应尽管是运动学效应,然而却是真实的,定义物理实在于四维也就放弃了三维性质的实在性;重建微观过程时空描述的努力并不成功,而“隐变量理论”也不具备与量子力学同等的解释力和预言力,甚至导致了与狭义相对论的冲突。保守论的缺陷在于仍未认识到传统“性质实在观”的弊端是使性质的实在性立足于其独立不变性,即量与质的确定性,从而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而量子性质却本质上是非独立不变(依赖于仪器)的、非确定(本征值非一元、非决定论性)的。继续保守下去,只能是或者冒与相对论、量子力学冲突的风险,或者违背实在论的初衷,趋于反实在论的结论。
否定论者则试图通过从根本上否定“性质实在观”来摆脱它所面临的困境和可能的非实在论趋向。否定论的主要形式之一以实体实在论作为其坚实的基石,主张实体(包括场)是第一实在,甚或是唯一实在,是所有属性、性质和关系的载体,是真正独立的存在,反对“实体是性质的总和”的哲学本体论甚或哲学认识论。他们认为实体在本体上不能还原为性质,任何性质都不能单独存在,由此从本体论上截断了从性质到实体的下行路线,从而使性质的非实在性不致危及作为实在论基石的实体的实在性,甚至成为这种实在论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实在论的代表有张华夏的“实体实在论”⑨,邱仁宗的“个体实在论”⑩等,它们基本上属于哲学家提出的形而上类型的实在论,或者是并不在意量子力学问题中“性质实在观”的困境,认为它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无关,或者干脆视而不见,回避它。然而这种实在观上的“实体一元论”如果不与性质描述挂钩,则只能得出罗素的“什么也不是”的结论,即一种形而上学的“空名论”,无以界定自身并与其他实体相区别。仅凭抽象的“自我同一性”等于无所言说;而一旦论及性质表述,则无论回溯到本文起始的那种实在定义方式,性质都具有无可争议的实在性,但这种实在性在“性质实在观”框架中却面临着现代物理学的挑战。这就又回到了本节的出发点。对于实体实在论,困难还在于微观领域的特异性使实体不再是直接可感知和触及的,我们通过仪器所亲知的,反而是量子性质的实在性,而由这些性质,我们无法对实体作概念一致的描述和建构。
改造论则致力于变革“性质实在观”。在承认实体和性质二者的实在性的前提下,通过破除“实在性在于独立不变性”这一“性质实在观”的教条,改造论得以摆脱“性质实在观”的困境而保持其实在论立场。实在论者强调实体和性质的独立不变性,指的是它们相对于人心的独立不变性,而并不简单地排斥一切关于它们的非独立性和可变性。它们在不同的参照系和实验装置中表现出不同的量或质,表现出对物理环境的某种依赖性,这非但不影响其实在性,而恰恰揭示了实在的丰富内涵。尤其是在微观领域,实体的状态本身就非完全确定的,其物理量(性质)的本征值本身就非唯一的,二者的确定本身就非决定论性的,这些都有赖于它们与包括测量仪器在内的物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而体现出某种整体论特征。无疑,参照系的选取,仪器的设计、制造和使用,都不是独立于人心的,但实体和性质在确定参照系中的取值、与确定仪器的相互作用、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等都是物理的、客观的、不依赖于人的意志的;即使其作用结果的非唯一性,也可对每一结果作不依赖于人的确定的几率预言。因此,试图依据参照系或测量仪器的“人工性”或其选取、制造中对人的依赖性,加上参照系和测量仪器对于物理量取值的影响得出反实在论的结论,实际上是立足于或隐含了关于实在性的两个假说或教条:其一即机械地理解关于“实在是独立于人心的存在”的定义,由此则否定了参照系和仪器等人工物的实在性,一旦它们对测量结果有影响且这种影响原则上不可排除,则危及客体性质的实在性;其二是把“实在性在于不变性”绝对化,坚持第一性质或本质属性的不变性,甚至在物理实在已有本质不同(微观实在)或者物理环境已经改变(不同仪器)的情况下也固守于此,这种僵化的实在观显然难以苟全于科学实践的新进展中。
第一个教条的要害,如本文第一节中所说,在于片面理解人工物的实在论地位,缺乏对它们的全面分析。它强调了在目的论的意义上,仪器是人们为辨别、认识和变革对象而选取、制造和使用的,在认识论的意义上,它们是主体认识器官的延伸、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而忽略了本体论意义上,它们已成为独立的物理系统,它们与被测客体之间的关系,无论在运动学还是动力学上,都是确定的(包括几率上确定的)、客观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们对测量结果的影响也同样如此。当然,这种客观的影响会波及测量结果,这就又牵涉到“不变性”教条。实在的不变性观念显然来自对日常经验和感性直观的抽象,但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即使是“客体实在论”者,也不全都赞成把实体看作是孤立的、不变的永恒实体(11),而实体的多样性、可变性恰恰是基于性质的多样性、可变性。我们所说的相对不变性,是指在确定的参照系或测量仪器中,在确定的物理环境或条件中,性质是不变的、确定的,至少是可几率地预言的,它不为科学家的个人品性和意愿所影响,具有认识论意义上的“主体间性”。我们把这种具体(确定)关系中的性质不变性,作为变革后的“性质实在观”的基本主张。而探讨包括实体实在、性质实在在内的物理实在的关系特征,揭示这些关系的客观性、实在性、在实在描述中的必要性及其与性质描述的互补性,则是关系实在论的基本内容。
四、关系实在论视野中的实在概念
通过引入关系因子加以限制,性质实在得以保持其相对不变性和对人心的独立性,继续作为描述和构造物理实在的基石。但显然,这种对物理实在的描述和构造已不再是“性质一元”的,而表现为性质和关系的二元组合。在确定的关系中,有确定不变的客观的性质表象;而在不同的关系中,则有不同的性质表象;这些不同的关系、亦即不同的性质表象互斥又互补,由此所生成的一组关系因子制约下的性质表象,构成对实在的完备描述和建构。这样,波粒二象性所体现的微观实在的特异性将不再因直接归之于本体上的实在而令人观念上难以接受,相反它不过是微观实在在不同关系中表现为不问性质的“潜能”。换言之,波粒二象性的概念困难,在于它忽略了自己作为实在的二元描述的特性,忘却了自己发生学意义上的关系因子,仍然试图对微观对象作经典一元的、而又是完备一致的性质描述。诚如E·马奎特所言:“我们只能断言电子在一组环境中表现其类粒子性质,而在另一组环境中表现其类波性质。这样,人们就不能说电子作为量子客体,是粒子或是波,也不能说它既是粒子又是波。波粒二象性所表明的不是波和粒子的相互渗透,而是量子客体不同的现象学显现。”(12)
同理,测不准关系所反映的,是原本相容的共轭物理量在量子领域只能在互斥的关系中分别确定。原本互斥的(粒子性和波动性)成为相容的,相容于由不同关系中的性质表象构成的实在描述中;原本相容的(共轭物理量)成为互斥的,又互补于由不同关系中性质表象构成的对实在的描述;其共同特征,在于揭示了量子描述的关系特征,即如玻尔所说的描述对于关系的相对性。
关系特征,并不止于似乎更多认识论色彩的量子描述,也见之于本体论意义上的量子实在的构造。微观实在的特征之一,就是它不能为我们所直接经验,其实在性不是直观自明的,而有赖于在实验中与仪器的物理作用,或者说在关系中的显现;其概念构造则立足于对在与不同仪器的相互作用、或不同关系中显现的各种量子性质的整合。量子实在的关系特征,既包括作为实在要素的量子性质对于物理环境和关系的依赖性,也表现在量子层次上以EPR关联为代表的系统间的彼此缠结的关系中。由揭示量子性质对于关系的依赖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现代物理学的生成论特征——性质在关系中生成;由揭示量子系统与仪器之间及量子系统相互间的关系,则以一种更为具体和可分析的方式表现出现代物理学的整体论特征。关系特征是对象的基本特征,也是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13)。
关系特征,也并不止于微观领域,宏观的物理实在同样处于关系的制约中。我们已经提到过相对论揭示了运动物体的时空性质及质量等对于参照系的相对性。同样,在力学中,马赫原理认为物体的惯性来自与宇宙间其它物体的作用;在热学中,非平衡态热力学告诉我们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交换而形成有序结构;在电磁学中,带电体在电磁场的作用下运动,等等。实在在关系中定义和描述,也在与外界的关系中运动和变化,以至于彭加勒甚至于提出“真实对象之间的真正关系是我们能够得到的唯一的实在”,“唯一的客观实在在于事物之间的关系”。“科学能够达到的实在并不是象朴素的教条主义者所设想的事物本身,而只是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关系之外,不存在可知的实在。”(14)
通过引入关系描述,我们修改和补充了实在的性质描述,摆脱了“性质实在观”的困境。通过强调关系特征,我们也提出并论证了关系实在论的基本主张,这就是实在是关系的,作为物理实在的性质实在和个体实在,都限定于特定的关系结构中而得以定义、描述和构造;也正因为关系已成为实在的构造要素,我们又主张关系是实在的,它已成为实在描述中的一元,并符令其“独立于人心”的规范定义和“可描述的”的描述性定义,它的客观性在于物理系统之间的耦合及其结果的确定性。我们甚至主张关系对于关系者在某些情形中的在先性以突出和强调关系(如在量子关联和系统论中等);最后,我们主张性质描述和关系描述是互补的,也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我们从科学史上可以看到第二性质、第一性质如何被次第揭示为客体与人们的感官、与参照系和测量仪器之间的关系,而在关系因子确定后,这些关系又可转化为对客体的性质表述(15)。
上述性质与关系的二元转化说,表明关系实在论在对实在的描述中并不试图追求一种一元的关系论,一种终极的实在观。关系实在论的初衷是变革物理实在观,它从传统的“性质实在观”的困境中体察到了“性质”作为一元的、终极的实在的悖谬;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关系实在论的本性是多元的、平权的,它拒斥那种绝对的终极实在的观念。因为关系本身就是多样化、多层次的,限定在不同种、为同层次关系中的实在也必然是丰富多彩的,由此不同种、不同层次间的实在是不可比、不可还原的,彼此无优越性可言,不能说物理实在就一定比常识实在优越,例如不能说一张桌子的粒子表象比它的感官表象优越,而只能说它们分别在不同的关系中揭示了对象的不同侧面,常识的桌子之为桌子的“质”,是不可还原为粒子的“质”的。人们在确定的物理关系中把对象确定为物理实在,在确定的日常经验关系中把对象确定为常识实在,在确定的立足于审美教学和经验的美学关系中又把对象确定为美学实在。实在实现于特定的主客体统一的实践关系中,甚至即使这些实在的对象是(潜在意义上)统一的,但作为实在却是非同一的,作为物理实在它是一堆粒子的集合,作为常识实在它是一张破旧的桌子,而作为美学实在,它则可能是一个具有文物意义的红木家俱。脱离具体的关系,很难说哪一种实在更优越,也没有超脱于各种具体关系之上的评判标准。仅当若干不同实在的研究主体同一时,这种不同实在、或对象的不同图景之间的隔障才得以跨越而达到一定程度的交流。由此,关系实在论给人们以描述实在的更为细致具体的笔触和更多自由度的空间。
注释:
①⑩邱仁宗:“实在概念与实在论”,《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
②陈晓平:“也谈实在概念与实在论”,《学术月刊》1995年第3期。
③④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14、260页。
⑤洪定国:“论量子力学在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争中的中性地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2期。
⑥(14)(15)胡新和、罗嘉昌:“从物理实在观的变革到关系实在论”,《自然辩证法通讯》1993年第3期,[注]20,21;[注]22;第16-17页。
⑦E·Schrodinger,"Are There Quantum Jumps",British Journal of Philosophyof Science,3(1952),PP.109-123,233 247.
J·Butterfield,"A Space-Time Approach to the Bell Inequality',J·Cushing and E·McMullin(ed)Philosophical Consequences of Quantum Theory,Univ of Notre Dame Press,Notre Dame,1989,PP.114-144.
D·Bohm,"A Suggusted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Physics Review,Series 2,85(1952),PP,166-179,180-193
⑧F·Rohrlich From Paradox to Reality,Cambridge Univ Press,Cambridge,1987,P.179.
⑨(11)张华夏:“实体实在论”,《哲学研究》1995年第5期。
(12)E·马奎特:“量子客体的波粒二象性构成对立面的统一吗?”《哲学研究》1991年第10期。
(13)胡新和:“现代物理学视野中的自然观念”,《自然哲学》第一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7-23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