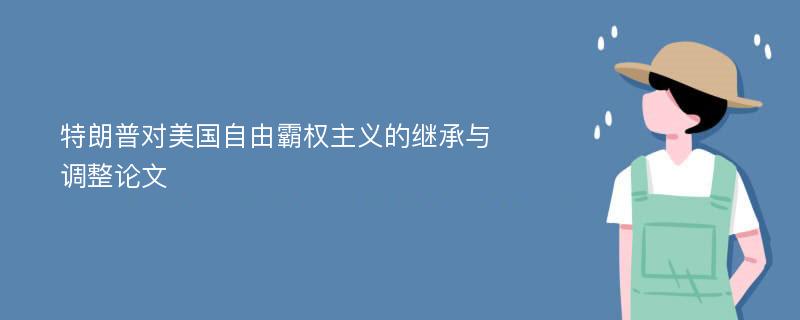
特朗普对美国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与调整*
李永成
[内容提要] 自由霸权主义是冷战结束后贯穿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任美国总统对外政策的大战略,以“单极时刻”格局下美国实力优势为后盾,致力于推广美式自由民主制度。特朗普总统就任两年多来,对外政策未能跳出自由霸权主义的窠臼,兼有继承与调整的两面,试图在扩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与霸权护持的双重目标中找到更好的平衡。其继承性集中表现为对外政策的强烈意识形态性;其调整突出表现为霸权护持优先的政策偏好,以突出经济安全、强调公平贸易、减少海外用兵规模等手段护持美国霸权。特朗普一些被视为背离自由霸权主义的政策行为,实质上是以退为进,依然具有典型的自由霸权主义本性。自由霸权主义已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遗传基因,未来将继续对美国外交产生基础性的影响。
[关键词] 自由霸权主义 米尔斯海默 特朗普 美国外交
自由霸权主义(liberal hegemony)被认为是在冷战结束之后贯穿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三任美国总统对外政策的大战略。特朗普就任总统两年多来,在对外政策上颇具个性,联合国、北约、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主义制度屡屡遭其冷眼,似乎已跳出了自由霸权主义的窠臼。然而,透过特朗普政府若干重要对外政策行为的表面迷雾,挖掘其深层次的战略驱动逻辑,可以发现特朗普既继承了自由霸权主义战略框架,又试图在霸权护持优先与自由干涉主义行动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本文以自由霸权主义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为基础,分析特朗普对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与调整,解释一些看似背离自由霸权主义逻辑的政策行为,并展望其未来影响。
一、自由霸权主义的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
自由霸权主义是美国学者近年来频繁使用的一个概念,有人用它来指称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将其排在“民主的扩展”“不断深化的经济相互依赖”之前,位居冷战后维护世界总体和平的三大要素之首。[注] Michael Mandelbaum, The Rise and Fall of Peace on Earth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认为,自由霸权主义是冷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大战略,是与现实主义的离岸制衡等更具克制性的战略相对的概念,其要义是“寻求全方位扩展”美国价值观,追求三大目标:一是“将尽可能多的国家变成自由民主国家”,二是“推广开放的国际经济”,三是“构建国际制度体系”。[注] John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y ,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p.1. 类似地,沃尔特(Stephen Walt)强调自由霸权主义的两个特征, 一是“运用美国实力保护、扩展个体自由、民主治理和市场经济等传统自由主义原则”; 二是“将美国视为‘不可或缺的国家’,只有美国有资格扩展自由主义政治原则,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国设计与主导的联盟体系与制度网络”。[注] Stephen Walt, 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 ’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 ,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p.14.综合而言,自由霸权主义的基本特点是,美国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以经略霸权、护持霸权为宗旨,认为“美国不仅必须运用其实力解决全球问题,亦必须着力扩展基于国际制度、代议制政府、开放市场、尊重人权的世界秩序”,致力于“大力推广民主”,“重塑他国社会”。[注] John J.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M. Walt, “The Case for Offshore Balancing: A Superior U.S.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 July/August, 2016, pp.70-71.归根结底,推广美式自由民主、护持美国霸权优势是自由霸权主义的两大基本构成。
需要指出的是,米尔斯海默与沃尔特对自由霸权战略的界定没有充分突出“霸权护持”在美国对外政策目标中的核心地位,他们更多强调的是扩张美式自由民主模式的一面,专注于自由主义的首要影响。根据米尔斯海默的分析,自由主义可以还原为两大核心要素:一是强调权利是不可剥夺的,保护人权是最基本的政治生活准则;二是主张个体的人是最基本的政治行为体,国家不是高于个人的政治单位,相反,国家是为个人服务的。[注] John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y , chapter 3.这两大要素可浓缩为“权利主义”和“个体主义”,二者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影响是促成其意识形态普世主义情结,在美国实力优势明显的情况下,滋生一种“自由黩武主义”做派(liberal militarism),使美国在世界范围内以保护人权、扩展自由民主制度为名,陷入干涉主义军事行动。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自由黩武主义”根源于五个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一,在全球范围内推广民主是个“大使命”,本身便意味着大量的战争风险;其二,自由主义决策者相信自己有权利、责任、技巧使用武力实现推广民主的目标;其三,自由主义决策者往往以传教士般的激情推进扩展民主的工作;其四,自由霸权国家因其实力超强,往往弱化外交手段,难以与其他国家和平解决争端;其五,自由霸权主义往往导向侵害他国主权,损害主权制度的权威性,侵蚀其作为限制国家间战争的国际规范的有效性。[注] 同上,pp.152-153. 毫无疑问,美国的超强实力与自由主义情结催生了美国精英们的“权力的傲慢”和“制度传教士激情”,自身的内部克制因此被弃,主权制度、大国制衡等外部约束失效,往往导向以实力为后盾、推广民主的自由干涉主义议程和行动。
自由霸权主义从理论到政策的必要环境条件是美国具有“单极”的实力优势,冷战后的国际格局被视为“单极时刻”,刚好满足这一条件。因此,在克林顿、小布什和奥巴马三位总统任期的24年里,美国对外政策呈现了典型的自由霸权主义特征。克林顿政府首先将“在海外推广民主”列为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中心目标”之一,[注] The White House, 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 , 1996.奠定了自由霸权主义以推广美式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政策基底,并为其后两任总统所继承。具体而言,自由霸权主义的主要政策内容包括:在欧洲和俄罗斯方向上,推动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不断增进西方在欧洲的势力范围;在中美关系上,以接触为对华政策基底,试图以经济自由化谋求中国走向政治自由化,实现和平演变;在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关系中,抓住机会,推行颜色革命甚或“政权更迭”,因而不时异变为黩武干涉主义。
在美俄关系中,自克林顿政府开始,美国便力推北约和欧盟的双东扩,挤压俄罗斯的战略安全空间,在俄推行美式自由民主模式也是美国的俄罗斯政策的重要内容,曾有美驻俄大使直言其使命之一是在俄罗斯“推广民主”。[注] Michael McFaul, “Moscow’s Choice,” Foreign Affairs , November/December 2014, p.170.美国还在俄周边大力煽动“颜色革命”,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乌克兰的“橙色革命”。正如米尔斯海默所言,尽管自由霸权主义很难在中国、俄罗斯等大国身上奏效,尽管美国不大可能对一个大国使用武力来保护人权,或推动政权更迭,但美国采取的干涉方式不少,如将人权与援助、国际组织成员国地位、贸易关系等挂钩,克林顿一度将人权与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便是典型例子。[注] John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y , pp.162-163.
对于中小国家,因其缺乏足够的军事威慑能力,政权更迭被认为军事成本较低、政治收益较高,往往成为美国推行社会改造工程的对象。因而,克林顿政府对海地、波黑、前南联盟科索沃问题进行了强势的军事干涉。“9·11”袭击后,小布什政府在阿富汗、伊拉克暴力推行“自由议程”,其初衷是将这些国家打造成“民主国家”,不仅可以扶植亲美政府,还有利于在防扩散和反恐等领域助美国一臂之力。尽管美国领导人对彻底改变上述几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充满信心,然而事实无情,美国的干涉在大中东地区带来的不是稳定的民主与繁荣,而是贫苦、暴力与极端主义,美国也深陷泥潭,脱身之日遥遥无期。
第一,特朗普政府对拉美的政策高度强调意识形态性,反映了其对外政策的自由霸权主义内在本质。特朗普政府认为,拉美民主国家之间以共同价值观与经济利益为纽带,会“减少威胁共同安全的暴力活动、毒品走私与非法移民”,也会“限制对手利用拉美邻国领土开展活动的机会”。相反,古巴和委内瑞拉两国政府则被认为“固守过时的左翼威权模式”,两国人民“持续遭遇失败之苦”。因此,美国政府的政策会“孤立那些不负责任的政府”,“期待古巴和委内瑞拉人民享有自由、共同繁荣之利的日子”,“支持西半球其他自由国家促进这项共同事业”。[注]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2017, p.51.特朗普关于古巴政策的总统备忘录表明,在古巴“改善人权”“促进民主”是美政府重要的政策宗旨,[注] National Security Presidential Memorandum NSPM-5 , “Strengthening the Poli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oward Cuba,” Federal Register , Vol. 82, No. 202, October 20, 2017, pp.48875-48878.美国要加强遏制古巴的力度,支持古巴国内的自由化势力。美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博尔顿将古巴、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称为拉美“暴政三套车”的提法和对抗姿态,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指标。2019年伊始,委内瑞拉问题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话题。美国拒绝承认马杜罗新任期的合法性,针对委的经济、金融和贸易制裁更加收紧。1月11日,博尔顿发表声明,称特朗普政府“将继续运用美国经济和外交力量全力施压,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摆脱当前的宪政危机”。[注] The White House,“Statement from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mbassador John Bolton on Venezuela,” January 11,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national-security-advisor-ambassador-john-bolton-venezuela/. (上网时间:2019年1月27日) 1月23日,委国民大会主席瓜伊多宣布自任“临时总统”,特朗普第一时间予以外交承认,承诺继续以经济和外交手段施压马杜罗,同时声称“不排除任何选择”,施加军事压力。随着事态的发展,美国不断加码对委军方和其他高官的制裁,特朗普、彭斯和其他高层官员不断接触包括瓜伊多在内的反对派人物;哥伦比亚总统访美时,与特朗普会谈的话题紧紧围绕委内瑞拉问题展开。2019年3月29日,博尔顿就域外国家在委内瑞拉“建立或扩展”军事存在发表谴责声明,称“此类挑衅行为”为“国际和平与地区安全的直接威胁”,将“捍卫、保护美国利益”。[注] “Statement by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Ambassador John Bolton on Venezuela,”March 29,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statement-national-security-advisor-ambassador-john-bolton-venezuela-2/. (上网时间:2019年4月2日) 4月10日,彭斯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发言强调“马杜罗必须下台”;[注] Mike Pence, “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n the Crisis in Venezuela,”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New York, April 10, 2019. 4月11~15日,国务卿蓬佩奥展开南美四国(智利、巴拉圭、秘鲁、哥伦比亚)之旅,进一步在外交上孤立委内瑞拉,美其名曰推动委内瑞拉实现“合乎宪法的和平权力交接”。[注] Michael R. Pompeo, “Seizing the Opportunity for Freedom in the Americas,” April 12, 2019,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9/04/291096.htm.(上网时间:2019年4月16日) 智利等国有关不支持军事干涉委内瑞拉的表态暗示,强制性外交正在美委关系中上演;5月1日瓜伊多未遂政变后,蓬佩奥有关“军事行动是可能的”的表态,意味着美国推进政权更迭的姿态更加强化。[注] Michael R. Pompeo, “Interview With Maria Bartiromo of Mornings With Maria on Fox Business Network,” May 1, 2019, https://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9/05/291429.htm .(上网时间:2019年5月2日)
第三,特朗普对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模式的反思是他转向霸权护持优先、降低海外用兵规模与成本的催化因素。根据特朗普的说法,截至2018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干涉行动已耗费了7万亿美元,但成本与收益极不对等。[注]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Secretary General Stoltenberg of NATO Before Bilateral Meeting”, May 17, 2018. 出于对“十字军主义”超低性价比的失望,特朗普试图回归美国外交传统中“榜样主义”,认为美国在海外促进民主扩展的最好方法是以身作则,为全世界“树立榜样”,让其他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美国成功经验的教化。如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言,“我们不寻求将美国的生活方式强加于任何人,而是让其成为所有人效仿的榜样”。[注] Donald Trump, “Inaugural Address,” January 20, 2017. 在“榜样主义者”看来,美国应该明智地置身于国际政治纷争之外,在把自己打造为自由的庇护所的同时,不应干涉海外的军事冲突。2018年12月,特朗普不顾强大的政治压力,决定停止军事干涉叙利亚、大规模削减派驻阿富汗美军,尽管这些决定能否落实尚未可知,但的确表明了其战略收缩的倾向。不过,特朗普的安全战略明确要求“在中东地区保持必要的军事存在”,一方面“保护美国和盟友免遭恐怖袭击”,另一方面“维持有利的地区均势”,[注]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2017, pp. 49-50.因此不能将必要的收缩夸大为美国不再重视中东的战略割舍。
第三,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亦颇具自由霸权主义色彩。从自由主义层面看,特朗普政府认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具有“专制体制”与“自由社会”之争的性质,中国试图塑造的世界“与美国价值观和利益格格不入”,美国对华政策过去40年的基本理念是“支持中国崛起、支持中国融入战后国际秩序会促使其走向自由化”。但中国道路越走越有特色,离美国的期待越来越远,令华盛顿失望至极。近期,美国国务院官员甚至提出所谓中美“文明冲突论”,[注] Joel Gehrk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Examiner , April 30, 2019,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defense-national-security/state-department-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with-china.(上网时间:2019年5月5日)可以说是美国展开与中国意识形态竞争的最新发展。从霸权护持层面看,美国将中国定位为“修正主义大国”,批评中国追求“权力扩张”“军事现代化”“推广威权体制”,指责中国“谋求将美国逐出印太地区,推广其国家驱动型经济模式,重塑地区秩序以于己有利”。[注]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2017, p. 25.由此可以看出,自由霸权主义的思想依然贯穿于特朗普的对华战略之中,而发起对华贸易战等具有“特朗普特色”的政策举措,更多地是实施其战略的新手段。
第一,推广自由民主被视为美国“生死攸关利益”的必然要求。小布什总统宣称美国的政策是“追求、支持民主运动和民主制度在所有国家、所有文化中的生长,终极目标是终结世界上的暴政”。小布什下达伊拉克战争的作战命令时的措辞是“为了世界和平,为了伊拉克人民的利益与自由”,[注] 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 , London: Virgin Books, 2010, pp.396, 223.自由主义情绪溢于言表。奥巴马也认为,“世界正经历着深远的政治变革,美国要发挥有效的领导作用,就必须在国内践行我们的价值观,同时在海外促进普世价值”,他强调说,“对美国安全的众多威胁便来自于若干威权政府反对民主力量的行动”。[注]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2015, p. 19.
第二,“强制性外交”(Coercive Diplomacy)是自由霸权主义的基本实操手段,即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条轨道上推进外部干涉或政权更迭的准备工作。[注] Condoleezza Rice, No Higher Honor :A Memoir of My Years in Washington , 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1, p.172.在美国主导北约对科索沃战争的干涉中,克林顿以充分的北约军事准备为后盾,向米洛舍维奇进行外交施压,但在干涉主义与民族主义两种政治逻辑的影响下,双方立场差异巨大,北约空袭、战后驻军科索沃成为必然。[注] 比尔·克林顿著,李公昭等译:《我的生活》,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909~912页。 在伊拉克战争中,外交上美国致力于“与一些国家组成联合阵线,明确萨达姆对国际义务的挑战是不可接受的”;军事上则“研究可靠的军事方案,以便在萨达姆拒绝履行国际义务的情况下加以实施”。外交和军事两方面起初可以平行推进,但随着军事选择日益明显,二者合流于军事行动。[注] 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 , p.230.“强制性外交”的本质是政权更迭,即康迪·赖斯所说的“促进善治民主国家数量的增长”。[注] Condoleezza Rice, No Higher Honor :A Memoir of My Years in Washington , p.425.
在河湖周边区,结合平原区造林,在城市河道两侧50~100 m范围内,按照乔灌草立体配置模式,建设河滨植物过滤带,进一步过滤、净化入河水质。
二、特朗普对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
特朗普前任们的自由霸权主义涉及对武力的使用,消耗了大量的实力资源。有资料表明,1990~2018年间,美国因为海外冲突、潜在冲突或出于其他目的而在外国部署武力的频度,比1798~1989年近200年间高了6倍。[注] Barbara Salazar Torreon and Sofia Plagakis, “Instances of Use of United States Armed Forces Abroad, 1798-2018,”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Report, R42738 version 23, Washington, DC, December, 2018.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当今国际关系中的实力分配格局已进入告别“单极时刻”的进程,国际政治环境条件开始向制约美国自由霸权主义的方向发展。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中对武力的使用主要是继承下来的旧战事,还没有开辟新战场。包括米尔斯海默在内的学者们都预判特朗普有可能摒弃自由霸权主义,转而采纳更加注重维护美国实力优势的大战略,减少自由国际主义承诺,降低美国霸权护持的海外成本。[注] John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y , p. 6.
第二,特朗普利用美国的经济技术实力及其在国际贸易相互依赖体系中的不对称地位追求公平贸易的政策,看似经济孤立主义,实质上是以退为进的策略调整,其目的依然是为了维护美国实力地位,护持美国霸权。美国国内历来存在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两种主张。自由贸易论者认为,贸易的扩展有利于美国消费者、美国经济和美国外交,同时为世界带来经济增长机遇;推动自由贸易的最优方法是通过世贸组织推进多边贸易议程,继而是继续追求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安排。公平贸易论者认为,无节制的贸易扩展不仅会使进口竞争行业工人面临大的失业风险,也会变相鼓励进口不符合美国劳动和环境政策标准的产品。因此,公平贸易要求管控贸易增长以实现社会代价最小化,不主张通过多边或单边措施实施强有力的贸易规则,减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进程,即便牺牲贸易增长及其带来的经济收益,也在所不惜。[注] Daniel W. Drezner, US Trade Strategy :Free versus Fair , New York: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2006, p.2.特朗普有关“公平贸易”的决策理念无疑反映了这种逻辑。他坚信,“不公平贸易实践”是美国贸易逆差的罪魁祸首,造成2018年高达8786.8亿美元的逆差,[注] 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转引自中国商务部:《2018年12月美国贸易简讯》,https://countryreport.mofcom.gov.cn/new/view110209.asp?news_id=63517.(上网时间:2019年5月6日) 导致美国经济失血和就业机会流失。为逆转这种形势,夯实美国经济基础,特朗普贸易政策议程的头号支柱便是以经济安全支撑国家安全,强调美国国内经济繁荣是海外权势和国际影响的必要条件,因此不时以“退”相挟,致力于以公平之名重新谈判多边、双边贸易协定,或推动世贸组织改革。特朗普视为大功一件的《美墨加协定》,为美国农业和制造业“大大地打开了市场”,减少了针对美国的贸易壁垒,也为美国的知识产权拿到了更多更好的保护。[注]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Has Forged New Trade Agreements to Revitalize American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president-donald-j-trump-forged-new-trade-agreements-revitalize-american-industry/. (上网时间:2019年5月6日) 可见,公平贸易之说实质上是为美国争取更有利于本国出口的贸易关系服务的,旨在护持美国霸权的经济基础。
实际上,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依然将促进民主价值观作为主要任务之一,意识形态色彩浓厚,充分体现了特朗普对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性。根据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第一”理念下的执政任务包括复兴美国经济、重振美国军力、保卫美国国界、保护美国主权、促进美国价值观。[注]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2017, p. I.这五项任务的基底无疑是巩固美国实力优势,护持美国霸权,扩展自由主义价值观,完全符合自由霸权主义的内涵。尽管特朗普不时表态他不会在对外政策中过度看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但另一方面他又坚称会“动用外交、制裁和其他工具孤立那些威胁美国利益、背离美国价值观的国家与领导人”。[注] 同上,p. 42. 用白宫的解读说,“促进人权是‘美国第一’愿景的基本要素”,特朗普维护的国家主权也必然是“尊重人权的主权”。[注] The White House, “Promoting Human Rights Is Essential to an ‘America First’ Vision”, https://www.whitehouse.gov/articles/promoting-human-rights-essential-america-first-vision-2/. (上网时间:2019年4月27日) 换言之,不尊重人权的国家,其主权不可能得到美国的尊重,因此不能排除类似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成为自由霸权主义新战场的可能性,因为美国在西半球拥有单极优势,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又具有如此显著的自由主义傲慢情绪。总体看来,特朗普对自由霸权主义的继承性主要在于其对外政策的意识形态性,这在以下几个案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稀土矿非法开采、乱采滥挖现象,不仅严重扰乱了矿产资源开发秩序,还由于开采技术含量低、工艺落后、采富弃贫,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土壤污染、河道淤塞、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1-3]。因此,加强稀土矿监管、保护生态环境越来越受到政府部门的重视。
花粒期是从抽雄开花到成熟,包括雄穗开花散粉、雌穗吐丝、受精及籽粒形成到成熟的过程。这一时期是玉米产量和质量形成的关键时期,每一个环节都会影响到玉米的产量和质量。雄穗抽出到开花的时间因品种而异,气温、水分也有影响,雄穗抽出后2-5天开始开花散粉。每个雄穗开花时间的长短因品种、雄穗和长短、分枝多少、温度高低而有所不同,一般5-6天,天阴可达7-8天。当天气晴朗时,9-10时开花最多,散粉也最多。一天中遇阴雨间断,雨后还是会开花散粉。
第二,特朗普政府对俄罗斯、伊朗的政策具有显著的自由霸权主义色彩。特朗普的对俄政策基于俄罗斯是美国的军事竞争对手和世界秩序挑战者的战略定位。美继续以乌克兰危机为支点,深入黑海,抵近俄罗斯进行军演施压,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边界,扩展欧洲与北约的势力范围。特朗普对伊朗的政策一反奥巴马的温和路线,呈现出更加强硬的自由霸权主义作风。在特朗普眼里,伊朗是“流氓国家”、“野蛮对待本国人民”的“独裁体制”和“世界头号支持恐怖主义国家”,认为伊朗利用地区动荡局势,通过“伙伴与代理人、武器扩散、资金支持”等方式扩张势力,“固化地区暴力”,是中东乱局的主要源头之一。特朗普的中东政策有三大目标,一是防止中东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或滋生温床,二是避免任何敌视美国的国家支配中东,三是中东成为维护全球能源体系稳定的贡献者。伊朗被认为是在这三个目标方向上构成了对美国全方位的挑战。特朗普的伊朗政策指针是“拒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和“抵消伊朗的恶性影响”。[注]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2017, p.2; p.26; p.48; p.49.退出伊核协议,全面恢复对伊制裁,将伊朗石油出口压到零,将伊斯兰革命卫队列为外国恐怖组织,支持伊朗国内的民众抗议运动,这些是特朗普对伊朗政策的主要手段,其用意在于削弱伊朗的经济基础,催化伊朗国内的反对意志,终极目标依然是政权更迭。
审视自由霸权主义的政策实践,有两点值得特别关注。
三、特朗普对自由霸权主义的调整
特朗普的自由霸权主义实践既有继承性,也确有一定的调整,最主要的变化便是“霸权护持”的考虑优先于“推广民主”的野心,表现为强调经济安全,诉诸公平贸易以止血贸易赤字,寻求降低海外使用武力规模,维护美国实力优势。对于特朗普对自由霸权主义的这种调整,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在一些学者看来,特朗普的调整表现出了偏离自由霸权战略的决策倾向。美国资深国际关系学者巴里·珀森便给特朗普的大战略贴上了“非自由霸权主义”的标签,认为特朗普一方面继续寻求维护美国的实力优势地位,维持美国的全球军事存在和主要地区安全仲裁者角色;另一方面不再坚定地致力于推广自由价值观,也不愿承担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成本。[注] Barry Posen, “The Rise of Illiberal Hegemony: Trump’s Surprising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 March/April, 2018, p.20.但特朗普这些看似背离自由霸权主义传统的政策异变,可以理解为是以退为进的自由霸权主义。
(3)西特简化法和北京水电勘察设计处利用砂土相对密实度对砂土液化的判别结果表明,当排岩厚度超过5 m时,各种水位埋深的尾矿砂都不会发生液化。这说明排岩增加了尾矿砂的上覆有效应力,加速了尾砂的排水固结,提高了尾砂的相对密度,增强了尾砂的抗液化性能。所以在废弃尾矿库上排岩是有利于尾矿库稳定的。但必须注意尾砂层本身的承载强度,通过计算确定上覆排岩厚度,否则可能发生剪切破坏而失稳。
观察两组患者治疗效果,分为显效、有效、无效三个等级,患者肌力及神经功能基本恢复正常为显效;患者肌力及神经功能有所改善为有效;患者肌力及神经功能无变化为无效。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有学者认为它标志着“单极时刻”的终结。[注] Amitav Acharya, The End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 , Cambridge: Polity, 2014.随着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衰弱,奥巴马对武力的使用总体上比小布什更为审慎,但他利用“阿拉伯之春”,在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推行自由主义干涉行动,亦是典型的自由霸权主义行为。譬如在是否武力干涉利比亚问题上,时任美防长盖茨明确反对,认为“利比亚的国内政局不是美国生死攸关的国家利益”,他坚决反对“美国在十年时间里进攻第三个穆斯林国家,推行政权更迭”。[注] Robert M.Gates, Duty :Memoirs of a Secretary at War , New York: Alfred A. Knopf,2014, pp.511-512.然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等人以“保护的责任”之名强烈主张军事干涉,[注] Hillary Clinton, Hard Choices ,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Paperbacks, 2015, p.302.奥巴马决定有限使用武力,美国主导空中打击,协助反叛力量,“将利比亚从几十年之久的独裁体制下解放出来”,[注] The White House,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NATO Secretary General Anders Rasmussen After Bilateral Meeting”, May 31, 2013, https://obamawhitehouse.archives.gov/the-press-office/2013/05/31/remarks-president-obama-and-nato-secretary-general-anders-rasmussen-afte. (上网时间:2019年4月29日) 创造了自由霸权主义的“利比亚模式”。
第一,特朗普关于美国经济安全面临挑战的战略判断是霸权护持优先的经济动因。特朗普突出强调“经济安全也是国家安全”的主张,认为美国的成功滋生了国内的自满情绪,出现了诸如美国权势不容挑战、自动持续的看法,美国的优势被视为理所当然,而“其他国家却坚定地推行长期规划挑战美国”。其结果,“美国原地踏步,其他国家却一直利用美国协建的国际制度谋利,它们补贴自己的产业,强制技术转移,扭曲市场,诸如此类的行为挑战了美国的经济安全。”[注]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2017, p. 2.因此,对美国实力优势的忧虑促成了霸权护持优先的调整,夯实、提升美国的经济优势,谋求再工业化成为特朗普关注的重要政策议题。
第一,特朗普外交上的一大变化是多边主义倾向明显淡化,对承担国际领导的意愿不强,动辄退出或威胁退出各种国际多边机制。但实际上,特朗普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有7处提到“多边”一词,只比奥巴马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少1次;47处提到“领导”或“领导力”,他在报告卷首部分更明确讲在他的领导下,“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再次发挥领导作用,面对挑战勇往直前,毫不退缩,千方百计促进全体美国人民的安全与富足”。应该说,特朗普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态度是承认其“依然服务于美国利益”,但“必须改革”。例如对于世贸组织,他认为必须纠正其体系中“选择性遵守规则和协定”的行为,推进“基于公平、对等、诚实遵守规则的经济关系”。另外,倘若一个国际组织得到了美国远超其他国家的支持,特朗普希望美国“对该组织的方向与行动具有对等相称的影响力”。[注]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 2017, pp.I,17,40.特朗普对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这种政策,表明他依然有意愿承担国际领导责任,但比前任们更加强调权责对等,仍然具有典型的自由霸权主义特性。
第二,特朗普对北约的态度被视为另一个重大外交改变。2019年哈佛大学一份题为《北约七十年》的报告披露,特朗普在北约内部被广泛视为该组织面临的“单一最大挑战”,因为他不愿在北约发挥“坚定可靠的美国领导力”。[注] Douglas Lute, Nicholas Burns, “NATO at Seventy:An Alliance in Crisis,” report by Project on Europe and the Transatlantic Relationship,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February 2019, p.13. 但这种看法缺乏有力的事实支撑,即便特朗普在口头上多次轻慢北约,不时称之为“过时”之物,但特朗普仍反复重申美国的承诺。他推动其他成员国提高军事开支,减轻美国的联盟负担,目的就在于让北约更好更有效地服务于美国与西方的霸权护持。另外,他也推动北约盟友集体加入打击“伊斯兰国”反恐行动。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就曾充分肯定特朗普“对北约的承诺和在责任分担问题上展示的领导力”。[注] The White House,“Remarks by President Trump and NATO Secretary General Jens Stoltenberg Before Expanded Bilateral Meeting,” April 2, 2019,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s-statements/remarks-president-trump-nato-secretary-general-jens-stoltenberg-expanded-bilateral-meeting/(上网时间:2019年4月28日)
结语:关于自由霸权主义的未来影响
自由霸权主义经过近30年的发展,已成为美国大战略的遗传基因,对美国外交行为影响巨大,以大同小异的表现贯穿冷战后共和、民主两党四位总统的对外政策,未来将继续对美国外交产生根本性的影响。自由霸权主义之所以能超越党派之别,成为冷战后几任总统的外交大战略,一是全球实力分配结构具有单极特征,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无须过多担心来自其他大国的有力制约,享有较为充分的行动自由;[注] John Mearsheimer, The Great Delusion :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y , p.218.二是美国拥有优越的地缘位置,用沃尔特的话说,美国“在西半球没有威胁,又坐拥两洋的保护”,因而可以远赴海外进行干涉,本土安全无虞;[注] Stephen Walt, The Hell of Good Intentions :America ’s Foreign Policy Elite and the Decline of US Primacy , p.xi.三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建制派精英们对扩展美国式自由民主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具有高度共识,通过夸大国际威胁、掩盖政权更迭成本、鼓吹安全与道德收益等手段,诱导民众支持。
1852年Rokitanksy首次提出该学说[1],认为由于血管内的局部凝血机制亢进形成血栓,增生的血管细胞将凝集在冠状动脉壁上的血栓覆盖,成为冠状动脉粥样斑块的一部分。血小板的聚集过程中释放的一些前列腺环过氧化物、激素、多肽、血栓素等物质最终形成粥样硬化病变。
毫无疑问,在上述三因素中,第二点是常量,第一、第三点是变量,且第一点会对第三点中的“可能性”判断产生直接影响,因此,考察自由霸权主义的未来影响,最需要、最应该关注的便是国际力量格局的发展变化。显然,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中国崛起势头不减,新兴国家整体力量持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更趋平衡,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国际秩序的演化持续推进,美国独霸的单极格局已经根本改变,不再享有“单极时刻”的战略优势。特朗普对自由霸权主义的调整,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这种格局变化的反映。可以预计,在非单极环境下,自由霸权主义会更多地受制于推广民主的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之间的挣扎,在政策手段的选择上更加审慎,特朗普以极限经济制裁为手段,谋求伊朗的政权更迭,或许代表了这种趋势。
国外对修建过鱼设施的共识度高、起步早,技术较为成熟。如美国在哥伦比亚河干支流修建了16座鱼道,成功地解决了鲑科鱼类的洄游问题。国内关于修建过鱼设施仍存争议,有学者认为,过鱼对象主要是为了解决上溯繁殖的鱼类洄游问题,葛洲坝工程修建后,已没有必须上溯繁殖的洄游性鱼类。但从遗传多样性保护层面来看,阻隔会影响坝上、坝下种群的基因交流,造成种群的遗传分化,加剧物种的濒危,建造过鱼设施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
当然,也要看到,美国在西半球依然具有地区霸权地位,门罗主义和罗斯福推论的历史遗产影响仍在,因此,特朗普和未来的美国领导人可能会继续伺机在拉美地区奉行自由霸权主义,但前车之鉴犹在,很难再复制阿富汗、伊拉克式的超大规模、超高成本、超长时间的社会改造模式,特朗普政府在委内瑞拉扶植代理人、策反军队与强力部门领导人的操作,也可能成为自由霸权主义的常规选择,但使用武力强加政权更迭无疑将继续是美国的政策工具。○
[作者介绍] 李永成,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主要研究国际关系理论与中美关系。
* 本文是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项目“国际合作的基本学理与中美合作关系构建”(批准号:YY19ZZB024)的部分成果。
(责任编辑:王文峰)
标签:自由霸权主义论文; 米尔斯海默论文; 特朗普论文; 美国外交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北京外国语大学公共外交研究中心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