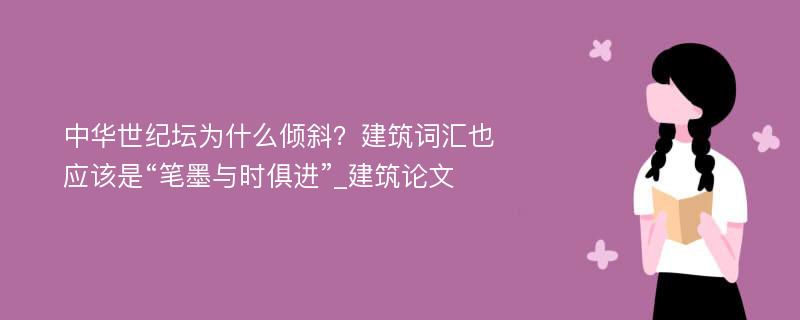
“中华世纪坛”为什么倾斜?——建筑语汇也要“笔墨当随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语汇论文,也要论文,笔墨论文,中华论文,世纪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建立“中华世纪坛”(以下简称“世纪坛”)是以表现中华民族几千年悠久历史文化和光辉未来为主题的。在北京,“千年创意”最早于1994年公诸于世。当时设想建立“中华世纪墙”来作为千年之交的纪念性建筑。然而“墙”本是一种阻断性建筑,人们到此须停步“回首”。形式本身缺乏纵深感和空间开放感,事实上古今世界一些著名的纪念墙虽主题庄严,但沉重多于喜悦。而取“坛”立意,不仅获得了空间纵深,也创造了时间向度。北京作为历朝都城,筑坛祭祀日月天地、江山社稷,因而“坛”不仅具有表达国家意志的符号功能,而且具备表达民族悠久文化历史之传承的符号功能;而今日筑坛,显然已实际超越祭祀原义。从“世纪坛”主体建筑看,它不仅“祭祀”着已铸在青铜甬道上的五千年历史,凝聚着对未来的憧憬,而且还用新的建筑语汇和先进的科学技术演绎着对社会与自然、时空与环境的认识与理解。
1
这是一篇命题文章。确定了主题只是解决了“做什么”,而“怎么做”才是把建筑作为艺术真正见出风采的地方。经过邀标最终评选出的方案是由余立博士主持设计的。他要尝试在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情趣有了很大改变的情况下,用现代人的心绪去演绎传统,抑或用古典的风格来展示现代(注:参见余立:“‘中华世纪坛’的建筑形象语言”,刊于《建筑学报》1999年第6期第16-19页。)。历经反复孕育的痛苦,感悟天坛的建筑语言强烈而神秘的民族气息,设计师深深执著于如何用现代建筑语汇去表达悠久民族文化历史的精髓(注:说到“执著”,雕塑家钱绍武曾向陷于深沉构思的余立讲述了四个寓言: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女娲补天。这四个在中国流传极广的寓言展现的是同一种民族精神:执著。)。作为建筑,“世纪坛”的设计必须要体现出对民族文化历史的承载。它本质上是对其精神内在气质的承载,而不是对个别外在的形式或零部件的表面铺陈。“世纪坛”的作者认为,中国传统建筑的形象特征不仅仅指那些具体的外露建筑构件(如屋顶、柱子、墙体等),还应包括构图原则、材料的使用规律、构件的连接方式等。这些才是中国传统建筑形象特征最本质的内容(注:参见余立:“创造建筑形象的制约因素”,刊于《建筑学报》1996年第9期第37-39页。)。关于传统形式的继承与发展一直是个争论不休因而还将一直争论下去的问题。传统形式的形成与传统的建造工艺及材料有直接的密切关系,外在形式就是本质内容的直接体现。这是实实在在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因此它的形式是“真实”的,否则它的形式就是“虚假”的。虽然这在建筑学界早就有人点拨,但在城市建设的许多实践中却屡见败笔。“模仿秀”不仅上演于影视大众传媒,也被遗憾地凝固在城市大街两旁。一种风格样式或一个明星人物一旦被认可,就要不论洋古,群起效尤,拿来就是。喜爱模仿和不得不模仿交织在一起,反映了我们相当一部分国民的一种心态,它有着深厚的基础,尽管不全是消极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感到搬用外在的传统样式或构件有悖于现代技术应赋予建筑形象的时代感,那么就要冒一点风险才会不去搬用它。这就是“世纪坛”的作者今天做给我们的样子。
实际上,“世纪坛”设计的根基是传统的。“坛”这个名字本身就为寻找适宜的建筑语汇提供了明显的线索。天坛从寰丘、丹陛桥到祈年殿的构成形式被用作“世纪坛”的语言构架。三层基座,三级台阶,坐北朝南,中轴对称……当然,好似音乐的变奏,每个对应部分都根据需要被不同程度不同方式地予以变形,在变形中依然保持每个部分的地位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比如说,在东西仅宽90米、南北总长450米的狭长地带的条件限制下,依次通过圣火广场的下沉、青铜甬道的平直和主体建筑的高耸这种“凹、平、凸”的变化体现出中国建筑特有的韵律感(从主题创意上讲,表达的是沉思、追忆、升华的心理历程),令人联想起从天安门广场到景山或者南京中山陵的类似的匠意。人们从深层的建筑语言结构中可以体味到这座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的渊源关系。
最能直接把“世纪坛”与中国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的就是“坛”的主体建筑造型。它启迪于庄重和谐的天坛寰丘。但是与原型不同的是,它是由静止的回廊和转动的坛面组成,而且坛体的上顶面有19.4度的倾斜,再加上27米长的钛合金指针斜向天空,更强化了平衡被颠覆的不稳定感。这种对传统的大胆变奏,说来也“传统”,缘于一次灵感。“坛”的作者希望它“动”起来。他并不是想颠覆“凝固的音乐”这一建筑定义,而是执著于对主题创意的“上下求索”以及对民族传统文化理念的感悟。朗朗乾坤,大至宇宙,小至原子,无不遵循着一个基本的物理运动形式:转动,而且最自然又最科学的运动就是圆周运动。在先秦老子的道家学说思想中,对于生命循环不息、永恒运动的特征用了“周行而不殆”的叙述来作为宇宙天地的法则,而且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精辟地表述出中国人对宇宙,对时空的独特认识。“中华世纪坛”以“一条主线,两大精神,三个和谐”为其创意宗旨(注:见《“中华世纪坛”创意》,朱相远撰稿,“中华世纪坛”组委会1998年编辑出版。)。其中这“两大精神”便是《易经》中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人们用“乾”和“坤”来象征这两个精神传统。“世纪坛”主体建筑上部的47米直径的旋转体可以被看作是表达这类理念的建筑语汇之一。不可否认,“世纪坛”作者最初只是想寻找和创造新的建筑语汇来表现“动”与“静”的对立与转换以及这种语汇和建筑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但是当这个3200吨重的坛体真的转动起来时,原来建筑学意义上的进步探索刹那间升华为对一种古老哲学宇宙观的现代诠释。最早给这一动一静的“新生儿”起名“乾”“坤”的不是设计者余立本人,而是它们的“教父”,最初的创意人朱相远先生。然而“世纪坛”设计人对传统与现代的感悟以及对建筑语汇和建筑形式的新追求,使得作品内涵的这一表达得以完美实现。“动”赋予了“世纪坛”以灵魂,恰如其份地展现了乾坤天地。正所谓:著得一字,境界全出。
2
“世纪坛”作为世纪之交的纪念性建筑,在它一开始提上日程就受到国内外广泛关注。这种关注包含一种期待:它会怎样与众不同?今天人们看到,除了造型与众不同,坛体能够旋转是其新颖性的最主要标志。处于核心部分的旋转坛体不能用传统的静态方法进行设计和制作。像这样重载、倾斜、低速旋转的建筑物尚属国内外首创。那么在其设计、制作、安装和动力控制诸方面的科学技术难题是怎样解决的呢?
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第303研究所接受了这项挑战。他们对圆坛转动的关键技术问题进行了专题试验研究。其中包括:在不均衡重载下摩擦系数的变化对起动力矩的影响;变频器限流起动;多台电动机强迫同步运行时各台电动机之间负载分配和相互之间负载转移;重载低速驱动时所需功率等。经过多次试验与论证,专家们的一致意见是,方案可行,“世纪坛”肯定能转起来。
“世纪坛”的旋转部分是个外径为47米的斜截圆柱体,钢框架结构,外挂花岗岩,重三千余吨。转坛底部装有内外两圈96组滚轮,坐落在内外两圈环形轨道上。在外环的64组车组中,有32个主动车组,其中16个车组的滚轮同时用作摩擦驱动,集支撑驱动于一体。驱动电机就吊装在圆坛底盘下面。滚轮组中设有蝶形弹簧,在旋转过程中可以自动适应由于安装误差、焊接应力的缓慢释放、地面沉降等原因造成的轨道与旋转体底面之间间距的变化,蝶形弹簧同时起到抗震、消噪的作用。转坛的控制系统采用计算机位置、速度及电流闭环控制,设有光栅实时检测旋转圆坛的位置及速度。当圆坛起动时,控制系统通过监视各电动机的工作电流,自动调节,使各台工作的电动机(分两组共16台)负荷均衡。在转坛起动后,摩擦阻力矩减小,就可以根据实际所需驱动功率,自动减少工作电动机的台数;当负荷增大时,还可以根据情况自动增加工作电动机的台数。这种适当增加电动机总台数、减小单台电动机功率的做法,不仅可以减少电能消耗,而且减小了振动和噪音。在解决了大平面基准、中心定位、滚轮车组自适应以及控制系统等诸多技术难题之后,旋转圆坛可以按照预定值沿正、反两个方向以4到12小时一圈匀速或变速旋转(注:有关材料与数据参见“中华世纪坛旋转圆坛工程技术内容简介”,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第303研究所编。)。本着科学严谨的态度,303所等有关单位在转坛传动机构的设计、加工、安装和调试的各个阶段精心制作,使这个庞然大物的装调精度完全达到了设计要求。内外导轨实际平面度达到2毫米。96台车组的安装形整如一,使旋转过程没有因安装偏差而产生附加阻力;此外在驱动与控制系统方面又成功地进行过模拟试验,因此在对旋转体钢结构进行旋转试验时一次调试成功。这一“转”终于使“世纪坛”能够成为永恒。在转坛的试运行仪式上,专家对“世纪坛”旋转体的高科技特点的评价是,“用多轮支撑、多轮摩擦驱动大吨位、大尺寸、低速、又是偏重的坛体,这在国内外还是第一次”(注:有关材料与数据参见“中华世纪坛旋转圆坛工程技术内容简介”,中国航空工业第一集团公司第303研究所编。)。“中华世纪坛”旋转圆坛也由于其技术上的突出特点和重大突破,被国内相关的权威杂志评为1999年机械行业十大新闻之一。依靠科学技术的帮助,“世纪坛”实现了转动,实现了“动静相济”的构想。可以说,“世纪坛”由于转动而获得了它自身存在的方式。
3
在赋予了灵魂与动力之后,“中华世纪坛”以其独特的形态出现在世人面前。它的新颖造型体现出上文所述的科技工程手段与艺术构思之间、形式与内容之间的有机结合。作为纪念性建筑,它极具象征意义。“世纪坛”倾斜的坛面和指针在造型上很像中国古代的观测仪日晷。于是人们把建筑主体的造型解释成象征着日晷。它的作者说这纯属巧合(注:参见余立:“‘中华世纪坛’的建筑形象语言”,刊于《建筑学报》1999年第6期第16-19页。)。之所以那样造型是出于建筑设计自身内在关系相互制约的需要。依照作者的初衷,为了克服不利因素的限制,需要加大建筑构件的尺寸,但又不能向高发展,只有尽可能加大横向尺寸。按照作者计算,85米主体建筑的基座直径是现实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极限,而富于动感的旋转部分需要47米直径以便与基座形成和谐的尺度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不到30米的高度成了问题。如果让人们在350米外的距离从长安街北望,并且能够从梅地亚中心和军事博物馆之间的狭窄视界中“感受”“世纪坛”的高大雄伟,那么“世纪坛”很难满足这个要求。因为既不能为单纯拔高而破坏整体的比例关系,又不能在坛体上再加一个祈年殿或方尖碑。这时,“乾”的倾斜缓和了这种尴尬。它与“坤”形成角度,半向苍天,半向人间,雍容大度地展示出自身的风采,有效地吸引了远近视线,成为众望所归之处。用打破平衡的倾斜面来解决高度不够但又不能增加高度的矛盾,是环境的制约所使然。不过,“世纪坛”的作者并不满足于此。他让它倾斜依然是为了“动”。一个斜面的旋转要比平面的旋转从视觉效果上感觉强烈;惟其不够,再加上一个倾斜向上的指针,还不把它立在圆心。这样,通过指针的位移展现出的旋转效果就更强烈更直观。斜向天空的指针自然地把人们的视线再次向上引导,不仅多快好省地又一次增加了高度,还有力地强化了人与天空、人与自然的主题表达。设计师因地制宜,用倾斜的坛体和指针不仅增强了“乾”体的旋转效果,而且增加了“世纪坛”本身无法再增加的高度。由此看来,“世纪坛”的造型设计是出于对它自身尺度以及对它与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考虑。至于它的造型与日晷相像,可能实属偶然。
然而无独有偶的是,2000年4月在上海浦东世纪大道上树立起了一座巨大的、像日晷形状的景观雕塑《东方之光》。
由1000多根不锈钢管焊接而成,高约20米,倾斜的椭圆晷盘直径22米,扶摇斜上的晷针长40米,指向正北,与地面形成的夹角恰为上海所在的纬度31度14分。依照创意人与设计者的构思,《东方之光》采用中国古代的日晷为原型,可谓承袭传统,师出有名;然而设计者仲松在材料使用、灯光设置、体量与变形诸方面赋予日晷以当代的美学风格。比如说由于在材料技术和造型结构上的创新,这座50吨重、八层楼高的雕塑质感轻巧、玲珑剔透。在城市夜幕的灯光中“酷”而冷峻的太空色调明确地宣示着自身的高技术派风格。同时,庞大的日晷被设计成具有真正的利用阳光指示时间的功能,其准确度可以精确到“分钟”,从而更加强化了在世纪之交的重大时间主题。该作品无疑是现代都市公共艺术与科学技术相结合的成功之例,因而获得由上海市政府颁发的“上海浦东开放开发10周年精品项目”雕塑金奖(注:参见拙著:“公共艺术和公共精神的超越性——记仲松的城市环境雕塑《东方之光》”,刊于《雕塑》2000年第3期第30-31页。)。
《东方之光》的造型与“世纪坛”相比,在“似与不似之间”。然而问题不在于“世纪坛”启发于寰丘,《东方之光》启发于日晷或别的什么;问题在于,它们对古代传统原型的创造性运用不是仅仅表达对过去历史的纪念和追忆,而是面向未来,要赋予所在城市某种新的文化气质。正像北京不能停滞于对陈年老照片的无限追思那样,上海也不能沉溺于对三十年代所谓黄金时期的缠绵怀旧。城市雕塑和城市建筑要“帮助”自己的城市与人完成新旧世纪的转换与超越。在这一点上,两个作品可以说是异曲同工、南北呼应,它们都在造型、材料和技术上分别实现了自身的逻辑统一,并且去努力重塑新的文化环境,创造新的审美群体。
4
毫无疑问,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是“世纪坛”作者着重考虑的问题,而且建筑的时代特征也正是通过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来体现的。“世纪坛”场地狭窄,两边高楼“邻”立,这些因素显然具有消极性。建筑师必须考虑化制约因素为有利于展示特点的积极因素,利用所能提供的舞台上演最适宜上演的剧目。北京的市区今天不可能再有像天坛(272公顷)那么大的地方来供筑坛和建造相关设施。“世纪坛”占地面积只有4.5公顷。它不能像天坛那样用面积和围墙来把自己与世俗人间隔离;相反,它必须用亲和民主的态度与周围环境相互协调以求扩大自身的空间。在它的北面是玉渊潭公园茂密的树林,既可以映衬又可以生辉;在它的南面,坛的主体建筑通过青铜甬道的合理延展不仅使建筑形象完整地展示给长安街的行人;而且再向南顺着大道伸展,与北京西客站的标志性建筑共同形成了新的城市轴线关系。由于没有围墙的分隔,“世纪坛”通过“借景”扩大了本来不能再扩大的空间面积。与传统的“围墙意识”相比,这种“开放意识”显然是现代的。是环境的制约促使它走向开放,走向现代;而且,“世纪坛”的倾斜打破了四平八稳,很自然地弱化了那种帝王时代“祭坛”的正统威严的内涵。倾斜本来是出于建筑学自身的科学意义,但是从造型的艺术效果来看,“乾”“坤”的这种相倚相伴更具人间气息,蕴含了现代人的惬意感。为了支持这种说法,只需举出一个强有力的事实就够了:由于坛的主体能够转动,因此可以朝向四面八方。当它面向北方时,原来作为背景的大片丛林与绿地立刻就成了整个世纪坛建筑群的有机组成部分。因为它们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露天舞台的观众席。2000年的夏夜曾在这里举行过几场现代音乐演唱会。成千上万的人坐在开阔的草坪上,观赏着临时搭建的舞台上的精彩演出。而此时此刻面向北方的世纪坛主体建筑被四周射来的灯光照耀得晶莹透亮,它的耸入天际的时空探针放射出奇光异彩,整个坛体成为演出舞台的绝佳背景,呈现出与白天迥然不同的风采。慕名而来的一些国外演出界人士赞叹不已,说这是世界上最有特点的露天舞台。由于坛体的倾斜与转动,使得“世纪坛”无需“借景”就向四周扩大了自身的空间。因此可以有根据地说,“世纪坛”的作者运用新的建筑语汇不仅解决了由高度和面积等诸多不利因素所带来的矛盾,也为文明与复兴、历史与未来这类抽象意念的表达提供了相适宜的形象媒介。不仅如此,它自身的“灵活”以及对周围环境的“开放”也使本身超越了传统形态所赋予的单一固定的功能。比如说它对大众多元文化的那种亲和态度就足以证明:“世纪坛”的建筑语汇确实是人文的,是现代的。尽管它取名为“坛”以彰显自身的历史渊源,但是已今非昔比,换了人间。
“世纪坛”的时代特征通过它与周边环境的灵活相处而体现出来。在这一点上它与天坛又一次形成了对照。人们很快就能通过这种对照发现,二者之间在建筑理念上最为鲜明的对比就是对“人”与“天”的态度不同。天坛建筑群所运用的全部艺术手法都在于突出“天”的肃穆崇高,渲染“远人近天”的氛围。仅从对周边环境的关系来看,它就体现出这种时代特征。由于它占地面积广阔(东西长约1700米,南北长约1600米,合面积272万平方米,相当于紫禁城的三倍多),满园苍松古柏,静穆森严,高高筑起两重围墙。这种封闭状态已经营造出与世俗人间隔绝的带有隐邃神秘的色彩;唯此不够,为了强化这种气氛,筑起的内墙并不在外墙所围面积的正中,而是向东偏移;由寰丘和祈年殿所形成的中轴线也不在内墙所围的面积正中,同样也向东偏移。这样的两次偏移显出由寰丘和祈年殿所形成的纵轴线比整个天坛园区的中轴线向东偏移了200米,从而加长从天坛西门进来的距离。正如建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空间序列的丰富与延长使时间的因素得以充分发挥,从而在时空交汇中孕育和深化从环境中获得的感受(注:参见王世仁:“建筑艺术”,刊于《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Ⅱ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0页。)。至于蓝瓦攒尖的祈年殿耸入云天,空无一物的寰丘晶莹洁白,高出地面的丹陛桥宽阔平直,都使“远人近天”、“超凡人圣”的宗旨得到完美渲染。天坛建筑语汇的这种处理符合它的功能要求,也符合它的时代审美特征。意境的营造有赖于对空间环境的创造。我们从天坛建筑密度极低、绿化面积与建筑面积之比极高的“经营位置”中见出天坛意境创造的特点。
然而这里还要着重说明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坛并非自古以来就是这个样子,同样也是经历了发展变化。它在明朝初年建成时是作为天地坛(现存天坛基地平面的形状上圆下方——象征天圆地方——即形成于明初),与西侧的山川坛形成在中轴线两旁左右对称的态势。嘉靖年间恢复天地分祭,改天地坛为天坛,改山川坛为先农坛,在城北中轴线偏东的地方建地坛,与天坛南北对应(注:见萧默:《中国建筑艺术史》,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页。)。由于天坛西门正对着北京城中轴线,而且当时整个天坛仅在西墙开有二门,了解了这种历史沿革,也就理解了地坛—天坛纵轴何以东偏以及天坛内的祈年殿一寰丘纵轴何以显得东偏。孤立起来看,这种轴线的偏移好像有悖于均衡对称的传统法则,但却在总体的布局中统一于和谐。在天坛的历史上,根据时代要求作出的相应变革还不止于此。天坛的祈年殿前身为大享殿,原先在三重檐上铺设的琉璃瓦并非今天看到的这种颜色,而是分别为青色(象征天)、黄色(象征地)和绿色(象征万物)。清乾隆十七年(1752年)把三重檐都铺上了青一色,并改名为祈年殿(注:见萧默:《中国建筑艺术史》,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625页。)。这一重大改动想必符合当时的文化政治需求;就是用今天的审美眼光来看,这种三色归一的色彩改动也是很成功的。此外还有其它的例证表明,天坛今天的面貌是在变化的历史中逐步形成的,传统的体现就像“传统”这个词一样,是一个发展过程。被今人视为传统的建筑元素在古人那里也许正是一种打破传统的创新。以上列举有关天坛的两个例证,一个是“因地制宜”,一个是“因时制宜”,表明了古人也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来处理所面对的难题,厚“今”不薄古,去“改造”历史传统,创造出与所处时代相协调的建筑语汇。
从上述而言,有一点已经很清楚:建筑与环境的关系不单单是建筑学的技术问题;此外还有一点也应该很清楚:“环境”不仅仅是地理空间,还有人文环境与社会心理。像“中华世纪坛”这样作为千年跨世纪的标志物,包括设计者在内的人们对“环境”的考虑自然想到的是建筑与时代大环境的关系。“坛”的设计者确实想表现今天中华民族在崛起奋进的那种力量。用“转动”体现能量的聚集,体现自强不息;用“倾斜”展示转动的风采。并在打破传统平衡的同时建立起具有现代感的新和谐。为了建筑理念的实现,“世纪坛”的作者不仅从造型结构上而且在材料使用上都保持着内容和形式上的逻辑一致性,比如用玻璃栏杆而不是用汉白玉石栏杆以维护语汇选择的标准统一,这里面当然体现着作者的审美个性,然而正是这种现代追求使“中华世纪坛”作为建筑不仅与它周围的环境相协调,而且作为“千年世纪之交”的标志物与今天的时代特征相协调。“世纪坛”的根基是传统的,它的叙述方式是现代的。借用清代画家石涛的话讲,这就是“笔墨当随时代”。它或许能够解释“中华世纪坛”为什么要倾斜。
5
按照最初的宗旨,“中华世纪坛”应当是新旧世纪之交我们国人对历史的总结:它既要表现出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沧桑,又要蕴含着12亿炎黄子孙对新世纪的憧憬向往。它要体现和谐与奋进,还要体现人类与自然以及东方与西方的相融……它承载着众多的意义,因此对它的要求也就很多很多。有关部门不仅为此广泛征求了历史、文化、哲学、美学、雕塑、壁画、民族、建筑、规划、园林、灯光等各界数百名专家学者的意见和建议,还要在资金、技术、施工等诸多方面保障有力。作为建筑艺术,“世纪坛”已决非设计者一个人的孤芳自赏,它成为民族心气的象征、时代的标志、科技水平的显示。用建筑语汇为民族的想象力和时代感寻找一个答案,而且还要用当今最高的技术水平和最完美的艺术手法来予以完成。需要考虑的问题很多。美是难的。不过“世纪坛”的设计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职权范围:“建筑物被赋予的象征意义,特别是政治涵义一般都不是建筑师决定的。建筑师只不过是用建筑的语言来表达这些意义或涵义,类似电影导演把一个别人写的故事搬上银幕。”(注:参见余立:“‘中华世纪坛’的建筑形象语言”,刊于《建筑学报》1999年第6期第16-19页。)话说得对,但他有些谦虚了。因为,人们赋予“世纪坛”的只是各种意义,而建筑师要按照建筑学自身的原则和美的规律把它“创作”出来,所有的“意义”才有意义。建筑师用自己的逻辑语汇把自己的感觉讲述给今天的人们听,用形象来为观念辩护。为什么要辩护?辩护的又是什么观念?辩护是因为还存在着争议,是因为还没有被人人认可,是因为如果一旦被人人认可就有可能遭受被模仿的命运;至于观念,简单地说就是建筑与环境,包括人文环境与时代环境,之间的关系要和谐,建筑语汇要真实表达这种和谐。具体说到“中华世纪坛”,它与时代的和谐是通过用倾斜打破传统的平衡来实现的,是通过建筑语汇与材料技术的逻辑统一来实现的,是通过与我们的时代相称的科技手段来实现的;而且正是由于艺术与科技的完美结合,才使得“世纪坛”在永恒不止、周行不殆的运动中寻找到与时代变化并行不悖的平衡点即新的和谐。这永恒不止,闪烁着愚公移山的精神、精卫填海的风采;这周行不殆,显现出女娲补天的执著、夸父追日的气概。中华民族有过辉煌的历史,也遭受过深重的苦难。但她就像那只灿烂的凤凰,每次涅槃,都在熊熊烈焰中洗尽污浊,浴火重生。一个五千年民族在21世纪到来之际依然保持着这种生机与活力,那么就完全有理由对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和希望。“中华世纪坛”就是一个证明。它用永恒的运动证明着自身存在的价值,也因此超越自身的存在实体而再次表明,一个悠久民族并非仅靠追求物质生活的发达富有来维系其凝聚力,中国人不断需要精神上的追求和超越以获得对发展着的文化属性和变化着的时代属性的认同,惟其如此才能真正强大富有,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与众不同,才能从积极的方面实现人们一向所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全部内涵。“世纪坛”留给今人的,除了开宗明义就提到的那些意义之外,还应当包括所有这些观念和为之进行的辩护;至于它留给后人的,怎样才能学它而又不像它呢?答案依然是辩证的:像思想的那样去行动,像行动的那样去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