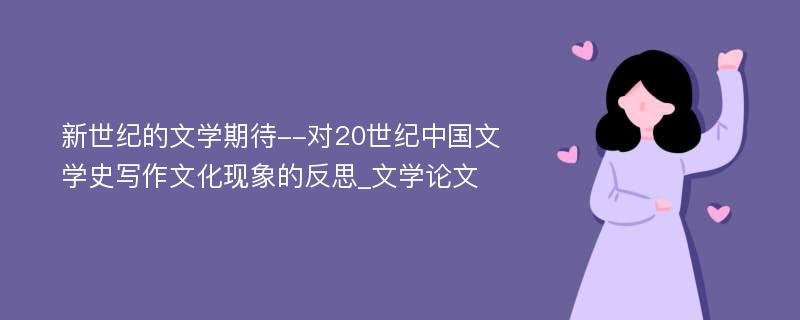
新世纪的文学期待——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文化现象反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世纪论文,现象论文,期待论文,世纪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 (2000)04—0094—07
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新话题了;但是,在今天文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中,它愈来愈呈现出不是单一理论或实践范畴的问题,而具有文化、历史、文学、文艺整体整合、更新、建构的意义。本文将文学史写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认识,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具体问题,并兼谈其学科的建设。 世纪之交, 我们反省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旨在对当下文学研究现状进行思考,并探索文学史未来的趋向。
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化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建设,直接与文学史的写作联系在一起。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问题,就是本学科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文学史写作肇始于本世纪初,1922年胡适的《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为最早的历史文本。此后,关于现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编著一发而不可收。据不完全统计,仅各类版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80 余年来就有200种之多。文学史问题是在学科建设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凸现的。历史记载了传统,同时又在不断重铸着传统。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既融合了一段特殊的文化历史语境,又直接反映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形成与建构。20世纪中国文学是在一个过渡和交汇的大文化情境中运作的,它与中国史学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引进有着直接的联系。中国传统文人的最高理想就是修史。为此,出现了蔚为壮观的各种体式的史书,如“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等;“编年体”的《左传》、《资治通鉴》等;“纪传体”的《史记》、《汉书》等,甚至还有“纪事本末体”的《左传纪事本末》、《通鉴纪事本末》等等。这些史书重在强调对历史的真实记载,即遵循“考信、实录”的原则标准。中国历史修撰成为传统文人毕生追求,他们以极大的热情,将修史的成绩作为自己学业有成的标志。清代学者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不仅开拓了中国史学理论的领域,而且使得历代修史有了新的史学理想,即“文章”亦史(列传)亦文,“文苑必致文采之迹”;强调传统史部之学与集部之学的沟通。历史内涵与外延的扩大,使得历史有了较大文化的包容性。
中国文学史的问世伴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连锁性的政治改革,伴随着中国社会由传统转向现代的历史进程。这时期西方新的自然科学发明和崭新的人文精神观念,带来了现代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大解放。文学史的写作也在“传教”的进来与“留学”出去的文化大交流的背景中应运而生。我们首先见到的两部《中国文学史》,均出自大学堂里学贯中西的国学大师之手,即南方东吴大学的黄摩人(字摩西)和北方京师大学堂的林传甲。前者摩西之作为学校国学课本,油印成讲义稿发给学生;后者林传甲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上“支那文学史”课程时受到启发,回国任教京师大学堂,也是由讲义而后编纂成书。显然,中国文学史的写作,一是中国源远流长的史学传统,一是文化交流中新学堂的教学急需。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在探讨中国文学史的编写原因时,很注意西方文化思想的影响、文学观念的变化而引发的中国文学史的新写作。固然这是重要因素之一,但是一种现象的出现,往往是观念与现实要求共同驱使。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与其说是文学史自身写作的探索,倒不如说是大学教材的不断更新和外国文学史的影响。20年代至3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形成雏形,其标志是王哲甫和朱自清新文学教学讲义的成型和出版。5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确定和建设,以教育部制定《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高等院校将其作为主干课程之一,王瑶、张毕来等新文学史讲义先后出版为标志。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恢复调整期,也首先从高校教材更新中传出信息,山东的田仲济、孙昌熙主编本,黄修己的中央电视大学教本,北京大学的钱理群等主编本,都是在这个阶段有所突破有所影响的文学史教材。90年代末,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进入重要的深入发展阶段,又是在高校面向21世纪强化素质教育的精神指引下,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洪子诚、陈思和率先尝试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教材更新,再次将文学史的写作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当然,本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教学化的写作,不可忽视世界性的文化语境,即中西文学史写作的互相影响[1]。 勃吕纳狄尔的《法国文学史教程》,朗松的《法国文学史》,丹麦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高尔基的《俄国文学史》,美国勃克维奇的《剑桥版美国文学史》,前苏联维霍采夫主编的《俄罗斯苏联文学史》,90年代美籍华人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中国大历史》等史书,对于中国文学史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写作,对于为适应大学教学不断更新重写的文学史,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作用。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原创性写作,由胡适、周作人、陈子展、朱自清等现代作家自觉的历史“实录”开始,受到潜移默化的传统文化中史学精神的熏染,并置身于世界文化交流之中,深受外国文学史影响。这些又都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中国文学史教学课程和教科书的需求相联系着。为此,中国现代文学史完成了自己从传统史学的蜕变,形成了多元现代文化交汇的独特话语和叙述方式。文化新传统的建立与其新问题的出现,总是结伴同行。显然,必须从多元文化语境中,探寻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形态(现象)的成因和问题。这段文学史的一切因与果,将不是孤立的纯文学、纯政治、纯道德评判的尺度可以解释的。
二、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话语与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记载了20世纪中国文学由传统走向现代的丰富历史原生态,也联系着百年来人们记忆的历史和不断重写的文学史。20年代的文学史家绝大多数是现代文化思想的传播者和建构者。作为本世纪第一批新文化新文学实践者和传播者的胡适、周作人、鲁迅、朱自清等现代作家,文学史写作是他们新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22年胡适为上海申报馆五十周年的纪念特刊撰写的《最近五十年中国文学》,有着浓重的学术文化总结的意味;1926年后鲁迅先生先后在厦门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作中国文学史课程讲义的一部分,后出版了《汉文学史纲要》;1929年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教授“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编写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讲义以及30年代初周作人应北平辅仁大学之邀所作的演讲稿《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等,都将现代中国文学置于文学史长河中考察其流变。这些史著出自大学课堂的新文学史讲稿,重在在文化历史的总结中描述文学的演进,具有理性色彩和学术规范性(纲要思路清晰);史家一般不作孤立的文学史评述和勾勒;著者表现出极其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自觉地参与了现代学术文化建设的重大工程。
30年代至8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成为文学研究者、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和研究课题,从而中国现代文学史完成了从一门必修课程到一个独立学科成熟的过程。大学的讲坛和现代中国的历史变革,独特的文化生存环境,逐渐形成了现代文学史思想观念等同文学话语,侧重文学教科书的规范性、系统性,以及密切联系现实的学科特点。第一部中国新文学史著《中国新文学运动史》(王哲甫)中“什么是新文学”的设问,引发出对新文学与旧文学的区别、发生经过、具体内容等的界定和辨析。随后,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和吴文祺《新文学概要》的史著,开始表现出现代文学史坚持社会思想的阶级论、唯物论的写作原则,仍注重历史系统性的追求。建国后,王瑶的“史稿”长长的“绪论”,不仅使新文学史的开始、性质、领导思想、分期等问题规范化、系统化,标志了学科的成熟,而且加强了现代文学史写作的现实性要求。
20世纪的最后15年,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受到世纪末社会转型的冲击,开始全面反省文学史的生存与发展,逐渐趋向个性化、 多样化。 1987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率先更新了文学史写作话语,其概括的“改造民族灵魂的启蒙文学”、“文学的忧患意识”、文学的“悲凉”的美学特征及新的体例框架,都给现代文学史教学、编写带来了新的启迪。但创新与保留共生。10年后,孔范今和黄修己两位教授分别主编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他们不只是在体例上打通过往的近、现、当代的文学史格局,更重要地也在思考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问题。诸如,这段文学与政治、经济、文化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文学史的价值范畴如何确定?可是,他们重在文学史时间的贯通和内容补缺上的突破和充实,影响了问题思考的深入。仍然以集体编写的形式,也呈现出较重的过渡性痕迹。倒是世纪末问世的“北大”和“复旦”出版的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浓重的个人化写作,创造了全新的文学史叙述话语、观念、体例。史家诸多方面的探索和尝试,预示了一种新的文学史写作话语的诞生。同样,他们极富个人化的历史体验与教科书规范化的写作;文学史写作风格的多样化与文学史对象本身的秩序性;文学史叙述重心转向历史情境、隐性结构及作家的潜在写作等方面,与文学史显在作家作品、社会客观情势等传统中心任务,这些诸多问题的矛盾冲突,依然是作者、主编者未能解开的结。无疑,洪子诚和陈思和两位史家的追求和实践具有积极的探索性。
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文化语境,来自作家、史家自觉的世界文化交流意识的建构。自胡适、朱自清等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作为新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以兼收并蓄、融化新知为宗旨。文学史在他们的手中,一是中国传统史书的编年、纪事、纪传三体综合化的延续,一是西方现代科学思维实证主义、历史主义的渗透。30年代王哲甫在解释他所理解的“新文学”的六个方面时[2], 无论是对文学性质的认识还是对文学样式的分类,已完全将西方文学文类的标准纳入了新文学中。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新文学整体性的成熟。此后的若干种新文学史,对文学发展的勾勒愈加凸现了对19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思潮线索的模仿。德国的格尔维努斯、V.M.Friche(费理契),英国的泰纳,俄国的别林斯基等文学理论家的文学史观,强调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与时代的密切联系,均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文学史写作。
建国后,单一的“反映论”,统一的文学阶级斗争化叙述左右着文学史的写作。“文革”时期集体编写文学史成风,加之文化交流的断裂,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更加模式化了。80年代初,政治上拨乱反正,文学史写作也得以恢复。主要表现为封闭状态的打破,西方文学理论的再次涌入,激发了对现代文学的重新思索。
“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开文学史写作的新风气。其改观联系着文化交流的进一步深入。最突出的是边缘性学科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苏和振兴,西方的各种史学、文学史理论纷至沓来。这个时期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一边对各种外来文学史理论消化吸收,一边自觉地反省,探索、尝试多样化的文学史“重写”途径。可以说,钱理群、洪子诚、谢冕、黄修己、杨义、陈思和等这时期有影响的文学史家,在其史著中,基本都贯穿了这两方面的思考和努力,力求建构自己的文学史话语。如杨义以“图志”[3]的形式探索写作文学史的新形式。 洪子诚、陈思和在反思传统“当代文学”概念和旧的描述方式时,提出了“努力将问题‘放回’到‘历史情境’中去考察”[4](P5); 注意文学史“创作现象、作品艺术内涵的阐发”, 同一时代的“潜写作”[5]等文学史新话语。而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序言”里明确表述“丛书主要是受《万历十五年》、《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的启发,通过一个人物、一个事件、一个时段的透视,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著作[6]。 文学史家的这些探索和新追求,自然并不令人十分乐观。在反思与接受基点上的探寻,也是在不断重写的过程中的探寻,他们又切切实实面临着许多具体问题的困惑。这使得我们发现“权宜”[4](P3)一词, 自然成为彼此共同习惯运用的“关键词”。世纪末全球化的趋势和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文学史的当下写作问题,不只是文学研究的全局问题,更联系着历史的过去与未来。
三、中国现代文学的功能与文学史的未来
20世纪的中国文学已成为过去,文学史的写作也留下了历史的印迹。但是,它不是仅仅作为历史陈列的博物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文学需要历史的观照,更需要历史的创造。
其一,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价值功能,被动的多向度发展的历史经验,提示了新世纪文学史的认识应该转变到创造、建构文学功能的重新审视,必须在充分发挥史家主体意识中,探寻真正意义的文学精神特征、文学史本质形态。
近代中国社会从封闭的封建王朝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蜕变过程中,诞生了中国现代新文化、新文学。她经历了晚清的社会变革、新兴知识分子的成长,产生了超越传统的五四新文学;接着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波澜起伏与文学生存相交织;随后改革开放的社会转型期和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再度焕发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大解放,文学在复归、探寻、期待中迎来了新世纪。这是一段不可不注意历史背景的时代文学,也是不能不关注自身生存命运的文学时代。诚如德国的文学史家赫·绍伊尔所言:“文学既有反映的功能,又有建构的功能。它是特定的意识形成和流变过程的媒介,肩负着塑造特殊历史环境的重要使命,是各个历史时期的自我确定和意义构成的表现形式,影响历史发展进程的重要力量。只有这样来看问题……文学是静止的,被动的,才会被抛弃,文学的动态发展的本质及其能动作用才会被承认。”[7 ]以此文学观念调整文学史的写作,最重要的是对文学本质功能的重新认识,重新确定它的考察视角、叙述方式。从动态的文学特征上思考文学的功能、价值取向,文学发展史的创造性建构将是新世纪文学史写作的重要理念。中国现代文学史总是陷入不断被重写或必须要重写的困惑。这本身就说明文学是一种生产过程,文学史是对文学与历史理解、建构的产物。五四文学的历史本质界定,有白话文学、人的文学、反帝反封建的文学,激进文学、保守文学、精英文学、西化文学以及现代性审美观念、价值尺度、创作方法等初建文学多种,恰恰正是在这些观点阐发中为今人逐渐认识五四文学的全部,为还原整合历史全貌提供了可能。其中对文学史资料的不断挖掘,是还原历史重要的一方面,但对史料作用的理解和建构,可能才是文学史真正意义上的还原。文学史是一幅需要不断补充和增加色彩的图画。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使我们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共和国建设的历程,认识现代中国人尤其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心灵的历程;更应该使我们看到现代人对审美的观念、方法、形式的追求。文学作为反映功能,这个“历程”是时间概念,是静止的被动的。因此它所产生的认识价值,往往有着特定的意义。而文学的“建构”与“追求”永远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文学史的任务不可能是盖棺论定、终极的判断。陈思和先生以“没有结束的结语”为题,说“中国20世纪的文学史(包括当代文学史)只是一个时间的自然概念,新文学的传统和发展都不可能‘世纪末’结束,也看不出当代文学到了下个世纪会出现大的变化的迹象。”这里透露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新理念已经生长的信息。文学史的写作目的应该在这种动态过程之中,旨在引导人们做出批判的评价(即理性的反省),启发人们进行历史的思考,提高人们解读文学作品的能力。20世纪中国文学在富有张力的创造性审视中,才可能显现历史完整和进步的价值,才可能由过去对现在乃至未来产生影响和帮助。文学精神代表着人类文化最自由的创造精神。文学史的使命不仅要延续这种精神,而且还要不断进一步创造这种文学精神。新世纪中国文学史家的主体意识愈获得长足的扩展,文学史也就愈有多彩的色调,精神的自由才有文学扩大的阐释空间,才有文学史的鲜活性、可读性。
其二,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以教科书为传播的主要形式,以教育课程设置的规范化、系统性为学科建设的基本要求。今天,在学科发展与教育改革的大趋势下,文学史写作须在探索文学审美的本体和文学教育素质能力的培养这两者有机融合中寻求新的途径。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在“文学”与“历史”两极徘徊得太久,形成的不是文学的文体史就是史料汇编,就是以社会史、思想史替代的模式。文学史的写作究竟是“历史决定论”,还是“文学决定论”?在世界文学影响下的20世纪中国文学,对此问题几乎陷入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悖论。一方面世界文学和传统文学交织的复杂的现代文化语境,与接受者的文化误读;另一方面20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特殊的浓重的社会历史纠缠,与文化历史情境的片面性理解,使得20世纪中国文学史失去了文学学术性和历史真实性的光环,直至世纪末也未能获得“重写”的共识。这种状况又与现行教育目标文学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同相关。文学内容的程式化、统一化,使得文学史自身的悖论问题,没有得到认真的反省,相反造就了文学认识(更多是误读或绝对化的认识)的约定俗成。教科书中文学史在体例上的翻新,顺应现行政治标准的重写,使得愈来愈多的人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就是五四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民主文学、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等统一的批评,构成了百年中国文学阐释和称颂的基本思路。正是遵循共同目的、功能的“文学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史有了人为的可寻“规律”。文学鲜活的原生态阅读感悟,文学在批评中的关系、功能、地位等有机把握,被一种程序、共同目的追求所遏制了。文学教学的程序化和文学观念的社会化,恰恰集中地暴露出我们文学史写作的真正危机所在。20世纪中国文学就其思想和形式的本质言,它是现代作家运用现代汉语(白话文)文字工具,反映了一个世纪以来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封闭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现代知识分子感时忧国的丰富精神世界。文学史中的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也不是几个板块(时代背景、文学运动、作家作品)的简单相加。它表现为作家丰富的文本形式,即展示现代人丰富情感、精神感应、丰富生活的文本形式。这里没有规律、没有模式、没有绝对的因和果,只有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学文本,表现出社会历史行进的过程和人类文明创造精神的现象与形态。因此,文学史的教学不能以明确的目的性判断和主要掌握基本历史知识为中心,必须立足文学史的本质特征,注重用心灵去体验、理解、感受丰富的文本和历史的进程。文学本质特征是精神的情感活动,是人类精神文明的重要表现形式。青年人了解人类精神文明就是体味感受精神的过程。文学教学首先应在这样的基点上,探寻讲授者、接受者交流对话的主要方式。文学史的教学过程是文学知识接受的过程,更是文学理解和创造能力培养的过程。新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将以适应素质教育的要求,强化学生的能力训练作为基本的原则。这一文学史教学方式的转变,对于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科结构不无积极意义。文学史的未来无论学术层面还是教学层面,永远属于对文学自身精神的记录和创造,以及坚持面向接受者的不断整合机制。
其三,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又是传统文学不断更新再造的民族文学。这就决定了文学史的写作必须从观念形态、理论方法、具体操作,乃至生产途径等多方面,走进开阔的文化语境寻求文学昨天、今天、明天的相互联系,及描述与建构的新思路。
今天,文学史的开放性、多元性,将愈来愈为更多的人们所接受。在世界文化视域中的中国文学的现代化目标的真正所指,文学边界的扩大,文学史的写作自然会发生较大变更。我们主动参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对话,文学史的写作既是民族文学的追求又是世界文学的内容。这些基本点的确立恰恰是中国现代文学学科走向深入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文学的开放性文化视界中,文学史的未来和中国文学史的写作路向,可否从这些方面理出一些运作的线索:1.文学的功能、价值虽然依旧是文学史家探讨的重要问题,但是对文学精神主体的重新审视,创造建构功能将激活文学史写作的多样化追求。那种从文学史教学成长起来的学科和形成的写作模式,随着人们对文学功能、本体认识的扩大和深入,文学史著和教科书的矛盾,被体现个人化的多样文学史所消解。文学的讲授与文学的阅读及文学精神的延续,对于文学史写作不论途径如何,目的都将是一致的。文学史的教学旨在通过对文学“经典”的阐释和沟通,培养学生丰富的精神创造力。2.反映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规律性等一系列传统观念的,将文学史的史实或“大事件”编纂而成的编年体、纪事体将更多得到青睐,读者能够接受这种方式的“历史真实”。同时,历史是记忆,又是每个人心目中的历史。文学史的主观的“记忆”,可能是“小人小事”,但是直接传达了一种个人与“过去”的关系。这使得历史成为互动的、活的、复杂的存在,这个存在具有了与文学本体相似相近的生命同构。编纂的史实与开放的记忆,两者共同完成了我们对文学过去、现在、未来的三者互动联系。3.文学史的文化身份随着上述认识的变更,需要重新定位。文学本身的复杂性,其情感的交流性,决定了文学史不可能仅仅是文学+历史,或者文学运动+文学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的简单模式。文学交流的过程是一种多因素、跨学科的复杂过程。文学史的任务既要注重这种文学的特征,又要揭示这种“过程”的丰富性、创造性。文学史的内容在作家、文学生产的机构、社群、读者、历史情境及文本本身的范围内,又与诸多学科(哲学、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相联系。文学史的话语应该是与其他学科整合、联系的话语。我们文学史的写作将从这些方面入手,探寻自己理解的整合话语、叙述方式,为丰富世界文学史提供自己的声音。4.文学史的核心是文学,文学的核心是作家作品。如何理解作家作品成为进入文学、文学史的关键。诗学、比较诗学在今天跨文化的文学研究中愈来愈受到重视。因为“文学的存在取决于其他具有独立性的知识体系的存在。其结果必然是,某些要素——对于美学来说也许较一般,但对文学来说却很特别——必须被赋予存在的形式,而诗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去确认这些要素。” [8]比较诗学是在更大的文化语境中探讨“这些要素”。它从跨文化视域中关注文学的“文类”研究和文化历史的“关键词”(即个人化理解文学的视角、概念)等基本要素,将有益于对文学作品的解读和文学历史情境的沟通。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史写作的使命和追求的目标,依然是对文学自身的本体认识,它是文学理论、文艺学研究的范畴,更是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重要内容。
总之,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写作留给我们的经验和问题,显然,已经超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需要思考的范围,也不仅仅是中国文学史的问题。它联系着一个世纪来诸多复杂的历史文化语境,构成了一种“文学史写作”的文化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充分说明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我们也只能在不断反思中,期待文学史的明天。
收稿日期:2000—04—13
标签:文学论文; 中国文学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现代文学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艺术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历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