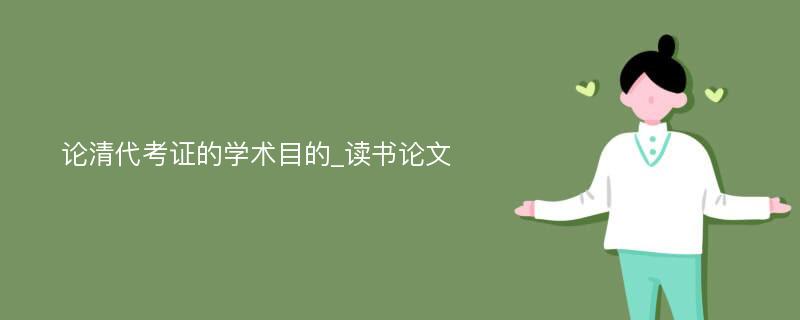
论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考据学论文,清代论文,宗旨论文,学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769(2002)05-0055-04
一
考据学的学术内容相当广泛,其核心是治经,在考据学者们看来,经书中包含有圣贤 之道,只有通过对经典的研究,才能求得圣贤之道,而道的求得不仅有利于修身,且有 利于治世。戴震云:“《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1]将经看成是道义之 源,舍经而无从得道义。阮元云:“圣贤之道,存于经。”[2]焦循说:“习先圣之道 ,行先王之道,必诵其《诗》,读其《书》,博学而详说之,所谓因也。……先王之道 载在《六经》。”[3]崔述云:“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六经》以外, 别无所谓道也。”[4]他们都把经看成是载道之书,欲求道,必通经。在这种思想的驱 动下,学者们将他们的主要兴趣放在通经上。他们研究小学、史地、天文算学无不是为 了通经明道,在这些众多的相关学科中,小学最为重要,被视为通经明道的最主要的工 具。
清初,首先提出由小学以通经明道者是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 ”[5]顾氏的这一主张,成为考据学派的不二法门,此后的考据大师无不以此为宗旨。 阎若璩指出:“昧以声音训诂,则不识古人之语言文字,而无以得圣人之真意。”[6] 阎若璩的弟子宋鉴尝曰:“经义不明,小学不讲也。小学不讲,则形声莫辨而训诂无据 矣。”[7]他们都高度重视训释文字的重要性,把研究语言文字放在解读经典首要位置 。由此看来,清初就已牢牢地树立起小学在通经中至关重要的作用。
吴派创始人惠栋极其重视小学的通经明道作用,其《九经古义述首》认为“经之义存 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钱大昕认为,“夫《六经》皆以明道,未有不通训诂而 能知道者”[8],“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 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9]把训诂看作是通向义理的必由之径。惠栋的另一 位弟子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序》中亦阐明了这一观点:“经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 空执义理以求也。但当正文字、辨音读、释训诂、通传注,则义理自见而道在其中矣。 ”可见吴派学者都是遵循这一宗旨的。
皖派在考据学阵营里影响最大,其创始人戴震倡导由小学而通经明道的言论最多,也 最具有说服力。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 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10]他在十七岁时就抱定了从小学、制度、 名物入手探求《六经》之道的志向,他在乾隆四十二年正月十日,即逝世前四个月写给 段玉裁的信中说:“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 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 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11]一言以蔽之,只有通过小学、名物、制度的研究才 能通经,才能求得经书之道。戴震强调小学在通经明道上的桥梁作用,所以他十分重视 “六书”的研究,认为“六书也者,文字之纲领,而治经之津涉也。载籍极博,统之不 外文字;文字虽广,统之不越六书”。[12]戴震研究小学、预算、典章制度之学的最终 目的是为了求道,即“理义”;而《原善》、《孟子字义疏证》是他求道的心得。
他的弟子段玉裁承其师说,精研《说文》,其目的在于通经明道。“《说文》《尔雅 》相为表里。治《说文》,而后《尔雅》及传注明,《说文》《尔雅》及传注明,而后 谓之通小学,而后可通经之大义。”[13]把研究《说文》与研究经典结合起来,治《说 文》就是为了治经。他说:“夫不习声类,欲言六书治经,难矣。”[14]戴氏的弟子以 训诂校勘精绝而闻名的王念孙亦认为,“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15] 。可见皖派学者无不以小学为通经的工具。
自戴氏反复倡言由小学以通经明道之后,这一思想在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官修 《四库全书》,将它写入了《凡例》之中,“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文字之训诂,则 义理何自而推”。作为一种价值取向,四库馆臣把这一思想贯穿于对历代著述的评价之 中。纪昀亦曾说过:“不明训诂,义理何自而知。”[16]这一宗旨影响之大,由此可见 一斑。
继承了戴震义理之学的扬州学派,同样坚持这一宗旨。焦循云:“训诂明乃能识羲文 周孔之义理。”[17]阮元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 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18]“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舍诂求经,其 经不实。为文者尚不可以昧训诂,况圣贤之道乎!”[2]由此看来扬州学派也是十分重视 训诂文字之学,把它看成是探求义理和圣人之道的门径。
“为正统派死守最后壁垒”的晚清考据学者俞樾等,同样坚持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宗 旨,俞樾在《文庙祀典议》中说:“义理存乎训诂,训诂存乎文字。无文字是无诂训也 ,无诂训是无义理也。”所以,他十分重视《说文解字》的价值,“《说文解字》一书 尤为言小学者所宗,士生今日,而欲因文见道,舍是奚由哉?”走的是乾嘉大师们由小 学通经的老路。
从以上大量的史料可以看出,从清初的顾炎武到晚清的俞樾等考据学大师们无不以小 学为通经明道的阶梯,小学被视为通向圣人之道和经典义理彼岸的桥梁和舟楫,舍此而 无路可行。这是考据学派的根本宗旨。以反汉学而闻名的宋学家方东树,在《汉学商兑 》卷中叹息道:“此是汉学一大宗旨,牢不可破之论矣。”“此论最近信,主张最有力 ,所以标宗旨,峻门户、固壁垒,示信学者,谓据其胜理,而不可夺矣。”
二
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学术宗旨,是考据学区别于宋明理学的最显著标志之一。不可否 认,理学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其特定的地位、价值,曾对中国的学术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但在对待传统经典的态度上,却存在师心自用的弊病,他们摆脱汉唐的传注疏释, 不重视小学在通经方面的价值,将自己的思想,强加给经典,甚至以“六经注我”,发 展到后来,不仅不读传注,不讲训诂,甚至连经典原文都不读,只背诵朱子语录就夸夸 其谈,而陆王心学更是反对读经,否定知识的价值,主张求之内心,参禅顿悟,其未流 达于“狂禅”的境地,故而在明末就有一批学者起而批判,呼唤回归经典,探求经典本 义,并初步认识到了小学的价值。明清鼎革,满族入主,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反省理学之 弊,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舍经学无理学,后起之学者无不重通经,反对“束书 不观”、“游谈无根”,强调训诂名物的重要性,主张通过客观地对字义字音的探求来 阐发经典本身蕴含的义理、圣道。可以说,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治学宗旨是考据学派在 对宋明理学流弊的批判、反省之中形成的。
考据学派由小学以通经的方法,具有合理性,古代人类所创造的知识能够留传到后世 ,主要靠语言文字的记录,靠典籍代代相传,而经书是经过历史长河的大浪淘沙之后所 积淀下来的精华,这些典籍大多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形成,随着时间的流逝,后世人们 去古愈远,文字、制度、名物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不可能用后世的文字语义去解读 经典中的语句,不可能用后世名物制度,去附会古代的名物制度,若强为之解,只能造 成误读,求其确切的原义,唯一方法只有重视距经典形成期较近的注疏,工具书,通过 对古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的研究,由字通词,由句通经,求得经典本义。这种摒弃 主观臆断,讲究客观研究,严格地从语言材料出发的解经方法无疑十分科学。就连对考 据进行过猛烈批评的理学家姚鼐,也不得不承认“夫六书之微,其训诂足以辨别传说之 是非,其形音上探古圣初制度之始,下贯后世迁移转变之得失。”[19]周予同对考据学 的这一宗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清代戴震、焦循等由文字训诂到经典研究再到哲理探 索的主张和方法,我觉得在今天仍是有效的‘基本功’。”[20]
明了考据学派主张由文字音训以通经明道的宗旨,为我们理解考据学派为何孜孜不倦 地从事文字、音韵、训诂、名物研究,辑佚古经注疏,兢兢探求一字一物的本义旧制, 找到了一把钥匙,同时也说明以往对考据学派是“为考据而考据”,是为了“求奇炫博 ”的指责有重新检讨的必要。汉学家之所以要向“纸上与古人争训诂形声传注”,[21] 是他们的治学宗旨所决定的。明了此旨,就能更好地理解考据学的反对者如程晋芳的观 点:“今之儒者,得唐以前片言只字,不问其道理如何,而皆宝而录之,讨求而纂述之 。群居坐论,必《尔雅》、《说文》、《玉篇》、《广韵》诸书之相砺角也,必康成之 遗言,服虔、贾逵末绪相讨论也。古则古矣,不知学问之道果遂止于是乎?”[22]具有 极大的片面性。只有明此旨,才会理解王念孙、王引之等人所从事的看来似乎是纯学术 的研究工作表象背后的更深层的动机与目的。现代学者肯定王氏父子著作的价值,大多 是从他们对语言学、校勘学的贡献出发。而古代考据学者却看重的是他们的研究对阐发 经典“微言大义”所发挥的作用,清人王绍兰评价王氏父子的研究说:“以众经诂一经 ,而经之本义以立;以一经贯众经,而经之通义以明,而又合之以形声,函之雅故,微 言大义,时见于篇。”[23]可谓深得王氏父子的苦心。
考据学派由小学而通经明道的宗旨,对于批判程朱理学具有积极的意义。“乾嘉学者 注重从声音文字、训诂、校勘等方面入手来整理古代经籍的作法,不啻把学术思想界千 百年来虔诚信仰、奉若神灵的偶像一变而为可以研究探讨的对象,从而廓清了许多长期 以来附加在古书上的误解和歪曲,使古代经籍逐渐呈现出它本来的面貌,这显然有利于 削弱宋明理学的理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解放思想的作用。”[24]正是本着这一宗 旨,考据学者不以钦定的朱子对经书的解说为是非标准,从语言文字的研究入手,重新 阐释经典本义,对以朱子学说为主的宋学无疑是很大的打击,因而遭到宋学派的极力反 对,宋学家陆陇其认为熟读朱子之书就可以求得孔孟之道。“夫朱子之学,孔孟之门户 也。故今日有志于圣学者,有朱子之成书在,熟读精思而笃行焉,如河津余干可矣。” [25]这种信奉权威,以朱子言论作标准的做法,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做法。与这种观念相 反,考据学派认为“训故明乃能识羲文周孔之义理……未容以宋之义理即定为孔子之义 理”。[26]陆氏意识到考据学由小学通经明道的治经方法,最终会粉碎宋学的理论基础 ,剥下宋学家附会在古代经典上的假道,故欲仿效汉代董仲舒要汉武帝独尊儒术的做法 ,倡导独尊宋学,独尊朱子,对宋学的反对派考据学进行封杀,其《四书集义序》云: “昔董生当汉武之世,百家并行,故其言曰:‘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不使并进。’此董生所以有功于世道也。继孔子而明六经者,朱子也,非孔子之道 者皆当绝,则非朱子之道者皆当绝,此今日挽回世道之要也。”基于陆氏同样的心理, 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指责汉学家“离经叛道”乃“几千年未有之异端邪说”,甚至 破口大骂,考据学是“洪水猛兽”,原因无非是“近世有为汉学考证者,著书以辟宋儒 攻朱子为本”。他在《辨道论》中攻击考据学云:“以六经为宗,以章句为本,以训诂 为主,以博雅为门,以同异为攻,……亦辟乎佛,亦攻乎陆王,而尤异端寇雠乎程朱, 今时之弊,盖有在于是者,名曰考证汉学……其言盈天下,其离经畔道过于杨墨佛老。 ”[27]晚清宋学家唐鉴在《国朝学案小识》中斥骂考据学家陈启源是“横生妄议,诬毁 圣人,专门之病,其狂悖一至此乎”陈氏激怒唐氏是因为陈氏的《毛诗稽古篇》“训诂 一准诸《尔雅》”,“所辨正者,惟朱子《集传》为多”。[28]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由 小学而通经明道的作法所具有解放思想的意义。戴震撰写《孟子字义疏证》,从小学入 手,阐发《孟子》的本义,对宋明理学的“天理”“人欲”等学说进行了彻底有力的批 判,戴氏由小学以通经明道实践的成功,从正面证明了这一宗旨的战斗意义。
考据学由小学通经明道的宗旨不仅是一种治经的步骤,而且也是一种指导思想,我们 不能简单地认为由小学通经明道只是从经典的字义入手去释经,而应看到,这一宗旨对 清代考据学重视小学研究,重视基础性研究的指导意义。或许某一位,某几位考据学者 的研究看起来与经学关系不大,但从最初的动机上都是围绕经学而展开的,只是一种在 有意无意之中的分工上的不同罢了。也正是因为这一指导思想使考据学在很大程度上逸 出了经学的范围,因为仅仅从解释个别经文语义的角度进行纯经学的研究往往解决不了 问题。宋儒如朱熹等并不是完全不注重前人的注释成果,但古人的注释往往是随文释义 ,很难做到贯通,所以朱子对经书的解释仍然有抵牾不通之处。清代考据学者为了通经 ,不得不向语言学的更深层次去作探讨,以寻求真正彻底地解决(客观上未必做得到), 也就是阮元《经义述闻序》所说的“其间未发明而沿旧误者尚多,皆由于声音、文字、 假借,转注未能通彻之故”。因此这一宗旨,对小学、史学、地理学、历算学等逸出经 学的范围,各自相对独立的发展并蔚为大国,具有积极的意义。
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宗旨,不仅影响治经,也影响到清人研究古代历史、地理、天算 、子学等相关学科。首先,有关古代的历史、地理、天文、哲学之书都是用古代文字记 录下来的,小学的发达为理解这些典籍提供了语言工具。其次,经学本身是一个包容哲 学、史学、文学、天算等学科的集合体,对经书中有关问题的探讨,不得不从经典的同 时代或相近时代的子书、史书中寻求材料作证据,这就大大地推动了对子书,史书的研 究。再次,是方法论上的影响,以史学为例。“说经主于明义理,然不得其文字训诂, 则义理何自而推;论史主于示褒贬。然不得其事迹之本末,则褒贬何据而定”。[29]这 种影响在王鸣盛身上表现得尤其突出,其《十七史商榷·序》曰:“主于校勘本文,补 正讹脱,审事迹之虚实,商榷经传之异同,最详于舆地职官、典章制度,独不喜褒贬人 物,以为空言无益也。”即仿照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治经方法,从文字训诂、名物史实 、典章制度的源流演变、地理沿革,以及史文、注文的讹误、脱漏、增衍、抵牾等方面 进行考核,以达到正史籍之讹谬、诠解史籍之蒙滞,使史实条理清楚,史文明白晓畅的 目的。
三
考据学由小学以通经明道的宗旨,也有一定的局限性。
其一,在这一宗旨的指导下,考据学家们认为只有经书中包含的道才是真道,过于相 信圣人之道,这就限制了他们对现实世界许多“道”的探求。从认识论上说,这仍是唯 心主义的范畴,造成只重间接真理的寻求,而忽视对现实真理的探求。在这一点上章学 诚的认识要深刻得多,他说:“就经传而作训诂,虽伏郑大儒,不能无强求失实之弊, 以人事有意为攻取也……离经传而论大义,虽诸子百家,未尝无精微神妙之解,以天机 无意而自呈也”[30]考据学派认为《六经》中含有圣人之道,宋儒求道的方法错了,应 从文字,音韵、训诂,度数等方面去考求,章氏则认为用这种方法,也未必没有“失实 之弊”,而离开经传亦可以求得真道。其所谓天机,即道也。
其二,通经明道的目的与宋明理学殊途而同归,即借助对经义的阐扬,圣道的探求为 走向末路的封建统治阶级提供理论依据,通经明道的最终目的是“致用”。
但我们要认识到,这种局限是时代的局限,清人在资本主义还未成长壮大以前,很难 看到新社会的曙光,他们不可能从思想上完全越出经学的樊篱,即使是那些先进的改革 者,思想家都是如此,顾炎武的“经学,理学也”,傅山的“五经皆王制”,黄宗羲对 上古社会的礼赞,都是把上古三代看成人间盛世,而经典正是盛世制度道德规范的结晶 。历代学者欲致君尧舜上的法宝无非是通经致用。这是历史的悲剧。
收稿日期:2001-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