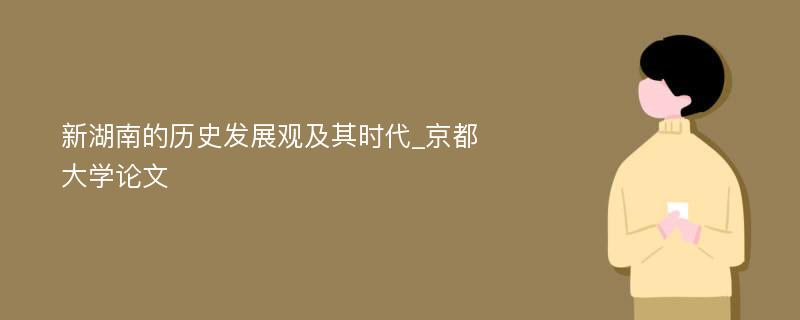
内藤湖南的历史发展观及其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南论文,发展观论文,时代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59-8095(2008)04-0090-12
内藤湖南(名虎次郎,1866-1934),为日本东洋史学京都学派的奠基者之一,其史学之主要成就,在其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提出,易言之,即其史学研究法。其时与日本东洋史学之发展时期相当,本文期对此一大环境的了解,进而究明内藤史学发展观之原型。内藤之史学理论,大别为历史发展观、历史研究法,前者又可分为:“天运螺旋循环说”、“文化中心移动说”及时代区分论,后者为古史研究法及考据朴学论,本文主要探讨其历史发展观,附论考据朴学论。其“天运螺旋循环说”乃为反驳欧洲学者的中国史研究观而提出,“文化中心移动说”则显示其对边陲文化的注重及文明开化的进程。此外,就其考据朴学论点,可知其所要求的乃一“实事求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者。
一、日本东洋史学与“支那学派”
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已与传统汉学稍有所差异。然今之研究者,仍有以汉学一词来表示东洋史学者,其实两词之意义已不能等而观之,彼此仅有部分重迭。汉学意指有关中国之所有研究,东洋史学则指(有时不包括日本)亚洲历史研究。②但日本东洋史的研究观点有派别之差异,因而在此领域有所谓“东洋史学派”与“支那学派”之别。前者,以东京大学的学者为主,但不限于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亦有此学风者,如桑原隲藏(1871-1931);后者,则以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及狩野直喜(1868-1945)为主导,②特别是内藤的史学观点。对于京都大学诸东洋史学者之研究,国外统称之为“京都学派”,其时对东洋史学界的影响力亦以京都学派为高。
(一)东洋史学之发展
日本“东洋史学”的发展,为明治以后之事,首倡者为那珂通世于1894年于高等中学校的教师会上,以东洋史意指所有东亚国家(日本除外),并以中国为中心,且经与会全体同意,于1897年正式得到日本文部省的承认,东洋历史与西洋历史二部并立于高等中学课程中,并明定东洋史的意义是以中国为中心说明东洋诸国治乱兴亡的大势。而其授课要目的制定,则经几度修正后才于1931年(昭和六年)2月确定。③前述为高等中学之情形,有关大学的东洋史学研究则以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为主。
东京大学成立于1877年,其东洋史学科的独立则迟至1911年。有关史学科部分,当时尚无东洋史学科,仅在“和汉文学科”中有一中国历史。直至1905年,史学科中始分“国史学科”、“支那史学科(案:指中国史学科)”、“西洋史学科”三门学科。“支那史学科”即为东洋史学科之前身,亦即东洋史学在此时才有其独立地位。1911年中国史学科更名为东洋史学科,至此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才完全独立。④
京都大学立校于1897年,较东京大学晚二十年,史学科又晚十年,于1907年成立。⑤同年,内藤即因当时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长”(即文学院院长)狩野亨吉(1865-1942)之极力推荐,⑥担任东洋史学科第一讲座,直至退休。故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的研究发展虽早于京都大学,但其东洋史学科的正式独立,反较京都大学约晚四年。在东洋史学中,又以中国史为大支。
美籍韩裔学者金基赫谓:日本汉学研究,已有千年历史,但将“中国史”作为一种独立的学问来研究的,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具体言之,是在中日甲午战后及日俄战争前后,始有组织性的研究。近代性的中国史研究,首先是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开始的。[1](pp.103-104)上述为日本东洋史学,于学校教育中之发展概况。
(二)东洋史学派
日本东洋史的近代性研究,因史观的不同,分为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洋史学派”,及以京都大学内藤湖南为中心的“支那学派”两大系统。[1](p.104)“支那学派”以内藤及狩野直喜(1868-1947)为首,“东洋史学派”以白鸟库吉(1865-1942)、那珂通世(1851-1908)及京都大学的桑原隲藏为主。
白鸟库吉是东京大学第二届的学生,学自兰克(Leopold van Ranke,1795-1886)弟子利斯(Ludwig Reiss,1861-1928)的西洋史及西洋史学方法论,而利斯的研究方法论是基于科学的实证主义。白鸟库吉毕业后任教于学习院,后因为三浦梧楼(1847-1926)之劝导,转而从事东洋史研究。[1](p.106)⑦其后,白鸟库吉回到东京大学,与那珂通世同被称为“东洋史学”的领军人物,白鸟库吉即以“东洋史学派”的领导者而活跃于东洋史学界,进而建立起日本独特的史学传统。此种学术发展的独特性,为日本东洋史研究所专有,中国与欧美并不存在。[1](pp.104-105)
“东洋史学派”以东京大学为中心,亦被称为“东京学派”。因此派的中国史研究观点,继承自兰克弟子利斯之研究方法论,故“东京学派”对中国文化文明所采取的立场,一如欧洲史家的观点。当时欧洲史家由比较西洋文明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文明的角度出发,认为两者间有根本性差异。欧洲历史学者所采取的史观是以中国文明既无进步亦无变化的“中国文明停滞说”,亦谓之为“环线循环说”;而西洋文明是“直线展开说”的见解。即西洋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其走向是直线的,且常是边变化边前进的。[1](pp.112-113)欧洲历史学者对东方社会的看法不同于西洋文明,认为东方历史是反复不断循一定环线的过程。此种环线循环说,以中国的王朝周期说为代表,即中国历史在几千年间均是王朝反复交替兴盛衰亡的过程,中国的社会并未有些许根本性的变革,中国的文化总是停滞的。因此,中国文化普遍被认为无法适应现代世界。日本“东洋史学派”对西洋此种中国史观有接受者,而采取极度否定中国文化的态度,对西洋文明的优秀性与普遍性信而不疑。此派的研究者,较著者除那珂通世与白鸟库吉外,还有津田左右吉(1873-1961)、⑧箭内亘(1875-1926)、池内宏(1878-1952)等人。[1](pp.113-115)
对于“东洋史学派”的此种“中国文明停滞说”或谓“环线循环说”的反驳,即是“支那学派”的内藤湖南所提出的“天运螺旋形循环说”。[1](pp.115-119)
(三)支那学派
京都大学以内藤湖南为中心,缔造“支那学派”的中国史研究观点,乃是相对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东洋史学派”。桥本增吉以白鸟库吉为“东洋史学派”,内藤则为“支那学派”的中心。“支那学派”的专门杂志《支那学》,具有清朝考证学派的色彩。[2](pp.420-421)⑨
日本东洋史此种不同的研究史观,事实上,亦表现在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学科诸教授间。即在京都大学内亦有所谓的“东洋史学派”,其代表者是始自桑原骘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人。将中国文学或中国哲学等合并为一,用文化史角度来处理中国史,是为“支那学派”,内藤湖南为此学风之首,其下为富冈谦藏、冈崎文夫等人。[3 ](p.323)然就个人于硕士论文中探讨所得,“支那学派”的创始者除内藤外,尚有狩野直喜,富冈与冈崎已是晚辈,又在此之后的,尚有神田喜一郎、吉川幸次郎等人。“支那学派”的学风,用内藤自己对东洋史的看法,即其被引用最多的,是“我所谓的东洋史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4](p.1)内藤此言,意表中国在其研究中的重要性,当是其学派被称为“支那学派”的主要原因。
京都大学之“支那学派”有两个特点,首先是着重考证。宫崎市定对此特点曾有所论述:“当时京大东洋史的学风是,以内藤先生和桑原先生为代表,两先生之不同点,大体桑原先生是德国派,内藤先生是法国派的吧。”[5](p.5)宫崎市定所谓的德国派,意指在东京大学兰克弟子利斯所传的历史主义。而其所谓的法国派,或即意指对法国汉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研究敦煌卷轴等新出土文物事,内藤等京都汉学家对此颇为重视。⑩亦即“支那学派”对新史料的重视,除敦煌卷轴外,对甲骨文、简牍等新史料亦高度的关怀。(11)谭汝谦亦指出,东京与京都汉学之间的差异,最好的例证或许是在对中国考古发现的态度上。[6](p.227)此言意指东京学派忽视甲骨等出土文物,而京都学派则对出土新史料有极大的兴味,此大体已为学界所接受。内藤等人对新出土史料的重视,则为郭沫若以“京都学派”来称呼京都大学东洋史研究的主因。(12)三田村氏以内藤的史学虽是东洋史专攻,但其根本完全由历史本质看事物,内藤即是在此意义上展开各种研究的。(13)
京都支那学派的另一特点是与中国学者互动密切。吉川幸次郎有言:“当时所谓‘支那学’,是由狩野直喜氏和内藤虎次郎氏的大力协助。”谭氏则由人性微妙的角度来看并指出,京都学者与中国学者的交往,常使东京的学者忌妒。桥本增吉亦指出:支那学传统的形成,不仅由于内藤和狩野的努力,也由于中国学者罗振玉的影响。[6](p.227)[2](p.423)美国学者傅佛果(Fogel,Joshua A.)以京大汉学应将其智识归功于盛清“考证学”,狩野与内藤使用之发展出汉学分支的“支那学”。内藤和狩野则将“考证”变成哲学和方法学,他们均热爱中国文化,并终生与中国人保持友好关系。[7](p.118,p.119)在傅佛果之论述中,以京都汉学乃应用考证,为中国研究之必要。竹田笃司亦提出,当时主要以“京大支那学”来称呼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学。[8](pp.23-30)青江舜二郎亦述及:“内藤湖南是日本‘支那学’的创始者,但不只是欧洲‘支那学’的移植,而是根据他独自的见识。而此种基础是,由其祖父天爵、父十湾至湖南经历三代的‘鹿角学’的传统。”[9](p.339)青江舜二郎之说词,显明内藤“支那学”的建立,乃以其汉学训练为根抵,加上其对中国博通的研究而得。
又由诸家著述中可知,当时京都大学的声望在东京大学之上。青江舜二郎在其著作中有如是的说法,西田几多郎的“哲学”,河上肇的“经济学”,内藤的“支那学”,即“巨匠”们健在的时代,是当时全国(日本)高校生所向往的。[9](p.354)竹田笃司亦有类似之说法,“其时,在京都大学最优越的学问,一是西田哲学,另一是东洋学,我们三高的学生亦会知道。总之,在狩野直喜先生、内藤虎次郎先生时,应用与以前汉学完全不同的方法,以新的方法从事中国的研究,这可说是不世出的卓越人物。”[8](p.25)青江舜二郎及竹田笃司两氏均是时代的见证人,虽竹田氏的说词没有青江舜二郎的直接,但可窥知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在当时声望之高。
据上述,则在京都大学的“支那学”,不仅是在京都大学与东京大学研究理念有所不同,即使在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间亦有所差异,然其大别依然是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意识形态的对立。但就私谊上,他们是谐和互有往来的,不管是内藤与东京大学的白鸟库吉、那珂通世,或与京都大学的桑原、羽田亨之间,均有好的学术交流。京都大学初期的东洋史学研究状况,在《东洋学の系谱》中有很好的说明文字:“在文科大学(今之文学部)是在第一任文学院长狩野亨吉等人的构想下,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洋学受到重视。其后以狩野直喜、内藤湖南为起始的支那学派,与始自桑原骘藏的东洋史学派,形成二大潮流尽力于教育与研究,而形成来自国内外所称之为‘京都学派’的精密学风,直至今日。”(14)当今亦为“京都学派”的学者邱添生先生,对“京都学派”一词的解释为,“乃一非正式的学术名词,系指以日本京都大学为中心之学者的研究,他们奉内藤虎次郎为泰斗,对于中国的历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学术地位上获有相当高度的评价,甚至说京都学派是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主流,亦不为过”。[10](p.105)
总结日本东洋史学研究中的“支那学派”学风,即以中国的历史、文化、哲学为其研究主体,其所应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即重视清考据法,且其研究者热爱中国文化并与中国文人雅士终生保持良好关系。其研究成果,已被视为日本东洋史学界的主流。此外,即是考古出土新史料的运用与重视,如敦煌文书、甲骨文、简牍等文物,并由此提出具体可行的研究方法。又在京都大学的训练中,得运用新史料,且得有研究成绩者,如贝冢茂树于甲骨文,森鹿三、大庭修于简牍研究上,贝冢与森鹿三两人均为与内藤有亲缘之学生。但若仅以清考据法来界定内藤的史学研究,则有失之偏颇。内藤不仅提出新的史学研究法,且因其对中国史之博通,而对中国史有新的时代区分及第一部中国史学史的完成,这方面笔者已另有专文论述,(15)本文仅就其历史发展观作一探讨论述。
二、历史发展观
内藤的历史发展观,是其被注目的史学理论观点之一,有谓之为时势论或大势论者,它包括天运螺旋形循环说及文化中心移动说两方面。三田村泰助以内藤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是在空间上探讨文化的变迁,而天运螺旋形循环说,则在时间上考察历史的变化。”[11](p.175)三田村并以内藤“史观的预言性得有高评,其秘诀即在其思考方法。”[11](p.175)在另文中,三田村谓内藤的历史学首在方法及史观的确立。[12](p.90)三田村泰助此说,并未深入的论述,本文即拟深入论证其历史发展观的“天运螺旋形循环说”及“文化中心移动说”。
(一)“天运螺旋形循环说”
较早指出内藤历史发展观点的是池田诚,其注意及内藤对“时运”、“时势”或“气运”、“时势所趋”、“世运”、“形势”、“运”等等措词的运用,池田诚以此所指的乃是历史的变迁。[13 ](p.4)池田诚以内藤所谓的历史:“就某方面言,可谓总是下层民众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日本的历史大部分也是此种下级人民渐渐向上发展的记录”。[14](p.130)池田诚以内藤的论点,是进化论的,亦有观念论、辩证法发展观。[13](p.4)三田村泰助则以内藤的历史发展观为“天运螺旋形循环说”,[11](p.174)内藤此说,前已述及,乃为反驳欧洲学者及接受欧洲观点的东京学派的“中国文明停滞说”,亦名之为“环线循环说”。[1](pp.112-117)内藤的反驳,发表在其《学变臆说》中,兹引述如下:
天运是循环的吗?意其所循之圆,非完全之圆环,而是为无穷的螺旋形,因为由一个中心点展开可填充三度空间的一条线,是须无限支线地螺旋缠绕者。[15](p.351)
上述,为内藤于其文中开宗明义所点出,天运非一完全的圆,而是一种无穷的螺旋形。兹再引述内藤对此种学理的解释与期望如下:
经过无限时间的历史变迁之所谓天运,唯看作是循环的亦复有一番道理。断定天运循环的说词,可谓稍稍得真理之一端的,无智妄信的一致,在经研究解释的分裂后,当归于解悟心证的一致,然其终之始的性质则已异,但仍谓一致者,因亦知有当然相类同地方。惟在一流的学者,专求此理于智识之一途,不省道义或美妙的发展亦然,致偏失于应用范围之小局。今若扩充之,捡来可达于真、善、美三者之极致路程的堠树,(16)其间有无限的兴味,可得发明有至大作用的事理,且听吾就学变立言之所。[15](pp.351-352)
上述内藤之意旨,明显内藤认为历史的变迁路径虽是循环的,但其发展过程之间是有差异的。此外,即是内藤主张须将其应用范围扩大,其所期望的是达于真、善、美的完全之境,如此可得发现一有大作用的学理。对内藤此种观点,三田村泰助有如下之解说:“因此历史‘真’的掌握是来自真、善、美的综合性观点,只追求真的知识是不完全的。此是根据由湖南的科学乃至哲学直观,而有历史特别是文化史优势的确信。”[11](p.175)
在天运循环观中,内藤亦分析其所展现于世界历史大一统的形势,兹再引述如下:
天运果为循环的吗?今之一致与昔之一致虽不可得,然分裂的形势,看来将结束的,然为何将来仍无统一形势的征侯?欧洲诸国之封疆戒严,倍加于昔,国家主义流行更促进分裂的形势,此实无疑为大一统作准备。若春秋合于七雄,进而为秦所并吞,兼并之极而归于一,今日欧洲诸国,在内于欧陆,在外于亚洲、非洲,均竞相兼并而致大,必不得不谓为将来更大之强者铺路。若强力结合,俄国现非成为列国深患大敌乎?若结合于财力,中国人、盎格鲁·撒克逊人唯利是图,现非尽吸取坤舆精华之全部乎?加之交通之便利渐开,大势遂系于东西的隔阂,举大块之面作为一团,天运其果为循环。今暂且不论世界一决于争夺胜败,或归于推攘并存,然现今除宗教的统一外,不得不成其教义各殊者,长短融合竟不得不落于一味,不仅止于基督教各派,东西的一统亦显于佛教及其它诸宗教的关系。[15](pp.353-354)
原文字有点零乱难懂,笔者作了一些调整,然内藤冀望以宗教为世界文明之统合是清楚明白的。此外,其中所言:“欧洲诸国之封疆戒严,倍加于昔,国家主义流行更催进分裂的形势,此实无疑为大一统作准备。”就这句话来看,内藤之历史眼光,有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观,因此,其对欧洲情势的推论观点是:分裂的形势实为大一统作准备。且明显的,内藤是由中国的历史大势来看欧洲的变迁。而此种史观,使其作出如此的论断:欧洲的进化论是为欧洲一统时代的准备。兹再引述其所论如下:
进化论一方面彻底破坏人类中心的旧信仰,余势所及,破坏往古一致的思想,不可胜数,因此,一方面实可视为分裂时代思想的后劲;在另一方面,此分裂时代的气运熏熟,使各个独立科学,为进入统一时代作准备。……故进化论于学术上,实可谓有效形成分裂、统一两时代的过渡。[15](p.354)
据上述,内藤以进化论虽有破坏,但却是由分裂过渡到统一的有效因素,亦即吾人可推论:内藤以破坏的因子为新文化再造的契机。内藤此种以破坏为统一作准备的论点,亦可见于其《支那上古史》中论述秦的统一中国,兹引述如下:
战国可以说是,一方面破坏所有的秩序致社会分裂混乱,另一方面则有形成统一气运的时代。乘其气运而出的,即是秦始皇。[16](p.146)(17)
即内藤以统一之前可以有破坏,而统一的主要因素除了人之外,时势亦是一大因素。在同书中谓:“其合并当然亦因秦始皇的伟大人物,但亦可说始皇是代表其时势而出。”[16](p.138)此说,在《支那上古史》中有两处,其以时势气运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而此则为统一的趋势。内藤于《学变臆说》中所谓的统一,是何种统一?兹再引述之:
有星雾说说明天体,统一各个分立的中心,进化论的发展,渐促使各科学统一,统一之极,而为求真、求善、求美之念,皆有所归一。因东西境遇之阻绝而特养成偏局之气风,经过销融和合,一统的大功或完成于此。此统一,非彼专制的统一,是个个独尊的统一,以枝统于叶,非以干统于枝的统一,帝释天纲,百千明珠,相照相映,是融通无碍的统一。[15](pp.354-355)
据上述,其“星雾说”推测应为科学上的“星云说”。内藤以统一之极,则进而有追求真、善、美之念。由此可知,内藤以为学之终极目标在真、善、美。而内藤所谓的统一,又必须是“个个独尊的统一”。内藤此说,或有庄子《齐物论》的观点,此或可待于对此有所得者之研究者再探讨。此外,内藤这个统一的观点,衡之实际是一难以达成之境界。最后,其对天运循环论作了如下的结论:
今之形势实若秦皇统一以前的中国、若罗马统一以前的欧土,其思想亦匹似董仲舒未出,基督教未为罗马国教时。则虽类似,所异亦多,故今后的形势是未必全若秦皇统一、罗马统一之后,今后的思想界未必全若儒教、基督教大一统之世,是则螺旋循环的(历史发展)必不经故路的缘由,或者以环形思考进化变迁的路径,或者以为直线进行,两者均各执一偏,故不相通。吾另有思想界中心变动说,涉言颇繁,故不在今之所论。[15](p.355)
因此,内藤以历史的发展是螺旋而非圆环之循环,必不会全循旧路径,亦非直线进行。故其形虽似,但质已变。此外,其以欧洲进化论,作为学术由分裂进于统一的催化剂。此种看法,或为美国学者傅佛果所述,内藤以“转变(change)是历史的本质,而改革(reform)是影响历史发展之路”。[7](p.53)傅佛果以内藤的观点:“历史不是重复的循环或螺旋,而是发展和进步的”。[7](p.53)内藤在《支那学变》中的观点,主要在谈中国学术变迁之大概,且还未加入文化的空间变迁形迹,但于该文末提出,欲阐明“文明中心移动说”,其曰:
冈仓觉三氏(18)曾有河边开化、江边开化说,我亦曾有文明中心移动说,此虽仅限于中国,即使仅对中国的观察亦是有趣的,待异日再详述。[17](p.357)
即两文所谈虽皆为学,然其面相实未必全然相类。《学变臆说》的面相大于《支那学变》,前者主要在谈历史变迁之大势,含盖历史全体虽亦偏于学术,而后者所谈主要为中国学术文化变迁之大概,尚未加入空间的变迁路径。
(二)文化中心移动说
内藤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在其《支那学变》已有提出,但并未细论。此《文化中心移动说》,亦为内藤历史发展观点之一,即其史学研究观点之一。据三田村泰助书中所言,内藤文化中心移动说即对那珂通世“旧中国社会停滞说”的反驳,其观点主要在《地势臆说》与《日本の天職と學者》二文中。三田村解读其文化中心移动说,即文化中心是与时代同移动,又政治与文化中心不一定一致。文化是超越国家民族,且优于政治。[11](pp.161-163)小野泰氏亦以内藤的文化中心移动说,是因之于清赵翼的地气说。[18](p.126)
笔者即据前述诸家的说法,欲探讨内藤文化中心移动说之原型。内藤于其《地势臆说》中,首论及地势与人文之关系,次论日本的地势与人文,再次为赵翼的地气说及其所未尽者,并论中国其它有地气说者,最后则是论满洲的将来及蜀、两广的形胜。其所论即人文中心,一如赵翼所已提出,自西北转东北,即自长安东移燕京,(19)而其转移的关键时刻即在唐开元、天宝之间。内藤认为赵翼此说尚有未完全者,因赵翼未注意及中国东北、东南、西南等地的发展大势。[19](p.117)以下即就内藤所论,摘述之:
地势与人文是相关的,或地势为因,而人文为果,或人文是因,而地势是果,小至都邑的盛衰,大至邦国的兴废,民物的丰歉,文化之隆污,征其往,可推其来,较之龟卜数计更为著者。[19](p.117)
据上引文,内藤以人文与地势是相为因果的,其大者可致邦国的兴废,而由其地之民风文物,可推知其将来,此较之于利用龟卜占卦更为显著可靠。
又一如前述,内藤认为赵翼的地气说,言有未尽者,因长安之前有洛,“禹贡九州岛,其开发之源泉,发起于冀、豫两州之间,盖资于黄河之利”。[19](p.117)而对于燕京,内藤则认为非人文之中心,其言如下:
其若燕京是,因赵氏为以东北之气积而产生之所,此特有地势所然也,至其人文,则未必然也。夫燕京之建,始于辽,而金、元、明、清皆都于此,……故所谓东北之气积者,若为权力之所托,言形胜则可,若以其为人文,则向往集中之所,别有所在也。[19](pp.120-121)
据上述,内藤以今之北京因地势而为一政要之地,然亦仅为一政治中心,并非人文中心。内藤对江南之态度则转为积极,他取明开国时献策者之言,以金陵为帝都所在,为经济、文化中心。并取明人章潢之论,以中国属南强北弱之势。故以赵翼略东南,而仅说东北为王气之积聚,实为“皮相”之见。[19](pp.121-123)而对满洲之于燕京的意义,则有如下的看法:
满洲之地,颇称膏腴,其百年之后,地力的开发未必难期,则燕京负此新兴之地而南俯,王气的旺盛,于此得其实,以致颉颃南方文物亦未可知。然满洲之河水,其大者,背南而向北,其地力人文,是否集中于燕京,犹有不可不待铁路畅通之后论之,且其风化渐开,地气益倾向于东北,燕京之力,因而不可控制南方益甚,是则中国的势力竟其两分吗?[19](p.123)
上述,为内藤对满洲之自然地理环境与人文发展,其论述燕京所可能造成之正反两种形势。继之,论中国自中世以后,地气渐偏于东边沿海地区。其势强时亦可制西部,但仍不免于强弩之末。亦即内藤取顾祖禹之说,以燕京并非可为帝都者,而南京亦非可图大宅之业者。即在内藤的论述中,北京与南京均非可以雄图之都。对于蜀地,内藤述三国时吴不能侵蜀,即因蜀地有其不可轻视之地理环境,且在西汉时其地即有可观之人文涵养。此外,即是两广,内藤以岭南风气最晚开,然与西洋交通,感染西洋文化亦最早,且其地为北临吴楚、东制瓯闽的中枢地位,故昔之偏隅,今已为乐土。[19](pp.123-124)
前述,为直引、意引自内藤《地势臆说》者,亦即内藤对中国之地理大势作一分析探讨。内藤特别留意东南、西南等地区,在非大一统的政治所在地时的发展。最后,内藤提出何以作此种探讨:
呜呼!中国之存亡,正表坤舆之一大问题,则其分合之形势,地力人文之中心处所,征往推来,于今概论之,以思考文明大势转移之方向,知未必无意义之事……。[19](p.125)
据此引文,则内藤以中国的存亡兴衰,乃世界上的一大问题,而其统一或分裂,则由其人文、地势可推知之。前述,大体对内藤《地势臆说》之要点作一引述。总之,内藤主要在论人文之发展未必为政治所在地,而政治所在地亦未必为人文荟粹之所。然由往昔人文发展之迹,即可考知政治国家未来之大势,及以考查文明大势转移之方向所在,并非没有意义之事。因此,笔者认为,内藤该文并非“文化中心移动说”的代表作,谓之为“大势论”或依其标题为“地势说”当更为切合内藤所论。
内藤的“文化中心移动说”当比地势论更为具体,内藤于《支那上古史》中《战国时代》一章确有一节谈及“文化中心的移动”。其大要为:在战国时代即有统一大势的外部变化,而文化中心亦在其间有所变化移动,此即为内部统一的趋势。战国初期,魏是文化中心。其地有谓大梁者,后为秦、魏所争之地,魏惠王时失去该地而势力大受打击。此是为第一期的文化中心。[16](p.142)内藤论战国时代文化中心的移动,乃由魏而齐、燕、楚、吴,兹节引之如下:
其次是齐威王、宣王时的稷下,……后因败于燕乐毅而不继,燕昭王集游士,作黄金台,但此仅为短暂。……再次代稷下而盛的是楚春申君所在之地,即原来的吴国,……吴昌盛于阖闾,再昌盛于春申君时。……楚文化的兴盛,即春申君时代。……而继楚的是秦,即吕不韦出而招集学者著述时。我认为文化中心移动之处,即其日后趋向于统一之所在。[16](pp.142-143)
据前述,则内藤以文化中心第一期为魏;第二期在齐的稷下;第三期为吴国但内涵则为楚文化;第四期为秦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时。第二、三期有一短暂的中心,即燕昭王时。据上述,这个文化中心的转移方向,由东而西,又由西而南。而内藤所谓“文化中心是移动的,我认为这是不久趋向于统一的所在”是颇值得注意与探讨的,此种思维模式与其所谓的“进化论实于学术上,可谓为形成分裂、统一两时代的过渡性的有效者”[15](p.354)有异曲同工之处。另就笔者初步的理解,内藤所谓的文化中心移动,并非一必然的兴衰,而是有文化广被的意义在,亦即文化中心转移到何处,该文化随即跟着流到何处,而文化所到之处,该处即被开发进而成为文明之境,因而促进了大一统的来临。如此的理解,与未深入了解前,仅对“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字面理解是大不相同的。继之,再引内藤所言如下:
文化在其移动过程中,于其盛行各国中产生一定特色,然就其影响于后世一点而言,最终则成为最后一国所开之特色,亦即与汉代文化有深厚关系。……如汉初完成的《淮南子》,即受惠于战国最后的文化中心秦吕不韦《吕氏春秋》。总之,这又是受战国最后成熟的文化之一例。……总之非中原地区的秦、楚文化,大有影响于汉代的事是发展上必然的事。[16](p.143)
据上述,内藤以文化的流动过程中,必与其当地文化相结合而产生出具有其本国(案:这里的国指的是诸侯国)特色的文化。此外,内藤亦注目于非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亦即所谓边陲文化对中原文化发展上具有相当的影响力,且视此为文化发展上所必然,这是个颇值得再探讨与思考的问题。或因此种论述,使其“文化中心移动说”成为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把柄。
内藤的“文化中心移动说”,不仅用于解释中国文化中心的转移,当其在写《近世文学史论》时,即已应用此种思考模式于日本文化中心的移动。(20)可见此一思考理论模式,与其学术研究相伴随,或可视为其史学理论研究通则之一。
三、考据朴学论
所谓考据朴学论,即为一种史学理论,可视为内藤的历史研究态度。内藤于1900年8月14日、15日,在《大阪朝日新闻》上发表《京都大學と樸學の士》文中倡言:“京都三百年来,文运渐兴,……京都为朴学先声。……京都大学于朴学之士之养成,岂非为其最大之天职哉!”[20](p.274)此为内藤明确以“朴学”为标题,极力宣扬“学问研究需以实事求是为其方针”。[21](p.30)当时为京都帝国大学中国文学·中国语学科第一讲座的狩野直喜,与内藤同样有此想法。因之,此一研究学问之方法即成为京大初创期东洋学的基本方针。[22](p.12)
内藤于《京都大學と樸學の士》中所言,其主旨乃在批判当时的东京大学教授、学生的职业取向,太过于泛政治化,因此,期许京都大学能以朴学为尚。[20](pp.272-273)
本文主要就有关其对朴学之士的看法,逐段引述如下:
其实朴学之士辈出,乃因社会倾向于沈滞,才力出群者,不能一一展其所能于其所处之社会,其激昂奋发者,或触刑辟,死于道涂,因而成为太平的牺牲者,而其于俗事有多方才能者,则耗其精神于雕虫小技之有余者,乃去而为朴学之徒,倾其一生于名物典故之琐屑,于空疏之性命理谈之中。……然社会秩序过整,倾于沈滞,虽有豪杰之士,当不得展其才能时,犹能发展人类之智慧,使其世代灿然为文物之粉饰,此乃不得志者之力。[20](p.271)
据上引文,内藤以“朴学之士辈出”,乃因不得志于其当世,乃转而为学,但其世代之文物,则因有不得志的朴学之士的注入而更加灿烂。有关朴学,其所举证的乃中国清世的考据朴学风,兹再引之如下:
清二百余年,朴学之士辈出,历代所罕见,昆山的顾宁人、余姚的黄梨洲,以前朝的遗民,不仕使高尚其志,太原的阎百诗、吴县的惠定宇、婺源的江慎修、休宁的戴东原、江都的汪中,以及近时番禺的陈兰甫,研经家法之守,小学训诂之学,极空前之盛者,实此等朴学之徒之力。若在西洋诸国,近世学术的进运,须各专业的钻研,终究非于世途有野心者所能兼,所谓学者即朴学之徒,二百年来,新主义的倡道,新学说的发现,尽出此艺窗之下,出自无病呻吟之辈,彼等亦不自以为时代之继儿,而至为学者之天职,其社会亦对之表示高度之尊敬,自古被称为文学之邦的中国亦有过者,为智慧发挥的方法,使得极为顺便,只可谓之为美风。[20](pp.271-272)
即内藤以中国清朝二百年来,出朴学者无数,自顾炎武、黄宗羲、阎若璩、惠栋、江永、戴震、汪中及文廷式之师尊陈澧等人。又上引文中的“近世学术的进运,须各专业的钻研,终究非于世途有野心者所能兼,所谓学者即朴学之徒”,此言已有学术与政治分途的意涵在,即专业于学的要求,此与中国古来所谓“学而优则仕”的为学趋向,有不同的气象。于中国朴学乃因政治风向不得已的作法,而此种为学风尚则为东瀛的内藤虎次郎要求之于日本京都大学诸学士。内藤追溯日本亦曾有此等朴学之风,乃出于德川中叶,至宽政以后转以实学为尚,明治维新后此风更甚,兹再引之:
在我邦,草野之士以学术为专业,纔三百年来之事……。及德川氏中叶,颇出朴学之士,……宽政以后,以实学为名,以文章为贵,学者皆以无经世之用为耻,希得升斗之禄,希施展其小才能,至无思为垂空言为万世开太平者,朴学之风遂熄,忽而为明治维新。……因此泰西风的大学,经三十年,出所谓朴学之士不免极匮乏,其于明治时代作为文运之鼓吹者,至后世可特别标榜者,几未闻也。[20](pp.272-273)
就上引文,显然内藤对实学并不标榜,因其未能以“为万世开太平”为职志,且为朴学风熄灭之因素。若解读无误,则内藤所讲究的为朴学非实学,(21)亦即实事求是的为学术而学术,学术不当与政治同伙。此种观点亦可见之于《支那史学史》,其以《晋书》为历史编纂堕落的开始,即因有政治的介入。[23](p.188)内藤该篇《京都大學と樸學の士》,已如前述,其主旨在指出东京大学学风太过于靠近政治,因此,其期盼京都大学能有朴学之士兵辈出。是其论京都朴学风与考据如下:
其(京都帝国大学)教授是最保持其朴学钻研之风,摆脱考证烦琐之弊,由文明的批评、社会的改造起见,古来关西学者所特有,兴起宁固而不杂、峻而不泛的学风,三十年间为东京大学所缺乏,不能满足世人新思想的特据,或由此间出,未必可知。京都大学远离中央政府,京都大学教授处在不得浮慕于俗界名利的境遇,作为时代的继儿,处于停滞社会,发挥人类的智慧,担当文明粉饰的大任,不可谓乃自然资格的具备者乎,而其成功,或更超越东洋流的朴学的地位,一蹴而得受如泰西学者的社会的尊敬……[20](pp.274-275)
由上述,则内藤于朴学者,并非仅为饾饤考证者,即其朴学并非可等同于中国考据学。此种学风则为东京大学所缺乏,而关西学者自古即有此学风,京都大学则为此学风的“自然资格具备者”,其若得成功,甚或可超越东洋流的朴学,当可得而为欧西学者般受到社会的敬重。内藤此处所谓的东洋流,推测其意指中国清朝的朴学风。
上述为内藤于《京都大學と樸學の士》所论,又其对“朴学”之定义,更为明白的用词即为:“闭门苦学专心研究”。[24](pp.358-359)其在《新支那论》中亦有所论,兹引译如下:
关于所谓政治或伦理等中国近世的趋向,是保留在中国过去文化阶级的遗物,毕竟作为政治是尚实践,作为伦理思想的如儒教是被实行的,此是政治与伦理同为文化主体时的现象,于今政治与伦理已不是文化主体,故呈现如斯的现象。故近来中国的文化是学问、艺术成为其主体,在其中的学问是,清朝的“朴学”兴起乃代表时代的特殊讯息。所谓朴学自文字来解释,即持有此种学问的阶级表现出不以仕宦者为主,而变成是民间读书人的工作,此种方法与欧洲近世的科学方法一致的地方是多的,在其中仍然产生了两种学问,可暂时以高级学问及低级学问命名之。[25](pp.141-142)
在《清朝史通论》中,内藤仅点出“朴学”于研究方法上的意义。而在上述引文中,“朴学”亦展现出其时代意义,即朴学者不以仕宦为目的,且其应用的方法与欧洲近世的科学方法一致的地方很多。此条引文,已可与前述相呼应,学术研究与仕宦分离,亦即清时学术与中国传统的学而优则仕已大不相同,此应为内藤于《汉学新法》中所提出,乃在明、清朝学风。[26](p.137)又其对高级学问的解释如下:
高级学问是在其方法中带有哲学性的规范,由严密地考证而促成其极伟大的进步,因而依此以前不明的古代文化的内容,变成非常明确。然另一方面,此种方法,规矩于带有卓越智慧人所建立的规范,仅作琐屑的考证,据此亦能完成卓越之成绩,此种趋向特别是在清朝时扬州的商人。此即至清朝文化的中心已转移于商人阶级,亦可说是特别的现象。[25](pp.142-143)
据上引文,则内藤以高级学问中,须有“哲学性的规范”,若解读无误,其意应为一通则性学理的应用,或各门学科的应用,如其应用“文化中心移动说”于历史解释中,但仍须有严密的考证,然不仅为饾饤考据,如此,则可得一杰出之研究成果,而在清朝,得此卓越成果的乃是扬州的商人。而此亦表现出一个时代特色,即文化中心转移于商人阶级,特别是扬州商人。大陆学者马彪则理出内藤对历史考据学的特征,有三点:
一、实事求是,朴实无华。
二、博览多识,指通晓各分科学问,如数学、天文学等。
三、精密治学,即指对史料的撰择由“粗末”成为“精密”及专门化。[27](pp.4-7)
据前述,内藤所谓的“朴学”之风的实证精神,其所强调在为学术而学术,实事求是的为学精神,当为万世开太平,不当以仕宦为职志。即其所求乃实事求是的“朴学”风尚,而非为政治的实用之学。此与“东京学派”承自德国兰克史学的实证精神,自有所不同。此说曾言之于硕士论文中,[28](p.213)现验以谭汝谦氏之研究,可知笔者当时的看法并非论之无据。氏以“内藤代表了现代日本首位企图打破兰克的研究观点,转向归纳的历史研究。”[6](pp.354-355)又对于内藤之“学问研究需以实事求是为其方针”的看法,与王国维所言之于林泰辅“当以事实决事实”[29](pp.49-50)的说法雷同。
本文所论乃内藤之历史发展观,事实上均可视为内藤的史学研究法。首略述日本东洋史学之成立,以明白内藤史学研究之时代背景。其时的日本东洋史学已独立发展,不能等同于汉学或中国学,最早提倡者为那珂通世于高等中学的教师会上。而在各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成立中,首倡者那珂通世虽在东京大学,但东京大学东洋史学科的成立尚晚于京都大学。在京都大学东洋史学科三讲座中,又因讲座教授者受训背景的差异,因而在京都大学形成两种不同研究理念的学风。即以内藤为首的“支那学派”,及以桑原骘藏为首的东京学风。表现在京都大学的两种不同学风,实即日本东洋史研究观点的缩影,亦即表现于京都大学内的东洋史研究风尚,有“支那学派”与“东洋史学派”之分。两派的中国史观,分别是“东京学派”采极端否定中国的文化与文明,即以德国兰克学派为史观;而“支那学派”的中国史观则是极为推崇中国文化,且与中国学者保持良好的往来关系,三田村泰助喻之为“内藤学”,亦是所谓“京都学派”的主导奠基者。两派主要的歧异,在于对中国考古文物的看法,东京学派以甲骨等考古文物为伪物,而内藤等“支那学派”则视其可证之史实。但此种对立的中国史观,并未影响两派学者间的私谊。持此种对立史观的学者,亦被后来的学者以对比的方式进行研究,如增渊龙夫的研究,即以内藤虎次郎与津田左右吉为对比,研究成其大作。继其后者,尚有五井直弘等人。两大学派虽史观不同,但都不可免的,参与了日本为侵略亚洲大陆所设立的研究事业。或因此,被讥为为帝国主义者服务。又由青江舜二郎及竹田笃司二氏的回顾,可窥知当时京都大学的东洋史学科的声望,更在东京大学之上。然此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所在,仅作为时代背景的了解,主要还是在探讨内藤史学研究方法,及其学术观点。
内藤的历史发展观中,本文主要探讨其“天运螺旋说”与“文化中心移动说”。前者,有喻之为“天运螺旋循环说”,亦有学者视为大势论或时势论,然其间应有些微的差异。内藤此说的提出,即在反驳欧西学者的“中国文明停滞说”,即内藤有中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史观,但其认为历史变迁虽是循环的,然其发展过程则是有差异的。此外,内藤期望“天运螺旋循环说”的应用范围需加以扩大,期达于真、善、美之境,如此可得有一大有作用的学理。另一历史发展观即是“文化中心移动说”,内藤以文化中心的移动促成了统一大势,即其文化中心的移动非相对的兴衰,乃是文明的普及,即文化中心移到哪儿,文明即被带到那儿。即文明所到之处,该地即得到开发,开发的成果当会使文化差异缩小,因此而带来统一的气运。或因此种史观,内藤看中国五代的割据,不仅未妨害文化的发展,反而有助长文化的普及。又其“文化中心移动说”,早已应用在其第一本著作《近世文学史论》中,可知此一史学研究理论,与其学术研究相伴随,可视为其史学研究通则之一。此外,即其在“文化中心移动说”的历史观中,表现其对边陲文化的注目。因此,其以汉代的发展受秦、楚文化的影响。就内藤所论,其实也是一种文化交流,而每一种文化交流必当汇流产生出自有的特色。因文化交流是缔结人类文明的重要元素,笔者深信所有灿烂的文明都是经此文化交流的过程而来。
在考据朴学论中,发现内藤并非标榜实学,而是主张学术与政治分离的朴学论。即其学风乃在“实事求是”,非为政治服务的实学。此为本文与美国学者傅佛果不同处,傅佛果以“实学”乃认识内藤学之主要线索。其对“朴学”之定义为“闭门苦学专心研究”,即朴学者不以仕宦为目的,当以为万世开太平为职志。内藤认为考据朴学方法,一如欧洲之科学方法,然不仅为饾饤考证,须有“哲学性的规范”,即须有通则性的学理于历史解释中,此亦可视为内藤史学研究法的特色之一。
(本文修自博士论文《内藤湖南史学研究》第四章第一、二、三节,资料搜集期间得交流协会日台交流中心的经费补助六个月,滞在京都大学一学年,及修改期间得有鲁迅美术学院文化传播与管理系教授李勤璞先生的斧正,谨此志并致谢忱!)
注释:
①有关这方面的文章,详参见高明士:《战后的日本中国史研究·导言——日本东洋史学的成立与发展》,台北:东升出版公司1982年版,第l-l5页;中山久四郎:《東洋史學の回顧と展望》,《歷史教育》第7卷第9號,(1932年11月28日),第381-389页。
②狩野直喜,熊本人,号君山。曾为“台湾旧惯调查会”(案:为日本据台期间,于1901年(明治34)所成立的官方组织,设置会长一人,及委员15-25名,进行大规模的有关台湾原住民风俗习惯及台湾农工商等经济产业的调查活动,主要的调查成果报告有:《台湾私法》、《清国行政法》、《蕃族惯习调查报告书》等。详参台湾总督府编《台湾事情大正七年版》,台北:仝编者,1918年11月,第96-102页。)事务员,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中国文学中国语学科教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为京都学风的创立人之一,与内藤虎次郎及我国罗振玉、王国维等颇有往来。详参见狩野直禎:《狩野直喜博士年譜》,《東方學》第42輯,(東京,東方學會,1971年8月),第157-158页;何培齐:《王国维与“京都学派”之论学》,《简牍学报》第18期,(2002年4月),第165-225页。东方文化学院为日本外务省以庚子赔款于1939年设立于日本,为经营其“对支文化事业”而设的学术研究机构之一。此机构分别在东京与京都各设一个研究所,其后分别为东京大学及京都大学所合并。狩野为京都研究所的首任所长,内藤亦为其研究成员之一。又日本外务省以庚子赔的经费,除了在日本设东方文化学院外,在上海成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在北平设人文科学研究所(以上为笔者于硕士班期间的读书报告“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及其汉学研究”所得)。
③参见三宅米吉述:《文学博士那珂通世君传》,《那珂通世遗书》,东京大日本图书1915年版,第32-33页;中山久四郎:《東洋史學の回顧と展望》,《歷史教育》第7卷第9號,(1932年11月28日),第381-383页。
④参见中山久四郎:《東洋史學の回顧と展望》,《歷史教育》第7卷第9號,(1932年11月28日),第387-389页。在这篇回顾文中,提到各大学的东洋史教授群时,京都大学的教授群中,竟没有内藤虎次郎的名字。
⑤东京大学创立于1877年,京都大学创立于1897年。
⑥狩野亨吉,哲学家,自然主义、无神论者。他生于秋田县大馆市,祖父为武士,父亦长于学问。1876年他随父移居东京,曾进东京帝国大学理科大学,后毕业于文科大学。1898年其为一高校长,约于1899年发现安藤昌益的“自然真营道”,被视为最大的文化业绩。1906年为京都帝大文科大学首任学长,不久辞任。其后以经营古书、古笔、绘画的鉴定终其余生。其藏书,后于东北帝国大学附属图书馆成立“狩野文库”。详参见新野直吉:《狩野亨吉》,《秋田の先覚者》3,秋田县总务部秘书广报课1970年版,第125-140页。
⑦三浦梧楼,号观树,军人、政治家,出身长州藩士,任陆军中将。为驻韩公使时,引发闽妃杀害事件。
⑧津田左右吉,明治末年至昭和前半期的历史学家及思想史家。1891年毕业于东京专门学校,为白鸟库吉的学生。著有《津田左右吉全集》全33卷,在其中有关日本古代史的研究,日本视其为学术界的共有财产。详参见松島榮一:《津田左右吉》,《日本歷史大辭典》10,東京:河出書房新社1972年版,第91页。
⑨桥本增吉于文中,将日本东洋史学界的变迁,由明治初年到昭和初年,大体分为四期:第一期即明治初年至同二十二、三年间;第二期约为明治二十二、三年至仝三十年;第三期明治三十年至大正三、四年间;第四期大正三、四年至昭和初年。第一期仍袭德川时代以来的传统学风;第二期乃移西洋近世史学研究法于日本史学界,即新东洋史学渐渐萌芽至发生时代;第三期则因中日甲午战争的刺激而引发的一种民族自觉;第四期则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法国取得南洋诸岛的管理而引发日本的南进研究政策,及对民俗学的研究。文中主要对当时的研究文献作一介绍,详参见趫本增吉:《先秦時代史》,《明治以後に於ける歴史学の発逹》,東京:四海書房1933年版,第395-430页。
⑩有关内藤与敦煌文书事,详参见神田喜一郎:《敦煌學五十年》,東京:築摩書房1970年版,第3-39页;何培齐:《王国维“京都学派”之论学》,《简牍学报》第18期,(2002年4月),第165-170页。
(11)内藤乃日本最早亲眼目睹甲骨文的汉学家,并有研究成果,虽其在此方面的研究不多,但提出利用甲骨文等出土文物进行古史研究的“古典研究法”。有关这方面论述详参见何培齐:《内藤湖南的古史研究法》,《静宜大学2007年“日本学与台湾学”暨第36回南岛史学会大会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集》,2007年版,第B5-1—B5-28页;何培齐:《王国维与“京都学派”之论学》,《简牍学报》第18期,(2002年4月),第191-209页。
(12)“京都学派”首为郭沫若所提出,三田村泰助则认为,郭沫若以“京都学派”回报内藤对甲骨文研究重视的说法是不切实际的。三田村氏认为没有所谓的“京都学派”,实际只有“内藤学派”。三田村泰助认为继内藤者,即使在京都连一人也没有,因此只有“内藤学”,所谓“京都学派”只是虚构的说法。虽说三田村泰助不认为有所谓“京都学派”的存在,然在其标题依然不能免的以“京都学派”为其标目之一,因此,所谓“京都学派”已是约定成俗。惟此并非本文探讨之重点,然其观点则颇值得再思考。详参见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史學の風光—東京學派と京都學派》,《日本及日本人》1591號,創刊100周年纪念論集(2)盛夏號,(1988年7月1日),第82、90页。
(13)三田村所谓的“历史本质的”,到底何所指并非完全清楚,推测或指内藤的历史理论及史学方法。参见三田村泰助:《内藤湖南史學の風光—東京學派と京都學派》,《日本及日本人》1591號,創刊100周年纪念論集(2)盛夏號,(1988年7月1日),第82页。
(14)江上波夫编:《東洋学の系譜》,東京:大修館書店1992年11月1日初版,1993年3月10日再版发行。转引自礪波護、藤井讓治编:《京大東洋学の百年·まぇかき》,京都:京都大學學術出版會,2002年版,第iii頁。
(15)参见何培齐:《内藤湖南的时代区分论》,《中华简牍学会通报》,2006年第2期,第95-117页;何培齐:《内藤湖南〈支那史学史〉之历史定位》,《书目季刊》第41卷第3期,2007年12月,第85-100页。
(16)据《中文大辞典》所释,古五里指堠,十里双堠,堠以记里。《北史·韦孝宽传》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据此因而推论,内藤于此处用“堠树”有里程碑之意。
(17)内藤的《支那上古史》是其在京都帝国大学的课程《东洋史概说》的一部分,该课程曾反复讲过几回,出书这部分大约是大正十年以后所讲授的部分。其成书与《支那史学史》同样,乃据听课同学的笔记,由作者亲自订补而成。内藤于病中曾希望再重写,然时间已不允许。又书中章节同样为编者所拟,内藤原来并未列章节。(详参见内藤干吉:《支那上古史·跋》,《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年版,第237-239页。)内藤所谓《东洋史概说》应如《中国通史》,其在《支那上古史》中所述,大体已如今之各部《中国通史》有关上古之部分。本文以探讨其史学方法与观点为主,是对其书中较特出之说法,仅在附注中转述,其后括号内之数字为《内藤湖南全集》第十卷之页次。内藤对中国史论述最大的不同,乃时而与日本史对比。如其以殷代的事情比日本同时代的史事清楚;中国在三代时有的田猎,日本则存在于德川初期(62页)。周的封建与德川时代的封建是同样的,内藤认此种封建为真正的封建制度(90页)。东周初期的内乱,有如日本御家的骚动(114页)。春秋末期吴、越以僻远之地方为根据,争取进入中原的势力,犹如日本足利末期的细川大内等以地方为根据地争取京都相似(124页)。又如秦始皇集富豪于京都,其后汉在长安置五陵,乃为繁荣及集中财富于国都所在地。此在日本以大阪、京都为首都及江户开府时均有类似的作法。其谓在政治上重要的事情,即使后世的君主亦得要跟随(152页)。又如其以移六国之后于关中以防范于未然,此犹如同德川家集诸侯妻子于江户(164页)。此为内藤所述中国与日本有相似史实之部分,此外,即其对中国史有较特出之部分。该部分仅就个人对中国史之了解,并未作比较。其较特殊的说法,如其以今之殷墟遗物,可看出中国艺术发展,是中国文化先进的证据(70页);第二个说法是,其以周公在中国历史上两度被理想化,第一次是由于孔子而起,故此次起于以礼乐为主的儒家,第二次是起于刘歆,因此而被视为规模宏大的制度制作者(103页);第三个说法,即是其认为子产,就中国政治的发展上,是相当重要的人物,因其在中国始建立成文法,其改革是法治性的(123页);第四个说法,其以四君时代,即齐孟尝君、赵平原君、魏信陵君、楚春申君时代,是游侠堕落的时代(136页);第五个说法,即其推论如果改革成功,可在秦之前统一天下的是赵武灵王(137页);第六个说法,其以秦始皇时在中国形成一种征服者采取被征服者文化的情形(154页);第七个说法,内藤以秦始皇遗毒于人民的是封禅、巡幸及求神仙取长生,但秦始皇就今日言之乃一有为的君王(154-155页)。此种说法,在当时应是不被中国所接受的说法;第八个说法,即其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社会现象之一,其以游侠以腕力控制某些地方,货殖即商人则以财力支配某些地方;第九个说法,其以武帝好儒学,乃因儒学最适合其时代要求。而使武帝学术为之一变的,是董仲舒的贤良对策(179-180页);第十个说法,其指出西汉的皇后出身甚杂乱,如卫皇后乃出身于歌者(184页);第十一个说法,其指出中央与地方权力的调和是一困难,而其征兆起于宣帝时,因其杀了颇有人望的地方官赵广汉。其论断中国名君多仅其人一代,其人亡则其政不继(206页);第十二个说法,内藤以王莽一朝对中国国势上是重要的时代,在内部文化上亦可谓是重要的时期,因其将经书实际应用于政治上(225页)。内藤并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将《周礼》应用于政治上而失败的,一为王莽,一为王安石,但王安石的还不算全部失败(214页)。此为内藤在《支那上古史》中,个人认为较特殊的论点,遂作一简述。详参见内藤虎次郎:《支那上古史》,《内藤湖南全集》:第10卷,東京,筑摩書房1976年,第9-236页。
(18)冈仓觉三(1862-1913)又名天心,明治时代,横滨人,美术界的指导者。东京美术学校校长,创设日本美术院。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东洋部部长,著有《東洋の理想》等。
(19)燕京即今之北京。
(20)内藤此说,详见何培齐:《内藤湖南史学研究》第二章第一节《家乡学统·折衷学派》,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2003年12月,第35页。
(21)这里所谓的“实学”与“实事求是”之意义,乃完全不同之定义。前者在为当世所用,后者则为学术而学术之胸襟,据事直书而已。“实学”与中国的“经世致用”,其胸襟气度应有所不同。有关“经世致用”之定义与论述,详可参见李纪祥:《“经世”观念与宋明理学》,《书目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三期,(1989年12月),第30-40页。
标签:京都大学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文明发展论文; 经济学派论文; 天运论文; 东洋大学论文; 湖南发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