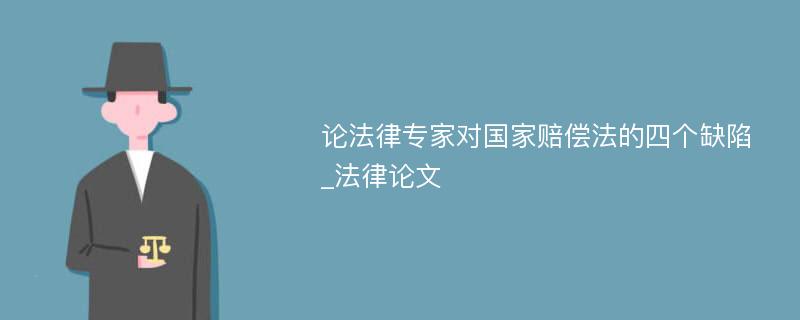
法学专家谈《国家赔偿法》四个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学论文,缺陷论文,国家赔偿法论文,专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赔偿法学是一个十分年轻的法学。从世界上发生第一起国家赔偿案件到今天,也只有2 00多年的历史。而国家赔偿制度的普遍建立,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在饱受战争创 伤的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呼吁政府切实保障人权的背景下形成的。以《国家赔偿法》的出 台和实施为标志,新中国才具有了法治意义上的国家赔偿制度。
《国家赔偿法》已实施6年多,暴露出这项新法律制度的不少缺陷。法学专家把它归纳为国 家赔偿范围窄、赔偿标准低、程序不合理和赔偿费支付存在漏洞4大问题。
赔偿范围过窄导致公民部分权利丧失
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关于赔偿范围的规定行政赔偿方面共3条12款,其中2条9款是对行政 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了人身权、财产权而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的规定, 有 1条3款是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刑事赔偿方面共3条13款,其中2条7款是对行使侦 查、检察、审判、监狱管理职权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职权时侵犯了人身权、财产权而 受害人有权取得国家赔偿的规定,1条6款是国家不承担赔偿的规定。专家认为,目前规定的 行政与刑事共16项的赔偿范围显然过窄,当事人应当受到保护的权利没能得到充分保护,无 形中导致了当事人权利的丧失。
第一,刑事赔偿范围过窄。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马怀德指出,对于刑事赔偿的范围来说,免 除的排外的条款太多了、太广了,有些甚至是不明确的,含糊不清的,导致了刑事赔偿的范 围过窄,有的条款竟成了公、检、法机关规避赔偿责任的“挡箭牌”。比如《国家赔偿法》 第17条第三项的规定:“依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的人被羁押的”,国 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有的司法机关为逃避自己的过错责任,虽然当事人无罪,但在释放被羁 押者时往往要写上一条“有违纪、违规、违法行为但不构成犯罪”,以此给当事人留一尾巴 ,并表明“抓你是对的、放了你我也没有错”,这一条被人们称为“留尾巴条款”。
应松年教授指出,国家赔偿法规定了若干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形,即免责规定。从实 践上看,有些免责规定过于宽泛,需要作些限制。例如,“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而 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践中,一些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 “招供”是刑讯所逼,但在有关机关拒不承认有刑讯逼供时,受害人虽然清白但往往被援引 上述规定推掉赔偿责任。
应松年还指出,国家赔偿法对于人民法院在民事、行政诉讼过程中的违法行为,只限于违 法采取妨害诉讼的强制措施、保全措施或者执行错误三种,“错判”一律不赔,其它违法也 不赔。对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中故意造成的错判,并导致当事人无法执行回转的那部分损失 ,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是说不过去的。裁判行为以外的其它司法行为违法的,如错发传票致 人损害,也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行政与刑事不能统一用“违法”的归责原则。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的归责原则采 取的是违法责任原则,即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时的违法行为侵犯了公民、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失时,国家承担赔偿责任。这一原则在审判实践中易于把握, 但也存在着不足。比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某些虽不违法、但却明显不当且损害了公民、 法人等合法权益的行为没有包括进来。袁曙宏教授指出,将行政机关或司法机关虽不违法, 却明显不当的行为排除在外,显然不利于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这也与国家赔偿 法的某些条款相冲突。如行政机关执法时滥用法定幅度内的自由裁量权的;司法机关对“没 有犯罪或者没有事实证明有犯罪重大嫌疑的人错误拘留的”,以及“对没有犯罪事实的人错 误逮捕的”,这里的“错误”显然包括违法和明显不当在内;公共设施设置或管理有瑕疵致 人损害的。国家因以上“明显不当”行为致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受到损失或损害的,国家 应当予以赔偿。
“在刑事赔偿方面,违法责任原则暴露的问题更多,”马怀德教授说,比如,由于证据不 足 ,司法机关将关了很长时间的人放了。这时如果指责检察机关违法,检察院的同志会认 为“我们批准逮捕他的时候有根有据,没有违反任何一项法律”。但是对于无辜被关押的当 事人而言,却是非常不公平的,无论如何,他受到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他理所当然认为自 己 应当获得赔偿。马教授认为,行政赔偿适用违法责任原则,而刑事赔偿则适用结果责任原则 ,即不管司法机关的行为有没有过错,有没有依照法律,只要这种行为的结果给当事人造成 了损害,都应当进行赔偿。
第三,应增加公共设施损害的国家赔偿范围。现行《国家赔偿法》只适用于国家机关在行 使职权中侵权的情况,而道路、桥梁等公共设施设置、管理欠缺而致人损害的,因不属于违 法行使职权的问题,没有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而由受害人依照民法通则等规定,向负责管 理的企事业单位要求赔偿。北京市友邦律师事务所主任周卫平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公共设 施的经营管理体制仍处于改革过程中,《国家赔偿法》着眼于解决国家机关行使职权中的违 法,没有规定公共设施致人损害的国家赔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注意现代国家在行 使国家权利之外还提供大量公共服务的事实,把公共设施设置、管理不善的侵权纳入国家赔 偿范围,能够全面反映现代国家的职能。
第四,应增加因公共利益损害的国家补偿范围。应松年教授说,《国家赔偿法》没有提到 国家补偿问题,但在实践中存在着国家机关合法行使职权也可能给人们造成损失的情况,对 于那些因公共利益而承受特别牺牲的人,根据公平原则,应该给予适当补偿。例如,因军队 演习、训练、配合执行国家公务,见义勇为,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致人身、财产损害等,需 要采取适当方式给予补偿。
过低的赔偿标准远不能弥补受害人的损失
在已被裁定获得国家赔偿的案件中,人们对过低的赔偿金意见最大,有当事人竟认为给予 的低额赔偿是对他们的再次“羞辱”。现行《国家赔偿法》立法时,出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 和国家财政负担能力的考虑,采取了直接的物质性损失赔偿的原则。这个标准旨在保障公民 最基本的生存所需,而不是充分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专家们说,从6年多的实践看,现有赔 偿标准的问题不是国家财政负担不起,而是赔偿标准太低,远远不足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
法学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普遍认为,仅仅赔偿直接损失对受害者是不公平的,赔偿不应当单 是直接的经济损失,它还应包含超过直接损失的赔偿及精神上的赔偿。如果某人一天的工资 是10元,他被无辜关押一天赔10元是不对的,失去自由的代价(或政府给公民造成的其它损 失)决不能简单的以直接损失计算,仅赔直接损失实际上等于纵容了政府的错误。
第一,财产损失赔偿应包括可得利益损失赔偿。应松年教授指出,对于财产损失,现有规 定原则上只赔偿直接损失(有些情况下,连直接损失标准也可能达不到),对于可得利益损失 一概不赔。其中,对于违法罚没、违法征收的,只返还本金,不计利息;财产已经拍卖的, 即使拍卖价格明显低于实际价格的,也只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 产停业的,只赔偿停产停业期间必要的经常性费用开支。例如,某个连年利润70万元以上的 企业,因行政机关的一纸违法决定而停产,最后倒闭,依照现有法律,国家对该企业可得利 润不予赔偿,对该企业的倒闭也不承担责任。国家对行政侵权应当给予充分赔偿,其赔偿标 准不应当低于民事赔偿的标准。在这方面,有关民事损害赔偿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可以在 国家赔偿法修订时予以借鉴。
第二,应给予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根据现行《国家赔偿法》,侵犯人身自由的,每日赔 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5倍;造 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精神赔偿显然不在规定的赔 偿事项内。应松年教授说,一个人被违法拘留3天,他能够得到的全部赔偿不足100元。这样 的赔偿怎能给受害的心灵以抚慰。在国家机关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和健康权的情况下,给予 一定数额的精神损害赔偿,既能够弥补现有赔偿标准的不足,又符合受害人对精神损害赔偿 的普遍期待。应松年教授介绍说,在私法领域,虽然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明确规定精神损害 赔偿,但在民事司法实践中,判决精神损害赔偿已经屡见不鲜。国家赔偿法可以也应当在修 改时,先行一步,对国家侵权的精神损害赔偿作出规定。
第三,可考虑增加惩罚性赔偿金。一些国家对政府人员故意侵权的行为(如殴打)规定了惩 罚性赔偿。我国民事立法中也出现了个别的惩罚性赔偿的规定。在国家赔偿领域,惩罚性赔 偿也值得考虑。对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故意侵权行为设立惩罚性赔偿,有助于遏制 违法,伸张国家赔偿的功能。
赔偿程序不合理使正义难以伸张
只有程序的公正,才能确保实体的公正。赔偿程序是国家赔偿责任的实现过程,更是受害 人的权益得到救济或恢复的途径,其设计科学与否直接决定着赔偿请求人的权利能否实现以 及如何实现。现行的《国家赔偿法》恰恰在赔偿程序上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刑事赔偿 程序上。法学专家指出,我国刑事赔偿程序设计极为粗糙,确认违法基本上是由违法的机关 自身或者其上级进行。这种“自己当自己案件法官”的程序使得确认违法极其艰难,堪称国 家赔偿法的“瓶颈”。
第一要简化现有的赔偿程序。周卫平律师认为,根据《国家赔偿法》第9条、第20条规定, 无论是行政赔偿还是刑事赔偿,均以赔偿请求人先向赔偿义务机关提出赔偿申请,由赔偿义 务机关予以先行处理后,方可进入实质性索赔程序。而实践表明,让赔偿义务机关主动承认 并纠正自己的行为违法极其艰难,他们或对赔偿请求人的请求怠于行使职权,或者置之不理 ,更 甚者对赔偿请求人百般刁难,尽可能的规避法律,逃避责任,从而致使有些赔偿请求人状诉 无门,苦不堪言。周律师指出,在修改《国家赔偿法》时,应对行政赔偿和刑事赔偿实行不 同的赔偿程序,即行政赔偿继续实行现有的赔偿程序,而刑事赔偿程序可以简化,这是考虑 到刑事案件对赔偿请求人的特殊影响,对错拘、错捕、错判后赔偿请求人提出国家赔偿的, 只要该赔偿请求人能提供公安机关的释放证明、检察机关的不起诉决定书、人民法院的生效 法律文书等确切法律证明文件的,可以不再经过确认程序,而直接进入实质性赔偿程序。
第二应提高审级,并设立专门的独立的国家赔偿裁判机构。在高级以上人民法院设立独立 的国家赔偿裁判机构,并采取合议、上诉等形式,实行两审终审制。应松年教授指出,我国 现行的国家赔偿法的赔偿程序中让赔偿委员会最后作赔偿决定,虽然法律在中级以上人民法 院设置了3至7名法官组成的赔偿委员会,作为司法赔偿的最终决定者,但这个机构既没有辩 论程序,也没有上诉程序。更成问题的是,它没有被法律赋予对“违法”的确认权,只能勉 强解决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双方在赔偿方式和金额上的分歧。陈瑞华教授指出,目前 赔 偿委员会可以设在法院,但要提高它的审级,比如说可以放在高级法院,应由高级法院赔偿 委员会处理。此外,高级法院处理不了的可以考虑由国家设国家赔偿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 以放在人大或相应机关,但不应放在公检法里,要任命大法官作为赔偿委员会的委员来主持 裁决。
第三,对赔偿委员会的审理期限应作出明确规定,两审最长不应超过1年时间。现行的《国 家赔偿法》只对赔偿义务机关的答复及其上级机关的复议作出了时间限制,但对法院赔偿委 员会的审理期限却没有任何规定,直接导致了国家赔偿案件久拖不决。因此要规定审限。但 审限不宜过长,两审的时间最长不应超过1年,因为涉及国家赔偿的案件一般都在赔偿请求 人和赔偿义务机关之间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行政或刑事诉讼,事实较为简单;而且从社会效果 上看,时间越短对受害人的抚慰作用愈大,较能发挥国家赔偿制度的功能。
第四,应增加赔偿义务机关受理索赔申请的强有力的约束条款。除了现行规定中对赔偿义 务机关受理索赔申请的时间规定外,应增加对赔偿义务机关超越规定时间不予答复的加重处 罚规定。袁曙宏教授说,现实中某些赔偿义务机关明知自己的行为已经侵犯受害人的合法权 益,应予赔偿,但就是对受害人的索赔申请迟迟不予立案,或在对应共同承担赔偿义务的案 件中互相推诿、“踢皮球”,把受害人引向其他部门,使受害人始终不能进入实质性索赔程 序。对此情形,法律对赔偿义务机关并无明确的规定加以限制和约束。袁曙宏指出,现行赔 偿法对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不予赔偿的法律责任没有规定,这是很不应当的。行政诉讼法 、行政处罚法都规定了,强者应该负有更多的责任,如果拖着不赔,应当像行政诉讼法那样 ,加收滞纳金、给予行政处分。因此赔偿法应当给予行政机关更大的责任,包括最后追究刑 事责任及经济责任,这是推动赔偿法实施的一项有效途径。
赔偿费用支付漏洞明显
按照《国家赔偿费用管理办法》的现有规定:“国家赔偿费用由赔偿义务机关先从本单位 预算经费和留归本单位使用的资金中支付,支付后再向同级财政机关申请核拨。”然而这一 规定却使赔偿费用的支付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有些地方财政困难或收入很低,不愿或无法将赔偿费用列入财政预算;而有些赔 偿 义务机关以各种理由搪塞拖延支付致使一些受害人获准赔偿后却拿不到赔偿金。
另一方面,许多地方的国家赔偿基金花不出去。深圳市每年拨出5000万元的国家赔偿金, 专门为行政机关打输行政官司作赔偿之用,该市不少败诉官司涉及国家赔偿,但至今就是没 有一个机关动用过一分钱。据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统计,1999年全区法院 直接受理国家赔偿案件32件,涉及赔偿金额22万元,经自治区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受理的赔 偿案件44件,决定赔偿的有27件,涉及金额25万元以上。但自治区财政部门设立的国家赔偿 专用基金设立6年多,只有一家提出过申请。那么,其他的国家赔偿金是如何支付的?最高人 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汤鸿沛指出,这是由于赔偿义务机关从部门“小金库”中支 付赔偿费用之后,不愿再向上申报,因为只要“申请核拨”,就得向上级部门申报,就得暴 露自己的过错,还要被追究当事人和部门领导的责任。因此,不少赔偿义务机关宁可“私了 ”。
汤鸿沛认为,赔偿费用的法外运作使国家赔偿的监督功能大大丧失。可以考虑,将赔偿费 用的支付方法改为赔偿请求人凭赔偿决定书或者判决书直接向财政机关申领赔偿金。同时规 定,财政机关在赔偿请求人申领之后,必须在一周内予以支付,否则将受到有关法律或政纪 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