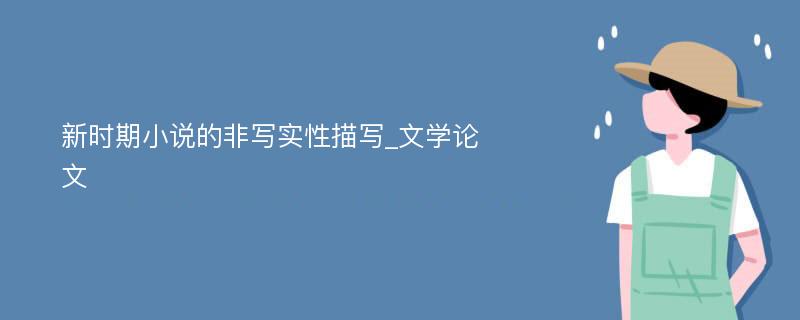
新时期小说的非现实性描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时期论文,现实论文,性描写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学起源于神话。这一命题亦可转换成另一种表达:文学起源于非现实性描写。神话是“一种崭新的象征方式——艺术方式的第一朵花或第一批花中的一朵。”〔1〕神话发现并接受超自然力量, 并将它从普通世界中分离出来,它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由我们自己的感情所点燃的“预设的事实”。〔2〕神话创造“幻想世界”,〔3〕通过一种“想象方式”,一种关于大自然的想法,讲述“外在于彼”的世界。〔4 〕……这些表述虽各有侧重,但都指出了神话非现实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起源于神话与文学起源于非现实性描写这两个命题是等值的,它们彼此可以互相说明、互相阐释。
从神话出发后,文学(特别是小说)就与非现实性描写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将其转换成一种悠久的文学传统。譬如中国小说,它的大致走向是:神话——传说——仙话——志怪——传奇——话本——明清人情世态小说——现代现实主义小说。在漫长的文学历程中,非现实性描写始终是文学观察世界、表现世界的一种最主要的艺术方式。
与非现实性描写相对应的现实性描写晚起。在文学经过浪漫幻想的神话传说时代而进入仙话、志怪小说时,现实性描写开始滋长。它与非现实性描写并驾齐驱、共存不悖、浑然一体。但是,随着文学的发展,现实性描写的地位逐渐提高,非现实性描写的地位逐渐下降,两者在文学中成反比地并行着。到现代现实主义小说,由于反映现实的迫切需要,以及小说自身转型的必然,非现实性描写呈萎缩状态。继之而来的当代小说,高扬革命的现实主义,这一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系统提供的文学观念在真心诚意拥抱现实时,毫不犹豫地否弃了非现实性描写。因此,在17年的小说中,我们很难看到非现实性描写,偶尔出现一下,也是作为封建迷信的遗存,予以批判的对象。至10年文化大革命,非现实性描写终于被赶得无影无踪。
从80年代初开始,沉寂了30多年的非现实性描写悄然出现,但到80年代中期以后,它便蔚然成风了。在许多作品中,凡有现实性描写的地方,几乎都有非现实性描写。
非现实是与现实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现实是客观的、实有的、可信与合乎理性的、并且是可验证与可分析的存在。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5〕这一论断基本上切中了现实的性质。 非现实一般是非客观的、抽象的、不可信与不合乎理性的,并且是不可验证与不可分析的存在。它包括神灵、鬼怪、迷信、巫术、方术、神秘意识、荒诞、魔幻等。
按照通常的理解,这些非现实性内容大量涌入新时期小说,会对文学的现实性内容构成消解或颠覆的威胁。然而恰恰相反,非现实性描写不仅没有消解现实,降低现实的力量,反而强化深化了现实,丰富了现实的内含,促进了当代小说的发展。
在新时期小说中,非现实性描写描绘的非现实可分为三种形态:荒诞、神秘现实、魔幻。三种非现实形态的艺术机制迥异,荒诞是现实的非现实化,神秘现实是非现实的现实化,魔幻是非现实的现实幻化,它们各自显示着独特的艺术功能。
荒诞:现实的非现实化
需要指出,本文论述的荒诞,是限于荒诞小说而言的。我对中外小说作了大量的比较,发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荒诞小说中的荒诞与非荒诞小说中的荒诞的性质截然不同。在荒诞小说中,荒诞是现实的非现实化,荒诞形象成为作品的主要形象,荒诞小说质的规定性来源于此。而在其他小说中,荒诞有时以局部形象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时常被当作现实来对待,即非现实的现实化。有时是作为神秘现实、魔幻等非现实形象的外显特征出现的。只有把荒诞放到荒诞小说的语境中,才能对它的性质和独特的艺术功能作出准确的把握,才能将它与神秘现实、魔幻区别开来。虽然神秘现实和魔幻均具有荒诞特征,而荒诞有时也显出神秘的或魔幻的特征,但它们毕竟是不同的。
荒诞,意为荒唐、虚妄而不可信。关于文学的荒诞,各种解释之间没有差别,概括起来是这么几点:不合乎情理或不恰当的;不合逻辑、不可理喻、不谐调的;不真实、荒谬可笑的。所谓荒诞小说,就是荒诞不经的小说。
荒诞小说在文学发展的长河里时有闪现,由于没有积累起足够的强度,致使它一直到19世纪末也没有获得命名权。荒诞小说是在20世纪西方现代文学运动中定型化、经典化并获得命名权的。本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末是荒诞文学的“经典化”时期。首先确立荒诞小说的文学地位和经典意义的是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卡夫卡,他于一二十年代创作的《变形记》、《地洞》、《城堡》等小说,是荒诞小说的经典之作。所此,卡夫卡被称为荒诞文学的先驱与经典作家。到40年代,萨特、加缪等作家,尤其是文坛怪杰、荒诞文学大师加缪,将荒诞文学推向更高的水平,在已成为荒诞文学经典之作的《局外人》、《鼠疫》等小说和《卡里古拉》、《误会》等戏剧文学中,加缪创造了一系列经典性的荒诞人物形象。50年代,荒诞文学进入全盛的顶极状态,即荒诞派戏剧风靡文坛大获全胜的年代。荒诞派戏剧家们尊加缪为先师,并以他的荒诞哲学思想作为认识世界和创作的指导思想,把荒诞主题推向极致。60年代以后,经典性的荒诞文学式微。
80年代以前,中国当代文学中基本上没有荒诞小说。从80年代初开始,受西方文学影响而发生艺术嬗变的新时期文学,陆续地推出了一批荒诞小说,其数量相当可观,仅我阅读所及,就有六七十篇之多。
荒诞小说以非现实性描写为标识,但是,荒诞小说营构非现实情境,并不以非现实为指归,而是以非现实性描写为叙事策略,将现实非现实化,现实与非现实互指,即非现实是现实的改装,现实的替代形象——现实的象征符号。根据非现实化程度的强弱,可将新时期荒诞小说分为三种类型:现实性的荒诞小说,可能的现实性的荒诞小说,非现实性的荒诞小说。
1.现实性的荒诞小说
现实性的荒诞小说与真实的现实靠近,变形度不大,它一脚伸入非现实的荒诞,一脚又踩着现实。它的这种特性决定了它是近现实的荒诞,亦可称之为“轻度荒诞”。这种荒诞小说多描写从现实中呈现的荒诞,非现实与现实共生共存,仿佛与真实的现实一般,荒唐而真实。这类小说有范小青的《出门在外》、刘心武的《白牙》、韩少功的《归去来》、陈村的《一天》、余华的《河边的错误》、洪峰的《湮没》、残雪的《阿梅在一个太阳里的愁思》,等等。
《出门在外》构设了一个荒诞的情境,写辛教授出门在外的一次“奇遇”。学术会议结束后,辛教授到一座历史古城旧地重游。到古城的当天傍晚,辛教授走出旅馆散步,结果迷失了方向,丢失了旅馆。丢失了旅馆,自然要寻找旅馆。在长达一天两夜的“寻找旅馆”的奔波中,辛教授遇到的种种不可思议的境象,似真似幻,充满着荒诞色彩。这篇小说的荒诞是戏谑性的,意义在荒诞的正面,叙事自我指涉,善意地描写一位聪慧而遇事有点迂腐的智者无伤大雅的一幕生活喜剧,荒诞的反面不负载深度意义。《白牙》的荒诞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设计,“我决心做一个试验,整整一个月一句话也不讲。”一位漂亮活泼的姑娘突然在单位、在家里、在交往中不与任何人说话,可想而知,这个试验是艰难的,但她终于做成了。她游戏自谑,没想到这个荒唐的做法竟然使她由自谑达到自悦自悟,并在沉默静观中,猛然认清了世界和他人,意外地发现一本正经的生活中掩映着种种乏味庸俗的现象。这么一来,叙事的自我指涉越过荒诞的非现实性的形式而直指生活的荒诞,一个戏谑性的自设游戏置换为一个解读现实生活本相的策略性的设计,一个看世界的观点。
2.可能的现实性的荒诞小说
韩少功的《爸爸爸》、谌容的《减去十岁》、邹月照的《第三十三个乘客》、残雪的《山上的小屋》、刘铁的《过客》、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多多的《大相扑》、马原的《虚构》等,都是这类荒诞小说。
可能的现实性的荒诞小说开始与真实的现实拉开了距离,变形强度增大,荒诞的形象或情节成为小说的主要形象或主要内容。荒诞的形象或情节是强度变形、强度虚构所致,但它们又有很好的现实性,仿佛是现实的一个误会,一个精心设计的改装,具有成为现实的种种可能性,因此,它们是可能的现实性的。此外,可能的现实性的荒诞小说的反面一般都承载着深度意义。
中篇小说《爸爸爸》是一篇深透的荒诞小说。小说中的丙崽是一个十足的荒诞人物:语言混沌、思维幽闭、行动呆痴、猥琐卑贱、奇形怪状,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怪人。他对外界的全部思考和反应一是翻白眼,二是叫“爸爸”、“X吗吗”。他不知道这两句话的含义, 无论遇到什么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的第一句话是叫“爸爸”。跟着来的第二句话是“X吗吗”。丙崽是个贱人,受人嘲弄戏耍欺负的玩物, 然而有一天,打械斗失败而归的乡亲们猛然醒悟过来,他们觉得丙崽很神秘很奇特,认定他不是这个世上的人,并断定丙崽只会说的两句话是阴阳二卦。于是,丙崽被敬神信鬼的乡亲们尊为“丙仙”、“丙相公”、“丙大爷”。更为荒诞的是,他们竟然根据“丙仙”无意识的动作和含混的咕哝占卦,决定与邻村再次械斗的方式。这样,展示在我们面前的丙崽和他的乡亲们,就成了一群荒诞的“陌生人”。这篇小说的内容是现实的,人物是荒诞的,而荒诞人物的行为又是“可能的现实性的”。荒诞的丙崽是实实在在的形象,又是意义的载体、象征性符号,即形象的能指具有现实的规约性,形象的现实性得到落实,而形象的所指在隐喻关系中则构成一种明显的深度意义:在一个原始愚昧的社会环境中,只能产生形形色色的丙崽。正是这种愚钝落后,把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拖向文明的毁灭与精神的窒息之中。
表现荒诞要有荒诞意识,荒诞意识来源于对荒诞的深刻体验和感知。谌容的《减去十岁》在喜剧的观照中揭示了人意识中深刻的荒诞潜存。小说从一个小道消息开始:听说上边要发一个文件,把大家的年龄都减去十岁。这个消息显然是荒诞不可信的,然而,正是这个谎言导演了一场闹剧。正要退位交权的局长为可再干十年而精神振奋;一对中年夫妇一变为风华正茂的青年,顿时心花怒放,浪漫满溢,要用离婚结束窝囊的日子,开始新的人生;老姑娘青春又再,心荡神摇。而刚工作的小青年们闹着不愿再回小学,幼儿园的娃娃们吵着不乐意再回到娘肚子里去。现实中有这等事吗?没有,但人的意识中有这种潜存,因此,这篇小说的非现实性情节是可能的现实性的。
可能的现实性的荒诞小说是荒诞小说中最常见的类型,它最突出的优势或特点是它在现实与非现实、实在与荒诞之间有很宽的区域,广面涵盖了荒诞的内容。其次,它通常不采取纯粹的非现实或纯粹的非人的形式,而是潜入现实本身作非现实性描写,从现实的深层托起荒诞的内质,因而它的荒诞更多地显现为内在性。西方荒诞文学中的大多数优秀作品如卡夫卡的《城堡》、加缪的《局外人》、《鼠疫》、《误会》、《卡里古拉》、尤奈斯库的《椅子》、《秃头歌女》,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都是这种类型的作品。
3.非现实性的荒诞小说
荒诞走向极致,便淡化并扭曲现实的本相,非现实性的荒诞小说由此产生。非现实性的荒诞小说对现实的强扭曲是以非现实或超现实的方式来实现的,在这里,纯粹的荒诞和极度的变形夸张受到推崇而成为遮蔽现实、悬置现实或消解现实,以达到非现实化的最主要的艺术手段。非现实性的荒诞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前提是:作品中所写的形象或生活内容是现实中根本不存在或基本上不存在的。然而,非现实性的荒诞小说并非真要否弃现实而完全进入非现实的界域,这不过是它们的艺术策略,用非现实的荒诞手法将现实极度变形,彻底改装,以便在转喻的艺术置换中抵达现实的深度或现实的本质,即以一种荒诞的形式书写荒诞的现实。宋璞的《泥沼中的头颅》、斯妤的《出售哈欠的女人》、陈村的《美女岛》等小说,将现实“非现实化”,但它们又完好地保持着现实的全部内容。
《泥沼中的头颅》描写的“泥沼”是一个令人恐惧的世界:浑黄腐烂,黑暗混沌。一个思想家为找一把改变泥沼泥糊状态的钥匙,处处碰壁,身躯又被泥浆化掉,最后只剩下一颗头颅在不停地旋转。作者的意图很明显,用“泥沼”象征腐朽窒息的社会现实。
《出售哈欠的女人》是篇“以荒诞的方式对抗荒诞”的荒诞小说,〔6〕写一个荒诞女人的一次荒诞的经历。 荒诞女人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据她迷朦的回忆,她诞生已有二三百年了。她最大的特点是擅于打哈欠,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睡醒了打哈欠,哈欠打累了再睡觉的习惯。她像梦一般迷糊,像风一样飘忽不定,终于有一天,她在飘荡中误入俗世的一座城市。心智未开、原始混沌的她一入俗世,便无所适从。一个无赖的“鬼男人”发现了她打哈欠的价值,威逼她出售哈欠,为他赚钱。于是,她成了“出售哈欠的女人”。哈欠的功效出神入化,购买者蜂拥而至。鬼男人生邪念,想把她高价卖给一家公司。恰在这时,她心智突然开启,立即心明眼亮,聪慧机敏,识穿了鬼男人的诡计。她学会按城市的规则办事,将鬼男人出售给一家公司,自己来控制他,当他的老板。她将新角色扮演得十分出色,一时春风得意。然而没过多久,她对人世厌倦了,觉得这世界处处隐藏着虚伪、无聊、阴谋,处处存在着荒诞,不如在“故乡”轻松自由。于是,她从鬼男人身上收回哈欠,决定返回离失了10个月的故乡。出售哈欠的女人以她的人生选择和对新的生存境遇的抵抗,对现实的拆穿、瓦解和嘲弄,以至超越俗世追求生命的本身状态而给现代人一个深刻的讽刺。
《出售哈欠的女人》是荒诞的非现实与实在的现实的结合,将现实的荒诞置于非现实的喜剧的观照中,最终以出售哈欠的女人的厌世逃循直指现实世界的荒诞,揭示商业社会和现代文明畸型联姻后秩序崩溃、价值失落,人性被欲望、金钱等扭曲变形的现实。〔7 〕这使我想起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以及作者对这部作品荒诞意义的表述。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要使人明白,这个世界从根本上讲是荒诞的,我想证明的就是这种荒诞。更主要的是,我想让自己和我塑造的主人公一起去体验一个真正的世界,进入到它百分之百的荒诞中去。〔8〕不过, 《出售哈欠的女人》有所不同,它在拆穿现实存在的某些荒诞的同时,明示了作者对当下社会现实中某些意义匮乏的忧思,对意义、价值构建的吁求。
神秘现实:非现实的现实化
与荒诞截然相反,神秘现实是将非现实的神秘现象和神秘意识现实化。新时期小说中,特别是地域文化小说,以及以地域文化为背景的寻根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新历史主义小说中,神秘现象和神秘意识蔓延丛生,构成现实的“特殊内容”。这方面,贾平凹表现得最充分。他80年代初创作的“商州系列小说”,弥漫着雾一般朦胧而又神奇的神秘色彩。他把鬼怪、神灵、巫术、迷信等非现实的神秘现象和神秘意识交织在现实内容之中,不仅没有损害现实的本质,反而对现实作了独特的文化观照。
神秘现实是神秘文化的现实化,它大体由以信仰为核心的观念(如鬼魂观念、冥界观念、泛灵观念、迷信等神秘意识)和仪式、风俗等为表现形式的行为事象(如巫术、方术、禁忌等神秘现象)两个互为表里的层面构成一个整体。前者是抽象的、隐秘的、深层的,后者则是具体的、显现的、表层的,是对前者的“物化”。〔9〕观念、 意识的形式化便是现象,而“心理上的内容一经成为习俗性的规范,便带来奇异性和神秘性。”〔10〕如果观念和意识本身就是神秘的话,那么,它们物化为现象时,神秘性就会放大而脱离现实的依据。因此,不论是神秘意识,还是神秘现象,基本上都是以非现实、非理性和不可信、不可验证与不可分析为特性的。维特根斯坦说:“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这是自己表明出来的、这就是神秘的东西。”〔11〕神秘现实是不可理解的,但必须是绝对相信的东西。“神秘的不是世界是怎样的,而是它是这样的。”〔12〕这就是它的文化性格,它的神秘性全于它是私有的内设,因而“未被人的思维认识过,或是人的思维不能理解的;超出了理智和一般知识认识的范围。”〔13〕于是,它在通常意义上就成了非现实的存在。
非现实的神秘现实(神秘文化)并非无意义无价值的存在,存在的东西都是有意义有价值的。关于中国神秘文化的价值定位,我同意樊星先生的看法,“对神秘文化的深入体验和传神表现,是有利于达到对中国人生、中国民族性、中国文化乃至人性奥秘的深层把握的。因为,神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部分。”〔14〕
神秘文化是古老文化的遗存与发展,因此,越是古老传统的社会,神秘文化的遗存越丰厚。中国是一个延续了数千年的农业社会,传统文化的遗存相当丰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写道:“中国本信巫,秦汉以来,神仙之说盛行,汉代又大畅巫风而鬼道愈炽;会小乘佛教亦入中土,渐见流传。凡此,皆张皇鬼神,故自晋讫隋,特多鬼神志怪之书。”〔15〕唐之传奇,“不甚讲鬼神,间或有之,也不过点缀点缀而已。”但有一部分小说,“仍多讲鬼怪的事情,这还是受了六朝人底影响。”〔16〕宋代崇儒并容释道,“而信仰本根,夙在巫鬼,故徐铉吴淑而后,仍多变怪谶应之谈。”〔17〕明清之际,神魔小说和志怪小说盛行,如《聊斋志异》,“书中所叙,多是神仙、狐鬼、精魅等故事”。〔18〕鲁迅从文学的视角,将中国神秘文化的源与流、神秘文化与文学的关系作了精确的概括。
从文化发生学的观点看,神秘文化源起于原始社会是最古老的传统文化。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为低下,思维蒙昧,人们受认识能力的限制,对自然界和人自身的许多现象无法作出合理的解释,误以为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力量在支配着万事万物。列维—布留尔对原始人的这种神秘意识作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原始人的知觉是神秘的,亦即逻辑思维所认为客观的和唯一的实在的那些知觉因素,在原始人的思维中则是在神秘因素的不分化的复合中发展着。原始人对自然原因不关心,他们的思维不去自然里面寻求解释,而是立即转向“超自然的东西”〔19〕。因此,他们把一切疑惑不解的现象,把吉凶祸福的根由全归因于超自然的神秘力量,信奉、尊崇、敬畏之,并由这种神秘意识而导出图腾崇拜、禁忌、灵魂、占梦、卜筮等等神秘事象。这些神秘事象与神秘意识一道,依靠本身特有的神秘力,以及社会群体趋同去异的整合力,渗透到人的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的行为和意志。在后来的岁月,这些原始的神秘文化并未因社会的变迁而消失,由于文化的延续性、一贯性以及人们崇古性的护持,其中的许多神秘现象和神秘意识,作为文化遗存,沉淀到民族文化心理中,世代相传,成为传统文化的构成部分。
既然神秘文化是实存的,那么,它就是现实的。不过这种现实主要是精神的、观念的。由于它是非客观的、抽象的、因而它又是非现实的。非现实的存在转化为现实的存在是以观念意识为中介的。于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非现实性的神秘现实是被当作现实来对待的。鲁迅先生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在论六朝志怪小说时说:“盖当时以为幽明虽殊途,而人鬼乃皆实有,故其叙述异事,与记载人间常事,自视固无诚妄之别矣。”〔20〕有趣的是,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21〕因为他们看鬼事和人事,是一样的“统当作事实”,〔22〕看作实用的东西。实际上,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及至现代小说、新时期小说都是在这个意义上描写神秘现实的。这个奥秘一经发现,就为我们研究新时期小说的非现实性描写解开了一系列疑点难点。用这个观点,我们来看贾平凹的小说。
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对神秘现实的描写,广面涵盖了神秘意识和神秘现象的内容。神秘意识是指潜存于意识中的神秘观念,它是神秘现象产生与存在的根据。神秘现象是外显的,它包括各种神秘术,主要指各种巫术、方术,如易占、卜筮、风角、望气、风水、相术、幻术、金丹、服食、吐纳、导引及祈禳禁劾、召呼鬼神、存思、行跻变化、厌胜、扶箕、咒术、扶乩等,以及通灵、通说、轮回转世、预言、禁忌等神秘现象。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我们看到:木犊远行,老爹念神秘咒语,祈祷神灵保佑儿子(《黑氏》);吴三大抱娘的拐杖到城隍庙,送娘的神灵到阎王处报到,娘才闭目(《远山野情》);师娘制红肚兜、红裤带,为天狗过门坎年生日,以喜冲凶避邪(《天狗》),《浮躁》中也有这个情节;赵家三坟一夜之间自动合为一体(《故里》);造美穴吉地,家道兴旺,毁吉穴散脉气,家道随即衰败(《美穴地》),《故里》、《远山野情》、《浮躁》、《瘪家沟》等小说都有风水描写的情节;《浮躁》中,乡民的图腾崇拜,民间对阴阳风水的重视,韩文举卜卦观天象,和尚谈玄言空,小月左眼跳金狗果然到,久病女人高烧“通说”,阴阳师施巫术避妖镇邪……《龙卷风》和《瘪家沟》的神秘现实描写更盛。《龙卷风》中赵阴阳观天象预测明年成黑豆,第二年黑豆果然丰产;赵阴阳临终前久不瞑目,单等七岁的秃女到来,看着他入棺成殓才咽气。他的奇异之念,村人不解。40年后,秃女的两儿子盗墓作孽将殃及赵阴阳墓时,秃女才明白赵阴阳闭目之前等她的缘故,吃惊不小。赵阴阳预言应验,神秘无解。《瘪家沟》里张家媳妇在瘪神庙祈祷后果然得子;侯七奶奶预言自己第5天进天国,到时天空会出现5个太阳,结果一一应验;炳根爷盗“牛过秤”爹的墓,见墓中白绢上的预言之精确,吓死在墓中;牛过秤买通冥府的鬼,阴里转阳,又活过来;张德仁老婆高烧昏迷,赵玫的鬼魂附其身“通说”;寿星老贯患怪病,要么一睡半年不醒,要么一醒半年不睡……
这些描写,使商州系列小说弥漫着幽深的神秘氛围。当这些神秘现实从文化心理深层一一浮现又一一隐入现实中后,一种鲜活的艺术效果产生了:历史与现实、神秘与世俗、传统与现代混沌一体,原始古朴而又灵秀美丽的商州获得了美的展现,既突出了商州地域文化特有的风貌和神韵,又升华了小说的审美价值。
贾平凹为什么爱在商州系列小说中描写神秘现实,让作品产生一种神秘感?在我看来,主要有两个原因。这两个原因对其他同类作品同样有效。一是商州文化本身具有神秘色彩。有文章指出:商州文化的神秘性的来源,归根到底是商州和三秦文化特质。三秦文化包括楚文化因子,商州地理位置的过渡性,使商州亚文化中楚风更烈。〔23〕商州位于陕南,一座为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的主要分水岭及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的秦岭,将它从中原的版图隔开而推至长江流域的边缘。它是南北文化的过渡区,又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区。商州地理位置的独特造就了它文化的独特,它与曾有13个封建王朝建都的西安古城毗邻,长期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因此它的文化在思想观念上接近中原文化,但在文化的风俗风情与精神上,它又有楚文化风范。楚地浓郁的巫风神气浸透到它文化的各个层面,从表层到中层到深层,形成世代累积的文化遗存。而现实的商州由于山高林深,闭塞落后,原始传统的文化遗存与山与民同在,翕然成风。贾平凹说:“商州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一片相当偏僻、贫困的山地,但异常美丽,其山川走势,流水脉向,历史传说,民间故事,乃至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构成了极丰富的、独特的神秘天地。”〔24〕贾平凹在商州山区生活了20年,深深地体验了商州文化的内涵,加之他后来有意识地研析佛、道与民间的各种神秘术如风水、相术、算命等,使他对神秘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因此,当他在描写商州时,神秘文化也被他自然地吸纳进来了。“这有时还不是故意的,那是无形中就扯到这上面来的。”〔25〕描写这一切,“并不是一种装饰,一种人为的附加,一种卖弄,它应是直接表现主题的,是渗透、流动于一切事体、一切人物之中的。”〔26〕二是作者创作个性与美学追求所致。贾平凹对中国文学重精神、重感情,重气韵的传统心驰神往,经用心历练,终于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尽管他后来一再推崇秦汉文化的粗犷、浑厚、有力、心向大汉之风,但本质上,他始终是一个浪漫的、写意的、诗人气质的作家。楚风的浪漫的抒情、写意诗化的传统对他创作个性的形成,比其他任何传统文化对他的影响都大。只要看一看他对爱情的描写,对生活、生命的女性化的感性把握与抒写方式,以及拙朴而又幽柔的语言风格,就会确认这一点。在他的小说创作中,非现实性的神秘文化后来居上,势所必然,既是文化的追求,也是美学的追求。
魔幻:非现实的现实幻化
察香生前积德行善,皈依三宝,戒除了女人天生所具有的“五毒”,〔27〕广积资粮,功德圆满。在洞中隐居修行的高僧默默地为她超度亡魂时,她的脑门突然破裂,脑浆飞迸。察香的灵魂从头颅里飞出升向了天界。随后尸体自动被抬起飘出门外,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托向哲拉山的一块奇峰上。
这是西藏作家扎西达娃的中篇小说《西藏,隐秘岁月》中的一个情节。终身虔诚地供奉隐居山洞修行的高僧的察香,造业受报,死后灵魂升入“六道”的最高境界:天界。这个情节是荒诞神秘不可信的,但它不是将现实非现实化的荒诞,也不是将非现实现实化的神秘现实,而是非现实性描写的又一种形态——魔幻。它表现了佛教的“果报”观念。果报观念是非现实的,不过,在民间它是被当作现实来对待的。把非现实的果报观念以魔幻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被表现出来的形象是幻化的,实际上不存在的,但在这个幻化的形象里暗含着一个幽深的观念,即佛教的果报观念。魔幻的形式包藏着观念性的现实存在,这就是魔幻有别于荒诞和神秘现实的关键所在。
这地方吃紧,为了把它讲得更清楚,我们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入手。
同荒诞一样,也只有将魔幻放到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才能对它的性质和艺术功能作出准确的论述。
魔幻现实主义是本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拉丁美洲形成和发展起来,一直持续至今的一种文学流派,由于成就斐然,成为当今世界文学的奇观。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特点是把现实放到一种魔幻的环境和气氛中,为现实创造出浓郁的魔幻色彩,却又不损害现实的本质。
这一创作方法的产生,并非凭空臆想,而是以现实为依据的。拉美作家认为,魔幻就存在于现实中。古巴作家卡彭铁尔这样描写拉丁美洲:“拉丁美洲的生活,从根本上讲,就是不连贯,异乎寻常的怪诞。在拉丁美洲,一切都显得不符合常规:崇山峻岭绵延无际,群峰叠嶂杳无人烟,瀑布千仞凌虚而下,荒原广漠无边无沿。密林深处虚实莫测,繁华城市建在飓风常常侵袭的内地,古代的和现代的、过去的和未来的交织一起,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和封建残余结合在一起,史前状态和乌托邦共生共存。”〔28〕这样的现实本身是神奇的,又是魔幻的,但魔幻不等于“神奇的现实”。
何为魔幻?何为“神奇的现实”?二者之间究竟有何区别?委内瑞拉评论家马尔克斯·罗德里克斯在1974年发表的论文《澄清有关阿莱霍·卡彭铁尔和两个问题》中对此作了科学的表述。他说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家与神奇现实的艺术家是不同的,当读者看到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关于升腾的情节时的反应,大概和在读到《这个世界的王国》中马康达尔被处以死刑,被火烧着的时候,人们看到它变成一只飞禽振翼高飞的情节所产生的的反应是不相同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他的作品里,对基于民间信仰的场面作了想象上的加工,而卡彭铁尔不是加工一个想象的事实,而只是囿于把当时记录下来的情况如实地转达给读者。后一种情况当然也有艺术上的加工,然而这是不同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加工。在魔幻现实主义中,魔幻在于艺术家;而在神奇现实中,神奇却在于现实。〔29〕这段表述与因贝特对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下的定义是一致的,“作者不是拿魔幻的事物当作真实来表现,而是把现实作为魔幻事物去描述”。〔30〕这里的“现实”,不是指客观物化的现实,而是指观念化的现实。阿斯图里亚斯的一句解释很重要,“在那里,人对周围事物的幻觉和印象渐渐转化为现实”,〔31〕再将现实魔幻化。这就是魔幻同神奇现实(即神秘现实)的根本区别。
拉美作家坦言,他们运用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非要回避现实或消解现实,另外虚构一个虚幻的世界,而是要面对现实,用魔幻的形式深刻地反映现实,表现存在于人类一切事物、生活和意识中的种种神秘。
这些论述符合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的实际。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中,尤其是在长篇小说中,普通现实、神秘现实、魔幻三个方面的内容融合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其中,普通现实是作品的主体,神秘现实作为非现实的现实,一方面与普通现实一并进入现实范畴,使现实具有神奇、神秘的色彩,一方面又通入魔幻,为魔幻超现实的腾升提供基础。魔幻则弥漫于其间,起着渲染地域文化特色,揭示民族文化心理,以及原始感情、意识、观念与现实关系的作用。
新时期作家中,西藏青年作家扎西达娃最得魔幻现实主义的真谛,他80年代创作的小说,被称为西藏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在《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世纪之邀》、《风马之耀》、《悬岩之光》等小说中,我们能看到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许多典型的艺术表现方法在这里汇集,能感觉到马尔克斯,或者是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们的魅力。这个携着古老又携着现代的扎西达娃,“把神秘的西藏从宗教和神话传说的浸泡中,从遥远而切近的岁月长河里拈出来,攥在手心儿里,用力揉捏,然后蓦地将巨掌松开,便从那里面飞出一个个富有魔幻与荒诞意味的故事。”〔32〕《西藏,隐秘岁月》中,米玛为母亲清洗身子时,从空中飘来一张偈语正好落在母亲干瘪的胸脯上。一位外道的持密修士修“起尸法”致死加央卓嘎,在静修中,他没有咬住女尸的舌头,反而被女尸咬住舌头致死,而女尸因此起死回生。从未生育过的察香到了近70岁时突然怀孕,两个月后生下次仁吉姆。次仁吉姆两岁时显示出诸神化身的奇迹。次仁吉姆的父母祈求隐居山洞的修行大师为女儿出家当尼姑受戒加持,突然,一条纯白的哈达从洞中飘出,挂在次仁吉姆的脖子上。房前的大石头会慢慢移走。神秘老人从天而降……《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中,扎妥寺第32位转世活佛弥留之际,在幻觉中对一男一女两个去找通往人间净土香巴拉之路的康巴青年指点迷津。他对“我”讲起的这两个青年来到帕布乃山冈的事,恰恰是在背诵我锁进箱子里谁也没有看到过的关于婛和塔贝的虚构小说。我翻过喀隆雪山后,时间开始倒流,手表上的指针向反时针方向作快于平常5倍的速度运转。当我带着婛从莲花生大师的掌纹地往回走时, 时间也往回走。《世纪之邀》里桑杰去参加好友加央班丹的婚礼,不经意中,城市在他身后消失,他突然走入加央班丹前世的故乡——桑堆庄园。虔诚的村民们在等待沦为囚徒的加央班丹少爷的到来中衰老,而加央班丹在流放的路上则逆生长,从成人——十几岁的孩子——儿童——婴儿,最后缩进一位女人的肚子里成了胎儿,至此,生命处于零度生长状态。……在扎西达娃的这些小说中,魔幻始终纠缠着现实,消解着现实,同时又猛地扎入现实神秘的深处。魔幻描写成了扎西达娃表现西藏神奇魔幻的地域文化色彩,藏民族文化心理的神秘性的重要手段。魔幻中深含着扑朔迷离般的神秘意识,映现出民族心理的巨大阴影。——一个以原始宗教、苯教、佛教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庞大的神灵主宰着高原雪域的藏民族,其文化心理积淀着沉重的历史负累。魔幻是构成扎西达娃小说的基本内容之一,通过魔幻描写,他的这些小说在奥秘费解中差不多蕴含着一个共同的思想指向:思考原始感情、意识、观念与文明的现代进程之间的关系;对本民族文化价值进行的现代审视和评价,基本持一种反省和批判的态度,同时又寄托着美好的希望。正如《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的结尾所示:我代替了塔贝带着婛往回走,时间又从头算起,预示着一个新的轮回的开始。
到贾平凹的《太白山记》、《烟》,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格局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魔幻的成份增大,大多数情况下,魔幻内容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或主体形象,现实的成份相应压缩。《太白山记》由20篇故事组成,除《领导》、《饮者》、《父子》、《儿子》4篇外, 其他16篇为魔幻现实主义小说。死去的爹夜夜还魂与守寡的娘行房事而娘朦胧迷幻、浑然不知(《寡妇》);猎手与狼搏斗,到头来发现狼幻变为人(《猎手》;木匠杀人灭口,用斧劈下的人头竟是一层厚厚的垢甲(《杀人犯》);一觉睡丢了头的无头香客到处找头(《香客》);公公仅是“意淫”媳妇,却使媳妇连生下几个酷肖公公的孩子(《公公》);丈夫外出一趟,妇人往回年轻一次,最后竟变成美丽绝伦的少女(《丈夫》);一高寿老翁逆生长,80年后还童继而又进入子宫,成为一妇人的新生儿(《村祖》);儿子的影子有感觉,人影一体(《丑人》)……这些魔幻描写,将观念、潜意识、生命体验幻化为非现实的实体,诡秘玄奥。它们的意蕴深浅不一,《观斗》、《小儿》、《丑人》、《阿离》、《香客》等篇的意蕴深潜而又飘逸,你或许能感觉出什么,意会到什么,但又难以将其确切地全部表述出来。尽管它们的具体意蕴有些是朦胧的,但深究揣摩之后,其整体的意蕴还是能把握的,那就是以魔幻的形式对世界、存在、生命以及现实作出玄奥幽秘的体验和感悟。
《烟》将佛教的“轮回说”、“阿赖耶识缘起说”(宇宙本体论)具体化——现实幻化,对宇宙人生之谜作了形而上的佛学式的回答。 7岁的石祥突发烟瘾,恍惚中显示出知道前世的特异功能。80年前,他的前身是一位面目俊秀、威武显赫、神功盖众的山大王,即使抽烟也极有神功,能吐出神奇的烟圈套住想暗算他的人。山大王遗落在古堡乱石之下的烟斗,80年后竟被他的来世、7岁的石祥凭记忆, 奇迹般地从人迹不至的险处找到。石祥成了南疆的一位军人。在前沿的石洞里,石祥犯了烟瘾无烟可吸,昏迷中又梦见了来世。他的来世是一个囚犯。如今,他成了一个通观三世的奇人。现世的石祥无烟可吸,梦中他的来身也面临无烟可吸的困境,一直到死才抽上一口烟。当石祥从昏迷中醒来时,一块飞进石洞的石头击中了他的脑袋。临死前,他终于抽到了一口幸福的烟。石祥死后化为烟,化为阿赖耶识,〔33〕复归于宇宙的本原。
石祥三世消失了,“烟”却浮升为一个巨大的意象。烟既是石祥通观三世的诱因,又是存在于宇宙的一种神秘力量,它摆布着人的生死。它还是一个神秘象征,无论是昔日显赫一时的山大王,今日守边关的军人,还是来日的阶下囚,都不免一死,化为烟。人生如梦如烟,空无虚幻,在漫漫宇宙中,唯有阿赖耶识是创生一切的永存。
《烟》为探究人生的意义提供了佛理阐释的视角,但它蕴含的“轮回观”和“五蕴皆空”的思想,也容易引发消极的思想,这一点,应引起作家和读者的注意
结论
非现实性描写是我考察新时期小说的一个视角,从这个角度我看到了非现实性描写的意义和价值。
非现实性描写中的神秘现实描写,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窗户。中国传统文化历来由正统文化与非正统文化、官方文化与民间文化、普通的经验性文化与神秘文化构成,神秘文化是非正统的、民间的,它虽然常常受到正统文化、官方文化的排斥,但它同正统文化一样,既然是历代人民在生产劳动实践与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就必然要以物化的形式融入世俗生活中,以观念的形式沉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作为文化遗存世代相传。从这个意义上说,新时期作家描写神秘现实,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猎奇心态与怀旧情结,而是用一种科学的历史眼光对民族文化进行发掘与重新认识,表现民族文化的丰富性。
神秘现实描写通向传统文化,但着眼于当代和未来。它在揭示中国传统文化神秘性的浪漫情怀展示中国文化丰富性之时,强调了神秘文化对于构成地域文化特色的重要性。也就是在这个方面,它既让我们看到了神秘文化的价值,又让我们看到了神秘文化对于文明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负累。
非现实性描写对于当代文学的发展无疑是有益的。荒诞描写与荒诞小说,魔幻描写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为当代小说提供了新的小说品种与新的艺术表现手法,拓展了当代小说的发展空间。神秘现实描写接通了文学传统,丰富了当代小说的内容。不过,这一切都是有限度的,一旦它们在作品中泛滥,遁入消极虚无,于文学于接受者都是有害的。例如荒诞小说,一般指向现实及存在的荒诞,虽然它不是一味地诋毁、否定现实及存在,但当作家的创作意识与生命体验中溢满了荒诞感后,极易走上价值虚无主义之途,视整个世界、人生都是荒诞无意义的。关于这一点,西方的荒诞文学作了一次极充分的演示。当荒诞派戏剧将荒诞推向极端时,同时也将荒诞文学引向终结。这方面,中国作家应引以为戒。
注释:
〔1〕〔2〕〔4〕苏珊·朗格:《崭新的哲学》, 理查德·蔡斯:《神话研究概说》,菲利普·惠尔赖特:《论神话创造》,引自约翰·维克雷编:《神话与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16 —17、23—24页。
〔3 〕路易斯·莱阿尔:《论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引自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194 页。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序言第11页。
〔6〕女作家斯妤近几年来由散文创作转入小说创作, 以“新小说”创作为当前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素质”。小说《故事》、《梗概》、《红粉》、《风景》、《梦非梦》、《线》、《走向无人之境》、《蜈蚣》、《出售哈欠的女人》等,以书写人的“生活的荒诞”,现实的荒诞为旨向,是新时期文学中,在荒诞小说创作方面最有成就的作家之一。
〔7〕吴义勤:《遥望废墟中的家园——斯妤小说论》, 《当代文坛》1996年6期,第13页。
〔8〕引自廖星桥:《法国现当代文学论》,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3页。
〔9〕参见赖亚生:《神秘的鬼魂世界》,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年版,导言第1—2页。
〔10〕陈来生:《无形的锁链——神秘的中国禁忌文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3年版,第4页。
〔11〕〔12〕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96、97页。
〔13〕引自米尔希·埃利亚德:《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62页。
〔14〕樊星:《贾平凹:走向神秘》,《文学评论》1992年5期, 第77页。
〔15〕〔16〕〔17〕〔18〕〔20〕〔21〕〔2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4、429、154、447、64、423、425页。
〔19〕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1 年版, 第280—351页。
〔23〕崔志远:《贾平凹神秘心理图式探源》,《河北师院学报》1996年4期,第68页,
〔24〕〔26〕贾平凹:《求缺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29、334页。
〔25〕见贾平凹、韩鲁华:《关于小说创作的答问》,《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1期,第35页。
〔27〕五毒,即贪心、忿怒、愚痴、娇矫、嫉妒。
〔28〕〔29〕〔30〕〔31〕引自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201—202、200、197页。
〔32〕王绯:《魔幻与荒诞:攥在扎西达娃手心儿里的西藏》,引自扎西达娃:《西藏,稳秘岁月》,长江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 第387页。
〔33〕《烟》中将“阿赖耶识”说成“古赖耶识”,有误。一些评论文章也以误传误。阿赖耶识,法相宗所立心法“八识”之第八识。八识为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末那识和阿赖耶识。前六识是依据“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对于见、闻、嗅、味、触、思虑所起的作用而产生的。第七识末那识指“执持我见者”,也就是“我执”。阿赖耶识别称“种子识”,它蕴藏着变现万事万物的潜在功能。是一切事物的根本,也是生死轮回的主体,具有能藏、所藏和执藏三种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