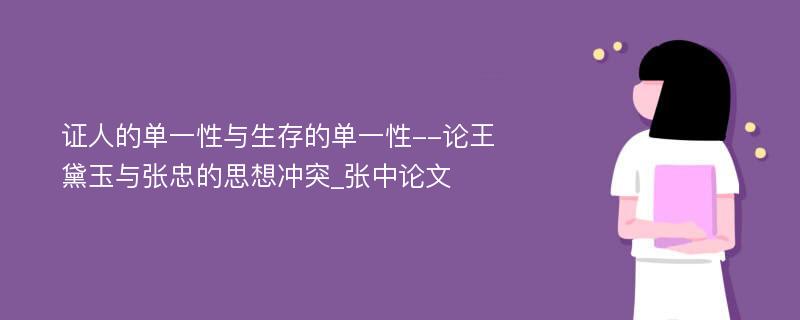
见证的单一与存在的单一——试论王岱舆与张中的思想冲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试论论文,见证论文,冲突论文,思想论文,王岱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
在中国宗教史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明清之际伊斯兰教汉文译著非常值得注意。南京学者王岱舆(约1570—1660)和苏州学者张中(1584—1670)是当时江南伊斯兰学界最著名的两个学者。王岱舆和张中都有汉文著述传世,影响很大。王岱舆和张中生活的时间相近,主要活动的地域都在南京一带,他们有没有学术上的交流和争论?如果有,那么讨论、争论的实质问题是什么?和当时域外伊斯兰教的学术思潮有没有关联?研究这个问题,对伊斯兰教思想的本色化有什么价值?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
王岱舆著述之旨有二,一为对外阐教,一为教内去蔽。阐教与本文主旨无关,今只谈去蔽。《正教真诠》有《易真》一篇,专谈去蔽问题,此文对《证主默解》指名批评。“所谓易真者,……惟恐精于文翰,而鲜知经义者,纵然资性明达,惜乎未经正指,遂以异端之学,搅乱清真,虽然似是而非,但其巧媚能夺人之心志,此清真之最恶,正人之深忌者也,若《证主默解》是也。”① 但是《证主默解》一书的内容,除《正教真诠》此处所引文字,无人提及,大概都以为已经失传了。张中的第一部著作是《克里默解》,长期流传不广,有人也认为早已失传,一般以佚书视之。两者之间有什么关系,自是无从谈起。很幸运,《克里默解》在甘肃被发现,1983年第2期《中国穆斯林》刊出,从此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杨晓春比较《正教真诠》所批评的《证主默解》和《克里默解》,发现《正教真诠》引述《证主默解》的内容,不少可以在《克里默解》中见到。《正教真诠》所引《证主默解》的文字,有的系综合《克里默解》两处文句而来,有的与《克里默解》完全相同。他认为《克里默解》就是《证主默解》,二者是一书两名。②
季芳桐归纳王岱舆所批评《证主默解》主要有四点:1.万殊一本,彼此不分,岂特人类而已,虽鸟兽昆虫,莫不与造物一体,略无差别。2.认为“眼耳是我,观听是主”。3.至圣乃主宰显化,开示迷人,普济万世。4.主宰备有万物之性,为万物根本,为万物大父。无主宰则无万物,物自主宰而生,主宰不从万物而出。他认为王岱舆所批评的只有某些文句存在于《克里默解》中,然文意并不相同。不能因为一些文句、比喻相近、相同,就断定彼此为一书。杨晓春的观点不能成立。③ 同时,他也承认,如果《证主默解》错误同时存在于《克里默解》中,《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是一书两名便毋庸置疑。
王岱舆不是一个遵守所谓现代“学术规范”的学者,他在批评《证主默解》的时候,不是对着《证主默解》一句一句找出来批评的,他批评的是一种思想,如果张中的其他著作,刊印于《正教真诠》成书之前,思想和《证主默解》一致,就不能排除王岱舆所批评的内容来自这些著作,而把它们和《证主默解》放在一起批评。如果《证主默解》中体现的思想,能够在张中的其他著作中找到,王岱舆和张中有思想分歧的观点就依然能够成立。
事实上,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的思想,确实和张中的思想有关。成书早于《正教真诠》的《四篇要道》云“心相既除,虽具人形,其一动一静皆属真主矣。故经中赞许如是之人为喇巴呢,即所谓凭主观、凭主听、凭主言者是也”④。显然和“眼耳是我,观听是主”的看法一致;“知以麻呢原根是真主所垂赐,便见真主是其原根矣!”⑤“天地万物生生化化之理,皆凭真主本然而有而在。且如草木一茬之细,一核之微,其色香花叶相传而生,经亿万载而不变,其根于有荣枯,其受命流形处,绝无变更也。于此参之,苟非无根之体,安得万古常然。”⑥ 和“主宰为万物根本”的观点相似;而“经言真主止一,训之者云:此一非数中之一。此处言一切者,当知非徒指真主而言,正是明我人本地风光如此耳。故曰:我同真主一切尊名、妙用,圣人谓真主造化阿丹在其模样上,即是此义。在犹肖也。模样,或云指真主一切动静言”⑦。“真主无似无相,故曰清。圣人作为一尘不染,故曰净。此节指念清净之言,便是清净实际处。是主钦差全体呈露,将来与人看个样子之意。若是单以遣命为论,便失经旨。”⑧ 明显和“至圣乃主宰显化”的说法一致。如果把《四篇要道》和《克里默解》放在一起看,杨晓春的结论似乎可以成立。
伊斯兰教义学来源于阿拉伯语‘Ilm al-Kalam,一般译作“凯拉姆”。事实上,张中用的“克理默”就是该词的另一种音译。‘Ilm al-Kalam的本意为“对话”,引申为“思辨”,凯拉姆学就是伊斯兰教各派讨论信仰教义教理等问题中产生的。中国穆斯林学者常译为“教义学”、“认主学”。因其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真主独一”,有时亦称“一神论”(‘Ilm al-Tawhid)。⑨《克里默解》一书,所讨论的就是认主独一的问题。《证主默解》就是《克里默解》,一依其音,一用其义,两者确是一书两名。
《正教真诠》的定稿在1657年之前(何敬汉序作于1657年),《希真正答》约略同时(马忠信的序作于1658年)。张中的《克里默解》有崇祯四年(1631年)的序跋,定稿应在此前,《四篇要道》有顺治癸巳(1653年)沙维崇序,则定稿也应在此前,两书都早于王岱舆的著作。《归真总义》是张中在南京听印度学者阿世格讲学的笔记,付印在顺治末或康熙初年,但成书则可能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⑩。付梓之前,已有流传,同时阿世格在南京讲学三年,有一定影响,王岱舆作为南京学人,对其相关内容,明显也很有了解。(11) 本文即尝试分析《证主默解》和《四篇要道》、《克里默解》的相关文字,看看王岱舆批评张中的根本原因在哪里。
二、王岱舆与张中的主要学术分歧
王岱舆和张中都承认,伊斯兰教的首要问题是认主独一。张中说“一切经典中都教人以认主为本”(12),王岱舆说“客问,正教之本?答云,认主”(13)。在看重认主独一这一点上,王岱舆和张中表面上并无分歧。但是对“认主独一”的理解,两人看法并不相同。正是在这一点上,王岱舆和张中表现出明显的思想分歧,这就是《正教真诠》指名批评《证主默解》的根本原因。
张中承认真主是万物的主宰,“主者,造化天地,宰制生灵,始终万物者之总称。”(14) 同时认为万物是真主的显现“万物之所有,皆主之所有;万物之所在,皆主之所在。不识者见之,以为物之荣枯生死;识者见之,以为主之运用大能。故曰:见物即见主矣!”(同上,第25页)一切存在,都是真主的外化,“‘真主止一’,是要人晓得天、地间万事、万物,总是一理,改头换面在那里。譬如以金造器,体质本金,只是名、相不同;但名、相有时败坏,所以为那名、相的恒古常存,然毫无更改也。可见一切‘诸有’,乃是真主的‘有’。除了真主的‘有’,更无别个‘有’了。故又是一句说到‘无伴在主’。”(15)
人心性合天,“真主、天仙、经书、圣人、幽明、善恶、生死总不外我一身耳。绎师之言,当知我之一身,其关系非小。”(16)“天借人传,人显天道;无斯人,则主之功化不明;观其人,而后主之体随用露;主无形似无如何,人之形似如何,即可以证主也。如是而后乃知大化生人,本无凡圣,同源共脉,的的不爽。推是性习远近,上智保而庶民失,君子存而庶民去,此人心皆由危,而道心所由失。欲证本真,须循圣行,圣人之所为,吾为之,圣人之所禁,吾禁之。行尧行而是尧,行桀行而是桀。穆罕默德,主之钦差,即人之榜样。诚能依圣而行,何虑天人歧路?第人高视天而卑视人,尝谓真主至尊,吾人宁敢参与?曾不思目视、耳听、手持、足行,我果能乎,亦主能乎?如谓主能,则我适为证主之。奈何不敢以我作证也?不敢以我作证者,是自任庶民,自离君子,吾恐禽兽去斯不远矣。”(17)“总而言之,万物未生之先,浑然一主。万物原是‘无’的,真主俄而从‘无’中造出‘我’这‘有’来。譬如水中显的冰泡,以水为体,了不离水,到了冰消泡散时,依原是水,绝无彼此对待也。可见真主造化物我之后,真主居然在耳。人自当面错过,反把天、地、物、我这些假相当真,迷头认影,忘却本来,只管在这里边寻索受用,幻中觅幻,无路归真,乃致堕灭。人若肯因天、地、物、我‘原无’的道理,各付之‘原无’,如父、母未生前相似,一无所着,身子虽做世间事,心却不为世间牵引,无心于事,无事于心,一味听其自然行去,这此间杂自然融化,原复如初,惟有真主超然独在。”(18)
万物与人原属一体,“实见得己性、人性、物性,俱在真主调养中,是晓得万物一体也。”(19)“米洒格,是气聚理分,天人剖判之际。要知分聚二字,乃影子话,不必泥是。……鲁合者,此云天命之性也。或问只今全体呈露,其意何如?曰:比如水聚成冰,其明昏通碍。虽云差别,然总是一水管摄。此义《勒娃以哈》论之甚详。可见浑体是冰,而浑体是水也;故曰全体呈露。但水是原有的,冰是新生的,而冰有昏碍聚散者,皆新生之故也。”(同上,第108页)“万相既无,岂非只有真主乎?故曰:‘定有’。人因蔽于一物,不能放下,故不遂其本初,便当下自迷,不能见其真主,若推开万相,见物非物,此时境界方是真正清净实际。……人能体贴清净之旨,通身放下,一尘不染。即如浮沤一散通身是海,此中觅我了不可得。故云只有真主常有常在。”(同上,第21页)“即人人当存此心,不专在权位之有无者。如此看,才得一体万物之意。天经云:‘一切穆民即如一体兄弟。’夫一体兄弟者,乃互相为兄弟也。同气连枝,谓之兄弟。今人一膜之外,痛痒不关,何异自披其面,自断其手足也哉!”(同上,第48页)
人能认识真主本然,“只要一心领受,一定行去,不拘智愚,竟直归于主上,自然不灭常存,而与真主毫无间隔矣。”(20)“凭真主说话为真言,人形虽具,其体已属真主矣!”(21)“天经云:‘主将以玛尼与在他们心间。’……主与二字可味,如月浸寒潭,与之无有丝毫欠缺,亦无丝毫间隔之意。”(同上,第40页)“‘我同以玛尼,以玛尼在我矣!’……同之一字,着眼乃一体之意,莫作偕字看。须以从心之从字看,是其妙用返照处,非人功可议,故随即云以玛尼在我,便见其旨绝非两层。始终提我字,见以玛尼之在与不在,系与我之同与不同耳!此又欲人瞬存息养,不得悠悠被境缘流转之意,所谓尽人合真是也。……上文言同、言在,似乎以玛尼与我犹为二之。此章言外,有扫除同、在二字之意。言到穆民地位,一私不染纯粹无杂,直合本然清净。”(同上,第43—44页)“盖真主本然至清至净,吾人能一私不染,通身放下了,其本然即与真主毫无间隔矣!”(同上,第20页)“垂赐乃印照之意。如镜写容,是一是二非彼非此。要知以麻呢原根是真主所垂赐,便见真主是其原根矣!”(同上,第18页)“令我认者谓真主原赐本光在我,故能照彻自己清净本然。原赐本光,即非受造化之以麻呢也。凭我主,是凭此原赐本光,认我主之本然。一比如珠体与珠光,光从体现,光还照体。究意到此,即通身放下一语,亦觉剩赘。”(同上,第100页)“前半截,言认得真主本然是原有的;后半截,言认得自己是新生原无的。无的还无,有的常有。如冰涣水,那里分个两项。通章文面似分开,其意在合并,不可不知。”(同上,第101页)“雪消成水,自合本来,岂俟借待。……心相既除,虽具人形,其一动一静皆属真主矣。故经中赞许如是之人为喇巴呢,即所谓凭主观、凭主听、凭主言者是也。”(同上,第103页)“如镜写容,无不毕肖。无吃无饮,观不凭眼,听不凭耳;言不凭舌,所以为不凭私意,不凭己私则皆顺命而行,顺命而行则我之所为皆化为真主动静矣。”(35页)“我相融而真主现,是何等紧要。譬如雪消成水,含着本来,岂待商量做作?细参上下文理,本是一意相承的。”(22)
王岱舆认为,单另之一,乃造化天地万物之真主,而与天地万物无干,“真主止一,无有比似,乃无始之原有,非受命之有也。……须知真一乃单另之一,非数之一也。数之一,非独一也。……诸所谓一,乃天地万物之一粒种子,并是数一。真一乃是数一之主也。……若夫真一与万物而同在,其原有新生,是无别矣。”(23)“所谓本然者,原有无始,久远无终,不属阴阳,本无对待。独一至尊,别无一物。……能命有无而不落有无;造化万物而不类万物,绝无比似,此真主原有之本然也。”“自己原有始终,而有来去。真主本无起尽,而无方所。设以有始有终之人品,而欲穷无起无尽之真主,何异于水火方圆,强自合为一局,必不能也。……至于真一、数一、体一之间,有主仆、圣贤、至大之别,尤不可不察也。”“真一单独无偶,固为原主;数一为万物之根,故称大父。若非真一,岂有数一?然兹无极之数一,不是原主,而实本原主之能有也。”人“以区区萤火之微明,而欲较真主无量之玄妙,亦妄诞之甚矣”。(233、240、242、141页)
人不可参悟真主之本然,“经云:‘尔等在己身,如何不参悟也。’圣曰:‘尔等参悟真主内外之恩赐,不可参悟真主之本然。’何也?本然者,不干声色,不落有无,至玄至妙,无始无终,不容思虑,因人之聪明智慧,文字语言,惟施于上下、四方、始终、声色之内,若超越诸品之外者,虽参悟所及,终觉渺茫。”“凡所有之微物,莫不有主,况天地之巨物乎。天地譬如一座宫室,其中列设即斯万物,但此宫室必有成立之主人,抑知其主人果该耶?须知宫室毕竟是宫室,主人毕竟是主人,未有以宫室即谓之主人也。”(110、42页)
人主根本有别,不可说尽人就能合主。“凡受制生死者乃众生,为其由性命而建立;不落生死者乃真一,为其无起始而原有。先天为命,后天为性,命非性,不离于性。命为种于而下降,性为果于而上升,虽同一体,其实有异。至此方知无始之谓‘主’,有始之谓‘人’。是故以己受命之形神,方显露能造生死之真主,此至大之别也。”“夫人之观以目,听以耳,有远近,有方位,有阻隔,有晦明,有断续,有盛衰,有大小,与主迥不相似,何以妄言人之观听乃主之观听。”“独一与万物无干,数一乃物之资始,岂可淆混不分,只言万物之本原,不识万物之真主可乎?……切不可以天地万物之大父,而当天地万物之真主也。……清真至道,惟言造化万物,能命万物生死,不言孳生万物,而予万物一根一种也。是故惟称真主,决不言根本,……子孙万亿,固出原父一人,然原父不能命子孙生死。夫众父之父,万有之根,乃至圣之品,所以清真只言真主,而不言原父者此也。凡以人类而为主宰,以至卑而僭至尊,诚迷之甚矣。”(245、45、46页)
绝不可合万物为一体,这是大本大原的问题,“真主乃无始之原有,人极乃有始之原宗。无始无终者,惟有单另独一之主。其尊大清静皆具于己,不假乎外,无天地万物亦不灭,有天地万物亦不增。此外人神天仙,莫不有始,然不能自创其始,惟真主能创之,其能乃全能,故无所不能。”“是故太极乃真主所立,天地万物之理,而后成天地万物之形。凡达此理者,必不以天地万物之原种,而当天地万物之原主也。”(24)“夫圣人尚不自居于圣,而今世人皆为万物主宰可乎?……智人之心,含大地,具万物,非果有天地万物之体也。”“主仆之分,真一、数一也。若言人同品于真一,则太过;若言人同品于万物,则太卑。真主造化天地万物,或同宗异类,或同类异体,或同体异用,凡欲强之一体,岂不匿造化之全能也。”“所以论万物之殊,或有同体,或有各体,安得合万物为一体也。盖体之相续者为一体,相间者为异休。且人之一类,品逾牛毛,鸟兽何止千种,草木岂啻万端,是渭各同具类,非为同体也。倘泥于万物一体之说,则轻造化,混赏罚,昧同异,一南北,革是非,其妄言之罪不浅鲜矣。”“若万物果为一体,富贵穷通,生死寿夭,安危得失,饱暖饥寒,当无分别,彼此皆同,乃竟不然,何得谓之一体?”(24、42、47、65、66、267页)
天地万物,都是受造,凡人不会和真主同体。“天地若画师之图画,人极譬美人之镜子,无天地则不显其大能,非人极则不显其全品,此真主之自证也。”“若止水明镜映诸万物,即谓水镜之中,真有天地万物,便能造化天地万物,其可乎?言必合行,始可信也。凡人果与真主同体,必亦能造化天地万物,然谁曾造一人一物于此乎?”“动静尚有两分,主仆岂可同浑?少有讹误,永堕迷途,诚可悲悯。……‘海显江湖海若初,江湖原本分明海。休猜此海即江湖,江是江湖海自海。’若水翻竹影,其两体无干,风弄花香,虽同而不共,即此之谓也。”“即若镜外无光,海外无水,美人固在镜中,明月现陈水底,然必不可说镜光外无人,海水外无月。但人能成镜,镜不即是人;月能出水,水不即是月。”(42、231、47、243、61页)
王岱舆承认宗教体验意义上的人主合一,“盖因渴慕至极,偶尔得契,即若酒后无己,但有时而醒。是以诗云:‘醉后言行身不悟,皆因斯酒御形神。星月光辉非寂灭,少时收卷大明中。”但是不可沉迷其中,“动静尚有两分,主仆岂可同浑?少有讹误,永堕迷途,诚可悲悯。……‘海显江湖海若初,江湖原本分明海。休猜此海即江湖,江是江湖海自海。’若水翻竹影,其两体无干,风弄花香,虽同而不共,即此之谓也。”不可因此而忘却人主之别,认性为主,“若夫已有全熔,妙明顿露,不因正教之仙丹,何以点化其自性。然后因缘性解,大性光明,到此田地,始知天地万物为一人,方认得自己乃天地之始,万物之母也。今之人皆误认此一粒无极之种子,为无上正真,顿忘其栽植之真主也。悲夫!”“得道之忍者,乃超越天地,旋乾转坤,起死回生,造化若已。当此之时,得圣人知见,堪入全人品内,可登真主禁中,见天地悬无根,系在尊阙,恰似微尘,显妙明普照万方,在真主乃如萤火。倘若外道无知,认性为主,神通自在,误作己能。”“体认之一,其理总具当身,真性为光明,正心为镜子,身治即妆台,万物为陪侍,此又数一之样式矣。然则美人不与焉,故云:‘美人独另孰何颜,欲显丰姿待可传。妆台玩好工夫备,始现光明宝镜间。’有等醉梦,妄以美人即是镜子。噫!果如是说,美人之与镜光同熔于炉治,共入模范而均受磋磨,其造炉成镜者谁欤?设人中一人,自称与天子同尊,遂与其抗礼,其罪可免乎?况欲与造化天地人神之真主同为一体也。”(240、243、82、118、244页)
三、见证的单一与存在的单一
比较张中和王岱舆的论述,明显可以看见其思想有冲突。其实质,是伊斯兰哲学“见证的单一”与“存在的单一”的冲突。张中和王岱舆都是深受苏非思想影响的学者,但苏非内部情况比较复杂,“有学者把苏非理论分为三派:1、创世派,即真主从无中创造世界,所创造之物并非等同于主的本质;2、见证派,即宇宙、世界是一面镜子,藉以反映主的属性,真主则超验地存在于宇宙万物之上;3、存在派,依据该理论,‘一切是主’”。(25) 很明显,张中的思想接近“存在派”,王岱舆则更接近“见证派”。
张中那里,真主是单一的和统一的。一切有形、无形之物皆系真主的产物,因而是虚幻的,只有真主真实,除真主外,无物存在。宇宙万有是作为真主的一种影子,预先存在于真主之中,从真主中显化出来。宇宙万有本质上都是真主的显化。终将返回真主。本质与现象、真主与宇宙万有实质上没有区别。这显然就是“存在单一论”,这种思想,有泛神论的痕迹。“按照这种学说,唯有安拉是实在,其余的一切则是虚幻的,它们仅仅是安拉神光之‘闪现’。其口号是:‘真主即是一切,一即是真主。’”(26)“世间万象不过是真主的表象,真主是唯一的存在,他使万物得以存在。当真主被遮蔽时,他的仆人同时见到这两种存在。而真主一旦显现,他的仆人将看到他与其他众物毫无关系,视者亲见所视者,见者亲见被见者。”(27) 哈拉智的“入化”说,即真主降临人身,人主合二为一好像也对张中有影响。(28)“入化”说认为真主与世界是融合的,真主和世界内在的作用力是同一的。
这些思想,都有泛神论倾向,引起了伊斯兰教内部的反对。伊玛目·冉巴尼(1563—1624)是著名印度伊斯兰学者。当时印度的卡迪里、车什挺耶等苏菲教团都接受了“存在单一论”的思想,以实际行动推动了泛神论。希尔信迪(即伊玛目·冉巴尼)针对“存在单一论”而提出“见证单一论”。他认为伊本阿拉比的“一切都是真主”的命题混淆了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宇宙是真主的创造物,但创造物不能等同于创造者,真主是必然的、永恒的存在,世界只是暂时的偶然的存在。因此“一切皆真主”,毋宁说“一切皆源于真主”。宇宙万物见证真主的独一存在。他认为,“安拉的自我、品格和行为是独一实在,一切受造物皆为他的意志的‘反映’,因而不能与独一无二的安拉的品格和行为相提并论。正确的提法不是‘一切即真主’,而是‘一切皆来自真主’。苏非教义的宗旨不是追求与安拉合一,而是热爱万能之安拉,见证自我为安拉的‘创造物’。”(29)
伊玛目·冉巴尼认为,“真主不同于世界,他与世界不即不离,不在世界,不离世界,不围绕世界,不贯穿于世界;我知道万物的本体和特性都是真主的所造,被造物的特性不具真主的特性。被造物的行为不具真的行为;而且我知道被造物的行为受真主大能的控制,万物的能力不会影响真主的行为。”(30) 又云“我原来持‘存在单一论’的立场,正如我在信中反复说明过的那样,我把真主的用为、德性看作是根本,当事情真相大白后,我抛弃了这一立场。我认为‘万物皆源自他(真主)’的话,是最好最正确的。我看到这句话比‘万物都是他(真主)’的话有更多的完美性。我从另一个方面知道了真主用为、德性的道理。我看到万物是单独的个体,我的认识超越了更高的层次。我没有了丝毫的疑惑和不解。揭示所带来的一切都符合教义教律,其中与教义的表意无有一根发丝的矛盾”(31);他认为“‘见证单一论’是‘觉单一’,即行道者所见的只是一个;而‘万有单一’是行道者知主认为存在者只是一个。他推测和认为,其他的都是无的、不存在的。在认为其他的都是无的、不存在的同时,他妄称其他的一切都是那一个的显然、镜子。万有单一思想(否定真主的本然以外的东西存在的思想)是与理智、教法相悖的。万有单一论家们,他们所见的只是见证单一的幻影,而并不是说,他们得到了那个单一。实际上,见证单一和这个幻影毫无瓜葛。绝大多数人抓住万有单一理论不放,有的更是以偏教、外道的形式出现,他们主张:一总都来自于真主,不然他们主张,一总都是真主”(32)。
这些都和传统伊斯兰教哲学的看法一致,王岱舆坚持的也是这个观点。
有学者认为“王岱舆对教内的类似于张中的这种所谓‘易真’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实质是正统派对苏非主义的批评”(33)。这个结论虽然没有找到张、王冲突的思想根源,但是已经感觉到了张、王冲突的实质是思想冲突,无疑是一个有学术价值的看法。白寿彝先生早就发现王岱舆、张中思想的不一致,说:“经学家的学风,可以说是大不相同的。”(34) 其实除了学风,思想的差异很可能是差异的实质所在。
清代早期伊斯兰教外来传教人员为数不少,《经学系传谱》云“西域来游之辈,自有清以来,约千百计”。(35) 王岱舆和“见证的单一”思想一致,是否受冉巴尼思想的影响,我们不得而知,张中接受“存在的单一”的思想,则是一个明显的事实。张中和王岱舆,明显有思想分歧,明末清初的中国伊斯兰教学者,在从事汉文著述时,背后有中外多种流派的宗教哲学资源,各个学者的经历不同,取舍有异,他们的宗教思想,并不一致,情况比较复杂。传统上,把明末清初时期活动在金陵一带的张中、王岱舆、刘智回族学者,都划归中国伊斯兰教金陵学派。(36) 或称作金陵学派,(37) 从张中和王岱舆的宗教思想分歧看,这样做有冶朱陆于一炉之嫌。不同师承、不同思想的学者,能不能仅仅因为地域相近,就划归在一起?金陵学派的说法在何种意义上能够成立,这个问题还值得深入研究。
注释:
① 王岱舆:《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余振贵点校,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4—45页。(以下凡引此书,俱简称《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
② 杨晓春:《论晚明江南穆斯林学者的文化纷争——从王岱舆〈正教真诠〉批评的〈证主默解〉说起》,《南京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③ 季芳桐:《王岱舆批评张中一说之质疑——兼论〈证主默解〉与〈克里默解〉的关系》,《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④ 《四篇要道》,马宝光主编:《中国回族典籍丛书》(内部资料),第六册,第103页。
⑤ 《四篇要道》,第18页。
⑥ 《四篇要道》,第98页。
⑦ 《归真总义》,马宝光主编,《中国回族典籍丛书》(内部资料),第五册,第48—49页。
⑧ 《四篇要道》,第19页。
⑨ 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284页。张中云“此学之正义,是学滔黑得”。(《四篇要道》,《中国回族典籍丛书》(内部资料),第六册,第37页。)“滔黑得”就是“‘Ilm al-Tawhid”音译,一般译作“讨黑得”。
⑩ 李兴华等著:《中国伊斯兰教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63页。
(11) 王岱舆所批评的《证主默解》的思想,也常见于《归真总义》。为严格起见,本文不引用其文字。
(12) 张中:《克里默解》,《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2期。
(13) 《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第258页。
(14) 《四篇要道》,第96页。
(15) 《克里默解》,《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2期。
(16) 《四篇要道》,第50页。
(17)(18) 《克里默解》,《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2期。
(19) 《四篇要道》,第109页。
(20) 《克里默解》,《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2期。
(21) 《四篇要道》,第26页。
(22) 《克里默解》,《中国穆斯林》,1983年第2期。
(23) 《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第19页。
(24) 《正教真诠·清真大学·希真正答》,第42页。
(25) 李振中等:《阿拉伯哲学史》,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166页。
(26)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39页。(以下凡引此书,俱简称金宜久,《伊斯兰教史》)。
(27) [埃]艾哈迈德·爱敏著,史希同等译:《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八册),《正午时期》(四),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58—159页。(以下凡引此书,俱简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八册),《正午时期》(四))。
(28) 《归真总义》云“满素尔尊者(哈拉智)一日突云:我是真主。此经书有禁,教法不容者,是以为国人所害。然而千载之下,皆识其为得道真人,此其所谓承领真主断法,而不为法缚者欤。”《归真总义》,第63页。张中师徒对哈拉智是完全认同的。
(29)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第339页。
(30)(31) [印度]伊玛目·冉巴尼,马廷义译,哈三·马鸿章、马永正校译,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麦克图巴特·书信集》,10—11页,18页。
(32) [印度]伊麻目·然巴尼,周进福译,《书信集》,香港:蓝月出版社,第51—53页。
(33) 许淑杰,《明清汉文伊斯兰译著运动再考察》,《世界宗教研究》,2010年第2期。
(34) 白寿彝:《回族人物志》(清代)附卷之八,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3页。
(35) [清]赵灿,《经学系传谱》,杨永昌,马继祖标注,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1页。
(36) 马多勇,《伊斯兰教金陵学派与中国传统文化》,《滁州学院学报》2005年5期。
(37) 参米寿江《金陵学派产生的背景、思想渊源及当代意义》,《世界宗教研究》2009年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