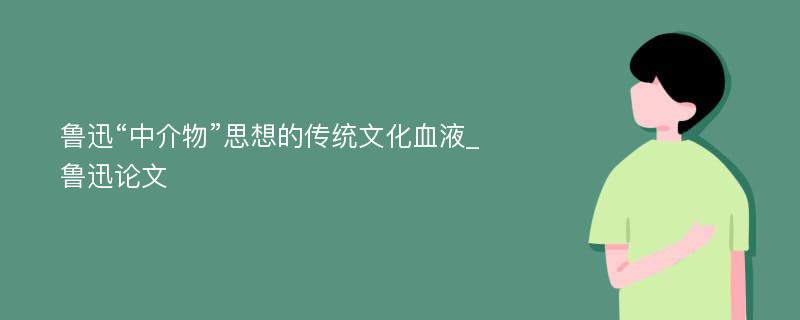
鲁迅“中间物”思想的传统文化血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血脉论文,传统文化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现代启蒙知识分子中,鲁迅是激烈反传统的。但是,对传统的反叛并不意味着反叛者与传统之间毫无关联。恰恰相反,要对传统做出合理的反叛,必须以对传统的深刻理解和认知为前提。作为鲁迅与传统文化相关联的一个侧面,鲁迅“一切都是中间物”的哲学命题使我们看到了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不可分割的历史联系。可以说,鲁迅的“中间物”思想是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思考紧密相关的,正是由于鲁迅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层联系,他才有可能在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对具有所扬弃、有所继承。
解读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可以“天人合一”为切入点。学者王乾坤认为:“要讨论鲁迅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离开了‘天人合一’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因为中国文化的基色或背景便在于此;要认识他的生命的性格,必须将其置于这个背景中才有可能……其实他的整个生涯不仅与此有关,而且紧紧地与此纠缠在一起,正是这种复杂的纠缠关系构成了他的生存境况,没有这种纠缠便没有鲁迅。”
鲁迅首次提出“中间物”这一概念是1926年底在《写在〈坟〉后面》一文中。鲁迅说:“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倒似乎和我不相干。大半也因为懒惰罢,往往自己宽解,以为一切事物,在转变中,是总有多少中间物的。动植之间,无脊椎和脊椎动物之间,都有中间物;或者简直可以说,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当开首改革文章的时候,有几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当然的,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但仍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至多不过是桥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标,范本。”鲁迅的这一段话是由他翻译与写作所采用的白话文与古文的关系而引发的。这是因为鲁迅先生的作品《坟》是一个“古文与白话合成的杂集”。这里我们注意到:尽管鲁迅说了孔孟的书“似乎和我不相干”的调侃的话,但毕竟他承认“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而这种自幼的学习和影响是潜移默化、渗透在骨子里的。这也就是鲁迅常常戏称的他自己身上的“鬼气”吧。另外我们不可把鲁迅这里所说的“中间物”仅仅按“进化论”的观点来理解,因为鲁迅说“一切都是中间物”。既然“中间物”被鲁迅抽象为一个有着指谓一般的概念,“其在鲁迅思想中应该有更高层次的定位。它之于鲁迅,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时间概念,而是说它既是世界观、历史观,也是价值观;既是时间之维(历史的),也是空间之维(逻辑的)”。如果将鲁迅的“中间物”思想这样定位,将其看作是一种“世界观”和感知世界的“方法论”,我们就可以由此追溯到它的中国传统原点,并比较其与儒家“中庸”之道的异同。而将其与中国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我们就找到了深入探究鲁迅精神实质的道路。从广义上看,鲁迅说“一切都是中间物”就是说世界上绝对的完美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鲁迅的“中间物”是指世上一切事物都并非圆满,而是处在一个动态的“中间”的、然而不断趋向于“圆满”的变化过程。由此,鲁迅的“中间物”思想就找到了中国传统文化“贵中”思想的渊源。
鲁迅“中间物”思想与周易贵中、孔子中庸之道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缘源关系首先表现在对待“天人合一”的基本哲学问题上。在孔子看来,“德”是人与天的契合点,这是因为人道与天道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一致的。天的根本德性是当含在人的心性中的,天道运行以化生万物,人若得天地之正气,就可以与天相通。因此,作为宇宙根本的德,也就是人伦道德的根源,人伦道德也是宇宙大道的体现。“天人合一”是孔子“中庸之道”的“无限之至境”。而“中庸”对孔子来说,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但它体现的是儒家对人生理想“中道”追求的进取态度和执著精神。
鲁迅也恰恰是在对他念念不忘的人生“大德”的理想追求的思考中,提出“中间物”的思想的。从鲁迅的“中间物”观点来看,人要与理想的“中庸”之“天”“合一”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人是不可能尽善尽美的,“倘使世上真有什么‘止于至善’,这人世间便同时变了凝固的东西了。”和孔子一样,鲁迅“韧性”的战斗,就是为从有限的“中间物”趋向完美的“中”的理想境界的精神体现。鲁迅对孔子的理想追求精神是赞赏的,他曾说:“‘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即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定要有这种人,世界才不寂寞,这一点我是佩服的。”
除此之外,鲁迅的“中间物”思想与佛教影响也有关系。鲁迅与佛教的因缘来自幼年就开始的对出生地绍兴信奉佛教风俗的耳濡目染,在故乡浓厚的佛教氛围中,佛教文化精神自幼就渗透到他的心灵中去。到了青年时代在日本师从章太炎研读佛典,他的这种对佛教的无意识接受就变成了一种积极主动的汲取和吸收,这是鲁迅在异国他乡接受外来影响时,“内不失固有之血脉”的一种精神追求。在1908年到1918年期间,鲁迅更是在寂寞失意中潜心默化佛教典籍,思想认识不断地向成熟和深刻转化。正是通过这段时间的思考和研究,鲁迅在佛家教义下进行着精神的对话和人格的重整,也正是这种经历使他能够在后来的精神痛苦和病痛折磨的生命历程中,升华出一种大无畏、大了悟的人格境界和生命感悟。鲁迅的“中间物”是不完美的“有限”、“缺陷”、“偏至”和“暂时”,但鲁迅反抗绝望的生命哲学和悲剧性的英雄气质也正是由他的“中间物”的世界观延伸出来的。鲁迅的这种“中间物”含有对“无限”、“永恒”的超越性思考,它是中国传统“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精神的写照。由此,鲁迅成其为“以‘中间物’自任却苦寻无限,不选择圆满却不忘情于终极的思想者。”鲁迅对国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也与佛家对众生不言的悲悯与启示态度相一致。鲁迅在精神的苦旅中,执著不变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挚爱,也有因为他作为章太炎的学生深受其佛教思想影响的结果。由此他始终怀着对这个“有情世间”的挚爱,为寻求光明与自由而抗争,即使失败也不退却,即使“明知道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鲁迅的抗争,是在自觉地甘做“进化链子”上的“中间物”,“肩起黑暗的闸门,放青年到光明中去”,做“进化的梯子”,为青年人铺路搭桥。鲁迅的“中间物”思想是对自我生命的一种深切感悟,是对佛教的“以大智故,不住生死。以大悲故,不住涅槃”的深刻领悟。由此可见,和儒家文化一样,佛教文化也是鲁迅生命意识和精神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鲁迅是在对传统文化的扬弃继承中,在积极汲取儒家、佛教文化的一切合理因子、以现代理性和科学民主精神进行人格和精神的整合重建中提出他的“一切都是中间物”的价值观的。
《周易》所包含的人生哲学还告诉我们世界万物的运动变化,不可固执地拘泥于常规法则,只有变化才是永远的不变。《周易》所说的阴阳和谐中正思维并不是僵化不变的,阳刚和阴柔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和发展着的,而是相互作用和转化的。孔子和鲁迅都以自己的方式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的“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念。孔子和鲁迅都是要通过不同事物间的互动、互补,在变动中达到一种新的平衡与和谐统一。这种新的平衡就是运动变化中的平衡,是“时中”,是“与时偕行”,适时变通,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创新精神的体现。和孔子一样,鲁迅也是一位伟大的变革者。鲁迅对孔子也不仅仅只是否定的批评,鲁迅曾经说过:“孔丘先生确实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鲁迅还认为孔子“不满于现状”,对社会现实是“要加以改革”的。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一文中鲁迅还指出:“至于孔老相争,孔胜老败,却是我的意见:老,是尚柔的;‘儒者,柔也’,孔也尚柔,但孔以柔进取,而老却以柔退走。这关键,即在孔子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无大小,均不放松的实行者,老则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一事不做,徒作大言的空谈家”。由此可见,鲁迅对孔子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进取精神是充分肯定的。也正是在孔子的影响和感召下,鲁迅甘做“中间物”的桥梁,“别求新声于异邦”,成其为伟大的国民思想的启蒙者和新文学的开拓者。由此可见,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鲁迅的“中间物”就是一种改革创新的现代意识。“中间物”思想是在融会贯通中国传统文化优秀因子和外来文化优秀因子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新的更加完美的统一体。也就是说,鲁迅的“中间物”的现代意识与周易的“时中”、孔子的“以柔进取”也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都包含着改革创新的思维和理念。
鲁迅的“一切都是中间物”思想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例如他以生命做“中间物”来翻译沟通中西文化,他主张与不同文化的内在关联,主张以公正和科学的价值标准来评价不同文化,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融合,对民族文化的建构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就文化交流来讲,鲁迅所说的“中间物”不属于中西方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但是它又保持着与原属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这种“中间物”的文化意识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道”优秀因子,又超越于特定的某种文化意识之上,从而可以从更为客观公正的视野下来建立新文化的价值标准,来更新与沟通不同文化之间的联系,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融合与创造繁荣。可见鲁迅所讲的这种新的民族文化既有异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又不同于外来的西方文化,它是一种“中间物”的、世界文化大视野中的崭新的民族新文化。这是因为鲁迅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深刻的理解吸收和批判扬弃,另一方面他对西方现代文化各个层面有着全面的了解与把握,他才能在中西两种文化的对比和研究中提出自己对民族文化的创新见解和思路。
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鲁迅说:“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可见鲁迅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与继承问题上是“好古而不忽今,力今而不忽古”的。鲁迅指出的这一文化继承和发展的道路,是一条与周易传统文化精神相符的“融合”的“中正”之路,它的原则与理念至今仍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鲁迅不仅是最富于中国特色的文化巨人,而且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最能以宏大的气魄、正确的态度接受外国文化滋养的伟大先哲。”由于鲁迅确立了“一切都是中间物”的根本观念,他就能够在思想上超越他人,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解放思想,进行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化转换,而不是像他以前的知识分子那样抱残守旧,紧紧抓住“中学西学”、“体用”、“道器”之类的传统概念不放。由此,鲁迅勇敢地走出固有的传统文化的圈子,去迎接中西两种文化的冲突与碰撞的“中间”地带,探究吸收西方文化中自己所没有的新的文化因子,以利改变更新落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此来迎接“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综上所述,鲁迅说“一切都是中间物”,就是说世界上绝对的完美是不存在的。但“中间物”给我们的启示并不仅仅如此。我们还看到“中庸”之道虽然是凡人所高不可及的至善的“恰好”的度,但人却是可以无限地接近这个完美的“中”的,人是可以也应该有这种精神追求的。这一点是和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致的。由此可见,鲁迅的“中间物”是一种变化发展着的、无限接近“中庸”的完美境界的一个节,鲁迅说:“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可见“中间物”尽管是“不满足”、是有限、是欠缺,但它却有着一种永久性的向上的追求和发展的趋势,而正是这种趋势推动着社会向前发展和生命的不断追求。所以,我们可以有理由说鲁迅的“中间物”思想是对《周易》中道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对中庸价值观的扬弃演绎。正是因为鲁迅从“一切都是中间物”的观点出发,他才能够高瞻远瞩地审视中西两大不同文化的异同,并融合两种文化的合理因子,为本民族的文化指明“外之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的文化发展新方向,理性地以西方文化的参照系来对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来寻找阻碍民族文化现代化的深层文化障碍,从而提出自己的关于人的启蒙,改造国民性,重铸民族精神的主张与思想,而又正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中道思想给了鲁迅“中间物”意识以思想的启迪和演绎的成功。
标签:鲁迅论文; 儒家论文; 孔子论文; 鲁迅的作品论文; 文化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中国传统文化论文; 读书论文; 国学论文; 中庸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