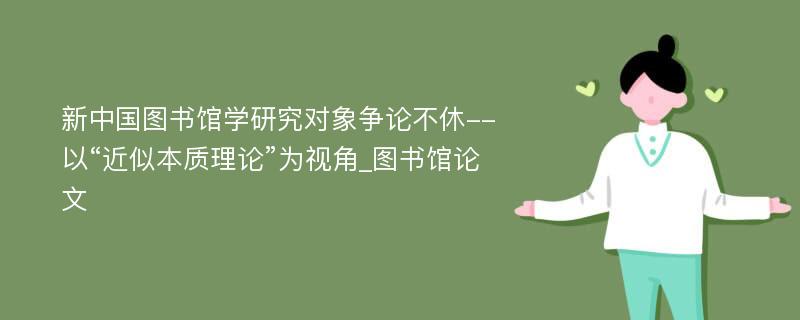
新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争鸣六十年———个“近似本质说”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书馆学论文,近似论文,新中国论文,视角论文,研究对象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250
因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决定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体系结构、学科性质和相关学科等的首要问题,所以,图书馆学者对此问题都特别关注。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国图书馆学者对此问题的探索和争鸣几乎没有停止过,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新观点(即“对象说”),取得了重要突破和进展。学界对此问题的认识大致可分为“非本质说”和“近似本质说”两种类型。因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其中的“近似本质说”之代表性观点进行综述。所谓“近似本质说”,在此是指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已经达到本质性认识的层次,但仍未找到其本质,只是在不同程度上接近了本质性的认识[1]。(注:如果“对象说”跨多个类,则入在我国首先出现的“对象说”,如“文献知识交流说”入“知识说”而不入“交流说”。)
1 个案视域中的中国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诸“近似本质说”及争鸣
1.1 “矛盾说”
1960年,黄宗忠等指出,图书馆事业中藏与用这对特殊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首推“矛盾说”[2]。197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编的一书认为,“收藏”与“提供”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3]。曾浚一(1980)认为,“管理与利用”的矛盾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4]。2002年傅正指出,上述“矛盾说”忽视了图书馆外部的矛盾。因为“图书馆是社会的一分子”,图书馆事业的发展必然受图书馆内部矛盾运动和外部环境因素两方面影响,所以,“研究图书馆的矛盾运动,不仅是研究内部矛盾,还应包括制约图书馆事业发展的外部矛盾”[5]。
1.2 “知识说”
从1981-2009年,我国学者相继推出了不同的把“知识”作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对象说”,统称为“知识说”。
1.2.1 “知识说” 1981年彭修义指出,“知识”是图书馆学的“四大研究对象”之一,首次推出“知识说”[6]。1988年和1992年他又两次发表论文,强调“必须将知识作为图书馆学的一种研究对象”[7-8]。
1.2.2 “知识交流说” 1984年,宓浩和黄纯元首次提出“知识交流说”,并明确指出图书馆是“促进社会知识交流的社会机构”,认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知识交流”[9-10]。王子舟(2002)指出了此“说”的“不足之处”,指出“它能涵盖图书、情报、档案等多门学科,但最后如何返回图书馆及图书馆学中,用于揭示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机理,却显得较为乏力”[11]。李爱民(2009)指出,“图书馆与现代性关联”,“将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界定为‘知识交流’而不是作为机构的图书馆,会使这一关联更具建设意义”,赞同此“说”[12]。
1.2.3 “知识组织说” 刘洪波(1991)、王知津(1998)、蒋永福(1999)等撰文探讨知识组织、知识揭示与图书馆学的关系,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组织”,相继推出了“知识组织说”[13-15]。针对此“说”,学界多人参与讨论和争鸣。金胜勇等(2007)指出,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不应把握在“知识”的层面,应把握在“信息”的层面。因为“我们只有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定位在信息层面,才能使其具有更广阔的适用范围”,“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基于信息检索需要的信息组织”,提出“信息组织说”[16]。这实质上也是一种“知识组织说”。周久凤(2001),储流杰(2002)否认此“说”,详见本文第2部分。
1.2.4 “可获得性论” 梁灿兴(1998)强调,“图书馆学要研究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认为“文献群中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创立了“可获得性论”[17]。2000-2007年,马恒通等多人就此“论”与梁灿兴展开争鸣。马恒通(2000)认为,此“论”因缺乏专指性不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详见本文第2部分)。朱少强(2003)指出,此“论”“自身也没有摆脱‘就文献论文献’、‘就馆论馆’的倾向,表现出思维上的局限性”,如“图书馆员是直接推动图书馆的力量”等[18]。王梅(2004)指出,此“论”“远离了图书馆活动和图书馆学的社会本质”,不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19]。张辉(2004)认为此“论”缺乏人文性,强调建构人文图书馆学的必要性[20]。黄宗忠(2006)指出此“论”不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详见本文第2部分)。孙长虹(2006)认为此“论”对图书馆并无特殊性,情报、目录、档案、文稿编辑等也同样存在此“论”[21]。葛园园(2007)就“图书馆发展的内在动力”等问题质疑此“论”,指出此“论”缺乏专指性,不能与情报、档案区分,而且“这一可获得性的立论基础也是站不住脚的”[22]。
1.2.5 “知识集合论” 王子舟(2000)认为,图书馆的研究对象应转向“知识集合”,知识集合就是指用科学方法把客观知识元素有序组织起来,形成提供知识服务的人工集合;指出“知识集合”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创立了“知识集合论”[23]。针对此“论”,马恒通(2002)提出质疑,认为“知识集合”的概念具有模糊性、宽泛性,因此对图书馆缺乏专指性,未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此“论”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24]。而后,马恒通与张玉珍就王子舟所提出的关于图书馆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知识集合论”、研究对象等)展开争鸣。张玉珍(2007)指出,“图书馆学不仅要揭示图书馆‘这一个’事物的本质,并在此基础上,要揭示出与图书馆相类似的诸多事物的本质”[25]。马恒通(2008)反对此观点,认为“图书馆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正是因为在本质上与其他任何事物存在着严格的区别”,所以,图书馆学研究对象只能是“揭示‘图书馆’‘这一个’事物的本质,如果还同时‘揭示与图书馆类似的诸多事物的本质’,那就不称其为‘图书馆学’了”[26]。张天霞(2009年)提出与王子舟不同的另一种“知识集合论”,认为“主客观知识、知识集合、知识受众及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27]。
1.2.6 “知识管理说” 吴慰慈、罗志勇(2000)指出,在信息时代,“图书馆的概念有可能包括传统图书馆之外的一些组织机构和图书馆内部新的工作机制”,“图书馆学研究必须果断地参与到知识管理领域中去”,推出“知识管理说”[28]。盛小平(2003)指出,知识信息的组织、传播与利用是现代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赞同“知识管理说”[29]。陈耀盛(2005)认为,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研究对象是显性知识活动和隐性知识活动,即知识管理,支持“知识管理说”[30]。
1.2.7 “知识存取论” 周久凤(2001)认为,“图书馆本质特征就是知识存取”,“知识存取”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推出了“知识存取论”[31]。
1.2.8 “信息组织与传播说” 王京山(2002)认为,“图书馆的本质属性是信息的组织与传播”,“信息组织与传播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提出了“信息组织与传播说”[32]。
1.2.9 “客观知识说” 蒋永福(2003)认为“客观知识是图书馆学的逻辑起点”,“图书馆是管理客观知识的社会机构”,“人是客观知识的动物”,“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客观知识、图书馆和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推出“客观知识说”[33]。
1.2.10 “公共知识管理说” 龚蚊腾等(2003)指出,“图书馆的实质是公共知识中心”,“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公共知识管理学”,创立了“公共知识管理说”[34]。此“说”一推出,便引起强烈反响。针对此“说”,张践明(2004-2005)连发3文予以否定,指出此“说”“没有体现龚文所说的‘图书馆学区别于信息学或情报学的主要特征’,也掩盖了图书馆学的本质特征”;认为“图书馆实质是研究读者与图书馆资源互动关系及其规律的科学”,推出“互动说”[35-37]。龚蛟腾等(2005)发文否认了张践明的“互动说”,指出“图书馆资源中的馆舍、设备”,“它不可能与读者简单的互动”,而且没有划清图书馆学与信息学、情报学及书店的界线,这种“互动关系说”仅是“公共知识管理学的一个方面”[38]。杨端光,汪全莉(2008)指出,“公共知识管理学和公共管理学之间是部分与整体、归属与包含的关系;显然,公共知识管理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存在矛盾,既归属知识管理学又归属公共管理学的观点值得商榷”[39]。
1.2.11 “知识资源论” 2004年柯平强调,“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知识资源”,“知识资源也就是与知识有关的所有资源”,包括知识、知识人、知识工具、知识活动四个要素,推出“知识资源论”[40]。许西乐(2006)推出“文献信息资源论”,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资源的整序与传递过程”[41]。针对“知识资源论”,马恒通(2007)指出,“知识资源”的内涵和外延都很宽泛,远远超出了图书馆的范畴,此“论”仍未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所以“知识资源”仍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42]。赵益民(2009)却支持此“论”,详见本文第2部分。
1.2.12 “知识功能说” 伊鸿博和常青(2004)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的知识功能”,推出“知识功能说”[43]。
1.2.13 “共享知识说” 熊伟(2004)认为图书馆的存在在于满足人类共享知识的需求,指出图书馆学研究(本质)对象是“人类共享知识的实现体系”,提出“知识共享说”[44]。
1.2.14 “知识信息传递服务说” 李林(2006)指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是知识性、信息性和服务性,将知识信息的传递与服务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能够最准确地反映图书馆活动的本质,真正确立自己的学科地位,推出“知识信息传递服务说”[45]。
1.2.15 “知识传播论” 马恒通(2007)指出,“图书馆的本质是图书馆馆藏知识的传播”,“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馆藏知识的传播”,首推“知识传播论”[46]。周久凤(2008)指出,“‘馆藏知识的传播’并未准确地揭示图书馆活动的本质”,因为“馆藏知识的传播”“不能涵盖图书馆学研究的全部”[47]。马恒通则不同意周文的看法,认为其没有真正理解“馆藏知识的传播”[48]。赵益民(2009)也不同意此“论”,详见本文第2部分。丛全滋(2009)撰文分析了此“论”,认为“在图书馆本质问题上用‘传播’不如用‘传递’更有方向性、可控性、目的性和针对性”,“用‘知识’一词不如用‘文献’更准确”[49]。同年,李后卿等指出,此“论”“忽略了图书馆的内部本质活动及其与外部的社会联系”,“知识传播论只是图书馆活动以及图书馆学研究的一部分”[50]。笔者认为,以上三位学者都没有真正读懂“知识传播论”,应当全面分析理解拙文的论述,不能断章取义。对此,笔者拟将另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1.2.16 “文献知识交流说” 吴海波、黄立冬(2008)认为,“交流说”中的文献信息“超出了图书馆学的本质所在,所以用文献知识来代替它”,“图书馆学就是研究文献知识交流的一门学科”,推出了“文献知识交流说”[51]。
1.3 “交流说”
在我国,“交流说”可分为“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文献知识交流说”四种观点。周文骏(1983)指出:“图书馆学的理论基本上是利用文献进行情报交流工作的经验的结晶”,首推“文献交流说”[52]。1986年,他在一专著中将“文献交流说”展开和发展[53]。“知识交流说”以宓浩(1984,1988)为代表[9-10]。倪波、荀昌荣(1986)指出“文献信息交流是图书馆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文献信息交流”,首推“文献信息交流说”[54]。黎盛荣(1986)认为“文献信息的开发与利用”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此种观点实质上也是一种“文献信息交流说”[55]。“文献知识交流说”如上节所述。“交流说”一出台,就受到多人质疑和否定。刘兹恒、管计锁(2002)指出,“‘交流说’现在看来确实存在不足,比如‘文献信息交流说’能否涵盖数字图书馆?社会其他领域的文献信息交流现象是否属于图书馆学的范畴?尽管它表达了图书馆与知识、知识交流的相互关系,却未能揭示图书馆内部的本质和机理,即忽略了知识组织问题”[56]。高波、吴慰慈(2000)推出新“文献信息交流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文献信息流(信源)、图书馆(信道)、读者(用户)(信宿),“三者共同完成了文献信息的交流过程”[57]。
1.4 “符号信息说”
郑金山于1997年首推“符号信息说”,认为“现代图书馆学基本理论,应当是符号信息的收集、整序、存储和再生产、再创造、再发现及其利用的理论,其灵魂是创新增值”,指出“符号信息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58]。
1.5 “公共信息流通说”
1998年丁国顺认为,“图书馆是一种公共信息的特殊流通形态”,“公共信息流通则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提出“公共信息流通说”[59]。
1.6 “信息时空说”
1998年叶鹰指出,抽象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有序化信息时空”,认为“以有序化信息时空”“作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范围将极其广泛”[60]。
1.7 “资源说”
1998年徐引篪和霍国庆借鉴美国图书馆学家切尼(B·E·Chernik)的“资源说”,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图书馆是一种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所以,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在中国首次推出“资源说”[1]。1999年于鸣镝批判此“说”,指出“图书馆向读者提供的主要是‘文献信息’而不是一般的信息”,“把‘文献’二字去掉,是不是太大了呢?”,认为“资源说”在为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下定义时犯了逻辑(同义反复)的错误和句法错误,否定了此“说”[61]。
1.8 “转化说”
2000年于鸣镝推出“转化说”,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对文献信息进行合理地组织并有效地通过读者完成信息的转化(包括物化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62]。马恒通(2001)不认同“转化说”,认为图书馆不能完成于文所说的两个“转化”,“转化说”其实质已脱离了图书馆[63]。
1.9 “管理说”
孟广均于2003年指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对整个文献信息系统的运动和发展进行有目的、有意义的控制,使整个环境和所有对象有序化、确定化、科学化”,推出新的“管理说”,也是一种“文献信息管理说”[64]。
1.10 “结合说”
王睿、张开凤(2003)认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与读者在知识传播中的有机结合”,推出“结合说”[65]。蒋鸿标(2003)指出,此“说”“未能反映图书馆的本质,也未能揭示图书馆的发展规律,因而不符合研究对象的条件”[66]。
1.11 “本质说”
2004年黄权才指出,既然“大家的研究对象都是本质”,“都是把图书馆的本质作为研究对象”,那么,把图书馆的研究对象确定为“图书馆的本质和运行规律”,“也就没有必要再争图书馆的哪一种本质是图书馆的研究对象了”,推出“本质说”[67]。
1.12 “保障说”
王学进(2006)强调,只有图书馆能够为读者(用户)提供文献信息的三大保障:“数量、质量保障”,“揭示和检索保障”,“空间和时间保障”,因此,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图书馆为需求提供文献信息保障的全过程及其相互关系”,首推“保障说”[68]。
2 集中批评视域中的上述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诸“近似本质说”
1993年赵媛指出,“矛盾说”只“侧重于事物间的特殊矛盾,而忽略了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不能“充分体现图书馆与社会中的其他子系统及社会大系统的关系”。赵嫒还认为,“知识交流说”无法与同样进行着知识交流的情报部门、书店、学校等区别,“知识交流”只是图书馆的功能中的一部分,因此“不能成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69]。
1993年曾建认为,“‘交流说’(笔者注:指“知识说”、“文献交流说”、“文献信息交流说”、“知识交流论”)由于忽视了对图书馆现象的认识,着重于图书馆外界环境的研究,即知识在社会中的产生和传递过程的研究,难以扣紧图书馆自身整体,尽管它理论抽象性较强,但对图书馆具体工作的指导是不够的”[70]。
1996年茅振芳指出,“矛盾说”对于图书馆无特殊性、专指性、唯一性,不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交流说”(包括“情报交流说”、“知识交流说”)只能说明图书馆工作的性质、任务和功能作用,不能将其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混同起来;“知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内容(不是全部内容)”,“但绝对不是图书馆学研究对象”[71]。
1998年徐引篪、霍国庆指出,“这三种观点(笔者注:即“矛盾说”、“交流说”(包括“文献交流说”、“知识交流说”和“文献信息交流说”)和“新技术说”)也都有着明显的缺陷:“矛盾说未能理清图书馆的所有关系”,“交流说普遍超越了图书馆学的学科范围”[1]。
2000、2007年马恒通两次撰文,集中对上述2005年之前的大部分“对象说”进行评判,认为这些“对象说”都把研究对象扩大到包括图书馆在内的所有与知识有关的机构(事业)或组织中,都因无专指性而未能揭示出图书馆的本质,当然也不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笔者提出的“知识传播论”也只是一种“近似说”[46],[72]。
2001年王子舟指出,“知识交流说”“未能很好地解释图书馆内部活动的根本机制”;“‘知识组织说’作为‘知识交流说’的补充,无疑是克服了上述缺陷,但所刻画的是图书馆内部活动过程的本质,忽略了知识受众,其哲学特征属‘方法’而非‘本体’层次,不是以某种‘社会现象’当成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而一门学科的研究对象往往是由一种有‘本体’意义的‘社会现象’来充任的”[73-74]。
2001年周久凤指出,“‘知识交流论’把研究重点放在图书馆与社会的联系上,而较少关注图书馆的内部活动”;“‘知识组织论’强调的重点在于(知识)整序的‘过程’,即关注的是知识的‘存’,忽略了知识的‘取’”[31]。
2002年王续琨、罗怀远认为,“矛盾说”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而非研究对象;“知识说”、“知识交流说”、“符号信息说”、“信息资源说”等,“由于知识、文献、符号、信息资源等作为研究对象,对图书馆而言不具有专指性”,因而皆非图书馆学研究对象[75]。
2002年储流杰对上述诸“说”进行批判,指出“矛盾说”、“交流说”、“资源说”、“信息时空说”、“知识可获得性说”、“知识集合论”、“知识组织说”等“都在一定阶段、一定层次、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经验性、技术性、片面性、非本体性、神秘性等认识偏差”,这些“对象说”中除了“知识组织说”“反映的不够全面”外,其余诸“说”“不仅概念过于宽泛,没有专指性,不能揭示图书馆的本质,而且远远超出了图书馆学的规定性”,或“理论本身还不太完善”[76]。
2003年黄宗忠指出,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是信息、是知识、是文献”,“这些说法都不够准确”,“知识、信息、文献都是图书馆不可分离的因素,但不是图书馆专有的研究对象”[77]。2006年他又指出,当前出现的“‘信息资源’、‘知识资源’、‘知识组织’、‘知识集合’、‘知识管理’、‘知识单元的可获得性’等都是含义广泛、涉及领域众多,为多个学科共有、通用或不是图书馆学专有、专指的对象,是上位类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内容,如果图书馆学以这些为研究对象,必然丢去或淡化主体,走上泛泛议论,不解决实际问题、无针对性的‘空壳学科’”[78]。
2006年陈源蒸指出“知识集合论”“是书、人、法三要素新的阐述”。关于吴慰慈、高波推出的新“文献信息交流说”,他认为,“关于文献信息的产生,另有所属学科,读者则是图书馆的一个组成要素。此论层次不清,与确立学科的基本原则不符”。他又指出,“关于‘资源说’的阐述,只是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图书馆学的一个方面,不能作为整体的图书馆学”[79]。
2009年赵益民两次撰文,认为“过去许多‘对象说’均因未能完全准确地区分图书馆与其他公共文化机构而没有取得广泛的共识”,“纵观已有的知识交流、知识集合、知识组织、知识管理、知识传播、知识共享等相关概念,如果将它们视作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和图书馆工作的实质,难免有所缺漏或存在认识上的偏颇”;“‘知识资源论’力图解决这个问题”,并将“知识传播论”与“知识资源论”对比分析,反对“知识传播论”,支持“知识资源论”[80-81]。
综上所述,建国60年来,我国学者在不同时代条件下,由于主客观多种因素的影响,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近似本质”的认识也不尽相同,这是必然的。尽管“对象说”至今仍众说纷纭,见仁见智,没有达成共识,但每一个观点都是向本质层次的步步逼近,反映了我国学者对图书馆学研究对象认识的不断深入和进步。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史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争鸣,能有效地促进图书馆学理论的进步和图书馆事业的发展。“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82]。笔者坚信,“对象说”之谜必将在未来的“百家争鸣”中解开!“对象说”的不断争鸣,必将推动图书馆学可持续健康发展,走向美好的未来!
收稿日期:2010-03-16 修回日期:2010-05-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