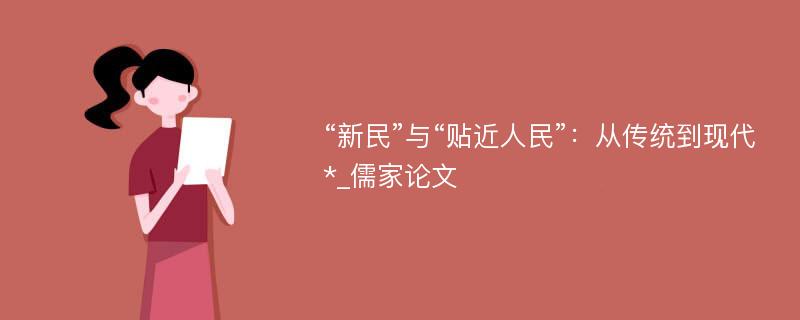
“新民”与“亲民”:从传统到现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论文,亲民论文,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大学》本为《礼记》之普通一篇,在宋代以前并未受到特别关注。二程始表彰《大学》,称之为“孔氏之遗书”,“初学入德之门”。朱子进一步为其作传,《大学》一跃而成为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①朱子承袭程子将古本《大学》之“在亲民”,改为“在新民”。而王阳明《传习录》第一条即是对此改法的质疑。但现代学者在讨论朱、王《大学》今古本之争时,多收紧在“格物”、“致知”、“诚意”等条目。虽偶有提及“新”、“亲”二字,但亦止于蜻蜓点水。惟在徐复观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那里,新、亲之辩上升到重要的理论高度被加以认真检讨。本文拟重新追溯“新”、“亲”之争的思想谱系,并将以徐复观、牟宗三为代表的当代新儒家对传统儒家德治思想的解读,置于这种思想光谱之下加以检视,藉此揭示不同时代的儒者之不同诠释进路,同时进一步阐发儒家“新”、“亲”之辩的现代意义。
一 朱子之“新”
众所周知,朱子从程子将《大学》之“亲民”易为“新民”,《大学章句》序曰:
程子曰:“亲,当作新。”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尽管朱子的章句在后来也成了“经典”,但在当时,朱子之改字是受到强烈质疑的,毕竟轻改经文,是注家之大忌:
曰:“程子之改亲为新也,何所据?子之从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己意轻改经文,恐非传疑之义,奈何?”曰:“若无所考而辄改之,则诚若吾子之讥矣。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程子于此,其所以处之者亦已审矣……若必以不改为是,则世盖有承误踵讹,心知非是,而故为穿凿附会,以求其说之必通者矣,其侮圣言而误后学也益甚,亦何足取以为法耶?”②
“以文义推之则无理”,当谓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之义是自明其明德,既明其明德,则推己及人,使他人亦明其明德,此即新民。自明而明他,己立人立、己达人达,在文义上自顺理成章。如作“亲”字,则与上面“明明德”意思较为有隔。用朱子本人的话说:“我既是明得个明德,见他人为气禀物欲所昏,自家岂不恻然欲有以新之,使之亦如我挑剔揩磨,以革其向来气禀物欲之昏而复其得之于天者。此便是新民。”③朱子将“亲”改作“新”,可以说在“文义”上是反复拿捏、细致推敲过的。
“以传文考之则有据”,系指《大学》所谓“传”之部分有关“新”之论说。依朱子《大学》之汤之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作新民”,以及《诗》“周虽旧邦,其命惟新”等文本属于“传”文,是来解释“三纲”之“在新民”这一经文的。如朱子经传之分成立的话,那么,在后面的传文部分确实有相应的文字分别对应于“明明德”与“止于至善”,而传文之种种“新”之文本显然对应新民这一纲。
《书·金縢》之“惟朕小子其新逆”,陆德明《经典释文》即指出“新逆”马本作“亲迎”。而我们对照郭店竹简,《老子》通行本“六亲不和”,竹简本作“六新不和”,“名与身孰亲”,竹简亦作“名与身孰新”。另外竹简中尚有“教民有新(亲)也”(《唐虞之道》),“不戚不新(亲),不新(亲)不爱”(《五行》)等语,其中“亲”皆写作“新”,可见,“亲”、“新”本可通用。④职是之故,我们可以为朱子补充说,以“新”易“亲”,不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而且以文字酌之亦有凭证。
二 王阳明之“亲”
王阳明对朱子的《大学章句》颇多不满,他坚持认为《大学》一书本来就“止为一篇”,并无朱子所谓的“经传之分”,更无缺传可补:“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⑤既“悉从其旧”,则不当以“新”易“亲”。《传习录》第一条即是关于“亲”、“新”之争: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⑥
阳明的这番话完全是针对朱子主“新”的论证而发的,“作新民”之“新”与“在新民”之“新”确实不同,前者是“自新”,后者则是“使民新”,而君子贤贤亲亲、民之父母等文本,于“新”并无发明,显然在阳明看来,朱子“新”之“以传文考之则有据”,实不足为据。而针对朱子“以文义推之则无理”的说法,阳明在指出“治国平天下”处种种亲民文字后,又历数孟子亲亲仁民、尧典“以亲九族”,直至点出夫子“修己以安百姓”,“亲”字自有其义理上的权威支持。
在《亲民堂记》中,王阳明进一步阐发了“明明德”与“亲民”之间的内在联系: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过阳明子而问政焉。……曰:明德、亲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而万理之所从出也。人之于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于其兄也,而莫不知弟焉;于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灵昭之在人心,亘万古而无不同,无或昧者也,是故谓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蔽,以全其本体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何以在亲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也,则必亲于其父,而后孝之德明矣;欲明其弟之德也,则必亲于其兄,而后弟之德明矣。君臣也,夫妇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⑦
阳明在这里的说法颇为不类。观南元善问政,则主体自是从政之君子,“明明德”与“亲民”皆是针对君子而论的。故“德不可以徒明”,“人之欲明其孝之德”云云,亦仍是扣紧修己之君子而言的,如是,亲于其父、亲于其兄等等的那个“其”字并不指“民”,而仍是君子自家之父、兄,仍然属于修自家的明德,如是而讲“明明德”与“亲民”合一,实只是讲知行合一,而并未真正涉及“民”字。倘我们不做如此理解,而将“其”字不作君子自己解,而是直接理解为“民”,则“亲民”实是令民自相亲,亲民的意涵便变成了“使民明其明德”,此不正是朱子坚持的“新民”吗?这难免给人一种这样的印象,阳明虽将朱子之“新”字重新改回“亲”字,但对其义理的解释却又不自觉沿袭了朱子的新民说。实际上,我甚至认为“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这一阳明早年的说法在后来并未得到坚持。我们不妨看看他晚年所撰的《大学问》中有关亲民的说法:
曰:物有本末:先儒以明德为本,新民为末,两物而内外相对也。事有终始:先儒以知止为始,能得为终,一事而首尾相因也。如子之说,以新民为亲民,则本末之说亦有所未然欤?
曰:终始之说,大略是矣。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其说亦未为不可,但不当分本末为两物耳。夫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新民之意,既与亲民不同,则明德之功,自与新民为二。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可析而为两乎?先儒之说,是盖不知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而认以为两事,是以虽知本末之当为一物,而亦不得不非为两物也。⑧
这里,阳明对朱子“新”字不满在于后者将“新民”与“明明德”视为“两事”、“两物”,而阳明坚持明明德以亲其民,亲民以明其明德是一事、一物。至于亲民兼教养、新民则偏的说法,则无一语涉之。
其实,无论朱子抑或阳明均将“亲民”与“明明德”合观,将之归属于孔门“修己安人”之内圣外王的传统,两人发生分歧的地方并不在于对“治人”本身的理解上面。两人的分歧实是表现在对《大学》主题的解读上面,朱子认为《大学》的主题是教育问题,他反复强调《大学》之书,是“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朱子之主“新”与其对《大学》这一“教”主题的定位密切相关。而王阳明则认为《大学》主题并不只是“教”问题,而且涉及“养”问题,故力主“亲”字。这丝毫不意味着说朱子讲教化,故对养民不予重视,实际上,朱子亲民的政绩完全不逊于阳明;同样这也丝毫不意味着说阳明讲亲民,故对教化重视不够,实际上,阳明一直以讲学、化民、教民事业为“首务”。
三 “新”与“亲”:后儒之辩
王阳明之后,有关“亲”、“新”之辩仍不绝于缕。“主新”派在支持朱子以“新”易“亲”的立场同时,一方面不断提供新的证据补充朱子的论证,另一方面又针对王阳明的持论加以辩驳,兹分别举顾应祥、陈龙正、胡渭等数家言述之。
顾应祥(1483-1565)指出:
《大学》古本在亲民,程子以为当作新,朱子以为程子存疑之辞。今尊用古本,以亲字兼教养。愚谓《大学》一书恐专主教而言,故不言修德而曰明明德,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也,新民者明民之明德也。后章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皆专言教也。或以为末章言理财用人,似兼言养,曰:非也。理财用人亦本乎德,故曰君子先慎乎德,又曰必忠信以得之,皆自明德而言,能明己之明德,则好恶当乎理,而不拂乎人情,皆本于教而言也。大抵古人论治皆以教为先,伊尹曰:予天民之先觉者,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先觉即己之明德也,觉斯民即明民之明德也,亦同此意。⑨
顾应祥(字惟贤)少即受业于阳明,为阳明亲炙弟子⑩,然而在新、亲之辩上,他倒并不支持阳明“悉从其旧”的立场。相反,对阳明之以亲字兼教养,而尊用古本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大学》通篇的主题皆是讲教化,即便末章言理财用人,看似近于亲、近于养,但亦是“本乎德”、“本于教”而言的。顾氏又引伊尹先觉、觉斯民之说,进一步证成《大学》之“主教”与古人“以教为先”的治论若合符节。后来王夫之(1619-1692)亦重申了这一“主教”的立场:
《大学》于治国平天下,言教不言养。盖养民之道,王者自制为成宪,子孙守之,臣民奉之。入官守法,仕者之所遵,而非学者之事,故《大学》不以之立教。所云厚薄,如《论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之旨,即所谓“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也。其云以推恩之次第言者,非是。(11)
王夫之虽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颇多不满,但在“新民”问题上却坚定支持朱子的立场。一方面,他认为《大学》是讲学者之事,故其主题理所当然是“言教”,而不是“言养”。这并不是说“养民”不重要,“养民之道”早为“王者自制为成宪”。另一方面,王夫之还提供新的“证据”支持“主教”的解读,被“主亲派”用来支持“主养”的“厚薄”文本,并不是推恩次第意义上的“厚薄”,而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意义上的“厚薄”,故仍属于“修己”的范畴,而与“明明德”前后呼应。
高攀龙、吴志远的弟子陈龙正(1585-1645)在其《学言》中对“亲民”二字之不当痛加贬斥:
亲民之必为新民也何?居亲可施于亲,不可施于民也。孟子曰: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民是兼爱。己书曰:百姓不亲,亲者自相亲也。犹云小民亲于下也。圣人亲亲,墨氏亲民,佛氏亲物。亲亲则功至于百姓,而恩及禽兽矣。亲民则不得不薄其亲矣,亲物则不得不弃其亲矣。或曰:亲亲、子百姓子之义何以异于亲?曰:子者,养育训迪之耳。亲则爱敬兼隆,所以殊也。君子之于子与百姓也,固有用敬时,为其为亲之枝也,为其为邦之本也,又别一义也。墨氏欲亲民,视其亲亦如民耳。故忍于薄亲;佛氏欲亲物,视其亲亦一物耳,故忍于弃亲。亲新二言之间乃吾道异端之界。(12)
亲亲、仁民、爱物,儒学推恩次第井然,“亲”字不能用于“民”字,不然,亲民不得不薄其亲,墨子兼爱即属此;“亲”字更不能用于“物”字,不然,则不得不弃其亲,佛氏亲物即属此。“亲新二言之间乃吾道异端之界”,显然在陈龙正看来,“亲民”二字让儒家与墨、佛二家无法区隔。
倘若说顾应祥、陈龙正皆是从正面对朱子“新民”加以辩护的话,胡渭(1633-1714)则直接从驳斥阳明“亲民”说之无当入手,捍卫朱子新民之立场:
阳明言亲民不当作新,……此说似是而非,愚请奉《学记》以正之。《记》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又曰九年大成,然后可以化民易俗,此大学之道也。夫化民易俗可以言新,不可以言亲,是《大学》之治人元以教化为主也。即以此篇论之,明明德于天下,齐治平之事也,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谓之亲民其可乎?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可谓于新字无发明乎?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已而后非诸人,此而言故有父母斯民之说,然亦在兴孝兴弟不倍之后,是大学之道养前豫有教,与他书不同也。况传者历引五新字,正为新民而设。安得据如保赤子民之父母以证亲不当作新乎?……或问:他书言治道者,皆先养后教。《大学》独以教国为先,而继之以絜矩,何也?渭曰:教亦有浅深之别,传之所以释新民者,教之深者也。举其全功而言之也。传之所以释齐治平者,教之浅者也,就其始事而言之也。举其全功而言之,故必如汤之曰新又新,武王之作新,文王之新命,以至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后为新民之极。就其始事而言之,则不过尽吾孝弟慈之道,以教于家而成于国,使之兴起其善端,此道之以德之事,而齐之以礼,犹其后焉者也。盖王者继乱之余,人心陷溺,风俗大坏,必先自明其德,以示之标准,俾有所观感,而兴起以去其旧染之污,而后可以施吾不忍人之政,不然则虽有良法美意而人心不正,法之所立,弊辄随之,而国卒不可得治矣。此君子所以立敎为急也。若夫谨庠序、兴礼乐,则又在衣帛食肉不饥不寒之后,所谓劳来匡直辅翼使自得之,渐民以仁,摩民以义,使之浃于肌肤,沦于骨髓,而礼乐可兴者,传皆未之及也。故曰就其始事而言之也。盖絜矩乃道德之后、齐礼之前中间一段爱养之政事。其实大学之道始终以化民易俗为主,故谓之新民,不可谓之亲民。亲当作新无可议也。(13)
胡渭的亲、新之辨可谓丝丝入扣,说理绵密。析其要,大致有三端:(1)以《礼记》之中与《大学》相关的《学记》之主题作为“新民”说的有力旁证,《学记》篇之中的大学之道的主题便是化民成俗,是故《大学》篇之中的大学之道亦当不出此范式。(2)就《大学》本身的义理来说,明明德于天下,无非是“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其意思无非是“使民新”,而不是亲民。“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等文本也是发明“新”字之义的,更不用提传文中五处历引“新”之文句了。(3)胡渭已经注意到儒家其他经典言及治道均先养后教,而惟《大学》以教为先,并对此专门加以解释。这样一来,“主亲派”以儒家言为政之道总是“先养后教”作为《大学》亲民说佐证的说服力,便打上了折扣。
主新派所驳斥的种种观点,正是主亲派所力持的。而主新派所主张的论点,也正是主亲派所极力辩驳的,两派针锋相对,此自不待言。
活跃于清中叶的秦笃辉说:
在亲民,孔疏言大学之道在于亲爱于民。按孔疏最确,不应如程子改作新字。在程朱之意,不过因下文引《康诰》作新民,欲并《盘铭》四节,作此句之传,遂改亲作新,以从之耳。夫改经从传,已为截足适履,况作新民亦谓振作其自新之民,其义重作不重新。《康诰》新字属民,程朱所改经文新字属治民者。语势悬绝,岂可因有新之一字,不顾语脉之歧,强比而同之乎?自此字一改,《大学》身无完肤矣。(14)
秦笃辉“自此字一改,《大学》身无完肤”之批评,可谓耸人听闻,细究其提出的理由,则实乏善可陈。阳明早已说过“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又说“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均是强调作新民之新字属于民字。秦氏“其义重作不重新”虽有拾人牙慧之嫌,但也反映出他贬朱(熹)扬王(阳明)的学术立场与他一贯的亲民史观。(15)
惠士奇(1671-1741)对“亲民”说提出了新的证据:
程子破亲为新,可乎?曰可。《康诰》作新民,奚为不可?然仍当以亲民为正。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达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于民,远于佞。”近于民,非亲民乎?亲民者,子庶民也,长养而安全之是为亲,教训而变化之是为新。惟能亲之故能新之,不能亲,焉能新哉?
又: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首章言亲民,此言新民何也?曰惟能自明,故能自新。惟能亲民,故能新民。以汤盘自新证自明,故以康诰新民证亲民也……(16)
在这里,惠士奇举出《康诰》祝雍“近于民”之语,“近于民”即是“亲民”。由此,他提出更强的证据来支持主亲说:亲民是新民的必要条件,所谓惟能亲之故能新之,不能亲民,则新民无从谈起。显然在惠氏那里《大学》一文的内在理路是“自新(明明德)—亲民—新民”,《大学》文本后面所引《诗》、《书》之中关于“新”之种种说法,皆是顺此理路而展开的,故不能成为“在新民”的根据。
段玉裁(1735-1815)则对新民派《大学》“偏言教化”说提出质疑:
至于程子之读亲民为新民,则又失其音读者也。汉儒有改读经字者,而大学之道在亲民,不得援此例。人与人患隔而不亲,亲民之事,必先富之教之。未有不使民菽粟如水火而责以仁者。即《大学》一篇言之曰,“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是岂偏言教化耶?失其音读而为政之次第失矣,尚何至善之可求耶?(17)
为政次第之失,实因“失其音读”,此是顾亭林汉学一系极夸张之说法。但是,段氏拈出儒家先富后教的思想路线,并指出《大学》之“民之好恶”以及“义利”说法皆未逸出这一思想路线,因而《大学》主题并不是“偏言教化”,一字之差,谬以千里,儒家“为政次第”失矣之断语自有其儒家义理系统之支持。
清末之改革派刘光蕡(1843-1903)在其《大学古义》中继续申发此义:
从古本亲民当如字读,从朱注亲民当作新民,两解均可通,而新民不如亲民之义精深宏大。人惟视民不亲,故忍以法术愚民,刑威迫民,后世一切猜防民之覇政,皆由视民不亲而生。故亲之一字为王道之本源。改为新,则王道之作用也。(18)
刘光蕡视“亲”字为“王道之本源”,并将后世一切霸政归咎于“视民不亲”。应该指出的是,无论是胡渭抑或是刘光蕡,尽管均极为强调儒家亲民在为政思想之中的基础地位,但二人并未完全否认朱子以“新”易“亲”的正当性。
主新派的论说,在继续申明《大学》的主题是教化这一朱子本人的核心立场之外,还从《大学》之外的其他儒家经典著作中寻找这种解读的合法性支持。而主亲派除了重申阳明“作新民”与“在新民”不同这一论调之外,更多凸显亲民之在儒家先养后教的“为政次第”。不过,主新派亦不否认这一次第,只是坚持《大学》偏言教化。(19)换言之,两派在为政次第上并无分歧,儒家先养后教思想是两派的共识。分歧惟在于《大学》的主题是什么,如此而已。
四 现代新儒家:扬“亲”限“新”
徐复观(1903-1982)对“养”与“教”的关系最为注重,他有一系列文章专门讨论这一主题。在他看来先养后教是儒家治道的一个核心教义。他以“修己治人”概括儒家德治的基本内涵。他一再强调德治的本质是对统治者提出要求,是责备统治者,而不是责备人民。修己治人的标准有着严格区别:修己的标准“总是将自然生命不断地向德性上提,决不在自然生命上立足,决不在自然生命的要求上安设人生的价值”。而治人的、政治上的标准,虽然并不否定德性的标准,但是,“这只是居于第二的地位,而必以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居于第一的地位。治人的、政治上的价值,首先是安设在人民的自然生命的要求之上,其他价值必附丽于此一价值而始有其价值”(20)。
儒家此种修己治人之道有一源远流长的思想谱系。孔子讲修己时即主张“居无求安,食无求饱”,甚至要求“杀身成仁”。但在政治上,则只是“节用而爱民”,“因民之利而利之”,以至“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孟子对士的要求是“尚志”,是“仁义而已矣”,但在政治上则认为“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而其“王道”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老者衣锦食肉,黎民不饿不寒”。《礼记·表记》对孔子躬自后而薄责于人的精神有进一步的引申:“子曰:仁之难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而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仁义法》中,“内治”与“外治”亦是得到严格区别的:“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而后获。以此之谓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先其事,后其食,谓治身也……求诸己谓之厚,求诸人谓之薄;自责以备谓之明,责人以备谓之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为礼不敬也。”同篇尚有人我之别说:“君子攻其恶,不攻人之恶,非仁之宽与?自攻其恶,非义之全与?此之谓仁造人,义造我。是故以自治之节治人,是居上不宽也;居上不宽,则伤厚而民弗亲。”
在此思想光谱下,养与教的关系成了政治的基本方向问题:
养与教的关系,不仅是政治上的一种程序问题,而实系政治上的基本方向问题。儒家之养重于教,是说明人民自然生命的本身即是政治的目的,其他设施只是为达到此一目的的手段。这种以人民自然生命之生存为目的的政治思想,其中实含有“天赋人权”的用意。所谓“天赋人权”,是说明人的基本权利是生而就有,不受其他任何人为东西的规定限制的……所以政治的根本目的,只在于保障此种基本人权,使政治系为人民而存在,人民不是为政治而存在。较儒家为晚出的法家,以耕战之民,为富国强兵的手段,人民自己生存的本身不是目的,由人民的生存而达到富国强兵才是目的,于是人民直接成为政治上之一种工具,间接即成为统治者之一种工具,这样一来,人民生存之权不在于自己而在于统治者之是否需要,这是中国古代法西斯思想,当然是与儒家根本不能相容的。(21)
这一修己治人、先养后教之传统思想光谱,亦延伸于《大学》文本之中:诚意、正心、修身都是对修德之君子自己说的,而对人民来说则只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由此回头看阳明与朱子的“亲”、“新”之异,一字之差,意味迥异。王阳明之主“亲”:
一方面是真正继承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因为孔、孟、荀,都是主张养先于教的。同时,也是他对当时专制政治的一种抗议。阳明为其勋业所累,经常处于生死的边缘,所以一生很少直接谈到政治。他之所以再三反复于《大学》上的“亲”字与“新”字的一字之争,这是他隐而不敢发的政治思想之所寄。他看到越是坏的专制政治,越常以与自己行为相反的道德滥调(新民),作为榨压人民生命财产的盾牌;所以他借此加以喝破。他的话,尤其对现代富有伟大的启示性;因为现代的集权政治,一定打着“新民”这类的招牌,作自己残暴统治的工具。只有以养民为内容的亲民,才是统治者对人民的真正的试金石,而无法行其伪……所以王阳明的反对改亲民为新民,乃有其伟大的政治意义。(22)
“亲”、“新”之一字之争,成了王阳明隐而不敢的抗议专制思想之所寄!“新民”往往成为暴政的意识形态,成为集权政治的招牌,这究竟是王阳明所“看到”,抑或是徐先生本人所看到,明眼人一眼即可看到。黄俊杰先生指出:“徐复观著书是深深受到他的‘涉世’所浸润的”,“他对中国历史的解释中有太多时代的投影”,有时“不免因时代投影过多,而影响他的历史判断”。(23)徐先生亲眼目睹了同时代“思想主义”成为政治上的“设施”,成为“政治势力”之后患,故对“新”字自有高度之警惕。
徐复观先生的修己治人之辩、新亲之辩得到了牟宗三先生(1909-1995)的强力支持。后者在论述“儒家德化的治道”时指出,“德之最高原则”是“直接以主观服从客观”,客观系指人民,人民直须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客观地肯定之,如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还之,全幅让开,顺此存在的生命个体所固有之人性、人情而成全之以达乎人道。服从客观,不为别的,即以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可贵可尊。(24)忧民之忧、乐民之乐、与民同富、藏富于民、尊重民意,此《孟子》之《梁惠王》之主题,《大学》概之以“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而“德治之大端”则不外正德、利用、厚生,其中利用、厚生是人民生活的幸福,而在“正德”与“利用、厚生”之间、“内圣”与“外王”之间则存在着一条严格的界限,牟先生称之为“政治与教化之限度”以及“政治与道德之分际”。“正德”属于内圣、属于修己,亦有其安人的一面,所以德治重视“就个体而顺成”,必然会顾及“生活之全”而含有教化的意义,但是,无论如何,教化本身必须有“其内容表现上的最高原则以限制之”:
此即是“先富后教”,而教亦是顺人性、人情中所固有之达道而完成之,而不是以“远乎人”、“外在于人”之概念设计,私意立理,硬压在人民身上而教之。此为“理性之内容表现”上所牵连的政治上的教化意义之大防,所以亦是一个最高原则,不能违背此原则而教……在政治措施上,就个体而顺成,生存第一,即以其为一“存在的生命个体”而必须保住之……“然就个体的“生活之全”而言之,不但生存第一,畅达其物质的生活幸福,亦须畅达其价值意义的人生而为一“人道的存在”……教者,即教此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道,……此皆起码而普遍的人道,非外在的概念与理论而加于人民者,乃是根于人性人情之实事与实道,故曰“达道”。教者不过教此。难说人如其一人,不应有此也。故在内容的表现上,就生活之全而言之,牵连至此种教化的意义,不得谓为妨碍自由也。然在政治上所注意之教化亦只能至乎此,过此即非其所能过问,亦非其所应过问。此即政治上的教化意义之限度。此限度,在以前之儒者皆自觉地公认之。律己要严,对人要宽,此是一般地言之。若落在政治上,此对人要宽,第一是“先富后教”(此先后是着重义,不一定是时间上的先后),第二是教以起码普遍的人道。过此以往,非所应问,非所能问,即不能在政治上责望人民做圣人。不但政治上由此限度,即一般言之,做圣人亦是个人自己之事,不能责望于他人,此即所谓恕道也。(25)
于是,就道德本身而论,此属于个人之事,是个人追求自我实现的领域,在这个领域内,个人之成德是一无限的前程,“深度与广度俱无止境”,但此成圣之无限过程全然是“内在的”、“个人的”;而“政治教化上的道德与一般社会教化上的道德”,则只是维持“一般人道生活上的规律”,这种维持只能是“外在的”:“既不能内在地深求,亦不能精微地苛求。此‘不能’是原则上即不能,这是政治上所固有的限度。”这也意味着“教化”所涉之道德不是成圣的道德,不是宗教性的道德,而只是一般人道意义上的、社会性的道德。(26)个人性的、内在的成德与社会性的、外在的教化之界限便成了道德与政治之界限不能逾越,也不应逾越,否则后患无穷:
个人自己实践上的人格成就,无论怎样伟大与神圣,若落在政治上发挥,他不能漫越这些限制(政治世界的最高律则),而且必须以其伟大的人格来成就这些限制。能成就这些限制,在古人就称他是“圣王”;在今日,就称他为大政治家。否则,在古人就叫他是霸者,是暴君,是独夫;在今日,就叫他是集权专制者,独裁者。(27)
不难看出,徐复观将儒家“修己”、“治人”视为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与牟宗三强调“正德”与“利用、厚生”之分际,两者实际上均将“明明德”原则严格限制在“道德”领域,而一旦进入“政治”领域,则“亲民”才是最基本的原则,违背这一原则谈“新民”,则不仅属于道德的僭越,更是暴政、专制弄权的通行伎俩。修己与治人之别在两位新儒家这里变成了群已权界问题,变成了政治的方向问题。
针对“亲民”观念之分疏,牟宗三先生在强调“先富后教”的同时,亦补充说:
正因为德是指道德的真实心、仁义心,故一夫不获其所,不遂其生,便不是仁义心所能忍。从个人道德实践的立场上说,律己要严;从政治王道的立场上说,对人要宽、要恕。正德求诸己,利用、厚生归诸人,而亦必教之以德性的觉醒。此正所以尊人尊生也。尊生不是尊其生物的生,而是尊其德性人格的生,尊其有成为德性人格的可能的生。若只注意其生物的生,则是犬马视之,非所以尊人也。(28)
显然,牟先生在这里将修己治人统摄于道德心之中,并且更加重视亲民之“亲”所蕴含的尊重人格的意味,换言之,亲民、养民固然是针对民之“自然生命”,然而这种尊重自然生命的要求并不是不讲人的尊严与人格。毕竟人的生存不是动物生命的简单维系,不是赖活在世间的苟延残喘。对于那些以生存权就是最大的人权作为抵挡一切人权批评的挡箭牌的当权者来说,牟先生的话犹如利剑,直刺要害。(29)
五 结语
如前所述,朱子之主新并不意味着朱子否认新民应以亲民为前提,阳明之主亲,也不意味着阳明忽略新民之重要。两人对“亲”与“新”二字之取舍之歧异,固有文本解释上的分歧,亦有思想分歧的因素,但关键在于两人对《大学》主题的把握上面。明清两代的学者关于亲新之争依然是在朱子与王阳明所确立的基调下进行的。在这场有关“亲”、“新”之辩中,一字之定夺取决于以下诸种因素的综合考量:
1.《大学》文本本身的前后呼应的关系。主新派承袭朱子经传之分说,并以传文之中的“新”之种种说法,印证经文“在新民”之合理性。主亲派或如阳明否定经传之分,如此以传文之“新”印证经文之“新”则完全成无根之谈,或力辩前文“在新民”之“新”与后文“作新民”之“新”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关乎他人的“新他”,后者是关乎自己的“自新”。因此,后文之种种“新”字并不能成为易前文之“亲”为“新”的证据。而后文讲治国平天下均扣紧“亲”字,故“在亲民”三字才与后文前后呼应。
2.《大学》的义理论述的脉络。主新派认为“首纲”之“明明德”,既是“明”自家的“明德”,则下一步必是推己及人,而明他人的明德,此即是“新民”,此为顺理成章之事。主亲派则坚持“明明德”与“亲民”是体用、本末关系,讲明明德必与亲民联系在一起。
3.《大学》的主题。主新派认为《大学》通篇皆是讲“教”的问题,是“教人之法”,“新民”自与此主题若合符节。主亲派则举《大学》文本之中“民之所好”等文字,反驳《大学》主题为“偏言教化”说。
4.《大学》之外的其他儒家经典有关教化、德治之论说。主新派认为《大学》之讲教化,并不与儒家德治论说冲突,况与之相近的《学记》篇就直接将“化民成俗”定为“学”之主题。主亲派则坚持儒家先富后教的德治路线不支持“新民”之解读,惟“亲民”方与儒家德治路线、王道理想、为政次第融洽无间。
其中的核心因素在于《大学》主题的定位,《大学》主题究竟是教化,抑或是教养并举,成了定夺“新”、“亲”二字的关键性因素。无疑在这场争论的过程之中,随着《大学》主题的阐释,儒家新民的思想路线、亲民的德治传统、为政次第都一道清晰起来。但在传统儒家思想之中,从未有人明确将政治与道德、教化加以区隔,儒家讲治道、讲德治,虽涉及修己治人、养教之关系问题,但毕竟未明白标出此属于道德领域,彼属于政治领域,领域不同,游戏规则各异。夫子有言“《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30)即是例证。何况《大学》亦明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新”字何曾严格限制在“君子”上面!王阳明曾说圣人忧不得人人都作圣人,又何曾像牟宗三先生那样明确分辨出“不能在政治上责望人民做圣人”!
只有在当代新儒家那里,亲、新之辩始被置于新的脉络下加以解读,这个新的脉络即是政治与道德的分际问题。可以说,“政治与道德的分际”这一现代思想的先行介入,成了定夺“新”、“亲”二字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无论徐复观先生抑或牟宗三先生当然都很清楚这个分际只是现时代的问题,毕竟在传统中国,道统为立国之本、日常生活轨道之所由出、文化创造之源,故传统之道统、政统、学统名为三,实为一,即是“以仁教为中心的道德政治的教化系统”。然而,“在吾人今日观之,此三者为一事之一套,实应只名为‘道统’。其内容自应以内圣之学为核心,此即为道德宗教之本义,而其外王一面,则应只限于日常生活的轨道而言之,此为道德宗教之末义。在此末义下,化民成俗之礼乐亦涵于其中。至政统一义,则须另为开出”。(31)于是政治与道德之分际在当代新儒家那里,实是关乎政统之开出问题。依牟先生所述,内圣之领域属于“道统”,属于以道自任的君子之修身领域,外王之领域属于“政统”,属于民主宪政之领域,而介乎两者之间属于“日常生活”之领域。这三个领域分别由不同的规则系统加以调整与引导,任何领域之僭越不仅会伤害到侵入领域的自主性,而且最终会导致它本身的某种自残。
(1)“政统”领域的民主原则越位进入日常生活领域,“师生之间讲民主,则先生无法教学生。父子之间讲民主,则父兄不能管教其子弟。夫妇之间讲民主,则夫妻之恩情薄。民主泛滥于社会日常生活,则人与人间无真正的师友,无真正之人品,只是你不能管我,我不能管你,一句话是‘你管不着’。民主本是政治上对权力的大防,现在则专而为掩护生活堕落的防线。”(32)牟先生所担忧的是这种社会日常生活的“泛民主主义”态度最终会摧毁民主以外的“人伦人道之大防”,不啻如此,“日常生活之泛滥”,“原子的、个人主义的个体性以及激情冲动任意任性的自由”必将造成混沌暴乱乃至无政府状态,而最终激起“另一集权专制之反动”(33)。
(2)“道统”领域的自治修身的圣贤取向越位侵入“日常生活”领域,以道自任、以圣贤自期的士人如将“圣贤”的标准强求他人,则不仅是对他人主体性的扭曲,亦同时伤害自家的德性生命:“一个知识分子,以圣贤自期,应当在自己几微之地,反省内观,不使有丝毫自私自利的夹杂;在日用寻常之际,居敬行礼,不使有丝毫疏忽怠慢的行为;将自己的生命,从物欲势利中,不断向上超升,向下落实,以显示人生的价值……但若以此要求于他人,以此作为论断他人的准则,则将发现每一个人都失掉了生存的意义,每一个人都算不得是人,在这种否定一切人而只有肯定自己的一个孤独生命的一念之间,已充满了暴戾乖僻之气,自己的生命,实际已堕落到一切人的脚底下去了。”(34)
(3)在政统领域,“只要求统治者自己有德,而以尊重人民的好恶为统治者有德的最高表现。只要求统治者提供教育的工具——学校,只要求统治者以身教而不以言教。言教乃是师儒立教之事,统治者是要自己通过师傅、谏诤、舆论来终身受教”,倘处在政治领域的人君不肯安于“受教”而越位去“立教”,则在儒家看来,此人君乃“非昏即暴”。(35)况政客谈论道德,往往成为弄权之招牌、专制之工具,用当代德国政治家Eppler的话说:“政治竟要谈道德,那总是启人疑窦的。因为通常从这种道德里面跑出来的,总是不该从那里跑出来的东西:一种工具,而且是权力斗争的工具。”(36)不过新儒家并不笼统地反对“站在政治立场以言教”,只是反复强调说,此种“教”仅是“一种最低调的人生规范”,且依然必须放在“养”之后面。这种出自政治立场的“教”,是为“养”而存在的,即是为人民的自然生命而存在,“只是以教来加强自然生命,而决不是以教来抹煞自然生命的存在。用现在的话说,即是不以任何思想或主义来动摇天赋人权”。“这是儒家与极权主义的大分界”!(37)道德与政治的“分际”、儒家与极权主义的“分界”,这是当代新儒家的政治论说一直念兹在兹的。当代新儒家之所以对“新”、“亲”表现出高度的敏感,实与此隐忧相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出自自由主义传统的西方当代学者,在讨论《大学》文本时,对“新”、“亲”之异所蕴含的“政治态度的差异”不仅没有丝毫的敏感,而且大赞“新”字之“自由”的意味。狄百瑞在《中国的自由传统》一书中,将朱子的教化思想视为儒家传统中“自由教育”的重要一环,对于程朱以“新”易“亲”给予了充分肯定,(38)倡导儒家民主主义的安乐哲甚至说《大学》的全民修身思想与孔子“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一致,致力于协调个人与家庭、进而协调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力图建立一个“自治的人类社群”,并将其视为保障“个人自由”的最重要条件。这种“儒家民主主义模式”靠两个强大的却又是非形式化的力量来维系,一个是耻字,一个是礼字。这种设想为“公民”(citizen)或公共个人(public individual)这样的概念提供了比自由主义民主传统“更加合理的解释”。因为现代民主宪政制度的核心在于保护个体权利,限制国家政权越位干涉个体的自由。在这样一种限制性框架中,人们有选择他们自己的价值观与目标的自由。原则上说,政府既不鼓励也不阻止人民对任何美好生活的憧憬。于是,法律所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这种概念化的自由给社会留下一个真空,使得形形色色的带有褊狭性质的说教迅速乘虚而入,如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激进的反堕胎主义、新纳粹主义等等,这一切最终会导致自由空间的收紧乃至毁灭。(39)
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西方治儒学者青睐“新”字,实是基于他们对现代个体主义的自由主义论说的不满,而徐复观、牟宗三等现代儒家致力于辨明道德与政治之分际,并将这种界限意识一直追溯至孔子修己安人的思想,则明显表现出他们在儒家传统之中挖掘与民主宪政之最基本的群己权界架构接榫之处这一良苦用心。(40)可以说,在当代新儒家那里对“新”之限制,最终是为儒家思想系统之中安顿“消极自由”。他们虽与同时代的台湾自由主义者颇多分歧,但却从不否定消极自由,反而以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欠缺的,必须加以吸收的。(41)基于消极自由的现代民主主义的政治形式在现代新儒家看来是“客观的、普遍的政治常数”,是人类政治的“正轨与常道”。没有这个民主政治的架构,“人的尊严,价值的实现,即不能保存”。与此相关,新儒家亦意识到传统“新民”之不足:儒家讲德化,教之,养之,有“兴发作用”,但这种作用只是道德的、伦常的,而不是政治的,“人民即不能在政治上自觉地站起来而成为有个性的个体”,成为一个“政治的存在”。(42)两人对“新”之警惕均扣紧在“思想主义”与“权力”结合而成为杀人之工具、专制暴政之武器上面。他们着意强调儒家之“新民”完全限于人类行为的“基本规范”,限于“最起码的人道之教”,其用意也不过是要表明儒家之“新”并不构成对“自由”的限制与威胁。近年来李泽厚先生大谈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之别,(43)实际上仍是这一思想谱系的当代延续。而一旦作出相应的制度安排(民主宪政),一旦“政道”获得一客观的架构,则“新”之价值不仅不容抹杀,而且对此制度架构自有提升与滋润之作用。因此,徐复观之“植根论”抑或牟宗三之“开出说”(44),均不曾把民主之制度架构与道德全然隔绝,恰恰相反,他们对将政治与道德完全隔绝的观点持严厉批判立场(45),在二人看来,民主政治只有接受儒家德与礼的思想,提升到道德的自觉,才能生根,才能发挥其“最高价值”。
“亲”抑或是“新”?一字之争,在传统那里关涉经典文本、主题之理解,在当代则关涉经典所承载的传统思想的现代意义。问题域转换了,亲、新二字之争遂具有了高度的政治意义。“亲”、“新”二字之取舍主要是基于“思想”进行的。“亲”字被大力弘扬,甚至与“天赋人权”联系在一起。“新”字在“范围”与“程度”上均受到了限制。
“亲”、“新”并举,或是正道。“亲”字凸显政治之为人民而存在,显示人民之主体性。“新”字则在不同领域表现出其意义:在“道统”领域,在以道自任的儒家共同体,德性生命的展开与实现是一个“自新”不已之过程;在“日常生活”领域,儒家新民(教化)所涉及的基本价值清单之中,例如同情、诚信、宽恕、包容、忍让等等一系列关乎他人的德性(other、regarding virtue),实是“社会人”所当具备之美德;在“政统”领域,为政者在其位,当具其德,当自新其德,而政治主体自由之挺立、作为“政治人”之权利意识与义务意识之培育,此在传统儒家新民内涵之中所阙如的,亦是儒家之“新”字所应赋予之新意。
*本文初稿曾宣读于台湾大学儒学研讨会第21次会议(2009年12月13日),承蒙郭晓东、丁为祥、蔡振丰、陈昭瑛、陈少明、高瑞泉诸师友先后提出不同建设性意见与评论,后又承彭国翔、张丰乾、黎汉基等君指正,此再修稿已酌而采之。
注释:
①《大学》地位的上升以及《大学》改本之演变,分别参杨儒宾:《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从性命之书的观点立论》及《水月与记籍:理学家如何诠释经典》,收入李明辉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二)儒学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59页以下。
②《大学或问》,收入《朱子全书》,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9—510页。
③《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第14册,第445页。
④梁涛:“《大学》新解”,收入《经学今诠续编》,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4页。聂中庆:《郭店楚简〈老子〉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16页。
⑤《答罗整庵少宰书》。王阳明对《大学》文本之怀疑与诠释有一变化之过程,参陈来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8—159页。
⑥《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页。标点有改动。
⑦《王阳明全集》,第250—251页。
⑧《王阳明全集》,第970页。
⑨《静虚斋惜阴录》卷二,明刻本。
⑩《明儒学案》卷十四,“尚书顾箬溪先生应详”,《黄宗羲全集》(增订版),第七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
(11)《读四书大全说》卷一,《船山全书》,第6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404页。
(12)引自胡渭《大学翼真》卷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胡渭:《大学翼眞》卷四。
(14)秦笃辉:《经学质疑录》卷十五,清道光墨缘馆刻本。
(15)秦氏之主亲与其亲民的史观是一致的,如其在《读史剩言》中所言:“人皆可有私财,惟天子不可有私财。天子以天下之财为财者也。有子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千古之格言也。”(卷三)又如:“历观全史,大抵于国家之利减一分,则于百姓之利增一分,其实利国家者也;于国家之利增一分,必于百姓之利减一分,似利国家而实害国家者也。”(卷一)
(16)惠士奇:《大学说》。常增在其《四书纬》之中与惠士奇持类似看法,他一方面指出,传文中的“新”字(如盘铭曰新)专主“自新”,仍所谓明其明德也,而即便《康诰》有新民之义,但其词曰作,仍主士之能自新也。至于“新命”亦夲之能新其德也。“古本为亲民未有新民之说,亦未尝以此为释新民也”;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亲民”是包含“新民”之义在内的:“天下岂有不亲其民而能新民者哉”?(《四书纬》卷一,清道光刻本)
(17)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三“在明明德在亲民说”,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五册,济南:齐鲁书社,1994年,第246页。
(18)刘光蕡:《大学古义》,民国刻烟霞草堂遗书本,第1页。
(19)明代理学家蔡清(1453-1508)尽管认为亲当为“新”字,但他同时又指出:“新民之事只是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新民二字,固是就教化上说,然非制田里,教树畜,立法制,以安其生,则亦无以为施教化之地也。故使民乐其乐利其利者,正为新民之事,而理财用人皆明明德于天下者之大节目也。”(《四书蒙引》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收入《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第266页。另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收入《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47—52页。
(21)徐复观:《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267—268页。
(22)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第258—259页。
(23)黄俊杰:《东亚儒学视域中的徐复观及其思想》,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70页。徐先生本人对此“投影”并不是没有自觉,在《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中,他就曾主张个人的哲学思想和研究古人的哲学思想史,应该完全分开,万不可将古人的思想涂上自己的哲学。但他同时意识到这个“简单要求”实不容易达到:“这里便遇着一个难题,没有哲学修养,如何能了解古人的哲学思想?有了哲学修养,便会形成自己的哲学,便容易把自己的哲学与古人的思想作某种程度的换位。”
(24)徐复观:《政道与治道》,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9页。
(25)徐复观:《政道与治道》,第106—108页。另参牟宗三《历史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48—149页。
(26)因此,严格说来,尽管两位新儒家都对“亲”字情有独钟,但也并不因此而否认“新”之价值,毕竟“饱食暖衣而无教,则近于禽兽”也是儒家之一贯看法,二人对“新民”的阐发不约而同。徐复观先生指出,儒家之所谓教,是就每个人的基本行为而启示以基本规范,与今日一般之所谓“主义”完全异质。牟宗三先生亦着意强调说,儒家之“教”完全是最起码的人道之教,不是西方“宗教”意义上的“教”,故中国以前的“政教合一”与西方不同。
(27)《政道与治道》,第108—109页。
(28)《政道与治道》,第25页。
(29)直到今日,西方学者在论及《论语》子路篇“子适卫”一章有关“富之”、“教之”之文本时,还认为这是为当代人权论进行“背书”:“孔子主张‘先富后教'”。孟子和荀子也都继承并发挥了这一主张。其影响一直波及主张经济和社会保障权利高于政治权利的当代人权论。”(安乐哲、罗思文:《〈论语〉的哲学诠释》,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24页。)
(30)孔子政治概念的特色,可参江宜桦《论语的政治概念及其特色》,载黄俊杰编:《东亚论语学:中国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7—272页。
(31)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台北:学生书局,1980年,第260页。
(32)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第257页。
(33)牟宗三:《道德的理想主义》,第144页。
(34)徐复观先生对此有精辟阐发,徐复观:《大节与大礼》,收入黎汉基、李明辉编:《徐复观杂文补编》,第四册,国际政治卷下,中研院文哲所筹备处,2001年,第84—85页。
(35)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收入《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268页。
(36)Erhard Eppler著、孙善豪译:《重返政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11页。
(37)徐复观:《释论语“民无信不立”》,收入《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编》,第268—269页。
(38)狄百瑞著,李弘祺译:《中国的自由传统》,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第3—9页。另参狄百瑞著,刘莹译:“《大学》作为自由传统”,收入《儒家与自由主义》,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4-193页。
(39)参郝大维、安乐哲著,何刚强译:《先贤的民主:杜威、孔子与中国民主之希望》,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
(40)用徐复观先生本人的话说是将儒家精神“落实在政治上而切实有所成就”,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第171页。
(41)李明辉:《儒家视野下的政治思想》,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第27页。
(42)牟宗三:《历史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9—171页。亦参徐复观:《儒家政治思想的构造及其转进》,收入《学术与政治之间》,台北:学生书局,1985年,第55页,第59—60页。
(43)李泽厚:《历史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44—83页。
(44)吾友肖滨在其《传统中国与自由理念:徐复观思想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中将徐复观先生的政治思想称为“植根论”而与牟宗三先生的“开出说”加以区别。冯耀明先生在其《形上与形下之间:徐复观与新儒家》对徐复观与牟宗三政治取向之别亦有类似看法,见《“徐复观学术思想中的传统与当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2009年,第4、6页。
(45)详见李明辉:《当代儒学的自我转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86—10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