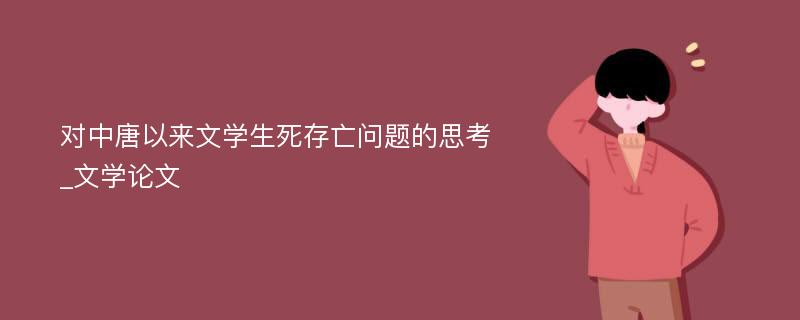
梅开二度话死生——对中唐以来文学好谈生死问题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来文论文,对中论文,死生论文,生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文学史上对于生命思考有两个凸现的时期:一是汉末魏晋,二是中唐到北宋时期。第一个时期文学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作为“魏晋风度”,已经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和较为充分的研究,被人们称为“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时代予以肯定,而对中晚唐五代及至北宋时期凸现出来的生命思考,这一梅开二度的现象迄今仍未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一次的生死问题较之于魏晋时期内涵有无变化?思考的角度是否不同?得出的结论又是什么?此外,生死问题的再度提出,其思想基础、社会背景、社会心理等因素有什么变化?再度提出这一问题的意义何在,等等,都还未给予充分的论证。研究这一文学现象,对于了解我们民族对生死问题的认识进程,了解中唐至北宋这一时期的社会背景、思想意识、社会心理以及文学风格、作家的创作心态等问题,无疑有较大的价值,可以挖掘出较本质的东西,对古典文学的研究,从深层次上提供理论依据。
一
在中国封建史上,凡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出现大的争论,基本上都是因为作为封建意识领域支柱的儒家思想遇到现实的困厄和挑战,面临危机和措手无策,使人们在思想上失去依托而急于寻找归依之时。魏晋是如此,明代中后期和中唐至北宋时期也是如此。儒家思想的“崩溃”带来的恐慌和混乱,虽还不至于象西方尼采呼喊“上帝死了”的时候,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恐慌和空虚那样严重,但那种茫然失措和急于寻找依托的心理还是极为强烈的。那么,魏晋时期“人的觉醒”的侈谈生死与唐中后期的人再度醒悟而喜谈生死异同何在?
从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来看,汉末与唐后期有以下几点相同:
第一,灾难唤醒了人的价值感,死神惊醒了人。较之于信仰宗教的西方民族极重死亡而言,中国人是不大谈生死问题的,这与构筑我们民族文化心理大厦基石的儒、道二家生死观直接相联系。儒家学说是理性、现实的,其中决无宗教色彩,而是典型的世俗生活的思想指导。孔子认为:死的意义只在生,只有懂得生的价值才能明白死的意义,这就是“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所以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对死亡与鬼神问题,孔子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方式。孔子很明智,他深知死是无法亲身体验,也是无法避免,多谈无益,不如紧紧把握现实的此在人生;不去离群索居冥思苦想,只应积极投身社会,加入群体,追求功业,在人际关系中来确定和实现个体价值。这样既最大限度地取得了人生价值,又稀释了死亡的恐惧。庄子珍爱人的生命,从本质上讲,他也是恐惧死的。所以庄子讲“保身全生”,讲养生,追求齐生死。对那些为名利而死的人,无论是圣贤,还是盗贼,在庄子看来都是可悲的,因为这些人轻视的自己的自然生命,他说:“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则以身殉利,士则以身殉名,大夫则以身殉天下。故此数子者,事业不同,名声异号,其于伤性,以身为殉,一也。……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庄子·骈姆》)。既然现实社会异化和戕害了人的本性和生命,转而亲近自然并追求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这就是庄子淡化死亡恐惧的方式。
从深刻的意义上讲,无论孔子还是庄子都没有解决生死问题带给人们的恐惧,问题可以回避一时,却不能永久回避,一旦死亡之神降临于时代,生死问题就会泛起。汉末和唐末正是死亡和灾难频临的时代,这首先表现在战祸频仍方面。汉代自灵帝中平元年爆发黄巾起义,到西晋统一的近百年间,大规模的战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生灵涂炭,人命如草芥,出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人间悲剧;唐朝则从“安史之乱”起就战火不断,这在杜甫诗中已有反映。到了中晚唐,唐王朝与其他民族的边疆战争,王朝与藩镇,藩镇之间的战争连年不断,接着是席卷全国的黄巢起义。唐亡后五代十国的攻伐,延续到北宋立国,一个多世纪的各类型战争,使繁荣的大唐帝国满目疮痍:“风吹白草人行少,月落空城鬼啸长”(吴融《彭门用兵后经汴路三首》之三)、“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韩偓《自沙县抵龙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真正是死亡枕籍,惨绝人寰。史传所载尤为详细。汉末与唐末的天下大乱有着惊人的相似和一致。
其次,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残杀和清洗,使知识分子触目惊心。汉代自和帝以降,外戚与朝官、宦官之间围绕着权力争斗,拉开了杀戮的帷幕,相继发生的窦宪、邓骘、阎显、梁冀、窦武、何进六个外戚集团的惨遭覆灭;桓、灵之时的两次“党锢之祸”;曹操的诛杀孔融、杨修、许攸、娄寺、崔琰等等;继之而来的司马氏集团对曹魏集团的清洗,延续到南北朝的门阀争斗,何晏、嵇康、二陆、张华、潘岳、郭璞、刘琨、谢灵运……,一批批的文人士大夫相继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再看中唐以来,牛、李党争与宦官专权交替出现,“永贞革新”、“甘露之变”等事件相继发生,文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仅就“甘露之变”而言,宦官就“杀诸司六七百人,复分兵屯诸宫门,捕(李)训党人斩于四方馆,流血成渠”(《新唐书·李训传》),参与除宦官的宰相王涯、贾束、舒元舆等人遭灭族之祸,死者近千人,宦官因此“迫胁天子,下视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延至北宋的新、旧党争亦让文人士大夫心怀余悸,人生无常令人不得不想到死。“灾难加强价值感”(德·立普斯《悲剧性》);“真正的存在之本体论的结构,须待把先行到死中去之具体结构找出来了,才弄得明白”(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汉末和唐末的灾难和死亡唤醒了人们对自身价值的看重和对死亡的思考。
第二,信仰危机造成的心理失衡。儒家思想不是宗教教义,孔子不是上帝,但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秩序却是在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维系下得以延续的。不过,儒家思想并非没有遇到过困境,汉末和唐末就是儒家面临挑战的两个时代。
东汉后期由于社会动荡、政治黑暗、知识分子为了维护皇权、改弊匡失,按儒家理论,尤其是董仲舒创立的天人感应的理论去干预现实,企图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建功立业的理想。但是忠心不纳,反遭杀害,“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后汉书·党锢列传序》),传统的价值观面临着这突如其来的巨变,顿时失去了方向。士人迷惘了,天人感应的神学崩溃了!一时间老庄、刑名、法家、阴阳,乃至刚萌芽的道教纷纷粉墨登场。就在这个信仰大危机的空隙中,人们目睹的全是血与火、战争和死亡,由此整个社会陷入了巨大的死亡恐惧中。《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首发悲音。近百年间,不管是乱世英雄,还是脆弱文人;无论行名法之道,还是讲黄老之术,抑或谈庄玄之学,都无法解脱人们对死的恐惧。建安风骨、魏晋风度、正始之音,构成人的觉醒和文学自觉的时代强音,都与对死的思考和企图解脱联系在一起。
与上述情况相似,中唐以后人们尽管在口头上还在高唱儒家理论,但骨子里已经对这一理论的现实可行性失去信心。道、释二家本来在唐代就与儒家鼎足而立,儒家思想在现实中是如此,释、道也就乘虚而入,大有取而代之之势。加上类似魏晋“非汤武而薄周孔”(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之论的提出,使儒家思想的地位在晚唐时期大为降低。李商隐曾说:“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邪?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上崔华州书》);杜牧、罗隐等人诗文中表现出的对儒家思想的怀疑和对享乐人生情绪的流露,“月于何处去,日于何处来?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酌此一杯酒,与君狂且歌。离别岂是更关意,衰老相随可奈何!”(杜牧《池州送孟迟先辈》);“得即高歌失即休,多愁多恨亦悠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罗隐《自遣》,这些都是与传统儒家积极进取精神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形态的混乱使人们盯住的是现实加在人的生命中的灾难,于是死亡问题继汉末之后再一次被提出,并笼罩在人们心头。
综上所述,汉末以至魏晋在时代背景与思想意识,社会心理上,和唐后期直至北宋都有许多相似之处,有学者就曾指出:“总起来说,除先秦外,中唐上与魏晋、下与明末是中国古代思想领域中三个比较开放和自由的时期”(李泽厚《美的历程》)。这里的开放和自由,主要是思想意识和学术思想上的不囿于一家,其本质则是在这几个时期中,看重个人价值,看重个体生命,将人格自由发展提到本体论的高度等方面的相似,而这种相似恰恰又都建立在对外在权威的怀疑和否定、对生死极为关注这一生命意识的张扬基础上的。
二
世间万物的发展常常有许多相似处,历史发展是如此,思维的进程是如此,文学现象因受着历史的、思维的发展影响,当然也会出现相似的时候,上面所述汉末和唐末在文学领域中对生死思考的文学现象就是这种相似。然而,相似总是相对的,差异才是绝对的,只有体现出差异才会见到质的不同。所以,如果我们只把中唐以来文学领域中的生死吟咏简单地视作《古诗十几首》似的重复,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么,这两个时期文学对生死主题思考的差异何在?这些差异在本质上有何不同?各自的意义何在?这就是本文探讨的中心所在。
第一,如果说战争灾祸和政治动乱是汉末魏晋和中唐以来产生生命忧患的背景,那么在这个大背景之下直接导发这两个时期的生命思考的着眼点却是不同的。从生命的威胁来看,战争的牺牲往往是下层民众,文人直接死于战争的并不多,无论汉末还是唐末都是如此。魏晋文人的生命思考主要由于政治杀戮引起,上章所述一大批被杀的汉末以来的文人,只是政治斗争被杀的典型,绝大多数还在史籍记载中,未曾记载的当应更多,所以魏晋以来畏惧杀戮的情绪在文学中多所表现出来:
“常畏大网罗,忧祸一旦并”(何晏《言志诗》);“人生寿促,天地长久。百年之期,孰云长寿“(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诗》);“一身不自保,何况恋妻子”、“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阮籍《咏怀》);“密网栽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陶潜《感士不遇赋》)……政治杀戮给魏晋文人带来的是对死亡的恐惧,嵇阮齐名,但嵇康“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样他就只有成为刀下冤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说:“叔夜悻直,所触即形,集中诸篇,多抒感愤,招祸之故,乃亦缘兹。夫尽言刺讥,一览易识,在平时犹不可,况得意如仲达父子哉”!阮籍较嵇康聪明,他“口不臧否人物”,曾以大醉六十天的方式拒绝与司马氏联姻。表面看来十分洒脱,内中却充满了恐惧。李善《文选注》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嵇阮二人都不满当朝,都有所刺讥,但一隐一现,故嵇死而阮存。所以陶渊明在畏惧“网罗”密布的政治危机时有“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之举。
中晚唐以后的文人在死亡面前不象魏晋人那样充满恐惧,而是一份伤感。其原因在他们虽面临政治杀戮的危机,却较之魏晋人有更多的抽身事外的机会以避免被杀。这种机会是魏晋文人不易得到的。因为在中唐以前,中国的封建社会处于贵族统治阶段,文人大多是贵族或紧紧依附于某个贵族集团,朝廷的斗争往往是两个或几个贵族集团的利益之争。所以此一时,彼一时,一个集团的胜利是以消灭另一个或几个集团为前提的,而置身在被击垮的贵族集团中的人,要想逃避胜利者因预防失败者死灰复燃而采取的斩草除根的政治清洗并不容易。“竹林七贤”之所以分化,山涛、向秀、王戎之所以投向司马氏怀抱,阮籍、刘伶之所以在醉乡中度日,就是鉴于嵇康被杀的教训,但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也是十分惨重的。中唐以后,情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庶族地主阶级的登上政治阶级舞台,过去贵族集团那种在政治斗争中以血缘宗亲遭祸的可能已大大减少,除去极少数直接卷入政治漩涡中心的人外,大多数文人可以抽身事外,进退也较魏晋文人(尤其是贵族文人)要裕如得多。无论“永贞革新”,牛、李党争,还是宋代新、旧党争,在政治杀戮的恐惧上显然不如魏晋人那么厉害。那种时常如履薄冰的危机心理也要淡些。文人虽也惴惴不安,但真正死于刀下者并不多。所以中唐以后的生命思考主要来自对历史的反思,直接的死亡恐惧极少,而潜在的、对于人自身最终难逃一死的恐惧为多。同时因恐惧是潜在的而非迫在眉睫,所以就以感伤的形式流露出来。这种感伤虽不象魏晋的恐惧那么令人震惊,但却显得更为深沉和极难摆脱。
第二,由于一种是现实的巨大恐惧,一种是潜在的深深感伤,所以在表现形式的思考方向上,汉末以来与中唐以来在死亡问题上有明显的差异。
汉末以来人们是以眼前的死亡为参照物而发出的悲叹,其思考的是如何逃避死亡和体认人生的现实意义,试看《古诗十九首》所云: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飘尘”;“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是基于个体生命的短促和脆弱发出的喟叹。接着就是魏晋文人那无穷的慨叹: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曹操《短歌行》);“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曹植《赠白马王彪》);“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阮籍《咏怀诗》);“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陆机《门有车马客行》);“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刘琨《重赠庐谌》);“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陶潜《闲情赋》)……生命如此短促无常,这已令人伤心,而这短促无常和唯一的生命中又充满了那么多的不如意,为这无常的人生添加了惨淡的气氛。
中唐以后人们是面对着古代的坟墓与废墟而进行着生死的思考。这一时期是古代怀古题材的突发和高峰期,虽然在怀古时作者创作目的有不同之处,但由生死的思考牵发出来的却是历史与现实、生命与自然关系的总体反思:
“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刘禹锡《石头城》)“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杜牧《题宣州开元寺水阁》);“千年往事人何在,半夜月明潮自来”(刘沧《长洲怀古》);“人事任成陵与谷,大河东去自滔滔”(韦庄《河清县河亭》);“市朝迁变秋芜绿,坟冢高低落照红”(李群玉《秣陵怀古》);“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许浑《金陵怀古》)……在这里,人生百年被放进了历史的时间长河中,个体的生命被安放在永恒而无垠的空间中,人生的短促和渺小被时空的无限反衬到不值一提的地步,正如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所云:“辽阔悠久,无际无穷可使个体缩小至于无物……象沧海之一粟似的在消逝着,在化为乌有”(《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在这里没有巨大的恐惧,只有无穷的伤感和无可奈何。
第三,面对着无法回避的死亡,汉末以来与中唐以后在缓解恐惧和伤感时方式不同,结果不同,意义也有差异。
汉末以及魏晋文人缓解死亡恐惧的方法大致有三种。其一是抓紧时间享受现实人生,即“饮美酒”、“服纨素”、“秉烛夜游”,以加大生命享受的密度去弥补人生的有限长度。其二是以“行散”、“行气”、长啸等方式企图延长生命的长度,有些人甚至企求羽化登仙。其三是追求立功、立言,既实现了生前的人生价值,又求得死后的声名,“策高足、据要路”;曹操、刘琨等人的追求功业;曹丕“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提出,一大批文人学士的著书立说和写诗作文,以求“声名自传于后”(曹丕《典论》)。总之,这几种缓解和稀释生命的恐惧方式,都是立足于现实人生,紧紧把握住眼前。正因为汉末以来文人看重生命的此在和价值的重要,所以其虽有及时行乐的毫不掩饰,但亦有激励人们追求理想的精神。在那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苦闷带来悲观,悲观却没有堕落到颓废,而是以执着于人生与颓废抗争,因此形成具有悲剧美的“魏晋风度”,不失为我们民族“人的觉醒”的悲壮时代。
中唐到北宋,由于禅宗思想的巨大影响,人们对死亡似乎看淡了,但是产生于本土的儒、道二家的对人世、生命的执着,道教追求现世享乐的思想却依旧在影响着人们,于是在执着与超脱的激烈矛盾中,就充满了人生如梦的虚幻和梦魇难以摆脱的伤感,这种伤感浓厚得难以驱散,使人发出无可奈何的哀怨。魏晋人追求的功业富贵、享受和长生,在这一时期许多人眼中已经没有意义:
“南山漠漠云常在,渭水悠悠事还空。立马举鞭遥望处,阿房遗址夕阳东。”(刘兼《咸阳怀古》)
“南朝三十六英雄,角逐兴亡尽此中。有国有家皆是梦,为龙为虎亦成空。”(韦庄《上元县》)
统一中国的秦始皇生前可谓显赫,甚至令汉高祖羡慕得认为“大丈夫当如是”,但一样被死神追搜;南朝帝王你争我夺,自以为人中英雄,死神一样吞噬了他们,除去荒坟废墟表明他们曾经存在过之外,他们的功业又有何价值?
“残花旧宅悲江令,落日青山吊谢公。止竟霸图尽何在?石麟无主卧秋风”(韦庄《上元县》);“北邙坡上青松下,尽是铿金佩玉坟”(徐夤《十里烟笼》);“尽谓黄金堪润屋,谁思荒骨旋成尘”(杜荀鹤《登城有作》)。功臣将相、富贵荣华曾令多少人投来钦羡的目光,最终还是“繁华事散逐香尘”(杜牧《金谷园》)。这一种“对整个存在、宇宙、人生、社会的厌倦,无所希翼,无所寄托的深沉喟叹”(《美的历程》)到了北宋那一批才华横溢,睿智机敏而又在功业上颇有建树的地主文人笔下,发展到了顶峰。晏殊、范仲庵、王安石、欧阳修等人或为朝廷宰相,或为封疆大吏,身处太平之世,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但他们的作品中总有一种缺憾情绪,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伤感挥之不去。现实人生中该占有的都占有了,能追求到的都到了手,却依旧不满足,这本质上就是生命忧患的阴影在作崇。苏东坡却把因生命思考而引起的怀疑人生意义、厌倦和希求从纷扰的人世中解脱出来的情绪全面反映出来,以至这样一种无法解脱和了无意义的伤感传递给后人,使整个封建后期的地主文艺始终笼罩在这种情绪中。及至纳兰性德而有现实无味、梦幻无味,生不如死的大悲哀,他们无法消除生命忧患的伤感。
魏晋人对生命的思考引出了中国人的“人的觉醒”,因处在儒家天人感应权威学说崩溃的信仰危机之际,魏晋人一方面在追求把握现实,高扬个体的同时,在理论上也进行了道本儒末、越名教任自然、内圣外王和三教合一的模式的建树,因此而冲淡和缓解了生命的恐惧,使其隐伏下来。这一过程使我们民族在认识个体价值方面较之先秦两汉有了质的飞跃,但也因此埋下了精神的危机。中唐以后,这个危机再次爆发,并使人对整个封建秩序产生怀疑和否定情绪,使封建统治秩序失去其强大的向心力,尽管宋明理学权威确立也无法再重新增强这种向心力,以至引起明代后期一大批思想家在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影响下对个性的极大重视,并呼唤着一个个性解放的近代世界的降临。这种个性解放的呼声难道在北宋苏东坡“长恨此身非我有”的不满中不是早就透露出来了么?尽管遥远、微弱和模糊!
魏晋人对生命的思考唤醒了中国人的个性,中唐以来的生死思考尽管显得如此伤感、沉重和无可奈何,但却要求已经苏醒了的个性得以张扬。从这一点看,中唐以来的思考显然发展了魏晋的思想,并带有近代个性解放的色彩和意味。它虽然也曾产生了某些悲观厌世和消极的负面影响,但无疑对宋代以来完善了的封建铁幕政治和秩序有着不可小视的破坏力。同时,在明代后期与带有资产阶级的性质的要求个性解放的因素相合拍的思潮中,中唐以来由好谈生死的生命思考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明乎此,也就明白了中唐以来“梅开二度”话死生的文学现象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