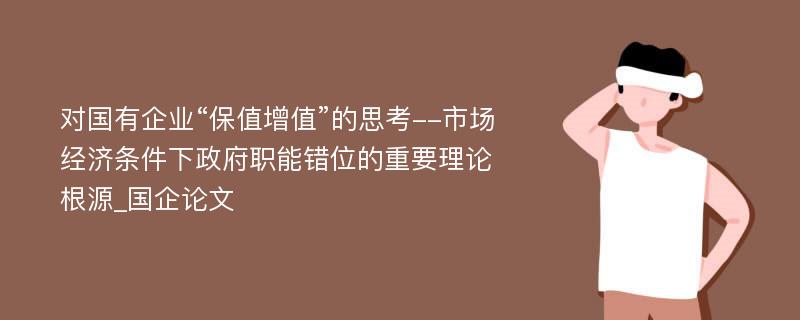
对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思考——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错位的重要理论渊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渊源论文,国有企业论文,市场经济论文,政府职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党的十四大以来,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习惯提法,演变成了“保值增值”的固定格式。这是一组在经济生活中影响很大、在体制改革中事关全局、在理论上处于基础地位的重大范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对此不能熟视无睹,政治经济学教材更应该对此做出科学的分析和解释。
我在《资本新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3年4月第一版,162-174页)、《经济研究资料》2004年第5期、《广东商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等著作和刊物上,分别就这一组范畴的由来、异同等问题做过详细的说明。持有相同的看法的人还有厦门大学的胡培兆先生(注:胡培兆:《国有资本的保值、增值和增殖》,载《理论前沿》1999年第8期。)、江苏省委党校的李炳炎先生(注:李炳炎:《社本论》,人民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韩朝华先生(注:韩朝华:《“增值”与“增殖”》,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3年6月12日。)等。
当然许多的人认为这种区分是不必要的。北京大学的弓孟谦教授在自己的专著的后记中明确地说,凡是《资本论》中关于“增殖”的说法,到了今天这个时代,统统都应替换为“增值”。按照弓孟谦教授的意思,今天是社会主义时代了,人民当家作主了,经济主体发生变化了,所有带有剥削含义的旧范畴,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所以基本范畴和概念的替换和取代也是必然的(注:弓孟谦:《资本运行论析——〈资本论〉与市场经济》后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出版。)。还有更年轻的同志比如赵炳贤(注:《资本运营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出版。第18页上写道:“企业兼并收购加速了资本的集中、积聚、增值和资产规模的扩张,促进了一批巨型、超巨型和跨国企业的产生和发展……”。在该书的第202页上写道:“所谓资本家实为‘资本经营家’资本运营的专家。他们具有在利润最大化原则下,使资本增值的知识和技巧。”)、李阳、王国刚(注:李扬、王国刚主编:《资本市场导论》(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7页上也有类似的“经营资本并追求资本增值的经济组织”这样的说法。)、赵云喜(注:赵云喜:《资本学——中国经济的温和革命》,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出版。本书在令人吃惊地肯定了“从原始人用石块投向野兽的那一时刻开始,资本就产生了”这样的老生常谈的观点后(见第五页),通篇都是“资本具有增值能力”的说法。)等人在自己的著作中干脆不分历史特点和时代背景,统统用“增值”取代“增殖”。
正是从这里出发,我们认为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讨论,并由此引发出如何界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问题。
二
讨论的问题之一:“增殖”和“增值”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它的意义何在?
我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不止一次地遇到同学们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熟知马克思学说的人来说,这也许不用费太多的口舌,但是对很多热衷于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的青年人来说,恐怕就不是一句两句话能说明白的。尽管你告诉他,在中文或英文中,它们都有不同写法(increment,value added\multiplication,breed)和意义,但多数情况下,摇头的仍然居多。
分歧起因于看问题的角度上,请大家注意:我们讨论的前提是承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因此强调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而市场条件等因素只对价值的实现或表象起影响的作用。比如说,养牛场的老板在饲草降价或牛肉价格暴涨时,一夜之间就把自己牛圈里的牛由1,000元变成了10,000元,但是他饲养的牛的数量和质量并没有变化,他就是说社会真实的物质财富并没有增加。在最简单抽象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增值”,它和劳动,准确地说是抽象劳动并没有直接关系。
而“增殖”的解释则有着更高一层的含义。养牛场的老板雇佣养牛工人,让他们修筑牛舍,添加饲料,精心料理看护,通过这些具体劳动,使一头牛变成了10头牛。这个具体劳动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是抽象劳动,它是价值的真正来源。正是这个抽象的过程使牛的价值由原来的1,000元增加到10,000元,翻成10倍的价值,这就是“增殖”。
应该说这就是马克思关于“增值”和“增殖”的最基本区别,在经济过程和范畴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会逐渐演变出纷繁复杂的形态,但在目前这个阶段上,不会影响我们对问题的看法和理解。(注:参见《资本论》第二、三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我现在要强调的是这个区别的重大意义:它深刻地说明了财富的真正源泉,和以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划清了界限,由此建立的剩余价值的学说,成为工人阶级的思想武器,也在为我们动员千百万群众投身革命运动,建立新的人民民主政权的强大动力。
三
讨论的问题之二:今天的时代有没有必要区分“增殖”和“增值”?
从解放后到1978年改革以前,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我们对“增殖”提法都是完全否定的。在极端时期,我们甚至连商品经济都持批判态度,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坚强决心,反映着党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迷茫和种种失误。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理智上清楚了许多。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反映着党中央和理论界对经济问题和社会管理不断成熟的过程。
随着个体经济、乡镇企业、民营经济、非国有经济等各种提法的逐渐演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也日益深刻。实践的发展告诉人们,经济因素的存在和消失,不能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而要以客观存在社会实践的需要为转移。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的文件里第一次使用了资本概念,提出了建立资本市场的重大举措,标志着我们党在一些重大的基本理论问题的认识上有了重大突破。在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上作出的《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重申了这些认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有企业的“增殖”,自然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也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我们注意到了当时的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和各大新闻媒体中都使用“国有企业保值或增殖”这样的提法。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不难作出判断:
承认“资本”的概念,就应当承认“增殖”的原理,否则那将是一种悖论。
区分“增殖”和“增值”是必要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二者的活动目的以及运动内容是有原则差别的。如果承认“资本”的概念,却只求“增值”的目的,就很可能倒退到古典经济学或者更古老的重商主义那里去。那将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
四
讨论的问题之三:否定“增殖”说法的理论倾向会给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将国有企业承担“保值增殖”的说法,换成“保值增值”,其深层的含义是:
1、从根本上否定国有企业定性为资本实质或实体。一些人至今对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伟大创举表现了极大的不适应。对国有企业的定性为资本持怀疑态度,自然也就否定“增殖”的提法,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著作里所讲的资本以及“增殖”原理早已经不存在了,再用马克思的提法,容易和旧社会雷同起来,不利于政治宣传和社会稳定。
2、确立国有企业的非资本地位,有利于和民营经济等非国有企业划清界限,从而更容易寻求经济上的独立利益,保护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
不能说这种想法一点道理没有。但我们担心:在经济体制改革迅速推进的今天,这种理论倾向会给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带来更大的损害。
我们从反向思维的角度对此作出批评:
1、这种说法可能会导致政府和企业关系更严重的扭曲,为政企分开设置难以突破的障碍。
目前国有企业和政府的关系可以说是制约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问题。这一点不突破,整个经济就难以走上良性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国有企业和政府长期维持一种不正常的关系,党委书记、市长兼任企业董事长、总经理的现象长期得不到纠正,不仅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还极大地压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腐败提供了丰富的土壤。为什么这一现象长期得不到纠正,这里既有实践操作的难度问题,更有理论认识问题。
按照马克思对“增殖”概念的理解,这首先是发生在生产领域里的活动。国有企业是生产单位,发生“增殖”是理所当然的。而“增值”的外延和范围则更要大得多。除了上述所讲的市场条件变化外,抢夺、偷盗、彩票、财政转移、战争赔款等也可以是“增值”的原因。如果让国有企业和政府在“增值”的目标下站在一起,自然难以分清二者的职责。我们喊了十几年的复式预算,迟迟难以上路,国有资产预算和社会保障预算仍停留在设想之中,深层原因都和这一根本性的认识有关。
让企业和“增殖”直接连在一起,把“增值”的功能交给社会有关部门并妥善管理和处置,是解决政企分开的理论出发点。当然不要忘记,国有企业的“增殖”在国有资本的预算帐目上也是一种增值。
2、它会恶化已初步形成的市场经济环境,加剧社会不公平现象,让大社会小政府的希望化为泡影。
让国有企业承担“保值增值”的任务,让民营经济和其他非国有经济滑入“资本”和“增殖”的轨道。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经济歧视的做法,不值得提倡。而且它会加大交易难度,提高社会管理成本,不利于大社会,小政府格局的运行。
在中国,国有企业的确是一个享受特权的角色。多年来,国家通过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把70%的贷款放给国有企业,又通过降息、政策性的财政支出甚至特有的股市等方式,把大量的本属于居民的财富圈在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群体中。但是劳动效率和社会满意度并不十分理想。从全新的角度审视并着力改革国有企业的旧有格局,是这一代人光荣而艰巨的使命。
五
讨论的问题之四:如何在“增殖”的理念下摆正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
如上所述,从马克思关于“增殖”范畴推论中,我们不难得出重视生产劳动、强调平等观念,坚持效率第一的观点。用这种基础性的研究审视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关系,我们又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1、政府要高度重视生产领域的活动。工人、农民是这个领域的主力军,知识分子在生产领域的活动当然属于生产劳动,理应得到尊重。
2、政府要摆正生产劳动和其他活动的关系。军队、警察、法院以及社会的其他任何活动都要为生产劳动开路。一切对生产劳动造成障碍的活动都应无条件的停止。类似郑州馒头办的故事应当永远终结。
3、政府要用平等和效率观点去管理包括国有企业在内所有经济因子。
在资本面前,人人平等。银行、铁路、航空、电力、邮政、电讯、供水供气、石油、医药、新闻出版各种体制上的独大排他的垄断现象要尽早打破,在“增殖”机理面前,国有企业不可取代的说法是无效的,“搞活”、“主导”、“控制力”一类的说法也失去了存在的理由。
具体到行业中:在一般竞争性行业中,国家要下决心从干预、支持、发展大中型国有企业的做法,转变为向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提供平等竞争环境这一目标上来。把一切都置于发展生产,追求增殖的框架下去考虑,如果效益不好,该死的就要死,把资源节省下来转移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对其他提供公共产品和金融服务的行业来说,要用行业准入制度代替现在的仍然大量存在的行政审批制度,无论何种经济成分,只要符合条件,经过批准,就可以参与,保证国民待遇首先在国内实行。
国家对所有全部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应一视同仁。所有国有企业都可以分别不同情况采取独资、股份、出售、托管的形式,判断的根据就是如何使这些现有的资本尽快“增殖”。
在新的资本和增殖理念下,能由民间和社会承担的经济事务政府就不要再插手,这样既能避免垄断对经济和社会资源造成新的浪费,又能使政府腾出手来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