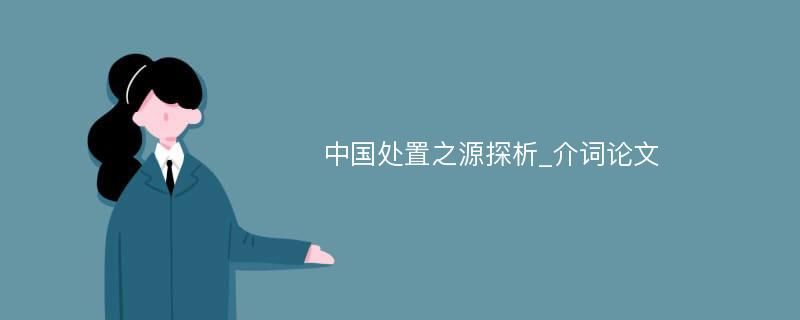
汉语处置式探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从王力1943年在《中国现代语法》(《王力文集》第二卷)中提出“处置式”这个术语以 后,长久以来“把/将”字句一直是汉语史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热点。但时至今日,人们 对于处置式的来源问题依然没有统一的认识,对这个问题还应作深入的研究。
有关处置式的来源,目前主要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起源于连动句式(下称“连动式
”说)。持这种观点的有王力、祝敏彻、贝罗贝等,他们都认为处置式的产生,是汉语发展
过程中逐渐产生的一种新的语法现象,而不是旧有句式的词汇替换。二是认为起源于介词“
以”字结构(下称“以”字结构说)。持这一说的主要有P·A·Bennett和陈初生。三是认为 一部分来源于“以”字结构,一部分起源于“连动式”(下称折中说)。持这一说的主要有太 田辰夫、梅祖麟、吴福祥等,其中梅祖麟明确提出了折中说。
三说对处置式的界定有所不同。“以”字结构说和折中说认定的处置式的外延要大得多。 根据对处置式外延认定的不同,处置式可分为广义的和狭义的两种。句式为“P+O+(X)+V+(Y )”(P:将/把,X:动词的前加成分,Y:动词的后加成分)是狭义处置式。句式为“P+O[,1]+V +O[,2]”(O[,1]≠O[,2]的是广义处置式,这类处置式就是梅祖麟文中的甲型句,即处置(给)、处 置(作)、处置(到)三类[1](pp.191-206)。吴福祥说:“广义处置式中的动词,动作性都不 太强,而且动词后面带有宾语,限制了补语特别是结果补语的进入,所以这类处置式的处置 性较弱。”[2](p.425)
比较而言,连动式说也许更为可信。王力和祝敏彻的观点早已为学术界所熟知,贝罗贝(A ·Peyraube)则在赞同连动式的同时又提出了一个假设。他说:B·K·T‘sou提出过在“醉 把茱萸仔细看”里动[,2]“看”后面重建“茱萸”这个名词,即“醉把茱萸仔细看茱萸”,认 为前者即由后者变化而来。贝罗贝认为“这个假设在我看来是完全合理的。为了进一步肯定 它,我们可以提出有代词‘之’在动[,2]后面的一些例子。这个‘之’的功能代替了动[,1]后面的
宾[,1]”[3](pp.6-7)。贝罗贝所举文例大多是成熟的处置式,而且时代较晚,还不足以证明他 的假设。本文则试图使用较早的文献材料进一步证明他的观点,并提出我们的一些不同的看 法。
一、处置式求源
1.1 处置式产生的语义基础
决定处置式性质的关键因素是介词,我们认为表处置的介词有两种必备的语义特征。一是 动感语义特征。处置句中的动词与一般句式中的没有什么差别,由于介词“将/把”具有把 受事介绍给行为动作进行处置的功用,才使得句子成为处置式。这“介绍给”含有明显的移 位性。处置介词的这种语义特征源自于“将”的“率领”义。二是处置介词对介绍对象 的能控制性语义特征。要实现把受事对象介绍给行为动作进行处置,从逻辑上说,介词首先 必须能够把握住对象,然后才能实现“介绍给”这种施为。这种语义特征由“将/把”原先 的动词义“握持”虚化而来。
“将”表示“率领”义在先秦汉语中就已十分常见。由于这种词义的“将”字后经常跟移 位动词,所以后来它本身也就附带上了移动的意味。“把”作为动词,意义较为单纯,大多 仅表“握持”义。与“将”相比,它不能引发人们移位的联想。因此,当“将”获得“握持 ”义并进入合适的句式,它就比“把”更容易语法化为处置介词。这也许是最初的处置式大 多为“将”字句的原因。
1.1.1 表示“率领”义的“将”能触发人们移位的联想。例如:(1)“楚子使道朔将巴客 以聘于邓。”(《左传·桓公九年》)(2)“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淮南子·人间 训》)在这样的连动句中,“将”字后的动词“聘”、“归”都含有移位义,使得“将”能 触发人们移位的联想。“把”的情况则有所不同。例如:(3)“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 ”(《墨子·非攻下》)(4)“相待甚厚,临别把臂言誓。”(《后汉书·吕布传》)例中的“ 把”表示静止的“握持”义,与移位无关,不会触发人们这方面的联想。
1.1.2 “将”的“握持”义的获得。“将”字的“握持”义在上古汉语中就已初露端倪。 例如:(5)“乐只君子,福履将之。”(《诗经·周南·蓼木》)郑玄笺说:“将,犹扶助也 。”到了中古,这种词义的“将”可与“扶”构成同义复词。例如:(6)“昕卒头眩堕车, 人扶将还,载归家,中宿死。”(《三国志·魏志·华陀传》)“扶将”就是扶持义。魏晋时 ,“将”还与“劫”、“略”义相近,其含“握持”义较“扶将”更明显。例如:(7)“其 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三国志 ·魏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注引《魏书》)(8)“或劝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 《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汉魏春秋》)“略将”、“劫将”都是劫持义。此期“将 ”还有“拘捕(押)”义(例见下文),这更是值得注意的一种词义。“将”真正表示“握持” 义的文例东汉时期即已见到。例如:(9)“楚熊渠子出,见寝石以为伏虎。将弓射之,矢没 其卫。”(《论衡·儒僧》)上举文例说明,至迟在三国时期,“将”进入处置式的语义条件 已相当成熟。
1.2 处置式产生的句式基础
只有语义条件,而不具备句式条件,处置式仍不能产生。处置式产生以前句式条件的具备 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是含“将/把”字连动式的普遍使用,第二是连动二宾语的相同 。
1.2.1 “将”字连动句的普遍使用。“将”字连动式出现的时代很早,先秦汉语中已见其 例:(10)“郑伯将王自圉门入。”(《左传·庄公二十一年》)吉仕梅又举出《睡虎地秦墓竹 简》的一条文例[4](p.129);(11)“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睡虎 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迁子》)这类用例到东汉已开始多起来,《论衡》就有4例,除上举例 (9)外,其他3例是:(12)“师尚父为周司马,将师伐纣。”(《是应》)(13)“其后数月,越 地有降者,匈奴名王亦将数千人来降,竟如终军言。”(《指瑞》)(14)“有仙人数人将我上 天,离月数里而止。”(《道虚》)值得一提的是,例(9)“将弓射之”,进一步发展就成了 工具语“将/把”字句。魏晋时期连动式“将”字句已大量运用,是一种常见的句式。例如 :(15)“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三国志·魏志·臧洪传》)(16)“又自将兵烧南北宫 及宗庙、府库、民家,城内扫地殄尽。”(《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续汉书》)(17) “布刺奸张弘惧于后累,夜将登三弟出就登。”(《三国志·魏志·吕布传》注引《先贤行 状》)这类连动式与“将”字的语法化还隔着一层,这一方面是由于“将”的意思大多仍为 “带领、携带”等,与“握持”义还不相近;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后续的动词都不能支配“ 将”的宾语。但不管怎么说,这类连动式为“将”字句向处置式发展奠定了第一步句式基础 。
1.2.2 “将”字处置式产生的枢纽句式。有了以上语义和句式方面的铺垫,下面这样的句 式也就自然地出现了:(18)‘帝时与御史大夫郗虑坐,后被发徒跣过,执帝手曰:“不能复 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时也。’帝谓虑曰:‘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 杀之,完及宗族死者数百人。”(《三国志·魏志·武帝纪》注引《曹瞒传》)(19)“太祖始 有丁夫人,又刘夫人生子修及清河长公主。刘早终,丁养子修。子修亡于穰,丁常言: ‘将我儿杀之,都不复念!’遂哭泣无节。”(《三国志·魏志·后妃传》注引《魏略》)《 魏略》的作者鱼豢是汉末三国时期人。《曹瞒传》的作者是三国吴人。总的说来上举两例“ 将”还都是动词,但从词义来说,例(18)的动词性稍强。这例“将”表示“押走”义,与一 般的不含强制性的“率领、带领”义很不相同。强制性义素的加入,使得“将”的词义与“ 握持”义更为接近。在这例“将”字中,我们见到了“握持”义与移位义的真正融合,处置 式的产生也就只欠“将”字词义的虚化了。与例(18)相比,例(19)的“将”字则已经开始虚 化。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春,曹昂随父征张绣而遇害。裴注引《世语》说:“昂不能骑, 进马于公,公故免,而昂遇害。”因此,曹昂虽不是父亲曹操所杀,但也不是没有关系。正 是因为这个原因,丁夫人才有例(19)的怨言:带走了我的儿子并杀了他。“将”虽仍有实义 ,但已经虚化,它距纯粹的处置介词只有一步之遥。
上举两例“将”虽然还算不上真正的处置介词,但却可以作为反映处置式产生过程的重要 证据,有利于我们看清“将”字虚化的轨迹。从这两条文例推测,在三国时期处置式产生的 语义和句式条件都已成熟。刁晏斌举出了目前看来是时代最早的处置式用例[2](p.442):(2 0)“于彼法中有一比丘,常行劝化,一万岁中,将诸比丘处处供养。”(支廉译《撰集百缘 经·须菩提恶性缘》)此例的动词“供养”之后,可重建宾语“之”,重建以后的句式与例( 18)(19)毫无不同。另外,例中动词之后还没有后代处置句那样的后加成分,反映出早期处 置式的句式特点,也可以让我们感知它们脱胎于类似例(18)(19)那样句式的痕迹。
从后代的处置句来看,典型的句式是:P+O+(X)+V+(Y),但是,“P+O[,1]+(X)+V+O[,2]”(O[,1]=
O[,2])这样的句式也不是不能见到。例如:(21)“船者乃将此蟾以油熬之。”(陆勋《志怪》) [2](p.442)(22)“上来说喻要君知,还把身心细识之。”(《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讲经文》) [5](p.136)(23)“遂从僧言,将胎埋之。”(《祖堂集·元寐禅师》)[5](p.136)(24)“把这 个妇人恰待要勒死他。”(《元曲选·货郎旦》)[6](25)“少时军马至,将恪全家缚于市曹 斩之。”(《三国志演义》一百零八回)用“之”称代O[,1]作句中的O[,2]是常见形式,但当“的 ”字结构产生后,形式又稍有变化,而实质未变。例如:(26)“我把那弟子孩儿鼻子都打塌 了他的。”(《元曲选·伍员吹箫》)[6](27)“把嘴撕烂了他的。”(《石头记》四十四回)[ 7](p.300)(28)“把皮不冻破了你的。”(同上,五十一回)[7](p.300)这样的句式在现代口 语中仍偶或能听到,但句中的“把/将”都已是处置介词,而不是动词。因此,我们承认处 置式的产生过程中确实有过贝罗贝所说的共时变化:主+ 动[,1] “把”(将)+宾[,1]+ 动[,2]+宾[,2]→主+
动[,1] “把”(将)+宾+动[,2],但“将/把”的虚化并非一定要在后种句式中完成。
1.3 处置句式形成的原因
这里所说的“处置句式”是指典型句式,即“P+O+(X)V+(Y)”式。早期处置式中的动词大 多是不带前、后加成分的光杆动词,这是不用宾[,2]留下的痕迹。当连动式二动词带同一个宾 语时,从修辞的角度说,像贝罗贝重建的“醉把茱萸仔细看茱萸”的句子,在汉语中实际上 是不会存在的,即使以“之”等来代替宾[,2]仍会给人以重复感。因此,人们在行文时经常会 不用两个宾语中的一个。这样,就有两种不同的选择:不用宾[,1]或不用宾[,2]。后来发展起来的 “将/把”字处置式选择了后一种。这是为什么?有无必然性?要回答上面的提问,可先看下 例:(29)“又收苗母舞阳君杀之。”(《三国志·魏志·董卓传》注引《英雄记》)(30)“绍 亦立收汉杀之。”(《三国志·魏志·袁绍传》注引《英雄记》)(31)“岐大怒,将吏民收渊 等皆杖杀之。”(《三国志·魏志·袁涣传》注引《魏书》)从句意方面说,上举3例与例(18 )没有多少差别,句式则完全相同,但“收”字并没有像“将”一样发展成为表处置的介词 。从文献语言材料来看,这是有原因的。请再看下例:(32)“将军董衡、部曲将董超等欲降 ,德皆收斩之。”(《三国志·魏志·庞德传》)(33)“时曹洪宗室亲贵,有宾客在界,数犯 法,宠收治之。”(《三国志·魏志·满宠传》)(34)“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 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注引《典略》)(35)“故将王 允被害,莫敢近者,戬弃官收敛之。”(《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典略》)可见,“ 收”字连动式采用的省略方式与“将”字连动式不同,它省略了宾1而不是宾2。类似情 形的还有“执”字连动式。例如:(36)“楚人执陈行人干征师杀之。”(《左传·昭公八年 》)(37)“坚卧与相见,无何卒然而起,按剑骂咨,遂执斩之。”(《三国志·吴志·孙破虏 传》注引《吴历》)这样的省略形式注定了它们不可能发展出处置式来。究其原因恐怕主要 是由于 “收”、“执”的动词性太强,并且在语义上与动[,2]始终处于并列的地位。这种语义关系使 得人们在遇到两动词带相同的宾语时,大多采取共用的表述方法,结果我们在形式上就见 到了似乎是省略宾[,1]的句子。
与“收”、“执”连动式相比,“将”字一开始就不与动[,2]处在并列的位置上,这在先秦汉 语就已如此,上举例(10)~(17)可证。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例的增加,这种倾向越来越明显 。 在这些句子中,“将”是次要动词,后续的动[,2]才是真正的谓语动词,“将”字动宾结构实 际上可以看作动[,2]的状语。由于“将”和动[,2]属于不同层面的语法单位,就决定了“将”与 在句中充当主要谓语动词的“收”、“执”表现出不同的使用特点:在“将”和殹带相同 宾语时,如果只须出现一个,那么,“将”字连动句就不可能像“收”、“执”连动句那样 采取共用的表述手法,形成探下省的句子形式,而只能采取通常的承上省,以使行文更为简 洁。这样,早期的处置式也就出现了。
通过两式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原本形式相同的句子,由于各自语义关系不同,在此后的 发展中分道扬镳了。从这里我们不仅能更为清楚地了解到处置式产生的内在原因,而且能透 过“收”、“执”等连动式,从侧面证明处置式产生以前确实经历过“动[,1] (将)+宾[,1]+动[,2]+宾[,2]”(宾[,1]= 宾[,2])这个阶段。
1.4 广义处置的来源
有关广义处置式的来源,通行的观点是“以”字结构说。梅祖麟对此作了最为详尽的论述 ,但此说尚可商讨。我们认为广义的处置式也是由“将/把”句自身发展出来的,而不是由 “将/把”对“以”字的词汇替换而产生的。吉仕梅所举的文例说明,广义处置式的原始句 式在秦代已经出现[4](pp.129-130):(38)“可(何)谓‘臧人’?‘臧人’者,甲把其衣钱匿 藏乙室,即告亡,欲令乙为盗之,而实弗盗之谓殹”(《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39 )“今鋈丙足,令吏徒将传及恒书一封诣令史。”(《睡虎地秦墓竹简·封诊式·迁子》)(40 )“牛生马,桃生李;如论者之言,天神入牛腹中为马,把李实提桃间乎?”(《论衡·自然 》)而梅祖麟所举的类似句意的最早“以”字句用例出自褚少孙之手,这就使得广义处置式 起源于“以”字结构的观点难以自圆其说。根据梅祖麟的归纳,广义的处置式有处置(到)、 处置(作)、处置(给)三类。从现有的语料看,“将/把”字广义处置式的产生和发展是不平 衡的,原始句式的出现首先是从处置(到)开始的。除了吉仕梅所举两条文例以外,时代较早 的 文例还有:(41)“今将辅送狱,直符史诣阁下,以太守受其事。”(《汉书·王尊传》)[8]( 42)“后被发徒跣行泣过诀曰:‘不能复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时!’顾谓虑曰 :‘郗公,天下宁有是邪?’遂将后下暴室。以幽崩。”(《后汉书·皇后纪下》)在这类文 例中,动[,2]后都带处所宾语。从逻辑关系看,“将/把”的宾语也是动[,2]支配的对象。换言之 ,“将辅送狱”可转换为“送辅(于)狱”,“将后下暴室”可转换为“下后(于)暴室”,转 换了的句子实际上是个双宾语句。这种句法特点,处置(作)、处置(给)也具备。正是因为这 个原因,梅祖麟才把三种句式合为一个大类称为“双宾语句”(即甲型句)。
吉仕梅所举文例和上举例(41)(42)中的“把”、“将”还都是动词,它们虽然已经具备了 语法化的语义和句式条件,但还不是真正的广义处置式。目前能见到的时代最早的广义处置 式之例是由刁晏斌举出的:(43)“急将是梵志释逐出我国界去。”(支谦译《佛说义足经· 异学角飞经》)[2](p.44)(44)“忽见将二百钱置妻前。”(《古小说钩沉·幽明录》)[2](p.440)处置(给)和处置(作)的用例较处置(到)晚些,但在魏晋南北朝的文献中也已见到:(45) “时远方民将一大牛,肥盛有力,卖与此城中人。”(竺法护译《生经·佛说负为牛者经 》)[2](p.440)(46)“悉将降人分配诸将,众遂数十万。”(《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上举 两例是处置(给)之例,例(45)的“将”与“卖与”之间由于有其他成分隔开,“将”字仍可 理解为动词,例(46)则已是处置介词了。(47)“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古诗源· 上山采蘼芜》)[2](p.440)这例可视为处置(作)的用例,在隋代以前十分少见。广义处置式 到隋代用例开始多起来,标志着这种句式此时已经完全成熟。
由以上的讨论,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五个结论:第一,“将/把”字广义处置式的产生是自身 发展演变的结果。第二,“将/把”字广义处置式的原始句型秦代已可见到。第三,“将/把 ”字广义处置式首先产生的是处置(到),然后推广到处置(给)、处置(作),表现出发展的不 平衡性,但在隋代以后它们都已发展成熟。第四,“将/把”字广义处置式的产生没有经历 过“V[,1] (将/把)+O[,1]+V[,2]+O[,2]+O[,3]”(O[,1]=O[,2])句式阶段,这与狭义处置式的发展不同。 主要原因恐怕是V[,2]已经跟了一个宾语,再加入一个重复宾语,句子会变得十分繁复。第五 ,大多数广义处置式特别是处置(到)、处置(给)都有提宾功能,这与狭义处置式相同。
二、“以”字处置式质疑
主张“将/把”字处置式来源或部分来源于“以”字句的学者,大多只注意两者的共性,而 这种共性又是建筑在对古汉语“以”字的今译基础上的,对于两者的差异性则重视不够。在 这种情况下,原本泾渭分明的两种句式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我们对“以”字有处置用法 的观点持怀疑态度,认为它与“将/把”有本质的不同。
2.1 “以”字有别于“将/把”的特点
2.1.1 “以”和“将/把”虚化为介词的语义来源不同。“以”作为动词,常见义有“用 ”和“认为”。虚化为介词以后,沿动词义“用”发展来的是表行为动作的凭藉,这种凭藉 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就具体语句而言,这类“以”可以随文对译成现代汉语 的“用”、“拿”、“把”、“率领”、“按照”,甚至“因为”,但这是对译,只是语义 的近似,“以”表凭藉的性质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我们不能因为“以”可以今译为“把” 就把它定性为表处置的介词,却对它的本质属性熟视无睹。假如那样的话,用于引进行为主 动者的介词“于(於)”因能对译为“被”而就可视为表被动了,王力也就用不着特意申明修 改自己的观点[9](p.273)。紧扣“以”字的本质特点来审视实际用例,我们的认识就会有所 改变。例如:(48)“复以弟子一人投河中。”(褚补《史记·滑稽列传》)(49)“渐离乃以铅 置筑中,复进得举筑朴秦皇帝,不中。”(《史记·刺客列传》)这是梅祖麟所举“以”用为 处置(到)的两个典型文例,两个“以”都可以对译为“把”,似乎处置意味的确很浓。但我 们以“用”来对译又有何不可呢?译成“用”则两句的处置意味顿失,而这恰恰是反映介词 “ 以”表示行为动作凭藉的本质的。
还有一类“以”与“为”字配合使用。例如:(50)“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孟子·滕 文公上》)(51)“王中郎以围棋是坐隐,支公以围棋为手谈。”(《世说新语·巧艺》)梅祖 麟把上举“以”字视为处置(作)的典型用例,这也很可商讨。假如此说可以成立的话,那么,“认贼作父”可理解为“把贼当作父亲”,岂不也是处置式了?我们认为古汉语中这类“ 以”大多并未虚化,“认为”之义仍很明显。何乐士将此类句子视为兼语式:“‘以……为 ’这是兼语式的一种固定格式,‘以’为动[,1],‘为’为动[,2]。表示‘把……视为(当作)…… ’,主要表示主观上以为如何。”[10](p.62)论者并没有因为这类句子可译为把字句而将它 们视为处置式,可谓深得其要。这种句式中,“以”字的宾语常可省略。例如:(52)“玉人 以为宝也。”(《左传·襄公十五年》)(53)“晋人归孔达于卫,以为卫之良也。”(《左传 ·文公四年》)如果承认“将/把”是对“以”的替换,那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不经常出现 “将(把)为”的省略形式。由此也足见两者的不同。
2.1.2 “以”字有别于“将/把”的用法。“以”字有的用法是“将/把”所不具备的,主 要表现在:
首先,“以”字介宾结构可位于动词前,也可置于动词后,“将/把”却只出现在动词前。 如“以地分给农民”也可说成“分给农民以地”[11](p.202),但却没有“分给农民把地” 的说法。这说明“以”的功能并不是表处置,故在句中的位置较自由。陈初生说:“‘将’ 字、‘把’字的职能更加专一,它们不能和介绍的受动者一块移到动词的后面做补语,这是 汉语处置式越来越精密的结果。”[11](p.203)果真如此的话,“以”字句没有理由不“越 来越精密”而仍停留在“粗糙”的水平层次上。
其次,“以”字后的宾语常可省略,这也是“将/把”句很少见的。除了上举例(52)(53)以 外 ,又如:(54)“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论语·微 子》)例中“以告”是“以之告”的省略,意为“把昨天的事告诉孔子”。从对译的角度看 ,这无疑是“处置式”了。但这种句式在“将/把”字句中是难得见到的。
2.2 “将/把”有别于“以”的特点
“将/把”是由“握持”义直接虚化为介词的,成为介词以后,原来动词义的意味仍很浓。 所以,它们所表示的处置义是“以”所不具备的。来源的不同,也使得“将/把”字句在句 子形式方面表现出与“以”字句不同的特点。如前所述,“将/把”处置式由“V[,1](将/把)+O[,1]+V[,2]+O[,2]”(O[,1]=O[,2])句式演化而来,在“将/把”成为真正的介词以后,它的原始句型 仍绵延不绝,历代可见(例见前)。这种句式“以”字句却从未见过。
综上所述,“以”字句从来也没有发展出处置式过,“将/把”字句成为处置式是从自身句 式发展出来的新生语法现象。至于为什么隋唐以后会出现“将/把”增而“以”减的趋势, 原因也并非是“在广义处置式里,‘以’、‘将’之间的词汇兴替”所致[2](p.110)。我们 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简单的词汇兴替问题,而是新兴句式对旧有近意句式的替代, 是处置式发展成熟以后,表意领域和使用面不断拓展的结果。概括地说是处置式的表达领域 覆盖了“以”字句的部分表达领域。由于两种句式从结构到表意都有近似性,也由于新型处 置式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隋唐以后原本可以用“以”字句的场合,人们更乐于使用处置式 ,从而形成了“以”字句的衰减之势。例如:(55)“以水浆给与众僧。”(支曜译《成具光 明定意经》)如果把例中的“以”替换成“将/把”,在句子形式方面并没有什么变化,在语 义方面则稍有变化。“以”字介宾结构表示的是行为动作的凭藉,是静态的状语;“将/把 ”字介宾结构表示的是处置,属动态状语。但从整个句意来看,结果都表示众僧得到了水。 在 这方面两种句子表现出了相似性。正是由于句意的相似性,使得人们在实际的口语中既可选 择“以”字句,也可以选择处置式。但句意的相近,并不能掩盖两者在语法方面的本质不同 ,更不能把隋唐以后处置式的全面成熟看成是对并不属于同种句式的“以”字句的承继。由 此看来,王力在《汉语语法史》中仍没有把“以”字句列入处置式中讨论[9](pp.266-271) ,不是疏忽,而是一种审慎处理。
标签:介词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