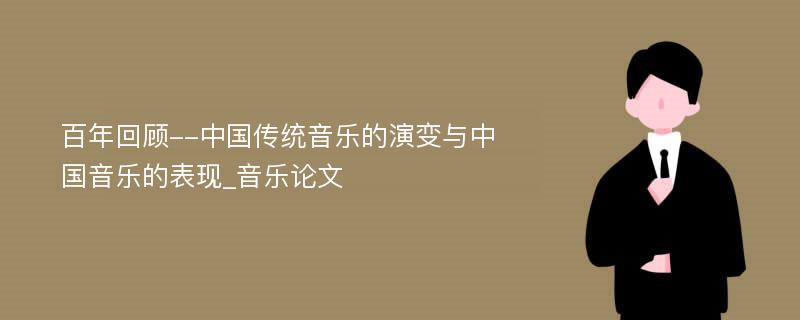
世纪的回眸——中国传统音乐的流变与当今中国音乐的表达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传统论文,中国音乐论文,表达方式论文,当今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音乐和音乐活动是人类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音乐传统及音乐的表达方式,总是与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形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观察本世纪中国传统音乐的流变和当今中国音乐的表达方式,不能不首先涉及本世纪中国的社会生活。
一、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二十世纪是中国社会大变革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
从社会形态和物质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变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
1、随着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推翻,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的历史宣告终结。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的三十八年间,中国社会经历了军阀混战、外敌入侵和国内战争的动乱岁月。
2、自五十年代至今,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建设和发展,中国逐渐确立了与现代工业社会相适应的、以城市经济为中心、农村经济为基础的社会经济体制。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的逐步实施,给人们在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行为方式带来了相应的变化。
3、由于交通、通讯和传播媒介的现代化,中国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和民族的交往日益密切,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也日益扩大,为中国人在科技、教育、思想、文化、体育、卫生等方面分享和利用全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方面,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二、中国传统音乐的“断层”
中国的音乐传统源远流长,是古代亚洲黄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出土实物(骨哨、骨笛、陶埙、陶铃、石磬等)可考的7000多年里,中国音乐大致经历了以金、石、土、革、丝、木、匏、竹为材料的器乐和远古舞乐时期,汉、唐乐府——歌舞大曲时期,及宋、元、明、清以戏曲、说唱、时调小曲为主的俗乐时期。在这三个大的连续发展阶段里,中国音乐分别以民歌、器乐、歌舞音乐、戏曲音乐和曲艺音乐的表演形式,繁衍、流传于农村乡野、城镇市井、宗教场所、文人圈层和宫廷之中。延续了两千多年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男耕女织”的劳动、生活方式,为传统音乐的保存、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生态环境”和衍生的“土壤”。中国封建社会占居主导地位的儒学文化思想,崇尚“礼乐”、“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主张“德治”、“仁政”,造就了中国音乐注重情操、道德教化作用;追求典雅、庄重、中和、谐美;讲究神貌、气韵、风骨、意境等美学特质。以可唱性旋律和单个音连续为主体的线状音乐思维;逐层递进、变奏展演的材料陈述手法;与语言、声调密不可分的五声性调式——旋律体系,构成了中国传统音乐鲜明的形态特征。
虽然数千年来,中国音乐一直随着历史的演进,总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中。其间由于社会的变迁及与邻近地域(东亚、西亚、南亚)其他民族的文化交往,中国传统音乐经历过多次大的转折和不断融汇、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但中国传统音乐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和人文土壤及其相应的民族音乐传统的主体特征,并无本质的和全面的变化。
可是,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却造成了中国传统音乐繁衍延续进程的剧烈震荡。其超常的冲击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1、社会的政体——经济形态和人民的生存——意识形态的变化。
这种变化首先使相当数量(或特定品种)的传统音乐丧失了创造(生成)——繁衍(传承)的基础。如宫延音乐和部分民歌。
2、 西方音乐和各种表演艺术形式——包括它们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的植入
这种植入以少数西方传教士的传播和殖民主义者的入侵发端,继之以众多留洋学子和各种传播媒体为中介,逐渐溶入中国的社会生活,进而凝聚成政府行为。如国家兴办和管理的交响乐团、歌剧院、舞剧院、话剧院、电影制片厂等艺术生产团体和音乐学院、艺术学院的涌现(欧洲乐器、记谱法、乐学理论、作曲技法和表演形式对中国音乐文化的全方位渗透、兼容和大面积覆盖)。
在这两股超常冲击力的合力作用下,十九世纪以前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种巨变,无论从流布场所的角度,还是从表演形式的角度来观察,大都程度不同地出现萎缩、退化,或转型、变异,甚而中断、消失的变迁。
这种变迁的过程,虽然在日积月累、潜移缓变中进行,但当人们将今天的中国音乐与上世纪末的中国音乐比较时;或因“生态环境”变化使某类传统音乐的生存难以为继时;也或因那些具有权威影响的老民间艺术家(乐种、流派的“传人”)逐个辞世而使某一曲种、流派濒临失传边缘时;更或因面对西方音乐形式及其体系的全面渗透和大面积覆盖的现实时,中国音乐界便一次次敲响传统音乐危机和断层的警钟。对民族传统音乐遗产的爱护、保存和弘扬问题,一直受到中国音乐家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采取了许多抢救民族文化遗产和保护、扶持民族音乐的措施,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事实上,民族音乐永远与民族群体同在,永远跟随该民族的社会发展而发展。这一客观规律已为人类文明史所昭示。尤其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十多亿人口和悠久文化传统的华夏民族来说,民族音乐的传统是不可能断绝的。正如中国民族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所说:“中国文化,就总体而言,从来不是一个全封闭的系统,它是一条常新常在的大河,从金沙江流到吴淞口,奔流入海。虽然在吴淞口很难分析出其中的哪一滴水是从金沙江流过来的。但长江却始终是长江。”〔1〕
因此,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变革,造成中国传统音乐繁衍、延续进程的剧裂震荡,有可能形成某些文化层面的表象断裂。然而,深植于人民生活沃土的民族音乐文化之根却是断不了的。它必然会根据土质、气侯、环境和养分的变化,顽强地再生繁衍,甚而在断裂的层面上开出新的花朵,结出新的果实。
“一部中国音乐史就是这样从不断的失传声中传下来的。”〔2〕
三、当今中国音乐的表达方式
二十世纪中国传统音乐流变的结果,即为今天中国音乐的表达方式。
如前所述,延续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音乐,在二十世纪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首先从传统音乐流传——展演场所反映出来。民间音乐一部分失去赖以生存的生活基础,如部分劳动号子和歌谣,由于人工劳作逐渐被机器替代,因此部分劳动歌谣渐渐衰微;相当范围的乡村,受到城市文化浸染,纯朴自然的民间音乐亦渐趋退化。宗教音乐七十年代末期以前,许多需音乐参与或由音乐来完成的宗教礼仪,一度曾被当作“封建迷信”,中断了活动。以后虽然逐渐得以恢复,但由于不少熟知音律和乐器的道士、法师、僧侣等年事已高,普遍存在后继乏人的问题。文人音乐随着社会变迁,封建时代深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道的文人阶层,已被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知识分子阶层取代,他们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的角色,生活、工作和交往的方式,以及与音乐活动的关系等,皆与过去的“文人”不能同日而语。因此,传统的文人音乐今天业已转型。宫廷音乐封建朝廷既不复存在,为皇室服务的宫廷音乐活动自然随之终结,加上传承手段(乐谱、音响)的局限,对往昔宫廷音乐面貌的追寻,只能凭借有关典籍,或部分依靠今人的复制。
在部分音乐传统萎缩、退化或表层中断的同时,中国传统音乐的“遗传基因”,仍以旺盛的生命力在不断地繁衍延续;或为适应新的社会生活,吸取外来音乐形式而转型再生。
于是,从音乐形式的角度观察,今天中国音乐的表达方式是由两个不同组成部分共同呈现出来的:
(一)传统音乐的“原种”延续
中国幅员辽阔,地理和社会环境千差万别。在较少受到都市文化和外来文化影响的广大农村和交通不太发达的内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统的民歌、器乐、歌舞和宗教仪式音乐,至今仍较完整地保持着原本的面貌。只要我们深入到民间,就不难体察到传统音乐顽强的生命力,就会由赞叹中国民族音乐的优异与丰富。比如山西绛州的鼓乐,云南的纳西古乐等。东西南北中,各地区、各民族、各具特色的传统音乐就蕴藏于人民的生活中。它们表达方式的共同特征是:不刻意追求舞台展现,而以朴素自然的形态,与劳动、爱情、生活习俗和宗教活动融为一体,成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其产生与流传的过程,不易区分创作者、表演者和听众。其中,一些精通音律的民间音乐家,以自己深厚的艺术积累和独特的创作方式,为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江南的华彦钧(瞎子阿炳1893-1950)、广东音乐的何柳堂(1872-1933)、吕文成(1898-1981)、西安鼓乐的安来绪(1895-1976)、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音乐的吐尔地阿洪(1881-1956)等即为他们的杰出代表。
传统的戏曲和说唱音乐,由于其声腔和表演艺术,经历了宋朝以来几个不同朝代近千年的变迁和锤炼过程,形成了相对定型的声腔体系和表演程式。因此,即使受到本世纪各种外部条件的影响和冲击,仍保持着自己的特色继续发展。其声腔、伴奏乐器、打击乐的运用,以及唱、做、念、打的综合表演形式,也保持了各自的基本面貌。对此,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以“移步不换形”的法则对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规律进行概括和总结,是十分确切的。
传统音乐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原种”延续,是当代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影响和人文价值,对民族音乐文化的构成,始终是第一位的。
(二)西方音乐形式的利用及中西合璧新音乐形式的产生和发展
西方音乐对中国音乐文化全方位渗透和大面积覆盖的结果,一方面是西方音乐在中国的传播,从帕里斯特列那、巴赫、贝多芬,到德彪西、巴托克、期特拉文斯基;从独唱到合唱;从独奏到交响音乐;从歌剧、舞剧音乐到电影、电视音乐;从音乐厅和音乐艺术院校课堂的典雅音乐,到体育馆、露天舞台、商店、歌厅流传的流行音乐。这些主要由西方人创造的音乐形式,虽然可以由中国音乐家进行再诠释(不少技艺精湛的中国音乐家还因演唱、演奏这些作品而在各种不同的国际比赛中获得奖励),或供中国老百姓进行艺术欣赏。但这些源于西方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的音乐作品,毕竟不是中国音乐。
而另一方面,中国音乐家们对西方音乐形式和表现技法加以利用、借鉴和改造,使之与中国传统音乐材料作有机结合,用以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及中国人的思想情感。这股中西音乐交汇与融合的潮流,经过一个多世纪的积淀,事实上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新传统的组成部分,并与传统音乐的“原种”延续,共同构成今天中国音乐表达方式的形式载体。
二十世纪中西结合新音乐的表达方式极为多样,大体表现为下列形态:
1、在保持或基本保持传统音乐形式的前提下,部分吸取西方音乐的表现方法,对民族音乐形式进行加工改编或创作新曲。如刘天华的二胡曲《病中吟》、《空山鸟语》、《良宵》,彭修文编配的合奏曲《流水操》,李焕之的古筝协奏曲《汩罗江幻想曲》,何训田的室内乐《天籁》等。
2、采用中西合璧的表演形式,融通使用中西音乐的表现方法,进行改编或创作。如刘文金的二胡曲《豫北叙事曲》,吴祖强、刘德海、王燕樵的琵琶协奏曲《草原小姐妹》,朱践耳的唢呐协奏曲《天乐》,瞿小松的混合室内乐《Mong Dong》等。
3、采用西方音乐表现形式,以传统音乐材料为基本素材,进行加工改编或创作。其一,是把单声旋律的民歌或古代歌曲改编为多声部的合唱。这方面有两种类型:一是按照现在通行的美声唱法来编写,如瞿希贤改编的内蒙古民歌《牧歌》(无伴奏合唱);二是要求演唱上保留中国传统的韵味风情,在吐字、发声及行腔上,都要原汁原味。下面举两个实例:①《胡笳吟》(古琴弦歌合唱,李焕之编曲);②《茉莉花》(河北昌黎地区民歌,李群编曲),这首民歌具有独特的音韵,不同于普遍流传的江南民歌《茉莉花》)。其二,是用西方乐器来改编演奏中国的传统乐曲,如王建中的钢琴独奏曲《百鸟朝凤》(根据同名唢呐曲改编),黎英海的钢琴独奏曲《夕阳箫鼓》(根据同名琵琶曲改编),何占豪、陈钢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根据越剧音乐材料)等。
4、采用西方音乐体裁,根据不同的音乐内容进行新的艺术创造。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音乐作品的体裁品种广阔多样地发展起来,诸如大量的群众歌曲(齐唱歌曲——Mass Song 群体演唱的方式)、艺术歌曲(Art Song)、合唱(Cantata)、清唱剧(Oratorio)、歌剧、舞剧、协奏曲、交响音乐及各种西方乐器的独奏、重奏作品。这些虽是借鉴西方的音乐体裁,但音乐风格具有浓郁的中国特色。如聂耳的歌曲《码头工人歌》(百灵词)、《义勇军进行曲》(田汉词),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韦翰章词),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光未然),贺绿汀的钢琴曲《牧童短笛》,丁善德的钢琴曲《儿童组曲》,马思聪的管弦乐曲《山林之歌》,吴祖强、杜鸣心的舞剧音乐《鱼美人》,金湘的歌剧音乐《原野》(万方编剧),朱践耳的《第二交响曲》等。
上述四种中国新音乐的表现形态,均为中西两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两种文化交融的成分或轻或重、或隐或显;交融的渠道或宽或窄、或曲或直;共同显示出二十世纪中国新音乐多姿多彩的风貌。总之,从事专业音乐活动的作曲家与表演艺术家,必须同时具有中西音乐两种文化修养。因此,尽管新音乐作品的表演形式千差万别,但作品的精神内涵(主要从作品的题材、内容、音乐语言材料、结构方式、艺术风格和情感体验等方面表露出来)无不与中国传统文化(或社会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评估与展望
如上所述,今天的中国音乐是由中国传统音乐的“原种”延续及中西结合新音乐这两大部类共同组成的。这种状况,与绝大多数非欧洲国家——尤其是东方国家(或民族)的音乐文化状况相似。如何认识和处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关系问题,是中国音乐家所不能回避的。
从本世纪中国音乐的发展历史和现状看,传统音乐“原种”延续与中西结合新音乐的并行,其价值可以从文化和社会意义两方面显现出来:
文化意义:中西音乐的并行及交融,扩大了中国音乐家的文化视野,这一方面可以促进对传统音乐的更好继承,另一面又直接推动新音乐形式的创造。二十世纪中国音乐的表现形式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为丰富,这一基本事实表明,不同文化的交融,客观上对原有的单向文化带来了发展的新机与活力。
社会意义:中国音乐家兼取“古为今用”和“洋为中用”的原则,将传统音乐形式和外来音乐形式都视为表现中国社会生活及中国人思想情感的载体。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一些西方音乐的艺术形式(如齐唱、合唱、歌剧、交响音乐等)、表现工具(如各类乐器)和表现手段(如多声音乐的作曲技法等),以其饱满的音响、宏大的气势及表演形式的群体性,从一个侧面形成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传统音乐注重“空、灵、淡、雅、飘、逸、虚、静”意境的补充。它与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变革所贯穿的昂扬激奋的精神合拍,并产生了许多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优秀作品。如亿万人次传唱、家喻户晓的《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深刻地展现了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生活的主流,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
同时,在中西音乐并行及交融的历史进程中,某些传统音乐形式弱化——退化——异化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却始终引起中国音乐家的特别关注。我们认为,虽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部分民族传统音乐形式的衰微与转型再生,是社会变迁的文化伴随物,自有其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但是,民族音乐的发展,绝不应以削弱或牺牲本民族的音乐传统为代价。
为此,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几代中国音乐家在采集、发掘、抢救、整理、保存、传授“原种”的传统音乐方面,做了大量的、富于成效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中西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音乐形式。从肖友梅、赵元任、刘天华、黄自、冼星海、聂耳、马思聪等,到贺绿汀、吕骥、丁善德、李焕之等人,都为二十世纪中国音乐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弘扬,作出了有益的、成就显著的贡献。
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和政府文化主管部门的规划和组织下,数以千计的中国音乐家,深入到山野、农舍、森林、草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正在完成《中国民间歌曲集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中国曲艺音乐集成》四部大型的民族音乐文献资料,为传统音乐的“原种”延续与保存,提供翔实、可靠的依据。此外,大力倡导在国民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中,形成民族音乐的教学体系,用母语文化的精髓滋养一代代新的国民和培育一代代年青的音乐家。还积极鼓励作曲家在充分表达自己鲜明个性的创作活动中,努力寻求民族文化之根,将创作的基点深植于民族音乐的沃土。
我们坚定地意识到,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品位独特的音乐传统,是中国音乐家进行艺术创作活动的根基。中国音乐经历了近一个世纪向西方音乐学习、吸收、借鉴的历史过程,从艺术实践的不断总结中逐步跨越了对西方古典音乐、浪漫派音乐和现代音乐模仿借鉴的初级阶段,步入一个相对成熟的创造时期。今天,在世纪之交的新起点上,中国音乐正以自己独具的传统文化特质和无比壮阔的时代兼容力,显示出蓬勃发展的生机。*
注释:
〔1〕引自《人民音乐》1987年第8期第3页黄翔鹏《在亚太地区传统音乐研讨会上的发言》
〔2〕引自《中国音乐学》1987年第4期第5页黄翔鹏《论中国传统音乐的保存和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