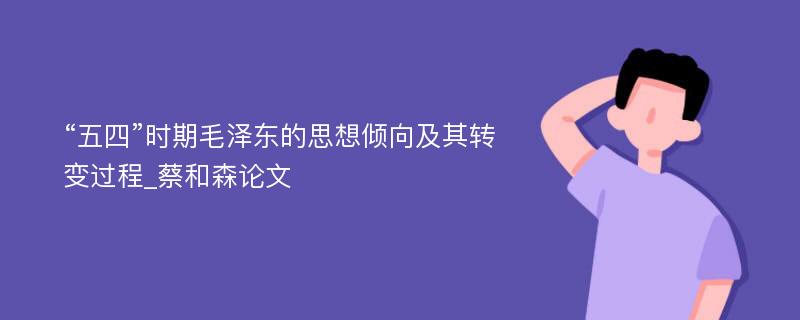
五四时期毛泽东的思想倾向及其转变过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倾向论文,过程论文,思想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04)02-0018-06
五四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这种传播是通过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译介、宣传,以及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冲突、论争、对话实现的,也是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学习、理解、认识马克思主义,不断反思自己的过程。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实践成为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者。其中较为著名的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蔡和森、毛泽东、恽代英、瞿秋白、周恩来等。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具有新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在实践中逐步展开,毛泽东后来成为这个过程的主要代表。和当时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一样,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是在实践中逐步确立的,有一个在政治上从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主义到共产主义,在哲学世界观上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五四期间及其以后的一段时期,是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开始形成的重要阶段。关于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思想的转变,我国理论界的一种比较主流的看法是,他已经在1920年冬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
毛泽东的文化启蒙教育是儒学,但他并没有真正读进去。1964年,他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中回忆说:“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还写过文章。”1910年,入东山高小,开始学习一些自然科学和社会历史的“新学”知识。在看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后,接受“维新”思想,赞成君主立宪。1911年到长沙进入湘乡驻省中学读书,1913年至1918年,就读于湖南第一师范。在此期间,发生了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帝制事件,受同盟会会员于右任主编的《民立报》和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的影响,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抨击了封建专制主义及其理论基础三纲五常,在哲学世界观上,则形成了自己最初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
1913年10月至12月间,他在湖南师范学校的课堂记录《讲堂录》中写道:“横尽空虚,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惟我(贵我)。”[1](P601)1917年至1918年间他读了德国康德派哲学家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后,写了万余言的批语,明确提出了“我即宇宙”的命题。他写道:“吾从前固主无我论,认为只有宇宙而无我,今知其不然,盖我即宇宙也。”[1](P231)
何谓“我即宇宙”?毛泽东在有关的文章中实际上从三个方面作了解释,一是“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也。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1](P148)。所以在世界万事万物中,唯我独可尊、独可畏、独可服从。这里的“我”,指的是一般的个人之“我”,团体、社会、国家、宇宙都可本源于、归属于这种一般个人之“我”。二是“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为宇宙之一体,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虽有偏全之不同,而总有几分存在”[1](P85)。三是万物之差别皆源于人的主观思想,“差别之所以生,生于有界限。为界域生活之人类,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动有限,对于客观界,遂以其思想能力活动所及之域,而种种划分之,于是差别之世界成矣”[1](P246)。
毛泽东的这种主观唯心论看法,主要是受康德主义与孟子思想的影响形成的,或者说,是他用孟子思想去读康德主义的一种体会。在《讲堂录》中,他述说道:“孟子曰:体有贵贱、有大小。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一个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个之我,肉体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我也。”他主张“我之界当扩而充之,是故宇宙一大我也”[1](P589)。
从“我即宇宙”出发,毛泽东一方面将精神和物质的对立统一于“我”,提出在“我”之基础上的精神不灭、物质不灭的命题,指出:“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灭,物质不灭为基础(精神物质非绝对相离之二物,其实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1](P199)另一方面在伦理学上主张个人主义,指出,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实现自我,实现自我就是“充分发达吾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因此,“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表同情于他人,为他人谋幸福,非以为人,乃以为己”[1](P203)。
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和个人主义的主张,与毛泽东当时的政治立场有内在的联系和一致性。对一般的个人之“我”的推崇,通过对封建专制主义的理性批判和对个性解放的宣扬,在政治上表现为自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对精神之“我”的过分推崇,又使他的民主主义容易陷入空想和走向极端。前者表现为1919年他从北京回到长沙后,试图仿效日本人武者小路实笃的设想,试验新生活,搞新村运动;后者表现为1918年他到北京后,很快就受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并接受了它。
关于前者,毛泽东当时谈到:“我数年来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7年(1913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因他们多不能久在湖南,我亦有北京之游,事无成议。今春回湘,再发生这种想象,乃有在岳麓山建设新村的计议,而先从办一实行社会说本位教育说的学校入手。此新村以新家庭新学校及旁的新社会连成一块为根本理想……”[1](P449)。至于这种新村的性质是什么,毛泽东没有留下详细的说明,他当时也没有一个系统而确定的设想,很可能仅仅是一种模模糊糊的空想社会主义幻想。关于后者,毛泽东后来谈到:1918年在北京时,“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2](P128)。
从时间上看,新村设想的再度提出与毛泽东接受无政府主义是同时的,可以推测,新村设想也是一种或者说部分上也包含着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确切地讲,是毛泽东自己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理想。
毛泽东是1918年8月第一次到北京的,曾在李大钊主持下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利用北京大学的有利条件,毛泽东有可能比在湖南更直接地接触一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和一些新思潮。当时的这些政治上的要求和社会理想,反映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一些新的变化,也反映了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些缺陷。一方面,他开始对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国家制度在个性解放上表示怀疑与不满;另一方面,正如他在1957年回忆时所说:当时我们还没有学到马列,想找个地方试验自己的新生活。毛泽东这时的思想状况是,在原有的民主主义中渗入了一些不确定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使他的民主主义的批判思想更为激进。这预示着他不会止步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而会努力去寻求新的改造中国社会的思想武器。
1919年4月,毛泽东从北京回到湖南不久,五四运动爆发。毛泽东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关注着运动的发展,他组织创办《湘江评论》,参与和主持驱逐张敬尧运动,联系世界范围高涨的民众运动特别是俄国的十月革命,高度评价了五四运动。在1919年7-8月间发表于《湘江评论》第2至第4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毛泽东欣喜地写道:“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施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崛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话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P390)
毛泽东呼吁民众大联合,是因为他认为,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运动,“一言蔽之,‘由强权得自由’而已。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1](P293)。平民运动的兴起,在毛泽东看来,是根源于吃饭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但是他反对用激烈的方法打倒强权,因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所以我们的见解,在学术方面,主张彻底研究,不受一切传说和迷信的束缚,要寻着什么是真理。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有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1](P293-294)。
《湘江评论》期间文章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毛泽东对平民运动的关注和肯定,这对于他曾经信奉的个人主义无疑会产生震动。对平民运动起因的研究也使毛泽东看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这些研究还没有导致他在世界观上的根本反思,而只是扩展了他的社会历史视域。毛泽东当时虽然意识到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但是这种意识还只是一种经验的意识,一些学者根据毛泽东在上述文章中讲了“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句话,就断言毛泽东已经初步确立了唯物史观,这是不确切的。在理论上,他还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辩证关系的原理,不了解十月革命的真正历史意义,把十月革命混同于一般的平民主义运动,因而当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发生时,他没有像李大钊那样看到论争的实质,而是在湖南组织了问题研究会,并撰写研究会章程,尽管在章程中有“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因此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和“问题之研究,有须实地调查者,须实地调查之”的条文,但毛泽东当时还没有觉悟到马克思主义在解决中国问题上具有根本意义。正如他在1920年3月14日给周世钊的信中所说:“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1](P474)在一定的程度上,他还是赞同杜威思想的,例如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中称,他所主张的改革,“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1](P293)。
《湘江评论》期间的毛泽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思想上,离马克思主义、离科学社会主义还有相当的距离。就其民主主义而言,虽然在思想上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意识,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主张非暴力,实质上还是民主改良主义,或者说,是一种混杂着无政府主义的民主改良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毛泽东当时更欣赏后者,就是在上面提到的那篇《民众的大联合》中,他认为,民众联合以后的行动有两派,一派是很激烈的,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其首领是一个生在德国的叫马克斯;一派是较为温和的,这派人的思想“更广,更深远”,其首领为一个生于俄国的叫克鲁泡特金。文中所提到的这位克鲁泡特金,就是对于当时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很大吸引力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倡议者。
毛泽东初步认识马克思主义的过程发生在1919年底他第二次去北京以后,与第一次去北京不同,毛泽东看到了许多新的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使他有可能重新认识十月革命的意义,1920年7月回到湖南后,他领导了湖南自治运动,创办了文化书社,组织了新民学会和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些活动,体现了青年毛泽东试图通过传播新思想来启蒙民众,进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新宪法,创建新湖南,“以增进湘人幸福,树立全国模范”的政治热情。但是与“新村运动”一样,这不过是又一个空想。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希望避免“流血革命之惨”,搞“呼声革命”的幻想基本破灭了。1920年11月25日他在给向警予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失望:“湖南人脑筋不清晰,无理想,无远计,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涂,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1](P548)
这要另辟的道路是什么,写此信时毛泽东自己也不清楚,但是总结自己政治活动的经验教训,思考新的路,可以肯定是毛泽东这段时间经常想的问题。正是在这段时间,毛泽东读到了他过去还不曾了解的三本共产主义书籍——马克思恩格斯著、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出版),英国人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1920年10月出版),考茨基著、恽代英译的《阶级斗争》(1921年1月出版)。这些书籍给青年毛泽东指出了一条改造社会的新的道路。据斯诺的记载,他后来回忆道:“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2](P131)
关于斯诺记载的毛泽东的这段自述是否准确,后面再分析。就从这段自述本身来看,也说明,第一,毛泽东是在1920年底1921年初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讲他在这之前已经是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的说法难以成立;第二,毛泽东在这段时期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包括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所认识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主要是马克思的历史学说,核心是唯物史观。所以,讲他的世界观在1920年冬已经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转变的说法也很难成立。事实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当时还不了解辩证唯物主义理论体系。(注: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的历史情况,另文介绍和分析。)
严格地讲,毛泽东当时的思想状况是,开始认识并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斗争学说,世界观正在发生转变,在政治上也开始脱离小资产阶级民主改良主义而转向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世界观和政治立场上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具有了新的实践要求,毛泽东自己积极参加了变化中的社会实践活动,在实践中通过艰苦的摸索才认识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蔡和森起了重要的影响作用。
蔡和森是毛泽东的朋友,成立于1918年4月的“新民学会”即由他和毛泽东等人共同发起组织。1919年12月,蔡和森赴法国勤工俭学,认真阅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早于毛泽东认识和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且很快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拥护者,他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有很深刻的理解,是这一时期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家。改造中国与世界这一新民学会新的方针,就是蔡和森等赴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在蒙达尔尼会议上首先提出、尔后在国内新民学会会议上得到毛泽东等的积极响应而最后被确立的。
蔡和森对毛泽东的影响除了经常以自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热情和理想抱负感染和激励毛泽东外,更重要的是引导毛泽东认识和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特别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走出空想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早在毛泽东热心于新村运动,希望通过这种试验引起社会的关注和效仿,逐步推广,实现新社会时,蔡和森虽然也表示赞成,但是认为这只是个“乌托邦”,在法国期间,蔡和森一直保持着与毛泽东的通信联系。1920年8月13日和9月16日给毛泽东的两封信有特殊的意义。
前一封信主要讨论了社会主义问题,蔡和森写道:“我近对各种社会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的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建设社会经济制度。”蔡和森在信中明确表示:“我认为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因为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抗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3](P50-51)后一封信主要讨论了成立共产党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前一封信已经涉及,蔡和森在前一封信中写道:“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3](P51)后一封信中,他联系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历史,进一步与毛泽东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这封长信给毛泽东的深刻印象还不仅如此,蔡和森在信中向毛泽东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这可能是毛泽东第一次接触唯物史观思想,所以给他以崭新的感觉。正是在仔细阅读了这些信后,毛泽东表示了与无政府主义划清界限的态度,他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著名回信中写道:“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惟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我固无研究,但我现在不承认无政府的原理是可以证实的原理,有很强固的理由。一个工厂的政治组织(工厂生产、分配、管理等),与一个国的政治组织,与世界的政治组织,只有大小不同,没有性质不同。工团主义以国的政治组织与工厂的政治组织异性,谓为另一回事而举以属之另一种人,不是固为曲说以冀苟且偷安,就是愚陋不明事理之正。况乎尚有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4](P4)
这封信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毛泽东的世界观根本转变的重要标志,可能不一定确实。仔细阅读这三封信,不难发现,“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个论断,并不是毛泽东已有的思想,而是他对蔡和森信中观点的一个概括,当然,毛泽东是同意这个基本观点的。但是他当时还不很懂唯物史观。根据之一,信中毛泽东自己坦言对此没有研究;根据之二,蔡和森在信中将惟理观与唯物史观对立所作的分析,可能为了“直捷简单”的缘故,有不甚准确的地方,但是毛泽东对此并无察觉,依毛泽东当时在许多问题所表现出的锲而不舍的研究态度和精神,如果他已经掌握了唯物史观,一定会借题发挥,深入探讨;根据之三,信中毛泽东将惟理观与唯物史观的对立,简单理解为唯物史观是可以证实的事实,而惟理观则相反,并以此类推,无政府主义也不能为经验事实所证实,所以是错误的。毛泽东这时还没有社会历史实践的观点,他对于真理与谬误的区别,还是一种朴素的经验判断,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有一些杜威的“实验主义”痕迹。
毛泽东的这封信中最重要之点是他在蔡和森的引导下在政治上从无政府主义转向了接受马克思主义,承认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一点,可以从1921年1月2日新民学会长沙会友第二次会议中他的发言得到进一步证明。这次会议是在毛泽东收到蔡和森的信以后开的,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讨论巴黎方面蔡和森等关于学会宗旨的提议。在议到用什么方法改造世界与中国时,毛泽东的发言是:“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办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4)(P2)
但是这只是转变过程的开始,毛泽东当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和提法,但在理论上还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西行漫记》上所记载的毛泽东1920年冬把工人组织起来和读《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等活动,实际上都发生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从时间上看,这三本书分别出版于1920年8月、10月和1921年1月,即毛泽东已经第二次从北京回到湖南之后而不是《西行漫记》上所记载的在北京期间(注: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的时间是在1919年12月至1920年4月。),毛泽东当时要在湖南得到这些书,也还应该有一段时间;从现有的资料记载上看,毛泽东与工人群众的接触较早,1917年10月就曾开办过工人夜校,而后又与黄爱、庞人铨组织的湖南劳工会(成立于1920年11月21日)有联系,他最早参与组织工人的政治活动即与湖南劳工会有关,这使得他有可能深入了解中国的工人阶级。但是从了解中国的工人阶级到真正认识中国的工人阶级的历史地位,对于毛泽东来讲,是在他参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以后才完成的,1921年8月,毛泽东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的主任,参与组织领导了1921年10月的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1922年9月的安源路矿工人的罢工和1922年10月的长沙泥木工人的罢工等运动,正是在这些工人运动的实践中,毛泽东逐渐从实质上搞清楚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确立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念。
如果这些分析可以成立的话,毛泽东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的转变应该发生在1920年冬以后,毛泽东的世界观的转变和政治立场的转变有一致的方面,也有不一致的方面。从最初的主观唯心主义到唯物史观的基本确立使毛泽东最终抛弃了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和民主改良主义而转向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但是对唯物辩证法的不甚了解,又使得毛泽东的哲学世界观只是初步的马克思主义。这种状况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相一致的,当唯物史观已经被陈独秀、李大钊以及后来的毛泽东所基本接受和掌握时,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传播尚在起步,中国共产党就是在有了一定的理论准备而这种准备又不很充分的情况下成立的。它预示着中国共产党必然会反复经受这种理论准备不充分而在实践中带来的困难的考验,并在考验中艰难地补上这一课而使中国革命在曲折中走过来。
收稿日期:2003-12-18
标签:蔡和森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1920年论文; 共产党宣言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政治倾向论文; 历史唯物主义论文; 无政府主义论文; 湘江评论论文; 五四运动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