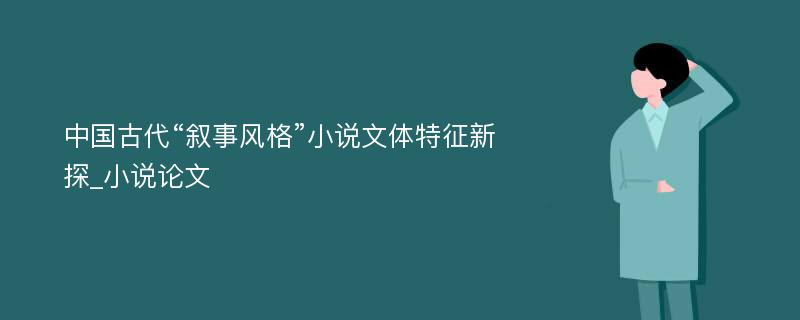
中国古代“说书体”小说文体特征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书体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文体论文,特征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0257-5876(2007)07-0048-08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起源于民间说书。通常被学者视为通俗小说萌芽的敦煌变文,就是记录、整理唐代“俗讲”、“转变”之成果的书面文本。宋元时期,都市“说话”艺术盛行,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民众的消闲娱乐需求,书贾与书会先生等联手将勾栏“说话”转化成了书面文本——话本,从而实现了中国小说史上的一次革命,为通俗小说确立了基本的文体形态和叙事传统,并直接导致了明代通俗小说的兴起。明代前期的通俗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力于民间说书的孕育,尽管其改编、写定者也曾在不同程度上付出过创造性的劳动,提升了民间说书的艺术品位,但并没有脱离或割断这些小说与民间说书的亲缘关系。明中叶以后,民间说书日趋繁兴,说书成果也就不断地被改编为通俗小说,如清代非常流行的英雄传奇小说和公案侠义小说就脱胎于民间说书。可见,没有民间说书的哺育,就不可能有通俗小说的生成和繁荣。对于受民间说书哺育而形成的通俗小说,我们不妨称之为“说书体”小说。该类小说占据了古代通俗小说的大半壁江山。尽管从题材内容上看,该类小说可以分为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怪小说和公案侠义小说等多种类型,但是由于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秉承了民间说书的艺术基因,或多或少地受到了说书艺术规律的制约,因而它们在人物塑造、情节模式、叙事旨趣、文体形态、语言程式等方面,都表现出了若干民间说书的艺术特征。
“说书体”小说与其他类型的小说一样,也把塑造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作为其主要的艺术任务之一。它所塑造的主要正面人物往往具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和鲜明的类型化倾向,诸如刘邦、刘秀、刘备、李世民等,就是仁民爱物、无与伦比的仁君楷模;姜子牙、诸葛亮、徐懋功、刘伯温等,则是足智多谋、神机妙算的智慧化身;而关羽、秦叔宝、尉迟恭、薛仁贵等,则属于本领非凡、武艺超群的武将典型;包拯、施士纶、彭鹏、刘墉等,则是为民请命的清官代表;武松、鲁智深、展昭、白玉堂、黄天霸等,则为抱打不平的侠客典范。同样,“说书体”小说塑造的反面人物,诸如曹操、高俅、秦桧、潘仁美、庞昆等,也是诸种奸恶品质的集大成者,从反面意义上说,也是常人难以企及的范本。
对于这些人物形象,当我们习惯于用真实性、典型性等现实主义的美学标准来衡量他们时,就会觉得描写过火、不近情理。比如,不少研究者都指出《三国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是类型化的,它说好的人一点坏处都没有,而说坏的人一点好处都没有,认为这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可能全好,也不可能全坏。言下之意,人物性格只有写得复杂一些,既有优点又有缺点,才真实可信。同时,又有不少研究者指出,《说唐全传》等通俗小说,对人物的智慧、勇武等的描写过于夸张,让人不可思议。孤立地看,这样说都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我们了解这些小说曾经过民间说书的孕育,多半是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改写成的,那么我们就会知道它们为什么要这样描写人物。
首先,民间说书是面向平民大众的通俗文艺,“说书人”为了赢得听众的喜爱,总是自觉从下层民众的生活出发,根据下层民众的生活、心理和想象,来塑造英雄人物的;当然,也是从下层民众对于这些英雄人物的追慕和崇拜出发,来夸大甚或神化其才能和武勇的。这样,它所塑造的英雄人物才能充分体现民心民意,受到下层民众的喜爱和崇拜。
其次,说书主要是诉诸听觉的艺术,“说书人”为了让听众过耳不忘,留下深刻印象,往往主要人物一出场,即抓住其外形的某些特征(如长相、力气、武艺、才智等),运用诗词赋赞等进行大胆的夸张,以求“危言耸听”,先声夺人。并且,人物一出场,就对其善恶美丑进行褒贬,所谓“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与之丑貌”,目的就是要让听众一下子就能分清好坏,否则性格复杂、善恶难分,就会给听众造成一种理解、判断上的障碍,影响现场接受效果。对于人物性格的描写,“说书人”也常用夸张的方法,强调其性格的一两个方面,因此人物性格往往单纯、明朗、突出、强烈。毛宗岗《读三国志法》论《三国演义》有所谓“三绝”:“诸葛孔明一绝也,关云长一绝也,曹操亦一绝也。”并判定诸葛亮“是古今来贤相中第一奇人”,关羽“是古今来名将中第一奇人”,而曹操则是“古今来奸雄中第一奇人”。所谓“绝”和“第一”,不就是说他们乃是人世绝无仅有的超人吗?如果《三国演义》不采用这种夸张化、传奇化、理想化的艺术方法来凸显人物的主要性格,那么诸葛亮、曹操、关羽等恐怕就不会给人如此强烈的艺术感受了。老舍在谈民间说书的人物塑造时说得好:“人物的描写要黑白分明,要简单有力的介绍出;形容得过火一点,比形容得恰到好处更有力。要记住,你的作品须能放在街头上去,在街头上只有‘两个拳头粗又大,有如一双大铜锤’,才能不费力的抓住听众,教他们极快的接受打虎的武二郎。在唱本中也不是没有详细描写人物的,可是都是沿着这夸大的路子往下走,越形容越起劲,使一个英雄成为超人,有托天拔地的本领。”①
再次,“说书人”为了更好地驾驭纷繁复杂的人物故事,也需要对人物进行分类、定性,赋予人物以不同的角色身份。著名评书艺术家连阔如曾说:“说评书的艺术和唱戏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唱戏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表情分为喜、乐、悲、欢。文讲做派,武讲刀枪架儿。评书的艺人每逢上台,亦是按书中的人物形容生、旦、净、末、丑,讲做派,讲刀枪架儿。”② 倘若人物性格矛盾、复杂,角色定位不明确,“说书人”就很难把握、记忆并演绎出这个人物的性格特点。因此,根据说书的需要,“说书人”常要设置几种人物类型,并设置对立方的人物类型,由此构成一定的人物关系模式。研究民间说书的专家戴宏森,曾从大量的长篇书目中归纳出一个由书胆、书领、书筋、书师、书柱、“反座子”(含书贼)构成的“六位一体”的人物模式③。“书胆”是指书中的主人公,是左右书情发展的核心人物,如《水浒传》中的宋江、《杨家将》中的杨延昭、《说唐全传》中的秦叔宝、《说岳全传》中的岳飞、《三侠五义》中的包拯等;“书领”是书中能够制约书胆和全书命脉的领袖,如《水浒》中的宋高宗、《杨家将》中的宋太宗、《说岳全传》中的宋高宗等;“书筋”是书中的正面诙谐人物,如张飞、李逵、程咬金、牛皋等;“书师”是书中辅佐主人公的正面智慧型人物,如诸葛亮、吴用、徐懋功、刘伯温等;“书柱”是协助主人公的配角,如辅助岳飞的马前张保、马后王横,辅助包拯的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反座子”是代表反面力量的人物类型,如《水浒》中的高俅、《说岳》中的秦桧、《杨家将》中的潘仁美等。正是靠这种人物关系模式,“说书人”才掌控了一部大书中复杂的人物关系和各种矛盾冲突,有条不紊地演绎出丰富多彩的故事。
不言而喻,如此设置人物关系,突出人物性格,难免会让人物不同程度地带有理想化、类型化甚至脸谱化的特点,但是从“听众”接受、书场演出以及说书经验的总结与传承等实际需要来看,这样做又是非常必要的和行之有效的;而且,考虑到“说书体”小说塑造的大批英雄人物,能以不可思议的艺术魔力潜入平民大众的心里,致使农工商贾、妇人孺子莫不向慕神往,我们也不该简单地说这些人物形象没有多少审美价值。
“说书体”小说都是比较典型的消闲文学,它以讲故事娱人为本位,因而非常注重故事情节的编撰与建构。但是阅读“说书体”小说,我们常会感到不少小说的故事情节就好像是一个模子套下来的,例如《杨家将》、《说岳全传》、《说唐后传》、《说唐三传》、《说呼全传》、《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以及《粉妆楼》、《万花楼》等,其所叙内容不外乎就是:番邦入侵或打来战表,朝中选派良将,奸臣勾结番邦、残害忠良,忠良之后破敌立功,得胜还朝,铲除奸臣。书中一些情节关目也常常雷同,如两将交锋、攻关劫寨、比武夺印、设台打擂、力举千斤闸、枪挑铁滑车、摆阵破阵、盗宝拿贼、摆空城计、祭铁丘坟、三请某某人、三打某某地,以及美女抛打绣球、女将坐山招夫,或番邦少女爱上中原小将,等等,诸如此类,屡见不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陈陈相因的现象?
如果对民间说书有所了解,就会明白这就是艺人常说的“摘挂”或“翻瓤子”。戴宏森说:“历代说唱艺人要说好长篇书,在市场上立住足,就必须掌握足够多的故事、事件、语言的‘部件’、‘零件’,以便对书情作随机处置,逢枝开花,遇路转弯。从别的书目中移植叫座儿的部分书情,改头换面,借树开花,叫做‘摘挂’。”④“摘挂”对于艺人学艺、说书,都是必不可少的。一个艺人在出道之前,首先是大量听书。连阔如说:“早年说评书的收徒弟,做徒弟的跟着师傅在场内听活儿(听活即是学书)”,“若是记性好的人,听个几年评书,怎么也能听会了一套两套的”。⑤ 金受申也说:“过去评书演员大部分是先有了职业,平日因为爱好评书,就天天听书,日子久了,拜了师就能说书。”师父教徒弟也是让他掌握某部书的情节梗子和一些基本的书套子⑥。耿瑛还说:“个别艺人没真正学过一部书,东听一点,西听一点,把人家的精彩回目七拼八凑都拢到自己这部书中来。也有的是某一艺人说不好书,同行们出于江湖义气,大家帮助,每人把自己的拿手书中的一个‘大坨子’给了他,他重新串连在一起,凑成了一部‘新书’。”⑦ 即使是艺人自己“纂弄”某部书,他也难以摆脱一些情节套路的影响,而多半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金受申说:“评书演员怎样进行创作呢?有的是个人制作,如石玉昆纂弄《三侠五义》,白敬亭纂弄《施公案》,都是个人创作,书中大梁子,不外乎藩王造反、皇帝家丢宝找宝、钦差大臣放赈等等庸俗套子活。”⑧ 如此一来,由艺人说书成果改编而来的“说书体”小说,出现情节套路化、关目雷同化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实,不独我国的民间说书如此,国外的说书艺术也不例外。以研究民间口头史诗著称的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在《故事的歌手》中说:“人们只要通读一国的口承史诗集便不难发现,相同的主要事件和描绘俯拾皆是。”他称这些“相同的主要事件和描绘”为“主题”,并举例说《博格达之歌》与《罗兰之歌》对“集会”的讲述是“惊人地相似”。“这类事件在许多歌中不断出现。经过无数次的聆听,年轻的歌手在开始演唱之前,便已熟习了这种主题的模式。”当他熟习了一定数量的“主题的模式”后,他就可以上场表演了。当然,他在袭用某一故事模式时,也会进行一些变异,这些变异“来自于细节、描绘的添加,修饰的扩充,行为的变异……还有一些变异来自于歌中人物出现顺序的变化,从这个位置移到另一个位置的变化,形成了新的平衡和模式,而故事的核心仍保持了原貌。”⑨
以上这些经验总结和理论概括,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评价古代“说书体”小说情节的模式化现象,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说书体”小说虽然情节模式化现象突出,但由于它们是用旧套子来装新故事,并且善于在故事情节的传奇化方面做文章,所以即使模式相近,也照样能翻新出奇,引人入胜。敦煌变文如《伍子胥变文》、《韩擒虎话本》等,就已表现出将人物故事传奇化的艺术倾向。宋元话本则更注重故事的传奇性,如“小说家”话本,即喜谈闾巷异闻、蹊跷怪事,并时常运用科诨玩笑,制造奇趣;讲史话本则以演说金戈铁马的兴废争战见长,它重在敷演交锋厮杀、惊险热闹的斗争场面,以求抓住听众。至于明清英雄传奇,则更把两阵对圆的交锋厮杀作为叙事重心,力图激起受众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公案侠义小说,也是靠曲折离奇的案件和惊险刺激的江湖恶斗来取悦受众。可以说对情节传奇性的刻意追求,已构成了“说书体”小说的艺术生命线。而这一点,也正是受民间说书的影响所致。
对于以娱众为要务的民间艺人来说,没有故事性和传奇性,实际上也就等于没有了听众。精通评书创作与演出规律的金受申在《老书馆见闻琐记》中曾举例说,民国时期一个著名评书艺人张虚白因自身文化水平高,不去说他拿手的《西汉演义》,改说《红楼梦》,结果失败了,听众的意见是:“谁听这么瘟的《红楼梦》。”因此,他指出:“评书就怕瘟,换句话说,谈情说爱的故事,决不能作为评书说。评书必须故事性强;必须有斗争故事(旧评书也不外两个或两个以上集团的斗争故事);故事必须有连锁扣……评书最忌讳烦冗地叙家常。”闻国新在介绍1914年北平的说书情况时也说:“在中国过去第一流的小说,除了《红楼梦》和《金瓶梅》两书之外,其余都被装入这一般说书人的嘴里。”⑩
这使我们不由得想起《金瓶梅》的成书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瓶梅》是根据民间词话记录、整理、加工而成的。但是从民间长篇说书的特点及其经验总结来看,像《金瓶梅》这种主要描摹琐碎的家庭生活,反映复杂的人情世态,结构线索又不单纯、明朗,更重要的是没有多少故事情节和悬念可言的作品,在其成书之前,究竟能否在书场上没完没了地讲唱下去?要知道,“评书最忌讳烦冗地叙家常”。宋元以至明中叶的长篇说唱文学,还很少看到有不以故事情节取胜的作品,《大唐秦王词话》即以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和矛盾斗争的激烈紧张见长,这与《金瓶梅》大不相同,“《金瓶梅》全书首尾相应的连续结构,在一回一回衔接之处很少见到那种‘未知如何……’式的紧张处,更不像一种由说书一场一场的独立回目组成的章回连环故事”(11)。《金瓶梅》问世后,目前也还没有发现有哪个艺人整本地演说它,顶多只是从《金瓶梅》中截取某些片断,以子弟书等短篇形式来加以说唱。因此,如果说“兰陵笑笑生”在创作《金瓶梅》时曾从民间说唱中汲取过一些故事片断,那倒有这个可能,但是如果说整本的《金瓶梅》都是根据民间词话改编而成的,恐怕不符合实际。
“说书体”小说除了追求情节的传奇性外,不同类型的“说书体”小说在情节内容方面还经常出现交叉、融合的现象。要解释这一现象,也离不开对民间说书特性的认识。民间说书的伎艺性、商业性与娱乐性,导致说书艺人在演说某一类题材的故事时不可能故步自封,而总是有意地打破门户之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只要是听众喜爱的人物、故事,不管其本来出于“讲史”、“神怪”,还是“公案”、“侠义”等,他们都能及时地加以借鉴、模仿,这就使其说书成果被加工成小说文本后,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文兼众体”的特点。因此,文体纯正的“说书体”小说,几乎是不存在的。这也是通俗小说文体的一个突出特点。也因此,对于“说书体”小说的文体兼容,我们不应仅从小说文本到小说文本,作单向度的考察,或只是从小说史的角度对之加以诠释,否则就会得出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比如,有不少学者指出清代英雄传奇小说借鉴了才子佳人小说、神怪小说的笔法、体例,这当然是言之有据的,但较少提到这是英雄传奇秉承了民间说书艺术的基因所致,因而就难以对这种文体融合现象作出确切的诠释。再如,有的学者认为把《三侠五义》等公案侠义小说看成是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产物是不正确的,因为小说史上公案侠义小说早就存在,用不着合流(12)。这样说似乎有理有据。但是,如果了解《三侠五义》等小说产生的背景与过程,便不难发现清代中后期出现的公案侠义小说乃是民间艺人在演说《龙图公案》等公案小说的艺术实践中,根据听众的兴趣和口味,逐渐在公案故事中融入侠义小说的成分而形成的,因此说《三侠五义》等公案侠义小说是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合流的产物,是切合实际的。
另外,“说书体”小说在情节建构上所表现出的缀段性和直线化的特点,其实也与民间说书的影响有关。因为说书人一张嘴不能说两家话,人多了,事件的头绪复杂了,不仅说书人自己会顾此失彼,听书人也会晕头转向。艺人常说“大书一条筋”,“一条线,头不断”,强调的就是情节结构的直线性特点。因此,“说书体”小说一般都以主要正面人物的命运线作为主线,把围绕着主要人物的遭遇、历险和磨难等产生的一个个故事单元连缀在一起。这种“金线串珠”式的结构,既易于设置悬念,抓住听众,使听众不断地为主人公担忧,又能灵活地适应书场分段演说的实际需要。因此,绝大多数英雄传奇小说、神怪小说、公案侠义小说,都采用这种缀段性和直线化的结构模式。
“说书体”小说中语言运用的程式化现象也比较突出。敦煌变文、宋元话本就已形成了程式化的表述方式,诸如开头有“入话”,结尾有“散场诗”,正文“散韵相间”,诗词韵语的安排,一般都是以“正是”、“但见”、“怎见得”、“端的是”、“有诗为证”,或者是“常言道”、“俗话说”等话头引入的,诗词韵语(包括描写人物形貌的赋赞)有不少是现成的套语,反复地出现在不同的作品里。讲史话本描写武将装束、披挂、坐骑,以及交战的方式,甚至连交战的回数等,也都是程式化的,在不同的打斗中随意套用;至于渲染打斗的诗词韵语也是套路化的。后来的英雄传奇小说更是如此。
这种陈陈相因的描写,几乎泛滥成灾,让读者不胜其烦。不过,如果从说书的角度看,这种现象体现的正是民间说书的艺术本色。说书艺人在演说某一题材内容的故事时,不仅要掌握一定数量的情节套路和叫座的故事关目,同时还要记诵足够的语言构件,以便根据人物、场景的变换和情节的发展,随时调用,并加以拆改或替换。这些语言构件,或是用于正话开头的诗词,或是用于描绘人物、场景的韵文套语,如各种人物赞、盔甲赞、兵器赞、战阵赞、景物赞等,艺人只有记得滚瓜烂熟,现场演说才能得心应手。扬州评话艺人有一个口诀,说:“记住地址、人名、府城、情节,一辈子说书有吃喝。”(13) 一些老艺人课徒授艺用的秘本,名为“梁子”,就是由某一书目的故事梗概和常用的诗词赋赞组成的(14)。可见这些程式化的语言构件对于说书伎艺的传承和书场演出,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在考察南斯拉夫说书时,也多次指出“程式”对于歌手学艺、表演的重要性:“程式是由于表演的急迫需要而出现的一种形式”,“年轻的歌手必须学会足够的程式以演唱史诗歌”,“歌手从别人那里听来的程式最终成为其诗歌思想的一部分,他一定要有足够的程式来进行创作”,否则就无法适应书场快速创作的需要。洛德所讲的“程式”,主要指“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为表达一种特定的基本观念而经常使用的一组词”。其中,“最稳定的程式是诗中表现最常见意义的程式。这些程式表示角色的名字、主要的行为、时间、地点”等,它们是“口述文体的基石”,“它们的实用性表现在,有许多的词可以替换这些程式当中的关键词”,可称之为“替换律”。歌手掌握了某些基本的程式后,便可以用其他的词来替换这些程式中的关键词(15)。洛德所讲的程式化与替换律,不仅适用于南斯拉夫的口传史诗,也与我国民间说书所体现的艺术特点不谋而合。
可见,中外的民间说书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和规律,当说书成果转化为书面文本时,这些特点和规律便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下来,诸如故事情节的模式化、雷同化和语言表述的程式化等,如果我们不从说书角度去理解,就有可能据之得出不合实际的结论。比如,有的学者发现《三遂平妖传》与《水浒传》有十三篇诗词赋赞是一样的,于是认为两书为同一人所作(16)。其实从说书艺术的角度看,诗词赋赞本来就是一种程式化的东西,说“水浒”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平妖”故事的艺人可以用,说“西游”、说“封神”故事的艺人也同样可以用(如《西游记》与《封神演义》至少有二十五首赞词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些诗词赋赞在说书领域几乎可以到处搬用。因此,当文人作家取材于艺人演说的“水浒”、“平妖”、“西游”、“封神”等故事来创作《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小说时,它们之间出现诗词赋赞之间的雷同现象,实不足为怪。这种雷同并非出自写定者之手,而是写定者汲取的民间说书成果原本就存在的。因此,也就不能以此说明它们的写定者是否为同一人,也不能据之说明《西游记》与《封神演义》谁抄袭了谁(17)。
“说书体”小说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书人”总是喜欢对所叙的人物、事件评头论足。倘若用一般的文艺理论观点来看,就会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因为故事、人物的思想倾向应当从情节和场面的客观描写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切忌把它直接说出来;如果作者老是对人物事件评头论足,这样的小说读起来还有什么玩味的余地?清末民初,著名学者黄人就说:“小说之描写人物,当如镜中取影,妍媸好丑,令观者自知,最忌搀入作者论断。或如戏剧中一脚色出场,横加一段定场白,预言某某若何之善,某某若何之劣,而其人之实事,未必尽肖其言;即先后绝不矛盾,已觉叠床架屋,毫无余味。故小说虽小道,亦不容着一我之见。”(18) 就阅读而言,谁又能说不是这样?如果了解“说书体”小说中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受民间说书的影响所致,我们也就无须苛求古人了。
早在宋元时期,评人论事就已构成“说话”的一大特色。所谓“以上古隐奥之文章,为今日分明之议论”,“讲论只凭三寸舌,称评天下浅和深”(19) 等等,都意在强调“评论”是“说话”的基本要求。后代的评书、评话更然如此。张次溪曾说:“评者,论也。以古事而今说,再加以评论,谓之评书。”(20) 艺谚还说:“有书无评,说书无能”(21);“评话,评话,先评理,后说话。”(22) 为什么“评论”对于民间说书如此重要?这得从说书的实际需要说起。书场说书面对的往往是文化程度不高、理解能力有限的下层民众,如果像文人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那样,喜欢采用“春秋笔法”,势必会造成听众理解上的困惑;再者,书场听书这种接受形式,也使听众没有时间停下来细细揣摩掩藏在人物言行和故事情节背后的“微言大义”;第三,说书人在演出时也需要与听众当场交流思想感情,有了这种交流互动,才容易感染听众,与听众共同去创造一种特定的思想艺术情境。因此,说书人总是不停地插话、议论,解释听众可能产生的各种疑惑,揭示人物言行、事件本身隐含的思想意义,其爱憎褒贬、情感态度等总是那么明朗、公开,决不暧昧、含混。那种为高水平文人所激赏的“不加褒贬,其义自见”的“春秋笔法”对于书场演说,其实是不适用的。如此一来,得到过民间说书孕育的“说书体”小说,就难免议论风生了。退一步说,即使不是直接源自民间说书的通俗小说,只要其作者将读者定位于下层民众,为了让读者明白小说的含义,他也不得不没完没了地议论、说教,如凌濛初编创的“二拍”即是如此。
除了上述所言之外,“说书体”小说中还有一些现象,如“时空倒错”,也可以联系说书作出较有说服力的解释。如《春秋列国志传》里居然出现了律诗、绝句。宋元话本《风月瑞仙亭》写司马相如月下见到卓文君后,兴奋异常地掉起书袋子:“小生闻小姐之名久矣,自愧缘悭分浅,不能一见!恨无磨勒盗红绡之方,每起韩寿偷香窃玉之意。今晚既蒙光临,小生不及远接,恕罪,恕罪!”这段话中所引“磨勒盗红绡”、“韩寿偷香”,分别说的是发生在唐代、晋代的爱情故事,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人,他如何未卜先知几百年以后的事情?笔者曾据此嘲笑编创者无知,后来研究民间说书,这才知道,这种“时空倒错”现象在民间说书中司空见惯,因为说书人为了便于听众理解历史上的事物,有时难免古事而今说,比如清末说书人如果面对河南、河北听众演说《水浒》中雷横到勾栏去听白秀英唱“诸宫调”一节,当地听众可能多数不知道什么叫“诸宫调”,说书人解释起来也费劲,这时他如果说雷横去听白秀英唱“梆子戏”,那么听众就很熟习,也容易感到亲切了。因此,考虑到民间说书的特点,我们也就无须对“说书体”小说中的“时空倒错”现象大惊小怪了。
以上是笔者从民间说书的特点和规律出发,对“说书体”小说中一些突出的现象和特点所作的初步思考,虽然还不成熟,但是对于改变以往就小说论小说的传统思路,确切地认识、评价通俗小说的艺术特征,也许是不无启发的。
注释:
①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老舍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②⑤连阔如:《江湖丛谈》,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年版,第261页,第244—245页。
③④姜昆、戴宏森主编《中国曲艺概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7—178页,第176页。
⑥⑧金受申:《老书馆见闻琐记》,载《曲艺》1959年第9期,第11期。
⑦耿瑛:《生搬硬套与死书复活》,《书林内外集》,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45页。
⑨(15)[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故事的歌手》,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51页,第40—50页。
⑩闻国新:《北平的说书》,载《太白》(半月刊),1934年12月20日。
(11)[美]蒲安迪:《〈金瓶梅〉非“集体创作”》,载《金瓶梅研究》第二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12)侯忠义、王健椿:《近代侠义、公案小说“合流”说质疑》,载《明清小说研究》2006年第4期。
(13)(22)参见《中国曲艺志·谚语、口诀、行话》(江苏卷),中国ISBN中心1996年版,第639页。
(14)汪景寿、王决、曾惠杰:《中国评书艺术论》,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第155页。
(16)罗尔纲:《从罗贯中〈三遂平妖传〉看〈水浒传〉著者和原本问题》,载《学术月刊》1984年第10期。
(17)方胜在《〈西游记〉〈封神演义〉因袭说证实》(《光明日报》1985年8月27日)一文中以两书中相同的五首赞词为例,分析指出《封神演义》抄袭了《西游记》;徐朔方在《再论〈水浒〉和〈金瓶梅〉不是个人创作》(载《徐州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一文中又多举出了十五首相同的赞词,分析指出方胜的观点失之于片面,实际上“它们之间是双向的彼此影响”。对此,方胜又撰文《再论〈封神演义〉因袭〈西游记〉》(载《徐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4期)反驳说:“从《西游记》和《封神演义》的这些赞词来看,是《封神演义》因袭了《西游记》,《西游记》是原作,它们之间,至少在赞词方面,不存在‘双向的彼此影响’”。
(18)黄人:《小说小话》,见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38页。
(19)罗烨:《醉翁谈录》,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20)张次溪:《天桥丛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2页。
(21)参见《中国曲艺志·谚语口诀、行话术语》(北京卷),中国ISBN中心1999年版,第598页。
标签:小说论文; 评书演员论文; 文学论文; 三国论文; 文化论文; 三侠五义论文; 读书论文; 封神演义论文; 说岳全传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