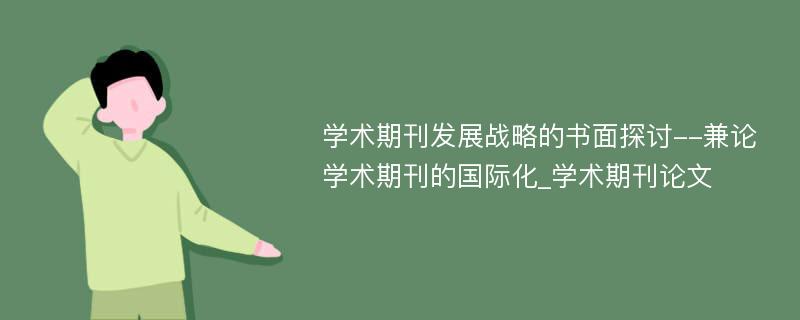
“学术期刊发展战略”笔谈——也谈学术期刊国际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期刊论文,笔谈论文,发展战略论文,也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光明日报》2004年3月1日发表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鱼类基因工程专家朱作言的文章《学术期刊国际化》,一些网站很快予以转载。文章指出:“通常情况下,一个国家能办出有国际影响的学术期刊,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反映了这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其影响可能比一个重点实验室的影响还要大。如果我国仅有很好的实验室和科学研究,却没有相应有影响的期刊,那是不全面的,也是令人遗憾的”。朱文说的是自然科学期刊,同样对社会科学期刊也是适用的。如果要讲21世纪中国社科期刊的发展战略,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办出若干份在国际学术界有影响的期刊,亦即中国社科期刊的国际化。中国的社科期刊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国际地位的重要表征。
其实,我们并不是今天才提出这个问题的。2001年,《历史研究》前任主编张亦工先生到香港参加学术会议,期间,与香港一所大学历史系师生座谈,表示欢迎他们投稿,得到的回答是:如果我们的文章达到一定水准,首选将是英语期刊,原因很简单,这对晋级升等有利。这次座谈会给张亦工先生留下太深的印象,或者说相当大的刺激;尽管这些对他及编辑部同事们来说并不是新闻,但毕竟是亲见亲闻,毕竟是在我们中国的学校(虽说是一国两制)。我个人也有类似的经历。一位留美大陆学者曾投稿本刊,我们经过审稿程序后准备刊用,后来由于一家美国刊物决定刊用,她便将稿件撤回,原因也是相同的:在国内发表文章,晋级时不算数。我们国内一些大学有明文规定,在外文期刊发表文章可以得最高分;而国外学者在中国的学术期刊发表文章,即使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即使我们的所谓权威刊物,也不能作为晋级的重要成果。这就是我们社科期刊今天的“国际地位”。这种地位虽然有几分尴尬,却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自那次香港会议后,张亦工先生多次提出,把提升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作为今后《历史研究》办刊的主要任务。
实现社科期刊的国际化,需要在两个方面努力,一个是刊物的学术水平,一个是刊物的学术规范。提高刊物的学术水平,有待于整个学术界的共同努力,没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也就无从谈起。但我们作为期刊编辑,应该有自觉意识,不能仅仅跟在学者的后面,甚至跟不上学术的发展,把不准学术发展的脉搏。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会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关注国际学术界的前沿问题,热点问题,了解学术理论的发展变化,参与国际学术讨论,不应自我边缘化;但国际化并非西方化,不能简单照搬,自觉不自觉地使中国学术“他者化”。任何一个西方的理论模式和解释框架,它所生发的环境是西方的,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是西方的,它的话语系统也是西方,复制到中国来,必然有水土不服之处。在这方面我们有太多的经验教训,无需赘述。关于这个问题,纽约大学张旭东教授曾指出:中国学术“国际化”的一个良性指标,是看能否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对西方理论产生冲击,并对“普遍性”的概念体系提出修正,中国学术如果没有一种超出中国范围的相关性,对世界范围的学者的思考有所启发,就谈不上什么国际化。这个良性指标对社科期刊也是适用的。这里我想强调的是,我们不应仅仅以西方学者的问题意识作为自己的问题意识,但我们应该清楚他们的问题意识所在;我们更不应简单以西方的话语为自己的话语,但我们应该明白他们的话语所指是什么;否则,在我们与国际学界主流对话时,就会难以把握彼此对话的基准点,也就失去了对话的意义。
关于学术规范问题,这些年来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文章,从不同角度阐释各自的看法,最近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杨玉圣等主编的《学术规范读本》,其姊妹篇《学术规范导论》也即将面世。我没有什么新见解,这里只想根据我们的办刊实践谈三个问题。一个是专家匿名审稿制。香港一所大学有一份中文学术期刊“排行榜”,我记得历史学科方面,第一序列是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等刊物,《历史研究》在第二序列,原因之一就是内地的刊物没有实行专家匿名审稿。现在海外及台湾学者在我们刊物发表文章,也常常要求我们开具一纸证明,证明他的文章是通过专家审稿后才发表的。《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实行专家审稿已有十多年的时间,最初是实名的,现在是双向匿名,而且所有投寄本刊的文章,都在总编室登记时经过技术处理,发到各编辑室时,已经没有任何与作者身份有关的讯息,也就是说对编辑也实行匿名审稿。实行专家匿名评审,不仅仅是为了与国际惯例接轨,这也是学术发展使然。就历史学而言,几乎人人可以发言的公共话题和宏大叙事越来越少,学术分工越来越细,学者的研究日益具体化、个性化,这就需要我们借助学术界的力量,对稿件的学术价值做出基本准确的判断。几年来匿名审稿制的实行,使编辑部获益匪浅,也深受广大作者的欢迎。当然,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在实行匿名审稿时,也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如经费问题,如时间问题,如专家意见与作者意见严重分歧问题,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发展和完善这一制度。
另一个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综述问题。这本身是撰写学术论文的一个规范问题,而如何综述又是一个规范问题。我们刊物发表的论文多数有这方面的内容,但并不是都做得很好。相当一部分作者是这样叙述的:关于这个问题,迄今未见系统研究,却没有说明相关问题的研究究竟已经有哪些进展,你的研究的贡献究竟在哪里。综述已有研究成果,即是对前人研究的尊重,更是为了避免学术研究的低水平重复,作者自己首先要明确,也要使读者知道,你是“接着讲”,还是“照着讲”;你是从哪里“接着讲”。这方面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往往忽略(或有意回避)国外学者和台湾学者的研究。关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可能是更高的要求,但却是必须提出来的。否则,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及社会科学期刊的国际化不过是一句口号而已。
还有一个是引用他人成果必须注明的问题。学术界的几次“打假”风波,使抄袭现象有某种程度的收敛。目前还存在着人使用第二手材料不注明而是直接标注原出处的情况,我们刊物几次被网上文章批评均与此有关(尽管有些问题还存在不同意见)。不同学者对史料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学者对同一史料的理解也不是固定化了的。一份史料,引用哪些,从哪里引起,可能直接关涉对历史的解释。因此,我们提倡学者亲自收集资料。但限于条件,完全不用第二手材料也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对世界史学科而言,需要做的就是老老实实地注明出处,这并不减损你的文章的价值。
中国社科期刊的国际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不能奢望短期内达成。上个世纪20年代初,学界巨臂陈垣曾不无感慨地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也大声疾呼:“我们要使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表明了那一代学人要在国际学术界争胜之心。八十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进入了新的世纪,我们今天是否可以坦然宣告“科学的东方学正统”在中国呢?
我们这代社会科学学者和期刊编辑,应该共同努力,为提升中国社科期刊的整体水平,为缩短中国社科期刊与国际一流期刊的距离,脚踏实地,从一点一滴做起,做出我们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