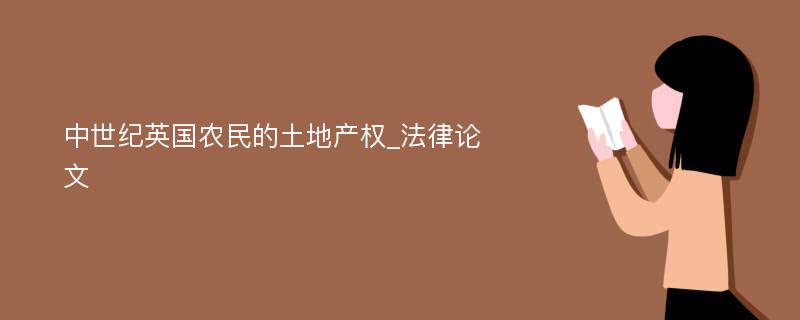
中世纪英格兰农民的土地产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格兰论文,中世纪论文,产权论文,土地论文,农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世纪英格兰的土地所有权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概念,人与土地的关系既不存在现代形式的所有权,也不存在古代罗马那种所有权。在欧洲封建制度下,土地的归属没有唯一性和绝对性。土地上往往涵盖着多人的财产权利关系,没有严格意义的所有权,而是称为保有权(tenure),土地称为保有地。所谓保有权,指某人因承担封建义务而持有土地的权利。社会上层的公爵、伯爵到骑士持有的采邑,社会基层的各种佃农持有的保有地,均是如此。因保有土地的权利而衍生出土地的持有和占有(hold)权,随着经济的发展、权力和权利的博弈,生产者对土地的占有权逐渐凝固,从而产生了seisin(法定占有)这一概念,借以描述不断强化的土地占有权。
英国率先确立了现代产权制度,因此,关于英国农业、农民和土地产权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厚,大致可分为三部分:其一,农民土地产权与社会过渡问题联系在一起,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三次大讨论中,许多著述都较深地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①如美国学者斯威齐、布伦纳,②英国学者波斯坦、哈彻、希尔顿,③法国学者布瓦、拉杜里等。④他们的视角不同,观点各异,但对于农民的土地产权与近代社会转型的内在关系均给予高度重视。其二,从经济—社会史角度研究农民的土地产权问题,如托尼、科斯敏斯基、克里奇、戴尔、坎贝尔、琼·瑟斯克、霍斯金斯、乔伊斯·扬和斯科菲尔德等。⑤他们密切关注日常经济生活、社会生活与农民土地产权的互动关系,对土地财产的继承和流动也给予了相当关注。其三,从法学和政治传统角度研究农民的土地问题,如伯尔曼、波洛克、霍兹沃斯、迪戈比、艾德金、辛普森、塔特等。⑥他们认为中世纪土地产权与欧洲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既不同于古典罗马的所有权,也不同于现代所有权,而是特定意义上的土地依法占有,农民土地产权的演变与其政治法律地位密切相关。近年来,国内学界也有一批研究成果。⑦不过,就英格兰农民的土地产权而言,尚缺乏专门性、综合性和长时段的探讨,尤其从法律与经济社会的相互联系来看,更存在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一、中世纪的“占有权”概念
中世纪英格兰农民的土地产权不是孤立的,不仅涉及经济领域、政治和法律关系,而且是整个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须从英格兰的封建制度及其财产权利体系谈起,有时则需要涉及欧洲大陆。
领主附庸关系是欧洲封建制的核心内容,与封建财产关系密切相连。何谓领主附庸关系的基本特征呢?由于公权涣散、软弱,社会秩序几乎荡然无存,为了获得安全,人们纷纷投靠在强者麾下,结成相互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附庸获得安全(往往同时获得封地),领主获得兵役或劳役,当然也获得人身的统治权和政治权力。一些学者认为其中包含了一定的契约关系,因为这种关系排除了血缘关系,是相互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且约束也是双向的。“由于行了臣服礼而封臣对封君有多少忠诚,则同样封君对封臣也有多少忠诚”,如果对方没有履行义务,封君可以宣布封臣不再是其封臣,封臣同样可以宣布封君不再是其封君。⑧显然,这样的臣服关系是有一定条件的,领主不能为所欲为。布洛赫指出:“附庸的臣服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契约,而且是双向契约。如果领主不履行诺言,他便丧失其享有的权利。”⑨9世纪,欧洲封建制一经确立,即有文献资料表明,人们普遍认为附庸拥有离弃恶劣领主的权利。⑩附庸背叛失信的领主是道德的、合法的,这就是欧洲“抵抗权”的起点。伯尔曼说:“附庸或领主基于足够严重的刺激因素而解除效忠或忠诚契约,这不仅从理论的观点看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在特殊情况下也具有实质性的实际重要性。如果一方违背其义务并由此给另一方造成严重损害,那么另一方就有权通过一种称之为diffidatio(‘撤回忠诚’)的庄严的蔑视性表示解除相互关系……撤回忠诚是从11世纪开始的西方封建关系的法律特性的一个关键。”(11)因此,不难发现国王与某贵族因地权、地界问题产生争议而对簿公堂的情况。比如,1233年,国王亨利三世指责伯爵理查德·马歇尔侵犯了王室领地,伯爵则宣称自己不是侵犯者,因为国王首先侵犯了他的土地。伯爵宣称,由于国王违约在先,根据相互的权利与义务原则,效忠关系自动解除,伯爵不再有效忠国王的义务,“为了国王的荣誉,如果我屈从于国王意志而违背了理性,那我将对国王和正义犯下更严重的错误。我也将为人们树立一个坏的榜样:为了国王的罪恶而抛弃法律和正义。”(12)这个例证表明,国王不能支配王国的每一个庄园,在中世纪人的观念中,附庸的服从和义务不是无条件的,如果受到国王不公正的对待,附庸有抵抗和报复的权利。
领主和附庸是不平等的,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同时存在双向的制约性,任何一方违背约定,另一方可以“撤回忠诚”。附庸的权利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完全依赖领主的善恶喜怒而变动,因此是有一定保障的。有关抵抗权的观念与实践存在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高贵者和低贱者的共识中,存在于原始的个人权利中,显然是欧洲封建制的重要特征。
在欧洲封君—封臣关系的语境下,附庸对采邑稳定的占有权就容易理解。起初,分封采邑与军事义务联系在一起,所授采邑及身而止,有效期以附庸在世为限。随着时间的推移,附加在土地上的占有权相对凝固起来,而且附庸的义务折算为货币支付,不再是从前那种人身服役的方式,采邑的管理也越来越远离领主的监督,这些都促进了附庸经济自主性的增大。早在加洛林时期就已显现出一种趋势,即封君对采邑的权力越来越小,土地一旦被封授,封君则很难支配或收回。布洛赫说:
在一个许多人既是委身之人又是领主的社会里,人们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事实,即,如果这些人中的一个人以附庸身份为自己争得某种利益,作为领主时他可以拒绝将这种利益给予那些以同样的依附形式依附于他的人。从旧的加洛林法规到英格兰自由的古典基石《大宪章》,这种权力平等观从社会上层顺利地传布到社会下层,它将始终是封建习俗的最肥沃的资源之一。(13)
采邑的继承权经历了极不稳定的发展,大约11世纪中叶才逐渐确定下来,真正成为法律。1037年,《米兰敕令》确立的原则是:任何领地,无论主教、修道院院长、侯爵、伯爵还是其他任何人的领地,都不得被剥夺,除非他被法庭认定有罪,而且须经由同级领主集体做出裁决。倘若附庸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而失去领地,可向王国最高法庭上诉。1066年采邑传入英格兰时,已经普遍认为可以传给继承人,“采邑”一词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世袭地产。
一旦采邑可以世袭,地产转移也就不远了。最初的让渡是部分出让,义务仍由原附庸承担。当采邑全部转让之时,义务不得不由新的租佃人承担,这与附庸制原则产生了尖锐矛盾。附庸制本是两个人面对面的约定,相互忠诚,一旦附庸变成一个陌生人,附庸制何以为继?怎能期望从一个不认识的人那里得到这种忠诚呢?(14)土地可以转让,“忠诚”如何转让?唯一的办法是领主先收回采邑,与新的租佃人确认效忠关系后,重新授地给新人。事实上,新的封地仪式往往沦为纯粹的过场。与其说领主重新封授土地,不如说只是采邑转让手续的一环。事实上,采邑可以世袭,也可以出售。
综观英格兰封建地产的发展,可以看到大地产日渐衰落,中、小地产不断加强,地产的转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在1086年《末日审判书》里,最大的庄园之一是柯拉普哈姆,占地面积达30犁(约合3600英亩),到13世纪末已分裂为5个庄园。艾克莱顿庄园到1279年则已分裂为10个庄园。剑桥郡的60个地产中,王室领地本来占16%,但1279年已几乎全归一般封建主掌握。(15)15世纪中期,王室仅拥有5%的土地,(16)已无土地封授,市场流通成为采邑转移的主渠道。
采邑本属于封君,但受封并占有采邑的封臣似乎成了真正主人,附庸对采邑的“占有”何以如此稳定?它在欧洲封建财产关系中意味着什么?如何理解中世纪的所有权和占有权?这些问题都需要明确的回答。
在古典罗马法中,possessio表示占有权,proprietas表示所有权,二者泾渭分明。一个人享有所有权,他就享受占有、使用和处分的全权,占有权不能脱离所有权而独立存在。在欧洲封建制度下,由于附庸的权利是相对独立的,于是附加在土地上的占有权也积淀并固化起来。在封建土地保有制中,每一块土地都包含着封建等级上级和下级的权利,甚至受到两种以上权利的限制,因此,保有地具有可分的利益,而不存在绝对的、不可分割的所有权。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臣民权利的稳定增长,财产重心出现向实际占有者转移的趋势。一个人实际占有的土地或享有的权利,不能由暴力剥夺,甚至不能由合法的所有者剥夺,只要这个人按照约定履行了义务。在这里,占有的概念扩展了。英格兰及西欧为此找到了一个新名词,即seisin(法定占有)。梅特兰说,在中世纪,“再没有任何其他比占有(seisin)概念更为重要的了……它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几乎可以说,英格兰整个土地法就是关于土地的占有及其结果的法律”。(17)
乔舒亚·C.塔特认为中世纪法学家不会不懂得如何区分所有权和占有权。12世纪晚期,学习罗马法的学生几乎肯定会被告知“所有权”(proprietas)和“占有权”(possessio)的区别。不过,在英王室法庭的早期记录中,更为常见的是另外两个词条:ius和seisina,即权利和法定占有(seisin)。事实上,土地权利的拉丁语seisina,不同于罗马法中的“占有权”,也不同于“所有权”。12世纪80年代,在教会法学家的《训导集》中,出现了所有权诉讼与占有权诉讼的明显区别。盎格鲁—诺曼教会学校的理查德乌斯(Ricardus)写作的《秩序》(Ordo)一书,也将所有权和占有权区分开来。不过它们都是将占有权诉讼置于显著位置。(18)法庭案例和教皇教令也表明,当争议发生时,占有权诉讼应在所有权诉讼之前。教职之争亦如此。1161年,一个名叫阿兰的人试图通过法庭恢复被夺走的教职。西奥博尔德大主教致信教皇说,阿兰最先提起占有权诉讼,遇阻后转向所有权请求,并在法庭提供了证据。该案例表明占有权诉讼在先。又如,西奥博尔德任坎特伯雷大主教期间(1139—1161),其辖区某庄园一个叫彼得的人要求恢复曾占有的土地,声称其父即占有这些土地,不过因不能提供相关证据而败诉。法庭告知彼得,他可以继续就所有权进行起诉。这两个案件都明显区分了所有权和占有权诉求,并显示诉讼须从占有权开始,恢复占有权是进行所有权之诉的前提条件。很明显,占有权诉讼被认为是独立的,与所有权似乎没有必然联系。(19)
在教会法中,占有权的概念首先独立出来,继而被置于优先地位。比如,主教或修道院长的位置时常发生纠纷,倘若一方用武力强行驱逐当下的占有者,教会法的原则是,在确定谁是最合法的权利主张者之前,先确保前占有者恢复原来的位置。12世纪中期,格拉提安提出“归还原则”(cannon redintegranda),他宣布任何人都有权恢复他被掠夺的任何东西,不论是土地、财物还是权利,也不论这种掠夺是通过武力还是通过欺诈进行的。“是否对被掠夺者一律恢复占有?”他的回答是肯定的。后来的注释者把“归还原则”不仅认作确认性的保护,而且也适用于独立的诉讼程序,即“夺回诉讼”(actio spolii)。(20)教会法的这套程序适用于教会人员,事实上也深刻影响了世俗法律。梅特兰认为教会法的“侵夺之讼”启发了英格兰的“新近侵占之诉”,因为两个程序均保护占有者的财产,反对另一方掠夺,不论他是谁。即是说,他们发展出完全不依赖所有权的侵夺之诉,在这种诉讼中,被告的所有权不能成为抗诉的理由。(21)
世俗普通法强调和保护“占有权”的第一个令状是权利令状(The writ of right)。这是亨利二世早期发出的法律令状之一,收录在1187—1189年的《格兰维尔》(Glanvill)一书中。令状的原则相当明确:甲持有领主的一块土地,如果该土地被乙夺走,令状要求领主“迅速做出正确裁决”,将被夺走的土地归还甲。令状警告道,如果领主没有这么做,那么郡长将“不再接受进一步的有关权利违约的控诉”。同时原告还可以通过移卷令状(writ of pone)上交王室法院。该令状的含义是,倘若领主不公正地对待失去土地的佃户,国王有权进行干预。“权利令状”的冗繁,很可能促使了新近侵占诉讼令(the assize of novel disseisin)的出台,它是英王亨利二世最重要的司法改革。与权利令状不同,它将诉讼提交给郡长而不是原告的领主。有关该文书形式的最早证据也来自《格兰维尔》。在诉讼令中,国王告知郡长:某甲抱怨某乙“在我上次去诺曼底旅行期间,不公正地、未经法律程序剥夺了我在某村自由持有的地产。”国王命令郡长先将夺走的土地以及相关动产复归原位,然后查证:“12个自由守法的邻居”,即陪审员将查验现场,并将查验结果当面禀告国王或国王的法官。最后进行审判,可缺席审判,即使被告不出庭,审判也照常进行。(22)有学者认为,新近侵占诉讼令是亨利二世“多次彻夜”思考的结果,更多学者则认为是关于土地占有法律的逻辑延伸。无论如何,这套解决纠纷机制的创立,对英格兰乃至欧洲的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土地财产关系的调整和向法律普遍性的发展都迈出了重要一步。
就土地财产关系问题,罗马法和教会法是否影响了欧洲早期的普通法?对此可以做出肯定回答,但要做出限定和说明。欧洲没有移植罗马的所有权法律体系,虽然对“所有权”概念并不陌生,但长时期予以淡化和改造,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形成了独特的土地产权体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欧洲法律与罗马法没有联系,显然有失偏颇。如果认为欧洲法律是罗马法的移植或延伸,同样不符合实际。历史事实是,英格兰及西欧大陆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需要,建构起一个新的法律政治体系,其中不乏从古典罗马法中吸纳一些概念和方法。笔者更倾向于密尔松的意见,他认为,必须在封君—封臣关系的语境下来理解占有(seisin)和权利(right)等法律概念,而不能简单地与罗马法的一些概念进行对接和对译,或看作罗马法相关概念的同义词。(23)即是说,应该充分认识中世纪欧洲财产体系的独创性。
梅特兰也多次谈到欧洲土地所有权被领主和附庸分割甚至多次分割的情况:“土地的完全所有权在A和B之间分割;封臣可能再次封授自己持有的部分土地,于是土地所有权在A、B和 C之间分割,C持有B的土地,B持有A的土地,如此循环往复。”(24)随着层层封授,在同一块土地上便产生了多个保有关系。例如:
爱德华一世时期,罗杰持有罗伯特在亨廷顿郡的土地,罗伯特持有理查德的土地,理查德持有阿兰的土地,阿兰持有威廉的土地,威廉持有吉尔伯特的土地,吉尔伯特持有戴沃吉尔的土地,戴沃吉尔持有苏格兰国王的土地,苏格兰国王持有英格兰国王的土地。(25)
一块土地涵盖的权益关系,竟达9人之多!梅因谈到类似情况时,把领主的土地权利称为高级所有权,附庸的土地权利是低级所有权。(26)然而,当附庸可以继承采邑、自由转移采邑之时,其土地权利还能被视为“低级所有权”吗?伯尔曼索性排拒了罗马法的所有权概念,或者说更重视、更倾向一种独立于所有权的特定占有权。他认为,封建制下的土地权利在各个方面通常都是有限的、可分的、共同的,“事实上,土地不为任何人‘所有’;它只是在阶梯形的‘占有权’结构中为由下至上直到国王或其他最高领主的上级所‘持有’。”(27)
不过,混合所有权并非欧洲独有的历史现象。封建等级中的契约性、附庸权利的独立性、抵抗的合法性,才是其土地关系最重要的特征。伯尔曼指出:“西方封建财产产权体系,在其有关各种对抗权利的相互关系的概念上,却是独一无二的”。一个人可以在某块土地上享有有效对抗领主的一定权利,以及对抗领主的领主乃至国王的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臣民权利稳定增长,财产重心出现向实际占有者转移,即经济自主的趋势。一个“实际占有”土地的封臣对任何“侵占”其土地的人甚至其领主,都享有一种诉权。随着附庸法律自主性的发展,“实际占有权”逐渐突出,seisin即依法占有、实际占有,独立于所有权,优先于所有权,最后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无限接近所有权,到近代最终与资本主义私人所有权接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实际占有权”这一概念流传到整个欧洲,对西方法律理念和法律制度,以及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如同1166年“新侵占之诉”一样,“在西欧每一个国家的法律中都有与此相类似的制度”。由此,封臣可以免受封君的强行侵夺。同样,佃户可以免受领主的强行侵夺。(28)
二、佃农地权的安全性
在欧洲封建制度下,附庸享有独立的采邑占有权,佃户对保有地同样具有稳定的占有权。封建法规定了封君与封臣的关系,庄园法则规定领主与佃农的关系。这两种法律体系紧密相连,具有同构性。梅特兰说:“封建主义在社会底层运行与在上层的运行一样。当武装的封臣围绕在国王身边的时候,底层人物也将自己分别置于各类领主的保护之下,他们耕种领主的土地,而领主则进行必要的战斗。”(29)有学者认为,直接生产者对土地的保有往往比贵族封臣对采邑的保有更为稳定,王权与贵族的政治斗争形成了对农民有利的态势。(30)佃户对所耕种的土地通常可以继承,并无限期占有,也有固定期限的土地占有,有的长达三代,有的只限于一代,甚至以若干年为期。(31)同时,存在身份性的差异,即人身依附性较强的维兰(Villaein)与相对自由的佃户之间的差异。无论哪一类佃户,都存在土地权利问题。哈德森指出,在佃户与领主的关系中,土地权的安全性、继承性、可转让性反映了土地保有人的顾虑:他希望确保土地持有的安全,在他死后,其家人能够继续享有土地权利,或者有权将土地赠送、出售给某个教堂和个人。三要素密切联系,是同一问题的不同侧面,(32)其中地权的安全性无疑居于核心地位。
曾有学者认为,维兰(33)的保有地来自领主,按照领主的意志而保有土地,领主可以随意处置。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事实上,维兰拥有家庭和财产,大部分维兰的土地权利是有保障的,既安全又稳定,即使在农奴制最残酷时期也是如此。土地的稳定占有不仅是他个人经济独立发展的基础,也是个人权利发展的基础。到11世纪和12世纪,庄园制流行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庄园法形成了法律体系,农奴制的法律概念第一次得到系统阐述。农奴被称为“束缚于土地上的人”(glebae abscriptae),这意味着,除非根据某些条件,他不能离开土地,同时也意味着,除非根据某些条件,不能将他们驱逐出去。佩里·安德森指出,当时,“束缚于土地上的人”这一术语表明,此前几个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关系在法律上得到了确认,而且是一种非常“滞后”的确认。(34)只要他们履行了相应义务,不过分对抗领主,其土地权利就是安全的。
如果佃户拒服劳役,领主可以扣押乃至剥夺佃户的土地,但必须依据法律,在法庭上履行一系列法律程序。正如《格兰维尔》所说:“如果佃户对领主不忠诚,领主可审判佃户并扣押土地,但要按照法律,通过法庭判决进行。”(35)当然,佃户的劳役和负担都受到法律限定,很难随意认定。尤其是进入13世纪之后,成文法出现,企图任意改变惯例的领主们会发现自己陷入漫长的司法博弈,对手往往不是一个佃农,而是组织严密的乡村共同体。(36)
如果发生争议,包括发生土地纠纷,领主不能独断专行,而是起诉至法庭。法庭对领主指控的事实进行调查,并依法进行裁决。裁决者是庄园全体成员,上至领主和管家,下至农奴,他们都被称为“诉讼参加人”(suitors),对判决具有决定性影响。后来,裁决者演变为陪审团,由那些与被告地位相当的人组成。陪审团是事实上的法官,领主或管家仅是庄园法庭的主持人。或许有人认为,领主及其代理人的权力可能会对法庭判决产生影响。这种推论虽有一定道理,但实际情况不完全如此,许多判决并不保护领主的利益。例如,在一次诉讼中,庄园主试图剥夺一个农奴的某块地产,理由是该农奴的持有地超过了限额。该农奴却争辩说,其他佃户也有类似的情况,“此前一直持有几块地产,而无需特许状,也未受罚和受指控”,他“准备通过佃户(即庄园的全体佃户)和其他必要的方法证明这一点”。这个案件记录的结果是:“将这个问题搁置起来,直到达成更充分的协商等。”(37)该案件和许多类似的案件都表明,如果发生争议,领主不能直接处置农奴的土地,换言之,不能随意驱逐佃户,必须经过法庭;而法庭不一定做出有利于领主的裁决,一些情况下是抵制领主而援助佃户。
领主剥夺土地多以佃户拒服劳役为口实,即使法庭查实并下达剥夺维兰土地的判决,与实际收回还有很远的路程。在越来越严格的法律程序中,要经过三个阶段:下传票提出警告;扣押动产;扣押、查封土地以至没收土地。没收之前必须举行法庭听证会,被告佃户可以当场辩解,而原告在达到基本目的后也往往乐于表明他是一位好领主。(38)其实,不仅听证会,三个步骤中的每个环节,都为妥协提供了机会。领主起诉佃户,以扣押土地相威胁,目的在于使其就范,按约服役。领主深知没收土地是一件很例外的事情。佃户也不认为会轻易失去土地,土地已属他,是安全的,这种自信随占有时间的持续而益增。哈德森总结道:“我们极少看到采邑内部发生过这种佃户失去土地的实例,这不仅仅是由于史料证据有限,也可能反映出当时确实很少实际发生佃户失去土地的情况。”(39)哈姆斯也指出,“事实上,大部分维兰很大程度上享有土地安全,即使是在13世纪也是如此。”(40)
与农奴相比,自由佃户的土地更加安全,不仅受到庄园法庭的保护,还有王室法院的干预。当自由佃户认为庄园法庭判决不公正,可以越过庄园法庭向王室法院申诉,后者正急于扩大自己的司法管辖权,因此总是设法援助佃户。自12世纪起,英格兰王权就介入自由佃户的案件审理。(41)前面提及领主扣押佃户土地前,先要扣押大牲畜一类的动产以示警戒,此时,如果他是一个自由佃户,即可求助王室法院,以期中断领主对他可能造成的侵害。王室法院提出了一种称为“收回非法扣留动产之诉”的简单诉讼程序,根据这种程序,郡法庭可以核准佃户是否没有履行劳役,领主扣押其动产的理由是否成立。否则,郡长有权对领主采取强制措施。(42)
王室法院对自由佃户土地占有权的保护,在早期普通法中,最著名的当属新近侵占之诉等王室令状。该令状是国王发给某郡守,后者代表国王干预强占佃户土地的案件。格兰维尔曾经记述了该令状的一般形式和内容:
国王向郡守问候。命令N.毫无迟疑地归还R.在某村庄1海德的土地。R.向我控告 N.侵占了他的土地:如果他没有归还,则由合适的传召者传唤他,在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在某地点到我或我的法官面前,解释为何没有做到。务必使他和传召者带着此令状一同前来。证明人:兰纳夫·格兰维尔·于克拉伦登。(43)
关于“法定占有”(seisin)的概念,前已有介绍。亨利二世及其法学家根据教会法学家的“归还原则”,发展出新侵占之讼,有利于保护封臣的权益,同样有利于农民的保有地免受领主及他人的强行侵夺。“如果自由持有土地佃户被不公正地侵占和剥夺财产,且未经审判,他便能够通过王室令状寻求救济:召集陪审团;在国王法官面前回答关于保有和侵占问题。继而为原告做出判决,他便能恢复其财产。”(44)诉讼中,原告只需证明先前的占有成立,这样的占有权就不会被改变。佃户对土地长期稳定的占有,强化了佃户的土地权利。另一方面,王权新的法律举措,特别是恢复土地权的法令,对人们的观念和争端的解决,都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12世纪末一位名叫萨姆森的修道院院长承认:他不得不依法处理此事,如果没有法院的判决,他不能对任何自由人保有多年的任何土地和收益予以剥夺,不管自由人的这种保有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如果他果真剥夺了自由人的财产,将会受到王国巡回法院的处罚。(45)
当然,不乏领主侵害佃户土地权益的事件发生,但结果并非都能如愿。1198年,林肯郡某庄园领主与亚历山大庄园领主发生土地产权纠纷,后者不得不把价值100马克的地产切割给了对方。但亚历山大庄园的两个佃户拒绝交出土地,也不给亚历山大交租。亚历山大领主诉诸王室法院,后者也无从置喙,因为佃户坚称土地让渡事先没有与他们协商,所以是无效的。案件前后拖了7年之久,土地仍在两个佃户之手。(46)又如,15世纪中期拉姆齐修道院的希林顿庄园,领主侵占了佃户的土地。佃农将该情况告知了王室复归财产管理员(royal escheator),王室便扣押了该土地,理由是拉姆齐修道院没有申请王室许可并支付相应款项,从而破坏了《没收法》(Statute of Mortmain)。最后,拉姆齐修道院不得不放弃占有该土地。(47)这些案例均表明,农民依法保护自己的持有地免受领主侵占是可行的。
随着农奴制的解体,原来的维兰佃户纷纷进入了王权保护的行列。公簿持有农大多是维兰的后代,其土地是“凭法庭案卷副本而持有”。(48)大约从15世纪中叶起,王室普通法开始受理公簿持有农的诉讼,为他们的土地提供保护,从而确立了他们的法律地位。1467年,大法官法庭开始受理公簿持有地的诉讼。1482年,普通高等民事法庭也开始受理此类案件。(49)1467年,大法官丹比(C.J.Danby)说:如果领主驱逐公簿持有农,他就错了,因为公簿持有农依据庄园惯例持有的土地与普通法意义上的自由持有地没有什么区别。不久,大法官布里安(C.J.Brian)表达了同样观点:“如果公簿持有农按照习惯法履行了义务仍遭领主的驱逐,该佃户可以对领主提起侵权之诉。”(50)现代学者里丹(Mr.Leadam)认为,自那时起,公簿持有农与自由佃农一样,享有完全的法律保障。(51)阿什利(Ashley)认为这样的看法过于乐观,由于习惯法对佃农强有力的保护已然衰落,土地占有并非那么安全。(52)塞维因(Savine)也指出,15世纪大法官法庭对公簿持有农命运的影响不可夸大。大法官法庭受理的诉讼案总数可达好几千件,其中公簿持有农的申诉数量颇为有限。(53)托尼则持折中态度,他认为这两种观点都过于极端,公簿农的法律地位与每个庄园的具体情况相关。(54)各地公簿农受到普通法保护不是一次完成的,而且接受王室法院的审理和保护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过公簿农越来越受到普通法保护这一事实是没有疑义的。时间对公簿持有农有利,如同伯尔曼指出,封建持有地的自主发展方向总是有利于持有者。一个世纪以后,爱德华·柯克敏锐观察到公簿持有农的土地是安全的,他们可以通过大法官法庭或侵害令状(writ of trespass)保护自己。(55)只要履行义务,没有违反惯例,谁也奈何他不得。(56)
这里所说的“安全”,一是人身安全,二是所占有土地的安全,至此,公簿持有农、自由农,都有了法律的保障。即是说,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大多数农民的持有地是安全的,可以自由支配。亨利二世颁布恢复地产制度不久,西欧大部分地区也都先后援引和推行了同样的保护占有权的法律。虽然罗马法的“占有”不同于中世纪的“占有”或“保有”,但欧洲法学家并未为此过于费神,他们只是将罗马法加以转化,为自己所有。这种转化为封臣、农民佃户的土地占有和占有权的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伯尔曼总结说:“欧洲人发展了sensin概念,用以满足未从所有权中取得占有权利的合法占有人的需要。在英格兰、诺曼底、西西里、法兰西和德意志公爵领地以及其他地方,新侵占之讼以某种形式赋予合法占有人并也赋予具有占有权利的人以一种重新占有的权利,以防止对他的不公正侵害。”(57)一直到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佃户合法的土地权利不断得到重申。一份1567年的文件表明,温彻斯特大教堂与158名公簿持有农郑重地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固定地租、固定税费以及可继承的公簿持有权,“从今以后永远被承认并得到尊重”。另外,埃尔斯韦克庄园的佃户就地产性质问题与领主对簿公堂,他们根据法庭记录逐项重申他们对土地的权利。法庭记录表明,法庭再一次给予了确认。(58)
欧洲中世纪的“占有”概念,不仅是对不动产、动产和职位的实际占有或支配;而且是对一种非实体的权利占有和支配。英格兰等西欧国家的法律像教会法一样,既保护对财产的占有,也保护附属于占有的权利。因此,当一个人在离开土地去参加十字军东征或朝圣时,仍然可以保持对土地的实际占有。即是说,当认为某人对其不动产保持占有和管理权时,即使没有实际的占有相伴随,他的占有也是有效的,并且受到保护。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庄园佃户对公用地的使用:对那些荒地、林地和沼泽,他们既没有所有权也没有实际的占有,但是拥有使用的权利,所以佃户可以依规定利用它们,从中获取生活必需品,同样受到法律保护。研究中世纪英格兰及西欧佃户土地产权的观念和实践,有助于人们理解整个中世纪历史及其发展。这个时期并非没有法律和权利,而是法律成长的时代。(59)中世纪晚期,在庄园的惯例土地之外,还出现了新型租佃关系,租佃双方不是根据封建依附关系和庄园惯例,而是基于双方订立的契约。(60)契约签订自由,租期、租金等依市场行情而定,(61)承租者被称为契约佃农或契约农场主,被认为是封建身份特征几乎完全荡尽的一种土地持有形式。庄园内的土地关系在变,以此为基础在庄园之外产生新的土地关系,从此,英格兰走上双轨制发展轨道。
三、佃农地权的继承与流通
法理上,一个典型的维兰是不能自行处置土地的,即无法自由离开土地、出售和出租土地,也不能订立遗嘱和继承土地。如果维兰离世,其土地应归还领主,领主再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分配。然而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极少情况下,领主才会让另一家庭接手份地。维兰的财产不仅可以继承,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自由支配。教会也认为维兰应该像自由人那样留下遗嘱,随个人意愿处置土地。(62)因此,领主通常让原来的佃户家庭继续占有这块土地及附属的权利,佃户则继续承担相应的维兰义务。当然继承人要交纳继承捐和入地费(enter fine)以表效忠,领主则表示承认该继承人继续保有土地。整个过程都要记入庄园法庭案卷,以资查询。
在领主同意授予佃户土地的契约里,总要说明土地将被授予保有人“及其继承人”。“继承人”经常以复数出现,明显意味着不止一代的、没有时间限制的继承关系。(63)当土地保有人去世,只要佃户没有违约行为,领主总是不得不接受其成年继承人的效忠关系,并立即将土地交给他。领主唯一所获就是取得土地继承捐和入地费,如同获得佃户的劳役一样。这再次说明领主的实际控制权如何缩小到有限的经济利益,后者并不与土地的实际价值等值,因为土地本身已在相当大程度上变成了保有人的财产。在佃户的土地继承问题上,领主几乎没有什么选择,除非土地保有人身后没有继承人,或者保有人被判重罪因而不能有继承人。可惜,这种情况极少发生。据《格兰维尔》记载,“成年继承人在其祖上去世后可以立即继承遗产;因为尽管领主可以将地产和继承人都控制在自己手里,领主仍需谨慎行事,以保证不致剥夺继承人对土地的占有。如果需要的话,继承人甚至可以抗拒领主的暴力行动,只要他们愿意向领主支付土地继承捐并履行其他合法的劳役。”(64)很明显,佃农的土地继承权受到法律保护。
按照领主的愿望,继承人应当在佃户最近的血亲中产生。庄园制初期的保有地继承人多是死者的亲属,如子女、孙子女、兄弟或姊妹。最为理想的情况是土地完整地传给一个儿子。(65)领主不情愿接受血缘关系较远或者没有血缘关系的继承人,最初的习惯法也总是支持血亲继承。1293年,纽英顿庄园发生一例案件:一个名叫托马斯的人到庄园法庭诉称,其父母未经他的同意,将他们位于布鲁克汉普敦的半雅得(yard-land)土地永久转让给了外人约翰。原告提出,依照本村庄的继承习惯,作为佃户的儿子,他理应成为该土地的继承人。其父母出庭并坚持否认托马斯的继承权,但法庭仍然将该土地判归原告。(66)该案件表明,家内血亲继承习惯占据上风。
然而情况不尽相同,尤其13世纪中叶以后,家庭土地继承的范围和性质发生了变化,突出表现在选择继承人的问题上,佃户的个人意志得到了越来越明确的彰显。麦克法兰指出,佃农的土地产权更多掌握在佃户而非领主的手里,而且由佃户个人而非其家庭掌握。(67)由于佃户个人的意愿,不乏佃户子女被取消继承权而且得到法律确认的事情。1225年,一个被父母剥夺继承权的佃户后代上诉到王室法院,要求恢复其继承人的权利,但遭到拒绝,可见王室法院支持佃户的个人意志。(68)在一份1444—1558年家内土地转移的统计表中,土地传给儿子仍然是主要走向,但夫妻之间的土地转移也占很大比例,尤其是转向夫妻联合占有的形式(joint tenure)。联合持有土地者享有同等权利,不少庄园惯例规定妻子无权继承丈夫的土地,为保证妻子的权利,丈夫生前常常把土地转为联合保有的形式,这样妻子在丈夫去世之后自动得到土地。(69)菲斯指出,尽管土地在血亲内继承曾是农民社会的共同理念,但到13世纪晚期尤其14、15世纪,这种理念动摇了,淡化了,甚至被抛弃。(70)正如怀特(Jane Whittle)所说,这一时期庄园保有地的继承,大多是佃户根据自己的意志设计,从这个角度讲,的确是个人主义的行为。(71)
结果,持有土地者在世时的非家内土地转移,逐渐成为流行的方式。史密斯汇总了萨福克郡雷德格雷夫庄园1295—1319年发生的土地转让,非家内转移已占半数,有时接近2/3。(72)瑞夫茨研究了亨廷顿郡沃博伊斯1288—1366年的土地转让,在31件土地转让中,父母转让给子女的只占11件,非亲属转让占14件,其余6件情况不明。菲斯研究了伯克郡布赖特沃尔顿1280—1300年的土地转移,家庭内部转移占56%。1267—1371年在温彻斯特的奇尔博尔顿庄园,因土地转移而交付入地费共70笔,其中29笔为家内继承,占41%。(73)戴尔通过分析1375—1540年亨伯里等4个庄园的卷宗,认为佃户生前土地交易的比率逐步提高,以致超过家内继承。(74)简·怀特通过对黑文汉姆教区1274—1558年农民家庭土地转移的统计,同样证明土地在非亲属之间转让的比例越来越高,持有者个人对土地的支配权在逐渐增强。(75)
即使子承父业,也与以往有所不同,契约因素更加明显。父母允许子女继承保有地是有条件的,最有代表性的证据是普遍流行的赡养协议。由于家长年迈不能继续劳作等原因,将土地让予子女,后者负责赡养,并签下协议。1321年,埃塞克斯郡海伊斯特庄园的寡居妇女伊斯特拉达·内诺,将一处宅院和半码地交给了女儿阿格尼丝,双方签订了赡养协议。6年后,母亲将女儿、女婿告上法庭,指控他们没有履行赡养义务。结果,寡母重新收回了土地,与另一个没有亲属关系的佃户签订了新协议。(76)可见,虽然赡养协议是母女之间签订的,但同样受到法律的保障。戴尔认为,持有人“实际上是安排自己的儿子们购买他们的继承权”;当亲属购买时,可能享受一些优惠条件而已。(77)赡养协议及实施情况说明,土地的归属权是明确的,而且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广泛承认。
土地产权的明晰化势必导致土地自由交易,实现土地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英格兰,诺曼征服之后领主竭力限制土地的转让。1215年《大宪章》有专门条款限制土地的出售。(78)13世纪中期之后,随着货币地租流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衰落,法律逐渐默认了自由佃农转让土地的权利。1290年颁布的《土地完全保有法》(Quia Emptores,即《土地买卖法》),未能完全脱去地产封建政治的附加成分,但毕竟承认了自由地产的合法买卖。(79)1259—1300年,萨福克郡某庄园法庭领主的收益中,通过土地市场交易取得的各种罚金占到3/4,(80)见土地市场的活跃程度。
维兰保有地是不能公开买卖的,他们采用变相买卖的方式让渡土地,大多为小块土地转让。莱维特在描述圣奥尔本修道院的法庭案卷时,将有关土地转移的案件放在首要位置,这些交易多是半英亩的小块土地,从1240年起充斥了法庭登记人的账簿。又如,1260—1319年,伍斯特郡里德戈拉夫庄园记载了2756起非家庭继承而转移土地的案例,涉及1304英亩,在庄园的依附性土地中占有很大比例。(81)实际生活中,维兰还经常私下交易,并不经过法庭。例如,圣阿尔本斯修道院长控告比塞,说他的土地属于修道院的土地,比塞辩护说,实际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他买自瓦特莱特,他还知道,瓦特莱特买自韦特,韦特领自布尔敦,布尔敦领自詹姆士,而詹姆士才领自修道院长。(82)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一块土地往往发生一系列的土地交易,都未取得领主同意,而是私下进行的。波斯坦指出:“他们能够购买任何土地而无任何障碍,还可以购买、出卖、抵押和租用家畜,可以取得动产并随意分割。”(83)科斯敏斯基也指出,“庄园法庭虽然谋求控制这些交易,然而相当大一部分土地逃脱了这种控制。”(84)随着货币地租流行和农奴制瓦解,土地更大规模地流入市场。(85)13世纪80、90年代,沃顿庄园的18份契约文献保留了小块土地交易实录,土地购置费分别是10先令、20先令和40先令等,土地交易后不保留任何地租和封建义务。这种土地买卖随着农奴制的瓦解而逐渐发展,反过来讲,土地买卖也使封建义务逐渐融化在货币交易之中。史密斯的研究表明,不同类型土地的价格不一样,表明附属在土地上的产权的差异。如自由继承地产(fee simple)最接近实际的所有权,价格最高,实际是商业性地价。(86)土地出租市场也相当活跃,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土地转租交易的中介人,受雇于那些富裕的公簿持有农。(87)
15、16世纪,土地流通更加普遍。15世纪亨伯里法庭的案卷记载,每次开庭平均有4件土地转移记录,这意味着每年10%的庄园土地要转手。(88)在阿尔希·伯里庄园,1377—1536年,共进行了747起习惯保有地和其他地产的转手。其中,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家庭内部土地转移71次;土地保有人离世后家庭内部继承161起;保有人生前转移土地转手481起;保有人离世后家庭向外部的土地转手34起。(89)显然,中世纪晚期土地转移频率和数量明显增加。1540年《遗嘱法》颁布,公簿持有农——多是昔日的维兰,像自由持有农一样,可根据遗嘱处分其地产,并且得到法律的确认。(90)此时,公簿持有者已占英国全部乡村人口的三分之二或更多。(91)
四、土地产权市场化对封建制的影响
农民直接参与土地市场对中世纪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土地买卖和租赁发生在佃户与佃户之间,也发生在佃户与领主之间。买卖双方系纯粹的经济关系,它的发展破坏和排除了附着在土地上的封建义务,侵蚀着庄园制度。由于土地不断转移,打乱了先前的秩序。许多农民的土地不是取自领主,而是取自其他佃户,后者私自将土地卖给外来人。这些外来人拒绝向领主交租,领主既不能将他们从土地上赶走,也不知道该地产位于何处,有时连确切保有关系都说不清楚。土地丢失的现象屡见于记载。(92)同时,领主的直领地出现分割出租或整体出租的趋势。以麦切伯爵的地产为例:诺福克的伯彻姆庄园和萨福克的克来特庄园直领地14世纪60年代出租了,不到10年,诺福克又有两个庄园出租,其他3个庄园到1400年也先后出租。教会地产亦如此。坎特伯雷大主教在14世纪80—90年代,至少有18个庄园的直领地出租,余下的几块到1450年全部出租。至16世纪,领主直领地几乎完全出租,传统的领主经济不复存在。承租者有商人、骑士,更主要的是上层农民。例如,在威格斯顿,1200—1450年,伦道夫家庭通过市场积累了150英亩土地、两三个农场以及大量资金。1432年一份契约称他为“理查德·伦道夫绅士”,此外,他还是一个杂货商。(93)又如,佃户乔治·理查德森成为佩尔姆斯教区的执事后,开始聚集小块土地。在24年中不断扩大地产,有时一次购进一两英亩,有时购进50英亩以上的整块土地。1528年去世时,他已持有297.5英亩土地。同时,他还在其他领主那里领有小块土地。(94)15世纪在贝德福德郡的希林顿庄园,一位名叫沃德的佃户1406—1450年进行了13次土地交易,积聚起4维尔格特土地和12英亩零散的土地。(95)显然,通过市场,逐渐涌现出具有一定规模的农场。
到15世纪晚期,许多佃户的效忠仅仅是象征性的,实际上的封建义务逐渐消失,自由程度进一步提高。(96)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成为小块土地的主人。土地自由买卖的结果,不是使土地愈益集中到封建领主手中,也不是趋于越来越分散的小农经营,就大多数情况看,是一般农户,尤其是经营不善或获得了更适宜谋生出路的小农,将土地出租或出售给大农,后者一心想通过扩大土地经营面积获得利润。这些在分化中逐渐崭露头角的富裕农民,不仅集中小农土地,而且还是领主直领地的重要承租人。货币地租实行后,原来依靠农奴劳役的领主自营地被迫改为雇工经营,与早已由雇工经营的富裕农民经济成为竞争对手,却又不敌后者。在市场规则下,领主经济穷于应付,大多入不敷出,庄园自营地不断分割和出租,结果进一步加强了这些富裕佃农的实力。正是从他们之中产生了资本主义农场主或租地农场主。随着土地产权的发展,不仅传统的佃农在改变,领主也在改变,领主不断边缘化并退出生产管理领域。同时,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孕育中,农业资本主义生产组织和产权制度呼之欲出。
欧洲封建制下的“保有权”是一个相当丰富的概念,包含着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也包含着权利义务关系、原始契约关系。严格而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里没有唯一的所有权,一块土地上往往涵盖着多种权利。这种混合所有权现象在世界各地并不少见,而各种权利博弈的相互关系才是英国乃至欧洲封建财产体系最重要的特征。佃农对领主甚至对国王的有效抵抗,推动了保有权下对土地的一般“占有”(hold)发展为“依法占有”(seisin)。土地的依法占有权如此行之有效,如此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以至中世纪的司法诉讼中,占有权独立于、优先于所有权,在新的社会条件下逐渐创造出新型产权关系。大约到15世纪晚期,生产者实际的土地权利不可避免地发展起来,尽管其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招牌后面。随着生产力发展,生产规模和资本的社会积聚不断扩大,小块土地所有制也就走到了尽头。
注释:
①R.H.Hilton,“Capitalism:What's in a Name? ” Past and Present,no.1(Feb.1952); M.Dobb,“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 Marxism Today,Sep.1962; J.Merrington,“Town and Country in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New Left Review,no.93(Sep.-Oct.1975).
②P.Sweezy,“A Critique,” Science and Society,Spring 1950; R.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no.70(Feb.1976).另见R.Brenner,“ 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talism,” Past and Present,no.97(Nov.1982).
③M.M.Postan and J.Hatcher,“ Population and Class Relations in Feudal Society,” Past and Present,no.78 (Feb.1978); R.H.Hilton,“ A Crisis of Feudalism,” Past and Present,no.80 (Aug.1978);R.H.Hilton,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The Four Lectures for 1973 and Related Studi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 R.H.Hilton,Bond Men Made Free:Medieval Peasant Movements and the English Rising of 1381,London:Methuen,1973.
④Emmanuel Le Roy Ladurie,“ A Reply to Robert Brenner,” Past and Present,no.79 (May 1978).
⑤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New York:Harper & Row,1967; R.H.Hilton,The English Peasantry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E.A.Kosminsky,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Oxford:Blackwell,1956; E.Kerridge,Agrarian Problems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nd After,London:Allen and Unwin,1969; C.Dyer,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The Estates of the Bishopric of Worcester,680-154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0; Jane Whittle,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1440-1580,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M.Campbell,The English Yeoman under Elizabeth and the Early Stuarts,New York:A.M.Kelley,1968; J.Thirsk,ed.,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IV,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W.G.Hoskins,The Midland Peasants: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a Leicestershire Village,London:Macmillan,1957; P.R.Schofield,Peasant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1200-1500,New York:Palgrave-Macmillan,2003.
⑥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F.Pollock,The Land Laws,third edition,London:Macmillan,1896; W.Holdsworth,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Land Law,Oxford:The Clarendon Press,1927; K.E.Digby,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Real Property:With Original Authorities,second edition,Oxford:Clarendon Press,1876; B.W.Adkin,Copyhold and Other Land Tenures of England,London:Estates Gazette,1911; A.W.B.Simpson,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Oxford:Clarendon Press,1986; Joshua C.Tate,“ Ownership and Possession in the Early Common Law,”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vol.48,no.3(Jul.2006),pp.280-313.
⑦赵文洪:《私人财产权利体系的发展——西方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沈汉:《英国土地制度史》,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年。
⑧R.W.Carlyle and A.J.Carlyle,A History of 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in the West,vol.3,London:W.Blackwood,1928,p.21.
⑨Marc Bloch,Feudal Society:Social Classes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vol.2,London:Routledge,2005,p.172.
⑩H.R.Loyn and John Percival,eds.,The Reign of Charlemagne:Documents on Carolingian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London:Edward Arnold,1975,p.84.
(11)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374页。
(12)Fritz Kern,Kingship and Law in the Middle Ages,New York:Harper & Row,1970,pp.88-89.
(13)参见Marc Bloch,Feudal Society: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vol.1,p.195.
(14)Marc Bloch,Feudal Society:The Growth of Ties of Dependence,vol.1,p.209.
(15)E.A.Kosminsky,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148.
(16)J.P.Cooper,“The Soc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and Men in England,1436-1700,”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New Series,vol.20,no.3 (Dec.1967),pp.419-440.17世纪中叶时,王室竟然拥有2.1%的庄园。Richard William Lachmann,From Manor to Market:Structural Change in England,1536-1640,Thesis (Ph.D.),Harvard University,1983,p.139.
(17)F.Pollock and F.W.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Ⅰ,vol.Ⅱ,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29.
(18)Joshua C.Tate,“Ownership and Possession in the Early Common Law.”
(19)Joshua C.Tate,“Ownership and Possession in the Early Common Law.”
(20)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549页。
(21)Joshua C.Tate,“Ownership and Possession in the Early Common Law.”
(22)Joshua C.Tate,“Ownership and Possession in the Early Common Law.”
(23)S.F.C.Milsom,The Legal Framework of English Feudalism:The Maitland Lectures Given in 1972,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6,pp.39-40.另见Joshua C.Tate,“Ownership and Possession in the Early Common Law.”
(24)F.W.Maitland,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A Course of Lectur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08,p.153.
(25)F.Pollock and F.W.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I,vol.I,p.233.
(26)Alan Macfarlane,“ The Cradle of Capitalism:The Case of England,” in Jean Baechler,John A.Hall and Michael Mann,eds.,Europe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Oxford:Blackwell,1988,p.193; 梅因:《古代法》,沈景一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67页。
(27)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382页。
(28)以上见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381—383、549页。
(29)F.W.Maitland,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A Course of Lectures,p.57.
(30)J.C.Holt,“Politics and Property in Early Medieval England,” Past and Present,no.57(Nov.1972),pp.3-52.
(31)John Hudson,Land,Law and Lordship in Anglo-Norman Engla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94,pp.97-98.
(32)约翰·哈德森:《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时期英格兰的法律与社会》,刘四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06页。
(33)维兰本意是村民villager,封建化后下降为农奴。见A.L.Poole,From Domesday Book to Magna Carta,1087-1216,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1,p.40.
(34)Perry Anderson,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London:NLB,1974,p.147.
(35)John Hudson,Land,Law and Lordship in Anglo-Norman England,p.28.
(36)John Gillingham and Ralph A.Griffiths,Medieval Britain: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p.76.
(37)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398—399页。
(38)John Hudson,Land,Law and Lordship in Anglo-Norman England,p.34.
(39)以上参见约翰·哈德森:《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时期英格兰的法律与社会》,第108页。另见John Hudson,Land,Law and Lordship in Anglo-Norman England,pp.33-34.
(40)Paul R.Hyams,King,Lords,and Peasants in Medieval England:The Common Law of Villeinag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Oxford:Clarendon Press,1980,p.49.
(41)Frank E.Huggett,The Land Question and European Society since 1650,London:Thames and Hudson Ltd.,1975,p.19.
(42)F.Pollock and F.W.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Ⅰ,vol.Ⅱ,pp.577-578.
(43)D.C.Douglas and G.W.Greenaway,eds.,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vol.Ⅱ,London:Routledge,1981,p.496.
(44)F.Pollock and F.W.Maitland,The History of English Law before the Time of Edward Ⅰ,vol.Ⅰ,p.146.
(45)约翰·哈德森:《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时期英格兰的法律与社会》,第205—206页。
(46)Paul R.Hyams,King,Lords,and Peasants in Medieval England:The Common Law of Villeinage in the Twelfth and Thirteenth Centuries,p.9.
(47)P.D.A.Harvy,ed.,The Peasant Land Market in Medieval England,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p.213-215.
(48)A.W.B.Simpson,A History of the Land Law,p.161.
(49)P.D.A.Harvey,ed.,The Peasant Land Market in Medieval England,p.328.
(50)E.Lipson,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vol.1,London:A.&C.Black,1915,p.136; Paul S.Clarkson and Clyde T.Warren,“ Copyhold Tenure and Macbeth,Ⅲ,ii,38,” Modern Language Notes,vol.55,no.7(Nov.1940),pp.483-493.
(51)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289.
(52)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290.
(53)Alexander Savine,“ English Customary Tenure in the Tudor Period,”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9,no.1(Nov.1904),pp.33-80.
(54)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293.
(55)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289.
(56)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291.
(57)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第557、550页,另见第十三章。
(58)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295-296.
(59)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300—1300年)》下册,耿淡如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332页。
(60)B.W.Adkin,Copyhold and Other Land Tenures of England,p.65.
(61)Bas J.P.van Bavel and Phillipp R.Schofield,eds.,The Development of Leasehold in Northwestern Europe,C.1200-1600,Turnhout:Brepols,2008,p.139.
(62)Cicely Howell,Land,Family and Inheritance in Transition:Kibworth Harcourt 1280-1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238.
(63)S.E.Thorne,“English Feudalism and Estates in Land,” The Cambridge Law Journal,vol.17,no.2(Nov.1959),pp.193-209.
(64)转引自约翰·哈德森:《英国普通法的形成:从诺曼征服到大宪章时期英格兰的法律与社会》,第230页。
(65)Jane Whittle,“ Individualism and the Family-Land Bond:A Reassessment of land Transfer Patterns among the English Peasantry C.1275-1580,” Past and Present,no.160(Aug.1998),pp.25-63.
(66)G.C.Homans,English Villagers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New York:Russell & Russell,1960,pp.197-198.
(67)A.Macfarlane,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The Family,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Oxford:Blackwell,1978,Chapters 2 and 5.
(68)Theodore F.T.Plucknett,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956,p.529.
(69)Jane Whittle,“Individualism and the Family-Land Bond:A Reassessment of Land Transfer Patterns among the English Peasantry C.1275-1580.”
(70)R.J.Faith,“Peasant Families and Inheritance Customs in Medieval England,” The Agriculture History Review,vol.14,no.2,1966,pp.77-95.
(71)Jane Whittle,“ Individualism and the Family-Land Bond:A Reassessment of Land Transfer Patterns among the English Peasantry C.1275-1580.”
(72)R.M.Smith,ed.,Land,Kinship and Life-Cyc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185; P.R.Schofield,Peasant and Community in Medieval England,1200-1500,pp.66-67.
(73)A.Macfarlane,The Origins of English Individualism:The Family,Property and Social Transition,pp.125-126.
(74)C.Dyer,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The Estates of the Bishopric of Worcester,680-1540,pp.302-303.
(75)Jane Whittle,The Development of Agrarian Capitalism:Land and Labour in Norfolk,1440-1580,p.120.
(76)Christopher Dyer,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Oxford:Clarendon Press,2005,p.47.
(77)Christopher Dyer,An Age of Transi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in England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p.121.
(78)Harry Rothwell,English Historical Documents,1189-1327,vol.Ⅲ,London:Routledge,1981,p.336.
(79)Ernest F.Henderson,Select Historical Documents of the Middle Ages,London:George Bell,1912,pp.149-150.
(80)P.D.A.Harvy,ed.,The Peasant Land Market in Medieval England,p.344.
(81)R.M.Smith,ed.,Land,Kinship and Life-Cycle,p.20.
(82)M.M.Postan,Essays on Medieval Agriculture and General Problems of the Medieval Econom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p.123.
(83)M.M.Postan,The Medieval Economy and Society:An Economic History of Britain in the Middle Ages,Harmondsworth:Penguin,1981,p.162.
(84)E.A.Kosminsky,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212.
(85)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p.90-91.
(86)F.Pollock,The Land Laws,pp.81-82.
(87)R.H.Tawney,The Agrarian Problem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p.81.
(88)Christopher Dyer,Lords and Peasants in a Changing Society:The Estates of the Bishopric of Worcester,680-1540,p.301.
(89)P.D.A.Harvy,ed.,The Peasant Land Market in Medieval England,pp.216-217.
(90)K.E.Digby,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Law of Real Property:With Original Authorities,p.356.
(91)C.Clay,Economic Expansion and Social Change:England 1500-17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p.87.
(92)E.A.Kosminsky,Studies in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p.80.
(93)M.M.波斯坦主编:《剑桥欧洲经济史》第1卷,郎立华等译,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621页。
(94)Mavis E.Mate,“The East Sussex Land Market and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in the Late Middle Ages,”Past and Present,no.139 (May 1993),pp.46-65.
(95)P.D.A.Harvy,ed.,The Peasant Land Market in Medieval England,pp.205,210-211.
(96)J.Thirsk,ed.,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IV,p.684.
标签:法律论文; 土地产权论文; 中世纪论文; 欧洲历史论文; 西欧中世纪论文; 欧洲王室论文; 庄园经济论文; 罗马法论文; 领主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