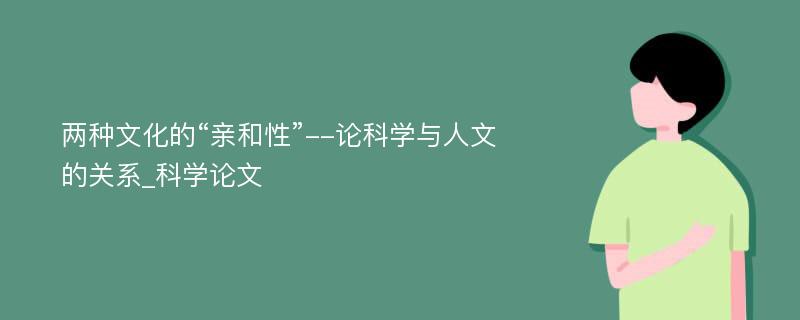
两种文化的“亲和”——罗蒂论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亲和论文,人文论文,关系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与人文的关系,是人类文化的一个恒久问题,不少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留下自己的观点学说。作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罗蒂也不例外,他以消解科学与人文二元对立的思想来告别传统的观点,主张以“亲和”(Coordination,又译作“协和”)的精神和态度来对待人类的文化现象,尤其是看待科学和科学以外(尤指人文)文化现象的关系,由此而形成了他独具特点的“科学-人文亲和观”。
1
在《哲学和自然之镜》中,罗蒂归结了传统观点中对科学与人文之间二元对立的看法。他指出,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将自然科学(如物理学)看作是“客观”的,而将其他的学科(如政治、诗歌等)看作是非客观的,并将后者统称为“精神科学”或“软性”学科(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人文学科”,罗蒂基本上是用“精神科学”来称谓“人文文化”的),且认为有一套只适合后者的特殊方法;这种观点还认为前者是一种“发现”的活动(即“发现自然已经创造了的东西”),而后者是另一种不同的“创造”活动(即创造自然还没有创造出来的东西); 前者所需要的是“说明”(explanation ), 后者则以“理解”(understanding)为前提; 前者可以进行精确的预测(因为“作为自在存在的非人的存在物,并不从内部改变自己,而只是被人们用更好的词汇加以描述、预测和说明”)后者则不能进行这样的预测;前者中可找到可以公度的概念之网,因而可以找到统一的语言,后者则产生不了可公度的概念之网,语词不能相对于一个共同的表达层次来规定(因为作为“人文”对象的“人是自我规定的动物。他的自我规定改变了,人是什么也随之变了,于是对其理解所根据的语词也必定不同了”。);并且还认为认识论适合于前者,而解释学适合于后者。(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99-309页。)。
在作了上述的归结后,罗蒂统称这种观点为“精神-自然二分法”,它根基于自柏拉图以来的观点,即人们都这样那样地坚持要在实在与现象,或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作出区分,即总是习惯于将事实与价值,主观与客观等等分别开来,也就是在科学的东西和科学以外的东西之间制造对立。
在罗蒂看来,传统的在硬事实与软价值、在真理与娱乐、在客观性与主观性之间的区别,是非常棘手、麻烦的工具,绝不能用它们来划分文化,即划分出所谓的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因为“它们造成的困难比其解决的还多”。例如,“人们提出客观与主观的区别,旨在同事实与价值的区别相应,因此客观价值听起来就象有翼的马那样极其神秘。”(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P76。)因此,“认为某些真理是‘客观的’而其他的真理则是完全‘主观的’或‘相对的’看法,即想把真实的划分成‘真实的知识’和‘纯粹的意见’,或划分出‘事实的’和‘判断的’企图,同样是错误的。”(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P79。) 思想家的任务就是要摆脱这种二元对立,摆脱由这种二元对立构成的理智和文化生活形式。
2
为什么人们会形成科学与人文二元对立的看法呢?在罗蒂看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长期以来人们形成的“科学至上”的传统观点。在这种传统的观念中,科学和真理基本上是等价的,正因为这样科学才获得了崇高的地位,格外地受到了人们的尊重,而其它文化现象,尤其是精神科学的东西则没有这样的属性,于是在地位上就自然形成了二元的对立。
罗蒂注意到,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用法中,“科学”、“合理性”、“客观性”和“真理”这样一些概念都是“搅在一起”的。由于人们总是把“理性”、“真理”、“有条理的”、“合理的”、“科学的”和“客观的”看作是同义词,所以他们“总是把追求‘客观真理’与‘运用理性’相等同,因而把自然科学看作是‘合理性’的典范”,“科学被看作是在提供‘硬的’,‘客观的’真理”。(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P75。) 这种看法在人们的头脑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人们判断一切文化形式或成果是否“正确”、是否称得上是“真理”,都必须看其是否是“科学的”。所以,“自从启蒙时代以来,特别是自从康德以来,自然科学一直被看作知识的一个范型,文化的其它领域必须依照这个范型加以衡量”。(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83页。) 科学的这种地位也是和现代知识发展中的“非人格化”相关的,即追求一种弃除了“主观性”的知识,于是“由于宇宙已被非人格化,美(而且最后还有道德的善)开始被看作是‘主观的东西’。因此真理被看作是人类可以对某些非人类的东西负责的唯一立足点”。(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P75。)
罗蒂认为,把科学和真理这样等同起来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一个结果是,任何想在这里占有一席之位但又不能提供自然科学所能提供的预见和技术的学科,必须或者装作模仿科学,或者找到某种无须发现事实便能达到“认知状态”的方法。而把什么都装扮成科学,会造成十分恶劣的后果,一是会形成所谓的“科学崇拜”,致使科学被当作“文化之王”;再就是人文学科“休想有资格成为合理活动。”(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P77。)尽管有的人文学者竭力用“行为科学”或“价值”这样的词来使自己和“科学的”东西靠近,但“社会总是……把人文学科看作是与艺术一致的,认为它们所提供的是娱乐而不是管理。可以肯定的是,这两者都被看作是在提供‘高级’而不是‘低级’的娱乐。但一种升级的精神的娱乐距离对真理的把握还很遥远”。(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P76。)既然如此, 科学与精神(人文)学科之间似乎就横亘着不可跨越的沟壑。
罗蒂认为,其实这是对科学的误解,科学并没有这样的特点,因此,绝不能将科学视为真理的同义语,科学对真理没有垄断权,人类文化的其它形式同样可以把握真理,“根据我们的观点,‘真理’是个单义词。它可以同等地运用于律师、人类学家、物理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判家的判断。”(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P80。)
由于科学并不与(客观的)真理必然地联系着,更何况所谓“客观的真理”与“主观的认识”之间并不存在有二元的对立(这一点在后面还要具体介绍),所以科学并不存在比其他学科更优越、更神圣的地位,它和其他知识部门或文化领域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应该把文化的一切都放在同一个认识论的水平上,并使社会科学家和人文主义者不再认为有某个值得追求的、叫做“科学状态”的东西。从方法上来看也是如此,科学方法并不能作为一切方法论的基础,因此不能认为科学家有一个其余的人都应该好好模仿的“方法”,也不能认为他们有一种得益于他们学科的、与其它学科之不可取的软性正好相反的、值得期望的硬性。
罗蒂认为,在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形成了理想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所假定的是存在有某种被称作“理性”中心的人的机能,这种机能的发展是人类存在的要义——而且自然科学表明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更善于使用这种机能,甚至“一荣俱荣”,只要在自然科学上领先了,似乎在文化的一切方面都优越了,这就是后现代主义经常批评的由“科学中心主义”而导致的“欧洲中心主义”,即这样一种西方观念:西方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领先地位表明了它具有优越的“合理性”,所以它才被抬到了近乎神化的地位,而这在认识论上就是根源于如同海德格尔和杜威所说的那种“希腊人的智慧追求”:这种智慧的意义是,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知识系统可一劳永逸地为道德和政治思考设定条件。罗蒂和他们一样视这种追求为“人类一大错误”,而今天已经到了纠正这一错误的时候了,这种纠正的活动甚至构成了当今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主题,即西方人必须意识到科学、理性和西方并不是文化的中心,对于自然科学的这种神化作用,是当代西方哲学逐渐在使自己摆脱的若干观念之一。在这一点上,罗蒂十分赞同海德格尔和杜威的“信念”:“西方文化今日需要以其先前使自身非神学化的同样方式来使自身非科学化。”(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序》,见该书序言部分第13页。)
将科学作为一切知识基础的传统观点,还表现在语言观上,力图寻求一种统一的语言,即假定存有一种人人可说的任何事情的“单一语言”,而其他的语言都可以向这种统一科学的单一语言“转译”。罗蒂对此指出“按照纯事实而非按照形而上学的需要,不存在‘统一科学的语言’这类东西。我们不具有一种将被用作一切有效说明假设的永久中性模式的语言”,如果设定有这样的语言,它就会堵塞我们的研究之路,“我们可能永远需要改变我们用以进行说明的语言”。所以“我们不应假定迄今为止所使用的词汇将对任何出现的其它事情有效”。(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4—305页。)
要摈弃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还要破除对于科学家的神话,用罗蒂的话来说,就是不应把科学家视为新的牧师。
由于在现代社会科学所拥有的地位,使科学家相对于别的知识阶层有了更高的地位,甚至科学家现在被看作是使人类与某种超人类的东西保持联系的人……科学家成了道德的模范,因为他无私地使自己反复面对坚硬的事实。于是,科学家似乎成了一种新的牧师。
罗蒂指出,科学家经常被视为某些道德品性的典范,如容忍、尊敬别人的意见,相信说服而不是压服等等。人们甚至可以看到,在英国,被选进皇家学会的人比选进下院的人更诚实、可信和公道;在美国,国家科学院明显地不像众议院那么腐败。但是,这并不是由其学科的性质决定了科学家必然会具有这些高尚的道德品性,“这只是历史的巧合,正如在今天的俄国和波兰,诗人和小说家之所以是某些其他道德德性的样板也是历史的巧合一样”(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P73。)。因此,想把自然科学家当成一种新的牧师,当作人与非人之间的连接点,肯定是错的。因为我们没有理由称赞科学家比其他人更“客观”或“逻辑性强”或“有条理”或“献身于真理”,他认为这并不是要驳斥和贬低自然科学家,而只是不要把他们看作牧师。
不仅科学家没有这种特殊的地位,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种特殊的地位,从事不同文化领域的人之间应该是地位上平等的关系,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学科存在的理由,“我们不应问科学家、政治家、诗人或哲学家是否高人一等……我们应当把科学看作适用于某些目的,把政治、诗歌和哲学(不被看作一门超级学科,而是看作根据过去的知识对目前思想倾向的一种明达的批评活动)都看作是各有目的。我们应当摈弃西方特有的那种将万物万事归结为第一原理或在人类活动中寻求一种自然等级秩序的诱惑”(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序》,见该书序言部分第15页。)。
在排除了把科学家当作牧师之后的新文化中,尽管可能还存在着“英雄崇拜”,但这不是对因与不朽者接近而与其他人相区别的、作为神祗之子的英雄崇拜。这只是对那些非常善于做各种不同的事情的、特别出众的男女的羡慕。这样的人不是那些知道一个(大写的)奥秘的人,已经达到了(大写的)真理的人,而不过是善于成为人的人。
3
人文学科或精神学科的地位长期以来之所以没有自然科学那么高,还在于人们对“合理性”的看法的狭隘限制。罗蒂分析道,人们通常认为“合理也就是有条理,就是说,拥有事先制定的标准”,“我们认为诗人和画家在其作品中使用的是‘理性’以外的官能……但科学家,由于事先知道什么是对他的假设的否证……而且,我们似乎有一个清楚的科学理论成功的标准,即其预见并因而使我们能够控制某部分世界的能力。如果成为合理就是能够事先制定标准,那么自然科学作为合理性的典范是有道理的”。(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P77。)
罗蒂十分不满用这样界定的“合理”来否定人文学科的“合理性”,于是,他竭力给合理性赋予另一种含意,来使人文学科这样的人类知识部门成为合理的活动,在这种意义上,这个词指的是某种“清醒的”、“合情理的”的东西。它指的是一系列的道德性:容忍、尊重别人的观点、乐于倾听、依赖于说服而不是压服……在“合理性”的这样一种意义上,这个词与其说是指“有条理”不如说是指“有教养”。在作了这样的解释后,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区分与艺术同科学之间的差别就没有什么特别关系了。根据这种解释,成为合理也就是指,在讨论任何问题,不管是宗教的、文学的还是科学的问题时,都要避免教条主义、自卫心理和义愤。
在这种合理性的关照下,科学与非科学的二元对立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据,以前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非科学”的人文学科也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看作是“理性学科”了,“如果没有了知识与意见之间的传统区别,即在作为与实在的符合的真理与作为对得到很好证明的信念之称赞的真理之间的区别,我们可能会更好些”。(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P81。 )传统视野中的一系列区别和对立也就消失了。“如果所有这些都发生了,那么‘科学’一词,从而还有在人文学科、艺术和科学之间的对立,就逐渐地消退了。”(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P93。) “在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传统区分,也就不如以往那样显得坚实可信了。”(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中文本作者序》,见该书序言部分第16页。)即使还有科学与其他知识领域的区别,这种区别也是无关紧要的了,例如,“如果我们说社会学或文学批评‘不是科学’,我们只是指,社会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在重要的工作上,在需要加以贯彻的工作上,所能达到的一致的数量比(譬如)微生物学家所能达到的要少”(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P86。)。
这样,科学就要与其他文化形式相“亲和”,用“亲和”的眼光看待自身和他物,比如“把客观性归结为亲和性”,(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P82。 )又比如科学和科学家将依赖的,是同其专业的其余方面的亲和感,而不是把自己描述成为在理性之光指引下冲破幻觉屏障的形象。
在陈述了这一系列视科学与人文为对立现象,尤其是泰勒对其进行的“两分法”划界的观点之后,罗蒂表达了自己的否定性观点:“但是现代科学(它似乎已经对说明针灸、蝴蝶迁徙等等感到无能为力)可能很快就会像亚里士多德的形质二元论一样捉襟见肘了。泰勒所描述的界限不在人与非人之间,而在研究领域的两个部分之间,在一个部分里,我们对于手边是否有合适的词汇感到毫无把握,而在另一个部分里,则对此感到颇有把握。这的确暂时大致符合精神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符合可能仅只是巧合。从足够长远的观点看,人或许证明比索福克勒斯想象的更少δεlvos(顽固性),而自然的力量或许比现代物理学家所想象的更多的δεlvos”(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6—307页。)。这样,对于传统观点所认为的解释学描述我们对精神的研究,认识论描述我们对自然的研究的看法来说,“我认为最好完全抛弃这种精神-自然二分法”(注: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08页。)。
弃除了把科学作为文化之王或一切知识的基础,是为了达到这样一种文化:“在这里,没有人,或至少没有知识分子会相信,在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个标准可以告诉我们是否与实在相接触,我们什么时候与(大写的)真理相接触。在这个文化中,无论是牧师,还是物理学家,或是诗人,还是政党都不会被认为比别人更‘理性’、更‘科学’,更‘深刻’。没有哪个文化的特定部分被挑出来,作为样板来说明(或特别不能作为样板来说明)文化的其他部分所期望的条件,认为在(例如)好的牧师或好的物理学家遵循的先行的学科内的标准以外,还有他们也同样遵循的其他的‘跨学科’超文化和非历时的标准,那是完全没有意义的”(注:罗蒂:《后哲学文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第14—15。)
4
罗蒂在科学与人文关系上的思想,是和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一致的,或者说是和他的后现代科学观、后现代文化观、后现代哲学观一脉相承的,比如他认为哲学不是为各门学科提供一个最终的判断标准或基础,而是各种声音和见解的对话,其实质是用比喻和反讽对时代的主流思潮加以否定,以发现新的思想方式。因此他和其他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一样,在文化观上持“非中心的”思想,他的“科学与人文亲和观”的主张,就是这种后现代精神的体现。
罗蒂对科学与人文关系的这种看法无疑包含着在当今值得肯定的积极价值,如不能将科学在文化中的地位至高无上化,不能在科学和科学以外的文化形式之间划上不可逾越的鸿沟,或在理性与非理性,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制造不可调和的二元对立,尤其在当今科学与人文不断融通的智力背景下,这样的见解更富有哲学上的启发性。
但是又不能不看到,罗蒂在竭力消解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时,又走到了似乎要完全取消它们之间差别的另一个极端上去。而这种极端,在其他后现代思想家那里也有充分的表现,如科学方法论上“无政府主义”的倡导者费耶阿本德将科学视为“什么都行”,以至于认为科学和非科学(如宗教、迷信等)之间不存在本质的区别;美国“后现代科学中心”主任格里芬则主张那些处理思想的存在的学问,如美学、伦理学等,也属于科学;而在另一位后现代思想家斯温看来,只有当诗人、艺术家、神秘主义者和大自然的热爱者都讲述了宇宙的故事时,才算有了宇宙的故事。而那种与人文知识分别开来的科学,即使是“苍白的真理”也不能提供给我们,它只能使自然“祛魅”;因此,在后现代科学的视野中,玄学、神学、诗人等自然界的“未被公认的立法者”,应该恢复为和科学一样的“公认的立法者”,这样才能使自然返魅;与此相关的科学的返魅,就是要对“科学”的性质进行重新认识,不再把科学看作是超越价值的事业,尤其要改变科学的“狭隘”的视界,把现代科学看作只不过是自然哲学的现代形式的一种选择,“现代科学的价值结果不大,它不配垄断科学这一令人尊敬概念的全部意义”。(注: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页。)这样的科学甚至“既不能给我们以真理, 也不能探求真理”。(注: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只有扩展了科学的含意,才能使人们摆脱机械的、(现代)科学化的、二元论的、家长式的和还原的世界观。这种完全取消科学之相对独立性的作法,实际上步入了取消人类追求(相对意义上的)客观性、精确性、稳定性、统一性的神秘主义深渊。所以后现代科学思想家的很多主张出现了回到中世纪的趋向,比如在中世纪时倾向性的看法是自然的秩序不能被人理解,到了现代思想那里,宇宙则是一个可直观想象和可知的秩序,而到了后现代,从某种程度上由相对论,在很大程度由量子力学引起了对现代思想的质疑,从而使世界的本质变得几乎难以描述,(注: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如此等等。
因此,避免科学与人文的二元对立,并不意味着要人为地贬低科学的地位或不切实际地抬高人文的地位,甚至,即使承认了科学的真理性,并不会必然导致否认人文学科的价值,把科学看作是主要追求“真”,与把人文视为主要追求“善”和“美”,恰恰是使它们各自都获得了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人类追求真善美统一的活动中达到和谐的一致。如果认为承认了一者就得放弃另一者,这才是不能摆脱二元对立思维的表现。
进一步说,否认在科学与人文之间的二元对立观点,绝不意味着要取消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别,科学与人文在学科性质和研究方法上无论如何都是各有不同的,否则就不会出现有的人(不)适合搞科学,有的人(不)适合搞人文的问题,尽管我们在教育中提倡“文理兼容”,在人的素质上提倡“全面发展”,但如果“文”(代表“人文”)和“理”(代表“科学”)就是没有差别的一回事,就不存在什么“兼容”的事情了,正因为有了不同,才有了二者中以一者为主,又要兼备另一者的全面发展式的教育。
所以,我们反对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搞二元对立,但同时也反对抹杀它们之间的一切差别,而主张二者在相互区别的基础上走向互融互渗,走向一种包容多样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