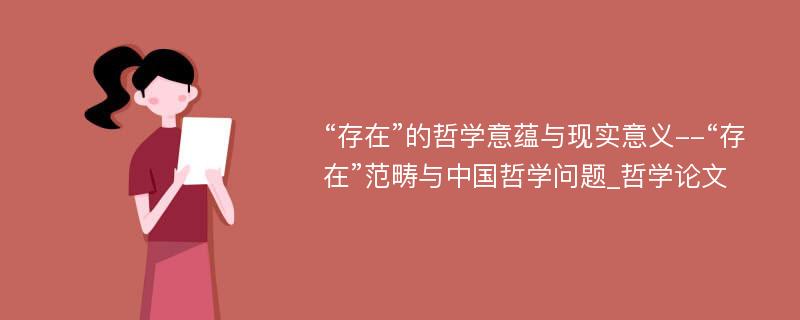
“存在”的哲学蕴含与现实意义(专题讨论)——“存在”范畴与中国哲学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中国论文,范畴论文,现实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存在”是哲学问题,也是哲学范畴,来源于西方哲学,却在中国哲学语境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既有各种关于“存在”之论,也有用“存在”范畴来解释各种思想。如果将“存在”范畴运用于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思想存在,“存在”作为问题具有怎样的意义?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处理“存在”问题的?对于我们当下的哲学思维来说,这仍然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
在西方哲学中,“存在”有两种显现方式:一个是“bing”(Sein),作为系动词在语言中构成各种叙述语句;另一个是“existence”,作为名词在语言中对某物进行表达。前者的意义可以用汉语中的“存在”、“是”、“有”等来表示,后者的意义更接近于实在与实际,可以用汉语中的“实存”来表示。按照西方语言习惯,作为名词的“存在”——“existence”一词本身就可以单独表达某物的存在(时空中的实际存在,简称“实存”),而作为系词的“being”(Sein)本身却无实在意义,必须以主词与宾词连接关系词项才能具有语言意义,但其语言意义只是语法意义,而不具有如主词或宾词那样的实在意义。这里的问题是,系词“being”(Sein)——“是”在语言中具有“存在”的意义,因为它在“是”着,但这种“是”着的“存在”又不具有如叙述语句中的主词和宾词那样的实在意义。那么,这里的系词“being”(Sein)——“是”着的“存在”的意义又如何确定呢?虽然这只是沿着语言词法的推论得出的一个逻辑空场,却蕴含着关于西方哲学的根本问题。我们可以观察如下:西方语言中对于“存在”的把握都离不开“being”(Sein)——“是”,即某物之存在都要由“being”(Sein)再现出来。同时,西方语言中只有一种“是什么”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那个某物的存在作为“什么”必然表现为一个“所是”,这个“所是”就是以“是什么”所表达的那个由“是”而引导出来的“什么”,即“Da Sein”。在这里,关于“存在”的表达要有三个语词,即“是”、“什么”和“是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们要对某物之存在进行表达时,首先就是“是”,其次要作为“什么”,如此就有了某物之存在必然要作为“是什么”而成为“所是”。于是,在西方哲学中就出现了“存在”本身作为“是”,只能以“是什么”的方式去表达,而“是”对自身却不能进行描述的尴尬。如此而言,“是”作为存在只能以“是什么”的“什么”来确定,这就是西方语言之“是什么”的逻辑中所蕴含的不可逾越的悖论情结。可以说,西方哲学是从“being”进入“存在”问题的,并且通过“在”与“在者”的分别来构成形而上学。
从我们的日常经验来看“存在”这个词,一般来讲,是以“看得见”、“摸得着”作为确定是否“存在”的标准的。日常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才是“存在”的。在这种语境中,“存在”只是对于“某种存在者”之“在”的状态的表述。这里的“存在”,往往是作为形容词或副词来使用的,只是说某物是“存在的”。当我们从日常生活经验视域进入“存在者”本身的语境中时,则“存在”一词就以“实在”的身份出现了,即“存在”以“存在者”的身份出现了。这种语境转换的背后隐藏着把“存在”当作“对象”来把握的知识论的思考方式。在这里,“存在”的语法属性是名词,即在使用中,“存在”与“实在物”、“对象”、“物质”在意义上是相近的。当我们超越知识论的对象化的思考把握方式,进入“哲学”的智慧语境中,“存在”的意义就可以表述为“存在”本身了,亦即由对象、“存在者”回归到“存在”本身。这里的“存在”作为表述“存在”本身的词语,仅仅是一种叙述的方便,但其“本身”之意却是超越“表述”的。“存在”一词的这三种语境意义,是我们当下对其使用的基本状态。“存在”一词的这种处境,既保留了西方哲学由“在”与“在者”的分别所衍生出的逻辑分析思维习惯,又蕴含了中国人以实用理性为特征的经验思维。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来看,之所以要确定某种意义的“存在”,就是要确定它是这样或那样的,就是要使人们能够相信它就是这样或那样的。所以,确定“存在”是为了确定人们的“信”,由“信”的确定才可能有“我”,才可能有“我”与“他者”。换言之,如何确定“存在”,就是如何确定“信”。确定“信”,就是确定了如何下手。中国古人的“卦”最初就是起这个作用的。这样,以何为信,如何为信,就区别为不同的为“信”的方式,其背后所蕴含的是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所谓不同的“活法”。如此说来,如何“存在”,“存在”如何,实际上所关涉的是如何“活”的“活法”。
如果将“存在”范畴用于观察中国传统的思想或哲学,从其作为“活法”的意义上来说,“存在”作为问题可以具体化为“活着”,“如何活着”,“如何活下去”等问题。“活”就是存在的本意,就是“生生之化”。在这个“生”中就内含着“活”的问题,由此而衍生出的思想作为哲学的言说与叙述就是中国思想语境的“存在论”。如果从中国传统思想或哲学语境来体会的话,笔者认为,这个“存在”就可以概括为:一曰“道”,二曰“生”。也就是说,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或哲学来说,达(成)“道”而“生生不已”,并以此为“真”,为“诚”,为“存在”,由此而为“信”。具体而言,“存在”的这种意义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道”之为“道”的“存在”。
“道”,是中国思想、文化与学术所独有的,它不是概念范畴,不是言语文字。在中国思想文化中,“道”与“我们”息息相关,是中国人的精神依怙与归宿,也是中国人如何生活与存在的根据。在“道”的思维中,对于“道”不能将其把握为一个可以规范的“什么”,即不能对其说出其“是什么”,但我们可以体会到它对于我们的制约作用。它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道”只是一个对“它”的方便性的比喻,显现为我们所走的道路。在中国思想史上,诸子学之儒、道都讲“道”,可以说,属于中国人的“存在”就在“道”上。从经典文献来看:
《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
“道常无名。”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庄子·达生》:“何为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于人道也,相去远矣。”
《庄子·齐物论》:“道行之而成,物谓之而然”。
《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
《易传·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生生之谓易,成象之为乾,效法之为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为神。”
这些是人们所熟知的古人教言,也是我们所认可的可以为“信”的道理。可以看到,在中国人的思维习惯中,“道”并非独立的存在实体,并非如西方哲学中的“这一个”、“某物”、“存在者”、“共相”、“理念”、“逻各斯”等可以被逻辑或非逻辑规定的那个“什么”。中国人对于这个“道”的把握是形而上的,即不是对这个“道”作出“是什么”的规定,而是以其显现之相作为叙述的对境,即以对“道”作为“相”的描述来把握“道”的存在和意义。道虽不能言及,却无所不在。如何而在?则为“道,行之而成”。
第二,“生生之为易”,“生生不已”作为“存在”。
中国人为何如此宠爱这个“道”呢?这涉及中国思想或哲学的目的与意义问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道作为存在,乃在于“生生”。“生生”之何以乃至如何,为“道”之所然。孔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是以“生”为意义的界限的。“生”就是“活”,“活着”,这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存在”。因为一切都要以“生”为出发点,为目的,所以“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意为不仅要“活”,而且要活下去,还要活得好。如何活下去?须依阴阳之道。《易传》云:“生生之谓易,成象之为乾,效法之为坤,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为神。”在这里,乾、坤、占、事、神都被归结为易之“生生”。也就是说,生命的存在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最高原则。
第三,以“孝悌”为基础的礼制、仁德之天人合一之道的“存在”。
从古人的生存体验来说,可以使中国人能够活着,活下去,并且活出个样来的那个理由和根据,就在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为教”。何以为礼?何以为仁?则在于血缘亲情基础上的“孝悌”。这样,由血缘亲情、孝悌、忠信、天道、人道、礼制、仁德等构成了中国式的德性政治与伦理构架。这一构架在思想文化上的体现就是以“天人合一”之“法自然”为根基,由古天文历法象数所建立起来的适于中国人的“活法”的思想体系。中国传统思想的主轴是以“出世”之心性行“入世”之世(事)道,或以“有为”,或以“无为”行“内圣外王”之纲。此即为中国本土的“极高明而道中庸”之学。这就构成了中国式的以“孝悌”为基础的礼制、仁德之天人合一之道。
如果能够认可“存在”作为问题在中国思想文化中是如上意义,那么,中国人是如何面对、思考、把握、处理如是之“存在”问题的?从思考方式来看,从中国传统思想或哲学中可以选出“中道、不二、中庸、双运、圆融”几个词。可以说,我们就是依“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的方式来思考、把握、实践着自身存在之意义。在儒、释、道的法脉传承中,“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的思维方式得到了持续的坚守,经由文化心理的积淀,遂成为中国人独特的“活法”。具体而言:
“中道”,已成为积淀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传统儒学、道家、佛学都倡导以“中道”为生命智慧的最高境界。将“中道”一词拆开来看,“中”字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释为“中,内也,从口,上下通”。意思是说,与外相对的内,贯通上、下者为“中”。“中”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代表一种古代的旌旗。旌旗飘扬在氏族部落的住地中央,是这个氏族的标志。有了这个旌旗,在其周围就有了生活,就可以“测日影,定时辰”。“日当午则旗影正”,从而引申出“中”字不偏之意[1](P88)。用哲学的术语来说,“中”这个字就是对于人或氏族存在的“命名”。从字形解义来说,“中”所表达的是“上下贯通、连接东西、维系南北、不堕两边”之意。“道”字在《说文解字》中释为:“道,所行道也。”在郭店楚简里,“道”字有两种写法:一种从“夔”从“彳”;一种从“人”从“行”。“夔”是完整的人形,“人”是简化的人形,“彳”与“行”相同,是路口象形。可见,“道”的意义在于“行”,“行”的意义不在于“行”的方式,比如“走”、“跑”、“爬”,而在于“在”“道”上。这个“在”不是一定之规的“直线”之路,而是要由“在者”作出选择的“路口”。“路口”的意义是要依据某种根据、理由作出抉择。古人之所以做任何事情都要进行占卜,并以占卜的“吉凶”为抉择的根据,大概与此有因缘关系。“中”、“道”二字,从字源来看,都与人的如何“在”有关。中国思想文化讲究“太初有道”、“太初有为”、“太初有行(动)”[2](P81),“太初”之道、之为、之行都要在“中”、“道”上才可以“在”。所以,“中道”作为儒家、道家、佛家都崇尚并秉持的生存智慧的最高境界,实际上表达着人之“存在”的如何。
中庸,是儒家所倡导的生命原则。在儒家看来,中庸本于天道,天由命而性,由性而道。也就是说,任何存在都具有合于天道的本性,任何存在率性就在道中,不率性就成为非道了。何以率性而合于天命?慎独也,能够慎独,则为君子。
“不二”,作为思考方式是从体用关系中抽绎出来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不二”具体体现为“体用不二”、“本末不二”的思想。熊十力认为:“以体用不二立宗,本原现象不许离而为二,真实变异不许离而为二,绝对相对不许离而为二,心物不许离而为二,天人不许离而为二。”[3](P169)在这里,体用为宗,具体化为本原与现象、真实与变异、绝对与相对、心与物、天与人,都是不二的。对中国传统思维来说,从二分入手,不二才为究竟。所以,不二作为思考存在问题的方式不是一直“不二”,而是从“二”到“不二”,“不二”是“二”的究竟,是对于“二”的思考与处理方式。
双运与圆融,是佛教的修行法门与修行境界。对于双运,有真俗、止观、智悲、显密、定慧等,在修行中都要秉持双运,由双运才能进入空性境界,亦即圆融无碍、无有分别。在佛教中,圆者周遍之义,融者融通、融和之义。若就分别妄执之见言之,则诸法尽事事差别;若就诸法本具之理性言之,则事理之万法遍为融通无碍,无二无别,犹如水波,谓为圆融。曰烦恼即菩提,曰生死即涅槃,曰众生即本觉,曰娑婆即寂光,皆是圆融之理趣也。佛教中的双运、圆融作为关于生命之存在意义与如何的思维及修行方式,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世俗谛与胜义谛(真俗二界)之究竟及方便的关系。在佛教看来,世俗谛、胜义谛二者可承许为方便与方便生,如《入中论》曰:“由名言谛为方便,胜义谛是方便生。”依靠世俗谛可以证悟胜义谛,从本体而言,其并非方便、方便生之本体;但从相续产生这一角度来讲,通过世俗之显现方可证悟空性之胜义谛。因此,从证悟这一侧面来讲,二者是方便与方便生的关系;从本体而言,则完全是一味一体的。以世俗谛的眼光来看,诸法事事分别,烦恼、生死、众生、娑婆都是显现而无有自性;从胜义谛的视角来看,烦恼即菩提,生死即涅槃,众生即本觉,娑婆即寂光,无有分别,了不可得,不可执着,这才是空性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才可能生起出离心、菩提心、空性智慧,从而解脱和成佛。
可以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于“存在”问题,是以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为思考与把握方式的。何以要如此来思考与把握“存在”问题呢?这可能来自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存在问题体现为无极而太极,进而由阴阳之易而为生生之道,进而为道器、道术、性命、身心等二分又如何为一的问题,从而形成了与其相应的中道、中庸、不二、双运、圆融的思考与把握方式。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所蕴含的中国人的这种“活法”,显然有别于西方哲学所取的“在”与“在者”之分别而依逻辑所建立的形而上的“活法”。从这个作为“活法”的意义上,似乎可以体会到以“存在”范畴来表达中国思想或哲学的味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