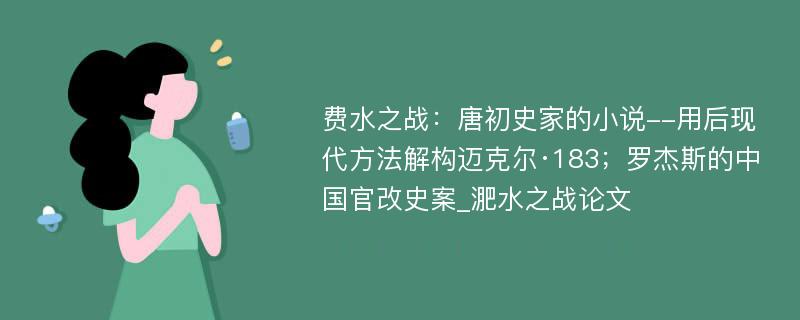
淝水之战:初唐史家们的虚构?——对迈克尔#183;罗杰斯用后现代方法解构中国官修正史个案的解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初唐论文,史家论文,之战论文,个案论文,后现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8;K23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4)01-0077-07
公元383年,东晋谢玄率八万军队在淝水击败前秦苻坚近百万大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淝水之战。东晋以少胜多,不仅使江山得以稳固,而且这场战争被后世史家视为决定中华文明能否生存和延续的关键性战役[1](P530)。然而,美国史学家迈克尔·罗杰斯(Michael C.Rogers)对这场重要的战役表示了怀疑,认为它不过是《晋书》编纂者们的杜撰。他在为《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The Chronicle of Fu Chien:A Case of Exemplar History)[2]所写的长篇序言中,运用十分娴熟的后现代的视角和方法,对于《晋书·苻坚载记》的史料、论史方法、史家的动机,前秦历史中的人物如苻生、苻坚等在隋唐历史中的原型,淝水之战的塑造及其动机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解构。对此,陈世襄(Shi-Hsiang Chen,音译)在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予以褒扬,指出: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可能就越有传奇性。一旦传奇故事得以确立,真实发生的故事就不再为人所注意,传奇就成了真实的历史,它超越了事实,成为历史事件,成了史学史上的历史。而我们理解历史,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只能凭借书写的历史(written history),正是这种书写历史左右着我们的历史研究、影响着我们的历史看法。因此,透视这种历史书写的活动,考察史书的成书过程及其相关的背景,对于我们研究历史相当重要,而《苻坚载记:正史的一个案例》正是这样—个范例[2](P4)。
作为美国加州大学的东亚史教授,罗杰斯的主要成就是对韩国史的研究,出版了数部韩国史著作。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对《晋书·苻坚载记》的研究与翻译。罗杰斯之所以选择《晋书》,是因为《晋书》在中国正史中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首先,它是唯一有皇帝御撰篇章的正史;其次,它又为后世官修正史的运作方式树立了楷模;再次,晋朝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假如不是晋朝抵挡住了前秦的进攻,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同欧洲一样,进入一个完全野蛮化的“黑暗时代”。所以,选取《晋书》作为分析的对象就十分有意义。而以往对《晋书》的评价,只是指陈其记载了许多怪诞不经之事。但罗杰斯指出,《苻坚载记》是《晋书》中一个非常特别的例子,《苻坚载记》所反映的并非苻坚本人及前秦的真实历史,“为了塑造正统性,神话和文学描写也成为基本的手段”[2](P5);进而把《苻坚载记》视同“一个狡猾的狐狸”,非细细分析,不能得其真实。笔者认为,罗杰斯对《苻坚载记》分析之精彩令人赞叹,但其结论之荒谬又使人难以置信。因为他不仅对中国历史开了个大玩笑,而且对中国传统正史的纂修亦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一、唐太宗的模型与初唐历史的折射
罗杰斯的序言,在简单介绍了《晋书》的相关资料来源及前秦的建立与历史概况后,就全力分析《苻坚载记》的几个来源及模式。罗杰斯认为,《苻坚载记》中既有晋朝自编的陷阱,更有隋、唐两朝具体历史的折射,而这些与真正的前秦历史可能毫不相干。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唐太宗的模型与初唐历史的折射。
在对苻坚本人的叙述中,以及苻生与苻坚关系的论述中,罗杰斯认为这实际是初唐史家们对唐太宗的描述。在罗杰斯看来,尽管房玄龄等人是受命编修《晋书》的,可他们并非专职的史官,史学修养值得怀疑。由于他们是朝廷中最为重要的大臣,所以,是否撰述真实的历史并非他们所关心的,而借助修史劝谏却成为他们的用意所在。他们虽对朝中政事了如指掌,但因为君臣的尊卑等级,即便是开明如唐太宗这样的皇帝,他们也并不可能畅所欲言。贞观十七年(643年)正月,魏徵去世后,朝臣之中就再也没有像魏徵这样的直言敢谏之士了。对于唐太宗敢于批评之士日少,而唐太宗骄横之心日盛,《晋书》的纂修恰恰在此之后。所以,《晋书》的编撰者们“把苻坚塑造成为一个特殊的英雄,而且与唐太宗本人的形象有密切的关系”。在《晋书·苻坚载记》中,“他们把七世纪发生的事情精心灌注于前秦的载记之中”[2](P41)。而这种“灌注”,首先体现在苻坚之前苻生时期的历史之中。《苻坚载记》之前篇为《苻洪、苻健、苻生载记》,乃是苻坚兴起之前的前秦几代君主。苻洪是苻坚的祖父,前秦政权的奠基者。苻健和苻雄为苻洪的两个儿子。对于《苻洪、苻健载记》,罗杰斯着重讨论了一些谶纬和神话及其背后的含义;对《苻生载记》,则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苻生是苻健的儿子、苻坚的堂兄,在位仅两年即被苻坚发动政变赶下了台,时年仅二十三。但在《晋书·苻生载记》中,却把苻生写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
(苻生)临朝辄怒,惟行杀戮。动连月昏醉,文奏因之遂寝。纳奸佞之言,赏罚失中。左右或言陛下圣明宰世,天下惟歌太平。生曰:“媚于我也。”引而斩之。或言陛下刑罚微过,曰:“汝谤我也。”亦斩之。所幸妻妾小有忤旨,便杀之,流其尸于渭水。又遣宫人与男子裸交于殿前。生剥牛羊驴马,活爓鸡豚鹅,三五十为群,放之殿中。或剥死囚面皮,令其歌舞,引群臣观之,以为嬉乐。宗室、勋旧、亲戚、忠良杀害略尽,王公在位者悉以疾告归。人心危骇,道路以目。既自有目疾,其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至于截胫、刳胎、拉胁、锯颈者动有千数[3](P2879)。
苻生在位不过两年,所干坏事却无数;凡天下暴君的罪行皆归诸苻生,虽桀、纣之残暴亦不过如此。难怪刘知幾在《史通·曲笔》中慨叹“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
在极力诋毁苻生的同时,对苻坚则备加赞誉。《苻坚载记》中首先神化苻坚的出生,说他出生时“有神光自天烛其庭”,其祖父“洪奇而爱之”。与其兄苻法发动政变、弑苻生以后,苻法为帝,但苻坚又弑其兄苻法而自立。编撰者叙述这件事时,却抬出其母亲:“初,坚母以法长而贤,又得众心,惧终为变,至此,遣杀之。坚性仁友,与法诀于东堂,恸哭呕血,赠以本官。”[3](P2885)这似乎显示苻坚极为“仁友”,但是极不合情理,因为苻法下台时如果苻坚真的“仁友”,为何非得置之于死地呢?随后,极力称颂苻坚政治清明,“于是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祇,课农桑,立学校,鳏寡孤独高年不自存者,赐谷帛有差,其殊才异行、孝友忠义、德业可称者,令在所以闻”[3](P2885),与苻生的暴君形象形成鲜明对照。
罗杰斯认为:诋毁苻生,并非仅仅是树立一个简单的暴君典型,而是有着深刻而内在的反讽意味。真正的历史只是片断的,因为“苻生的名字,在唐朝以前,一直是被谴责的对象”,所以房玄龄等在修《晋书》的时候就借机嵌入他们的虚构。而称颂苻坚,也是有史家们的政治目的的。在罗杰斯看来,房玄龄们是把苻生等同于李建成和李元吉,而把苻坚比附李世民。因为苻坚取代苻生的政变,如同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的玄武门之变;苻生与苻坚的关系,和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关系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史书记载,苻坚曾经毁国史,唐太宗也曾改写历史,由于唐太宗称帝后对史书的改写,使得唐初的历史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在罗杰斯看来,《苻坚载记》丑化苻生、神化苻坚,实际上是唐太宗丑化李建成、李元吉而神化自己的一种现实的折射:唐初的历史在唐太宗继位后,几乎全部改写,而苻坚亦曾改写历史。《苻坚载记》曰:“初,坚母少寡,将军李威有辟阳之宠,史官载之。至是(按:公元381年),坚收起居注及著作所录而观之,见其事,惭怒,乃焚其书而大检史官,将加其罪。著作郎赵泉、车敬等已死,乃止。”[3](P2904)史官被杀,史书亦被改写,苻生残暴形象岂不是苻坚故意塑造出来的?而唐太宗对于“玄武门之变”中弑兄灭弟、逼父退位等一系列行为也十分忌讳,所以对于史官之记载也极其留心,从而大改史书。对于起居注“善恶毕书”的原则,唐太宗是有所忌讳的。无论如何,玄武门之变总是唐太宗一块心病,所以他要想方设法看看实录。贞观十四年(640年),唐太宗向房玄龄索看《高祖、太宗实录》,当看到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语多微文”时,就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须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4](P223-224)起居注和实录,君主原本是不能看的,这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是唐太宗竟然打破了这条戒律,私自向大臣们索看实录;并且对于史臣们的记载非常不满,指令按照自己的想法修改,史臣无法直书其事。唐太宗索看唐高祖、唐太宗实录的事情,发生在《晋书》编修六年前,是唐太宗直接对房玄龄说的;对于玄武门之变,唐太宗则将其视为周公诛管、蔡,史臣们就只能以此原则来叙述,历史的真相就此湮没,以后的《新唐书》、《旧唐书》就如此载录玄武门之变。一场原本是李世民兄弟间争夺皇位的宫廷斗争,因为李世民本人的干预及其继位后当然的正统性,真相就此模糊了。李世民摇身一变,也就成为正义的化身了。唐太宗破坏了官修制度中的史官保护制度,“是则由追求实证定论历史的正史意义,已隐然偏向钦定历史的方向发展”[5](P491)。但由于魏晋以来史学中强烈的“以史制君”的传统,使得实录和《晋书》的编撰者们(实际上是房玄龄他们数人)对这种转变强烈不满,于是就只得采用曲笔来叙述历史(注:对于魏晋以来史学中“以史制君”的传统,雷家骥有详尽的论述,参见《中古史学观念史》[5]第七、八章。)。
在罗杰斯看来,公元643年,房玄龄呈上实录,唐高祖实录被全部改写;此事发生不久,唐太宗又任命房玄龄等人编修《晋书》,因为唐太宗的做法与苻坚的做法类似,而作为朝臣的房玄龄等人又不敢违背唐太宗的命令,于是,只得借修《晋书》的时机来实施他们的计划。所以,把苻生写得尤其残暴,而把苻坚又写得几同圣人。实际上,这并非苻坚的真实面目,而是对唐朝现实的一种反讽。罗杰斯认为,房玄龄等这样做,其实是一箭双雕的:“他既发泄了对皇帝的不满与怨气,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作为史家的失败,因为作为史家有种信念,即档案的真实应是神圣不可违背的。同时,他设下了一系列符号,以暗示后人应该对唐太宗时期的官修史书及英雄人物采取怀疑的态度。”[2](P44)
以这种分析为基础,罗杰斯进而又把苻坚的重臣汉人王猛视为唐初士人的代表;王猛与前秦诸豪族的斗争视为唐初士人对当时世袭家族的一种挑战。苻坚倚重王猛之际,遭到其部族贵族的反对,苻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强化王猛的权力。在罗杰斯看来,这些并非真实的历史,而是因为唐初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是唐初士人与世族间矛盾的一种反映,“《载记》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前秦的任何事情,我们也不能随意猜测。他所告诉我们的是,在他生活的时代(唐初)所看到的一些类似的问题”[2](P45)。而在公元380年,苻坚颁赐了一系列领地,把他家族的成员及亲戚安排到帝国内最重要的市镇中去,作为他南下攻打东晋前准备的一部分。罗杰斯以为,这实际上是唐朝在公元637年唐太宗给家族二十一位成员赐以封地的历史的反映,所以这也是唐朝初年历史的一个事例。因此,在罗杰斯看来,对初唐历史的折射,成为《苻坚载记》的真实意图之一。
二、神话、谶纬与想像
在罗杰斯看来,《苻坚载记》通篇都贯穿着神话与想像,而正统观念则一开始就决定苻坚出征东晋失败的命运。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罗杰斯解构《苻坚载记》的重要手段。确实,《苻坚载记》中有许多的神话故事,亦有许多的谶纬传说,给历史人物增加了几多神秘色彩,也给历史的进程增添了一种宿命感。
罗杰斯分析了几个神话模式。他先选取了一个地名——曲沃,一个官名——龙骧将军,这两个名词暗示着苻坚的命运及前秦帝国的兴衰。作为象征之一的曲沃,是苻坚命运变化的一个符号。罗杰斯由苻坚时期的曲沃联想到春秋时期的曲沃,当时是晋国太子申生的领地。由此,罗杰斯将申生与苻坚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是初唐史家们的有意安排。申生是苻坚的影子,申生的命运也暗示着苻坚的命运。春秋时期,晋献公宠爱骊姬,而骊姬生子奚齐,遂设计陷害太子申生。先是将献公诸子从献公身边支开,“使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献公与骊姬子奚齐居绛。晋国以此知太子不立也”[6](《晋世家》)。然后,骊姬又劝申生祭祀其生母齐姜,申生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上其荐胙于晋献公。晋献公当时正出猎在外,于是,就置胙于宫中,而骊姬使人将毒药放入胙中。等到晋献公回来要吃的时候,骊姬则从旁止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6](《晋世家》),于是借机诬告太子申生要害晋献公。申生知道这件事后,出奔新城,后来就自杀于新城。与申生巧合的是,苻坚也是兴起于曲沃而死于新城。《苻坚载记》云:“(苻)健……梦天神遣使者朱衣赤冠,命拜坚为龙骧将军,健翌日为坛于曲沃以授之。”[3](P2884)在曲沃被授予龙骧将军,是苻坚走向历史舞台的开始。而龙骧将军又被罗杰斯看成是另一个象征,因为苻坚的祖父苻洪最初也是被授予龙骧将军,苻坚得此官职,意味着他当得皇位大统。以后,他就日益得势,最终登上皇帝宝座。但是,在他出征东晋前,却将龙骧将军的称号授予鲜卑将领姚苌。史云:“及苻坚寇晋,以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谓苌曰:‘朕本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假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坚左将军窦冲进曰:‘王者无戏言,此将不祥之征也,惟陛下察之。’”[3](P2965)罗杰斯认为,在出征之前将龙骧将军授予姚苌,预示着前秦帝国江山不久;而崩溃之后,当是姚苌继承其天下。淝水之战后,苻坚大部分军队都被消灭,惟有姚苌统领的鲜卑军队得以保存。最终,姚苌的军队围攻苻坚于五将山,并执苻坚于新平,缢之于佛寺,果然取代了前秦苻坚的政权。《苻坚载记》曰:在苻坚强盛之时,有童谣云:“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3](P2929)后果然应之。
在罗杰斯看来,龙骧将军,这是苻健封给苻坚的一个官称,预示着苻坚将接掌政权,并有可能统一全国。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龙骧将军最初是西晋武帝赐封给王濬(206-286)的官称,而王濬在公元280年率军灭吴,使得西晋统一天下。而苻坚得以继承此号,预示着他将南征,以实现他统一全国的雄心。但是,在他发动战争的前两年,却把龙骧将军的称号授给了姚苌,这成为他致命的错误,暗示着他南征的失败[2](P35)。罗杰斯认为,“申生(曲沃)表示着苻坚的性格,而王濬(龙骧将军)则显示着他的雄心”[2](P36),曲沃与龙骧将军正是初唐史家们所设下的象征符号,预示着苻坚的兴衰。
三、淝水之战:事实与想像的结果
对于决定苻坚前秦帝国命运的淝水之战,罗杰斯把它看成是初唐史家们借用一个小小的事实,加上隋朝征讨高句丽战争的失败教训和一些虚构,无限的扩大而编造出来的,其用意在于反对唐太宗征讨高句丽的战争。罗杰斯把苻坚帝国的兴盛看成是唐初太宗时期历史的反映,而淝水之战及苻坚的败亡又视为隋炀帝的影子。由于隋炀帝征高丽的失败,初唐史家把隋炀帝作为苻坚的又一个原型进行塑造。虽然唐太宗是隋朝灭亡的亲身经历者,但是对于隋征高句丽所带来的恶果并不认同房玄龄等史臣的解释。所以,他依然把征高句丽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为了谏阻唐太宗的征伐,史臣们又塑造了一个模式。
罗杰斯对比了公元612年隋炀帝征高句丽战争中失败的萨水之战与公元383年苻坚南征的淝水之战的有关史料,认为《隋书·宇文述传》和《晋书·谢玄传》记载的这两次战争在细节上有着惊人的相似:第一,两次战争发生的地点都在一条大河边:隋炀帝的军队与高句丽在萨水边,而前秦与东晋则在淝水边。第二,一支先头部队从营地出发,急行军以阻止敌军退缩,企图一举消灭敌方。宇文述将大军丢在辽河边,自己率军孤军深入高句丽境内;而苻坚也只是自将先锋部队,追击东晋军队于淝水边。第三,侵略军自愿接受并实施敌军将领的建议。隋军宇文述接受高句丽将领乙支文德的诈降,苻坚接受东晋将领要其稍退以使东晋军队能够渡河的建议。第四,侵略者在河流的面前受到阻击,但是在一条支流边上就失去了一位重要将领。第五,只有少部分军队逃回,留下大批物资。萨水之战,隋军半渡之际,高句丽军队发动攻击,隋军将领辛世雄被杀,在30万渡过辽河的隋军中,只有2700人活着回来了;而淝水之战前秦百万军队亦丧于一旦,只有几千人逃回。第六,隋朝征高句丽失败不久,就被推翻,前秦在淝水之战以后也迅速垮台。正因为有这样多的相似之处,罗杰斯断定两次战争几乎是一个翻版,并认为这两次战争并非独自能够成立,而是互相依存的。因为《隋书》与《晋书》都是由同一批史家编修的,但罗杰斯把两次战争相似的原因猜测是臧荣绪的《晋书》或是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先影响了《隋书》的编撰,进而影响了《晋书》的编撰[2](P49)。
尽管淝水之战与萨水之战的相似性令罗杰斯产生了怀疑,但他认为有两点是毋庸置疑的:其一,公元383年,晋朝军队在寿春确实抗击过来自北方前秦的军队,但入侵者只是在寿春逗留了数天就被赶回了淮北。也就是说,淝水之战的真实战争,只是公元383年刘牢之的军队与前秦军队在寿春附近发生过一次战争。刘牢之的传记中对这次战争有所叙述,但只是一次规模并不大、影响也不大的战斗。其二,此后不久,前秦帝国就陷于分崩离析之中[2](P62)。但是,晋朝的正统论者对于这个简单的事情并不满意,于是,南朝的史家就无限的扩大这件事,并把刘牢之的战绩说成是谢氏家族的功绩,因为刘牢之以后反晋,而谢氏家族则一直牢牢地控制着东晋的政权。几经渲染,以致成为一个神话。所以,罗杰斯认为淝水之战是事实与想像的结合,模糊不清的事实与神话结合在一起,令人难以分辨。对于朱序这个角色,罗杰斯也加以怀疑,认为朱序是东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他原本是东晋将领,在襄阳被苻坚俘获而降秦。开战前,又作为苻坚的使节到了东晋,却把前秦的虚实全都告诉了东晋将领谢石,使得东晋将领最终采纳他的建议。在苻坚接受建议往后稍退之时,朱序又在阵中大喊“苻坚败矣”,致使前秦军队自乱其阵。在罗杰斯看来,这本身就值得怀疑,很可能是个虚构的角色。八公山的草木皆兵,亦是典型的杜撰。至于战争发生的地点和时间,罗杰斯都提出了质疑。因为不同的史书有不同的记载。在发生地点上,《晋书·谢玄传》说是在淝水之南,而有的史书却说是在淝水之北。在发生的时间上,《晋书》说是十一月三十日(己亥),是个“猪”日,而苻坚属猪的;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拒绝用此日子,只用一个平常的日子。罗杰斯认为这种自相矛盾的记载,更证明了淝水之战是虚构的论断[2](P64-65)。
在罗杰斯看来,淝水之战就是以公元383年刘牢之的战争为原型,再加上隋朝征高句丽失败的萨水之战而人为塑造出来的。在这里面,晋朝的正统性也扮演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因为无论是晋朝人还是唐朝人都认为,东晋有着无可置疑的正统性,而谢安就是维护这种正统性的代表人物。这种正统性,在《苻坚载记》中一开始就揭示了出来:王猛生前告知苻坚,不可轻易进攻东晋,因为东晋是正统所归,一旦进攻,必定失败。唐朝修《晋史》,亦有追溯其本朝正统渊源的意图,肯定东晋的正统性,也就是强化唐朝的正统性。罗杰斯认为,塑造淝水之战东晋的胜利,是中国文化的胜利,它满足了史家们心智上的需求,也证明了中华文化对“胡族”的优越。
总之,罗杰斯认为,《苻坚载记》运用虚构、想像、比附等手法,将唐太宗时期的历史折射到前秦中去,叙述苻生与苻坚的历史,是为了比附李建成与李世民的关系,用曲笔来展现唐初的真实历史概貌。而淝水之战的神化,不过是借用了公元383年刘牢之与前秦的一次战争,加上隋朝征讨高句丽失败的萨水之战的情节,刻意编造出来的,意在谏阻唐太宗东征高句丽的战争行动。而塑造东晋的胜利,是肯定东晋的正统性,也是为了满足初唐史家们心理上的需求。
四、对罗杰斯解构的分析与质疑
迈克尔·罗杰斯运用后现代的分析方法对《苻坚载记》的解构,其根本的思想就是要否定这些并非前秦的真实历史,而是初唐史家们借前秦苻坚的名义来表达他们的某些思想和意图。所以,罗杰斯多次强调,这些与前秦的真实历史无关,只是初唐史家们所建构的一种模式、一种文本。这印证了后现代主义大师德里达的一句话:“文本之外空无一物。”可见,即便是中国古代的正史,如果用后现代的方法去解构,一切也将变得支离破碎。用传统的理性的观点去看,他的解构非常荒诞,也许很难用“对、错”这样的标准来评判。因为,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原本就没有什么对错的标准。
罗杰斯对《苻坚载记》的解构,印证了詹京斯(Keith Jenkins)对历史的一项说明:“历史可说是一种语言的虚构物,一种叙事散文体的论述。依怀特所言,其内容为杜撰的与发现到的参半,并由具有当下观念和意识形态立场之工作者(亦即历史学和行止宛如历史学家的那些人),在各种反观性的层次上操作所建构出来的。”[7](P12)即历史是建构出来的,所以无所谓客观性问题。罗杰斯把《苻坚载记》说成是初唐史家们曲折地反映他们的现实关怀,也可以说是对这段话作了注脚。尽管看似荒诞,但并非一无长处。
罗杰斯透过历史的表象去分析背后的根源和深层的原因,可谓思路深邃。因为唐朝官修史书,原本就有许多问题,《晋书》的问题就更多。尤其是曲笔问题,在当时即受到史家刘知幾的批评。刘知幾曰:“自梁、陈已降,隋、周而往者,史皆贞观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伪可求。至如朝廷贵臣,必父祖有传;考其行事,皆子孙所为,而访彼流俗,询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实。昔秦人不死,验苻生之厚诬;蜀老犹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则自古所叹,岂独于今哉!”可知刘知幾对于唐修诸史、尤其对于《晋书》中苻生之“厚诬”是颇为不平的,故又曰:“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词获罪……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8](《曲笔》),而《苻坚载记》正是曲笔的典型。
而对于修《晋书》,唐太宗与史官们的确各自有着不同的目的,台湾学者雷家骥亦有类似的论述。他说,贞观二十年(646年)修《晋书》,君臣之间总是借修史来满足他们各自的目的。是年三月,唐太宗征高句丽还,六月又诏李世勣率军征漠北薛延陀,并亲往督师。铁勒诸部内附,上唐太宗以“天可汗”尊号,唐太宗甚为高兴。于是,就企图借修史来进一步强化唐朝及其自身的功业。原修五史,就是为了强化唐朝的正统性。而此时更要上溯到晋朝,“为本朝政权塑造更完美光明的理论根据”。更强调将唐朝发生的事情与晋朝类似者对比,以便寻得经验教训,“贞观君臣特富以史经世观念,他们重修《晋书》,与探究晋代兴亡之真相有关。尤其留意当时发生之事件与晋朝相类似者,俾更能从晋史中了解此类经验之得失,亦为其重要动机和目的之一”[5](P624)。可见,对于《晋书》编撰之原因,雷家骥之论述与罗杰斯有相通之处,他们都看到了君臣修《晋书》的背后根源,只是罗杰斯更多的是探讨史臣们借修《晋书》之际表达他们“以史制君”的观念,无论是丑化苻生、溢美苻坚,还是肆意塑造淝水之战的宏大场面,都蕴涵着史臣们进谏的心态。当然,更为重要的区别是,罗杰斯否认这些是前秦真实历史的记载,这和雷家骥对《晋书》的评价有着本质的不同。
综观罗杰斯对《苻坚载记》的分析,其实有几处致命的弱点。
其一,史料上的问题。虽然罗杰斯文中讨论了崔鸿的《十六国春秋》对《晋书》的影响,但是并没有系统地探寻《晋书》的史料来源,难道初唐史家们杜撰历史,真的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吗?在唐修《晋书》时,尚有十八家《晋史》存世。诸家《晋史》中,以纪传体而言,有王隐《晋书》、虞预《晋书》、谢沉《晋书》(未成而卒)、谢灵运《晋书》(未成被杀)、朱凤《晋书》、何法盛《晋中兴书》;编年体者,则有干宝《晋纪》、徐广《晋纪》、孙盛《魏氏春秋》与《晋阳秋》、习凿齿《汉晋春秋》、曹嘉之《晋纪》、邓粲《晋纪》、王韶之《晋纪》、刘谦之《晋纪》、张瑶《后汉纪》,等等。唐修《晋书》,正是综采诸家之说,一以贯之,编成一书。史料来源既广,而编修者亦众,有二十三人之多[9](P53)。具体的负责篇章,明代史家王世贞论曰:“其事例属敬播,《天文》、《律历》属李淳风,《掌故》属于志宁,纪、传属颜师古、孔颖达辈,而宣、武二纪,陆机、王羲之传,天子称制以叙论之,最称彬彬详雅矣。”[10](P2201-2203)。所以,唐修《晋书》是以诸家晋史为基础的,史家们只能是以这些资料为来源,编删排比而成的。罗杰斯只说是房玄龄等史家的虚构与想像,而未及讨论作为房玄龄《晋书》资料史家们的情况,显然其分析与解构是有极大的局限性的。且是书由众人分工合作编成,《苻坚载记》到底出自何人之手,并不清楚,但作为监掌其事的房玄龄等人并非《苻坚载记》的亲撰者,罗杰斯一味地指陈其反映了房玄龄和褚遂良等大臣的想法,这本身就于理不合。况且,尽管苻坚曾毁国史,但是唐初还是有前秦的资料流传。刘知幾言:“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著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始。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起,至二十八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记》十一篇。”[8](《古今正史》)《隋书·经籍志》则曰:“《秦纪》十一卷,宋殿中将军裴景仁撰,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11](P963)可见,裴景仁《秦纪》当是《苻坚载记》直接的原始材料之一。而罗杰斯却无一言涉及此书。
其二,选择对象的问题。晋朝有十余位皇帝,为何不选择晋朝皇帝作为唐太宗的影射对象,而单单选取前秦的苻坚呢?《晋书》有一百三十二卷,有纪十、志二十、列传七十、载记三十,并序例、目录,《苻坚载记》只是《晋书》的一部分。如果说初唐史家们要反映唐太宗时期的历史,为何不选择其他篇章,而单单选中《苻坚载记》呢?是全书都是初唐史家们的杜撰,还是只有《苻坚载记》?罗杰斯并没有对这些问题给予解释。罗杰斯的分析中,肯定了唐修《晋书》正统性的问题,对于唐朝借修《晋书》以强化本朝的正统性也表示赞同。但是苻坚是“胡族”氐人,不具正统性。如果说房玄龄们选取不具正统性的苻坚作为唐太宗的化身,难道房玄龄们对于他们君主的正统性也表示怀疑吗?这于情理不合,本身就自相矛盾。
其三,谶纬与想像的问题。《晋书》确有杂采而轻信之失,它所采用的史料多传闻、掌故之书。但是,魏晋时期多谶纬之言,魏晋时期是谶纬学兴盛的时期,无论君臣儒士皆信之。不仅当时一般的书籍中有很多这样的记述,如《世说新语》、《语林》、《幽明录》、《搜神记》皆有许多类似的故事,就连所谓十八家晋书,亦有许多类似的记载,故而《晋书》中有许多传闻之事也就不足为奇了。但《苻坚载记》中的谶纬与童谣一类传闻之事,却被罗杰斯看成是初唐史家们的想像与暗码符号。唐修《晋书》原本只是沿袭了以前诸史的特点,如果把这些看成是初唐史家们的想像,未免过于牵强。罗杰斯特别将曲沃与龙骧将军看成是决定苻坚命运的两个符号,这实际上是罗杰斯个人的想像。他于曲沃联想到春秋时期的申生,只是因为他们都曾在曲沃这个地方生活过,而死的地方又都是新城(其实,苻坚是被害于新平)。如果说在同一个地方生活过的历史人物冥冥之中都有联系的话,那么,在曲沃生活的历史人物,又何止一个申生?为何别的人物对苻坚没有影响和暗示,却单单是申生呢?至于龙骧将军,只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个官职,就是苻坚同时代的人中,东晋朝中担任过这一职位的人就有朱序、檀玄、刘牢之、胡彬等人,而罗杰斯把苻坚将龙骧将军授予姚苌看成是前秦帝国将亡的先兆,未免又是一个无稽之谈!显然这些都是罗杰斯的臆测,不足为据的。
其四,淝水之战的模式问题。正如前面提到的,淝水之战被罗杰斯看成是事实与想像结合的产物,是把一个原本很不起眼儿的战斗,加上隋炀帝征高句丽失败的萨水之战的情节而塑造成的一个关键性的战役。他分析了萨水之战与淝水之战在细节上的相似之处,认为两个战役是相互依存的。目的是借苻坚和隋炀帝失败的教训劝谏唐太宗,不要再进行征讨高句丽的战争。贞观年间,《隋书》是先修成的,《晋书》较之为晚,所以,初唐史家是先塑造了萨水之战的模式,然后再在此基础上构筑了淝水之战。但是,在谈到初唐史家如何构筑萨水之战时,罗杰斯却说是受到了臧荣绪《晋书》或崔鸿《十六国春秋》的影响,也就是说,先是臧荣绪和崔鸿所记载的淝水之战的情节影响了萨水之战的构筑,然后《隋书》中的萨水之战情节又反过来影响《苻坚载记》中淝水之战的模式。无论怎么说这都十分牵强。唐修《隋书》,当时隋朝的许多档案文书都保存完好,初唐史家们不用这些材料,却要用臧荣绪《晋书》和《十六国春秋》去构筑这个模式,岂不怪哉!又则,既然臧荣绪和崔鸿的书影响了萨水之战的构筑,那么不正说明以臧荣绪《晋书》和崔鸿《十六国春秋》修成的《晋书·苻坚载记》是真实可信的吗?那淝水之战的细节还有何值得怀疑的呢?
其五,对初唐史家们塑造这个模式理由的质疑。在解释房玄龄、褚遂良为何要塑造苻坚和淝水之战这一范例时,罗杰斯举出以下几个理由:一是房玄龄们并非职业的历史学家,而是唐太宗的重臣。二是在他们看来,道德与伦理的真实比历史的真实更重要,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可以随意塑造历史。三是唐太宗这个非汉族背景的皇帝,具有无限的野心和好战情绪,所以,为了阻止唐太宗的肆意征战,不管什么手段,只要房玄龄们觉得有用,就可随意采用。四是前秦作为一个已较为久远的少数民族政权,留存的资料已相当少,因此,房玄龄们能借用一些道德遗产、政治智慧来编造这样一个范例[2](P70-71)。罗杰斯所举出的四个理由,说到底,就是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房玄龄们塑造了这样一个模式。具体而言,资料问题,前面已经讨论过,就此略过。如果说是为了谏阻唐太宗的征战,用得着如此委婉和隐晦吗?房玄龄们直接上疏,不是更直接更有效吗?而把唐太宗说成是非汉族,则是常识上的错误,唐太宗是有些他族的血统关系,但这绝不能否定他的汉族身份。尽管房玄龄们不是职业史学家,但他们对于史家起码的职业道德还是非常清楚的;尽管他们修史有现实的关怀,但这一点也绝不构成他们去虚构历史的理由。所以,尽管罗杰斯对《苻坚载记》解构的思路令人耳目一新,但其结论是荒诞而无法立足的。
[收稿日期]2003-11-06
